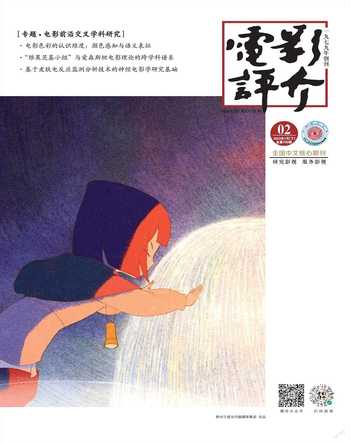电影色彩的认识维度:颜色感知与语义表征
2023-06-06王宜文史之辰
王宜文 史之辰
色彩是电影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认知科学与电影学跨学科联动的逐步深入,有关电影色彩及其叙事功能的理解与认知得到了丰富和拓展。借助人脑视神经系统对颜色的识别和感知原理,本文试图以认知主义的理论视角审视和考察电影色彩的叙事功能与特征。
一、电影色彩的技术沿革与心理驱动
电影早已全面进入彩色时代。由黑白向彩色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造成了一个既定观念,即从前的“老”电影是黑白的,而如今的“新”电影是彩色的。但从电影技术的发展史,特别是观众的心理欲求层面看,严格意义上的“黑白”与“彩色”之分界并不存在。而且在彩色电影成为电影制作标准后,仍有很多电影使用黑白影像进行创作,如《曼哈顿》(1979)、《愤怒的公牛》(1980)、《辛德勒的名单》(1993)、《白丝带》(2009)、《艺术家》(2011)等。
在电影诞生最初的几十年里,彩色正如今天的黑白影像一样,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对胶片进行着色是较为通行的做法。电影制作者会将夜晚的外景着色为深紫色或蓝色,既模拟夜间的光影,也在视觉上将其与白天和室内场景进行区分。彩色电影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英国布莱顿学派先驱乔治·史密斯(George Albert Smith)于1906年发明的双色电影制片工艺(Kinemacolor)。①此工艺通过红色和绿色滤镜投影胶片,尽可能贴近被摄物的实际颜色。较之需要多人手工作业的胶片着色法,双色工艺将电影色彩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其不足之处则在于无法准确地展现出所有颜色,过亮、褪色或无法显现的问题时有发生,特别是双色工艺制片的影片必须安装与之对应的播放设备,导致播映成本大幅升高。因而,尽管双色电影在英国本土观众中很受欢迎,但双色工艺技术始终无法得到真正的普遍采用。
大约在1915年,特艺公司(TECHNICOLOR,Inc.)②开发出了自己的双色工艺,即利用滤镜和棱镜的组合使放映出的电影具有色彩。随后,该公司继续研发颜色处理技术,将颜色直接印在胶片上。1925年的《歌剧魅影》就曾使用这一技术加入了几段彩色场景。1932年,特艺公司再次推出了一种利用染料转印技术的三色胶片拍摄技术③,将彩色电影技术推向了一个高峰。尽管呈现出的效果极佳,但制作三色胶片电影的前提却是更高的拍摄难度和成本,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前,只有好莱坞的大型制片厂才有能力选择这种拍摄方式,其著名的影片有《罗宾汉历险记》(1938)、《乱世佳人》(1939)、《绿野仙踪》(1939)等。
20世纪50年代后,彩色电影发展得更为迅猛。一方面,技术的演进使彩色影片逐渐具备商业上的可行性;另一方面,电视的出现导致电影受到巨大的冲击。因此,电影只有提供区别于电视的新奇体验,才能使观众走出客厅,重回影院。由于当时的电视只能放映黑白影像,因此大力发展色彩便成为电影抵抗电视冲击的首要应对策略。在此后的创作实践与艺术探索中,色彩成为电影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起着复现現实的功能,而且承担了重要的表意与主题性作用。
除了技术的革新和商业的探索外,关于色彩进入影像的讨论也伴随其间。早期,彩色电影曾经遭受过不少质疑,例如德国电影理论家爱因汉姆(Rudolf Arnheim)认为,较之可以更自由、随性地使用色彩的艺术类型,电影只是机械性地记录了物理现实中的光值,颜色并不能发挥真正创造性的作用。[1]英国电影理论家欧内斯特·林格伦(Ernest Lindgren)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电影色彩不太可能像声音那样带来技术上的根本创新,色彩在拍摄前已经“存在”,而拍摄只不过是一种机械性的捕捉和反射而已。[2]这类观点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流,一些理论家们认为色彩的加入虽然会加强影像还原现实的能力,但也会扰乱观众的视觉系统,以无关紧要的视觉信息干扰观众本应投注于人物和情节上的注意力。
这些质疑最终都未能阻碍彩色电影的发展,观众对电影复现现实的需求本身就已足够支撑彩色电影到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对视觉效果的不断探索,电影制作者们逐渐发现颜色并不像理论家们预设的那样刻板,观众对颜色的感知也并非是一成不变,不同的文化语言背景及个体生理差异,导致不同的人群对颜色的认识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色彩除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属性之外,也是一种主观化的、多样化的感受,具有语义上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赋予创作者更大的艺术发挥空间,色彩因此而成为重要的叙事要素和创造力得到彰显的重要手段。
二、黑白影像的独特叙事效应
当下,数字制作已逐渐取代了胶片摄影,彩色成为电影影像的主流,曾经被认为是电影标准形式的黑白影像正在逐步消失。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反倒使黑白影像逐渐发展为特殊的艺术手段,影片对黑白影像的调用,也引发了对此类影像认知问题的探讨。
美国电影学者惠勒·狄克森(Wheeler Dixon)在其专著《黑白电影:一段简史》(Black and White Cinema:A Short History)中对黑白影像进行了系统性的学术梳理。[3]狄克森认为,主流影像的环境和现实生活本身都是彩色的,因此当电影人拍摄一部黑白电影时,就有一种内在的风格化和对现实的重新诠释,从而导致一种完全不同的影像风格模式。黑白影像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正在“迅速从当下的世界滑落到过去迷雾中”的世界。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黑白影像逐渐具备唤起过去时态、记忆语境与历史感的功能。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2015)以一段长达6分钟的黑白影像开片,就戏剧功能而言,这段黑白影像以过去时态交代了全片的前提背景:聂隐娘跟随师父学习剑术,学成之后师父命令聂隐娘下山完成刺杀任务,而刺杀的对象正是她青梅竹马的表哥。开片与正片部分的彩色影像形成了时间区隔,有“前史”之感,也使观众能够更准确地理解此后人物的一系列行为及其动机。主题内容大致相同的两部电影——1989年的《开国大典》和2009年的《建国大业》,创作年代虽然相隔20年,叙事角度、风格均有所变化,但在毛泽东登临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段落中都选择了真实的黑白影像,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而言,黑白画面带出的历史厚重感符合人们最普遍的心理期望。
从物理学和视觉认知的角度看,人类视觉对物体的基本认知主要是靠辉度(luminance)对比而不是色彩对比来完成的。①这意味着较之形状、线条等属性,色彩虽然可以通过强化特定特征来帮助识别、记忆和检索物体,但却并不会根本性地影响人对物体的感知与把握。对于人脑的判断和识别而言,物体的颜色往往是一种非必要的附加信息。在此前提下,黑白影像的优势也便凸显出来。在多数认知情况下,黑白影像抹去了纷繁错杂的色彩信息,在不影响观众对空间和物体理解的同时排除了视觉上的干扰,促使信息更为单纯和集中。
科恩兄弟于2001年创作的影片《缺席的人》,是一部以黑白影像呈现的电影,获得第74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影片是以彩色胶片拍摄而成的,但在剪辑时,科恩兄弟与摄影师罗杰·迪金斯(Roger Deakins)发现,出现在背景处的蓝色建筑与穿着粉红色衣裙的行人等颜色信息,无意间成了干扰性的视觉赘余。因此,他们将彩色影像处理为黑白,以使影片传达出的信息和主题更加纯粹。[4]在这种去色彩的处理中,影像也产生了某种特殊质感,例如男主人公艾迪在多丽丝自尽后独自步行回家,在抽离掉背景中纷繁的色彩之后,艾迪成为画面的绝对主体,而他人不过是匆匆过客。当艾迪回到家中跌坐在沙发上时,艾迪和他人及周遭均保持着一层疏离感。正如其独白所说:“我坐在屋里,但屋里空无一人,我是一个幽魂,看不到任何人,任何人也看不到我。”色彩的隐去加深了人物的孤独,观众从影像上获得的信息有限,反而可以更专注于艾迪与环境的关系之中,并逐渐进入影片试图传达的“人的存在”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
另一方面,黑白影像并不是黑色与白色的简单并置,而是一种单色摄影及其附属的所有光影关系。在黑白的影像系统内,涵盖了介于黑色和白色之间的所有层次,银色、米色、灰色等颜色均居于其中,构成了事实上更为复杂的光影和色调谱系。因此,黑白在简化色彩的同时还保持有其特殊的艺术和想象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提供给被试者未着色的黑白线形图案,要求被试者依据自己的想象给出这一图案应被填充的颜色;随后,研究者根据被试者汇报的颜色为这一图案着色,并将其混入其他颜色的同类图案中,要求被试者进行图形识别。实验结果显示,比起其他随意填涂的颜色,被试者可以更快速和准确地识别出以其想象中的颜色进行填充的图形。[5]这即说明较之给定的颜色,人们根据黑白画面自行想象的色彩反而是最契合其认知的。因此,尽管黑白影像并未提供确切的颜色信息,但并未阻碍观众对色彩的主观想象和延伸。
三、电影色彩的认知与表征
黑白影像逐渐向特殊的表意形式过渡,主要是由于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下,彩色已是最主流的电影制作与观看模式,这种转折体现出的是观众对色彩接受习惯的深度转变。然而,无论是黑白电影时代中彩色作为特定形式,抑或彩色时代下黑白作为去色彩化的特殊形式,关于电影色彩最重要的前提性問题始终是作为接受者的观众对色彩信息的加工和认知机制。
人对颜色信息的认知加工分为早期的视觉加工和更深层次的语义分类两个阶段。视觉加工阶段也即颜色知觉阶段,指对颜色的色调、亮度和色度等三个物理特征的知觉。[6]在初级加工之后,大脑会对接收到的颜色视觉信息进行更为复杂的语义判断,在此阶段,个体认知、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参与进来。初级视觉加工涉及到的主要活动是对颜色的感知,语义加工阶段则涉及到对颜色的认知。感知是指将现实世界中的物体或事件映射到大脑中,而认知则是对感知到的物体或事件进行语义和言语分类的高阶意识活动。
目前,对语言神经基础的研究已经表明,颜色的感知、分类和语义加工活动可能涉及不同的神经结构。感知颜色的三个基本属性(色调、色彩和亮度)的概念依赖于一个神经系统,认识和表达颜色的词汇依赖于另一个神经系统,而理解颜色词汇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则依赖于第三个神经系统。[7]在大脑感知到颜色信息后,具体是如何建立起颜色和心理意象之间的关系,目前还很难依靠实验技术手段进行研究,但一些相关的实验已经证实记忆和语言文化是影响人认知颜色的重要因素。在一项典型的颜色记忆匹配实验中,被试者被要求观察并记住他们所看到的颜色,随后经过一段时间间隔,他们被要求从几种给定的颜色中选出之前所看到的那个颜色。结果显示;被试者的选择和他们最初看到的颜色之间产生了显著的差别。[8]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被试普遍倾向于对看到的颜色进行分类,然后只记住大类别例如“绿色”而忽略了该颜色的其他属性,如亮度、饱和度等。与此同时,被试者潜意识里的个体记忆会融入进来,并将所看到的颜色与记忆中的物体或场景进行联系,如绿色对等于草地的颜色。这一系列过程后,被试者对颜色的选择往往就是一个经过了多个认知环节的综合结果,而不再是实验当中所看到并获得的准确的颜色信息。
语言对颜色认知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研究的热门方向,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向母语为俄语的被试者和母语为英语的被试者展示了三个一组以品字形呈现的蓝色色块,三个色块的区别是彼此间的深浅不同,接着被试者被要求指出处于下方的两个蓝色色块的颜色哪一个更接近于上方的蓝色色块。实验结果显示,母语为俄语的被试者做出判断的速度要明显快于母语为英语的被试者。研究者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英语中蓝色被统称为一个单词blue,而在俄语中对蓝色没有统一的指称,但是会使用两个单词来区分亮蓝色和暗蓝色,这一语言习惯使母语为俄语的被试者做出判断时会更加容易。[9]尽管目前的研究尚未厘清颜色认知在大脑中完整的运作机制,但已有研究充分显示不同族群和个体之间对颜色的认知并不固定,而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对电影色彩的考查也应适度跳出主观化的阐释,而进入到一种认知的过程与视角之中。
(一)色彩的视觉加工与感知
早在牛顿利用三棱镜发现了光的色散现象之后,人们就开始意识到色彩也许并不是物体的固有属性。在此后的研究中,色彩的神秘面纱被揭开:颜色本质上是人类视觉神经系统对光的一种感知。[10]尽管颜色不是物质的本质属性,但它在人的认知判断过程中还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在目前的研究中,颜色被认为是一种关于场景的,额外的、详细的信息,应有助于图像的识别。在日本的一项研究中,通过给物体增加颜色属性,并与没有色彩的物体本身形成对照来考查在两种情况下,被试者即时的识别结果以及过后的回忆反馈,以此分析颜色是否具有辅助认识和增强印象的功能。最终实验得出结论:颜色在信息编码和检索方面确实是有效的,但是这种作用在即时识别中并不明显,且仅当颜色在编码和检索过程中都存在时颜色才有效。[11]这也就是说,当颜色对应编码于物体之中时,能辅助人们区分不同的内容并且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洛夫特斯(Geoffrey Loftus)的团队所做的关于人对图像识别的实验则进一步证明了颜色的积极作用。实验的材料是三组图片:第一组图片是60张以自然场景为主的照片;第二组图片是第一组照片中场景的简化,研究者将照片中的主要景物以线条形式勾勒出来,绘制成60张线条图;第三组图片是在第二组的基础上进行着色,将照片中原有的色彩涂绘在线条图上。被试者分为三组:第一组观看照片、第二组观看线条图,第三组观看着色图;接着实验者会随机展示一些图形,这些图形有些曾出现在原有的实验材料中,还有些是新加入的干扰图形,被试者需要依次判断看到的图形是否曾出现在之前观看的图片中。研究结果显示,观看线条图和着色图的被试者,识别正确率均低于观看照片的被试者。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照片含有的信息量太多,而线条图和着色图则不同程度地削弱、遮蔽了原照片中的颜色信息,从而降低了被试者对物体识别与判断的准确率。[12]上述实验共同说明:颜色与人对物体的识别、感知以及判断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人眼视网膜包含了数以百万计的感光细胞,其中每个感光细胞都含有光敏感分子,也称为感光色素。感光细胞又分为两种类型,即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其中视锥细胞是颜色视觉的基础。不同视锥细胞的感光色素对不同波长可见光的敏感性不同,这些不同的视锥细胞感知到各自对应的颜色后,经过视神经将信息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形成人脑对颜色的感知。神经美学之父萨米尔·泽基(Semir Zeki)在其研究中,使用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技术考查了被试者观看颜色时视觉脑区的活跃情况,最终发现了相对位置靠前的V4区①涉及颜色信息加工时有明显的活跃。[13]泽基的研究证明了在大脑视觉加工系统内部存在主要负责颜色信息加工的区域。
在考查电影中的色彩运用时,首先应关注人类视觉系统最基本、初级的生理反应。张艺谋的《红高粱》(1988)对色彩的使用算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即使用强烈的、富有冲击力的色彩直击观众的视神经。在这部电影中,红色作为主色调贯穿始终,并且在红色背景之中,持续叠加不同层次的红色物品:花轿、服装、盖头、红色的高粱地和高粱酒,以至最后牺牲场景中生命迸发出的极致的“红境”(红色滤镜片营造出的意境),呈递出一种强烈且不可抵挡的色彩冲击感。大片绿色的高粱地,在以上红色对比色的映衬下,呈现出强烈的分离感,平衡了视觉效果,加强了色彩对比,进而突出了主体颜色的位置,更衬托出《红高粱》中一抹抹大红色彩的直观感受。
在所有可见光中,红色光的波长最长,折射角最小,在视网膜上的成像位置也最深,所以红色光会给人带来最强烈的压迫感和扩张感。这种客观物理特性和人类既有的感知构造,决定了红色一直是最有力量的颜色。诚然,并非粗犷地使用颜色造成视觉冲击就能够获得一部颜色表意出众的佳作,电影色彩的使用并非是简单的堆砌,而应营造出色彩的对比和运动。同样是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却在视觉色彩的选择上饱受诟病,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便是充斥画面的金黄色造成了所谓的“重复劣势效应”②,即一个刺激信号反复出现时,并不一定能令人更快速地捕捉到它,反而可能由于该刺激重复多次导致人们形成惯性认识,而无法及时做出反应。2009年的一项实验说明这种基于颜色的重复劣势效应确实容易出现,研究者通过要求被试者对颜色进行辨别反应后发现,大量的注意资源分配在颜色信息上,可能促进了选择性注意机制对色彩信息的加工,进而导致色彩信息返回被抑制,出現基于色彩的重复劣势效应。[14]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几位主要人物均身穿金黄色服饰,而兵丁甲士也全部身着黄金战袍组成方阵,千篇一律的金黄色图景重复出现在画面的相似位置,而且没有任何区分度,再加上缺乏对应的补色进行衬托,导致观众无法准确地观察到画面的核心信息。即使在面对场景切换时,也难以及时地感知到图像的差异性,对影片的内容也就未做出积极的反应。同时,黄色又是相对比较醒目的颜色,刺激性较强容易造成视觉疲劳,二者叠加,势必导致观众的观感较差。
(二)色彩的语义表征
现实生活中的事物通常都具有色彩,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色彩之中。在电影中,色彩也通常被视为还原和表现现实的基本叙事元素。林德格伦和爱因汉姆等理论家都曾经认为公众对彩色电影的需求反映了人们对现实叙事的普遍偏好,彩色胶片的发明将使电影呈现出更真实的影像风格,色彩是电影史上更逼近现实表达的重要一步。①
但是,色彩在电影中的逼真还原性只是其基础功用。如前所述,色彩认知包含了物理、认知和文化成分,它既是生理现象,也是文化事件,因此色彩认知往往也被看作是感觉刺激和非感觉刺激的相互作用。
来自于认知和文化上的差异性决定着色彩的语义表征是多重可变的,如红色既代表激情,也可暗示血、生命或爱。在中国,红色可能代表喜庆,在世界的另一些地区则象征危险和邪恶。电影中色彩可以作为叙事手段的原因,色彩的类别数量是固定的,但其表意却丰富多元,它们不能被用来赋予程式化的意义,而必须在叙事的语境中,并与观众的文化身份和经验相联系来解读。颜色和其所代表的语义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多元随意的,这一现象在电影中意义重大,同样的颜色可能很容易引起较大的反应。电影中色彩的“意义”必须总是处于一个特定背景之下,色彩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感知,而这种感知本身取决于许多变量。由于所有这些变量,包括文化、经验和期望都会在我们个人对颜色的反应中起作用,因此颜色具备丰富的意义指向空间。
在复现现实之外,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往往是通过结构、渲染、变化使观众从强烈的视觉刺激或超常规的体验中感受到超出影像内容本身的内涵。首先,最为简单的处理是以具体直观的色彩形象代表特定的意象,如《战舰波将金号》(1925)中敖德萨阶梯段落升起的红旗,尽管彼时电影的染色技术还过于粗糙,旗帜的染色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导演爱森斯坦选择让这面红旗在银幕上“红”起来,用色彩传达了意识形态功能,体现了色彩的象征作用。“在银幕世界的造型空间里,形的作用偏重于理性,而色彩的作用则更倾向于人类的情感和本能,它擅于在银幕空间中传达与揭示人的情绪、心理和精神信息,使银幕形象更加丰厚、立体、生动和富有生命质感,它具有使人的内心世界外化的作用,使抽象的概念转换成可视的形象语言。”[15]王家卫的《花样年华》(2000)利用电影色彩表现了人物心理和情绪上的不同转变。男女主人公会面的环境色彩是黯淡灰白的,表达了被压抑、被束缚的情感,女主人公旗袍颜色的变化使人物精神内里得到了外化:当她与男主人公约会时穿上了红色的旗袍,昭示出内心的激动与雀跃;而当二人分离,她守在电话前默默无言时,旗袍的颜色则是象征忧郁与悲伤的蓝色。观众无法直视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但电影却用色彩将其具化显现了出来。
电影色彩的使用中,最特殊的形式是不可预测地使用颜色,或者将不恰当的颜色设置在“错误”的地方,以形成特殊的表意。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1964)用非写实的色彩来表现自然,主题上是为了反映日益增长的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对环境的破坏,影像认知上则是为了唤起观众的注意力,以促使其做出越来越复杂的反应。安东尼奥尼在影像上加入了明显的人工色彩,通过使用滤光片和为特定物体如水果等涂色,唤起了一个创造性建构和想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本身通过拍摄而改变,从而成为一种人工制品,一种性质被扭转的自然。在此,色彩不仅仅简单地演绎影像,更成为一个独立和开放的象征载体,根据时空语境和每个观众的创造性反应而改变其意义。
结语
色彩是电影视听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定的色彩调用,既可以協助影片完成主题表意,也可以参与奠定创作者的美学风格,进而影响观众的情感和心理进程。但另一方面,来自于认知主义的研究及其理论则不断昭示着,色彩首先是一种作用于视觉系统的信息,在经由脑神经与网络的加工处理后进入更高级的语义加工层面。从这个角度而言,理解和掌握人对色彩信息的接受和处理方式至关重要。北京师范大学神经电影学研究团队以fMRI为技术手段重测了“库里肖夫实验”,分别以黑白和彩色两种条件拍摄了模仿历史上库里肖夫实验中的素材(演员面无表情的面孔以及愉悦、中性、恐怖三种场景),随后招募等量的被试者分别观看黑白和彩色条件下的库里肖夫实验剪辑素材。实验研究发现,尽管两种条件下的观众主观行为上均表现出受库里肖夫效应影响(他们认为演员面孔表现出的情绪与后续所接的场景相一致),但是当演员面孔连接的是愉悦场景时,观看彩色视频的被试者要比观看黑白视频的被试者而言,更多地认为演员表现出了愉悦的情绪;而当演员面孔连接的是恐怖场景时,两种条件下的被试者表现得无差异。也就是说,相较于彩色,黑白颜色似乎抑制了观众对愉悦情绪的感知判断,但是fMRI数据并没有显示出在二者的大脑接受上有什么不同,这说明影响观众做出主观行为上不同判断的,并不是颜色的初级接受方式有所不同,而是语义加工时大脑对黑白和彩色的认知处理不同。这也为后续的电影色彩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挖掘的方向。
本文试图从认知的层面对电影色彩进行梳理和研究,突出色彩自身的视效特性及更深层次的语义表征,通过对电影色彩认知原理的探究,可以更科学地阐释一些电影的创作现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电影色彩的使用。
当下,电影技术的发展已为电影的制作与播映增加了许多新手段,“广色域”“高动态范围”等新技术的实现,意味着观众已不再满足于当下的观影习惯,而开始期待影像可以呈现更加宽广的色彩区域和光线明暗范围。这必将会不断丰富电影色彩的含义并提升色彩的价值,也为电影色彩的认知主义研究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简介】 王宜文,男,山东日照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电影史论、影像认知研究;
史之辰,男,内蒙古赤峰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影视史论、影像认知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神经电影学理论模型建构及电影认知的脑成像实证研究”(编号:16YTA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认知神经科学理论背景下电影视听元素结合效果研究”(编号:19BC04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Rudolf Arnheim.Film as Art[M].London:Faber and Faber,1958:150.
[2]Ernest Lindgren.The Art of Film[M].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Limited,1948:205.
[3]Wheeler Wiston Dixon.Black and White Cinema:A Short History[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5:2.
[4]The Coen Brothers interview about The Man Who Wasn't There[EB/OL].(2011-07-21)[2022-12-1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27F1iWTt0.
[5]Watkins,M. J.,& Schiano,D. J.Chromatic imaging:an effect of mental coloring on recognition memory[ J ].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982:291-299.
[6]Derefeldt G,Swartling T,Berggrund U,et al.Cognitive color[ J ].Color Research & Application,2010(01):7-19.
[7]Damasio A R,Damasio H.Brain and language[ J ].Scientific American,1992(03):63-71.
[8]Macdonald L,Luo R.Colour Image Science:Exploiting Digital Media[ J ].2002:75.
[9]Winawer J,Witthoft N,Frank M C,et al.Russian blues reveal effects of language on color discrimination[ J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7:104.
[10]Waldman G.Introduction to light: the physics of light[ J ].vision and color,1983:193.
[11]Suzuki K,Takahashi R.Effectiveness of color in picture recognition memory[ J ].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2010(01):25-32.
[12]Loftus G R,Bell S M.Two types of information in picture memory[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 Memory,1975(02):103-113.
[13]Michael S.Gazzaniga,Richard B.Ivry,Geroge R.Mangun.Cognitive Neuroscience:The Biology of the Mind[M].W.W.Norton & Company,2019:153.
[14]焦江丽,王勇慧,边国栋.认知控制对基于位置和颜色返回抑制的影响[ 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09(01):44-49.
[15]宫林,周登富.电影色彩的意义[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02):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