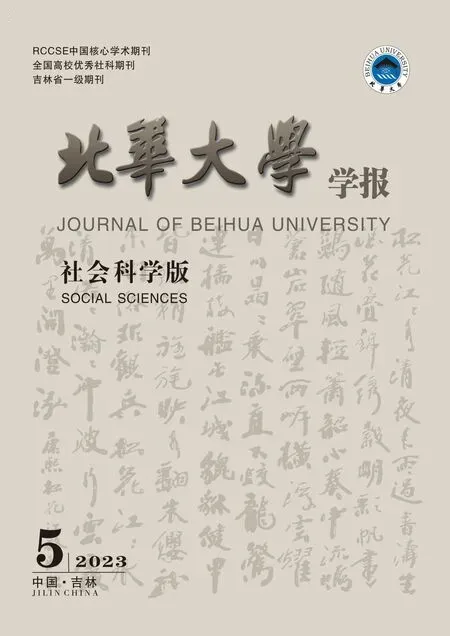启蒙运动思想传入拉丁美洲的过程及其影响
2023-06-05尹建龙沈昊凌
尹建龙 沈昊凌
引 言
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许多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启蒙运动的中心地区——英、法、德等国,对其启蒙思想与政治社会变革多有关注,不吝溢美。但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属的伊比利亚半岛(Iberia)缺乏研究,西方学术界认为: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是欧洲的边缘角色,被西班牙和葡萄牙长期殖民统治的拉丁美洲又是二者的外围。按照这个逻辑,拉丁美洲成为了离 “欧洲文明中心”最遥远,受 “欧洲文明”辐射最小,因而是最不发达的地区。(1)例如,丹·贝尔纳等科学史专家认为西班牙和拉丁亚美洲的科学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科学相比是落后的。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贝尔纳指出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的知识领域一直由天主教神父控制和统治,从未有机会来发展科学,拉丁美洲的科学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困境。(Bernal J D.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London:George Routledge&Sons Ltd,1944:290)奎托(Marcos Cueto)和卡尼萨雷斯(Caizares Esguerra)等拉美本土科学史专家研究发现,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的科学和技术实际拥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科学史之所以一直被忽视而成为 “隐蔽的”或 “秘密的”历史,被排除在主流科学史之外,只是因为 “欧洲中心论”在作祟,因为恰好欧洲的科学革命发生在一个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导致许多学者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不可能发生科学革命。(Jorge Caizares Esguerra.Iberian science in the renaissance:ignored how much longer.Perspectives on Science,Cambridge:MIT Press,2004:86-124)如此一来,若论及拉美的启蒙运动,一则认为拉美不存在启蒙运动,二则以欧洲中心主义与文化传播主义(2)“文化传播主义”的一系列假设——欧洲自然地不断取得进步和现代化,欧洲之外自然停滞不前,没有变化,保持传统和落后,只有通过引入欧洲文明才能获得进步。详见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的观点看待拉美的启蒙运动,认为它只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被动、消极接受者。
启蒙运动本身具有多个面相。它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政治上反对封建特权,思想上以理性主义反对宗教愚昧,法国大革命则是其最为激进的表现形式,康德曾评价法国大革命为 “第一场伟大的近代政治革命”[1]。启蒙运动还有另一个重要却常被忽视的一面—— “对推广有用的知识充满热情,尤其是商业、农业、历史等学科的知识”[2]4,而这恰恰是拉丁美洲启蒙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启蒙运动思想传入拉丁美洲的背景
了解拉丁美洲的启蒙运动,首先需要观察宗主国内部发生的变化以及相应的调整。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一时期受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伊比利亚半岛两大帝国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而开展了改革运动。这些改革直接或间接地将启蒙运动的成果传播到了拉丁美洲地区。
(一)伊比利亚半岛的启蒙运动
18世纪是伊比利亚半岛两大帝国经历剧烈政治、经济变动的年代,外交上帝国屡屡失利,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帝国在殖民地的权势日益衰微,欧洲新兴强国进一步染指美洲。在此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展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即 “波旁改革”与 “庞巴尔改革”。有学者认为,欧洲进步的思想体系实际上一直与伊比利亚旧的传统相抗衡,而18世纪的危机则是改革的催化剂,使伊比利亚人认识到现代欧洲文化与自身传统文化之间的鸿沟,以所谓的 “开明专制”使新事物与既有体制相互和谐融通,从而弥补这一裂隙。
1.波旁改革
在启蒙史学(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的书写中,18世纪的西班牙帝国代表了一个空前残酷的殖民世界:“凶残、愚蠢、宗教压迫、专断恣意的君权……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造就了许多无知且书生气十足的牧师、律师和医生。”[3]一言蔽之,西班牙帝国是一个笼罩在黑暗中,随时准备被科学、法治和人道主义的光芒照亮的世界。这种评价并不公允,实际上,在不影响其原有政治秩序的前提下,为了扭转帝国衰落的过程,西班牙主动开展了启蒙运动。
西班牙经济改革的最初目标是促使矿业生产尽快恢复,重振日渐衰退的黄金、白银和汞矿生产。[2]7帝国采取的手段包括降低贵金属税收,下调水银价格,减少生产成本,刺激白银产量回升,加强对矿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等。除了这些传统的手段,帝国还尝试革新采矿技术,为此需要培养采矿和冶炼的相关人才。[4]西班牙的艾尔胡亚尔兄弟——福斯托·德·艾尔胡亚尔和胡安·何塞·埃尔胡亚尔(the Elhuyar brothers,Fausto and Juan José)在和平之友协会(La Sociedad de Amigos del País)的支持下学习科学理论和应用科学,并曾在法国和德国学习。
另外,西班牙积极组织了许多学院和研究所。在推广有用的知识这一领域上,一些特殊的学院和研究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在18世纪履行了许多研究职能。大约于1760年,在巴斯克地区的阿兹柯伊提亚镇,佩菲亚佛罗里达伯爵(El Conde de Pefiaflorida)组织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院。这所研究院 “洋溢着启蒙运动的热情”,每天都举行讨论:星期一讨论数学问题;星期二讨论物理学;星期三讨论历史;星期四和星期天是音乐;星期五和星期六则播报时事。1766年,在国王首席大臣格里马尔迪(Grimaldi)的庇护下,这所研究院被转变为和平之友协会。当1767年耶稣会士被驱逐后,研究院很快获得了一所教会学院的所有权,并在那里建立了著名的塞马纳里奥·德·维尔加拉学院(Semanario de Vergara),这是一个反牧师教学和 “唯物主义”研究的中心,也是西班牙建立的第一所世俗学校。这所世俗学校的建立以及皇室的保护政策,极大鼓舞了西班牙各地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迅速在马德里(Madrid)、瓦伦西亚(Valencia)、塞维利亚(Seville)和其他地方建立了共约40个类似的组织。[2]8-9
2.庞巴尔改革
在17和18世纪,葡萄牙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一个边缘国家。但实际上,启蒙运动同样在此有所表现。庞巴尔改革中的教育改革正是葡萄牙吸收、践行启蒙思想的明证。素有 “开明专制”政治家之称的庞巴尔侯爵(Marquis de Pombal)认为,葡萄牙人民由于受到天主教长期的统治而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只有通过科学和理性来启蒙人民,才能由此实现葡萄牙的复兴。庞巴尔侯爵将耶稣会士逐出葡萄牙王国及其海外属地之后,便开始了他的教育改革。
庞巴尔致力于在全国设立大量世俗学校,并对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制度进行改革,他的教育改革同时也影响到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他被视为巴西公立学校的创建者。庞巴尔对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dade de Coimbra)进行的改革,直接体现了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庞巴尔在科英布拉大学增设了数学学院和哲学学院,由于教学对实验的需求,他相继创办了解剖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植物园、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实验室为科学实验提供了场所,使科学思想变得更好理解,有助于学生纠正常识上和直觉上的错误。除建立实验室外,相关实验仪器也是必不可少的,木制乐器是由葡萄牙人若阿金·何塞·多斯·赖斯(Joaquim José dos Reis)根据当时教科书中的模型制作的;金属仪器主要来自意大利夏帕·彼得拉公司(Schiappa Pietra);其他更复杂的仪器是在英国购买的。[5]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欧洲最新的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成果,庞巴尔鼓励学校邀请外国学者讲学。经过教育改革的科英布拉大学焕发全新的面貌,吸引了众多葡萄牙和巴西的学生。[6]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启蒙思想在拉美殖民地的传播并影响了其表现形式——注重实用科学知识的学习、传播和应用,而非对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
(二)拉丁美洲启蒙运动传播过程中的国际因素
由于统治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与法国的波旁王朝在政治和血缘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导致法国对这一时期西班牙的政治文化具有较大影响。法国的商品和思想大量涌入拉丁美洲,为启蒙思想在拉丁美洲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18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者学习法国的 “开明专制”进行改革。改革并不局限于宗主国内部,两国也采取了诸多措施以加强对殖民地的管理和控制,如扩大殖民地的财政收入,完善殖民地的军事防务等。这一过程,也间接促进了科学技术在拉丁美洲地区的传播,比如开展对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勘探和考察;加强对金属类原材料生产的研究;激励农作物种植技术的创新等。[7]61葡萄牙庞巴尔侯爵对科英布拉大学的改革以及西班牙设立的采矿学校对促进殖民地科学知识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贸易以及殖民地内部长途贸易发展迅速,农业和矿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波旁改革和庞巴尔改革的一系列针对殖民地的政策虽然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但归根到底是为了强化对殖民地的控制,排除欧洲其他势力,实现对殖民地的 “再征服”。宗主国在经济上加重了对殖民地的剥削,所谓自由贸易也只是帝国内部的自由贸易,在政治上又堵塞了克里奥尔人(殖民地上层精英)的晋升之路,加之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外部因素的强烈冲击,克里奥尔人与半岛人的分歧不断加剧,殖民地精英们的自我意识愈发高涨,以致寻求摆脱宗主国的压迫。反抗宗主国,不仅要付诸行动,还要赋予行动以合法性,启蒙思想则成为了拉美人寻求独立的思想武器。[8]205
二、启蒙运动在拉丁美洲的表现形式
拉丁美洲在启蒙时代并没有因为地理上的边缘化与政治、文化上的严密控制而与启蒙思想 “绝缘”,该地区具有接受、传播和发展新思想的渠道与机制。此外,受到自身社会情况以及宗主国的影响,拉美启蒙运动具体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追求,而非激进的政治与社会变革。
(一)启蒙书籍的输入与传播
18世纪,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对殖民地文化传播媒介的控制,未能阻碍科学思想的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在审查制度下实际上一直暗藏着一套有效的书籍输入系统,因此,新思想流入拉丁美洲实际上很少遇到困难。[9]99例如,卡亚俄(Callao)宗教裁判所的审查官迭戈·希斯内罗斯(Diego Cisneros)不仅允许17世纪和18世纪的哲学论文通过,而且他亲自收集这些论文,并将其提供给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然后提供给利马(Lima)的学生。巴西米纳斯吉拉斯的一位书商在18世纪中期为顾客提供相关服务,以致有时欧洲书籍的出版日期和该书运抵米纳斯吉拉斯的日期相隔才一年。[9]99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宗教裁判所的审查制度虽然在法律上已经确立,但本质上是官僚主义和无效的。”[10]
拉丁美洲的出版业在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报刊会定期刊登拉丁美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对殖民地知识分子进行新科学启蒙,并建立了一个以崇尚科学为共识的读者市场。[11]具有代表性的报刊包括《墨西哥文艺杂志》(Literary Magazine of Mexico),这是第一本宣传启蒙思想的科学杂志,由何塞·安东尼奥·阿尔萨特·伊·拉米雷斯(José Antonio Alzatey Ramírez)于1768年创刊。除此之外,医师和数学家何塞·伊格纳西奥·巴托拉切(José Ignacio Bartolache)创办了《信使导报》《文化入门》《墨西哥文学日报》《秘鲁信使报》《立马公报》《危地马拉公报》《格拉纳达新王国周报》,这些报刊刊载了许多有关启蒙思想和本土主义的文章。[9]101
尽管当时殖民地有着严格的文化管控政策,但是私人图书馆成为各类 “禁书”保存和传播的重要途径,对于殖民地民众,尤其是克里奥尔人思想的觉醒起了重要作用。17世纪后半叶,卡洛斯·德·西吉萨·贡戈拉(Carlos de Sigüenza y Gngora)和索尔·胡安娜·伊纳斯·德·拉·克鲁斯(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所藏的书籍中包括启蒙运动时期博物学家的著作。西吉萨的图书馆同时收藏了高等数学、占星术、天文学和物理学等领域的藏书。巴托拉切拥有一家藏有177册科学书籍的私人图书馆,所藏图书涉及文学、医药、宗教、法律、矿业、化学、历史、物理学、数学、植物学和自然科学、哲学、土著语言等领域。[12]另外,还有哈瓦那的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波哥大的安东尼奥·纳里尼奥(Antonio Nario)、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朗西斯科·德·奥尔特加(Francisco de Ortega)、马里亚纳的路易斯·比埃拉(Luis Vieira)等人的图书馆。[9]99-100
(二)学术组织的创立和发展
宗主国和罗马天主教对殖民地的文化管控和对先进思想的镇压,迫使秘密组织成为了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重要角色。独立运动前夕,各类秘密组织已形成一种先进思想的传播网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共济会。在拉丁美洲,共济会因传播法国启蒙思想,对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号召力。1795年成立的阿根廷 “独立会所”(Logia Independencia)是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会中心,其中大多数人都有在欧洲接受教育的经历,深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另外,米兰达建立的 “大美洲联盟”(Gran Reunión Americana)以及阿尔韦尔(Alvear)、圣马丁(San Martin)和奥希金斯(O’Higgins)成立的 “劳塔罗会所”(Lautaro Lodge)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共济会会所,后者在智利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有分支。[11]
针对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知识的需要,拉美各地成立了科研机构与新式学校。在矿主和商人的敦促和支持下,墨西哥创建了采矿学校(1792年)、植物学学校(1788年)和艺术学校(1785年);在危地马拉,国家之友经济协会(Sociedad Económica de Amigos del País)建立了植物园(1796年)和绘画与数学学校(1797年);在加拉加斯,数学学院的成立(1760年)得到了商务领事馆的支持;在利马,矿业法庭赞助成立化学冶金实验室(179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何、建筑和绘图学校是由商业领事馆于1799年创建的,航海学校(Escuela Náutica)也是由该组织创建的。[7]62-63另外,庞巴尔改革中的教育改革并不局限在葡萄牙本土进行。殖民地教育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印第安人的教育世俗化,并增设初等学校。同时,无论在教会学校还是世俗学校,都开始重视几何学、自然地理学和实验物理学等的教学。[6]在此基础上,巴西也设立了科学技术性质的院校和机构。为促进巴西农业、牧业以及种植园经济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帝国于1772年在巴西创办了第一个科学院——里约热内卢科学院(Sociedade scientifica do Rio de Janeiro)——专门研究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农业、医学、药学等。该协会尤为关注植物学,拥有自己的植物园以便进行有用的植物学实验。[13]1792年又成立了专门讲授科学和工程学的里约热内卢军事工程学院,它是巴西最古老的军事工程学校。[11]这些机构引发了人们对启蒙理想和现代科学的兴趣。
综上,18世纪的拉丁美洲并非不存在启蒙运动,只是与欧洲启蒙运动的表现形式不同,拉美不仅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欧洲启蒙思想,而且对启蒙思想进行了本土化改造。
三、启蒙思想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影响
启蒙思想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确实影响深远,但拉美绝不是欧洲启蒙思想被动的、消极的接受者。相反,它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下理解、利用欧洲启蒙思想。因此,我们不能片面看待拉美在启蒙运动中的角色。
(一)拉美政治家对启蒙思想的本土化改造
18世纪后半叶,孟德斯鸠、伏尔泰,尤其是卢梭的作品逐渐被拉美知识精英,尤其是大城市的上层克里奥尔知识分子广泛接受,他们的学说成为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根源之一。
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ívar)是拉美独立运动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玻利瓦尔在少年时期就通过他的家庭教师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而间接受到卢梭的影响。玻利瓦尔前往欧洲留学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著作都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1805年玻利瓦尔与他的导师罗德里格斯同游意大利,8月15日在罗马城萨克罗山顶当着导师的面宣誓,誓为西属美洲的独立而献身。[14]领导拉美独立战争的先驱之一,哥伦比亚的安东尼奥·纳里诺(Antonio Nario),也是一个虔诚的卢梭主义者。他热衷于唤醒拉丁美洲人民的独立意识,曾翻译和印刷了《人权宣言》,并在朋友之间传播。阿根廷的马里亚诺·莫雷诺(Mariano Moreno)是卢梭的虔诚追随者,他呼吁在建立真正的民主制过程中将卢梭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付诸实践。[15]143“为了教育美洲青年”,他于1810年编辑出版了《社会契约论》。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是卢梭思想在西属美洲的主要诠释者之一。在他的《旅美日记》中,曾提到他与约翰·特雷西的一次谈话,主题就是卢梭的学说。他在欧洲时还特意参观了卢梭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因此,他反对西班牙的行为与他所受卢梭思想的影响是一致的。[16]
无论是玻利瓦尔,还是纳里诺、米兰达、莫雷诺,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欧洲启蒙思想,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诠释。玻利瓦尔一方面支持独立,却对战后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革命深感恐惧,因此更希望出现铁腕人物能够掌控时局,将民主置于强势政府领导下。米兰达虽然捍卫人民主权,但他认为民权、主权这些权利应该是自上而下的,是由贵族政权所赋予的。他否定卢梭的 “公共意志”,摒弃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念,将自己视为人民主权的化身。纳里诺主张建立的是贵族共和国而不是民主共和国,他最不希望黑人、印第安人和农民充分参与社会建设与政治进程。莫雷诺虽然追随卢梭,但他又认为民主制应是社会上层阶级强制推行的,而不是由大多数社会底层的民意决定的,政治权力不能落在 “肮脏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手中。[15]138-147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克里奥尔精英几乎都信仰天主教,并没有像欧洲启蒙思想家一样激烈地反对教权。
启蒙思想让克里奥尔人获得了新的政治灵感,其中关于自由和共和的思想,激发了克里奥尔人对政治独立的要求,加速了克里奥尔人独立意识的形成。面对波旁改革的 “暴政”,对克里奥尔人来说,自由已经不单纯是从18世纪专制主义国家下获得自由,而是从殖民地宗主国下获得自由,平等则是与母国西班牙人的平等,而达到这两个目标的唯一途径便是独立。[16]但是,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启蒙思想对克里奥尔精英们的影响,也需要认识到,克里奥尔精英们对启蒙思想,特别是卢梭思想的有限接受与改造。他们认为理想型社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是一个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法团以及强大的精英领导阶层构成的有机统一体,[15]147土生白人精英就是这个有机体的 “头部”,天然地代表人民与公共意志,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与公共意志概念实际上反而为他们的威权主义、精英主义思想提供了正当性。
(二)启蒙运动促进美洲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启蒙运动以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政治理论和原则只是其中之一。启蒙思想中对科学的追求也间接影响到了拉美独立运动。18世纪后半期,科学研究在拉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甚至一些地区的科学发展愈加制度化。但是,当广袤的美洲大地被勘测,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被进一步研究,拉美的科学家们意识到,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欧洲的拉美研究存在许多谬误及偏见。在这种背景下,拉美的科学家们(主要是克里奥尔知识精英)提出 “美洲的科学”以区别于欧洲的科学研究,这对增强拉美地区的民族认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走向科学启蒙运动与争取政治独立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具有一致性。
值得关注的是,彼时存在一场关于美洲的气候、环境和人种是否劣于欧洲的激烈争论(3)这一争论源自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的著名理论—— “地理位置决定论”,他的具体表述为: “热带地区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懦弱;而寒带地区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寒带地区的人民体质和精神能从事长久、艰苦、雄伟和勇敢的活动,保持政治自由所以欧洲多民主政体。”这一理论之后成为欧洲人歧视拉美人懒惰、野蛮的理论支撑。,这场争论源于欧洲思想家对美洲的偏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普鲁士传教士科尼利厄斯·德·保夫(Cornelius de Pauw)和法国博物学家布冯伯爵(Comte de Buffo)。他们认为由于美洲不良的环境特征,与旧世界相比,新世界的生物是低劣的,生活在新大陆的克里奥尔人更是缺乏不屈不挠的精神,智力和体力均过早衰退。[17]这些充满偏见的论点激起了克里奥尔知识分子对美洲环境和美洲人的捍卫。拉丁美洲博物学家从根本上驳斥了二者的观点,乌纳努埃(José Hipólito Unánue)的论文《利马气候观测》(Observaciones sobre El clima de Lima)和弗朗西斯科·何塞·德·卡尔达斯(Francisco José de Caldas)的论文《气候变化观察》 (Del influjo Del clima sobre los seres organizados)力证新大陆的气候不仅比欧洲人想象的健康,而且具有广泛的变化。[18]为了适应这里的气候变化,生活在此处的居民也得了无畏和坚强的品质。除此之外,墨西哥的克里奥尔植物学家抨击他们的西班牙同行僵化地接受林奈(Carl von Linné)的学说。墨西哥对阿兹特克植物学的研究在18世纪末已经制度化,首席克里奥尔植物学家莫希尼奥(J M Mociio)提议创建墨西哥药理学,他认为 “这样墨西哥就可以自豪地拥有自己的药物”。[18]在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墨西哥统计报告》的序言中,卡尔达斯解释说,他的目的是为自己国家的研究和发展 “提出一个美洲模式”,这种模式是自觉的美洲模式,明确寻求与欧洲科学相分离。[18]虽然卡尔达斯敏锐地意识到 “没有与有教养的欧洲的加速交流,科学就不可能在新世界发展”,但他坚信,拉丁美洲摆脱欧洲的政治枷锁同时,还需要去除对欧洲的科学依附。[18]
独立战争前拉美殖民地的科学发展是一个逐渐摆脱 “欧洲中心主义”,从而实现 “印第安化”(Indianizing)和 “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即拉丁美洲民族化的过程。[11]因此,拉美不单单接受欧洲启蒙科学思想,还利用这种思想和方法探索、发现、构建自我。
在科学研究各领域不断取得有价值成功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学代表着进步。独立后新国家的诞生给予了拉美科学家们实现社会进步抱负的机遇。于是,科学和技术不再像殖民统治时期那样被视为私人事务,而成为一个与 “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有关的问题。[7]153科学和技术是实现公共利益、恢复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一个手段。
1833年,墨西哥杰出的医生瓦伦丁·戈麦斯·法里亚斯(Valentín Gómez Farías)推行了教育改革,废除了旧式的墨西哥大学,代之以现代科学机构,致力于研究地理和统计等学科。在秘鲁,圣马丁将军(General San Martín)解放利马后,邀请杰出的博物学家和医生伊波利托·乌纳努埃(Hipólito Unánue)加入第一届独立政府并担任部长。[7]154其任职期间,主持成立了研究办公室和自然历史博物馆。1821年当选为大哥伦比亚副总统的桑坦德尔,在代行总统的职责时,研究了建立运河和铁路的可行性,设立数学和矿业学校以刺激当地工业的发展,鼓励有技术的欧洲人移民。当葡萄牙法庭迁移到巴西时,新的军事和海军学院也应运而生。[8]207-208此外,拉丁美洲的宪法中也包含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规定,如各州政府有负责发展教育,推广科学知识,创办和支持科学机构发展的责任,技术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手段。这在1810年的加拉加斯宪法、新格拉纳达各省的宪法、1814年墨西哥宪法、1826年玻利维亚宪法和阿根廷宪法中都有记载。[7]154
启蒙思想中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对进步的永恒信仰,深深影响了独立后的拉丁美洲。科学成为恢复秩序与建设国家的良药,各国相继出台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公共政策,用以确定新国家的合法性。
结 论
综上所述,拉丁美洲并未与启蒙运动绝缘。殖民地末期的拉美不仅存在接受启蒙思想的渠道与机制,还以另一种方式——追求科学知识开展启蒙运动。独立运动前后更是处处映射着启蒙思想的光辉: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政治思想和原则成为克里奥尔精英反抗宗主国压迫的思想武器;启蒙思想中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促进了拉美地区科学研究的发展。
当然,拉美对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将启蒙思想与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进行了调和。正如宗主国西班牙、葡萄牙的有限改革一样,拉美地区的变革也是非常有限的。殖民地末期,经院哲学依然在当地教育占重要地位,宗教裁判所的审查依然存在,根本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并没有发生。拉美对欧洲科学思想并没有全盘接受,本土科学家们将目光聚焦于自己的家园,以美洲的科学对抗欧洲的科学。独立战争时期,崇尚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克里奥尔精英用启蒙思想诠释独立的合法性,但他们的政治表达处处折射拉美的政治文化传统。[15]138-147在独立运动中,启蒙思想更多是起到催化和加速的作用,更深层次的精神动力还需要从天主教经院哲学以及克里奥尔人的民族主义中去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