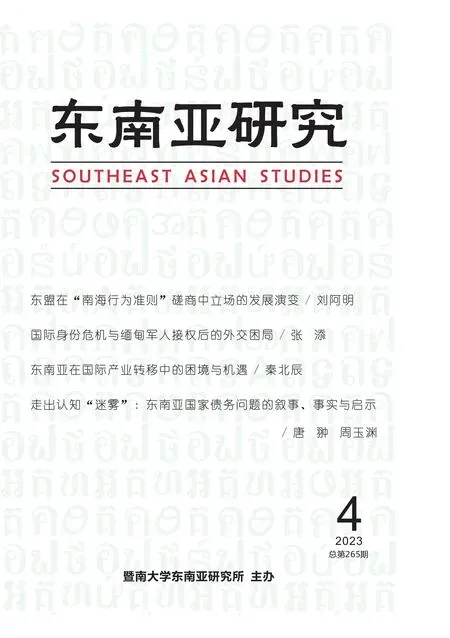东盟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立场的发展演变
2023-06-05刘阿明
刘阿明
一 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是中国与东盟管控海上权益争端,指导和规范各声索国在主权诉求相互重叠的海洋区域的行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合作,且具有约束力的重要国际协定。从1992年东盟外长第一次宣布要达成“一种关于南海的国际行为准则”的目标,到2019年7月中国、东盟提前完成“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第一轮审读,关于“准则”的磋商和互动(包括但不限于正式谈判)历经1/4个世纪,可谓世界上历时最长的外交互动之一。以2013年“准则”磋商正式启动为起点,学界对东盟立场演进的相关研究在磋商的关键节点大量涌现。
在磋商启动初期,李明江通过分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达成以来的中国与东盟互动,认为虽然东盟与中国开始了“准则”谈判,但“准则”要想具备“效力”,必须首先弥补“宣言”的“漏洞”和克服阻碍其实施的因素;卡尔·塞耶尔(Carlyle A. Thayer)认为,相对于中国,东盟在“准则”磋商中处于弱势地位,东盟国家无法团结起来形成一种共同立场,中国将利用东盟的分裂谋求在“准则”谈判中的优势地位;罗国强则认为,东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推动“准则”磋商启动,提出“零号草案”,中国应依据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原则积极参与这一进程(1)Mingjiang Li,“Managing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From DOC to COC”,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Issue 15,March 2014;Carlyle A. Thayer,“ASEAN,China and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3,No.2,2013;Carlyle A. Thayer,“ASEAN’s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Litmus Test for Community-Building?”,The Asia-Pacific Journal,Vol.10,No.4,2012;Mark J. Valencia,“What the ‘Zero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Says (and Doesn’t Say)”,Global Asia,Vol.8,No.1,2013;罗国强:《东盟及其成员国关于〈南海行为准则〉之议案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彼时研究着重于梳理从20世纪90年代“准则”构想出现到《宣言》达成再到“准则”磋商启动这段时期东盟立场的历史发展脉络,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囿于磋商刚刚起步,相关研究对东盟政策变化及效果的论述并不深入。
随着磋商的发展,尤其是2017年5月中国与东盟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以下简称“框架”)前后,国内外学界出现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从实然性出发,有学者认为“准则”磋商进程缓慢是由于东盟成员国之间利益差别极大,无法形成统一立场,这是客观存在的“弱点”而非中国态度使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越来越强大而东盟相对弱小的现实是“准则”磋商进展困难的实际原因(2)Taylor M. Wettach,“Don't Count on ASEAN to Save the South China Sea”,The National Interests,August 10,2016,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nt-count-asean-save-south-china-sea-17309;黄瑶:《“南海行为准则” 的制定:进展、问题与展望》,《法治社会》2016 年第1期;Carlyle A. Thayer,“A Closer Look at the ASEAN-China Single Draft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The Diplomat,August 3,2018,https://thediplomat.com/2018/08/a-closer-look-at-the-asean-china-single-draft-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张明亮:《原则下的妥协:东盟与 “南海行为准则” 谈判》,《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3期;Kei Koga,“Reassessing ASEAN on the South China Sea:What the 30th ASEAN Summit Can Tell Us about Its Utility”,June 2,2017,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assessing-asean-south-china-sea-what-30th-asean-summit-can-tell-us-about-its-utility;周士新:《试论建构南海地区秩序的行为准则》,《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5期;Le Hu,“Examining ASEAN’s Effectiveness in Managing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The Pacific Review,Vol.36,No.1,2023;Rahul Mishra,“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More Discord than Accord”,Maritime Affairs,Vol.13,Issue 2,2017.。此类研究大多关注“准则”磋商取得实际进展之前的东盟集体立场建构。二是从应然性出发,强调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应加强团结性,否则将导致其效用下降,无法在磋商中保护成员国利益;在今天中美竞争的环境中,中国与东盟应该抓住“准则”磋商契机,为南海合作订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3)Ian Storey,“Assessing the ASEAN-China Framework for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Perspective,No.62,August 8,2017,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ISEAS_Perspective_2017_62.pdf;Satu Limaye,“The Impact of South China Sea (SCS)Tensions on ASEAN:An ‘Eye-of-the-Beholder’ Dilemma”,The Asia Forum,July 31,2015;Yanmei Xie,“The South China Sea Needs ASEAN More Than Ever”,July 8,2016,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east-asia/south-china-sea-needs-asean-more-ever;吴士存、陈相秒:《中国—东盟南海合作回顾与展望:基于规则构建的考量》,《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6期;Ian Storey,“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n 2020-2021”,Perspective,No.97,September 3,2020,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0/08/ISEAS_Perspective_2020_97.pdf。此类研究受到2017年后“准则”磋商进展的鼓舞,较为关注未来磋商中双方立场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南海政策发生变化的阶段,虽有学者建议东盟立场应该是与美国一起应对中国,但事实上中国和东盟在很大程度上共同排除了域外干涉,掌握了“准则”磋商的主动权(4)Michael Beckley,“The Emerging Military Balance in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2,No.2,2017;陈慈航、孔令杰:《中美在“南海行为准则”上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3期。。重点各异的研究通过密切关注磋商进程,积累了大量素材,同时也由于研究对象和视角的巨大差异而呈现数量多、领域散、观点杂陈等特点,略有“盲人摸象”式不足。
2019年完成“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第一轮审读后不久,全球新冠疫情的暴发拖累了谈判进程。与此同时,美国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磋商前景暗淡,并倾向从更深的学理层面寻找原因。一类是从现实主义出发,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各方互信不足,东盟国家对“准则”倍感悲观,甚至认为即便达成,也非解决南海争端的良方,东盟无法遏制中国在南沙群岛的行动(5)Hoang Thi Ha,From Declaration to Cod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Engagement with ASEAN on the South China Sea,Singapore: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2019;Lee YingHui,“Is ASEAN Ready to Stand Up to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July 24,2020,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7/24/is-asean-ready-to-stand-up-to-china-in-the-south-china-sea/;Crisis Group,“Competing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Asia Report,No.315,November 29,2021,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north-east-asia/china/315-competing-visions-international-order-south-china-sea;Felix K. Chang,“Uncertain Prospects: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Negotiations,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October 6,2020,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0/10/uncertain-prospects-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negotiations/;T. Trystanto,“Assessing the Potential Effectiveness of the ASEAN-CHINA Code of Conduc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Constrain Chinese Aggressive Actions”,Padjadjar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6,No.2,2022.。另一类则是从制度主义出发,认为“准则”和东盟作为“地区安全机制”的能力非常有限,东盟最大的立场就是呼吁各方冷静,其机制框架和决策过程无法应对像南海争端这样的问题;“准则”的细节谈判道阻且长,即使勉强达成,也无法真正起到缓解紧张、管理冲突的作用(6)张琪悦:《“东盟方式”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的适用及中国对策》,《河北法学》2020年第2期;贺嘉洁:《东盟海洋合作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4期;Stephen Burgess,“Confronting China’s Maritime Expa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Fall 2020;Aristyo Rizka Darmawan,“ASEAN’s Dilemma in the South China Sea”,Policy Forum,October 6,2021,https://www.policyforum.net/aseans-dilemma-in-the-south-china-sea/;Leticia Simões,“The Role of ASE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June 23,2022,https://www.e-ir.info/2022/06/23/the-role-of-asean-in-the-south-china-sea-disputes/。在这些充满悲观的论调间隙,也有学者对“准则”磋商抱有期待,他们认为东盟规范虽有缺陷,但磋商进程本身就具有和平的价值,是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贡献。中国有必要支持东盟对维护区域安全秩序的积极贡献(7)贺嘉洁:《东盟的规范性影响力及其在南海问题中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Naifa Rizani Lardo,“ASEAN Way:Managing Expectation in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Global:Jurnal Politik Internasional,Vol.23,No.2,2021.。上述研究虽不完全聚焦东盟立场,但通过分析磋商所面临的困难和阻碍,从反向透视了东盟立场的发展演进,并为本文提供了前瞻性预测基础——如果东盟希望继续在“准则”磋商中发挥作用、取得成绩的话,这些难点和阻点应是其着力克服的“病灶”。
总体看来,自2013年“准则”磋商启动至今,关于东盟立场的研究成果丰富且观点纷呈,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充足资料,时间跨度之长也足以检视各类观点的正确性。笔者认为,谈判重启后,东盟立场仍将是影响各方互动及“准则”前景的最大单一因素,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尤其重要。因此,对“准则”磋商启动10年来东盟立场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进行概览回顾,并总结出影响其立场的长远性、结构性动因,从而为今后磋商中更加理解、进而影响东盟提供学理性支持,以期为中国—东盟有效互动、“准则”达成后取得实质性效果提供助力,实为必要。
二 东盟集体立场的演进及特征
纵观10年来“准则”磋商的进程,东盟集体立场的发展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一)第一阶段:2013年之前
在这一阶段,东盟逐步建立起共同性立场,即将“准则”视为东盟成员国能够达成共识的唯一的南海争端解决机制(8)Le Hu,“Examining ASEAN’s Effectiveness in Managing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The Pacific Review,Vol.36,No.1,2023,p.126.。其表现为“对内达成共识、对外团结一致”,结果是成功推动了“准则”磋商正式启动。
对内,东盟成员国在启动“准则”磋商上达成共识。2002年《宣言》达成后,南海地区维持了几年平静,“准则”磋商显得没有那么急迫。但随着各方对争端海域的占领和资源争夺加剧,2009年后南海局势的紧张程度明显上升。在海上争议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自2011年起,东盟开始在各个场合强调南海地区行为准则对于进一步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意义,并呼吁最终达成“准则”(9)“2011 Press Release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Retreat”,Lombok,January 16-17,2011;“2011 Chair’s Statement of the 18th ASEAN Summit”,Jakarta,May 7-8,2011;“2011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on Strengthening Defence Cooperation of ASEAN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to Face New Challenges”,Jakarta,May 19,2011,https://cil.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1/06/Documents-on-ASEAN-and-South-China-Sea-as-of-June-2011-pdf.pdf。2012年5月,时任东盟主席国柬埔寨宣布东盟已就“准则”草案的关键部分达成一致,并将开始与中国谈判(10)Vong Sokheng,“Progress on South China Sea Code”,The Phnom Penh Post,May 24,2012,https://www.phnompenhpost.com/national/progress-south-china-sea-code。虽然在7月的外长会议上,东盟因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意见不同而没有发布联合公报,但却一致同意并发布了印尼起草的“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六点声明”,其中第三点指出,要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11)“Statement of the ASEAN Foreign Ministers”,Phnom Penh,July 20,2012,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AFMs%20Statement%20on%206%20Principles%20on%20SCS.pdf。不久,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时任印尼外长纳塔莱加瓦(Marty Natalegawa)公布了在《宣言》基础上形成的“零号草案”。作为“东盟集体努力的产物”,其目的就是要开启关于“准则”的磋商(12)Marty Natalegawa,Does ASEAN Matter?:A View from Within,Singapore: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2018,p.124.。至此,(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基本上已成为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原则性一致的目标(13)张明亮:《原则下的妥协:东盟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3期。。
对外,东盟在促进中国尽早进行“准则”谈判上团结一致。中国是最强大的南海声索国,没有中国的参与,“准则”无从谈起。2011年7月,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称:“在条件成熟时候,中国愿意与东盟来商量制定《南海行为准则》。”(14)《杨洁篪: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解决南海问题》,2011年7月25日,http://www.china-aseanbusiness.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id=3231随后,中国—东盟外长会议达成《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Guideline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DOC),规定“应在有关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决定实施《宣言》的具体措施或活动,并迈向最终制订‘南海行为准则’”(15)《中国与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全文)》,中国新闻网,2011年8月1日,https://www. chinanews.com/gn/2011/08-01/3225262.shtml?t=1450712131114。次年,中国、东盟在峰会后发表《共同声明》,称双方共同承诺磋商一个以共识为基础的“南海行为准则”,确保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和合作(16)“Joint Statement of the 14th ASEAN-China Summit to Commemo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Dialogue Relations”,June 12,2012,https://asean.org/joint-statement-of-the-14th-asean-china-summit-to-commemorate-the-20th-anniversary-of-dialogue-relations/。2012年外长会议后,东盟再次表达尽早正式启动谈判进程的希望,柬埔寨时任首相洪森利用主席国的身份在与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的会谈中转达了东盟的共识和决心。“这是近来东盟国家罕见地就此问题达成一致。”(17)张明亮:《原则下的妥协:东盟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3期。此后,利用2013年访问北京和博鳌论坛的机会,时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向当时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提出了“准则”磋商意愿(18)Carlyle A. Thayer,“ASEAN,China and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3,No.2,2013,p.80.,磋商随即正式启动。
(二)第二阶段:2013—2016年
在这一阶段,东盟采取拒绝为单个成员国的自利行为“背书”的立场,成功维持了与中国的积极互动。
2013年后,在南海地区紧张气氛的惯性效应下,各声索国依旧“各行其是”,南海争端继续发酵,紧张局势加剧。2013年1月,菲律宾不顾中国反对,就中菲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的争端提起强迫“仲裁”;越南则加速了对争端海域的资源掠夺,通过与域外国家在南海加强石油、天然气开发和军事合作,促使争端国际化。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南海争端中外交斗争、资源争夺、法律博弈等各领域纷争发展最快、突发事件最多、紧张频频升级的阶段。
虽然“准则”谈判进展缓慢,东盟的一致性也受到压力,但东盟集体立场却格外坚定,并展现出鲜明特点:一是拒绝为某个国家的争端处理方式“背书”。2016年“南海仲裁”结果发布后,菲律宾和越南希望东盟发表支持性声明,但是东盟在裁定前后均拒绝发表支持裁决结果的声明或宣言,并拒绝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关于在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声明中提及“仲裁案”的建议。2016年9月召开的东盟领导人会议亦对南海问题措辞温和,并有意回避了与“仲裁案”相关的内容(19)贺嘉洁:《东盟的规范性影响力及其在南海问题中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这种不对争端发展做过度渲染的理性态度不仅维持了内部团结,也为与中国互动营造了积极的氛围。
二是拒绝指责中国,成功维持了与中国的积极互动。由于“准则”谈判启动后进展并不顺利,一些人开始将责任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在利用“准则”“诱惑”整个地区,其目的是拖延进程、分散地区国家的注意力,从而促进自己战略目标的实现(20)Ian Storey and Cheng-Yi Lin eds.,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Navigating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Tensions,Singapore: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2016,p.143;Ankit Panda,“For the ASEAN-China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Ninth Time Isn’t the Charm”,The Diplomat,August 1,2015,https://thediplomat.com/2015/08/for-the-asean-china-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ninth-time-isnt-the-charm/;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CRS Report,January 26,2022,p.77.。东盟一度发表过措辞激烈的“声明”(后迅速撤回),但总体上保持着与中国进行积极互动的立场,坚持以低调、“顾及颜面”的处理方式与中国沟通,而非一味地指责和疏离中国。2014年7月,中国正式同意文莱提出的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的倡议,即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这是中国首次明确表示在南海地区安全秩序构建上接受东盟的参与和推动(21)贺嘉洁:《东盟的规范性影响力及其在南海问题中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2016年“仲裁案”后,东盟与中国外长发布关于南海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保持南海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当事方’)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并宣布对争端采取“自我克制”和“合作行为”(22)“Joint Statement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SEAN Member States and China on the Full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Vientiane,July 25,2016,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7/Joint-Statement-on-the-full-and-effective-implementation-of-the-DOC-FINAL.pdf。2016年7月起“准则”谈判开始提速,中国、东盟均表达了希望在2017年上半年完成“准则框架”制定工作的愿望。
(三)第三阶段:2017—2019年
在这一阶段,东盟立场表现出一致性与分歧性共存的特点,“准则”磋商取得成效但不确定性同步显现。
借助2016年下半年的良好氛围,2017年8月中国、东盟就“准则框架”达成一致,东盟集体立场表露无疑:在“准则”功能定位上,称其不用于解决领土争端或是与海洋划界相关的问题;在国际法作用上,称坚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等一系列“普遍确认的国际法的原则”,但只字未提“南海仲裁案”;在实施的监督机制方面,东盟没有设立强制执行条款和仲裁机制,签字各方表示均有责任保护争议海域的海洋环境,以“实际行动”践行协定(23)See Ian Storey,“Assessing the ASEAN-China Framework for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Perspective,No.62,August 8,2017,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ISEAS_Perspective_2017_62.pdf,pp.3-6.。 2018年8月,所有各方就“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文本单一草案”(SingleDraft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NegotiatingText,简称“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面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变化,双方在将美国排除在“准则”磋商之外的立场也是一致的(24)Le Hu,“Examining ASEAN’s Effectiveness in Managing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The Pacific Review,Vol.36,No.1,2023,p.136.。在2019年7月第22届中国—东盟峰会上,中国和东盟国家提前完成了对于“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的第一次审读,“准则”磋商取得重大进展,南海地区第一次出现了由相关各方建立一个有效的争端管理外交机制的可能。
与此同时,随着“准则”磋商的细节化,东盟国家在很多方面仍出现分歧,2017年4月东盟峰会《主席声明》和8月外长会议《联合公报》均晚于预定时间发布这些事实本身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具体而言,关于“准则”适用的地理范围,越南希望特别提及西沙群岛,但无法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支持,因此只笼统提及南海。关于“准则”的效力问题,东盟秘书长黎良明(Le Luong Minh)等人认为“准则”必须具有法律约力才能是有效的,但东盟最终“回避”了有关设立强力执行机制的条款。作为折中方案,印尼提出建立一个“高级委员会”,在“准则”各方之间进行争端解决,但并未在其中清楚地加以规定。关于第三方能否加入“准则”及其在其中作用如何,以及在没有得到所有声索国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非“准则”签字国是否被允许在南海区域内进行军事演习等规定也不清楚(25)Carlyle A. Thayer,“A Closer Look at the ASEAN-China Single Draft South China Sea Cold of Conduct”,The Diplomat,August 3,2018,https://thediplomat.com/2018/08/a-closer-look-at-the-asean-china-single-draft-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弥合这些分歧并非易事,“因为这以后将用于南海,有很多事必须考虑:我们的利益、许多国家的利益”,因而各方都谨慎行事(26)Malou Talosig-Bartolome,“ASEAN,China Continue to Hold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Talks”,Business Mirror,July 29,2022,https://businessmirror.com.ph/2022/07/29/asean-china-continueto-hold-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talks/。
(四)第四阶段:2020年之后
在这一阶段,“准则”谈判没有明显进展,东盟立场不确定性增加,未来磋商将面临更大障碍。“单一磋商文本草案”是一个很长的文本,包含了所有竞争性的立场,目前达成一致协议的序言部分多涉及总体目标,争议点和内容均较少(占据总19页中的一页多),较容易达成一致,但是下一个部分“基本理解”就要复杂得多。从泄露的文本来看,各声索国之间几乎在每一个条款上都存在难以协调的分歧。
新冠疫情的暴发牵扯了各国大量精力,“准则”磋商也不适合以视频或网络方式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利用2020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推动东盟立场出现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国际法作用在争端解决中的回归。2020年第36届东盟峰会发表《主席声明》,称《公约》是决定海洋地物、主权、管辖权和合法利益的基础,也是所有海上行动的法律框架(27)Jim Goerez,“ASEAN Takes Position vs China’s Vast Historical Sea Claims”,The Diplomat,June 29,2020,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asean-takes-position-vs-chinas-vast-historical-sea-claims/;“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36th ASEAN Summit”,Viet Nam,June 26,2020,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Chairman-Statement-of-the-36th-ASEAN-Summit-FINAL.pdf。菲律宾外交部东盟事务助理部长埃斯皮里图(Daniel Espiritu)在中国与东盟准备启动疫情后第一次面对面磋商前表明立场,称《公约》《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国际海事组织(IMO)的相关规定和其他管理海洋的国际法将是起草各种机制的基础(28)Malou Talosig-Bartolome,“ASEAN,China Continue to Hold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Talks”,Business Mirror,July 29,2022,https://businessmirror.com.ph/2022/07/29/asean-china-continueto-hold-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talks/。
“准则”磋商启动10年来,东盟集体立场经历了特征鲜明的四个阶段,有效地维持了磋商进程并助其取得成果。但同时,干扰东盟立场的各种因素不断显现,如成员国国内政治演变、东盟主席国变动等,加之“准则”磋商步入“深水区”以及外部干扰因素的变化,目前东盟立场已经出现了分歧和摇摆不定。
三 东盟集体立场的动因与掣肘
“准则”磋商的曲折历程表明,无论是启动磋商,还是取得成果抑或面临不确定性,东盟集体立场在其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集体立场在东盟这一区域性地区组织与外部大国的协商谈判中并不罕见,但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却得来不易,其成因可归结为东盟的共同利益驱动、集体行动困境的掣肘,以及外部行为体施加影响所构成的张力。
(一)共同利益的驱动
共同利益驱动是东盟推进南海“准则”磋商的基础。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认为,当一些个体拥有共同或者集体利益,没有组织的行动将无力或不能充分地增进这种利益,组织的特有和主要功能就是增进这种共同利益(29)〈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一个能够有效管理南海争端的“准则”,恰恰承载着东盟国家这种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
第一,“准则”是建设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缓解成员国分歧与紧张关系的重要一环。“南海行为准则”是唯一专门针对南海、为南海地区局势而制定的地区秩序规则,其规范南海地区秩序的重要性被相关各方一致认可。东盟将“当前行动密切的成员国之间共同磋商来促使《宣言》的全面实施……并且共同工作以期达成一个‘南海地区行为准则’”作为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目标之一(30)ASEAN Secretariat,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June 2009,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APSC_BluePrint.pdf,p.7.。2009后南海地区争端频现,由此导致国家外交纷争、安全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东盟认识到回避敏感的海洋争议只会放任各国根据各自的私利寻求安全保障,进而分裂东盟。一个相对强大的、有约束力的“准则”能够制约声索各方做出过激行动,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海上紧张局势和提升相互信任关系,即使在“准则”磋商过程中出现种种困难和障碍也无法掩盖其功用。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比起磋商结果,磋商的过程更加重要。同时,“准则”也是中国—东盟关系的“睛雨表”。正如前新加坡外交官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所称:“准则是中国和东盟双方管理关系所共同使用的工具。当关系紧张时,我们就不讨论准则;当关系改善时,就开始讨论。”会谈为东盟国家和中国提供了交换观点的平台,达到这种目标就足够了(31)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CRS Report,January 26,2022,pp.77-78.。
第二,“准则” 磋商中的集体立场体现了东盟在地区争端解决中的中心地位。衡量东盟的价值和未来前景的一个关键标准是看其能否建设性地解决自己的内部分歧,而这只有在东盟面对挑战而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谐、持续和集体的回应时才成为可能(32)Mark Beeson,“Decentered?ASEAN’s Struggle to Accommodat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Global Studies Quarterly,Vol.2,Issue 1,2022,p.7.。将政治资源集中于推动“准则”磋商而不是支持国际法对于争端的管理效力,保持东盟在南海争端中的中心地位,并以此确保东盟作为一个地区内可信赖的组织,是东盟重要的共同利益。这一观念已经“深深嵌入东盟的日程安排,不论其效用如何,如果无法达成一个哪怕仅仅是文本的协议,则会被视作东盟本身的失败”(33)Donald K. Emmerson,“‘Ambiguity Is Fun’:China’s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 Donald K. Emmerson ed.,The Deer and the Dragon: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Singapore: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2020,p.153.。鉴于此,东盟唯有坚持其中心性作用,并在东盟框架下对海洋问题进行议程设置和规范引导,确保海洋问题的发展不脱离东盟的轨道(34)贺嘉洁:《东盟海洋合作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4期。。是以,东盟各国在恢复“准则”磋商这一基本立场上快速达成了一致,并从多渠道推动中国参与。当“准则”磋商过程中单个国家寻求其他途径处理南海争议时,东盟捍卫了其中心性和价值利益,坚守了集体立场——诉诸国际法或国际仲裁对于东盟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像菲律宾那种诉诸仲裁的例子已经表明仅仅对抗是不会产生效果的(35)Tenny Kristiana,“How ASEA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South China Sea Tactics”,PacNet,No.23,April 21,2020,https://pacforum.org/publication/pacnet-23-how-asean-should-respond-to-chinas-south-china-sea-tactics。
(二)集体行动困境的掣肘
如果说,各国支持东盟集体立场是基于希望“准则”协调彼此间关系、东盟能够在危机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共同利益,那么这种利益往往是总体性、原则性和长期性的,集体立场也因此大多停留在关于“准则”的总体方向、目标、基本原则等方面。在“准则”的具体细节上,东盟面临着更多的“集体性困境”的掣肘。正如奥尔森所言:“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所有个人在实现了集团目标后都能获利,由此也不能推出他们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那一目标,即使他们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36)〈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东盟在“准则”谈判过程中立场的曲折演进表明,东盟所面临的“集体性困境”要比其共同利益复杂得多。
首先,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决定了集体立场构建困难重重。一是声索国与非声索国之间的分歧。有学者这样评论2012年东盟外长会议所折射出的东盟分裂:如果越南和菲律宾同意使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提议以及柬埔寨赞同的“争议区域”这样的词语,东盟的团结性也是可以维持的(37)Carlyle A. Thayer,“ASEAN’s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Litmus Test for Community-Building”,The Asia-Pacific Journal,Vol.10,No.4,2012,p.6.。同样,关于“准则”法律意义的差异性也很明显。相比越南坚持“准则”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泰国、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并不反对中国对于海洋的司法权……而不情愿(接受国际法管理南海争端的作用),(因为)每一个东盟成员国都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和安全利益。”(38)“S China Sea Disputes Loom Large as ASEAN,China Struggle to Negotiate Code of Conduct”,Radio Free Asia,November 22,2021,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asean-scs-code-11222021163046.html可见,东盟的“分裂”与其说是由于中国的压力而产生,倒不如说是源于其成员国间深刻的矛盾和分歧。
二是声索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准则”的作用上,菲律宾最早提议“准则”应包括特别条款,“管辖从海洋研究到勘探再到开采区域资源……直至在争议岛礁上建立设施的一系列行为”,即成为一个有约束力的危机管理机制;越南虽然在“准则”法律地位上与菲律宾有着同样的立场,但在通过第三方机制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上并不与菲律宾站在一起;马来西亚则明确反对,建议规定“准则”不用来解决南海长期存在的领土和海洋边界争端(39)See Crisis Group,“Competing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Asia Report,No.315,November 29,2021,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north-east-asia/china/315-competing-visions-international-order-south-china-sea。在“准则”适用范围方面,越南寻求将其适用于西沙海域;菲律宾则希望扩大以适用于黄岩岛;马来西亚由于与越南的双边争端而坚决反对其提议。这些关于“准则”的不同观点源自于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和海域重叠所导致的长期资源争夺,也反映了大部分南海资源之争发生在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现实。印尼认为自己每年在捕鱼方面的损失高达30亿美元且多由越南造成,时任印尼渔业部长放话称要“击沉(越南渔船)”,两国外交关系一度相当紧张(40)Arrizal Jaknanihan,“Stiffening the ASENA Sp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March 25,2022,https://www. 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stiffening-asean-spine-south-china-sea。争议导致声索国之间“信任赤字”严重,阻碍了东盟集体立场的构建。
其次,东盟的组织特性决定了采取集体行动的困难。“集体行动的困境”相关理论认为,集体固有的属性是决定能否有效进行集体行动的条件(41)王利文:《集体行动的逻辑与东南亚反恐合作的困境》,《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从东盟的组织属性来看,它并不是能够有效处理困难问题和成员国观点、利益分歧的组织(42)David M. Jones and Micheal L. R. Smith,“Making Process,Not Progress: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1,2007,pp.148-184.。有学者称:“东盟方式”要为东盟这一组织在处理南海争端时常常无所作为负责(43)Leticia Simões,“The Role of ASE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June 23,2022,https://www.e-ir.info/2022/06/23/the-role-of-asean-in-the-south-china-sea-disputes/。一方面,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方式决定了东盟立场往往是成员国短期政治妥协的结果。《主席声明》《联合声明》《联合公报》等各类文件的措辞和语气随时间、主席国身份的变换而改变,并常常受到成员国内部政治变化的影响。这类文件经常被形容是在表明“一致同意各国之间有不同意见,然后各行其是”(44)Shaun Narine,“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Southeast Asia:The Case of ASEAN”,World Affairs,Vol.161,No.1,1998,pp.33-47.。在一些文件中,东盟甚至形成了技巧纯熟的语言来处理关于“准则”的分歧点。例如,不对法律程序的结果采取立场;完全尊重外交和法律程序;不诉诸威胁和使用武力;与包括《公约》在内的、得到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原则相一致,等等。这些“标准化的东盟语言”虽然较易得到各国的一致同意,但在促进共同行动上却明显乏力。
再次,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原则使得东盟立场难有实际约束力。今天,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原则仍然是东盟“最重要的单一原则”,是东盟规范的“基石”。自成立之日起,单个成员国就没有向东盟让渡主权,东盟无法成为一个有着强大执行力的地区机制。“面对南海争端,涉及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地区机制很难形成最佳回应……东盟没有被赋予法律命令和官僚能力来强制各国遵守和接受地区原则和规则。”(45)Richard J. Heydarian,“Face-Off:China vs. ASE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Beyond”,The National Interest,January 9,2015,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face-china-vs-asean-the-south-china-sea-beyond-12000有批评指出,“单一磋商文本草案”未能限制声索国对南海水域、地物或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声索,损害了“准则”处理紧张局势的能力,声索国之间的争议注定会再发生,并且燃起新的紧张态势。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种无奈的现实:东盟无法对成员提供一套选择性激励和惩罚措施或强制性手段,来保证单个成员的行为符合组织的共同利益。成员国接受约束的志愿性和规范的开放性使得成员国始终是自身行为的最终决定者(46)贺嘉洁:《东盟的规范性影响力及其在南海问题中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可以说,比起立场构建的困难,采取以集体立场为基础的集体行动更加困难。
(三)美国的双重影响
东盟采取集体行动的空间有限,导致域外行为体对“准则”磋商的影响无法避免。东亚地区安全本身就是建立在地区因素与国际因素的互动之上,面对冷战后多极化趋势下大国的地区存在,东盟以促进大国行为“社会化”为理念,采取了一种“全包型”方式,将包括中美在内的所有大国纳入地区安全倡议机制化构建中。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对东盟在“准则”磋商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既凸显了东盟捍卫共同利益的急迫性,也加大了东盟构建集体立场、采取集体行动的困难。
在凸显共同利益方面,东盟将“准则”看作是规避大国竞争风险不断上升的重要工具。2010年前后美国开始在南海“准则”问题上公开表达立场。时任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东亚峰会上呼吁:“……所有各方加快努力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南海‘准则’。”(47)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East Asia Summit”,November 19,2011,https://obamawhitehouse. 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1/19/fact-sheet-east-asia-summit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以维系其全球霸主地位为出发点,从军事安全角度规划南海争端在与中国竞争中的作用,导致这一海域“巴尔干化”趋势日渐明显。这使东盟各国感到不安,并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疏离美国政策的态度。在2014年东盟地区论坛上,东盟成员国不愿意回应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所谓“冻结南海挑衅行为”的建议(48)Paul Mooney and Lesley Wroughton,“U.S. Call for South China Sea ‘Freeze’ Gets Cool Response from China”,Reuters,August 9,2014,https://cn.reuters.com/article/instant-art-icle/idUSKBN0G904O20140809。2015年印尼国防部长里亚古都(Ryamizard Ryacudu)称:“如果地区国家能够自己管理南海,就没有让其他国家卷入的必要。”(49)Prashanth Parameswaran,“The New U.S.-Indone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fter Jokowi’s Visit:Problems and Prospects”,Brookings,December 8,2015,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the-new-u-s-indonesia-strategic-partnership-after-jokowis-visit-problems-and-prospects/2017年,当特朗普表示要调解争端时,越南谨慎回应,菲律宾总统则称“(美国)最好不要碰”争端(50)Shi Jiangtao and Liu Zhen,“‘Better Left Untouched’:Philippines and Vietnam Wary of Trump Offer to Mediat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November 12,2017,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119551/better-left-untouched-philippines-and-vietnam-wary。可以说,美国南海政策的大国竞争意图越是明显、强烈,东盟的回应则越是小心谨慎,足见其不愿任由美国将南海问题变为与中国竞争的战略工具。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重要的域外大国,美国政策加重了东盟“集体行动的困境”。一是恶化了磋商所需的友好、互信氛围。近年来,美国高官频繁使用“威吓”“恐吓”“胁迫”之类的词汇污指中国在南海的行为,鼓励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相关议题上采取更加强大的行动挑战或反对中国(51)See Hau Dinh and Yves Dam Van,“US to ASEAN:Reconsider Deals with Blacklisted China Firms”,AP News,September 10,2020,https://apnews.com/article/beijing-global-trade-south-china-sea-international-news-asia-d55e0c17498a09112216412a3f891bc2;Lynn Kuok,“Southeast Asia Stands to Gain as US Hardens South China Sea Stance”,Nikkei Asian Review,August 17,2020;Bhavan Jaipragas,“US Shift on South China Sea May Help ASEAN’s Quiet ‘Lawfare’ Resolve Dispute”,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uly 17,2020,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093450/us-shift-south-china-sea-may-help-aseans-quiet-lawfare-resolve。在与中国竞争的战略指导下,美国大幅增加南海区域内的军事活动,并将所谓确保航行和飞越自由视为首要目的,成为2017年南海地区紧张态势加剧的主要诱因。2021年9月,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建立强化了南海边缘区域的海上军备建设,增加了地区地缘政治紧张氛围,间接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磋商构成障碍(52)Maria Siow,“South China Sea:Will Aukus Affect ASEAN’s Code of Conduct Talks with Beiji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November 21,2021,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156694/south-china-sea-will-aukus-affect-aseans-code-conduct-talks。正如柬埔寨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金孔亨(Kimkong Heng)所称:“我不认为(美国)会有助于改善南海局势,美国有着自己的日程安排,只可能恶化而非促进南海谈判。”(53)RFA Staff,“China,ASEAN to Hold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Talks This Month”,Radio Free Asia,May 16,2022,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asean-southchinasea-05162022091755.html
二是增加了弥合“准则”相关分歧的难度。美国无视东盟在“南海仲裁案”上的态度,屡屡强调所谓海上国际规则,要求中国遵守《公约》和接受“南海仲裁”裁决(54)U.S. Department of State,“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Ruling on the South China Sea”,July 11,2021,https://www.state.gov/fifth-anniversary-of-the-arbitral-tribunal-ruling-on-the-south-china-sea/。同时,怂恿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将南海争端诉诸国际仲裁,希望通过法律战、规则战和舆论战挑战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与海洋权益,搅动南海局势(55)韦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美国特别关注“准则”草案中提及所谓的“第三方作用”,要求双方要确保“准则”“与现有的、反映在《公约》中的国际法保持一致,对在国际法下第三国的利益或所有国家的权利不存在偏见。”(56)U.S. Department of State,“Australia-Japan-United States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August 5,2018,https://2017-2021.state.gov/australia-japan-united-states-trilateral-strategic-dialogue-joint-ministerial-statement/index.html美国尤其反对中国提出的“禁止各方与区域外国家一起进行联合军事行动,除非相关各方都被通知且在事前没有表达反对”的建议。在美国的带动下,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表态“准则”不应忽视它们的利益,支持“准则”中如何让外部国家也能够签署“准则”的相关规定(57)James Borton,“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Clock Runs Down”,The Washington Times,June 22,2021,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1/jun/22/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clock-runs-down/。无怪乎有学者指出,美国通过其东南亚“代理人”影响“准则”磋商来施加影响,其立场已经从支持“准则”磋商转变为破坏和阻挠之(58)Hu Bo,“Sino-US Competi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Power,Rules and Legitimacy”,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26,No.1,2021,p.499;Wu Shicun,“Preventing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Vol.2,No.2,2020,p.39.。
过往经验已经证明,东盟若要成功地继续发挥亚洲地缘政治稳定的支柱作用,就需要更加团结,加强合作机制,以及在大国之间维持一种“中立的掮客形象”(59)Amitav Acharya,“ASEAN 2030:Challenges of Building a Matur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unity”,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No.44,October 2013.。10年来,在“准则”及其磋商进程中,东盟集体立场对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护持东盟中心地位,以及避免卷入大国竞争的积极意义是显著且相对恒定的,代表着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但是,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东盟立盟的行为方式和基本原则,以及美国政策带来的干扰,亦增加了东盟集体立场与行动的困难,“准则”磋商的未来也因此充满了不确定性。
四 以“准则精神”重构集体立场
在共同利益和集体行动困境的张力作用下,东盟在“准则”磋商过程中的立场来之不易。然而,经年纷争导致南海地区事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加之大国竞争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叠加影响,2020年后数次磋商都没有取得显著进展,使外界对“准则”磋商进程及其达成后的效力难有信心。在困难重重的当下,从多维度构建一种有利于形成东盟集体立场,进而推动“准则”磋商取得进展并使之发挥实际作用的“准则精神”,更显紧迫和必要。
第一,“去小集团化”,维护东盟团结共识的决策方式。“准则”磋商的艰难进程导致某些国家对于共识决策这一“东盟方式”的重要支柱产生质疑。在过去10年中,曾多次出现过所谓的“东盟-X”倡议,意图建立一个“更易达成共识”的“小集团”。 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含义的称谓,常常出现在“准则”谈判停滞不前之时,尤其对海上东南亚国家具有较强吸引力。2014年5月,越菲两国宣布一项战略伙伴关系计划,菲律宾重提建立一个东盟“意愿集团”的建议(60)Carmela Fonbuena,“Philippines,4 Other ASEAN Member-States Urged to Form Coalition in South China Sea”,Philippin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December 26,2021,https://pcij.org/article/7713/philippines-and-four-other-asean-member-states-urged-to-form-south-china-sea-coalition。随着美日印澳四边机制、AUKUS等小多边集团的出现,呼吁以“志同道合”国家之间合作的方式,应对诸如南海争端问题的倡议再次出现,被认为是克服东盟“缓慢和无效”的方法(61)Joanne Lin and Laura Lee,“Minilateral Cooperation in ASEAN May Help It Overcome Challenges in Multilateralism”,Fulcrum,March 16,2023,https://fulcrum.sg/minilateral-cooperation-in-asean-may-help-it-overcome-challenges-in-multilateralism/。“小集团”或小多边组织模式背后的逻辑是要避开共识机制,加强若干个国家之间而非整个东盟的合作,这种方式不仅会引发中国的警觉和反应,而且将侵蚀东盟的团结性,对于“准则”磋商有害无益。
第二,“去国际化”,维护东盟在争端解决中的中心地位。在“准则”磋商不断取得进展之际,2017年以来南海问题却出现了一波“国际化”趋势(62)详见齐皓:《印太战略视角下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特点与前景》,《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某些东盟国家无法抵抗南海争端“国际化”“诱惑”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担忧与中国力量对比悬殊,从均势现实主义出发,希望引入美国或其他海洋大国制衡中国;二是争端久拖不决导致对“地区问题地区解决”原则的失望,想要借助其他国际手段敦促争端解决取得进展。越南在南海争端国际化方面最为积极,不仅与美国发展了强大的战略海洋联系,还试图努力与日本、印度建立一种广泛的多边联合,同时从多个国际组织寻求帮助,也一直在为采取国际司法或仲裁手段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印太战略”下,美国将南海问题视为与中国竞争的工具和“试验场”,对南海盟国和伙伴的安全与军事支持进一步增加。南海问题国际化将损害东盟与中国在“准则”磋商上来之不易的互信和良性互动,也将增加东盟各国达成一致的难度,对东盟中心性和团结性均构成严峻的考验。
第三,“去安全化”,凸显争端的政治—外交本质。将某一问题“安全化”可以引起相关行为体对该问题的重视,促使相关行为体调动有限资源加强对该问题的解决。有研究表明,2009—2015年期间,东南亚海洋问题经历了一个“安全化”过程,相应地,这恰恰也是南海争端发酵最为严重的时期。2015年后,“去安全化”的趋势开始出现(63)贺嘉洁:《东盟海洋合作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4期。。“去安全化”是一个与“安全化”相对应的范畴,即将问题排除于安全领域之外,回到公共领域,或在问题变成安全问题之前得到控制(64)张青磊:《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动因与解决路径》,《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政治—外交本质使得各方妥协成为可能。时任印尼外长纳塔莱加瓦在推动东盟启动磋商中最为积极,他将“准则”界定为外交议题,指出“没有一个行为准则,没有一个外交进程,我们当然会在我们的地区看到更多的突发事件、更多的紧张。”(65)Scott Stearns,“Clinton Meets ASEAN Leaders about South China Sea”,VOA,September 8,2012,https://www.voanews.com/a/clinton-meets-asean-leaders-about-south-china-sea/1501147.html正是在这一定位下,菲律宾在与其他东盟成员国协商“准则”原则时作出了重要妥协,从而使东盟在关键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成为主动与中国展开讨论的基础(66)Carlyle A. Thayer,“ASEAN’s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Litmus Test for Community-Building”,The Asia-Pacific Journal,Vol.10,No.4,2012,p.17.。2015年以来,东盟明确将南海问题的威胁界定为非生存性的。各国之间的相互“妥协”减少了南海紧张气氛,为中国与东盟的商谈创造了更好的氛围。今天,“去安全化”也有利于遏制域外大国利用争端制造潜在冲突。东盟在与美国的历次会晤中强调“南海主权声索国及所有其他国家的任何行动保持非军事化和克制”(67)“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8th ASEAN-United States Summit”,Viet Nam,November 14,2020,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CHAIRMANS_STATEMENT_OF_THE_8TH_ASEAN-UNITED_STATES_SUMMIT.pdf,可谓“准则精神”的最好诠释。
第四,“去唯国际法化”,强调“准则”的规范约束力本质。如何认知《公约》等国际法规定的作用,是东盟立场的重要部分。虽然某些东南亚国家使用国际法解决了双边海洋争端,却并不依赖现存国际法去惩罚不遵守约定的行为。东盟在历史上也回避以法律主义处理地区事务,对于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泰国、马来西亚甚至越南都弱化了裁决的作用和意义(68)Tan Hui Yee,“ASEAN Urges Self-restraint in South China Sea Activities,No Mention of Tribunal Ruling”,Straits Times,July 25,2016,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asean-foreign-ministers-address-south-china-sea-issue-in-communique-but-not-tribunal;David Martin Jones and Nicole Jenne,“Hedging and Grand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n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22,No.1,2021,pp.22-23.。2017年达成“准则框架”后,“准则”在法律上的非约束性(没有强制执行机制)基本得到确认。不过,即使“准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它的规范约束力依然可以很强大。正如2017年“准则框架”第一条“原则”指出,“准则”将不是“一个解决领土争端或海洋划界问题的工具”,但却可以“提供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包括一系列的规范,来指导各方的行为以及促进在南海的海洋合作’”(69)Michael Vatikiotis,“Calming the Wat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Win-Win for China”,The Strategist,May 24,2017,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calming-waters-south-china-sea-win-win-china/。马来西亚前外长阿尔法阿曼(Datuk Seri Anifah Aman)认为:“南海行为准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它将是一个所有相关方的安全与和平的指导。”菲律宾前外长、众议长卡耶塔诺(Alan P. Cayetano)称:“许多国家希望(准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先从让它成为一个约束绅士的协定开始吧。”(70)Mark J. Valencia,“A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Don’t Get Your Hopes Up”,The Diplomat,May 30,2017,https://thediplomat.com/2017/05/a-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dont-get-your-hopes-up可见,“准则”是磋商各方认可的地区规则,将对各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产生“规范约束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第五,推动中国—东盟务实海洋合作取得进展。在东盟与中国的共同努力下,南海主权争议尽管并未得到解决,但合作与共同开发成为各方共识。2017年,“准则框架”纳入“24小时热线”和“敦促所有各方找到方法来遵守准则”等内容,聚焦于管理紧张关系和建立信任。在实践中,以在所有能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为原则,推动“准则”适用于管理除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之外的所有争议,诸如鼓励声索国之间就渔业管理、环境合作、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等所有重要的潜在冲突诱发点进行多边谈判(71)South China Sea Expert Working Group,“A Blueprint for A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October 11,2018,https://amti.csis.org/blueprint-for-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准则”磋商促使东盟成员国以协调一致的立场与中国在海洋事务上进行广泛合作。2013年9月,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开始用于资源和海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2016年9月,建立了双方海事部门之间的海上搜救热线平台和应对海上紧急事件的外交部高官热线。“准则框架”达成后,双方海洋合作更加深入和机制化。2018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明确“鼓励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促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开展海洋科技、海洋观测及减少破坏合作,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等”(72)《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全文)》,中国外交部网站,2018年11月15日,https://www. mfa.gov. 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1811/t20181115_7947869.shtml。2018年10月和2019年4月,中国和东盟以共同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主题进行了两次海上联合军演,传递出在海洋领域寻求安全合作的积极信号。“准则”磋商与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可谓相辅相成、彼此促进。
东盟与中国就“准则”进行的磋商之路漫长而曲折,在当前大国竞争加剧的地区环境中,作为中小国家联合体,东盟集体立场形成和发挥作用更非易事。一种强调东盟在处理地区争端中的中心性以及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降低南海争端安全化和地区军事化的风险、以规则构建地区海洋秩序、推动各方加强务实海洋合作的“准则精神”,不仅有利于指导东盟在“准则”磋商中集体立场的构建,而且将逐步形成地区国家管理海洋争端的行为规范,从而服务于东盟的成长与地区的和平,甚至促进大国关系的稳定。
结 论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东盟已将东南亚改造成了一个和平、安宁、繁荣的地区,这在东盟成立以前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即使在东盟共同体建成多年后的今天,南海争端依然是东盟所面对的最复杂难解的问题。自2013年以来,“准则”磋商一直是中国与东盟之间为数不多的管理海洋权益之争的外交平台。在巨大的共同利益驱动下,东盟总体上珍视和倚重这一机制化互动平台,并在“准则”启动和磋商过程中形成了集体立场,推动磋商一步步取得成果。但是,“集体性困境”的掣肘也阻碍了东盟立场的有效性和坚定性,加之国际局势变化,“准则”磋商时缓时急、起伏不定,导致国际社会对其最终结果和效果难免信心不足。
在“准则”磋商进程中,东盟集体立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东盟在地区重要事务中维持团结性和中心性的具体表现,也是东盟以集体合力成功与大国展开互动的关键前提。面对当前“准则”磋商中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东盟的集体立场需要更加明确、坚定的“准则精神”引领,这对于团结东南亚国家,克服现实协商过程中的分歧,塑造南海地区的共同规范和合作型秩序,避免地区沦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尊重东盟的集体立场,并将与东盟的积极互动和合作视为有效管理困扰双方关系多年的海上争端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国将继续支持东盟在地区问题中的团结一致和中心作用,推动“准则”磋商持续进行。双方围绕“准则”形成的互动模式将成为促进国家间海洋合作与构建未来地区规则和秩序的实践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