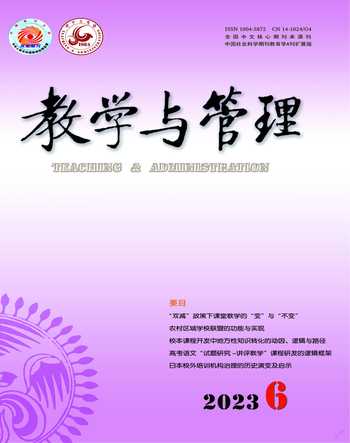校本课程开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的动因、逻辑与路径
2023-06-03李欣桐李广
李欣桐 李广
摘 要 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与普适性知识相对的非官方性知识,在校本课程开发中需要对其进行以课程为目的的转化。校本课程开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生成动因为间接性学问知识与直接性经验知识相弥合、事实的常规表达与课程的教学表达相适配、传统农业社会文化积淀与现代价值相协调的三重需求;其内隐逻辑表现为地方性知识在校本课程开发中的身份合理化、符号意义化和话语秩序化。在实践中,可通过构建社区地方性知识转化共同体、探寻地方性知识表层形式下深层意义结构、生成学校内部校本化地方性知识秩序推进校本课程开发中地方性知识的有效转化。
关键词 地方性知识 校本课程开发 课程知识 选择课程转化 文化阐释
引用格式 李欣桐,李广.校本课程开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的动因、逻辑与路径[J].教学与管理,2023(16):57-61.
校本课程是为本土性知识、地方性知识进入课程而开设的[1],地方性知识是校本课程的深厚文化基础,其构成了相应课程“校本”的基础条件。地方性知识是文化相对主义对于普适性知识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文化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性质,不同的情境催生不同的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产生与地方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当地民众习俗、行为、世界观皆具有极为紧密的联系,是极为重要的在地化校本课程资源。然而,校本课程开发不是课程资源的无序堆砌,课程的开发是对知识进行选择、分类、组织与评价的过程[2],文化的育人性和学生的接受能力是规范开发地方性资源的尺度,需要对未经过“深加工”的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分类与管理,才能将地方文化资源有序转化为课程形态或课程组成部分[3]。
校本课程开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指地方性知识的课程转化(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课程转化指在课程形成时将知识转化为学校知识的过程[4]。地方性知识的课程转化则是地方性知识科学化、体系化和符号化的过程[5],也是通过人为的选择与组织,将非教育场域中具有一定“非普适性”“非官方性”“非科学性”的地方性知识改造和融入教育场域中的学校校本课程,并不断赋予教育性、规范性的过程。在校本課程开发中,如何实现地方性知识课程资源的深度开发与高效利用,主要依据于课程开发主体对地方性知识转化的认识与能力,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必备环节,地方性知识转化的过程与结果直接影响校本课程的开发成效与质量水平。
一、校本课程开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的生成动因
1.间接性学问知识与直接性经验知识相弥合的需求
学问知识的去情域化忽略学生经验知识的生成情境。国家课程作为教育专业人员基于普遍受教育群体而设置的“主流文化”与“普遍知识秩序”,虽然实现了在更广阔范围内对同一性、确定性和普遍必然性学科知识的推广,但为满足更普遍受教育者所设置的学问知识体系,在强调科学性、客观性、中立性、去情域化的同时,也必然存在一定对受教育者个体经验差异和文化境域差异的忽略与压制,从而造成部分地方学生作为教育对象,其直接性经验知识与间接性学问知识相割裂的现实矛盾。不同地方学生拥有不同的经验发生情境,地方情境差异致使地方文化持有者群体直接性经验知识差异,所以单凭普适性知识无法满足与学生各自地方生活中“实践感”相适配的素材内容需求,需要寻求具有一定适切性、针对性、情境性的经验知识并将其纳入课程内容,推动学生生活情境的回归。
学问知识的片段式呈现与学生经验知识具有非连续性。学问知识的重心更倾向于对知识结果的片段式呈现,而不刻意强调知识自生成到科学化、标准化的过程以及与学生已有经验知识间的交互性与连续性,因而外部间接赋予的学问知识与内部直接验证的经验知识间存在一定非连续性断裂。作为普适性知识的学问知识,其脱域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学生用以解决日常情境性问题中存在一定的非适切性,学生难以仅依靠学问知识解决真实生活中的情境性问题。所以,校本课程开发主体需要从“局外人”视角转向本校学生的“内部眼界”,将能够关联本校学生基本生活经验的地方性知识纳入并转化为校本课程内容,作为克服普遍主义影响下课程内容缺乏异质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等现象的重要手段,从而弥补普世主义对学生个体差异与地方群体差异的忽视,解决教学内容脱离学生日常生活的问题[6]。
2.事实的常规表达与课程的教学表达相适配的需求
(1)“日常-教育”的话语规范差异。所谓“话语”(discourse),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事件或这样一类现象”[7]。地方性知识与学校课程知识分别具有对应语境、对应语境内功能与形态。地方性知识话语存在于地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生活化语境中,其话语规范尺度极为宽泛和自由,常以日常方言、俚语、韵文等口头交流形式存在,与地方群体日常生活一般性交流用语内容高度融合。学校教育话语则存在于发生学校教育活动的教学语境中,通过话语达成师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交往行为,指向实施教学任务和实现教学目标的“非一般性话语”[8],具有规范性、准确性、目的性、书面化的话语特征,话语主体也与日常生活话语主体不同,分为教师、学生、教材编写者等。因此,基于二者“日常-教育”的话语规范差异,地方性知识在校本课程中的话语表达需进行相应转化。
(2)“无序-有序”的呈现序列差异。地方性知识与地方社会生活深度融合重叠,不刻意以持有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对其进行序列性划分,其知识系统覆盖思维意识、制度乡约、符号系统、文学艺术、民间竞技等民俗文化,交织杂糅了思想政治、历史、语文、艺术、体育等多学科内容,且具有典型的非文字表述的知识特征。学校课程的基本特征之一为课程的组织性,强调课程要素间严密的脉络结构和呈现序列,同时,教材作为课程内容的重要书面载体,是以某一学科课程知识逻辑和知识结构为主体线索的特殊文本,也是一种由有序的知识序列组成的课程载体和课程工具,因而地方性知识纳入学校校本课程内容必须经历由“无序”走向“有序”的知识组织、整合与编排过程,以满足地方性知识话语与课程所需教学表达话语相适配的需求。
3.传统农业社会文化積淀与现代价值相协调的需求
地方性知识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而社会转型必然引发文化和价值的冲突。我国地方性知识的生成、沉淀与流通根植于本土传统农业文明,其知识产生、知识验证、知识应用皆建立并服务于小农经济,因而其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封建时期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制约与影响,也不可避免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内容,与当代现实社会价值观念相背离、相矛盾、相冲突。如地方性知识中有关宗教信仰、封建迷信、鬼神传说等内容往往与现代价值所倡导的科学、理性、唯物等观念相悖。再如地方伐木捕猎、烧荒开垦等劳作传统,也与当下主张的环保、绿色发展理念存在出入。也就是说,地方性知识虽然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积累与沉淀,但其内部依然具有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杂糅、进步与落后并存的复杂特征和时代局限。
因此,校本课程开发主体在对地方性知识的选择与组织中,既不能对地方性知识不加分辨地全盘接收,也不能因其落后性与封建性而对部分地方性知识进行简单切割与否认。需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将地方性知识还原至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与辩护,用历史去阐明文化,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对有悖于现代价值观念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充分解释与必要扬弃,以促进传统农业社会文化积淀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协调。
二、校本课程开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的内隐逻辑
1.身份合理化:知识选择者对原生情境中复杂地方事实进行的价值判断
课程研制的核心内容是对知识的选择与组织[9]。并非人类所有知识都能成为“课程知识”,只有那些经过社会认定“适合”进入学校的知识才能成为“课程知识”[10]。或者说,按照什么标准选择知识进入课程,这其中必然有价值的涉入[11],通过价值判断来实现转化主体判断依据与课程知识价值的统一。从课程发展的历史来看,自赫伯特·斯宾塞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经典问题开始,价值就成为选择课程知识的核心衡量和判断依据,再到阿普尔关于“谁的知识更有价值”问题的提出,对于课程知识的选择始终围绕“价值”展开。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就是学校自身对“什么知识对本校学生最有价值”这一问题的追问。在地方性知识纳入学校课程知识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对“哪些地方性知识对学生更有价值”这一根本性问题做出回应,即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价值客体,哪些地方性知识能够满足学生作为主体发展的需求。
地方性知识虽冠有“知识”之名,却并非全然以“知识”形态存在,其中更是存在大量日常生活中纷繁复杂的“地方事实”。在校本课程开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首先是课程开发主体从适应本校学生发展需求出发,对非学校教育场域中原生样态的“地方事实”进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一过程不是对“地方事实”机械地、毫无变化地完整再现,也不是对知识数量上的增减,而是对知识重新整理、组织、置换和替代,或明或暗地对知识赋予和渗透一定社会价值取向的结果[12]。经由学校以育人为目标的价值筛选取舍,实现部分地方性知识由非学校课程场域迈入学校课程场域,获得校本课程知识“身份”的第一步,成为一种与原地方性知识“既相同又不同”的知识,标志着它虽具有地方性知识的基本特征,但本质已经成为经过判断、筛选和意义赋予后可具有一定教育功能的课程内容。
2.符号意义化:文化持有者对地方性知识内部文化意义进行的自我深描
校本课程开发不仅是开发一门课程,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乡土文化的传承[13]。对于地方性知识的选择与组织不能仅裁剪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片断”,使很多知识实质上变为一些浅显的“文化符号”而缺乏深层的文化内涵[14],不能止步于对具体的、显性的地方性知识的统整,更需对其显性表象下蕴含的深层文化底蕴和文化意义进行深度剖析。所以,校本课程开发中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也是校本课程开发主体在以构建课程为目的前提下,不断对地方性知识显性表征下深层文化意义进行自我追问和理解性诠释的自我深描过程。
“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阐释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主张对于文化研究需要基于“经验接近”(Experience-near)的立场意识,从研究对象文化的内部眼界探寻表象动作行为与话语符号背后隐含的深层社会文化,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15]。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即便是由教师组成的校本课程开发主体,也无法做到对当地地方性知识系统性、全面性、深刻性地完整掌握。因此,需要校本课程开发主体进一步扩充自我在校本课程开发中的角色定位,基于地方文化内部的眼界对地方艺术文化资源进行深层的自我深描,从地方文化的“体验者”“参与者”与“持有者”扩展转变为兼具地方文化的“认识者”“审视者”与“研究者”的多重身份,对地方文化进行理解性诠释,这种理解、解释不仅仅是解释性的推论,而且还揭示隐蔽的意义[16],以一种阐释视角重新聚焦自身所在地方行为、制度、意象、事件、习俗等社会文化现象下深层次且不易察觉的文化意义体系,完成由“表象”到“内涵”、由“具体”表现到“抽象”地方本土文化的深描,从而实现对地方性知识作为校本课程资源的深度开发和系统组织。
3.话语秩序化:课程组织者对地方性知识话语形态进行的课程知识陈述
知识是课程的核心内容和基础要素,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对一门课程来说不可或缺[17]。知识陈述是在知识本质属性下的符号表征,其在课程领域的存在方式也需符合相应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呈现特点[18]。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与生活高度融合的亲密知识,在日常使用中的符号表征与课程知识的陈述方式具有本质区别。以科学知识为代表的课程知识凭借抽象的概念、符号、公式和推理,其表达形式是逻辑化、系统化的,而地方性知识则通过直观的、形象的叙事呈现自身[19]。所以,地方性知识被纳入校本课程过程中,其本质发生了由地方验证的“地方事实”到学校课程知识的转变,知识呈现也发生由经验陈述到学校课程知识陈述的形态变化。
(1)校本课程开发主体以课程知识话语规律对地方性知识进行表达。语言是人类思想观念和思维活动的物质载体与符号表征[20],无论是地方性知识还是课程知识都是一种语言的存在,然而因知识的生成与使用时空条件不同,造成二者间截然不同的话语规律。地方性知识的话语规律具有非正式、非书面、模糊化、实践化表达话语规律,校本课程知识话语虽然不被一般国家课程知识话语的高度普遍性、指令性、科学性、精准性的标准所严格框定,但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内容,依旧需要一定课程知识制度性、描述性、阐释性、概括性的话语规律作为基本标准。因此,通常情况下,地方性知识很难直接运用到教育活动中,如果不进行二次加工,进行提炼、概念化,就难以与课程标准、教科书直接关联[21],需要校本课程开发主体在充分忠实于地方性知识原始语义基础上,依据课程知识的话语规律对地方性知识进行规范化表达。
(2)校本课程开发主体对“准校本课程知识”进行结构化组织呈现。课程组织就是系统的结构,只有适当的课程组织才能将课程各部分紧密联系起来,并形成一定的秩序,提高整个课程的质量[22]。一方面,對已有累积的地方性知识内容主体进行分析考察,明确“准校本课程知识”集合内部的主体纲要;另一方面,依据课程理论、心理学理论相关知识对地方性知识体系进行由“无序”到“有序”的系统梳理,不仅包括对陈述性、事实性的静态地方性知识进行结构化、层级化组织,也要侧重对实践性、体验性、操作性的动态情境性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合理组织、编排与设计。
三、校本课程开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的实践路径
1.强化知识管理意识,构建以学校为中心的地方性知识转化共同体
(1)明确校本课程开发主体的地方性知识管理战略。学校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机构,应顺应学校本体乡村嵌入的环境逻辑,对本校内部以及所有区域地方性知识进行有效的知识管理,在知识的选择、获取、应用和创新上发挥自身作用,对知识的投入、知识的创造、知识的传播、知识的转化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学校特色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高质量办学要求的外部驱动下,学校不仅要确保对学校内部成员的个人知识、群体知识、组织知识的内部管理,还需着眼于学校所在地方环境中外部地方性知识资源,形成校内知识资源和校外知识资源的系统管理意识,促进学校建成符合时代要求和自身特色发展规划的知识型组织。
(2)联结共同体内部知识链成员进行协同互动。知识链(Knowledge Chain)是以实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为目的,通过知识在参与创新活动的不同主体间、组织间的流动而形成的链式结构[23]。学校不是地方性知识唯一持有者,地方性知识转化无法凭借学校一己之力完成,而需要联结持有地方性知识的多元主体协同实现。学校需通过关系成本的在地激活,促进学校外部、地方区域内部共同持有地方性知识的多元地方角色缔结形成地方性知识的知识链,有效利用知识链成员间知识储备、知识形态、知识视角等方面掌握的知识优势,对自身地方性知识转化过程进行指导、协助等正向干预,建立良好沟通机制,主动与各知识链成员进行跨越组织边界的协同合作,从而促进成员间的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
2.基于深度文化阐释,探寻地方性知识表层形式下深层意义结构
(1)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与一体性,纵向梳理地方性知识深层文化根系。地方性知识既具有微观层面的地区个殊性,同时于宏观层面而言也是构成中华传统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有机成分。地方性知识与中华文化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多元统一共同体。地方性知识差异化、个性化、特殊化的表层外显形式内容背后的文化意义隐喻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间具有高度同源性。因此,校本课程开发中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不在于塑造地方性知识与主流普适性知识间割裂与对立的关系,而是通过对地方文化的阐述与剖析,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与一体性并存的客观历史事实,探寻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知识间的浅层表征差异与深层意义共通,认识地方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异同与关联,奉行文化多元一体理念,实现二者在场的对立统一。
(2)基于批判性诠释,横向探寻地方文化与现代价值的观念交点。对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相冲突、相悖逆部分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历史的认识基础上,依据现代文化价值观念对其进行批判和扬弃。校本课程开发中地方性知识转化过程也是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相连接的过程,学校作为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时空场域,在价值冲突中需要寻找地方文化与现代价值的观念交点,从时代需求出发,用现代观念重新诠释传统,分析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穿越时空的普遍性价值内核,赋予这一价值内核独特的时代内涵,变传统文化为现代文化[24],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保持地方性知识的先进性与时代性。
3.促进文化再生产,生成学校内部校本化地方性知识秩序
学校不是地方性知识的简易收容站,作为代际文化、地方文化延续与传递的重要媒介,在面对“地方文化传承”“如何培养人”与“培养什么人”构成的复合命题中,学校须时刻回应地方性知识在学校教育中再呈现、再表述等再生产问题,重塑学校教育场域内部的校本化地方性知识秩序。
(1)超越形态,实现隐性地方性知识的显性转化。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也称默会知识,指体现在技能、诀窍、技巧、洞察力、经验、心智模式和群体成员的默契等不容易用语言来表达,不易用特定符号编码或者不能编码的知识。从地方性知识的存在样态来看,地方性知识存在一定程度的隐性特征,在与日常生活的高度统一中因集体无意识而被默认或忽略。所以,基于地方性知识自身的隐秘性,需要在课程化过程中借助深度观察与深度阐释,通过考察、描述、编码等书面化方式[25],捕捉地方性知识“现象”背后所承载的隐形地方文化意义系统,将隐性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显性地方性知识,从而应用于校本课程设置。
(2)超越学科,由“单学科知识呈现”走向“跨学科知识联结”。地方性知识在地方文化中并非以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形态孤立存在,而是与地方历史、地方文学、地方游艺、地方地缘等构成地方文化的复杂要素深度交融、互为联系,因而校本课程开发中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不能仅着眼于单学科知识的呈现,而需要面向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突破单一学科的思维定式,采用“学科+”的方式主动跨界,增强不同学科之间知识与方法的相互关联和结合[26]。根据地方性知识表层显性内容下深层文化根系,形成以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线索的跨学科主题,以学科内容,尤其是学科核心知识和思想方法为主干,运用和整合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围绕一个中心主题、任务、项目或问题,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发展学生的跨学科核心素养[27]。
(3)超越课堂,构建记忆共生与体验延伸的校园文化空间。地方性知识的课程转化不仅是课程内容的转化,同时也包括对构成课程的环境转化。一方面,构建反映地方生活特征、体现地域民族历史积淀、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收容、整理和再表征的校园环境空间,持续为学生输入特定环境,增强环境与自身经验的关联,激发学生身为地方社区生活共同体之一的区域意识,强化社区集体记忆。另一方面,需注重地方性知识与校园文化的互动式嵌入,促进地方性知识的校内环境兼容,将地方性知识由校本课程的“凝视”扩散到生活空间的“散视”,推动地方性知识在校本课程课堂外的体验延伸,实现原生性地方性知识与学校再生性地方性知识的内部循环。
参考文献
[1] 李定仁,段兆兵.校本课程开发:重建知识伦理[J].教育研究,2004,25(08):41-46.
[2] 劉丽群,周先利.校本课程深层开发:何以可能[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19(06):92-98.
[3] 刘旭东.论地方课程及其开发[J].教育评论,2000(06):32-34.
[4] Pacheco,J.A.On the notion of curricular transformation[J].Cadernos de Pesquisa,2016,46(159):64-77.
[5] 曾宝成.地方性知识的教育价值及其开发[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06):84-87.
[6] Eijck M V,Roth W M.Keeping the local local:Recalibrating the status of science and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TEK)in education[J].Science Education,2007,91(6):926-947.
[7] 施旭.文化话语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8] 刘桂影,李森.论课堂教学话语的实质、价值与优化[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06):38-42.
[9] 靳玉乐.课程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203.
[10] 郭晓明.课程知识供应制度与个体精神自由[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3(04):9-13.
[11] 蒋建华.知识·权力·课程政策视野中的课程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103.
[12] 金志远.课程知识选择:内涵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1(01):10-13.
[13] 刘丽群,周先利.校本课程深层开发:何以可能[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19(06):92-98.
[14] 叶波.校本课程开发中的知识选择:困境与突破[J].教育发展研究,2014,33(12):37-40.
[15] 孙宁宁.翻译研究的文化人类学纬度:深度翻译[J].上海翻译,2010(01):14-17.
[16] 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M].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29.
[17] 朱于国,姜向荣.关于构建语文课程知识体系的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22(01):102-107.
[18] 张文毅,于晓敏.西方课程知识观的演变:选择、组织与呈现[J].中国大学教学,2016(03):32-37.
[19] 潘洪建.地方性知识及其对课程开发的诉求[J].教育发展研究,2012,32(12):69-73+78.
[20] 王洪席.课程研究亟待关注的课题:课程语言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14,43(03):38-45.
[21] 李长吉.论课程知识的地方性质[J].课程·教材·教法,2019,39(01):11-17.
[22] 吕立杰,袁秋红.校本课程开发中的课程组织逻辑[J].教育研究,2014,35(09):96-103.
[23] 顾新,李久平,王维成.知识流动、知识链与知识链管理[J].软科学,2006(02):10-12+16.
[24] 范鹏,李新潮.界定与辨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涵解读[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9(02):110-118.
[25] 安梅琴.高校教育中如何加强地方性知识的传授[J].课程教育研究,2017(08):29.
[26] 袁丹.指向核心素养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意蕴辨读与行动路向[J].课程·教材·教法,2022,42(10):70-77.
[27] 吴刚平.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意义与设计思路[J].课程·教材·教法,2022,42(09):53-55.
【责任编辑 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