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享以礼与极欢而罢
——九部伎对元日宴会性质的影响
2023-06-01周婧
周 婧
自高祖至玄宗,唐前期的宫廷礼乐在不断调整中逐渐发展成熟,享宴之礼是与郊庙、冠婚、丧祭之礼等并重的礼仪制度。(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5页。其中的宴会礼仪音乐以明辨等级制度,加强君臣关系为目的推动礼仪进程。本文在以宫廷仪式性宴会用乐为对象的讨论中,将仪式性和娱乐性作为坐标系中的两个变量,(2)杨荫浏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纲》中讨论中古时期雅乐的范围时,认为“通常宴飨所用的音乐,有含有典礼意义的,同时也有偏重娱乐意义的”。即使用“典礼意义”和“娱乐意义”以区分宴会音乐中的两个部分。因典礼最直接和核心的内涵指向仪式,故本文在既有的讨论传统中,使用更便于讨论的概念“仪式性”和“娱乐性”。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杨荫浏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72页。以定位仪式及其用乐。从宫廷礼乐重要内容之一,即等级制度构建的角度来看,仪式性参与构建与加强等级制度,在用乐上表现为乐队、乐曲等与不同等级宴会或同一宴会中不同身份参与者的固定连接;而娱乐性则弱化或消解等级观念,在用乐上表现为上述固定连接的消失,亦即区分与等级的消失。例如,雅乐《太和》之曲几乎只在皇帝出入时演奏,而娱乐性乐舞如《霓裳羽衣》的表演就不限于某一类宫廷宴会,亦不限于宴会中某一环节。故从整个宫廷宴会体系来看,音乐的仪式性与娱乐性常在此消彼长的趋势中,实现一种具有张力的平衡。达到平衡时二者的比例即成为影响宴会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平衡不仅记录在制度的细节,也表现于表演的现场。而从具体宫廷宴会仪式对音乐功能的实际需求来看,二者并不互斥,且在很多仪式中共存,仪式性宴会即为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
这两种变量的明确让我们能够进一步区分宫廷宴会类型,以及仪式中的音乐之功能。当宴会礼乐在复古理想与音乐实践的不断磨合中定型,唐前期的宫廷宴会类型也逐渐清晰。其在时间上有定期与不定期之分,在性质上根据仪式在宴会中所占的比例,可分为以仪式性为主、仪式性与娱乐性并重,以及以娱乐性为主的宴会。史料对宴会类型两端的叙述明确而详细,对中间过渡类型以及二者的交流记载相对模糊而粗略,常隐匿在乐舞表演的具体叙述中。例如,本文的讨论对象元日宴会即以仪式性为主;景龙四年四月,中宗与从臣游樱桃园并置酒为乐就应属于娱乐性宴会。(3)〔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08页。而在那些既按照礼制规范使用太常雅乐,又在礼仪流程结束后上演舞马与散乐等的宴会则属于二者并重。以上抽象的区分在具体史料中,可对应于以“宴享以礼”与“极欢而罢”为两极的不同具体个案。这些个案中礼乐与娱乐音乐相互影响的尝试反映出宴会音乐制度与实践的博弈,也反映出唐前期宫廷宴会在“宴享以礼”与“极欢而罢”之间摇摆的性质。在这些宴会中,与仪式过程相伴的音乐即为“仪式中的音乐”(4)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研究现代仪式音乐的曹本冶教授提出“仪式中音声(ritual soundscape)”概念,以囊括仪式过程中更多层次与种类的音响活动,从而更充分的发掘和阐释仪式行为与价值。参见曹本冶:《“声/声音”“音声”“音乐”“仪式中音声”:重访“仪式中音声”的研究》,《音乐艺术》,2017年,第2期,第9页。在以历史人类学为导向的中古仪式音乐研究中,音响资料的收集非常有限。但同样为了深入讨论音乐功能的不同层次对仪式构建与价值呈现的影响,在此将上述概念稍做修改以适应古代音乐的讨论语境,使用“仪式中的音乐”,代替“仪式音乐”。因为后者以功能的同质性为划定内涵范围的主要标准,而前者给仪式中基于功能差别的音乐分类以更多空间。这样能更好的对比不同音乐之间仪式功能的强弱,即音乐参与仪式构建及复现仪式意义的程度,进而实现从音乐的角度讨论礼乐建构过程本身。,其仪式功能的强弱由音乐在仪式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决定,即音乐是否能够细化至各个仪式环节,作为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参与仪式构建、分享仪式意义、推动仪式进程,从而在制度上构建礼乐体系,在表演中复现礼乐精神。一种音乐的仪式功能减弱虽然不是其娱乐功能增强的充分条件,但是从宴会礼乐等级制度构建的角度审视这一过程,仪式性消解与娱乐性增强实际都指向等级观念在制度上的消融,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宫廷宴会从仪式性向娱乐性倾斜的趋势。本文即以元日宴会为切入点,从上述仪式功能的角度比较仪式中的雅乐与九部伎。
九部伎作为唐代宫廷重要音乐制度之一出现在元正、冬至的大朝会制度中,正是唐宫廷礼乐制度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案例。其演奏和功能既反映出西域音乐在唐宫廷的影响途径和程度,也反映出唐代礼乐建设中的困难与取舍。成立于隋朝的九部伎由七部伎发展而来,是贯穿唐代的重要宫廷音乐制度之一。前人的研究已敏锐注意到九部伎在仪式性宴会中的演奏,(5)〔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下册》,梁在平、黄志炯译,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第478页。并将九部伎作为唐代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6)参见项阳:《进入中土太常礼制仪式为用的西域乐舞》,《音乐研究》,2017年,第3期,第483—494页;余作胜:《唐代九、十部乐施用情况新考———兼与〈唐五代多部伎演出情况考〉一文商榷》,《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115页。但是,通过分析三种宴会仪式和宴会文本可知,九部伎以乐队为主的性质及其顺序演奏方式,难以在儒家礼乐建构的意义上充分实现与雅乐相当的仪式功能。相反,九部伎的出现为原本应“宴享以礼”的元日宴会添上了一缕“极欢而罢”的色彩。结合九部伎在其他多种典礼性场合的演奏情况,这是娱乐性音乐进入礼乐系统的一次持久而多元的实践。由于九部伎仪式功能的限制,这种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其所致力于构建的礼乐制度有消解作用,反映在仪式制度本身对于九部伎记载的粗略和模糊。但是这种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呈现出一种弱化等级制度的礼乐建构之可能性。
一、元日宴会中的音乐功能
九部伎的演奏场合非常丰富,其事由从外宴藩主到内享群臣,从夏麦大稔到雀鸟筑巢,不一而足。在对九部乐的记载中,常写奏乐于庭,偶记极欢而罢。在九部伎的诸多表演场合中,元正、冬至大朝后的宴会与宴请蕃国君臣的宴会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三种宴会是唐代五礼制度中嘉礼和宾礼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宴请藩国君臣两篇包括了宾礼部分所有的宴会。而元正、冬至宴会是嘉礼中其他宴会礼仪的范本,叙述最为详细和全面,在其他宴会礼仪部分往往省略具体过程,注明参照元会仪。其详细的制度记载在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颁行的《大唐开元礼》中:《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并会》中宴会的部分,《皇帝宴蕃国王》与《皇帝宴蕃国使》。(7)所据版本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藏公善堂本,参考文渊阁四库本,并对比《通典》与《新唐书》中此三篇的内容。对《大唐开元礼》现存版本的详细讨论和梳理,参见张文昌:《唐代礼典的编纂与传承——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08年,第102—108页。经过高宗末期《贞观礼》《显庆礼》《周礼》并行,以及武后时期的礼制更迭,《开元礼》中元日宴会对九部伎的使用既是对之前传统的继承,也反映出九部伎在唐前期演奏实践中的重要性。元日宴会也因为九部伎的出现在礼仪用乐上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使用了包括西域音乐在内的大量外来音乐;其次,这些乐舞所能承担的仪式功能有限;最后,元日宴会仪式制度中九部伎与传统雅乐作为用乐方案二选一,体现出平衡礼乐正统性与当时音乐多样性的策略。但是,由于九部伎的仪式功能有限,其虽频繁用于宴请蕃国君臣,却不著录于宾礼宴会仪式制度;虽纳入元会演奏,却没有形成详细的演奏方案。相反,九部伎的出现使以不断重申和加强政治等级秩序为目的的元正宴会偏离其设计初衷。
(一)元日、冬至宴会概述
玄宗朝礼乐制度中乐的部分是唐代宫廷礼乐发展的高峰,经过不断的尝试和修订,最终在玄宗时期的《开元礼》中落实为仪式和音乐配合的大量细节,其中音乐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于其曲目制度化的重复,也表现在曲目对仪式过程的标识和推进。每年元日、冬至大朝后的宴会正是宫廷宴会中“宴享以礼”的典型代表。元正即元旦,又称三朝,为年、月、日之始,是以月相为基础制定历法的一年之初始;而以太阳视运动规律分配节气时,冬至为岁首,被视为阳气生发之始。元正、冬至的大朝会是唐代三朝制度中最为隆重的大朝,另有朔望朝,以及常朝。从大朝到常朝仪式功能渐弱,而行政功能渐强。朔望朝仪亦设宫悬,而后无稳定的宴会制度,以行政为主的常朝则无制度化的宴会。《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并会》一篇记录了冬至与元日大致相同的朝会礼仪过程,并标注出皇帝服冕、群臣贺词、奏祥瑞、贡物等方面的区别。其中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皇帝受群臣朝贺之礼,二是与群臣举行宴会之礼。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以元日朝会的历代变迁为研究中心,将元会朝贺结束后的宴会部分概述为八个步骤:朝贺结束后的筹备;群臣、诸亲、客使门外整列;皇帝即御座;王公以下群臣、诸客使入庭;上寿礼;行酒礼;馐饭、赐酒;王公以下群臣、诸客使退。(8)〔日〕渡边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下文将尽量把完整的礼仪用乐细节还原到其简洁的叙述中。
《开元礼》中以太极宫之正殿太极殿为元会仪式场所,但自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建成大明宫含元殿后,元会多在含元殿。此篇共记录十项音乐活动。每两项音乐活动之间,主要记录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三级司礼者推动礼仪进行的程式化语言与动作描述:侍中于御座近旁首传,典仪承传于殿上,赞者再传于殿庭;二是王公以下官员、客使等在司礼者引导下的程式化语言与行动。元会参加人数众多,但皇帝、官员、藩客使、乐官与乐工、司礼者等所用区域主要是太极殿正殿及其殿庭的一部分。(9)另《唐六典》卷四记载冬至、元正的大朝会地点为太极宫承天门,而深入分析承天门结构可知其并不适合强调礼仪表演功能的大朝会。参见〔日〕渡边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2—393页;陈涛、李相海:《隋唐宫殿建筑制度二论——以朝会礼仪为中心》,《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08年,第117—135页。如图1,(10)唐长安太极宫平面复原示意图(局部),傅熹年主编:《中国建筑史·第二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385页。太极宫局部图中,元日宴会使用的太极殿殿庭由其前太极门、左延明门、右延明门,以及连接此三门的廊庑与太极殿及其左右横墙合围而成。承天门外有左右朝堂,为群官客使等候之处。渡边氏对元会的空间有更为详细的图示,如图2。(11)太极殿元会仪图,同注①。在太极殿建筑群平面图中,标出了主要礼乐器——乐悬的位置,陈设于横街偏南。图上未标注而根据仪式详情可知,鼓吹十二案摆放于乐悬四隅之外围,而登歌乐人及乐器则远离乐悬与十二案,置于太极殿上。

图1.唐长安太极宫平面复原示意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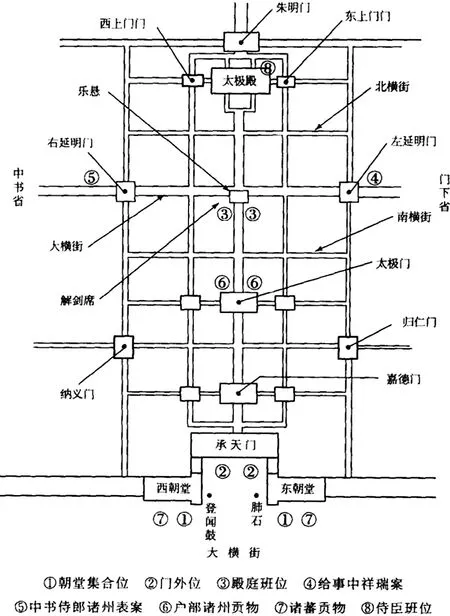
图2.太极殿元会仪图
(二)《大唐开元礼》元日宴会文本分析
公善堂本此篇仪式文本比四库本细节记载详细,文字使用更准确,与《通典》《新唐书》(12)参见〔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141—3149页;〔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5—429页。中所保留的《开元礼》相应材料相比,虽仪式过程叙述详略有差,但这些区别均没有在内容上导致根本的分歧。下面将元日宴会的十项音乐内容逐条列出并分析。
1.太乐令设登歌于殿上,引二舞入,立于悬南。(13)自此条起,1至10项均引自《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并会》中“会”的部分。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54—456页。
在元日朝贺结束后,宴会的布置先由太乐令在太极殿上放置登歌乐队的主要乐器,即编钟一架在东、编磬一架在西。(1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81页。与殿庭中的乐悬相比,登歌是更为小型的仪式乐队,这两架编钟、编磬为与乐悬相区别常称为歌钟、歌磬。而登歌亦包括其他乐器及歌者,将在后续仪式过程中入场。登歌乐器摆放妥当后,文舞与武舞工人须先行入场,站在乐悬后方等待表演。
2.皇帝将出,仗动,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奏太和之乐,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坐,南向坐。符宝郎奉宝置于御坐如常,乐止。
参加元会的群臣、藩客等三品以上升殿而坐,其他不升殿者设座于殿庭。在不升殿者就位后,皇帝从太极殿西端隔出的小间走出,此时太乐令使乐工行撞钟之仪,然后乐悬奏雅乐曲目《太和》,鼓吹十二案亦同奏。音乐伴随皇帝行至御座,止于符宝郎安置好宝玺。撞钟之仪与《太和》之乐实际是两个独立的仪式符号,撞钟之仪出自《尚书大传》,《周礼·乐师》郑注亦引之(15)参见〔清〕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吴仰湘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78页;〔清〕孙怡让:《周礼正义》卷四十四《春官·乐师》,汪少华点校,《孙怡让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166页。,宫廷雅乐常用以为制,以示对古礼的延续。而《太和》之乐作于唐初,是雅乐传统中唐王朝作乐的代表。这里奏乐所用的宫悬与鼓吹在前一日便由太乐令与鼓吹令陈设于殿庭,在大朝时已有演奏,朝后宴会无需重新布置,如下。
前一日,尚舍奉御设御幄于太极殿北壁下,南向,铺御座如常。守宫设群官、客使等次于东西朝堂。太乐令展宫悬于殿庭,设麾于殿上西阶之西,东向,一位于乐悬东南,西向。鼓吹令分置十二案于建鼓之外。
大朝会前一天,太乐令将宫悬乐器陈设于太极殿庭,并设两个麾位以指挥音乐之起止。麾,即旗,执旗者为协律郎。一在太极殿西阶之西,面朝东,一在乐悬东南处,面朝西,两人相对而立。协律郎举麾,乐工奏乐,协律郎偃麾而乐止。仪式空间包含台基之上的大殿,和阶下殿庭,要使殿庭中的乐悬工人在奏乐时音乐紧密配合仪式过程,就需要协律郎二人配合指挥,一如侍中、典仪和赞者从元会的权力中心逐级向外传递仪式进程的信息。可见宴会中的种种细节均旨在建立一个仪式与音乐的意义共同体,不仅配合紧密,且缺一不可。最后,鼓吹令置鼓吹十二案于乐悬四隅的建鼓之外。这便是前文宴会中“鼓吹振作”之所指。鼓吹十二案又称熊罴十二案,是十二个小型演奏台,分布于由镈钟、编钟与编磬环绕为正方形的四面宫悬之四隅。因宫悬四隅均置建鼓,故称置于建鼓之外。那么,上文第二项中皇帝将出时,《太和》之乐则由宫悬乐队和其四隅之鼓吹乐队共奏。与此仪式文本中其他乐曲的演奏相比较,这里的《太和》之乐不记演奏遍数,而是以配合皇帝就坐为时限。《开元礼》大朝会仪中以《太和》之曲配合皇帝就正殿位,武德初年祖孝孙所定的雅乐使用规则中,《太和》奏于皇帝临轩出入,至贞观年间协律郎张文收改定雅乐时,《太和》的功能则记为郊庙祭祀礼仪时出入伴奏。可见《太和》一曲对应皇帝在不同礼仪场合中出入这个功能始终未变。(1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1—1042页。
3.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诸客使以次入,就位。公初入门,乐作,至位乐止,群官、客使立定。
皇帝入座后,王、公入殿,亦奏乐,然不记曲目及乐队。根据唐初祖孝孙所定,王、公出入奏《舒和》之乐,与伴皇帝出入的《太和》均出自贞观初年祖孝孙所作的雅乐《十二和》组曲。
4.皇帝举酒,《休和》之乐作,群臣、客使等上下皆舞蹈,三称万岁,皇帝举酒讫,殿中监进受虚爵以授尚食奉御,奉御受爵复于坫,乐止。
上公上寿,群臣再拜后,皇帝举酒以完成上寿礼,此条为上寿礼之一部分。皇帝举酒,同时协律郎举麾,乐工奏《休和》之乐,奏乐过程中,群臣、客使均需完成身体礼仪“舞蹈”,并三呼万岁。伴随皇帝饮酒完毕,由殿中监接过空酒爵递与尚食,尚食再将酒爵放回置酒爵的台子上,此时音乐演奏才停止。根据宴会前的布置,此放置酒爵的台子在酒尊之南,均放置于太极殿东端。此时,皇帝饮酒伴随着其他参会人员在身体与语言上的礼仪程序。在整个元日宴会过程中,“舞蹈”并不多见,区别于其他部分常常使用的“俯伏”,从行礼种类上突出了上寿礼的重要性。向皇帝行舞蹈之礼常见于唐代史料,其具体动作如何已很难考证。(17)对身体礼仪“舞蹈”的详细讨论,见〔日〕渡边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此项中突出显示了音乐对仪式的标识与推动作用,因皇帝在殿上举酒,除三品以上在殿内就坐的官员等,更多在殿庭就坐的参与者需要通过乐悬乐队的声音来更清楚地获知殿中的仪式进程,并及时完成舞蹈等礼仪动作。这不仅需要协律郎的及时指挥,更依赖于乐曲《太和》与皇帝举酒之间被参与者熟知的固定意义连接。
5.太乐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阶,脱履于下,升就位坐。其笙管者进诣阶间,北面立。
此项为行酒礼之音乐准备,太乐令带领登歌工人中的歌者与琴、瑟演奏者入场。在太极殿阶下脱履,再登阶升殿,就位于宴会前太乐令所设之歌钟、歌磬位置。同时,演奏笙、管类乐器的乐工亦入场立于殿下阶间,面向帝王。此处登歌的安排遵循汉以来的传统,即登歌堂上而笙管立阶下。南北朝以来,不同的政权对于登歌乐队是否能在礼仪宴会上演奏颇有分歧,其具体乐器与人数的编配亦不统一,对登歌所奏之乐曲也常忽略不记,只记某某礼仪进程中登歌。在《开元礼》中则清楚记载了登歌乐队所奏之曲如下。
6.皇帝初举酒,登歌作《昭和》之乐,三终。尚食奉御进受虚觯,复于坫。登歌讫,降复位。
此项为行酒礼之音乐安排。在登歌工人就位后,尚食奉御等开始为皇帝及群官、客使布酒。而后皇帝举酒,群官再拜,殿上典仪与阶下赞者接连传“就坐”后,群官、客使行俯伏之礼,再坐下饮酒。与入场时配合皇帝即御座而不记遍数的《太和》之乐不同,从皇帝初举酒开始,登歌乐队作《十二和》中的《昭和》之乐,三遍而终,登歌演奏结束后工人出殿离场。此环节以音乐时长主导仪式环节时长,增强了音乐的主导性。
7.皇帝乃饭,《休和》之乐作,群官、客使上下俱饭,御食毕,乐止。仍行酒,遂设庶羞。太乐令引二舞以次入作。
登歌离场后,尚食奉御、太官令分别设皇帝与群官、客使的饭食。此时正式宴饮环节开始。乐悬奏《休和》之乐伴随皇帝吃饭始终。皇帝食毕,开始行酒,上佐酒之食。此时太乐令带领文舞与武舞按顺序入场表演。如第一项所示,在元日宴会开始前,太乐令以已经将文舞与武舞的舞蹈表演者一百余人领至乐悬南面。所以这里的“以次入作”指按照顺序进入四面乐悬所围成的空间内表演,文舞为先,武舞为后。
8a.酒行十二遍,会毕。殿上典仪唱,可起,阶下赞者承传。群官、客使等上下皆俯伏,起立席后。通事舍人引降阶,俱诣席后,跪着剑,俯伏,兴,纳舄。乐作,复横街南位,乐止。
8b.通事舍人引群官、客使等以次出。公初行乐作,出门乐止。
8a与8b均属宴会后群官、客使退场离开的环节。由于叙述简略,将以太极殿建筑群的位置图对照说明(参见图2)。8a起于行酒环节,记酒行十二遍后宴会结束,这里“十二”或是虚数,只指多次。殿上典仪与阶下赞者接连传达起立的信号后,参会官员等均起身。通事舍人引殿上参会者出太极殿,顺阶而下,到殿庭中的解剑席后方,佩剑并穿鞋。此处“乐作”应即“公初行,乐作”,参照群官入殿时的奏乐程序,这里并不是从王公离席开始作乐,而是在解剑席完成佩剑与穿鞋后作乐,回到横街南的等候位时,乐止。同一个环节以用乐与否精准区分不同部分,说明音乐本身已能够赋予仪式以意义,而非仅为仪式环节中的背景。
此时群官、客使都站立于太极殿殿庭中各自的位置,如果皇帝有赏赐,则在此时进行。赏赐完毕后仪式进行到8b项,即通事舍人引参会者离场,应是从横街南之站立位出太极门,奏乐同样始于王、公初行。这两项中,奏乐的依然是乐悬,并无述及鼓吹十二案。
9.皇帝兴,太乐令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奏《太和》之乐,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舆入自东房,侍卫、警跸如来仪,侍臣从。至阁,乐止。
皇帝起身,乘御辇从太极殿东房离场,行至太极殿横墙的东上阁门。从皇帝起身开始,太乐令便令乐工击乐悬中的蕤宾之钟,其左边五钟相应而击。而后乐悬仍然奏《太和》之曲,依然配合殿庭鼓吹熊罴十二案,与入殿时一致。结合前文,“鼓吹振作”只见于皇帝出入,可见鼓吹十二案在此文本中为皇帝专用,是以音乐区分等级,起到代替卤薄鼓吹的作用。等皇帝与其侍从等进入东阁门,音乐终止。至此,整个元日宴会结束。元日宴会的礼仪是很多其他宴会场合参照的标准,只是根据具体宴会稍作增删。
10.若设九部乐则去乐悬,无警跸,太乐令设九部伎位于左右延明门外,群官初唱万岁,太乐令即引九部伎声作而入,各就位以次作如式。
在宴会礼仪过程叙述完毕后,补充说明如果宴会准备演奏九部乐,就要把前面朝贺时演奏的乐悬乐队撤出,自然也无需再安排登歌就位。太乐令带领九部伎乐工在左延明门和右延明门外等候。当群官第一次齐呼“万岁”之时,就由太乐令带领九部伎“声作而入”,即在第四项,皇帝举酒标志宴饮开始后,群臣开始三呼“万岁”之时,九部伎乐人一边演奏一边入场,且入场就位后,按照顺序演奏,无更详细安排。如图2,从左右延明门外进入后,左右两组九部伎乐队可以汇合于中轴线。中轴线与左右延明门所在横街的交汇处即原先放置四面宫悬的位置,所以九部伎代替了乐悬在此处演奏。这与九部伎具体演奏记录中多次提到的“奏九部乐于庭”演奏地点一致。而雅乐登歌钟磬设于殿上,不在殿庭,由此可见元日宴会中的九部伎也没有通过区分不同乐队及其演奏位置,去标识仪式的不同环节。
对比前九项乐悬、鼓吹十二案与登歌的具体演奏情况,此项使用九部伎的简要内容已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九部伎在元会演奏中仪式功能的限制,其特点如下:其一,九部伎的演奏以撤出礼乐的标志性乐器,即乐悬为前提,相较于从北周武帝时期开始在元会“与乐悬合奏”的鼓吹十二案,(18)〔唐〕魏徵:《隋书》卷十四《音乐中》,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70页。九部伎对于传统礼乐队并非补充,而是替换;其二,九部伎在皇帝初举酒,群臣首称万岁时入场,无法承担这之前参会人员入场环节的音乐仪式功能;其三,其演奏“以次作”而无更详细信息,表明其极有可能没有形成曲目与功能对应的仪式音乐演奏制度,也就难以达到雅乐在礼乐系统中的功能与效果。
(三)九部伎入仪式宴会的传统
九部伎用于元正、冬至朝会并非玄宗朝新创,在高宗时期即见于记载。《大唐开元礼》中的记录也是对之前传统的继承。
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上祀南郊。黄门侍郎宇文节奏言:“依旧仪,明日朝群臣,除乐县,请奏九部乐。”(19)〔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13页。
高宗即位之初,于永徽二年冬至,即当年十一月二日(20)十一月二日即永徽二年冬至,见〔日〕平冈武夫编:《唐代的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2页。南郊祭天时,宇文节即提出当年冬至之大朝会,请撤出乐悬,使用九部乐。这与《大唐开元礼》文本一致,可以看出玄宗时期将九部伎修入礼典,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而永徽二年为高宗即位之初,宇文节称“依旧仪”,则大朝会用九部乐的传统可能形成于更早的时期。
二、仪式功能受限的九部伎
(一)以乐队制度为核心的九部伎
《大唐开元礼》元日宴会文末体现出的九部伎仪式功能缺失,可部分归因于九部伎本身的性质,即九部伎制度重在乐队而非曲目。其乐队的选择及排序是以政治因素为首要考量的人为选择结果。隋开皇初年始置七部乐,隋炀帝大业年间增至九部,初唐承隋制亦为九部伎。至太宗平高昌后,加高昌伎而增至十部。但在玄宗开元年间,载入礼典的是九部伎而非十部伎,在具体演出的记录中也以九部为多。(21)参见〔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梁在平、黄志炯译,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第489—491页;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36—348页;余作胜:《唐代九、十部乐施用情况新考———兼与〈唐五代多部伎演出情况考〉一文商榷》,《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115—128页。九部伎以政治为考量构建一套乐队制度的性质在其前身——七部伎创立之初已初见端倪。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22)〔唐〕魏徵:《隋书》卷十五《音乐下》,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07—408页。
在七部伎中,无论是乐种、乐器还是乐曲,都是一个以政治意义为先的重新选择与排序过程。据引文,七部伎最初从至少十四种音乐中选出,至炀帝又加疏勒与安国两部而成九部。又同书“龟兹伎”条,记载在隋时,已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三种。(23)对七部伎详细讨论,见王小盾:《论中国乐部史上的隋代七部乐》,《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4期,第103—111页。三种龟兹乐的名称已经反映出一个本土化历程。在排序上,以被认为保留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西凉伎与清商伎为首,而后才是外来音乐,最后以传承于晋的文康伎结尾,这样的安排本身已突出了政治考量在七部伎乐种选择中的重要性。(24)七部伎以国伎,即西凉伎为首,清商乐次之,至九部伎以清乐为首,西凉乐次之。两者的颠倒实际上是以被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音乐,即清乐,代替传统音乐与龟兹乐相融合的乐种,即西凉乐,是从音乐的角度对政治合法性的一次确认。七部伎中的国伎的所指在史料中有两种看法,以《通典》为例,“四方乐”条在记高丽乐与百济乐时认为,南北朝时期二国乐两次传入,后与西凉乐等七部“通谓之国伎”,亦即将国伎作为七部之总称。到隋文帝定七部伎时,由于新增了清乐与文康,而去掉了百济。这里显然是在描述七部伎的成立过程,然而论述中隋文帝平陈前后各乐伎即使在数量的发展上也无法吻合。但其中所记去掉百济乐而留高丽乐,与前文所述七部伎西域乐中用安国伎,而另杂有康国乐的情况均反映出一致的人为取舍过程。而在同书“前代杂乐”条,述及西凉乐时,认为在北朝时期,以龟兹乐与中原音乐相杂而生的西凉乐被称为“国伎”,一直到隋都备受重视。显然是认为西凉乐即为国伎。对比《隋书》所采纳的开皇年间七部乐,确实没有另外单列西凉乐,与“前代杂乐”条中的观点一致。参见〔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四《乐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718页。此选择过程还表现于史料对多部乐记载不一(如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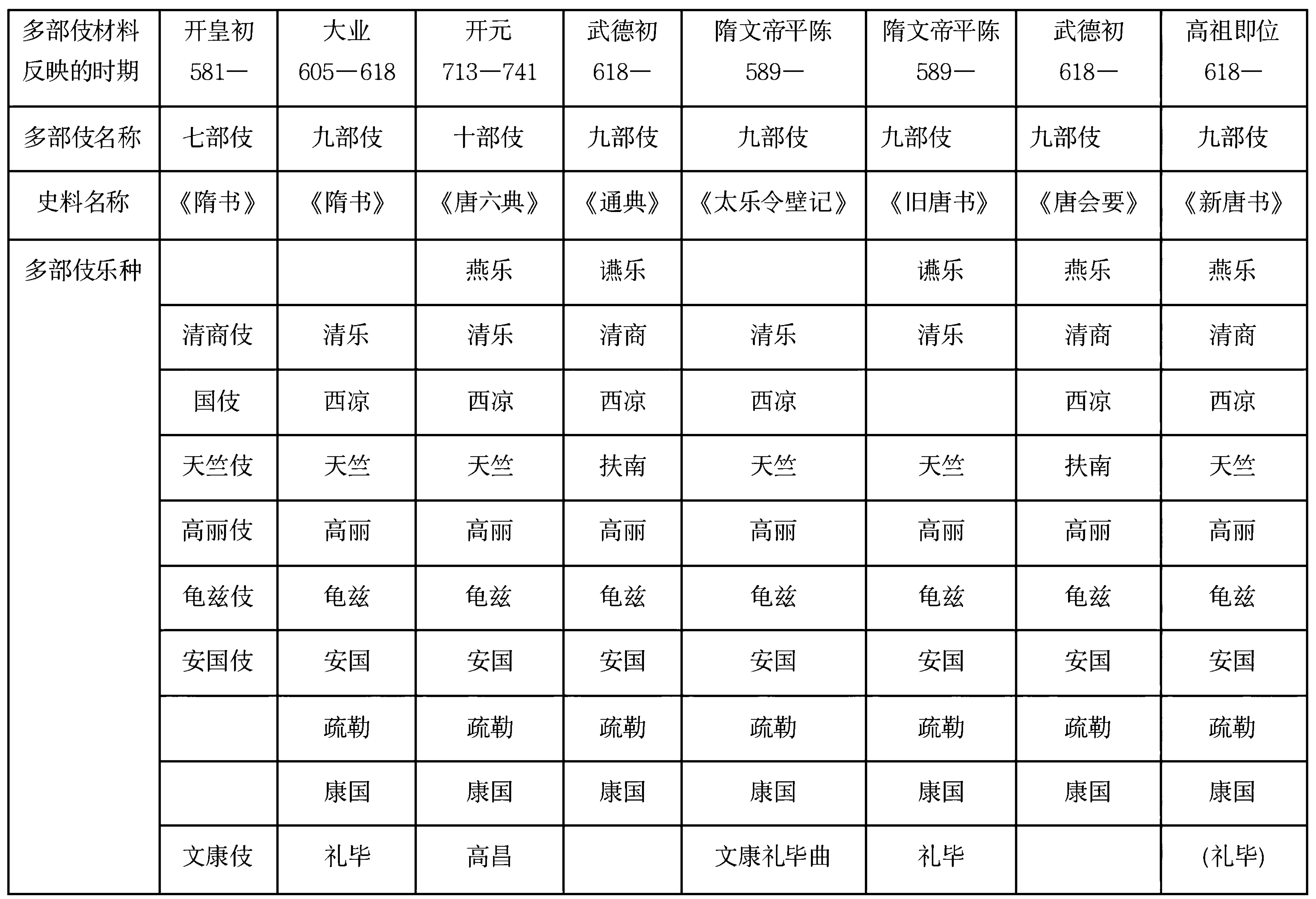
表1.九部伎相关史料比较(25)表1列出七部伎与九部伎的音乐种类记载,为了对比方便,调整了原书中各种音乐的次序。参见〔唐〕魏徵:《隋书》卷十五《音乐下》,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07—408页;〔唐〕李林甫:《唐六典》卷十四,林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04页;〔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707—3708页;〔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9页;〔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09页;〔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9—470页。
表1中七种史料,惟《太乐令壁记》已佚,其关于九部伎的材料保存于《玉海》。表中材料对隋、唐九部伎制度记载并不一致,反映出九部伎形成中带有政治目的的人为选择及记录过程。首先,《通典》等记载唐代九部伎制度的材料中都有燕乐伎,而《隋书》与《太乐令壁记》中对隋朝之七部伎、九部伎的记载中均无。燕乐伎作为唐代多部伎之第一伎,由张文收作于贞观年间,其意义是与隋七部伎中第一伎国伎相当的。但是在列举唐九部伎时,多称“仍隋制”,随即列出燕乐伎。这实际上是政治书写的一种表现,虽仍隋制,但隐去了从武德初至贞观十四年作燕乐伎之前,实际上有二十年左右没有代表李唐王朝的乐队与曲目这一情况。也正是因为燕乐伎是唐初新作且有重要意义,在唐九部伎中有最明确且稳定的曲目信息。
在对唐九部伎的记载中,与《唐六典》《通典》及《唐会要》中一致的记录对比,《旧唐书》无西凉乐而有礼毕,《新唐书》则同时保留燕乐伎与礼毕,认为礼毕是九部结束后的演奏的结束曲,以九部之名行十部之实。而对比可知,《旧唐书》与《太乐令壁记》中九部伎材料应为同源,或《旧唐书》采用了后者的材料。二者叙述逻辑一致,行文更为详细的《旧唐书》却去掉了此段中“合西凉乐凡九部,通谓之国伎”一句,同时保持此句前后所列乐伎与《太乐令壁记》一致,导致《旧唐书》中所列隋文帝九部伎实际只有八种,故应是编纂的遗漏。《新唐书》对九部伎的记载则有勉强折中之嫌,一方面张文收于太宗贞观年间任协律郎,于高宗后任太常丞,职责范围前者属乐而后者属礼,加之其他材料中均记贞观年间作燕乐伎,故作同名《燕乐》的时间应不在高宗后。(26)《通典》《旧唐书》均记为贞观年间协律郎张文收作《乐》,《唐会要》记为贞观十四年。惟《新唐书》直接注明唐继承隋《燕乐》之乐工、舞人不变,同时将张文收所作《燕乐》记为高宗即位后创作的同名组曲。参见《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第3708页;《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二》,第1061页;《唐会要》卷三十三,第614页;《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十一》,第469、471页。而张文收于贞观中任协律郎,高宗即位后任太常丞(参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第6204页),协律郎掌乐律,而太常丞掌祀礼(《唐六典》卷十四,第395—396,398页),故作《燕乐》应在贞观年间而非高宗即位后。另一方面从九部伎的政治功能来看,在有了代表唐王朝的燕乐伎后,同时保留传承自晋,代表中原王朝延续性的乐队与乐曲——礼毕,并无必要。这也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其他史料中的文康伎,即礼毕仅出现在隋之九部伎,而消失于唐之九部伎。
其次,《通典》与《唐会要》均不收天竺伎,而记扶南伎。同书又有“(炀帝)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乐器传写其声,而不列乐部。”(27)参见〔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713页;〔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20页。对比《唐会要》与《旧唐书》的记录,《通典》此处“匏瑟琴”应为“匏琴”。以天竺乐器演奏扶南乐曲,最终以天竺伎命名体现出九部伎制度对乐队的侧重。但是以不同的乐器演奏并不能改变乐曲旋律的来源,这应是文献中记为扶南伎的初衷。显然九部伎从成立起,就是一个不同音乐元素杂糅的创造过程。在此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的乐队制度是主要目标。
(二)九部伎曲目及其有限的仪式功能
九部伎曲目信息的记载粗疏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制度应以乐队为主。上表材料中,除了作于唐初的燕乐伎,只有《隋书》对其他每个乐队的曲目做出详细说明,《唐六典》的材料则从乐工教习的角度反映了玄宗时期九部伎的曲目状况,而其他材料多止于记录乐队构成。其具体曲目信息如下。
贞观中,景云见,河水清,协律郎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今元会第一奏者是。《景云乐》舞八人……《庆善乐》舞四人……《破阵乐》舞四人……《承天乐》舞四人。(28)〔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708页。
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
西凉者……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
龟兹者……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
天竺者……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
康国……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
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
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
高丽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
礼毕者,本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其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29)〔唐〕魏徵:《隋书》卷十五《音乐下》,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08—411页。清乐伎条中,《隋书》点校本中“并契”二字未作曲名,参考其他乐种的记录形式,以及《通典》清乐曲目中多次记《明君》曲,亦将“并契”作为曲名。
再者,《唐六典》“协律郎”条后有太乐署乐工曲目教习的注文如下:
太乐署教乐:雅乐大曲,三十日成;小曲,二十日。清乐大曲,六十日;文曲,三十日,小曲,十日。燕乐、西凉、龟兹、疏勒、安国、天竺、高昌大曲,各三十日;次曲,各二十日,小曲,各十日。高丽、康国一曲。(32)此处文末高丽、康国处与前文体例不符,似有脱文,在此先不讨论二者,只就现有部分做有限分析。参见〔唐〕李林甫:《唐六典》卷十四,林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99、424页。
除了以政治合法性和音乐正统性位居首位的雅乐外,此段颁布于玄宗开元年间的教习规则已删去文康伎,完全包含贞观后成立之十部伎。从教习时长所反映的曲目难度和分类所反映的曲目丰富程度来看,与其他诸伎相比,传统清乐曲目数量更多,难度也更大。从行文逻辑看,除雅乐外的诸伎可分为三部分:清乐、燕乐与其他六种十部伎乐种、高丽与康国乐。在教习时长上三个部分应依次递减,第三部分高丽与康国伎的曲目丰富性与难度应最低。将此条材料与《隋书》九部伎的曲目对比可知,唐后九部伎曲目没有完全遵循隋代旧制,理由如下。首先其分类以大曲、次曲、小曲等替换了隋之歌、舞、解曲;其次,如果说唐后九部伎曲目是因为复刻于隋而不记,那应该像记载燕乐伎那样补充贞观年间新成立之高昌伎曲目;再次,《隋书》中天竺伎只记两曲,而《唐六典》中分类有大、次、小曲三类,可见曲目确有增加;最后,清乐分为三类,自隋以来至于武后时期,一直保持几十曲的规模,武周之后仍有八曲能合于管弦,(33)清乐曲目的流传记载见《通典》卷146,第3703—3705页。清乐曲目考订参见教坊记中所保留曲目,参见崔令钦:《教坊记笺订》,任半塘笺订,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故每类曲目不可能只有一曲,而在九部伎中具体演奏何曲便再无详细记载。作为唐代宫廷重要的音乐制度,史料对于九部伎具体曲目的记载缺失暗示着九部伎重在乐队制度,而每次演奏的曲目并不固定。这种特征在以九、十部伎为基础重新组织的二部伎,即立部伎与坐部伎制度中有更明确的体现,可作参考。
若寻常享会,先一日具坐立部乐名,上太常,太常封上,请所奏御注而下。及会,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马,次奏散乐。然所奏部伎,并取当时进止,无准定。(34)〔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717页。
坐立部伎制度完成于玄宗年间,此条内容与《旧唐书》中描述玄宗时期宴会(3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1页。的内容相互呼应,应与《开元礼》将九部伎纳入元会为同一时期。材料中的宴会中,宴会上演奏哪种乐舞,每种乐舞的具体曲目都是会前一天依玄宗喜好所定,二部伎虽有明确的十四曲乐舞,但并不是依次演奏所有,而是只演奏前一天选出的曲目。这反映出玄宗时期确有在宴会中乐队固定,乐舞随机的惯例。
唐代九部伎乐队制度清晰,曲目与分类在隋唐之间有较大变化,且曲目详情的缺失,此三者共同反映出九部伎以乐队制度为主的性质,以及曲目不断调整的情况,这是九部伎在元会中仪式功能受到限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以隋之九部伎曲目,还是唐后扩充的曲目,在曲目与仪式步骤没有固定对应关系的前提下,都难以形成与雅乐相当的仪式功能。元会仪式文本中记九部伎“以次作”后,更无详情,就引出两个演奏的实际问题:第一,将九部伎从燕乐伎到礼毕全部依次演奏,即使每一伎中两至三种分类都只演奏一曲,其曲目数量都大大超过原本乐悬与登歌所演奏的《太和》等曲,即其在元日宴会中演奏的覆盖面将远超原本的雅乐,因而难以准确与诸仪式环节首尾相应。第二,就演奏方式来说,每一伎中分类相似,均有歌有舞,难以如雅乐以文武二舞突出宴饮正式环节一般,用表演形式有效标识仪式进程。而逐伎演奏,又失去了“重复性”这一对音乐仪式功能的重要塑造手段。故而难以实现雅乐以乐队或乐曲区分仪式性质或环节时,以音乐的重复性呼应仪式的同质性。例如以击钟示意皇帝身份,以乐悬与鼓吹十二案合奏《太和》示意皇帝出入。故九部伎的音乐很难与仪式进行有机结合,甚至有可能会扰乱仪式进程。这就显示出九部伎与本来在仪式中配合演奏的乐悬、登歌等乐队从演奏方式到仪式功能的极大不同。
在《开元礼》中元日宴会文本最后一项“若设九部乐则去乐悬,无警跸,太乐令设九部伎位于左右延明门外,群官初唱万岁,太乐令即引九部伎声作而入,各就位以次作如式。”并不是元日宴会的末项音乐活动,而是对元日宴会的两种用乐选择之一所做的补充安排和说明。以上细节均说明,九部伎作为元日宴会的音乐选择之一,在以儒家理想的礼乐制度为目标的仪式制度构建中,其仪式功能受到了较大限制,从而对于元日宴会的仪式性也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但是从高祖至玄宗期间,几乎找不到具体记载九部伎演奏于某次元会的记录。(36)《唐代九、十部乐施用情况新考》一文列出的四十九次九、十部伎使用记录中并无一次是在正月朔日。且对比《册府元龟》帝王部之“朝会”与“宴享”中唐高祖至玄宗部分可知,正常的元日宴会并不记入宴享部分,而是作为元日大朝的一部分简略的录入朝会部分,亦无具体作乐详情。参见余作胜:《唐代九、十部乐施用情况新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128页;〔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百七、一百九、一百一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74—1276,1299—1311页。在《大唐开元礼》元会仪式文本中纳入九部伎,是对太宗以来将九部伎用于大朝会之既有传统的继承,而这种传统则是在宴会礼娱双重性的前提下,由长期宫廷音乐实践推动的结果。
三、宴会的礼娱双重性:九部伎入元会制度的重要原因
唐建立之初,九部伎可沿袭隋制,而其中代表唐王朝的燕乐伎仍需新作,体现王朝合法性的雅乐则更不可照搬。在旋宫理论与实践、乐悬的编悬与陈布方式、以及具体的雅乐曲目创作与应用等等方面,唐从高祖到太宗时期逐渐建立起一套既崇古,又有别于前代的雅乐制度。而在这一时期,九部伎除燕乐伎外,皆可在继承隋制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其在实践中的重要性直接表现在演奏频率上。综观九部伎在唐的演出记录,确在高祖与太宗时期最为密集。实践中九部伎并不适用于不能包含娱乐音乐的祭祀仪式用乐,却非常适合具有礼娱双重性的宫廷宴会。故而史料中九部伎在宴会中与撞球、舞剑、绳伎等散乐,以及后来收入立部伎之五方狮子舞或太平舞同列。(37)〔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百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01—1303页。也在高宗显庆五年与总章元年两次非元会设宴中称“奏(设)九部乐,极欢而罢”,直接说明了很多九部伎演奏场合的娱乐性质。(38)同注②,第1306、1307页。从演奏场合来看,宴请蕃国君臣是九部伎的主要功能之一。而在《开元礼》另两篇宴请蕃国君臣的仪式文本中,却在仪式制度上完全没有提及九部伎,也没有在文末注明“如元会仪”,反而通过雅乐乐队与乐曲的不同安排,与元日宴会中的雅乐制度共同反映出宫廷仪式宴会的结构与层级。
(一)皇帝宴蕃国主
在《开元礼》的五礼分类中,相对于篇幅宏大的吉礼和嘉礼,宾礼、军礼与凶礼内容较少。而三者之中,又以只有两卷的宾礼内容最少。宾礼第一卷主要包括的是宴会前的接待礼仪:迎劳,即于都城之驿馆或郊外迎接外国君臣的欢迎仪式;遣使戒见日,即使臣去藩国君主下榻的鸿胪馆或其他驿馆告知朝见皇帝的日期;藩主于太极殿朝见皇帝。藩国使臣上表及进贡的迎劳、戒见日环节亦同前述。(39)对上述宴会前的几种礼仪研究,文本校勘及注释见尹承:《〈大唐开元礼·宾礼〉新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3辑,第146—173页。诸礼仪环节的研究及阐释见王贞平:《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10—46页。其宴会设计基本遵照元日宴会的礼仪流程,不同于元日、冬至朝会多举行于太极殿,或含元殿,宴请蕃国群臣或使节的场所众多,并不固定。宴会开始前,登歌与乐悬的位置摆放与元会礼仪相同。太乐令依旧将登歌乐队中的编钟、编磬各一架摆放于殿上,乐悬四面摆放于庭中,鼓吹令加鼓吹十二案于建鼓之外。皇帝入场仍是以击编钟上律高为黄钟的钟开始,后遍击黄钟钟之右边五钟。击钟完毕后,协律郎举麾,工人以此为信号鼓柷,整个乐悬乐队再开始演奏《太和》之乐,且同时位于建鼓之外的十二个鼓吹小乐队也与乐悬同奏。此句后以注文标明,凡是奏乐,均由协律郎举麾,乐工鼓柷为开始的标志,而以协律郎偃麾,乐工刮奏乐器敔为停止的标志。此注中的细节为元正宴会所不载。且此条中明确地将协律郎举麾的步骤置于撞钟之后,也是元正宴会所没有的细节,清楚地说明协律郎举麾所开启之乐是雅乐十二和之一的《太和》,而并不包括之前的击钟。在蕃主入殿门,行至乐悬南之等候位置期间,奏《舒和》之乐,而无之前的击钟之礼。在此位置,蕃国主及其国诸官要完成献壤奠的仪式环节,即向皇帝献其土产风物。献贡完成后,通事舍人引蕃国主等登西阶入殿。作为入场环节的一个部分,乐仍应奏《舒和》,且奏乐止于西阶,众人拾级而上并不奏乐。与此同时,不升殿的官员、蕃客也分别走至廊下站立,等待典仪唱“就坐”后,与殿上众人同时就坐。至此,入场及献贡环节完毕。
宴饮开始前,太乐令引登歌工人,即演奏钟磬、琴瑟之乐工及歌者行至殿前阶下,脱鞋后登阶入殿。吹奏类乐器的乐工则面朝皇帝,站立于阶间,此项与元会无异。乐工就位后,尚食奉御依旧进酒于御前,皇帝举酒,同时登歌乐队演奏《昭和》之乐,三遍而终,此处乐队从乐悬到登歌的转换与元会一致,登歌工人演奏完毕,须出殿离场。故而紧接着以《休和》之乐伴随皇帝吃饭始终的,并非登歌乐队,而是殿庭中之乐悬。尚食奉御、太官令分别撤走皇帝与蕃主及官员的食案,开始行酒,此时文、武二舞按照次序进入乐悬内表演。若有赐酒环节,亦与表演同时。至此宴饮环节结束。
退场环节与元会仪同。蕃国主行,乐作,出门乐止。据前文,此处应亦奏《舒和》之乐。皇帝起,太乐令使乐工击蕤宾之钟,而后以编钟上蕤宾律钟之左五钟以次应。据前文细节,协律郎此时举麾,乐悬演奏《太和》之乐,同时建鼓外之鼓吹十二案同奏。在宴会结尾部分,宴蕃国主与元日朝会最显著的不同,即并无“若设九部乐”一条。
(二)皇帝宴蕃国使
《皇帝宴蕃国使》在《开元礼》与《通典》中的叙述皆比上篇宴蕃国主简略,《通典》在收录时更以“余与宴蕃国主礼同,皆仿上仪”结束全文。而仔细对比二者,仍有几处重要差异,直接说明了宴会礼仪用乐的标准与等级,也间接反映出娱乐音乐在不同等级宴会中的需求与空间。相比于前两篇,皇帝宴蕃国使的仪式宴会既不是政治上最为重要的,也不像元会具有仪式上的示范性。但这一篇中对仪式音乐的详细记录,反映出等级从高至低的宴会中仪式性渐弱的趋势。在本篇宴会前陈设环节,太乐令设宫悬乐器于殿庭,以及两个协律郎举麾位,紧接着注明不是所有蕃国使者都如此陈设,只有大蕃大使、中使,以及小蕃大使才设乐。这里的“设乐”是指宫悬乐队,而不包括鼓吹十二案,因为在太乐令设宫悬后并无鼓吹令设十二案之文,且后文叙述中无涉鼓吹十二案,故这里并非省略,而是不设殿庭鼓吹。陈设就绪,太乐令率乐悬乐工以及文、武二舞的舞者入场等候。
宴会入场环节,除以下几处外,大体与前两篇一致。其一,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后标注,若不设乐,则改换常服。不设乐对应之前的蕃使等级,其设乐亦指乐悬。其二,在“奏太和之乐”一句后没有如元会仪和宴蕃国王仪一样紧跟“鼓吹振作”,也说明此等级宴会不设鼓吹十二案。其三,不像元会礼仪中先叙述整体的礼仪过程,后补注乐之起始,或直接省略。这个部分完全按照音乐起止的准确节点叙述,进一步证实了前文对元会中音乐起止的分析,使音乐与仪式的配合细节更加清晰。
宴蕃国使在音乐使用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宴蕃国使不设登歌,在元会和宴蕃国主仪式中本应由登歌乐队演奏的环节,并不设乐,只记太官令行酒、设食案。同时亦省去了皇帝举酒、皇帝饭这两项与登歌奏《昭和》、乐悬奏《休和》同时出现的仪式性环节。太乐令引文舞、武舞舞人入乐悬内表演,与元日仪和宴蕃国主仪一样,对应的是饭后行酒环节。在宴会尾声的退场环节中与宴蕃国主一样,此篇末也不记设九部伎之事。
综上,作为宾礼制度的两种宴会均使用雅乐,且均不注明九部伎的演奏。结合九部伎频频用于宴请外蕃君臣的记录,说明在外交宴会中的九部伎并没有作为礼制的仪式音乐被详细记录于礼典。两种宾礼宴会与元日宴会共同反映出一个层次分明的唐朝仪式宴会体系,并以仪式与音乐配合的细节展现出音乐在这个体系中的重要功能。元日宴会是其他宫廷礼仪宴会的范本,其音乐使用最为全面。而从政治意义上,元日宴内外兼具而更强调对内,宴蕃国主是对外的最高等级宴会,故其仪式音乐安排基本与元会无异。而宴蕃国使则充分展现出音乐在宴会等级及其礼仪性程度上的区分功能。所有对蕃国使的礼仪宴会均不设殿庭鼓吹与登歌,乐悬也只在宴请大蕃大使、中使,以及小蕃大使时使用。可见,这些礼乐所不及之处便可由娱乐音乐补足。不同宫廷宴会本身具有的双重性质,本就此消彼长,无法割裂。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先一日,金吾引驾仗北衙四军甲士,未明陈仗,卫尉张设,光禄造食。候明,百僚朝,侍中进中严外办,中官素扇,天子开帘受朝。礼毕,又素扇垂帘,百僚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充庭考击。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闲廐引蹀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若《圣寿乐》,则回身换衣,作字如画。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4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1页。
上文精准地体现出宫廷宴会的双重性质,弥补了《开元礼》侧重仪式音乐而其他史料中常以娱乐音乐为重的不足。在简略的叙述中,宴会前的陈设与准备虽不如前文三种宴会制度详细,但明显是依礼而行。音乐包括太常卿所引雅乐,以及坐、立部伎与舞马等两个部分,清楚区分了仪式与娱乐音乐的功能。正是由于宴会礼仪与娱乐的双重属性,以及九部伎自唐祚初始以来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使元日宴会将九部伎作为音乐选择之一纳入礼典。但是在不同等级的仪式宴会中,雅乐通过乐队的种类、音色特点与丰富程度、以及不同的表演形式建构出一个重要性与仪式性层层递进的宫廷仪式宴会体系,并在制度性的重复中不断加强其仪式意义。这种功能上的层次与精巧,是仪式环节与曲目缺乏固定搭配、不同乐队间缺少明确分工,且因顺序演奏无法以重复性标识同类仪式环节的九部伎无法完成的。
结 语
以上三个部分共同说明了九部伎在元日宴会中仪式功能受限的原因,及其入礼典的可能缘由。第一部分基于《大唐开元礼》嘉礼之《元正、冬至皇帝受群臣朝贺并会》,详细分析了元日宴会仪式音乐在各个环节的演奏详情,展现出其标识与推动仪式进程的重要功能。此功能以不同仪式环节固定搭配特定乐队或乐曲形成的仪式意义为基础,实现于每一次现场演奏中乐曲与仪式环节的同时起止。这种固定搭配不仅表现在同一宴会仪式中,如皇帝出入时击钟、《太和》、以及鼓吹十二案的相同安排;也印证于不同宴会仪式中相同环节的音乐复现,如元会及宴蕃国主均以文舞二舞和《休和》之乐伴随正式宴饮环节。
基于以上元会仪式的音乐特点,第二部分从九部伎以乐队为主,曲目为辅的制度特点出发,从九部伎曲目的隋唐变革、唐九部伎曲目详情的缺失、以及参考同时期二部伎于宴会表演前才确定所奏曲目几方面,说明九部伎曲目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元会仪式文末只记“九部伎以次作”,而缺乏具体曲目详情的情况互相印证。这与第一部分中稳定的雅乐曲目及其与仪式的固定连接形成鲜明对比,从中反映出九部伎难以在与仪式的有机结合中分享仪式意义,故而无法如雅乐般复现礼乐精神。
礼典文本之外,丰富的九部伎演奏史料显示,宴请蕃国君臣的宴会是九部伎的重要演奏场合之一。其记载常与各类型的散乐并列,亦称此宴会“奏九部伎,极欢而罢”。这些材料中凸显的九部伎之娱乐属性应是《开元礼》之宾礼两种宴会仪式文本中九部伎缺席的原因之一。第三部分即以《皇帝宴蕃国主》与《皇帝宴蕃国使》两篇仪式文本为基础,一方面说明两种宴会中仪式音乐均用雅乐,而并未将在宴请蕃国君臣相关史料中频繁出现的九部伎作为仪式用乐纳入制度;另一方面结合元会用乐,分析不同音乐在三种宴会中仪式功能的强弱。在元日宴会中,雅乐与九部伎作为仪式中的音乐,却在仪式功能的强弱上迥然不同。
在同一宴会的不同仪式环节,以及不同的仪式宴会中,雅乐曲目、乐队与仪式环节有相对稳定的连接,在对仪式的标识和推进中实现仪式意义的共享。这种立体多层次的仪式功能对于礼乐制度构建是有积极意义的。而目前材料中呈现出来的九部伎以乐队制度为主,唐以后的曲目详情记载模糊,再结合其单一的顺序演奏方式,在元日宴会中呈现出平面简单化的仪式功能,难以企及雅乐在仪式功能上的层次与精巧,故而无法在相同的意义上复制雅乐对礼乐制度的结构性贡献。所以九部伎被纳入元日宴会制度,更有可能是宴会礼娱双重性与唐前期九部伎在实践中的重要性所共同推动的结果,九部伎在元日宴会中所发挥的仪式功能有限,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元日宴会的仪式性。以上即为音乐在唐礼乐制度构建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