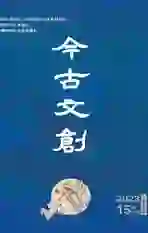《剪灯新话》中的幽冥地府
2023-05-31王汉昆
王汉昆
【摘要】《剪灯新话》中的幽冥地府是富于情与理的正义之所,它显现与执行着“天理”,并寄托着朴素的“人情”。幽冥地府本质上是作者内心理想政治世界的体现,映射着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文人哲学心理,是较为主观的产物,因而自身也带有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
【关键词】《剪灯新话》;幽冥地府;天理;文人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5-001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5.003
《剪灯新话》一书由瞿佑青年时期写就,并在老年时于流放之地重新校对,这段时间是很长的,可以说,最终完成的这部短篇小说集在相当程度上凝结着瞿佑一生的哲学理念与道德情操。他“生值元末兵燹间,流离四明,岌乱姑苏”[1],战争的离乱与末世政治的黑暗倾颓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现实世界无可指望时,愤郁悲痛的情感只能以想象的方式宣泄在其他地方,书中所建构的“幽冥地府”作为其中一所,便处处体现着瞿佑心中的理想范式,这种理式既是以他为代表的文人理想的寄托,自然也是他奔波而不得志的反映。
一、富于“情理”的正义之所
《剪灯新话》中的幽冥地府,主要之处在于惩恶扬善、彰显公正,现实政治难以达到的公平,在虚渺的地府中从不缺席。但值得注意的是,地府在面对一些令人唏嘘的人情世故中,也有着相当的宽限,宽容与雷厉并为其特点,这种矛盾实质上是瞿佑文人心理的主观外化。
(一)“天理”的显现与执行
在瞿佑构建的外世政治体制中,“天府”与“地府”是紧密连接的,提到“地府”,必须首先剖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牡丹灯记》中有一段话明了地揭示了瞿佑的理念:“降祸为妖,兴灾作孽。是以九天设斩邪之使,十地列罚恶之司,使魑魅魍魉,无以容其奸;夜叉罗刹,不得肆其暴。”[2]这里提到的“魑魅魍魉”“夜叉罗刹”显然不仅仅是鬼物的名词,而是一种“恶”与“暴”的象征,由此观之,“九天十地”的设立,本质上是为了惩治妖孽、彰显正义。但这种“正义”究竟为何物,如何判断与分辨?瞿佑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释,但观其书中所作,似乎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天府”与“地府”所展现的标准,即“天理”。
在瞿佑的心目中,“天府”与“地府”是有着等级区分的:“天府”的等级要高于“地府”,上者“九天设斩邪之使,十地列罚恶之司”,天在地先,实际已经说明了尊卑的顺序。最能体现这一等级的篇目是《太虚司法传》,冯奇饱经鬼怪折磨,临死却说:“我为诸鬼所困,今其死矣!可多以纸笔置柩中,我将讼之于天。数日之内,蔡州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时也,可沥酒而贺我矣。”[2]经历了非人的折磨与摧残,什么地方能真正让自己沉冤得雪?冯奇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天府”而非“冥司”,瞿佑笔下的“冥司”,其实也是恪守公平的,前有《令狐生冥梦录》篇,载令狐生言之有理,亦是冥司断案还其清白,足见冥司之正,然而即便如此,冯奇也必要“讼之于天”,可见天府之威严。
当了解地府严明背后的本质,瞿佑所代表的儒家传统人格便呼之欲出:“天理”在冥司判案中很大一部分的展现,我们今日看来,不过是儒家文化的老生常谈。瞿佑最看重的“理”,是爱国保民的儒家政治观,《永州野庙记》中假作神明的白蛇被诛之因便是“以威祸恐人,求其祀飨,迫此儒士,几陷死地,贪婪苦虐,何所逃刑”[2],不仅残害百姓,还要逼迫儒士,自然难逃制裁;《令狐生冥梦录》中“毒虺噬其肉,饥鹰啄其髓,骨肉糜烂至尽。复以神水洒之,业风吹之,仍复本形”[2]的秦桧,在瞿佑的眼中,是误国误民、十恶不赦的大奸大害,故有此刑罚。对“国”与“民”的重视,自然是儒家兼济天下哲学理念的最终表现。此外,冥司断罪之时,也特重贞洁观念。《令狐生冥梦录》中的偷情男女要“有夜叉以刃剖其胸,肠胃流出,以沸汤沃之,名为洗涤”,原因即是男医生“因疗此妇之夫,遂与妇通”;与其相对,《爱卿传》中的罗氏却因“冥司以妾贞烈,即令往无锡宋家,托为男子”,足见瞿佑对贞洁观念的重视。还有一些小处能够体现儒家的坚持与矛盾,《令狐生冥梦录》中的酒肉和尚被冥司“以牛马之皮覆之,皆成畜类。有趑趄未肯就者,即以铁鞭击之,流血狼藉”[2],他们被惩罚的理由,不单有不守戒律,还有“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耕织”的观念自然是儒家政体下小农经济的体现,但僧尼本以化缘、供奉为生,这却也是僧尼的传统,瞿佑在这里却以此作为刑罚之因,明晰地体现出他“尊儒贬佛”的理念。然而,《爱卿传》中却讲罗氏因贞烈被转世“托为男子”,“转世”一说并非中国本土的哲学体系,而是受佛学轮回观的影响,瞿佑在这里却不避讳夷夏之异,直以轮回为男作为对贞洁女性的赏赐。这种矛盾是值得玩味的,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瞿佑在区分佛、儒两家差异时,并非着眼于本质的深层哲学解释不同,而是着眼于二者对现实人生的作用,即便化缘本是佛家传统,但因其在行为上的“不劳而获”、对现实毫无作用,便应得惩罚;妇女贞烈,既然轮回为男能体现儒家伦理上的“善报”,便让她转世也未尝不可。这种“天理”,实际上是“儒理”,“天府”与“地府”要彰显的理念,即是儒家范式的理念。
(二)“人情”的赞许与寄托
《剪灯新话》中所着重展现的“天理”,或许于当时战乱背景下有一定意义,但于文学则稍显迂腐,倒是瞿佑在幽冥描绘中的一些支离琐碎的片段,渗透着不俗的“人情”,这种人理体现为对“约”与“情”的重视。
书中直接有关幽冥之情的篇章共四篇:《金凤钗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爱卿传》,这四篇的结局于瞿佑的情感觀念各有体现。《爱卿传》中罗氏的贞烈自不必说,这是儒家赞扬的伦理,结局必定是好的,值得注意的是《金凤钗记》与《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两篇。吴兴娘因不见崔郎,郁郁而终,然而死后还能还魂助其娶妹,并说:“妾之死也,冥司以妾无罪,不复拘禁。得隶后土夫人帐下,掌传笺奏。妾以世缘未尽,故特给假一年,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因缘尔。”忧郁而终,自然无罪,不加以拘禁是应当的,然而兴娘却能在后土夫人帐下掌事,并被许假一年,从任何角度看,这都像是一种赏赐,可赏赐的缘由在何处?唯一的解答便是深情。与此相仿,《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中的卫芳华本是魂魄,还能与滕穆欢好,分别之时,芳华讲到:“妾非不欲终事君子,永奉欢娱。然而程命有限,不可违越。若更迟留,须当获戾,非止有损于妾,亦将不利于君。岂不见越娘之事乎?”分开是必须的,因为“程命有限”,但冥司却对其与阳间私通之事未加追责,反观《牡丹灯记》中的符丽卿,同是鬼魂通阳,却被塑造成一个好色伤人之女,最终被打入地狱,两者的差别可谓天渊。
究其原因,造成这种差距的其实是瞿佑所寄托的“情”有一定的框架——“約定”。《金凤钗记》中的兴娘,早在幼年时便已与崔郎许下婚约,之后因为崔郎久久不归而死,这种“约定”被破坏了,因此兴娘必要“续缘”;《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中的芳华“特以与君有夙世之缘,故冒犯条律以相从耳”,也是约定未尽,故特意再续前缘;反观《牡丹灯记》中的丽卿,本与乔生毫无瓜葛,却以鬼蜮之体尽阳间之欢,这就不被瞿佑所允许了。在作者的观念中,有缘分与约定的“情”才是“深情”,是值得赞许,至少不应被批判的,并且通过文章的结局,不难看出瞿佑在作文中有意地给予未完成的约定一个具体的交代:约定终有完成的一日,这似乎是作者的内心写照。
对约定的向往与坚持,恐怕与瞿佑自身的经历不无关联。《秋香亭记》一篇经过历代学者研究,其为瞿佑自传基本可成定论。商生自小便被告知“吾孙女誓不适他族,当令事汝,以续二姓之妾,永以为好也”,遂与采采“倍相怜爱”,后却逢高邮战乱起,遂绝音信,后得采采书云:“倘恩情未尽,当结伉俪于来生,续婚姻于后世耳!”约定未成,不得不说是瞿佑一生之憾,据李建国、陈国军先生考,采采之后,瞿佑与安荣坊倪氏女也有一段情感,并“相送出门留后约”,然而倪氏最终也嫁与他人,这一约定终究又只是一汪春水。自身情感的缺憾外化到笔下,是十分正常的,既然自己的约定永不能实现,便让书中的有情人终能相见,并了结尘世的缘分,这便是瞿佑对“约定”与“深情”的向往,这种“人理”在理论上是否符合“天理”,按照宋代以降的理学看来,似乎是不妥的,但是这种哲学上的辨析对于瞿佑来说无足轻重,仍旧是上文提及的,《剪灯新话》中并不在意深层哲学的思考,地府的施政理念只是作者本人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范式、对一些事物的具体认知与自身情感的宣泄。
无论如何,对“人情”的描绘是这本书中相当具有文学价值的贡献所在,或许瞿佑在写作时仅仅是为了弥补情感的缺憾,但无心插柳,这本书虽然被禁,却于文士之间人人传诵,书中对“情”的感叹,也必然以许多方式影响了后世的文学。正因如此,《剪灯新话》中的地府形象才能在一定角度上显得颇为滑稽:与学究式的严格的儒理规范相交织的,是自宋代理学以来并不被提倡的男女情感,即便这种情感被限定在约定的范畴之内。由此观之,瞿佑笔下的幽冥地府,并非完全公正,它实在是带有一些“人情味”的。
二、文人观念的映射与矛盾
幽冥地府的形象也好、理念也罢,实际上皆出于瞿佑本人的想象与道德哲学观念,整个地府及其所属的种种皆是作者观念的映射,并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一批不得志文人的希望。自然,这种观念的映射以儒家思想为本,又因为瞿佑并未系统地考量过深层的哲学逻辑,因此也与“理”与“情”一样,呈现出一定的矛盾。
(一)现世文人地位的重构
《剪灯新话》中对地府众物形象的描绘显然以人间实物为蓝图:“见大官府若世间台、省之状”“駃卒引立大庭下,望殿上挂玉栅帘,帘内设黄罗帐,灯烛辉煌,光若白昼。严邃整肃,寂而不哗”[2],基本是人间官府的影响,不单形象一致,还要“光若白昼”,丝毫没有固有观念中的阴森之感。宫殿既然一致,人物群像也必然有尊卑等级,从整本书中来看,可以分为四种:
排在首位的是崔君,即所谓“王者”。《永州野庙记》载:“应祥还家,白昼闲坐,忽见二鬼使至前曰:‘地府屈君对事。即挽其臂以往。及至,见王者坐大厅上,以铁笼罩一白衣绛帻丈夫,形状甚伟。”[2]这里的“王者”便是崔君,崔君即崔珏,对他的崇拜当起于隋朝,后流传愈广,元代关于崔君的祭祀在民间有所流传,但未见《元史·祭祀志》中有详细记载,应是囊括在“凡名山大川、忠臣义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3]的名山大川忠臣义士祀典中,并非大神。然而到了瞿佑笔下,崔君便成了“王者”,无论是“被冕据案而坐”,还是阴司司长所说“昨县神申上于本司,呈于府君,闻已奏知天庭,延寿三纪,赐禄万钟矣”,都表现出崔君在瞿佑笔下于冥府的至上地位。
崔君之下,便是有司、判官一类形象。《令狐生冥梦录》中,令狐生“见殿上有一绿袍秉笏者,号称明法。”《富贵发迹司志》中,“有判官数人,皆幞头角带,服绯绿之衣,入户相见,各述所理之事。” [2]这些形象都是断案判官。《永州野庙记》中另有一种:“俄一吏朱衣角带,自内而出”,是传话者形象。他们受命于崔君,掌管各地事物。
有司、判官一众以下,便是穿梭于阴阳之间的使者,到了这一形象,文人的特征便消失殆尽了:“忽有二鬼使,状貌狞恶,径至其前”“应祥还家,白昼闲坐,忽见二鬼使至前曰:‘地府屈君对事。即挽其臂以往。”[2]“径至”“挽其臂”,都不像是接受儒礼教育的文人所作之举动,这些鬼使不但不守礼仪,更“状貌狞恶”,似乎不仅仅是礼数,连“人”的外貌特征都不太符合了。
鬼使以下,便是魑魅魍魉、夜叉罗刹之类。这些鬼物可以为阴司所用,但阴司的另一部分职责,便是“使魑魅魍魉,无以容其奸;夜叉罗刹,不得肆其暴”,实际上对他们的态度是管理大于任用。
对上述四种形象进行观察,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无论崔君还是下属判官、传话,都是文士的形象,文人在地府中的位置是毫无疑问的上位者,他们不单单清正法度,还规范着下层的“非人”鬼物。这其实是儒家政治理念的体现,如果没有信仰“天理”的儒生文人坐镇,“天理”就不能得以彰显,也就更不谈什么公正严明,这种理念,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代表文章便是《太虚司法传》。这篇文章讲述狂人冯奇路途中的种种异事,整篇故事里,所有鬼怪的形象皆是凶恶残暴,并无一点“理”,这并非与森然严正的地府形象冲突,这恰恰是瞿佑观念的表现:鬼怪本是鬼怪,并无善良可言,地府之所以能够惩恶扬善,是因为掌管地府的儒人掌握绝对的权力,能够强制统摄鬼物,而地府所听命的天府,其统治者自然完全是“天理”的具象了,万事万物的理念,归到本原上去,都应该遵从儒法,因此文章结尾,正是天府知道了冯奇之冤,这些不在府司统摄下的鬼蜮才都被“夷灭无遗”。
第二,上文提到,崔君在瞿佑的笔下统治着地府,但在现實当中,他仅仅是地方有声望的神灵。崔君以下的判官,或“绿服”,或“绯服”,《元史·舆服志》载:“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一品紫,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小杂花,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绯罗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绿罗,无文。” [3]这些判官在地府中的地位甚高,然而类比到现实世界,最多是六品之下,大多是八、九品官员的穿着,这样看来,瞿佑笔下地府的建制是依照地方政府所作,并非中央政府。这种架构是颇耐人寻味的。作为当时的文学名人,兼受杨维桢、凌云翰几位名士赏识,说瞿佑不懂基本的服饰制法,恐怕过于武断,则瞿佑笔下的“天府”才是朝堂,“天府”之下的“地府”,正是朝堂之下的地方,这种推测似乎较为合理一些。按瞿佑的生平经历,他在“洪武十一年 (1378) 释褐入仕,出任仁和县县学训导,当时三十二岁。”[1]32岁才真正步入仕途,并仅是一位训导,此后历年不得志,被流放保安之后,还是赖英国公说情才得以回归中土,瞿佑一生亲身的仕途,都与“大员”关联不大,在亲眼目睹地方政府同流合污、贪赃枉法之后,他心中的愤怒是更加真实、深刻的,不同于上层的虚无缥缈,他完全可以用笔墨改写出一个理想的自身生活环境,化在笔下,便是以地府为代表的理想地方政府的建构。瞿佑本身作为文人,自然也在“统治者”的范畴,领导人的英明神武加上下属的尽职尽责,这或许就是瞿佑最为憧憬的社会,他的志向并不远大,社会果真如此,他就算做一个“绿袍持笏”者,不做其上的“王者”,也是一定能够安然处之的。
(二)公正之外的“特权”
瞿佑所塑造的地府是否是“绝对公正”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可以作解:瞿佑笔下的“公正”,是未经深刻思考的“公正”,这种“公正”带有他自己的希望,例如对“情”的网开一面,它是一种主观的文人式的体悟,从这个角度看待所谓的“公正”,其实仅仅是普罗不得志文人的憧憬生活,本质上与《聊斋》塑造的瑰幻世界并无差别,这不是“公正”,而是“理想的公正”。按照书中的叙事逻辑所展现的作家理念来看,可以将瞿佑理想的世界简要地分为三个阶层:一是清正有为的文人阶层,这一阶层应当掌握绝对的权力,恪守儒家规范,明断事理、造福百姓;二是普通人阶层,这一阶层有少数可以上升到文人阶层的大众,但更多的是普通百姓,文人阶层对他们的生活与不平负有责任;三是作恶阶层,这一阶层应当受到文士阶层的惩罚裁处,文士阶层的存在就是为了消灭它。毫无疑问,瞿佑认为自己理应是文士阶层,理应与清正有为的同僚一起工作。与很多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构建相同,瞿佑的这种想法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处于文士阶层的人必然谨遵“天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作出错误的事情,如此一来,只要文士阶层内部同意,且对普通人没有影响,任何事情的决策都无须经过严格的程序,换句话说,能够制约文士阶层权力的,不是法律,而是绝对正确的“天理”。
这种观念在《修文舍人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修文舍人传》讲儒生夏颜不得志而死,后被冥司录用,遇友人而叹:“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然后官位可居,爵禄可致,非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攫取也。”[2]然而友人遇疾后,夏颜却对他说:“仆备员修文府,日月已满,当得举代。冥间最重此职,得之甚难。君若不欲,则不敢强;万一欲之,当与尽力。所以汲汲于此者,盖欲报君镂版之恩耳。”[2]这就显出此间矛盾:既然冥司用人如此精当,何故冥间如此重要的职位,只需夏颜一人“尽力”即可?而夏颜尽力的原因又是“报恩”,这不正与“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相冲突吗?对于这一矛盾,赖利明先生曾给出解释,他认为“作者似乎在借鬼界给读者也给他自己描述一个理想的社会,但在他的叙述之下,一切又似乎给作者自己瓦解了。留给读者,留给他自己的还是灰暗人生和不可捉摸的社会”[4],是一种“反讽”的艺术,也可备一说。但其实夏颜的做法按照瞿佑的理想观念,是完全能够解释得通的。瞿佑笔下的冥司以“天理”作为施政核心,又因其特殊的幽冥位置,实际上具有“全知”的视角,夏颜可以被选擢提拔,说明他已经具有冥司的认可的理念,至于如何提拔、经过何种程序,这是不重要、也是不需要的。因此,当夏颜真正地加入到冥司的行列中去,必然隐含着他已经纯然践行“天理”的潜在条件,他通过“举代”的方式举荐友人,在瞿佑看来并无任何不妥,这便是一种他笔下文人阶层的“特权”:天庭与地府的统治阶层并不会犯错,因为信奉着“天理”,他们做的事情必然正确,他们选拔的人才必然精准,不需要监督与纠错。由此观之,夏颜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至于文章为何提到夏颜如此做是为了“报恩”,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瞿佑为了展现夏颜的儒者道德而已。
三、结语
综观整本《剪灯新话》,书中塑造的幽冥地府形象俨然是儒家伦理范式的具象化,是作者内心主观理想政治世界的体现,从哲学角度讲,它是比较平淡的;从逻辑角度讲,它也未经过系统深入的思考。然而,文学作品的主观性正是其价值所在,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单纯的憧憬,“情”与“理”才能够在《剪灯新话》中交织辉映。
参考文献:
[1]李建国,陈国军.瞿佑续考[J].南开学报,1997,(03).
[2](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赖利明.《剪灯新话》言鬼述异的叙事谋略[J].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