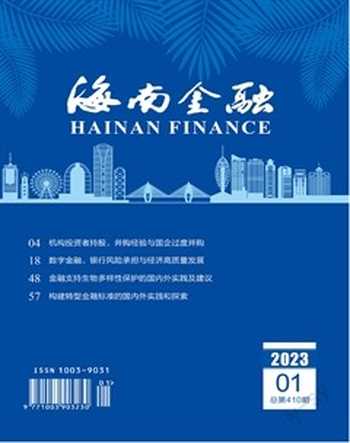证券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判定:美国范式与中国启示
2023-05-30汪伟
摘 要:一般而言,市场决定损失,司法系统分配损失。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当中,因果关系的证明,需要往返穿梭于哲学范畴、法律文本与案件事实之间。借助美国二元划分方法,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被划分为交易型与损失型。前者旨在全面确定可归责的损害事由,后者力图避免因果关系链无限延伸。最高人民法院《新虚假陈述规定》吸纳了欺诈市场理论,破除了概括式因果关系的举证难题。在发行注册制背景下,我国应优先运用“证券价格测试”对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重大性”加以判断,同時辅以“投资决策测试”作为兜底性考察工具,此外也要对因果关系链中的揭示标准加以明晰,合理拓宽可抗辩风险的情形,真正发挥因果关系在虚假陈述判定中的纽带作用。
关键词:证券欺诈;虚假陈述;因果关系;欺诈市场理论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3.01.007
中图分类号:D922.287;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23)01-0078-09
一、引言
2022年初,最高人民法院以美国判例法为镜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虚假陈述规定》),首次将因果关系的双重判别方式作出了严格区分。其中,在交易因果关系的认定中新增了诱空情形以及抗辩事由,在损失因果关系的认定中新增了内外部风险的阻却事由。此外,《新虚假陈述规定》取消了民事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促使“重大性”问题成了因果关系证明中不言自明的焦点。但如何在实践中落实因果关系的信赖推定方法,如何确定虚假陈述中因果关系的“重大性”标准,以及如何判定因果关系链中的揭示标准和可抗辩风险,成了当事人主张证券欺诈索赔以及法官审理证券集体诉讼案件的一大难题。事实上,传统的因果关系要素源于侵权法中的欺诈与虚假陈述行为,它因为能够揭示现实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某种联系,而成为当事人主张损害赔偿的基础要件。根据美国侵权法体系,因果关系能够划分为事实型与法律型两种类型。事实因果关系旨在逆向探寻客观上的事理成因,而法律因果关系重点针对原因力作出法律判断。相应的,在证券虚假陈述领域,因果关系也能够被划分为交易型与损失型两种类型,前者旨在证明经济损失确实存在,而后者力图避免因果关系链无限延伸。
当前,正值我国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推进发行注册制改革、稳步落实《金融稳定法》实施的重要战略节点,我国亟需借鉴美国证券虚假陈述的规制经验,完善证券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新规,稳步构筑证券市场行稳致远的“四梁八柱”。
二、美国侵权法因果关系的二元判别
(一)侵权因果关系的二元范式
抽象因果关系的证明,需要往返穿梭于哲学范畴、法律文本与案件事实之间。因而有学者感叹,因果关系经历过不加批判的奉承阶段、完全否定阶段,以及务实的利用阶段,是科学哲学发展史下的一个脆弱概念。在美国侵权法当中,因果关系的证成通常需要经历两个步骤:其一,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侵权与损害存在某种客观的事理成因或联系。其二,证明侵权致损事件中的联系不至于太过遥远。该证成步骤其实是以二元划分的思路,将侵权行为法中的因果关系分成了两类范式。前一类范式称之为事实因果关系,是一种不考虑法理政策,而仅以客观上促成损害发生作为归责缘由的机械性范式。后一类范式称之为法律因果关系,是一种基于介入因素考量,排除因果关系链上原因力无限延伸的政策性范式。从本质上来看,事实因果关系旨在客观确定可归责的损害事由,而法律因果关系旨在限制不合理的归责事由过分地加重被告负担。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事实因果关系的阐析不可能完全脱离主观上的经验判断与常识运用。
(二)事实因果关系判别:若非法则
事实因果关系根植于案件本身且依赖于经验查明,若非法则(But for test)是判别事实因果关系的必要手段。作为一种经典性假设,若非法则可以表述为:如果没有被告的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将不会发生。换言之,如果抽离了侵权行为后原告仍会受损,则案涉侵权行为不具有原因力。因此,若非法则其实是对损害结果的一种“反向调查”(Counterfactual Inquiry)。但它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理由是若非法则将陪审团的注意力从“发生了什么”转移到了“可能发生了什么”的猜测上。此外,若非法则也无法适用于污染、儿童色情、恐怖主义融资等某些非典型的“边角案例”(Corner Case)。尽管若非法则存在一些固有缺陷,但它仍是迄今为止最佳的判别方法之一,法院在裁决纠纷时,仍然会习惯性地作出假设性追问。从根源上来说,若非法则之所以会被视为判别事实因果关系的真理,是因为它让道德和政策都不足以强大到使无过错的被告承担损失,阻止了审理事实的诉讼活动转变为对被告道德的一般性考察。
(三)法律因果关系判别:多重测试
法律因果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事实因果关系必须要被合理限定。换言之,即便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受损的事实原因确为被告的过错行为,但只有当该过错行为是“近因”(Proximate Cause)而不是“远因”(Remote Cause)时,被告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强制要求被告承担过于遥远的后果,既不符合道义宗旨,又有悖于法律精神。对于法律因果关系的确定,美国司法实践通常会采用可预见测试、连续测试、实质因素测试、异常结果测试等多重测试标准。其中,可预见测试要求被告仅需对一个理性人能够意识到的风险或可预见的损害承担责任。连续测试强调任何实质有效的干预性力量或替代性因素都能够合法地免除被告责任。实质因素测试则将可归责的侵权行为限定为能够实质上产生后果的行为。而异常结果测试旨在排除任何荒谬的、疑惑的以及无法确定的行为。尽管这些测试标准并不能判别物质世界中的所有复杂因果关系,但它们依然能够公允、准确、简单地适用于大部分案件,并将法律世界中的损害与修复相连起来。
三、信赖导向:美国虚假陈述的交易因果关系
(一)虚假陈述的交易因果关系规定
在英美法系中,虚假陈述的交易因果关系通常只涉及因果关系的事实分析。因此,许多法院将交易因果关系类比为“若因”或者事实因果关系①。美国关于证券虚假陈述的交易因果关系规定,主要分布在《证券法》《证券交易法》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的10b-5规则当中。其中,《证券法》第11条(a)款是针对注册登记书中的不实陈述和隐瞒情形所作的专门规定,第12条(a)款是针对招股说明书、口头协议中的重大误述和遗漏情形所作的专门规定。这两款规定均未要求原告证明自己对虚假陈述产生了信赖,而仅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虚假陈述是重大的即可。与《证券法》规定不同,《证券交易法》第18条(a)款规定,主张重大虚假陈述或误导性陈述的原告还需要对自己信赖注册声明进行举证,以此排除原告恶意发起证券欺诈索赔。相应的,被告也能通过证明投资者早已知悉虚假陈述或虚假陈述不够重大,从而推翻交易因果关系。
除成文法以外,SEC颁布的10b-5规则中也规定了证券虚假陈述的交易因果关系。作为《证券交易法》第10(b)条反欺诈条款的重要执行机制,10b-5规则因为能够广泛适用于SEC所禁止的全部证券欺诈行为,而被称之为“长臂条款”(Long-arm Provision)。并且,它也一直被视作联邦证券监管体系中最有力和最万能的投资者保护工具。其中,对于虚假陈述的规定集中体现在10b-5规则的第2款上,即“对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地实施的重大误述、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均属非法”。虽然该条款并未直接明确虚假陈述活动中交易因果关系的成立要件,但在利斯特诉时尚公园公司案中,沃特曼法官首次提出信赖(reliance)是检验交易因果关系不可或缺的要素②。此后,信赖要素逐渐成为法院判定10b-5规则交易因果关系的重要标准。
(二)交易因果关系的信赖推定
在大多数证券纠纷案件中,交易因果关系等同于信赖。因此,美国法院要求原告通过证明信赖存在,从而确定交易因果关系。但在现代证券市场的集合竞价机制下,证券发行人向投资者作出欺诈性陈述并不依靠“面对面”交易中的经纪人、分析师等中介机构。这就为信赖的获取(即获得投资者对证券信息的主观定价)增设了一道障碍。此外,单独审查证券集体成员的信赖,无疑会挫伤证券集体诉讼的效率并阻碍诉讼程序推进。鉴此,美国在审判实践中创造出了信赖推定规则,用以减轻原告对交易因果关系的举证负担。其中,针对重大隐瞒的欺诈情形,可适用“可反驳的信赖推定”(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Reliance),而针对重大误述和误导性陈述情形,可适用欺诈市场理论。
“可反驳的信赖推定”源于犹他州附属乌特公民诉美国案①,其旨在解决原告无法证明重大隐瞒中的信赖要件问题。在该案中,两名雇员从毫无经验的证券持有人手中以低价买入证券并以市场价卖出,但未向原告披露二级市场上的真实交易价格。最高法院认为,在重大隐瞒型欺诈案件当中,要求投资者证明其交易决策依赖于被告隐瞒的陈述是荒谬的,因此,可靠的“信赖”证据并不是隐瞒型虚假陈述案件的必要条件。而后,下级法院普遍援引该案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信赖推定方法,以期合理分配信赖的举证责任②。但如果被告能够证明被隐瞒的信息并不会实质影响投资者决策,那么这种推定的信赖也能够被推翻。究其原因,符合立法意图和常识的司法推定方法,有助于实现公共政策目的、公平正义理念,以及司法经济追求。而可反驳的例外规定,能有效避免投资者以无关紧要的事由寻求恶意索赔。
欺诈市场理论是推定信赖要件成立的另一方法,其最早被应用于布莱基诉巴瑞克案③,而后在贝斯客公司诉莱文森案中被最高法院正式采纳④。最高法院认为,在一个成熟的公開市场中,即便投资者不直接依赖被告的重大误述或误导性陈述,这些重大的虚假陈述也会反映在公司的股票价格当中⑤。在有效市场假说与随机游走理论(Random Walk Theory)的支持下,该欺诈市场理论最终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并成功地推定了原告依赖有效市场的完整性对证券作出了准确定价。从本质上来说,市场将投资者据以依赖的信息以股票价格的形式传递给了投资者,客观上充当了证券投资者的“无偿代理人”(Unpaid Agent)。从功能上来看,欺诈市场理论弱化了原告对虚假信息的直接信赖,减轻甚至是消除了原告的举证负担,建立起了以重大陈述、有效市场和公开传播为要素的证券交易的因果关系链。但欺诈市场理论与联邦证券监管的信息披露理论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加剧了被告公司的诉讼负担与经济危机,致使损害赔偿变成了可疑诉讼中的不义之财。为确保良善的司法初衷不背离证券监管的根本目的,法院转而加强了交易因果关系的“重大性”审查。
(三)交易因果关系的“重大性”标准
证券虚假陈述涉及重要的投资决策信息以及琐碎多余的“噪音信息”,而金融司法实践中发展出的“重大性”标准是判断虚假陈述中交易因果关系的分界线。但表面上看似简单的“重大性”标准实际却是不可预测且难以捉摸的法律概念,其在解释与应用上存在广泛差异。如一些法院只是笼统地将“重大性”信息描述为非琐碎、非显而易见、非模糊性、非常识性的信息①;另一些法院将净收入、每股收益、企业兼并与破产等评估业务绩效的主要财务指标,视为对投资者而言具有“重大性”意义的信息②;美国最高法院则在TSC诉北路公司案中指出,“重大性”问题是关涉特定事实与法律适用的混合问题,其标准应当为虚假陈述是否极有可能显著改变理性投资者的“总体信息组合”(Total Mix of Information)③。但归根结底,它仍需通过审判者的主观臆测而非客观事实,对一般审慎投资者及其应知事项作出个案判断。
从本质上来说,“重大性”是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加以定义的情境性概念。为此,法官不得不经常将自己置身于投资者的处境之中,设想案涉虚假陈述会对其购买、出售以及持有证券产生何种影响。譬如,法官会认为,股息率的变化可能对于公用事业股的投资者至关重要,但对成长型股票的持有人而言不那么重要。再例如,法官会认为,公司高管发布的营销声明纯粹只是“虚张声势”(puffery)的软弱信息,并不会对投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仅以“理性投资者”作为“重大性”裁量标准过于抽象,法官需借助数字阙值的定量手段对“重大性”标准进行优化。定量重大性(Quantitative Materiality)其实是由财务业绩、股票价格等经济要素驱动而成,当某一信息足以影响资产、收益或负债的金额、数量或百分比时,就会触发强制信息披露的“重大性”阙值。然而,定量重大性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过于僵化的量化手段容易导致“重大性”被误判。例如,当100万美元的收入中只能实现1美元的利润时,即便利润被夸大100倍,也不会影响投资者决策。由此,“重大性”其实是一种有赖于情境分析的量化评估。
四、程式设计:美国虚假陈述的损失因果关系
(一)美国证券立法的损失因果关系
损失因果关系是原告主张虚假陈述侵权索赔的必备要素,其旨在确保信赖推定规则开启的诉讼闸门不至于过大。根据《证券法》第11条(e)款之规定,被告对于注册声明中虚假陈述的损失因果关系,负有倒置的抗辩责任。该款规定强化了罗斯福总统的“卖者自慎”观念,为注册证券的购买者提供了公平的保护。与上述条款立法宗旨相同,为保护投资者以及防范证券欺诈,《证券法》第12条(b)款亦规定,证券销售方若能证明证券价值的贬损并非是由招股说明书或口头协议中的重大虚假陈述原因造成,其可免于全部或部分损害赔偿。此外,上述两款规定亦能配合《证券交易法》第18条以及SEC的10b-5规则,共同适用于损失因果关系的证明。
(二)美国10b-5规则的损失因果关系
SEC制定的10b-5规则一直是私人投资者对虚假陈述进行追偿的默示手段。随着10b-5规则被广泛运用于证券私人诉讼,法院不得不借助普通法的侵权原则对滥诉活动加以限制。但普通法的一般侵权原则在证券法领域的适用存在大量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致使下级法院之间存在裁判分歧。例如,最高法院允许下级法院相对自由地制定关于责任和损害赔偿的普通法,但对于损失因果关系是否属于虚假陈述的独立要件问题,下级法院莫衷一是。为统一和提高证券虚假陈述的裁判标准,美国国会颁布了《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the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并在21D条(b)(4)项中规定,原告提起私人诉讼应当负担损失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①。尽管国会将损失因果关系确定为10b-5规则的欺诈索赔要件,但它却对损失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保持了沉默。因此,缺乏立法指引和判例约束的下级法院,在证券虚假陈述的审判实务中发展出了风险实现说、直接后果说等损失因果关系的判定依据。
(三)美国司法实践中的损失因果关系判定
损失因果关系经常被联邦法院称作是笨拙的、奇异的、令人困惑的,甚至是令人不悦的概念。这是因为它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被法官所把握。例如,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认为,损失因果关系是被告以直接或就近的方式造成的损失②。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认为,损失因果关系是被告因虚假陈述或遗漏而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害③。更进一步说,损失因果关系需要满足被指控的证券交易行为与待证明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不间断的、单一的直接因果链。最高法院却认为,损失因果关系应当被理解为被指控的损失必须直接来源于违规行为,且不可归咎于嗣后原因(Supervening Cause)④。归结而言,法官对于损失因果关系的判定依据可分为风险实现说以及直接后果说。
在风险实现说下,证明损失因果关系需要将被告隐藏在事前披露中的风险,视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在梅西能源公司证券纠纷案中⑤,法官认为,矿场爆炸是被告在旷工安全与环境合规信息中未加揭示的风险,爆炸事件直接导致被告公司的股票单日跌幅11.4%,足以证明损失因果关系成立。但直接后果说却认为,风险实现说放宽了损失因果关系的证明要求,扩大了虚假陈述的损害赔偿范围。因此,直接后果说遵循严格的损失因果关系证明标准,即证券价格的下跌必须是案涉虚假陈述的直接后果。譬如,在杜拉公司诉布劳多案中⑥,法官认为,虽然杜拉公司对哮喘喷雾装置所作的虚假陈述人为抬高了股东购买证券的价格,但从纯粹的逻辑上来看,虚高的购买价格与股东所持股票的价值相抵了。即便虚假陈述“触及”(touch upon)到了投资损失,但并不必然会造成实际损失。换言之,虚高的价格与损失之间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变化、投资者预期变化、特定行业事实等介入因素。自杜拉案以后,许多法院摒弃了以交易时价格膨胀为标准的风险实现说,转而采纳以嗣后价格下跌为标准的直接后果说。但仍有批判者认为,法院对损失因果关系的机械判定缺失法律根据与经济学基础,是一种过于经济简单化的伪科学(pseudo-scientific)判定方式。
五、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中国因应
第一,“重大性”的标准构建应当遵循“量化为先,分析兜底”的基本思路。其中,“量化为先”是指优先运用“证券价格测试”对虚假陈述事项的重大性属性加以判断。“分析兜底”则是将“投资决策测试”作为指引法官进行个案分析的原则性工具。优先以定量方式构建“重大性”标准的原因在于,在半强式的有效市场中,一切公开信息都会被准确、及时地传导至证券价格之中,重大的虚假陈述自然也会被证券价格所反映。此外,在司法实务中,以量化指标衡量“重大性”标准既能诠释刚性标准下的效率价值,又能避免错综复杂的综合批判难以被把握和操纵。但以计量标准为内核的“证券价格测试”具有以偏概全的固有弊端,不能完全揭示证券价格变动的真实原因,甚至还为虚假陈述的行为人规避责任创造了条件。因此,以定性分析为内核的“投资决策测试”成为了“重大性”标准的兜底考察工具。一方面,注册制改革下的“投资决策测试”已上升为《证券法》规定,投资决策标准的立法强化能对弱势投资者形成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包容度与可解释性强的“投资决策测试”能够发挥漏洞填补作用,避免“证券价格测试”发生失灵而导致“重大性”认定错误。
第二,虚假陈述因果关系链中的揭示标准应当符合更新性、真实性、具体性、相关性的要求。在证券虚假陈述的侵权赔偿案中,准确判断虚假陈述的揭示节点、揭示内容以及揭示载体,有助于法官认定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但2022年《新虚假陈述规定》并未明确虚假陈述被揭示的司法标准,《九民纪要》也未对此作出可操作性强的判断标准。对此,本文以美国虚假陈述的司法判例为借鉴,从四个维度完善我国司法实践的揭示标准。其一,揭示标准应当符合更新性要求,即被揭示的虚假陈述应当首次被公开。已为投资者所知晓或经过整合的信息已经反映在了股价之中,因而不足以构成虚假陈述的有效揭示。其二,揭示标准应当符合真实性要求,即被揭示的内容不得为未经核实的小道消息。但此處的“真实”并非指向全能上帝之眼下的客观真实,而是更加接近于民事诉讼中所追求的法律真实。其三,揭示标准应当符合具体性要求,即被揭示的事项至少应当载明虚假陈述的性质、类型、大致内容、实质影响等。如若该事项是前瞻性的预测信息或者警示性声明,则属于安全港制度下可以豁免的投资风险而非证券欺诈。其四,揭示标准应当符合相关性要求,即被揭示的内容应当与虚假陈述具有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仅要求被揭示的内容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充分、确定地提示投资风险,而不要求两者完全对应。
第三,允許系统性风险以外的因素作为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可抗辩风险。证券投资损失的直接原因不仅包括金融政策、突发事件、能源危机、政治更迭等系统性风险,还包括行业风险、企业经营风险等非系统性风险。一味排除非系统风险作为因果关系的抗辩事由,既有违证券市场风险自担、利益兼顾的基本原则取向,又会导致填补损失的证券欺诈索赔异化为投资者损失的市场风险。因此,如果被告能够举证证明非系统性风险致使股价波动幅度出现异常,亦可减免相应责任。例如,ESG信息披露与公司风险指标呈负相关,当被告充分证明股价的变动是由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所引起,则能抗辩虚假陈述侵权不成立。
六、结语
信息非对称化分布容易诱发虚假陈述的道德风险,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并最终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而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证成障碍常常使证券投资者对欺诈索赔望而却步。作为证券法领域中典型的侵权行为,证券虚假陈述的核心归责要件是因果关系确实存在。在传统的美国侵权法当中,因果关系能够划分为事实与法律维度的因果关系。当范围限缩至证券虚假陈述侵权领域,事实维度的因果关系表现为交易因果关系,而法律维度的因果关系可表现为损失因果关系。只有当两类因果关系同时得到推定或证明之后,原告才能依据证券法规定向被告主张索赔。另外,从纯粹的逻辑角度出发,触发原告经济损失的原因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仅包括被告先前的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还有可能包括经济环境、行业走势、投资者预期等发生变化。因此,在充分考察美国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判定后,我国应遵循“量化为先,分析兜底”的基本思路构建“重大性”标准,不断优化揭示标准以及可抗辩风险的判定规则,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责任编辑:孟洁)
参考文献:
[1]Sandra F Sperino.Statutory Proximate Cause[J].Notre Dame Law Review,2013(3):1199-1248.
[2]Christopher Bernert.The Career of Causal Analysis in American Sociology[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83(2):230-254.
[3]Wyatt Paine.Clerk and Lindsell on Torts[M].London:Sweet & Maxwell,1995.
[4]郭锋,程啸.虚假陈述证券侵权赔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David W Robertson.The Common Sense of Cause in Fact[J].Texas Law Review,1997(7):1765-1800.
[6]Leon Green.Are There Dependable Rules of Causation[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American Law Register,1929(5):601-628.
[7]Anon.Rethinking Actual Causation in Tort Law[J].Harvard Law Review,2017(8):2163-2182.
[8]Clarence Morris.Proximate Cause in Minnesota[J].Minnesota Law Review,1950(2):185-209.
[9]Albert Levitt.Cause,Legal Cause and Proximate Cause[J].Michigan Law Review,1992(1):34-62.
[10]Evan Hill.The Rule 10b-5 Suit:Loss Causation Pleading Standards in Private Securities Fraud Claims After Dura Pharmaceuticals,Inc. v. Broudo[J].Fordham Law Review,2010(5):2659-2670.
[11]Michael P Whalen.Causation and Reliance in Private Actions Under SEC Rule l0b-5[J].Pacific Law Journal,1982(4):1003-1066.
[12]Jill E Fisch.Cause for Concern:Causation and Federal Securities Fraud[J].IOWA Law Review,2009(3):811-872.
[13]Matt Silverman.Fraud Created the Market:Presuming Reliance in Rule 10B-5 Primary Securities Market Fraud Litigation[J].Fordham Law Review,2011(4):1787-1826.
[14]Zachary Shulman.Fraud-on-the-Market Theory After Basic Inc. v. Levinson[J].Cornell Law Review,1989(5):964-992.
[15]Andrew M Erdlen.Timing Is Everything:Markets,Loss,and Proof of Causation in Fraud on the Market Actions[J].Fordham Law Review,2011(2):877-922.
[16]Richard C Sauer.The Erosion of the Materiality Standard i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J].The Business Lawyer,2007(2):321-322.
[17]John M Fedders.Qualitative Materiality:The Birth,Struggles,and Demise of an Unworkable Standard[J].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8(1):41-92.
[18]Krista L Turnquist.Pleading Under Section 11 of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J].Michigan Law Review,2000(7):2395-2417.
[19]Michael J Kaufman.Living in a Material World:Strict Liability under Rule 10b-5[J].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0(1):1-78.
[20]Michael J Kaufman.Loss Causation:Exposing a Fraud on Securities Law Jurisprudence[J].Indiana Law Review,1991(2):357-398.
[21]Mercer E Bullard.Dura,Loss Causation,and Mutual Funds:A Requiem for Private Claims[J].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2008(2):559-588.
[22]Jay W Eisenhofer,Geoffrey C Jarvis,James R Banko.Securities Fraud,Stock Price Valuation,and Loss Causation:Toward a Corporate Finance-Based Theory of Loss Causation[J].Business Lawyer,2004(4):1419-1446.
[23]樊健.我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交易上因果关系的新问题[J].中外法学,2016(6):1495-1511.
[24]徐文鸣,刘圣琦.新《证券法》视域下信息披露“重大性”标准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20(9):70-78.
[25]缪因知.论证监会信息披露规则的不足[J].法治研究,2016(2):141-150.
[26]李有星,潘政.瑞幸咖啡虚假陈述案法律适用探讨——以中美证券法比较为视角[J].法律适用,2020(9):118-128.
[27]汪伟,乔雄兵.中概股跨境审计监管的实质、困局与进路——以《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为切入点[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2(2):103-115.
[28]Ann Morales Olazabal.Loss Causation in Fraud-on-the-Market Cases Post-Dura Pharmaceuticals[J].Berkeley Business Law Journal,2006(2):337-380.
[29]张叶东.论证券发行中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完善——兼议信息披露原则与投资者适当性原则之融合[J].海南金融,2022(1):7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