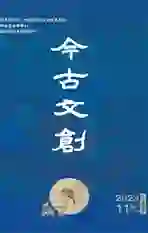从元杂剧看元代文化的通俗化
2023-05-30包莹
包莹
【摘要】 元杂剧作为元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因其文学性与通俗性,被历代评论家给予极高评价。本文通过梳理元杂剧的形成,以及从元杂剧看元代的通俗化教育、文学通俗化、语言的交融四个角度,分析元代文化通俗化成因,窥见元杂剧的文化影响,从而为正确看待元代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帮助。
【关键词】 元杂剧;通俗化;教育;俗文学;语言交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1-005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1.018
一、引言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是我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阶段。从文化角度来说,之前的诗词歌赋等雅文学形式占主导地位,从元代开始小说戏曲等所谓的俗文学成为主流。因此之故,元代文化处于一个饱受诟病的状态。一部分学者认为,元代统治者影响了汉文化的发展,并认为,元代君主普遍汉文化水平低,文化于元一代日渐衰落,儒生的社会地位极低,甚至有九儒十丐的说法。
但随着学术界对元代文化研究的深入,这些思想的片面性也逐渐显露出来。其实元代文化在多个领域都有所成就,有些方面甚至得到了超越前代的发展。而元代君主普遍汉文化水平不高以及元代儒生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观点也有所偏颇。事实上,从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角度来看,元代文化是继唐、宋以后的另一高潮时期。
由于在统一的元王朝境内,实现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民族混杂而居,普通民众直接接触和交流彼此。这些客观因素造就了元代文化繁荣的特殊性——文化的通俗化。元代较之其他朝代,出现了大量使用白话文或浅显的语体文面向大众的文艺作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产生了多民族作家所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元杂剧。
元杂剧的前身为宋、金时期的杂剧和院本,属于宋金时期商品经济发达、都市繁荣的产物。北宋杂剧源于唐代“参军戏”,主要是滑稽表演,出于某种讽刺目的去编写一个故事,再由两名以上演员将剧本表演出来,形式上更为偏重念诵和对白,但也夹杂着歌舞表演或杂技表演。到南宋时,杂剧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演出程序,并有固定角色,包括末泥、引戏、副净、副末等。金杂剧与宋杂剧大致相似,但又有一个新的流行名称为“院本”。其含义为行院人(演员)演出使用的脚本。元杂剧起源于金末元初的北方地区,是从院本中直接衍生出来的。
元杂剧的诞生与兴盛,还与元代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元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以及元朝统治时期,在文化方面都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重视保护各类人才,尤为喜爱汉地的歌舞艺术。进入中原之初,每占领一个城市,儒士、乐工、工匠、僧人、道侣都受到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为了自保乃至谋生,投身于乐工行业。元朝建立后,统治者注重吸纳不同民族文化。这些都给文人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与此同时,元初大量士人仕途中断,大量失意士人为适应社会需求,投身于市井艺术的创作。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元杂剧是他们创作出来用以谋生的手段,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元杂剧是人民大众茶余饭后所享用的文化作品,所以元杂剧注定是通俗化的文艺作品。王国维形容元杂剧为:“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从王国维的描述,可以看出元杂剧具有很强的通俗性与文学性。
二、从元杂剧看元代的通俗化教育
戏曲文化是大众文化,是在正统文化之外的“俗”文化,因此,戏曲是我国文化通俗化的重要标志。而至元一代,我国戏曲才真正走向辉煌。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2]
从元杂剧看元代的教育通俗化,先要从创作者看。元杂剧的创作者很多是传统儒家文化精英。他们在蒙元政治中地位特殊,入仕高层很难,因此他们从创作正统文学转而创作大众文学,但其儒学修养却根深蒂固。并且至元一代,虽科举时断时续,儒学传统却并未改变,元代的大量书院仍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儒家知识分子。因此,元杂剧在创作时必然带有一定的传统儒学思想以及教育意义。
元雜剧所体现的教育通俗化,还表现在元杂剧所具有的社会教化作用。这也可以看出创作者对儒家伦理观念的认同,儒家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这使得戏剧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说教色彩。作为大众艺术的戏剧文化与传统文学,共用一套道德标准,即儒家的道德伦理。这一套道德伦理也使戏剧成了政治教化的手段。
汤显祖就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戏剧:“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侠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己愁馈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病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言明戏剧的道德教化作用。清人刘念台在《人类谱记》中说:“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梯弟、忠臣、义士,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泅横流。此其动人最切,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钠登上座说佛法、功效百倍。”认为戏剧在道德教化上的作用,远超僧孺的讲经布道。
而杂剧的道德教化作用也被元政府察觉,朝廷会下令在地方排练,演出具有较强社会教育意义的曲目。明初宗室周宪王朱有嫩《元宫词》就描绘了戏剧因社会教化意义而被皇帝赏识,因此在全国各地上演的盛况。
三、从元杂剧中看元代的文学通俗化
元杂剧,作为通俗文学式样,使“俗”文学在元走向兴盛,在此后俗文学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从杂剧角度看元代的文学通俗化,首先从社会角度看。元杂剧的作者是社会地位不高的士人阶层,政治上失意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大多关心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作品也往往以劳动人民的生活为视角。例如《窦娥冤》《任风子》《救风尘》等等。
关于元代的文学世俗化,不得不提到知识分子的角色变化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元代的市民阶层构成极为复杂,既有小手工者、商贩,还有僧侣、道众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市民群体整体文化程度低,且流动性大。市民阶层并非自元始形成,但自形成以来,市民阶层一直存在于士人阶层的视野之外。然而,元代的社会环境较为特殊,元代科举时断时续,大量士人沦为市民阶层,他们从社会上层跌落,生活方式,审美意趣皆向市井靠拢。而这一部分人则是元杂剧的主要创作者,因而市民意趣也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体现了出来,完成了文学的“俗化”。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文学的“俗化”是自元开始的。
而从文学的自身发展角度看,杂剧文本对于现实高度仿真投射,使杂剧变得“俗”而亲民。元代民间生活中求变尚新,贵生重利,从而催生出了元杂剧反秩序,反传统的价值判断,以及重视个人情感的文化基因,这是前朝文学家的作品中很难看到的。
钟嗣成所著《录鬼簿》作为我国第一部为曲家立传之书,专门为无法进入正史的元代曲家作传。在该书自序中,钟嗣成公然声言:“酒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虽生,与已死之鬼何异?”[3]他赞扬“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的已亡名公才人为”不死之鬼”,而与他同时期的周浩也在散曲中表达过相似的想法。
想贞元朝士无多,满目江山,日月如梭。上苑繁华,西湖富贵,总付高歌。麒麟豕衣冠坎坷,凤凰台人物磁蛇。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双调蟾宫曲题《录鬼簿》】
这种不惜“得罪于圣人”得言论足可以看出,元代文学家反秩序,反传统的价值判断。
元杂剧作为一种通俗化文学,还创作了大量经典而优秀的女性角色,这对于把女性作为附庸的封建男权社会来说是个不小的进步。
将男女之情回归性别层面,是文学作品走向通俗的一大步。传统文学讲两性关系视为君子治国齐家平天下道路上的阻碍,就连《世说新语》都将描述夫妻间亲密情感的故事归入《惑溺》篇中。而元杂剧对于男女之间的情感俗欲加以正视,而非传统文学那样一味批判和躲避,绝大多数的曲家都涉及了闺怨题材。例如关汉卿的《救风尘》,王实甫的《贩茶船》,马致远的《青衫泪》,贾仲明的《玉梳记》《玉壶春》,戴善夫的《风光好》,乔吉的《两世姻缘》,张寿卿的《红梨花》,石君宝的《曲江池》《紫云亭》等。
除却社会发展以及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诸多因素,当时民族文化的交融也是元杂剧走向通俗的重要因素。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通俗化,往往在民族大融合时期。例如,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民歌。而唐末时期,变文,曲子等通俗文体又逐渐兴盛。宋金元时期,戏剧又成了文坛主流。
李成在《民族文化交融与辽金元文学转型》中说:“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发展史中,辽、宋、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促进了文化与文学的转型,在中国文化史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4]云峰在《民族交融与元杂剧研究》一书中提出,元朝时期,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学的通俗化。
四、从元杂剧看语言的交融与通俗化
关于元杂剧在语言艺术中的通俗化,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说:“古代文学之形容食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对于俗语的运用,有人认为是文学的退化,而胡适则说:“(元曲)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之语言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5]胡适从语言的角度对元杂剧这一特征进行了肯定。
元杂剧运用了大量的俗语、口语,以及现成词组,这种近乎白话的语言风格,使元杂剧能迅速民间流传。这种现象首先是由元杂剧的受众而决定的。观看者多为市民,不运用口语则不能被他们理解。而蒙古统治者由于对于文言文体的不精通,也提倡使用白话文,甚至元代的公文都偏向白话。此外,元杂剧的音乐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雄武的特点,节奏感强,而文言文无法自然和谐地匹配这种音乐。因此,与之前的文学语言相比,元杂剧的语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元杂剧并非全用通俗语言,它将通俗口语和曲的语言技巧相结合,有些语言十分华丽,带有很强的文学性和传统文言美感,形成了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不能仅用文言或口语来概括,极为独特。
元杂剧中使用了大量的非汉语词汇,是多民族语言文化融合的结晶。在元代,通晓蒙汉语言文字的人很多,而蒙汉在文化上的交流也十分广泛,因此元杂剧中引用蒙古语言文字成为十分广泛的现象。
例如《降桑椹》《哭存孝》《射柳捶丸》中的“米罕”为蒙古语的肉,“答剌孙”则为蒙语中的酒,“努门”“速门”为蒙语中的弓、箭,“抹邻”为蒙语中马,而“莎塔八”为蒙语中醉酒之意,“牙不牙不”为蒙语中的走。又如《汉宫秋》中“把都儿”为蒙语中的英雄勇士,“哈剌”在是蒙语中杀、杀害之意。这些蒙语名词,时而直接引入到宾白叙事之中。元杂剧中还出现蒙汉双语杂糅的句式,如关汉卿《哭存孝》第一折:“喝的莎塔八,跌倒就是睡”。张寿卿《降桑椹》第一折:“哥也,俺打剌孙多了,您兄弟莎塔八了”。
关于蒙古语言文字对于元杂剧语言的影响,早在明朝就有人认识到。明人张楚叔在《衡曲尘谭》中说:“自金元人中,所用胡乐嘈杂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制新声(散曲、杂剧)以媚之……大江以北渐染胡语。”[6]而自近代以来,又有贺昌群的《元曲概论》,方龄贵的《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等著作探討元杂剧与蒙古语之间的关系,收录元杂剧中使用的蒙古族词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也有很多,例如:严望舒、吴晓铃的《谈元曲的蒙古方言》、牧兰的《简析元明杂剧中的蒙古语》、王永炳的《元剧曲中的蒙古语及其汉语言译问题》、包双喜的《谈元杂剧中蒙古语的运用》等。
此外,元杂剧还保存了不少契丹语、女真语、回回语等词汇。如在《虎头牌》第三折中:“才打到三十,赤瓦不刺海,你也忒官不威爪牙威。再打者。”赤瓦不刺海就是女真语词。这样的运用还可见于《丽春堂》中。《丽春堂》第二折:“(正末唱)则你那赤瓦不刺强嘴,兀自说兵机。“赤瓦不刺海”为女真语“你这该杀的”之意。[7]
元杂剧在保留少数民族语言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对于杂剧内容并未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仅可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来看,因为中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至宋时已从包容走向了排拒。这种保留更像是受时代背景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尽管如此,这些语言也让元杂剧更增风采,极大丰富了元杂剧的词汇和表现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其受众群体。
五、结语
元杂剧作为元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是元代“俗文化”盛行的重要表现形式,“俗”由元盛行,而成了我国重要的文化分支,其文化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输唐诗宋词,而后世也不乏“俗文化”影响下的优秀文化作品。而元杂剧文化影响的深远程度,甚至遥遥可辐射至欧洲。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4]李成.民族文化交融与辽金元文学转型——兼谈中国古代戏曲繁荣的原因[J].大连大学学报,2004,(3):60-61.
[5]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6](明)张楚叔.衡曲麈谭·作家偶评[M].明崇祯十年(1377年)张师龄刻本.
[7]蔡美彪.辽金元史考索[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