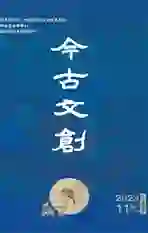论文学作品中女红民俗的审美意蕴
2023-05-30桑莉
【摘要】 古今文学作品中的女红民俗书写,既呈现了女性勤劳贤淑的妇德传统,也反映了女性对因袭命运的认同与接受,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对女性之“美”的认知和理解,展示了女性通过女红民俗表达情感、建构关系、重拾自信和寻找自我的表达方式,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蕴。
【关键词】 女红;小说;民俗;劳动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1-004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1.015
民间风俗,简称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中国女红自产生之日起,便与民间大众的生活密切相连,历经漫长的发展传续,其内涵早已超出了物质与技术层面的现实功用价值,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特别是在一些关乎民众生活习惯、人生仪礼等内容的社会制度民俗,关乎人们劳动生产、社会活动等内容的岁时节日民俗,以及民间娱乐习俗和民间信仰等方面,女红劳动与民间风俗常常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在相互缠绕与融合的关系中,不断演化为独特的女红民俗。本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古今文学作品中的女红民俗书写,探究其丰富独特的审美意蕴。
一、古代女红民俗书写中的生活趣味
在文学创作中,自古就有许多作家对女红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予以关注和呈现。《诗经·豳风·东山》中,“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2]即通过描写母亲为出嫁的女儿盘扎绳结的女红行为,反映了“结缡”的女红婚仪民俗。《诗经·小雅·斯干》言:“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3]即言女孩出生时,要送给她纺锤之类的女红之物,反映了民间的庆生习俗。唐代林杰《乞巧》诗:“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4]则以女性对月穿针引线以祈求拥有一双巧手的女红场景,呈现了农历七月初七乞巧节的岁时节日民俗。唐代李德裕《鸳鸯篇》:“夜夜学织连枝锦,织作鸳鸯人共怜。”[5]则又通过描写闺中女性缝制鸳鸯被的女红劳动,暗示了古代女性婚前需要苦学女红,以便将来出嫁时为自己缝衣制被的生活习俗。而唐代孟郊《结爱》则直接以古代女红编结活动入诗:“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一度欲离别,千回结衣襟。结妾独守志,结君早归意。始知结衣裳,不如结心肠。坐结行亦结,结尽百年月。”[6]生动展示了男女之间以编制心结表达爱情的生活习俗。宋代苏轼《浣溪沙·端午》则写道:“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掛绿云鬟。”[7]通过描写女性在端午节编结五彩绳的女红活动,表现了辟邪祈福纳吉的岁时节日民俗。而明清小说中常见的缝制香囊、刺绣荷包、馈赠绣帕等女红书写,也反映了男女之间以女红物件表达爱情的生活习俗。古代作家通过书写与民俗有关的各种女红活动,生动呈现了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地域环境中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与丰富多元的女性生活,同时,这些女红活动的民俗色彩也使作家在塑造人物、表现人物性格等方面独具魅力。
二、现代女红民俗书写中的反思意味
相较于古代文学作品中作家更注重对女红“妇德”与“艳情”内蕴的发掘与呈现,“五四”时期,“人”与“女性”的发现,有力推动了作家对包括女红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反思。从这一时期开始,女红中所包蕴的“妇德”“妇职”等父权文化内涵逐渐走向瓦解,传统女红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断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现代”面目。“五四”时期作家对女红的书写主要体现在对女红题材“反封建”意义的发掘、对女红和“新女性”人格建构关系的察视以及女红对现代家庭建设的影响等方面,代表作品有凌叔华、冰心、庐隐、冯沅君等创作的一些“家庭小说”。例如凌叔华《绣枕》中,通过描写女红刺绣与传统女性贤良淑德品格之间由相互“映证”到女红所具有的封建性别规约色彩的突然消解和打破,生动呈现了现代文明对传统女性生活的冲击,以及现代女性解放与普通“闺阁”女性生活之间依旧存在的遥远距离。而同样的女红素材,在冰心小说中又表现出不同功能。无论是《两个家庭》中,新女性亚茜在新式家庭生活中依旧坚持的为孩子织袜子一类的女红行为,还是《别后》中,穿紫衣的姊姊宜姑愉快忙碌地剪纸花,作家都着力凸显了传统女红对新式家庭秩序与温暖家庭氛围的建设性意义,以及女性在女红活动中所获得的精神愉悦。在冰心小说中,女红内涵与沉重辛苦的传统女性“妇职”已经明显不同,其对女红行为的着意凸显与强调,也并非是对传统封建家庭秩序的简单认同和倡扬,而是其对此时期如何更好地实现旧家庭向新家庭生活的转换所进行的有益思考与探索。冰心通过传统女红所表现出来的相对温和的女性解放观,充分反映了现代妇女解放初期,女性人格建构与成长的真实境遇,从而使寻求个体解放的新女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像《两个家庭》中陈太太那样,因为盲目追求妇女解放和建设新家庭而陷入夫妇失和、生活混乱不堪的“窘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较独特和重要的女红书写主要体现在鲁迅、柔石、王鲁彦、吴组缃等作家创作的一批“乡土小说”中,例如《菊英的出嫁》《箓竹山房》《为奴隶的母亲》等。这类小说“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对本土文化进行的历史观察与反思”[8],在女红书写方面,多通过呈现女红浓郁的“妇职”内涵来反映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身心的戕害。例如《箓竹山房》中,精于女红的二姑姑因为善绣蝴蝶而获得爱情,但也因女红所隐含的贤良妇德而使自己坠入到“阴阳婚”的不幸中,女红在此作品中被作家巧妙设置为造成女性悲苦命运的“导火索”,进而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女性人格的压抑与摧残。另外,沈从文《萧萧》、王鲁彦《菊英的出嫁》等小说中也以各种女红民俗书写,反映了底层女性仍旧因袭的封建传统生活方式。
三、当代女红民俗书写中的生存况味
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红民俗书写,主要指向与地域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日常女红、民间岁时节日女红以及生育、婚仪和丧礼中的人生仪礼女红。为了凸显女性对因袭命运的认同与接受,作家常常会借助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家庭女红习俗,将女性置于独特的民俗氛围中,在赋予现实生活浓郁的历史文化内涵之时,使人物的生存况味更加深邃与厚重。
王伶小说《塔合曼女人的五月》中,作家多次写到塔吉克族女性在冬季为婴儿缝制衣裳和缀满珠子的花帽的民俗:“塔吉克族女人把给未出生的婴儿缝制花帽,看作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她们洗净了手,盘腿坐在毡炕上,缝啊缝,与羊儿一起咀嚼那漫长又短暂的幸福时光,與羊儿一起回顾那些已逝的或悲伤或快乐的事。”[9]这一女红民俗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缝制花帽”这种单纯的女红活动,而转化为塔吉克族女性对这一习俗所隐含的女性命运的追溯与传续,正因为此,小说中古兰丹姆的母亲会坚持每年春天坐在石屋里,缝制花帽,并在这种坚持里,放弃了年轻时的美好爱情,黯然接受了命运对她的安排。而多年以后,和她一样曾经憧憬美好爱情和崭新生活的女儿古兰丹姆,也开始了对“缝制花帽”习俗的认同:“树枯了,草黄了,雁去了。古兰丹姆换上母亲的宽大裙子,像母亲从前那样,盘腿坐在毡垫上,开始缝一顶金丝绒的小花帽。从一个晨昏缝到另一个晨昏,永远没有疲惫的时候。她算了算,来年五月,她将跟高原上众多女人一起,跟她家圈里的母羊一起,生产。生孩子同产羊羔一样,永远是高原上的一件大事。”[10]
而王华小说《花村》也以同样温情忧伤的笔调书写了仡佬族女性出生和出嫁时,都要在衣服上绣花的女红民俗,这些绣制的“花朵”暗示了女性被固化的命运。王梓夫小说《幕僚》则通过对模阳女性制作“面花”手艺的细致描写,有力呈现了女性被“规约”的命运:“女孩儿刚会走路就学做馍馍是靠做出来的。一团面在女儿家的手里揉来揉去,揉成了她们身体的一部分也化成了她们灵魂的一部分。”[11]小说中那些与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女红民俗,总是更容易表现出女性“一成不变”的命运。作家通过女红民俗书写,在反映当代女性生存境遇的同时,也将那些具有浓厚传统之蕴的古老民俗再次纳入到现代文学叙事体系中,通过女红民俗观照当代女性的现实生活和潜在意义,使民俗传统从原初事象还原为现代生活实践[12],进而在古今文化交织中,实现对女性沉重命运和重复性生存状态的描摹与言说。
另外,当代作家还善于描写乡村婚仪民俗中的女红活动,例如,女性出嫁时,家中亲人要为其缝制婚服、喜被,待嫁的女性在定亲后要为未婚夫制鞋做袜,举行婚礼时,女性会剪窗花张贴于婚房墙壁与门窗上,以助兴与辟邪等。这些女红民俗在呈现当代女性丰富生活的同时,也成为女性表达情感、建构关系、重拾自信和寻找自我的重要方式。向春小说《西口外》中,按照婚仪民俗,为了给儿子准备相亲的“见面礼”,刘寡妇决定染布:“做这件事情最关键的环节是花结子要打得均匀,拆开以后每一朵花都一模一样,像是机器印的。刘寡妇是那样的专注,她挑亮胡油灯,睁大已经昏花的眼睛,像当年给自己做嫁妆那样兴奋。”[13]小说中的刘寡妇在多年抚育儿子的辛苦生活中,早已将真实的自我和内心情感深深掩埋,当其根据相亲习俗再次“染布”时,竟深深体验到一种重返青春的“兴奋”,她的身份也仿佛从“母亲”又回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于是她的生命因为“染布”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陈启文小说《仿佛有风》,则通过描写待嫁的女性为意中人或未婚夫做绣鞋的婚仪民俗,生动呈现了成长中的少女对爱情与婚姻的懵懂感知:“湖乡的妹子,中意了哪个男孩,就会给他做一双千层底的鞋子,任他走到哪里,就再也走不出这女子小小的手心了。”[14]付秀莹小说《旧院》则更加详细地书写了女性定亲后要为未婚夫绣鞋垫的婚俗:“我们这个地方,男女定亲以后,女方是要给男方绣鞋垫的。一则是表情达意的方式,二则呢,也有显示女红功夫的意思。为此,女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跟在姐姐们后面,细细揣摩鞋垫的事情了。”[15]这些独特的女红民俗深深寄寓了女性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也成为女性表达内心隐秘情感的“合法”途径。
陈忠实《白鹿原》、漠月《秋夜》、陆星儿《小凤子》等小说则又通过描写民间庆生习俗中,女性为孩子缝衣制袜、做虎头鞋等女红活动,在表现母亲关爱孩子成长的同时,凸显了女红在民间百姓建构社交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阎连科《受活》、东紫《芝麻花开》、张宇《乡村情感》、刘庆邦《黄花绣》等小说中对亲人生命将亡时,家人为其缝制寿衣习俗的书写,则表现了民间社会对待死亡的态度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思考。例如《黄花绣》中女性临终前必须穿童女儿做的绣花鞋才能“登天”的习俗,使得被忽然“委以重任”的乡村女孩格明突然成长起来,进而在这种女红活儿中开始了对个体生命与生存意义的思考。铁凝小说《麦秸垛》中,则通过描写现代女性沈小凤认同传统习俗,向大芝娘学习绣枕的细节,反映了女红对女性的精神抚慰意义,以及二者之间隐秘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女红民俗对女性生命成长产生的重要影响。
而李本深小说《奇药》对女红刺绣“鸳鸯戏水”民俗意义的“运用”,则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新颖独特的审美内蕴。小说中朴实善良的何神仙与美丽纯真的养女秀儿感情深厚,秀儿的母亲去世后,两人同住一院,引起村人们的“闲言碎语”,这让何神仙有“苦”难言,不得不在生活中对秀儿的照应有所避忌,而有所察觉的秀儿也自觉在个人卧室的屋门上挂了一条布门帘,为了使门帘好看,巧手的秀儿还在上面绣了一幅鸳鸯戏水图,却不料这种方式更加“惹恼”了何神仙:“秀儿用各色的彩线在半新的一条布门帘上绣了一对戏水的姆鸯挂在窑门口,叫何神仙看好不好。何神仙竟然大变了脸色说:‘快摘下来!快摘下来![16]在民间风俗中,刺绣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17]的象征意味。“鸳鸯”是一种观赏鸟类,其因喜欢成对出现,故常常被人们视为爱情的象征,“鸳鸯戏水”也由此成为刺绣中的常见纹样,寄寓了夫妻之间的和睦情深,由此,当何神仙看到秀儿竟然在门帘上绣了一幅“鸳鸯戏水”图时,原本就对村邻们的闲话十分烦恼的他,此时便更加“火上浇油”了。小说虽始终未直接描写何神仙对村人闲话的“反应”,但却通过家庭空间中这一独特的女红民俗物件,暗示了何神仙对传言的敏感与在意,也反映了确实存在于他心中的“鬼”,女红民俗在反映人物心理方面表现出一种以小见大、以微知著的价值。
四、结语
在由古至今的文学创作中,女红民俗始终未阻断其深厚的“妇职”意蕴,虽然时代发展和环境变迁使女红民俗的具体形态与内涵时有变化,但其在产生之初即与女性、家庭、社会等建立起来的独特关系,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而相對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红民俗书写,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红书写,受启蒙和革命话语影响,作家更多将其置于封建落后、愚昧保守之境,对其文化寓意和审美内涵的发掘与呈现,普遍指向封建思想对人之身心的束缚与戕害,从而使女红素材成为揭露批判传统社会秩序、挑燃民众反抗现实人生和对国民予以现代启蒙的独特“工具”与“武器”。而当代社会在发掘倡树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过程中,作家再次关注到日常生活中那些依旧存续的女红民俗,在对其精心描摹中,使其呈现出与当代社会生活相融合的风貌与文化内涵,不仅成为当代人认知理解民族文化、探索其当代价值的重要方式,同时,也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内涵,展示了源远流长的女红文化在当代社会空间中的演变风貌,和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呈现出丰富深邃的审美意蕴。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3.
[2][3]李立成校注.诗经[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1:121,158.
[4][5][6]王启兴主编.校编全唐诗(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2366,2490,1487.
[7]范之麟主编.全宋词典故辞典(上)[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255.
[8]赵学勇.新文学与乡土中国[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68.
[9][10]王伶.塔合曼女人的五月[J].北京文学,2004, (4):5,11,33.
[11]王梓夫.幕僚[J].北京文学,2005,(9):42.
[12]李向振.重回叙事传统:当代民俗研究的生活实践转向[J].民俗研究,2019,(1):43.
[13]向春.西口外[J].十月,2010,(4):116.
[14]陈启文.仿佛有风[J].十月,2002,(5):7.
[15]付秀莹.旧院[J].十月,2010,(1):149.
[16]李本深.奇药[J].当代,1991,(3):221.
[17]王欣.中国古代刺绣[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5:73.
作者简介:
桑莉,女,山东茌平人,博士,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性别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