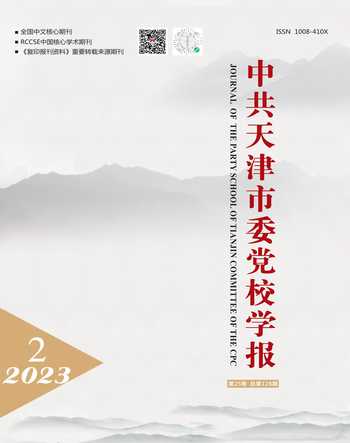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意义、实践要求及推进路径
2023-05-30戴激涛
戴激涛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政理、法理和学理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进行了多维创新,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与理论支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明确了根本性政治原则、奠定了系统性法治思维、筑牢了长期性制度保障,在实践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制度体系、全面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宪法商谈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应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以宪法商谈建制化路径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用,构建多领域多层次多元化的宪法商谈形式,培养公民的观念性宪法世界。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宪法商谈;观念性宪法世界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23)02-0003-11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習近平法治思想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建设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独特智慧,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法治维度的思想武器、科学指引、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高瞻远瞩的引领和导航,从而在法治轨道内更好地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典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科学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与实践发展经验,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规律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的新观点,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新境界,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系统的理论指导、科学的顶层设计”[1]。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典范,在政理、法理和学理三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进行了多维创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辩证思维、人民立场、价值旨归和时代精神。
(一)政理创新:政治和法治辩证统一关系的新阐释
当代中国法治领域的“政理”意指“以法而治、依法治国”的“政治之道”“政治逻辑”等含义[2]。 理解“政理”,应明晰政治和法治的关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根本问题,政治和法治的关系集中体现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政法体制是中国法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法系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3]。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政治和法治关系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释,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4](P33)。法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指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治国理政的价值、原则和方式,是按照规则进行治理的有序社会状态。在法治这种社会状态之中,本身就蕴含了政治要素;而政治同样需要法治的约束使其保持公共理性,“政治必须具有通过法律与所有其他被合法地确立起来的行动领域进行交往的能力,不管这种交往如何被形构和引导”[5](P30)。正确认识政治和法治的关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作。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显著特色和独特优势集中体现在从政治的高度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最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的结论,是在政理层面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时代创新。
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政治和法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读,并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证,得出党的领导和全面依法治国、政治和法治是辩证统一关系的结论。基于政治和法治辩证统一关系原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法治轨道内推进国家各项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确保全面依法治国正确方向的最根本保证。一方面,必须不断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机制,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各领域各方面全过程;另一方面,必须不断完善党领导立法、执法、司法的制度机制,保障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有效实施,不断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稳步推进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政治和法治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阐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
(二)法理创新:人民至上作为实质法治的最高原则
法理,即法之根本原理。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范畴,法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都是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明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立场就是人民立场,人民是贯穿依法治国各领域各方面全过程的主题词,“法治建设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6](P284),人民立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立场不仅意味着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最高原则,而且要求国家切实履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义务,切实保障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各项民主权利。将人民至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最高原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重要法理创新。
社会主义法治是一种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治国理政方式,集中体现了实质法治的价值内核。实质法治作为与形式法治相对的一个概念,包含了特定的经济制度安排、政府体制机制、人权保障观念等政治道德的法治,是一种深度的法治,而形式法治是一种浅度的法治[7]。与形式法治主张法律的形式正义相比,实质法治更强调法律的实质正义,“实质法治认为,法律的确定性只是法治应当追求的价值之一,法治还应当关注法律自身的品质,考虑法律原则等基本的正义准则”[8](P16)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在法理层面的创新,集中表现在提出了人民至上作为实质法治最高原则的观点。这不仅在我国宪法法律的文本规范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在法治实践中成为一切国家权力行使的最高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保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贯彻落实人民至上实质法治原则的重要制度载体。一方面,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求必须坚持人民的宪法主体地位,“宪法是由人民的智慧制定的,并且是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的,人民的意志是任何政府唯一合法的基础”[9](P58);另一方面,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构建的宪法制度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框架。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为此,在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要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最高原则,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各个环节。党领导人民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践亦表明,将人民作为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经验,也是维系良善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学理创新:以民主集中制破解法律合法性困境
现代法律正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考验,“法律呈现为要求和回应的活动或链条,这种要求和回应都力求以正义的名义被听见和被说起”[10](P211)。重构现代法律的合法性,需要化解人权与人民主权间的固有张力,在法治框架下改善自由平等的公民间开展公共协商的方法和条件,使民主程序在协商和谈判过程中被建制化,从而赋予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同源性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指引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在对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进行深入分析、作出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提炼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主张全面贯彻落实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和运行原则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化解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的紧张关系,实现人民主权与人权原则的同源性建构,为破解现代法律合法性难题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是分析法律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概念。19世纪后期,相关学者就意识到法律要从其自身获得合法性,就必须从法律主体的私人自主中的道德自主性寻求依据。耶林提出“主观权利”概念,將主观权利视为法律秩序授予个人的一种法律权能,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权利和利益。哈贝马斯用人权与人民主权的观念作为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规范性表达,认为现代法只有根据由人权和人民主权原则所构成的理念而获得合法性辩护,“法律的承受者同时是这些法律的创制者。一方面,人民主权在商谈性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中获得法律形式;另一方面,人权的实质就在于这种过程得以法律建制化的形式条件之中”[11](P128)。 西方理论界试图通过法律商谈实现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同源性理解以化解法律合法性危机,习近平法治思想则强调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通过民主集中制将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统一起来,实现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同源性理解。作为中国特色的宪法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充分体现了中国宪法制度的独特价值。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家机构组织运作中的贯彻落实,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实现了有机结合,既要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和作出决策的过程中必须有广泛讨论的民主基础,又要求通过集中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奠定了法律的正当合法性基础。作为我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显著优势。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持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切实保障人民各项权利,不断加强人权法治保障,构建起较为完备的人权法律保障体系,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不断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丰富多样的人权实践。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固有张力在中国特色宪法民主制度的实践运作中得到有效调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破解了现代法律的合法性难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重要学理贡献。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其鲜明的理论风格和实践特色,对百年大变局时代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深刻阐述,用“十一个坚持”系统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和宏观设计,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明确了根本性政治原则、奠定了系统性法治思维、筑牢了长期制度性保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一)明确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原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就是将坚持党的领导宪法原则置于首位,明确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宪法原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离不开党的领导这个政治根基”[12] 。我国现行宪法不仅明确规定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且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根本要求。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宪法基本原则,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各领域各方面,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制度理性与正确方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性政治原则进行了全面阐述。从历史上说,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领导带领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更大,我们的国家更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更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13](P281)。 就现实而言,习近平通过澄清长期以来在政党和法治关系上存在的各种模糊、片面和错误认识,明确了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性政治原则,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也有力证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14]。面向未来,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在纷繁复杂、充满变局的世界秩序中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始终将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作为国家权力行使的唯一理由,使全体公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实践中形成价值共识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奠定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系统法治思维
系统法治思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的系列观点表明,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统一。“在方法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始终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结合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以系统思维方法来谋划布局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15]。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法治思维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指引。
在理念层面,习近平法治思想本身就是一个严谨而开放、具有深刻的科学真理性的法治理论系统。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从新时代治国理政角度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法治概念、法治论断和法治命题,而且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全面阐述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基本理论,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体系化、整体化的理论指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的基础上确保各项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这就要求既要坚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又要依据法理实行良法善治,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统一,以良法善治思维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
在制度层面,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加强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制度机制建设等观点,夯实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体系化制度根基。这个体系化的制度根基是由宪法法律规定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一系列重要制度构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决定和影响着其他民主制度的实践运行和发展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必须运用系统法治思维,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置于整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制度体系之中,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其他民主制度的指导作用和示范价值,充分运用系统法治思维宏观谋划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建设方略,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实践层面,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必须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各民主形式在法治框架下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实践运作。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涉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方面各环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既关注国家发展大事和社会治理难事,也重视民众生活杂事和日常琐事,具有制度运行的持续性和合作性、人民参与的整体性和广泛性等特点,这就需要系统法治思维的指导,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具体民主制度机制实现资源整合,最大限度地释放法治在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强大效能,不断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项工作质效,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事业的新境界。
(三)筑牢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长期制度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深刻总结中央苏区和革命根据地时期制定和实施人民宪法,推进民主立法、为民司法等方面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传承了红色法治基因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形成了基于历史和人民选择基础上的治国理政重要经验。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地总结了新时代科学立法、依法执政、公正司法、法治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展示了社会主义法治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规范运行的重要意义和战略价值,筑牢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长期制度保障。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而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架构,集中体现了我国宪法制度内蕴的人民至上品格,夯实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石。
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的直接体现,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高形式和重要途径。我国的选举制度保障了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权利,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实践中主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能,实现了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方式,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制度载体,在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宪法制度体系中,人民至上是贯穿每一项具体制度实施运作的价值内核。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具有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安排,而且在宪法法律制度体系的保障下形成了丰富生动的民主实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继续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运作的规范化、法律化。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分别从原则、思维和制度三方面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在实践中应将坚持党的领导这项根本性政治原则、系统性法治思维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落到实处,而将这三个方面要求统一起来的基本路径,就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从国家组织与治理的高度来定位宪法、实施宪法、保障宪法”[16]。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就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过程。
(一)坚持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原则。宪法从国家根本法的高度確立了党是我们一切事业领导核心的宪法地位,因此,在法治轨道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大体制优势,也是我国法治建设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面领导,有助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党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制度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而且应贯穿全过程人民民主各项具体制度的实施运作过程,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一方面,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必须确保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环节都能得到有效执行,建立健全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和统筹协调。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调整国家政治组织及其职能,在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宪法确立的原则和制度,对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加强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和统筹协调,就是将党的领导这个宪法基本原则全面贯彻于宪法的实施过程。坚持把党的领导原则落实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领域全过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
(二)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制度体系
我国宪法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创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在宪法民主制度体系中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加强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宪法民主制度建设,在宪法制度的规范运行中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
一方面,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制度体系,必须处理好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宪法人民主权原则的规范表达,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义和本质特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是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尊重和实现人民宪法主体地位的应有之义。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运行原则,建立在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基础之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必须按照宪法的人民主权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运作,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民主的精神不仅是选举和投票,不仅是一种政治形式,它最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核是参与,是公共自主”[17](P15)。另一方面,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制度体系,必须处理好人民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人民参与国家治理,是通过选举制度来实现的。民主选举既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民主选举的实质就是把人民的权力委托给人民选出的代表行使,人民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来源。因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必须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积极履行宪法法律规定的基本职责,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制度体系的协同运作,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各项具体制度机制的有机衔接,以保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通过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制度体系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三)全面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保障人权夯实了法治基础。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自此,“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人权保障是所有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法律义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应全面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义务。
习近平法治思想认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就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依法保障人民权益,推进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特征。人权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法治是实现人权的根本保障。在我国,人权不仅仅是文本层面的宪法法律概念,更是人民当家作主主体地位的体现,是人民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公民地位的集中体现,“公民的地位是由那些民主权利来构成的,即个人为了改变其物质法律地位能够反思性地提出的权利要求”[18](P33)。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能够积极履行人权保障的宪法义务,人权的宪法法律化程度越高,法治对人权的实现和保障越充分,司法对人权救济和保障越充分,这个社会就越和谐稳定,公平正义就越能够得以充分实现。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全面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基本要求。
四、经由宪法商谈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推进路径
“我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国家法治上的最高体现”[19]。我国宪法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在法治轨道内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实质就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
(一)宪法商谈作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基本路径:理论模型与规范价值
作为当代立宪民主政体的构成性要素,宪法商谈被寄予实现真实民主理想的厚望,“宪法商谈是立宪民主的基本要素”[20](P27)。现代国家的立宪民主政体就是一种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宪法商談模型,宪法商谈主要通过宪法构建的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宪法试图建立协商民主,以制度的形式实现了人民的责任与反思和理性的良好结合”[21](P49)。现代宪法的核心目标就是创建一种帮助公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民主秩序,“一部宪法理所当然应促进协商民主,换言之,好的宪法应将政治责任与高度的反思、普遍的说理承诺结合起来”[22](P6)。宪法商谈的基本内涵就是基于宪法的协商、讨论和对话,“宪法对话……最重要的,即社会公众对宪法的讨论和交流”[23](P4)。宪法商谈不仅存在于正式的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运作之中,而且存在于非正式的社会领域。无论是在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层面,通过宪法框架下广泛的民主讨论和理性协商,不仅有助于保持商议性民主政府的活力,而且有助于发展公民的宪法美德,“宪法商谈有两个重要的美德:审慎和勇气”[24](P141)。宪法商谈是立宪政体保持稳健运行的规范模型,宪法商谈所追求的稳态民主社会,建立在民主协商和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这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前提。
宪法商谈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宪法商谈不仅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民主协商的制度框架,而且成为自由平等公民进行理性对话和互惠合作的基本方式。“宪法实施的本质也不是一个实施机关独断宪法规范含义的过程,而是一个人民就宪法问题持续性进行理性对话,不断展现宪法规范的道德内涵和语义深度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将增进政治共同体对共同善的理解和认识”[25](P196)。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商谈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内核,我国宪法规定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民主制度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的规范性程度。一方面,现代国家通过立宪构建开放、宽容、富有创造力的民主制度,通过民主制度的有序运行奠定了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正当性基础,宪法商谈使全体人民能够围绕公共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并形成理性共识。在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宪法对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的民主制度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体人民在宪法民主制度的框架内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制度优势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宪法商谈能够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汇聚在一起,契合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价值追求,真正实现了人民作为依法治国主体的宪法地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诉求、所行使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所创造的经验得到充分尊重,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义务在实践中得到切实履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也得到充分彰显。因此,宪法商谈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规范、引领和保障的重要功能。一般说来,宪法商谈主要包括正式的国家制度层面的建制化商谈和非正式的社会领域的日常商谈。通过宪法商谈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坚持依法保障全体人民享有广泛权利的基础上,通过法治实践整合社会行动与信念,逐步将宪法理念、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融入人民日常生活,进而让法治成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推进:国家层面的宪法商谈建制化
在现代法治国家,宪法商谈的理想内涵必须在国家法律体系的制度性框架内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宪法商谈仰赖宪法法律体系的制度化。习近平指出,我国宪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26](P215),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法规定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宪法法律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各种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它比较完善地体现着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不仅不依靠其他制度,而且它一经产生之后,就能够建立各种制度。凡是属于国家范围内的一切制度,都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建,或者经过它所授权的机关制定,并经它批准,才能生效”[27](P50)。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开放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现阶段的中国,离开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去谈民主,就会舍本求末、陷于空话”[28](P2)。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精神、发展民主制度、实现民主目标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遵循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因此,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着力点加强宪法商谈的建制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国家制度层面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公民享有广泛民主权利、不断扩大公民民主参与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存在诸多可以进行建制化宪法商谈的领域,如最具代表性的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的制度运作就是国家权力机关开展宪法商谈的生动实践。通过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实现宪法商谈建制化,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保障,可以为其他国家机构开展建制化商谈提供经验参考。一是信息公开制度。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要受到监督和制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重要原则,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要求。信息公开是确保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宪法实施过程中开展合宪性审查,还是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都需要各方公开证成其观点,“就最根本的层次来说,一个更多合作性、或者说更多参与性的政治体制,能够使公民身份所需要的标准内容更为丰富,同时,通过公开的权力角逐,它还可以更加全面地实现政治所具有的监护、或者说教育的作用”[29](P181)。通过建立在信息公开基础上的充分协商辩论,宪法商谈将使所有参与者明晰自身职责,理解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运行机理,将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作为正式国家层面宪法商谈的典范。二是公民权利保障制度。商谈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法治国家对基本权利和人权进行证立的程序主义理论,宪法商谈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国家切实履行公民权利保障义务的基础之上。宪法商谈直接体现了一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发展程度。众所周知,公民权利必须经由法律规范确认,才能获得法律上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作为公民身份的集中体现,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与国家履行尊重和保障人权义务的程度密切相关。尤其是当公民权利受到国家权力的不法侵害时,公民个人有权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提起诉讼或以其他方式请求救济。这意味着公民权利保障制度是经由宪法商谈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制条件。“在实行民主的社会中,某些原则是必须写进宪法中去的。这些即保证允许并保护公民从事参与社会管理所要求的各种事项的原则。这些保证就是民主的法制条件”[30](P121)。宪法商谈中最核心的民主权利是持有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保护公民持有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就是保护宪法民主制度运行的道德原则和实践条件,这也是国家制度层面进行有效商谈的基本前提。三是商谈责任制度。商谈责任主要对参与商谈的公权力行使者提出,要求其言论及主张必须向人民负责,在商谈过程中提出的理由及观点必须进行充分论证,这是有效商谈的规范性要求。落实商谈责任,不仅可以理性辨别和审慎反思参与者的基本观点,而且可以知晓何种主张和建议有助于达成價值共识和集体行动,保持各项民主制度之间的融贯性和协调性,并始终将人民至上的实质法治原则作为衡量宪法商谈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在加强上述配套机制建设时,要特别注意发挥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这不仅因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宪法商谈的质效,而且因为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决定着参与宪法商谈本身就是人大代表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基本职责,其履职能力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参与宪法商谈具有榜样作用和示范价值,这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的关键所在。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建构:社会领域的宪法商谈多元化
作为一种保持宪法生命力与稳定性的可行方式,宪法商谈不仅在现代国家的建制化领域得到普遍应用,而且在解决多元社会分歧、形成理性共识方面有着独特价值。这一点在非正式的社会领域得到充分体现,“民主制下的公民必须不仅要积极地、非独断地参与对权威的批判,而且要通过慎议追求相互理解而不是通过讨价还价或威胁去排他地追求个人利益”[31](P528)。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间进行沟通交流的语言与互惠合作的制度框架,宪法可以被定义成全体人民就涉及根本正义和公共善的问题,在宪法确立的民主制度框架下,通过运用公共理性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理由,最终构建有效平衡公共自主和私人自主的话语体系。在社会领域开展广泛的宪法商谈,既是培养公民基于自身的公民身份理解宪法民主制度价值意涵的基本途径,也是实现公民公共自主、有效维护社会团结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除了正式国家层面规范化的宪法商谈,也有广泛的非正式社会领域的宪法商谈,如人民团体之间的协商、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1982年对我国现行宪法修改草案的全民讨论,就是社会领域宪法商谈的生动实践,“全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充分体现了宪法的人民性与民主性,为宪法得到有效实施及凝聚宪法共识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在社会变迁中发展人民民主提供了规范与价值基础”[32]。社会领域的宪法商谈坚持人民是宪法最终实施者和捍卫者的价值理念,主张宪法实施的过程就是使宪法成为共同体共享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的过程,在宪法民主制度框架下的公共商谈不应仅仅面向正式的国家宪法制度和公权力行使者,而应同时面向所有普通公民、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基于宪法的商谈不仅可以形成对宪法的理解,而且能够塑造民族精神。宪法商谈并不是在一个真空里发生着,它可以发展我们对宪法的理解,同时将我们锻造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宪法商谈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既是形成宪法又是塑造我们社会的基本方式”[23](Pⅷ)。 社会领域的多元化宪法商谈形式不仅有助于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体系,而且能够培育公民的观念性宪法世界,帮助公民明晰其公民身份,履行其公民职责。
在宪法精神指引下根据不同的商谈主题建构类型化的宪法商谈模式,因地制宜设计出灵活高效的宪法商谈程序机制,帮助公民形成共同的观念性宪法世界,既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客观要求,也是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应有之义。目前,全国人大法工委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就是宪法商谈在社会领域的重要实践形式,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对关切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表达诉求,推动了人民有序参与国家立法过程,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更好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增加,辐射带动全国省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和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设立,形成三级联动的工作机制,搭建起基层群众共商共建共享的大舞台。 在多元社会主体对立法进行商谈的过程中,人民群众通过民主协商和共同讨论的方式,将对国家立法的相关意见和建议理性表达出来。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民主实践,不仅扩大了人民有序参与立法,而且通过民主协商方式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领域宪法商谈的生动体现。面对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宪法商谈既是培育共同体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督促公民承担公民义务、履行公民职责的基本方式,“政治平等、人类团结、互惠、公共性和责任,毫无疑问都是很重要的价值观念。但是,学习这些价值观念最好的方式是协商实践,而不是被别人告知”[33](P39)。此外,基层治理中建设民主法治村的“枫桥经验”、司法实践中的人民调解员、人民监督员、城乡社區里的村(居)民议事会、村(居)民论坛、民主恳谈会等形式,都可视为社会领域的宪法商谈实践。如果以促进根本正义和公共善的实现为目标的宪法商谈能够充分融入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普通公民都能积极参与宪法问题的讨论,宪法商谈无疑成为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最具活力的制度路径。多元化的宪法商谈形式,不仅促成了公民间普遍的相互理解与互惠合作氛围的形成,而且在实质上推动了国家与公民间形成和谐互动的伙伴关系,宪法由此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媒介和交流语言,并为公共生活中各种价值分歧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方案。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社会领域的多元化宪法商谈将唤醒公民的宪法认知能力,公民通过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宪法商谈实践,逐步养成依照正义和公共善原则行事的能力和品质,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厚植家国情怀。
参考文献:
[1]翟国强.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N].光明日报,2022-02-28.
[2]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J].政法论坛,2022,(3).
[3]黄文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政法理论述要[J].行政法学研究, 2023,(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5][美]塞拉·本哈比.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7]Randall Peerenboom.Ruling the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Law:Reflections on the Rule and Role of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J]. Cultural Dynamics,1999,(3).
[8]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
[9]杰弗逊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0][美]玛丽安·康特斯布尔.正义的沉默:现代法律的局限性和可能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3.
[12]莫纪宏.党的领导是鲜明优势[N].人民日报, 2018-08-31.
[1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4]王均伟.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N].人民日报,2022-03-29.
[15]周佑勇.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思维方法[N].人民日报,2022-08-29.
[16]王旭.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J].法学论坛,2023,(1).
[17][美]罗纳德·德沃金.民主是可能的吗?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8][英]巴特·范·斯廷博根.公民身份的条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19]沈春耀.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N].人民日报,2022-12-27.
[20]J.Mitchell Pickerill. Constitutional Deliberation in Congress:The Impact of Judicial Review in a Separated System[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21]Cass R.Sunstein.Infotopia: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2]Cass R.Sunstein.Designing Democracy:What Constitutions Do[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3]Melvin I. Urofsky. Dissent and the Supreme Court: Its Role in the Courts History and the Nations Constitutional Dialogue[M].Pantheon Books, 2015.
[24]Conrado Hübner Mendes. Constitutional Courts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25]王旭.憲法实施原理:解释与商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26]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27]许崇德,何华辉.宪法与民主制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28]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29][日]猪口孝,[英]爱德华·纽曼,[美]约翰·基恩. 变动中的民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30][美]科恩.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1][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32]韩大元.论我国现行宪法的人民民主原则[J].中国法学, 2023,(1).
[33][澳大利亚]约翰·S. 德雷泽克. 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责任编辑:王篆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and Promotion Path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to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Dai Jitao
Abstract: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has made 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s in the Marxist theories on the rule of law at the political, legal and academic levels, and provides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not only has clarified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principles, established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of rule of law, and strengthened the long-term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but also requires enhancing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should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dhere to and improve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fully implement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that the state respects and protects human rights in practice. Constitutional deliberation has important normativ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Enhancing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we should take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es as the center,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deputies to the peoples congresses for keeping close contact with the people through constitutional deliberative institutionalization, build a multi-disciplinary,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forms of constitutional deliberation, and cultivate the conceptual constitutional world of the citizens.
Key words: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deliberation, the conceptual constitutional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