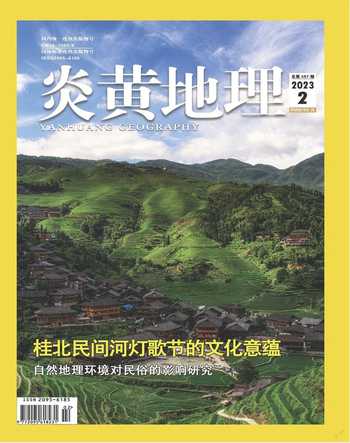略论康有为域外行旅经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生之影响
2023-05-30黄肖嘉
康有为所主张的民族融合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种民族融合思想的形成与其域外行旅经验密切相关。康有为在游历海外时,通过考察对比各国发展情况,产生了建立现代统一民族国家的意识,从而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强调民族融合时,他并不重视生物性血缘的同源性,而重视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
自从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家精神的理论范畴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回溯这一范畴的理论渊源、历史语境和流变机制时,许多学者注意到清末立宪运动前后(1905—1911)康有为的民族融合论,认为从中能窥知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政治表达的开端。
中华民族融合认同的事实古已有之,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自觉则发生在晚清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不断有朝廷官员被派往西方国家进行政治考察或担任驻外公使,也有许多民间知识分子远涉重洋求學或游历。而康有为民族融合论思想的形成便离不开他游历域外时的见闻与思考。异国的政治局面与风土人情给予了他反观本国社会状况的参照视角,使他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思路逐渐清晰,从而认识到民族团结对于挽救国运的重要性。正如与他同属立宪派的梁启超所言,“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1]。而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初衷正是“凡夫政教、艺术之同异得失,靡不取而?绎之,比较之,斟酌而选别之,萃群族之所长,择己国之所适”[2]。
源自现代统一民族国家意识的民族融合思想
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派往海外的官员与自费留洋的民间知识分子尚没有形成明晰的国家意识,而是继续秉持模糊的“天下观”“朝代观”。例如1847年受聘至美国工作的林鍼称域外各国为“化外”;又如徐继畲为1866年被派往欧洲游历的斌椿所著《乘槎笔记》撰写序言时称我国为“天家”等。
而康有为出洋的年代已是19世纪末。他于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数月后迫于清政府压力转至加拿大温哥华,又于1899年4月来到伦敦,此后直至1913年,他辗转漫游欧美各国及日本达16年之久。在这一时期,国人已在与西方国家的接触中树立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在自述时也不再使用“我朝”“天朝”等字眼,而是自称“中华”“中国”“国人”等。
康有为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要求明确国家疆界,坚持国家统一。他撰于1902年的《大同书》虽然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意味,却也在政治实体层面提倡加强边疆多民族地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今蒙古、新疆、东三省之民俗……若德、俄、奥之北鄙……此则与中国蒙古、东三省之穷民同其苦患,益可哀怜矣。夫满堂饮酒,一人向隅而泣则为之不乐”[3]。康有为因新疆、蒙古、东三省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远离主流文化核心而将之视为苦寒之地,希望能将之纳入统一国家的“满堂”格局中,像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大家共同发展,同享团圆欢乐。
这一思想源于与英、德、俄、奥等西方国家之现实对照之后,直至立宪运动仍未改变。康有为游览欧美各国,将国外情形与本国相印证,更加坚定了其通过加强民族融合来助推国家强盛的愿望。他于1904年提到“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4]。因看到爱尔兰、苏格兰等少数民族区域在政治归属上同属英国的事实后,他想到“拓跋、契丹、女真、蒙古之强盛,亦终必合于中国,徒为中国之促进扩大而已”[5],认识到中华民族是由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构建而成的。而这一历史进程与德意志、意大利、瑞典等民族国家在19世纪的统一独立颇为类似,均属建立“大同”社会的必经阶段,即消除民族对立,“若夫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则今日未至其时。然欧美人者,亦渐趋就是势矣”[6]。
因为康有为不遗余力地坚持政治区域意义上的国家统一,而民族融合又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所以,他把民族融合作为贯穿其建国方案始终的思想内核。这一点与立宪运动时期章太炎等人倡导的“排满革命论”截然不同。他在1902年讲到“欲抗外而自保,则必当举国人之全力……昔戊戌在京时,有问政体者,吾辄以八字言之,曰‘满汉不分,君民同体……故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满洲”[7]。 康有为虽然主张以国外经验与本国互鉴互证、以此寻求本国变革之法,却不欲照搬一切,而是以中国的主体性选择为出发点,以自强、自保为宗旨。他不能理解革命派动辄援引美国与法国之内讧、以“攘夷别种”立场攻击满人的做法,而始终认为维护国家领土统一、避免国家陷入分裂是救国、建国的第一要务,德国、意大利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强国,正是因为结束了国内小邦林立的分裂状态,而以“满洲”地区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地区如果不着意联络,便会酿成内乱,使国家陷入分裂。
康有为之所以如此抗拒革命、倡导民族融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在游历欧洲时对法国大革命的残酷后果心有余悸,深刻领会到骤然的暴力革命容易使各省离心离德、国家分崩离析,而法国虽然暂未分裂,亦为时不远,只有团结各民族的立宪政治才能拯救中国。“中国不当谬倡革命……罗伯卑尔诸贼,行其酷毒之极点”[8]。因此,康有为认为中国绝不可独尊汉族、盲目“排满”,引起民族矛盾。他对比了欧洲各国立宪与革命的经验,指出凡立宪之国,皆国势稳固,民权伸张,百姓安享自由;但法国革命、印度各省分而自立之后,其国家命运已至丧乱灭裂之境。虽然康有为侧重强调大革命群众暴力的残酷性、而少谈革命派的经济军事政策,但从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派放弃排满立场、提倡“五族共和”的举措来看,他团结满汉、民族融合的思想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
应当注意的是,康有为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而提倡民族融合,这正表明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性。近现代以来,对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认同与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基本一致,保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反侵略斗争正是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为号召的。国内学界对统一的政治实体意义上的“中国”的理解其实非常接近“中华民族”,例如费孝通先生认为,虽然国家与民族是不同的概念,但是“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9]。康有为的民族融合论虽然并未涉及各民族之间的“多元一体”关系、而侧重强调同质性,却表达了一种模糊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了最初的思想框架。
文化认同重于血统同源
章太炎等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序种姓上第十七》等文中将满族视作东胡后裔,与华夏汉族从生物性血缘上并非同一种族,因而应作为异类来加以驱逐。而康有为却认为,文化认同比血统同源对于民族的形成与融合来讲更为重要,即便满族汉族从悠长久远的的历史线索来看存在种族不同的事实,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也会接受同一种文化,也已在救亡图存、挽救国运等主流意识形态上达成共识,从而形成民族认同;而某一民族的后裔即便属于同一种族,因为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风俗文化习惯,形成不同的民族。例如满人、蒙古人与汉人,没有必要特别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如果说满人政府的专制统治有不善之处,那也是从汉、唐、宋、明等汉人政权继承而来,并非满人所特制,更与民族区别问题本身无关。从这一意义上讲,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在文化上的交往依存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是无法割裂的。
加之旅居俄国时有感于俄之强大,康有为提出哪怕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等地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屬于不同种族,为了国家的强大,也必须“旁纳诸种”“国朝之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俄罗斯所以为大国者,岂不以旁纳诸种之故?然则满洲合于汉者,乃大有益于中国者也”[10]。相反,鉴于印度的亡国,康有为认为全都是被国内民族疏隔、地域分裂所致,在短短数十年间种族尽灭而被英国所制。因此不难看出,康有为提倡民族融合的逻辑是闭环的,融合—保国—保种—必须融合,如果如法国、美国一般发动“攘夷别种”的内战式革命,便会引入打破这种闭环、使国家陷入动荡的因素。并且,康有为还认为汉人在清朝并未受到歧视,而是得到了应有的政治待遇,并列举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担任高官的例证。
康有为对德国的社会发展状况感触尤深。他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统一,固然因为日耳曼民族在国民人数中所占据的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因为德国语言文字的同质性,而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表征,这种文化同质对政治层面国家统一的助力不仅体现在国内,还令邻国的日耳曼人对德国产生归附之意,“德意志之自立也,以全邦语言文字一致也”[11]。德国人令波兰人放弃斯拉夫语族的波兰语而改用德语,撒丁王国通过舍弃本国的萨丁尼亚语而采用影响最广的佛罗伦萨方言作为意大利标准语,这都是出于国家统一的需要。而与德国毗邻的奥匈帝国虽然也有三分之一人口属于日耳曼民族,其余民众的文化风俗却各不相同,各邦又不满于中央王朝统治力的孱弱,所以康有为断定,待皇帝去世、匈牙利独立后,整个国家必将分崩离析,“夫奥也,十四州语文不同,各日月谋自立……于是坐视其强邻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则袖手待亡”[12]。一战之后奥匈帝国解体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推断。当他行至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时,更有感于因文化传统的驳杂、没有统一的政治文化建设而使民众对政府和国家的向心力不强,“民心既难一致,国亦最难统一,盖与突厥异种,久僻边方,无立国之观念感于其心。”[13]
有鉴于此,康有为认为昔日中国因交通不便,且周边多为经济贫困的弱邦小国,所以滋生了盲目自大的情绪,以天下自居,只有历朝历代改换门庭时的不同名号,而无国家与民族之名称;而如今国内外交通发达,国人足迹远布海外,自然应改变观念。因为部分国人已树立了列国平等的民族国家观念,所以应当摒弃“满族”“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等各种不同的民族名称,统称“中华”,将国名也定为“中华国”,不要如革命派所倡导的那样突出满汉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大家都团结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如此不但不会有革命暴乱之忧,国家强盛也指日可待。
当然,这种忽视民族差异、单纯强调民族合一、甚至主张少数民族完全化入汉族的观念其实并不符合中华民族经过漫长的锻造过程所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不过,这种观念在当时持有民族共和观点、且考察过西洋诸国政治文化情况的人中并不罕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早在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时,便有过“满洲之与中国,早已合同而化;倘尚强分满汉,满洲何以自存”的感慨[14]。1905年受清政府委派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也在日记中提出哪怕种族习惯各异,只需有文化认同感,亦能团结一致走向富强,“窃观彼富强之故……必有同相维系之谊。种族风土各殊,而心理则一”[15]。并且,他在日本访问伊藤博文,向其请教变法自强、施行宪政的方法时,对方也提到中国因幅员辽阔而导致的各省民情相差甚远,语言文化殊异是制定统一政策法律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无独有偶,与载泽同时出洋的戴鸿慈在考察奥匈帝国与俄国的政体时,也是从文化认同角度来预判两国的命运,“国中人种混杂,语言庞殊,有如异国。夫种族不统一,国语不统一,例之物质,则其分子游离,无爱力为之固结,欲不瓦解难矣”[16]。
这表明,康有为等人提倡民族融合时是有着明确现实考虑的。他们面对印度、波兰由于文化向心力不强而导致国家分裂或陷落的前车之鉴,依靠先知外事、预忧国难的政治前瞻性,喊出了“君民同治,满汉不分”的口号[17],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期,以弥合民族区隔为切入点,探索救国之路。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书中提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这种“对抗”不仅指政治上的博弈和军事上的战争,也包括文化思想领域的对照与借鉴。康有为的域外行旅经验促使其民族融合思想得以塑型,进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并非孤例,而是我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在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历史性选择。还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现场,对于当前的民族精神塑造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2][16]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3][10]康有为.康有为全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8]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M].长沙:岳麓书社,2008.
[5]康有为.英国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7.
[6][11]康有为.德意志等国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7.
[7][17]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M].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12][13]康有为.西班牙等国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6.
[14]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5]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序[M].长沙:岳麓书社,2008.
【作者简介】黄肖嘉(1983—),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