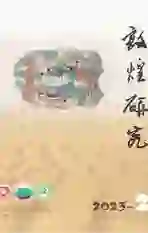敦煌壁画中的蜀葵:从药用到礼佛
2023-05-30岳亚斌张田芳
岳亚斌 张田芳



内容摘要:蜀葵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花卉之一,唐初始见于敦煌及周边石窟壁画,晚唐以后频繁地出现于敦煌莫高窟和吐鲁番地区的石窟壁画中,多见于菩萨、药师佛以及供养人的手中或盘中。表现手法各有千秋,或工或略,或写实或写意,取决于画工的审美意趣及对绘画技法的掌握程度。蜀葵入于石窟,不惟其花本身之高大、笔直、花色娇艳,更重要的因素在于蜀葵本身的药用功能。尤其是永徽四年,蜀葵用于治疗早期天花,疗效甚好,故而被赋予复生与禳灾之意蕴。同时,密教文献中也多次提到建坛城时用蜀葵擦拭,尽显其药用功能。因此蜀葵由药用而成为礼佛的供品,是石窟壁画的一种稀见现象,应引起关注。
关键词:蜀葵;敦煌壁画;礼佛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2-0001-10
Hollyhock in Dunhuang Murals:From Medicine to
Flower Offerings for the Buddha
YUE Yabin1 ZHANG Tianfang2
(1. College of Fine Ar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2. Dunhuang Textual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730030, Gansu)
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he northwest regions of China, hollyhock flowers first appeared in the cave murals of Dunhuang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before appearing frequently in the murals of the Mogao Grottoes at Dunhuang and the cave temples in Turfan beginning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flowers were either held in the hands of bodhisattvas, the medicine Buddha or donors, or were placed on plates. Many different artistic styles were used to depict hollyhocks—sometimes elaborately or in simple sketches realistically or in a more freehand rendering—which seems to have depended on the aesthetic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painters and their mastery of painting techniques. Hollyhock became popular in cave murals not only because its shape and beautiful colors fit well with other elements of Buddhist art, but also because it was known to possess medicinal properties. Especially after the fourth year of the Yonghui era(653 CE) when hollyhock was used effectively to treat small-
pox, the flowers became endowed with connotations of resurrection and the avoidance of calamity. In addition, hollyhocks are also mentioned frequently in Esoteric Buddhist scriptures as being used to wipe or scrub surfaces clean, especially when creating a Mandala, which further cement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ollyhocks and health and cleanliness. It can be concluded for the above reasons that hollyhock flowers became popular offerings to the Buddha because of its connection to health and healing; the inclusion of these flowers in Dunhuang cave murals following a period of calamity in the region is also worthy of careful attention.
Keywords: hollyhock; Dunhuang wall paintings; worshipping Buddha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問题的提出
蜀葵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花卉,花色艳丽,不仅有较好的观赏价值,还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我国很早就有蜀葵的记载,深受历代文人雅士及画家的追捧,因其特点称为“忠孝”之花。笔者在石窟考察中发现,蜀葵从唐代就出现在敦煌壁画中,尤以晚期石窟为最。如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第9窟主室北壁、第16窟甬道北壁、第83窟西壁南侧、第97窟西壁龛内、第310窟西壁龛外南北两侧、第164窟西壁龛外南北两侧、第169窟西壁龛外南北两侧、第207窟、223窟东壁门上、第245窟西龛外北侧、第281窟南壁、第309西壁及北龛北壁、第339西龛外南侧、第367北壁、第408东壁南侧,榆林窟第25窟主室西壁南北侧、第17窟等,还有敦煌周边的天梯山石窟、吐鲁番石窟以及高昌回鹘时期北庭古佛寺中都有绘制。非常特别的是,蜀葵出现在石窟中的时间与佛经对蜀葵的记载完全吻合,佛教密教文献中常常以药物礼佛,这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
学界虽不乏对莫高窟壁画植物花卉的研究,但对蜀葵的研究极少。近年来,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植物,但仅有只言片语,如韦秋紫对唐五代敦煌壁画中出现的植物做了梳理,虽罗列了蜀葵图像却不识其名而以“杂花”称之[1]。王胜泽对西夏石窟中出现的蜀葵形象做了分析,并提出“西夏新样”之说,认为蜀葵出现于西夏石窟与华严思想在西夏的流传和蜀葵所蕴含的 “忠贞”思想有关[2]。其文称蜀葵在西夏石窟中以装饰画的形式大量出现的,所言非虚,但是否属于“西夏新样”却有待商榷。张秦源对西夏葵纹植物做了分析,认为莫高窟第409窟中的回鹘王妃手中的长柄花就是蜀葵[3],惜未对西夏之外的蜀葵图像予以关注。
蜀葵本为普通的植物花卉,何以成为佛教礼佛供品,甚至在密教仪轨中为必备之花,颇值得深究。
二 蜀葵在敦煌石窟中出现及其定性
蜀葵[Althaea rosea(L.) Cavan.]是我国古代传统栽培花卉,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郭璞《尔雅注疏》曰:“菺,戎葵。今蜀葵,似葵,华如木槿华。”[4]蜀葵耐干旱抗贫瘠,环境适应性强。《广群芳谱》言葵:“本丰而耐旱……甚易生,地不论肥瘠。”[5]蜀葵喜阳,耐瘠薄,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在肥沃土壤中会生长得更茂盛。《花镜》曰:“若栽于向阳肥地,不时浇灌,则花生奇态。”[6]《农桑辑要》记载:“地不厌良,故墟弥善;薄即粪之,不宜妄种。”[7]蜀葵有对环境极度的适应性以及对不良环境的抗逆性,在适宜的栽培条件下则有助于产生新的蜀葵类型。蜀葵分布极广,各地命名不同。古时除菺、戎葵、蜀葵之外,亦有吴葵、芘芣、一丈红、红葵、卫足葵、秋葵等。
通过对敦煌石窟壁画中蜀葵图样的梳理,笔者发现,蜀葵在唐初就已出现,经历五代、宋、回鹘、西夏至元,是敦煌壁画中除莲花以外出现频率最多的花卉。蜀葵在壁画中的艺术表现手法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写实型。遵循蜀葵的自然属性进行双勾描摹,而后以分染法对其进行渲染,色彩内深外浅,以花头为甚,从而表现出花瓣的层次与色彩变化,形成凹凸之感。有些花瓣上甚至还用小笔丝出其平绒之质感。叶子如掌,型如锯齿的边缘以线条勾勒,再以平涂法填染色彩,与分染表现的花朵形成虚实对比关系。如武威天梯山石窟初唐第3窟右壁龛下边第一层三身伎乐天左侧一株,莫高窟盛唐第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府人供养像旁的蜀葵,莫高窟晚唐第9窟维摩诘经变中的蜀葵等,这种形式初唐和盛唐居多;第二,折枝花型。折枝花是中国绘画中常用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壁画中则大多出现在供养人或菩萨手中,有干有叶有花朵,有的甚至带有花苞,把握蜀葵的基本特点进行绘制,待勾线完成后,再随类赋彩。如武威天梯山石窟盛唐第2窟拈花菩萨手中的一朵;第三,装饰图案型。能够基本遵循蜀葵的自然属性,取其一花数叶进行绘制,在技法上依然运用双勾填色,但整体造型上采用极为对称的图式,并以二方连续的设计表现形式出现在菩萨周围,头部两侧居多,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如榆林窟第25窟主室西壁南侧普贤菩萨(图1),这种形式在敦煌及周边石窟中比较多见,尤其是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收藏的敦煌出土绢、麻、纸本画中更为普遍。另外,还有一些同样具有装饰意味的蜀葵图式与祥云图案一起呈现在几个飞天之间,这样既填补了画面的空缺,也使得整个画面浑然一体,画面转换自然天成。诚然,上述三种类型的表现手法不落窠臼,或工或略,或写实或写意,完全取决于画工的审美意趣及其对绘画技法的掌握程度。
唐代佛寺壁画中菩萨头顶有画葵习惯,宋代著名诗人、藏书家尤袤《全唐诗话·崇仁坊资圣寺》载:“团塔上菩萨,李真画。四面花鸟,边鸾画。药师菩萨顶上,茙葵尤佳。” {1}《图画见闻志》卷5《资圣寺》亦云:“团塔上菩萨,李嗣真画;四面花鸟,边鸾画。当中药上菩萨,顶上茸葵尤佳”。[8]这两部著作虽然都对资圣寺药师菩萨顶上所绘之“葵”做了记载,但出入很大。《全唐诗话》中曰“茙葵”,即蜀葵。《图画见闻志》曰“茸葵”, “茸”即“戎”之諧音,即戎葵,就是小的蜀葵花。《本草拾遗》曰:“蜀葵小花者,名‘锦葵,一名 ‘戎葵。[9]可以肯定的是,《图画见闻志》中的“茸葵”和《全唐诗话》中的“茙葵”皆为蜀葵。壁画中的葵纹图式较多,葵的种类难以遽断,借由《本草纲目》的记载或可获得正解:
葵有蜀葵、锦葵、黄葵、终葵、菟葵,皆有功用。时珍曰:葵菜古人种为常食,今之种者颇鲜。有紫茎、白茎二种,以白茎为胜。大叶小花,花紫黄色,其最小者名鸭脚葵。其实大如指顶,皮薄而扁,实内子轻虚如榆荚仁。四五月种者可留子。六七月种者为秋葵,八九月种者为冬葵,经年收采。正月复种者为春葵。[10]
敦煌壁画之“葵”纹图样可分为两大类,一者为蜀葵;二者为黄蜀葵(Abelmoschusmanihot(L.) Medic.)。黄蜀葵为锦葵科、秋葵属,一年生或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别称较多,有棉花葵、假阳桃、野芙蓉、秋葵、黄花莲、鸡爪莲等,不是蜀葵中的黄色者。两者同科不同属,外形上极为相似,但细观有差别。黄蜀葵始载于《嘉祐本草》,其后历代本草均有记载。《本草纲目》引其文曰:“黄蜀葵,近道处处有之。春生苗叶,颇似蜀葵,而叶尖狭长多刻缺。夏末开花浅黄色。六七月采,阴干之。”[10]1045《本草纲目》又引宋寇宗奭《本草衍义》云:“黄蜀葵与蜀葵别种,非是蜀葵中黄者也。叶心下有紫檀色。”[10]1045如黄蜀葵叶掌状深裂,裂口比较多,大约有5—9个深裂,单个的裂片为长圆状披针形。叶柄要比蜀葵长,大约长6—18cm左右,若鸡脚。蜀葵叶裂口较小,大约有5—7个浅裂或是波状棱角,单个的裂片为三角形或圆形,似鸭蹼。叶柄要比黄蜀葵短,长度约5—15cm左右。花朵不同,黄蜀葵的花朵颜色为淡黄色,里面部分呈紫色,花朵直径约12cm左右,比蜀葵稍大。蜀葵的花朵颜色很多,有红色、白色、黄色、紫色等,花朵比黄蜀葵稍小一些,直径约6—10cm左右。唐代山西籍诗人唐彦谦作《秋葵》诗云:“月瓣团栾剪赭罗,长条排蕊缀鸣珂。倾阳一点丹心在,承得中天雨露多。”[11]其描述符合黄蜀葵的生物学特性,“长条排蕊”指黄蜀葵花的雄蕊柱,呈现条状;“倾阳”指出黄蜀葵花的趋光性,黄蜀葵花对光线敏感,如同向日葵一般[3]123。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本观音菩萨像(图2),左侧观音菩萨手中所拿之花就是就黄蜀葵。张秦源认为榆林窟第10窟西夏壁画中出现的为黄蜀葵,形象逼真且生动。莫高窟第409窟回鹘王妃的供养图中(图3){1},王妃手持的蜀葵花枝有对生的花蕾和宽大的掌状叶,与现实中的蜀葵花近乎一致,唐宋时期也称蜀葵为千叶戎葵[3]124,可以信从。此外,第409窟墙壁也有大量的蜀葵。北京市八里庄发现的唐开成三年(838)幽州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王公淑墓中也绘有秋葵图,位于墓室北壁《牡丹芦雁图》“东边芦雁的身后,有一株秋葵,叶大花茂,枝叶伸展”[12]。
与之大体同时的吐鲁番石窟中也出现了蜀葵花。柏孜克里克第20窟门廊上的智通都统、惠通都统、法惠都统三个和尚均双手合于胸前,手持长柄花枝[14,15],叶片近圆心形或长圆形,边缘齿状,如鸭掌。花瓣5枚,边缘波状,齿裂,单瓣,从花蕊根部向外渐变——由深及浅,不仅与《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的蜀葵(图4)十分相近,更与现实中蜀葵的植物学特征完全吻合,可以断定它就是蜀葵。柏孜克里克第16窟回鹘贵族群像供养人,上下两层共有16人,有部分的供养人双手合于胸前持长柄蜀葵花[16]。同时在柏孜克里克第20窟、第65窟、吉木萨尔北庭回鹘佛寺以及拜西哈石窟第3窟等石窟中都能找到蜀葵的影子。而柏孜克里克第35窟回鹘王供养人像、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南塔道口出土的回鹘亦都护供养像以及西大寺S105殿八王争分舍利图西壁下方回鹘长史和依婷赤公主供养像等,持花供养人图像与莫高窟第409窟的图像如出一辙,可见敦煌和吐鲁番之间是相互关联的[17]。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蒙古人征服高昌回鹘以后,柏孜克里克第27窟有蒙古女供养人手持长柄蜀葵的图像。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的绘画技法和艺术特点“与吐鲁番回鹘时期的柏孜克里克壁画接近,与敦煌千佛洞唐五代宋时期的壁画也有相似之处”[18]。可见,高昌回鹘时期,无论是回鹘王、王妃,还是回鹘贵族供养人像,均喜欢手持蜀葵。
从唐代墓室壁画、敦煌与周边石窟中的蜀葵图以及《图画见闻志》中的“茸葵”可知,资圣寺药师菩萨头顶所绘之葵,当为“蜀葵”无疑。
三 蜀葵的药用性与壁画的内在关联
蜀葵为何在唐代出现于敦煌及周边石窟壁画中,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固定下来呢?首先从艺术学的角度言,蜀葵本身从视觉上具有成为艺术母题的资质。蜀葵植株高达2m,甚至3m,挺拔俏丽,叶片大,且花色艳丽多样,从花、叶、梗都符合艺术家对一种植物美的想象。但它与宗教结合起来,成为宗教壁画符号,却并非单纯因为美观。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除了晚期石窟中以装饰的形式出现在壁面的蜀葵外,蜀葵在壁画中常出现于药师佛头顶、菩萨头顶或手中、盘中以及供养人手中。首先,在诸佛画像中,蜀葵多出现在药师佛头顶(图5)。药师佛掌医药,念诵其名号不仅能增长福慧、积累功德,还能令众生消灾延寿,远离病痛,蜀葵与药师佛连在一起当为药用功能的体现。其次,蜀葵在观世音、文殊、普贤、大势至、不空绢索、千手千眼观音等胁侍菩萨的手中或盘中多出现。菩萨所持花草一般都是有寓意的,旨在施药于众生,令其从病苦中解脱出来。如藥王菩萨一般会以拇指、中指、无名指执持药树。是知,蜀葵在菩萨手中依然是以药物的形式出现的。其三,蜀葵在敦煌和吐鲁番石窟中诸多供养人手中也是频频出现,尤其是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贵族供养人手中的最多。德国回鹘学家葛玛丽(A. von Gabain)对这种现象做过如下解释:
这些花的原形是某种被认为能够起死回生的药草。在巴泽雷克(Pazyryk)古墓地毯上有这么一幅画:端坐的(冥府?)女神把一株既开花又结果的树枝置于一个(已死的?)骑士面前。墓室里采用这种题材的地毯,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花能让死者重获新生。[19]
诚如葛玛丽所言,佛陀及其他的侍从们是不用持花的,因为他们已达到不生不死的涅槃境界。世俗中的众生要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故而他们需要带花。其意愿有两种:一是希望已故的亲人能往生净土,重获新生;二是希望活着的人无病无灾,生活安乐。斯坦因在敦煌所获开宝四年(971)的观音及供养人像图中下层有六身供养人,左侧三身为女,右侧三身为男,每个人前方都有题记,除了站在最前方已故的父母手中各持花一朵外,其他人则没有持花[20]。葛玛丽认为持花者为死去的人,而没有持花的人是活着的人。亡人手中持花,以表子女对父母再生的期盼,希望父母往生净土[19]166。从图像上无法判断已故父母手所持之花是否为蜀葵,但从两侧供养菩萨盘中所盛之花的外形可以看出,与现实的蜀葵非常相似。这种情况在藏经洞发现的唐宋时期的绢、麻、纸本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三个位置无不表明蜀葵在敦煌壁画中出现与它的药用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第82窟表现的更为明显。在该窟《射物禳灾图》中出现了几株大个的蜀葵(图6)[21] 。高昌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禳灾的习俗,史载:
(高昌)俗好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以银或鍮石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22]
将蜀葵与禳灾相联系,犹道教禳灾之与灵芝仙草也。蜀葵嫩叶及花可食,皮为优质纤维,全草入药,有清热止血、消肿解毒之功,对吐血、血崩等症有显著的疗效。李时珍《本草纲目》对蜀葵叶、根茎、花及籽入药有详实的记载[10]1042-1044。成书于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的方剂书《外台秘要》卷3则有葵菜叶治疗天花的记载:
文仲陶氏云:“天行发斑疮,须臾遍身,皆戴白浆,此恶毒气方。云永徽四年(653),此疮从西域东流入海内,但煮葵菜叶、蒜、韭,啖之则止。鲜羊血入口,亦止。初患急食之,少饭下菜,亦得。”[23]
据宋岘先生考证,这里的“天行发斑疮”就是流行于中亚、西亚的天花病,此病在唐永徽四年经由波斯人传至高昌[24]。《外台秘要》中用煮葵菜叶和蒜、韭混合食用以为治疗天花之方。北宋王怀隐、王祐等奉敕编写《太平圣惠方》以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对此都有记载。
葵类植物品种多样,诸葵形状“虽各不同,但性俱寒滑,故所主疗不甚相远”[10]1046。从药用功能而言,上述葵类植物都有可能。比如龙葵,叶子含有大量生物碱,须经煮熟后可解毒。全株入药,可散瘀消肿,清热解毒。《本草纲目》曰:“(龙葵茎、叶、根)疗痈疽肿毒,跌扑伤损,消肿散血。”[10]1047除龙葵外,蜀葵和黄蜀葵亦有消肿解毒、排脓解毒之疗效。尤其是黄蜀葵,为治疮之要药。又云:“(黄蜀葵)花(气味)甘,寒,滑,无毒。主治小便淋及催生。治诸恶疮脓水久不瘥者,作末傅之即愈,为疮家要药。”[10]1045天花盛行之初称为“斑疮”,说明人们把它当“疮”来对待,因此采用清热解毒、化脓除疮的葵类植物来治疗天花。这一事件对吐鲁番的影响既深且巨,及至清代,吐鲁番的建筑和地毯还能见到蜀葵图样。结合敦煌和吐鲁番石窟壁画中的蜀葵图,笔者认为这里的葵极有可能是蜀葵或黄蜀葵。
河西地区自汉代以来就有使用各种葵类植物的历史。如肩水金关发现的简牍中就有对黄蜀葵的记载,73EJF2:47A:“黄葵六分,人参六分,石□三分。凡十物白□一升槖脂一升(□/)。”[25]6该简虽残,但能确定其为医药简,说明汉代戍边的将士已用黄蜀葵入药。不仅如此,葵菜更是生活必需品,如木牍73EJF3:212AB云:“□坐前:毋恙,前见不一二,叩=头=。因白:幸为并请麹一二斗及葵一二斗,所□请之,叩=头=,幸甚!为见不一二,叩=头=,谨使再拜。”[25]45此牍为一封书信,写信人、收信人姓名不详。主要内容是某人写信求一二斗酒曲(麹)和一二斗葵菜。再如73EJF3:38“(□/)买葵韭葱给刁将军、金将军家属”[25]11; 73EJT37:1479“(□/)葵子五升直廿”[26]。从这些汉简中,可以窥见葵菜,戍边将士常用作蔬菜。他们写信向别人求葵菜,还记载葵的价格及种植的情况。居延汉简中还有种植和买卖葵菜的记载。506.10A云:“城官中亭治园条,韭三畦,葵七畦,葱二畦,凡十二畦,其故多过条者,勿减。”[27]EPT2:5B载:“葵子一升,□遣使持门;菁子一升,诣门下受教愿□(□/)。”[28]不唯汉简,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对各种葵类药草治疗疾病也有记载。如敦煌写本P.3930治鼻疳方用“葵根灰”,治疳食龈方葵根灰入药[29]。吐鲁番出土龙谷530号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第582行“防葵毒,用葵”[29]579;同件第574行“蜀椒毒,用葵子汁,煮”[29]579;同件第710行“冬葵子,葵根,解蜀椒毒。”[29]579 这些都反映出河西及吐鲁番地区有悠久的葵类植物使用历史。《维吾尔简易验方》也有许多用蜀葵治疗脓疮、淋病的记载,如主治脓疮、疥疮及顽固性皮肤病的“验方十三”:圆柏根(10克)、蜀葵根(10克)、明矾(炮制)10克,小蘖根(10克)[30]。主治蛀牙热性淋病的“验方十六”:蜀葵子10克,菲岛铁线草10克,莴苣根10克,芹菜子10克,甜瓜子10克,西瓜子10克,红花子10克,冰糖30克[30]292。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河西及吐鲁番地区自汉代以来就有使用蜀葵的历史,既可入药,又可食用,而且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由是以观,蜀葵成为敦煌石窟壁画中的礼佛之物,完全合乎情理。
四 蜀葵之药用功能及其与礼佛关系蠡测
佛教对世俗众生的救赎是身心两方面的,佛教医药是佛教能够在中土迅速传播的重要因素。佛教初传之时,域外僧侣为了能够在中土立足,往往与域外医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僧伽大师从粟特僧侣到中土至尊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精通西域医药,通过幻术将域外医药与宗教结合来达到传教的目的。蜀葵的药用功能在唐代已经得到共识,在一些民间故事中就有关于佛教僧侣借蜀葵来传教的记载。《太平广记》卷67有唐陈劭《通幽记·妙女》,云:
唐贞元元年(785)五月,宣州旌德县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见一僧,以锡杖连击三下,惊怖而倒,便言心痛,须臾迷乱,针灸莫能知。数日稍间,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复食,食辄呕吐,唯饵蜀葵花及盐茶。既而清瘦爽彻,颜色鲜华,方说初昏迷之际,见一人引乘白雾。至一处,宫殿甚严,悉如释门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头赖吒天王小女,为泄天门间事,故谪堕人间,已两生矣。[31]
这则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不仅展现了蜀葵治疗吐痢的药用功能,还将其与佛教的关系呈现给读者。笔者在检索文献时发现,唐之前的佛经对蜀葵鲜有记载,而唐代佛教文献中频频出现,尤以密宗文献为最。如唐代密教典籍《建立曼陀罗护摩仪轨》、唐慧琳集《建立曼荼罗及拣择地法》、不空译《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新译仁王般若经陀罗尼念诵仪轨序》,以及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等都出现了蜀葵。唐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灌沐尊仪》云:
西国诸寺……草木之花,咸将奉献,无论冬夏,芬馥恒然。市肆之间,卖者亦众。且如东夏,莲华石竹,则夏秋散彩,金荆桃杏,乃春日敷荣。木槿石榴,随时代发,朱樱李柰,逐节扬葩。园观蜀葵之流,山庄香草之类,必须持来布列,无宜遥指树园。冬景片时,或容阙乏,剪诸缯 ,坌以名香,设在尊前,斯实佳也。[32]
西国建寺造像、燒香礼佛有严格的程序,四时花虽多,但蜀葵、香草是“必须持来”礼佛供养之花。寺院中一般要用时花来供养,蜀葵最大的特点是耐寒耐旱,花期长。一般为两个月,农历八月至十月,有些地方更长,非常适合在干旱少雨的河西及吐鲁番地区生长,是不可多得的时花,这也是蜀葵在敦煌壁画中出现的地缘因素。如果冬天没有新鲜的蜀葵花,则要用纸或绢造此花,用以供佛。1973年,新疆阿斯塔纳古墓中出土了不少造型精美的绢花,以第187号墓出土的绢花最为典型,该花通高32cm,由萱草、虞美人等花组成,鲜艳如新,完美的体现出唐代高超的绢花工艺[33]。
在密教择地仪轨中对如何用蜀葵来礼佛有详细的记载。密教择地建坛城是一件极为神圣的事,有数道工序。首先要把所选之地挖开,深度为一肘半,拣出土里面的头发、瓦砾之类的秽恶之物,然后取净土填之,洒香水,令其平实如平镜。再于坛中心置五宝(金、银、真珠、瑟瑟、颇梨)、五药(赤箭、人参、伏苓、昌蒲、天门冬)、五谷(稻谷、大小麦、菉豆、胡麻)等,还要用沉香、檀丁香、郁金、龙恼香等加持,以增加请诸尊之威力,坛城建好之后需用蜀葵、龙葵或莲叶等,从东北方向右旋将坛城打磨光滑,继续加持威力。唐慧琳集《建立曼荼罗及拣择地法》云:“如是数数,频涂三五遍,即用莲子草揩摩,或取蜀葵叶和小许墨汁,并捣香茅草相和,如法揩摩一两遍已,承湿扫令光净,如法正扫之时。”[34]不空译《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亦云:“加持已,后从东北隅起首右旋涂之,次取蜀葵叶或莲子叶,揩拭令其光净,于上取白粉和水,以绳分九位拼之,石上磨白檀香用涂九位。”[35]除了上述密宗建坛城需用蜀葵外,在止雨仪轨中也用蜀葵花。罽宾国三藏沙门般若、共牟尼室利译《陀罗尼功德轨仪品第九》中提到,在涝天需止雨时,要用钵器或瓶缸等盛蜀葵祈祷:“若雨过多,便诵止雨陀罗尼曰:‘唵阿蜜低底吽底瑟咤娑嚩贺。诵此陀罗尼七遍,或以钵器或瓶缸等盛蜀葵花,以钵瓶等覆在地上,便即晴明。”[36]在这些密教仪轨中,蜀葵的主要作用在于抹光坛城,令其光洁,增进所请诸尊法力,祈福驱灾。《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对此有更细致的描述,云:
佛告阿难陀:“若有男子女人,情所祈愿,或为大雨,或为大旱,灾横兵戈,众病疫疟,凡是一切,不如意事,欲读诵此大孔雀咒王,冀求消灭者……于像左边置大孔雀王像……以白遏迦华(此方所无,可以梨奈花等替之)或白羯罗毗罗华(岭南有,北地无,可以白杏柰华或蜀葵华等替之),或以尸利沙树华(即夜合树是也),或频蠡树叶(此方亦无,可以枣桑荷叶替之)散布坛上,先于佛前随其所有,设诸饮食种种供养。”[37]
在这个密教仪轨中,白遏迦华、白羯罗毗罗华、尸利沙树华等皆是药。据考,此处“尸利沙树华”和“夜合”就是梵语■irī■a的对译。印度佛教僧团中,患病的僧人使用该植物的皮、叶等物,以水煮涂身,用来治疗疮疥等类的皮肤病[38]。义净对该植物至少有两种意译名“合昏树”和“夜合树”。又,大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五《毗俱知救病法坛品》中提及“尸利沙树合欢树是,拘留孙佛得道树是。”[39]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卷中解释了佛教僧侣日常药物的四大分类,其中数量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是尽寿药(即一生可以随时使用的药物)[38]34。其中就有尸利沙,曰:
又有尽寿药,谓是根茎等;如法应守持,无限常听服。根鸡舌姜等,茎谓不死条;黄姜等可知,并诸香杂水。七叶苦爪苗,果谓胡椒等;及以三果类,准病服皆听。紫矿及阿魏,黄蜡诸树汁;油麻灰等五,复有五种盐。庵末罗苦木,七叶尸利沙;如斯树等皮,皆名尽寿药。如是诸药类,不拟将充食;但欲排饥渴,希心趣涅槃。[40]
在诸多的“尽寿药”中,尸利沙也位列其中。由此可见,白羯罗毗罗华和白遏迦华与尸利沙一样是印度僧侣常年必备之药。在这里译者特意提到北地没有白羯罗毗罗华时,可用白杏柰花或蜀葵花代替。杏柰花是茉莉花的别名,白杏柰花即白茉莉花,来自波斯。唐段公路《北户录》载“白茉莉花,不香红者,皆波斯移植中夏”[41]。它是花茶和香精重要的原料,其花、叶可用来治目赤、肿痛,并有止咳化痰之效。眼病和咳嗽是生活中长发的疾病,眼药是僧侣们常年携带的药物。这说明白羯罗毗罗华与蜀葵花或白杏柰花在疗效上有相通之处。
结合文献资料和石窟壁画艺术观之,蜀葵于唐代成为密教仪轨中的礼佛之花,并出现于敦煌吐鲁番等地石窟壁画中与其自身的药用性有很大的关系。随着汉唐以来各种疾病的频发,尤其是天花的传入,加深了人们对蜀葵药用性能的认识,故译经者将其作为印度药的替代品在佛经中出现,进而频繁地出现在佛画中,久而久之,成为佛教艺术图式而被固定下来。
结 论
综上所述,蜀葵在唐代出现于壁画中,多出现在菩萨、药师佛以及供养人的手中或盘中,绝非是偶然现象。诚然,一种植物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先天的条件非常重要,从花、干、茎叶等都要符合人们的审美标准,与信仰结合起来,并作为固定的图式反复绘制,则并不多见。蜀葵耐寒、耐旱,从汉代始,作为蔬菜和药物在河西戍边的将士中就已广泛使用。至唐代随着永徽四年天花病从波斯传到中土,蜀葵用于治疗早期天花疗效甚好,加深了人们对蜀葵的药性的认识,故而赋予了复生与禳灾之意蕴。与此同时,唐代密教中也因此将其作为必不可少的礼佛之花而用于重要的仪轨中,其形象更是反复出现于石窟壁画中,非特殊因素无以成就蜀葵仅次于莲花而入住莫高窟也。
参考文献:
[1]韦秋紫. 唐五代敦煌壁画中的花卉、动物形象技法研究[D]. 中央美术学院,2019:6.
[2]王胜泽. 敦煌西夏石窟中的花鸟图像研究[J]. 敦煌学辑刊,2019(2):153-168.
[3]张秦源. 西夏人应用植物资源研究[D]. 兰州大学,2016:123-124.
[4]周祖谟. 尔雅校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22.
[5]汪灏. 广群芳谱:一[C]//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书店,1985.
[6]陈淏子,辑. 伊钦恒,校注. 花镜[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335.
[7]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石声汉,校注. 农桑辑要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4:174.
[8]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96-97.
[9]陈藏器,撰. 尚志钧,辑释. 本草拾遗辑释[M].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293.
[10]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1038-1048.
[11]唐彦谦. 秋葵[C]//彭定求. 全唐诗. 北京:中华书局,1980:7666.
[12]杨桂梅. 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唐墓[J]. 文物,1995(11):49.
[13]唐慎微.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507.
[14]A. 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觟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Berlin,1913,Taf. 16.
[15]楊富学,赵崇民.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的供养图与榜题[J]. 新疆艺术,1992(6):53.
[16]A.von Le Coq,Die Buddhistis che Sp?覿tantike in Mittelasien,Bd. III, Berlin,1924,Taf. 14
[17]贾应逸,侯世新. 莫高窟409窟与柏孜克里克石窟供养人对比研究[J]. 吐鲁番学研究,2008(1):110-119.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M].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170-171.
[19]A. von Gabain,Das Leben im uigurische K?觟nigreich von Qo?o(850-1250),Wiesbaden,1973,S. 165.
[20]A. Stein,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 IV,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1,pl. lxi.
[21]《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编辑委员会.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6卷·柏孜克里克石窟[M].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210.
[22]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4111-14112.
[23]王焘. 外台秘要[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19.
[24]宋岘. 吐鲁番对中国医学的贡献[C]//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 第三届吐鲁番学欧亚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09.
[25]甘肃简牍博物馆,等. 肩水金关汉简(伍):中册[M]. 上海:中西书局,2016:6.
[26]甘肃简牍博物馆,等. 肩水金关汉简(肆):下册[M]. 上海:中西书局,2015:116.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59.
[28]孫占宇. 居延新简集释(一)[M]. 甘肃: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241.
[29]沈澍农. 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187.
[30]阿卜杜热合曼阿吉,著. 张焕鹏,译. 维吾尔简易验方[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5:291.
[31]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1:416.
[32]义净,著. 王邦维,校注. 南海寄归内法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95:172.
[3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考古专业.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75(7):8-26.
[34]慧琳,集. 建立曼荼罗及拣择地法[C]//大正藏:第18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0:928c.
[35]不空,译. 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C]//大正藏:第19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0:364b.
[36]般若,共牟尼室利,译.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C]//大正藏:第19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569a.
[37]义净,译. 佛说大孔雀咒王经[C]//大正藏:第19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476a.
[38]陈明. 汉译佛经中的天竺药名札记(五)[J]. 中医药文化,2018(4):33.
[39]阿地瞿多,译. 陀罗尼集经[C]//大正藏:第18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0:833a.
[40]义净.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C]//大正藏:第24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637a.
[41]段公路. 北户录[C]//王五云. 丛书集成物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