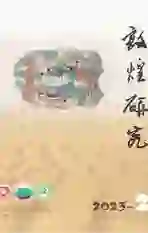归义军时期敦煌的乡族与社会
2023-05-30张艳玉
张艳玉
内容摘要:归义军时期敦煌的乡族力量主要包括乡豪、乡里胥吏、耆寿。乡族力量在敦煌社会中的功能有组织集体活动、倡导公共建设、推行社会教化、调解民事纠纷、参与政治活动。乡族是归义军政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得不依赖的对象,在建设乡村、推进社会治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归义军时期;敦煌;乡族力量;社会作用
中图分类号:K87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2-0128-07
Village Clans and Dunhuang Society during the Gui-yi-jun
Regime Period
ZHANG Yanyu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Gansu)
Abstract:During period of the Gui-yi-jun regime, the power of the village clans in Dunhuang mainly included xianghao乡豪 (powerful and wealthy people in the village), xuli胥吏 (village officials), and qishou耆寿(senior people in the village). The power of the village clans served many purposes in Dunhuang society, including organizing collective activities, advocating public construction, implementing social education, mediating civil disputes, and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Village clans were the primary political force that the Gui-yi-jun regime had to rely on in managing local society, and it played a particularly crucial part in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Gui-yi-jun regime period; Dunhuang; village clan power; social function
在古代,宗法制重视地缘与血缘的背景下,乡族是治理基层社会的重要力量。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基层民众活动的史料。前贤对唐五代敦煌乡里的建置演变多有探讨{1},基本厘清了唐至宋时期敦煌的乡里建置。学者亦利用敦煌文书考察唐代乡里职责权力,主要着意于乡长、里长在制作籍账、发展农业生产、协助司法、催驱赋役等事务上的作用①。另外,冯培红先生对归义军时期的乡里官吏及部落使的设置、职守与地位做了有意义的分析[1],主要从职官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学者对唐代的乡族势力已有一定研究②。相较于内地的乡族势力,归义军时期敦煌的乡族力量有其特殊性。目前学界对归义军时期敦煌的乡族力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未做专门阐述。研究乡族力量的社会活动,可以很好地观察基层社会中各种力量的互动及古代政治治理、了解民众日常生活史。
一 归义军时期敦煌乡族力量的构成
唐代乡族势力包括乡村社会中具有文化背景的士人、具有仕宦背景的退职官吏、乡县胥吏和乡豪[2]。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情况特殊,荣新江先生指出归义军政权在唐朝是一藩镇,五代宋初则是外邦[3]。由于该时期敦煌内部的人事任命权实际独立于中原政权外,更多的知识权利和仕途机会掌握在当地的大族名族手中,具有文化背景的士人和具有仕宦背景的退职官吏在敦煌乡村并不突出。
归义军时期,敦煌民间因各种事宜组建了社邑,加入社邑是民众获得社会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重要方式。由于本文考察的是乡族力量,故所述社邑不包括由官员组成的官品社邑及僧尼组成的社邑,主要探讨由村坊组成的社邑。大多社邑的三官有社长、社官、录事,一些社邑则有虞候、社老。S.6005《敦煌某社补充社约》有社长、社老、录事。P.3489《戌辰年正月廿四日袿坊巷女人社社条》有录事、虞候。就三官的选择条件,S.6537V(3-5)《十五人结社社条》(文样)记载:
且三人成众,赤(亦)要一人为尊,义邑之中,切籍三官钤辖,老者请为社长,须制不律之徒;次者充为社官,但是事当其理;更(?)无(英)明后(厚)德,智有先诚,切齿严凝,请为录事。凡为事理,一定至终,只取三官护裁,不许众社紊乱。[4]
社邑以三官为尊,由三官管理社邑,一般年老之人被请为社长、社官,有智慧严肃者被请为录事,相较于社长、社官,录事年纪较轻,承担着转帖等许多实际性的事务,需身强力壮者担任。孟宪实先生认为三官不具有特权,三官由众社之人共同选举,社内平等、尊重三官是为了社内日常事务的有序进行[5]。三官人选虽不尽是有地位的人当选,但需慑服众人,尤其是在村坊亲邻或宗族组成的社邑中,三官通常是有威望或有身份背景的人抑或宗族领袖更易担任,社长社官的选择以老者优先,在古代尊老礼制的约束下,这种平等的形式中包含着在尊卑关系及乡豪影响下的不平等。S.3540《庚午年正月廿五日比丘福惠等修窟立凭》记载:“众内请乡官李延会为录事,放帖行文,以为纲首;以押衙阎愿成为虞候,袛奉录事条式。”乡官李延会为录事,押衙阎愿成为虞侯,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充当三官的例证。一些宗族会组建社邑,Дх.11038《索望社案一道》是索姓宗族立社的社条。S.6424V(1)《乾德六年(968)十月社官阴乞德等请宾头卢波罗堕上座疏》记载:“谨请西南方鸡捉(足)山镔(宾)头炉(卢)波罗堕尚(上)座和尚,右今月廿三日阴族兄弟就佛堂子内设供,于(依)时讲(降)假(驾),誓受佛敕,不舍仓(苍)生,兴运慈 国。乾德六年戊辰岁十月日社官阴乞德、录事阴怀庆记。”[4]509此为阴氏家族组成的社,由宗族成员出任社官、录事,这个社有很深的宗族背景,三官也是宗族領袖。村坊亲邻或宗族组成的社邑,三官一般由有宗族背景、钱财地位或威望的乡豪担任,乡豪在基层社会权力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
古代小农经济下,社会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同一宗族聚族而居形成一些主姓聚居点,主姓是这一聚居点的主要势力,其他人口少的姓氏依附于主姓。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如P.3234《甲辰年(944)牧羊人贺保定领羊凭》记“宜秋邓家庄”,这是以邓姓为主姓的村庄,其乡族势力为宗族领袖。宗族的联合有利于在此生存空间争取更多利益,宗族长老为村庄最有威望者,杂姓村坊则由有一定地位、钱财或威望的人主持村坊事务。
归义军政权在敦煌实施乡里建置,但相较于唐前期发生了变化,关于里和里正活动的记载很少,更多见的是乡官的社会活动,如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记载“麦壹硕捌斗,郭乡官利润入”“粟壹斗,付寒苦春料官斋看乡官用”“油壹升,冬料官斋看乡官用”“面贰斗,冬料官斋看乡官用”[6]。陈国灿先生认为相较于唐前期乡的事务由5个里共同负责办理,归义军时期设置了各管专务、各负其责的各类知乡务官。里虽存在,但里正的任务已随之减轻,基层权力集中于乡[7]。虽是否设置了各类知乡务官仍存疑问,但里的权力缩小,基层权力集中于乡的观点是正确的。
唐代规定里的职责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8],而归义军时期,这些职责改由以乡官为首的乡司完成。P.2222B《唐咸通六年(865)前后僧张智灯状(稿)》记载:“僧张智灯状,右智灯叔侄等,先蒙尚书恩造,令将鲍壁渠地回入玉关乡赵黑子绝户地,永为口分,承料役次。先请之时,亦令乡司寻问实虚,两重判命。”[9]僧张智灯在申请土地时,要经过乡司核查。乡司亦负责按比户口、征收赋税,P.3324V《唐天复四年(904)八月八日应管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状》记载:“复令衙前军将子弟随身等判下文字,若有户内别居兄弟者则不喜(许)沾捭。如若一身,余却官布、地子、烽子、官柴草等大礼(例),余者知杂役次,并总矜免,不喜差遣。文状见在,见今又乡司差遣车牛艾芦茭者。”[9]450除了官布、地子、烽子、官柴草等赋税劳役外,如若单身,可免除其他杂役,但乡司仍给作为单身的衙前军将子弟随身等差遣其他役务,说明乡司管理着赋税差科。冯培红先生指出乡官的职守是分配土地、定户等、征赋税、摊差科,乡官还负责监修城堡、土门、仓库、监管寺院等事宜[1]。乡司处理乡村事务,除乡官外,乡司还设有乡判官,S.6981《诸色斛斗破历》记载:“五月廿三日,粟肆斗,垒苜蓿园看十乡判官用。”乡设有乡老、里正,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载“二十一日,准旧十乡里正纳毬场胡併(饼)四十二枚,用面二斗一升”“十乡老面二斗、油一升”[6]283、285。乡老负责社会教化,原先里正负责征收赋税。但归义军时期赋税以乡为单位征收,由“某头”负责,这些“头”非乡司官员,只是一般百姓,临时从纳税人选派出来承担乡役任务,负责征税,大多负责征收三至五人的赋税[10]。如布的征收由“布头”负责,柴的征收由“枝头”“白刺头”负责。乡村官吏大多活动于乡村,处理乡村事务。
耆寿是地方上有威望、年长之人。“大唐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以耆老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8]924归义军政权亦设置了耆寿。S.2174《天复九年(909)神沙乡百姓董加盈兄弟分书》记“见人耆寿康常清(押)”,P.2504《辛亥年(951)康幸全贷绢契》记载押衙康幸全充使伊州,因缺少货物,向耆寿郭顺子贷物。
综上所述,归义军时期敦煌的乡族力量主要包括由宗族领袖、社邑三官、乡村中的强势者等构成的乡豪,以及乡里胥吏、耆寿。这些乡族力量往往不是单一身份,德宗初年,时人感叹“里胥者,皆乡县豪吏,族系相依”[11]。多重的身份背景加强了乡族力量在乡间的顽固性,亦是官方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得不依赖的力量。
二 乡族力量在敦煌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乡族力量长期生活于基层社会,熟悉基层社会的风俗和惯例,在基层社会日常事务中发挥着作用。
(一)组织集体活动
敦煌民众参加的集体活动有印沙、脱塔、修窟等佛事活动及丧葬、宴饮、斋会等日常生活活动。举办这些活动时民众会组建社邑,一些社邑是固定的,一些社邑为临时活动组建,民众普遍参与社邑。S.778《王梵志诗》云“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以三官为代表的基层力量是基层社会集体活动的重要组织者,三官是社邑活动运转的重要条件,录事负责转帖等活动,几乎所有的社司转帖中都有录事的题名。P.3489《戌辰年正月廿四日袿坊巷女人社社条》载:“或有凶事荣亲者,告保(报)录事。行文放帖,各自兢兢,一一指实。”“凶事荣亲”为凶丧婚嫁事宜,此類活动是家庭的重要事务,由录事为代表的三官主持。三官不合会使社邑活动无法正常举行。P.4960《甲辰年(944)五月廿一日窟头修佛堂社再请三官凭约》载:“甲辰年五月廿一日,窟头修佛堂社……已上物色等伏缘录事不听社官件件众社不合,功德难办,今再请庆度为社官,法胜为社长,庆戒为录事,自请三官已后,其社众并于三人所出条式,专请而行,不得违背,或有不禀社礼,□□上下者,当便三人商量罚目,罚脓腻一筵,不得违越者。”[4]16-17录事和社官发生矛盾,致社邑事务无法进行,故对三官进行了调整,规定社众皆须听从三官安排,如不听从则会受到财力惩罚。有些社条规定的惩罚更重,不仅包括财物,还有体力惩罚。S.5629《敦煌郡等某乙社条一道》(文样)载:“自合社已后,若有不听无量,冲底(诋)三官,罚羊壹口,酒壹瓮,合社破用。……三官权知勾当,自后若社人不听三官条式者,痛丈(杖)十七。”[4]37-38入退社需经三官同意。P.4651《投社人张愿兴王祐通状》记:“投社人张愿兴、王祐通……伏乞三官收名入案。”S.5698《癸酉年社司准社户罗神奴请除名状》载:“社户罗神奴及男文英义子三人……讫(乞)三官众社赐以条内除名,放免宽闲,其三官知众社商量。”可见三官是社邑组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社邑中有一定权力。
社邑在三官的主持下开展各种活动,如祭祀亡人。P.2614V《甲辰年二月二日社长孙景华等祭宋丈人文》记载:“维岁次甲辰二月辛亥朔二日壬子社长孙景华举以茶浆之奠。敬祭于宋丈人贤者之灵……景华等忝倍子邑,悲悻(心)谁量,备单盘之路佐(左),跪祭茶浆。伏惟尚飨!”[4]686在社长孙景华的带领下,社众敬祭宋丈人。三官亦是社邑斋会活动的筹划者,P.2341V《亡考文兼社斋文》记“是以三官启发,合邑虔诚”,S.3793《辛亥年(951)社斋破除油面数名目》记载就社斋油面的支出,“一仰虞候监察,三等料算会,一一为定为凭”。
(二)倡导公共建设
归义军时期除了官方寺院外,存在私人或集体修建的佛堂、兰若、佛塔,是佛教信众修行祈愿的重要场所。佛堂、兰若的规模不会太大,可能由一间房舍改造而成。P.3490《都宅务知乐营使张某乙于当居创造佛刹功德记》记“厥今有清信弟子押衙兼当府都宅务知乐营使张某乙……所以割舍家产,钦慕良公,谨于所居西南之隅,建立佛刹一所”,即是张某乙在自家房屋西南角落造佛刹一所。一些佛堂、兰若因修建者而命名,P.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记周鼎佛堂,S.1824《受十戒文》题记“光启四年(888)戊申五月八日,三界寺比丘僧法信于城东索使君佛堂头写记”,周鼎佛堂、索使君佛堂分别因周鼎、索使君而得名。
修建佛堂、兰若等需一定财力,并非人人都能承担。敦煌民众普遍信仰佛教。为方便日常信仰,村坊会集体修建佛堂、兰若。P.3390《节度押衙张盈润孟授祖庄浮图功德记并序》记载:“厥有弟子节度押衙张盈润,奉为故和尚在日造浮图壹所……因以割舍珍财,抽减丝帛,谨于当庄佛堂内添绘功德圆就已毕。”[12]当庄佛堂说明这是属于孟授祖庄的佛堂。S.6424V(2)《开宝八年(975)十月兄弟社社官阴幸恩等请宾头卢波罗堕上座疏》记载:“谨请西南方鸡捉(足)山宾头卢波罗堕上座和尚,右今月八日南澹部洲萨世界大宋国沙州阴族兄弟,就于本居佛堂子准旧设供……开宝八年十月日兄弟社社官阴幸恩等疏。”[4]510-511阴氏家族的佛堂设在本居所内。同一村坊民众组成的社邑也会建设兰若、佛堂。S.474《社邑于当坊兰若塑释迦牟尼等像记》记:“时则有三官社众等,于当坊兰若内塑释迦牟尼佛并二菩萨,阿难迦叶、二金刚神等一坐。”另P.4044《修文坊巷社肆拾贰家创修私佛塔记》载:“维大唐光启三年(887)丁未岁次五月拾日,[修]文坊巷社肆拾贰家创修私佛塔者。”P.4044《修文坊巷再缉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云:“厥有修文坊巷社,敦煌耆寿王忠信、都勾当伎术院学郎李文建知社众等计卌捌人……互相谏谓,都无适寐之憩。今缀缉上祖兰若。”由修文坊巷民眾组成的社两次修建兰若、佛塔,这些兰若、佛塔为修文坊巷民众的公共财产,耆寿王忠信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以三官或宗族为首的乡族势力领导民众修建兰若、佛堂、佛窟等。北大195《重修唐家佛堂院记》云:“此坊有唐家佛堂院,五邻礼忏,常住年深;业海迁讹,陵谷星变。刹心摧坏,徘徊毁残;起意造新,何如修古。揣当来志,佥议允从。”唐家佛堂院,因年代久远,毁坏残损,众人商议集体修建。有时三官会诱谕社众。S.4860V《当坊义邑社创建伽蓝功德记并序》记载:“厥有当坊义邑社官ㄙ等贰拾捌人……三官谓众社曰:‘今欲卜买胜地,创置伽蓝,功德新图,进退忉怩,未知众意。社众等三称其善,雅惬本情。上唱下随,同心兴建……福所备资,益我节度使曹ㄙ,[□]祚安边,永保乾坤之寿。次为合邑众社,身如劫石齐宁。法界苍生,并获(脱)三途之难。”[12]1222P.2982V《社人修窟功德记》云:“诱亲佐共崇于佛刹,异口而五百王子,同契一心;齐声而三十三天,俱愿戮力。”三官以信仰、集体归属诱导社众,某种程度上也是给社众施压。
修建佛堂、兰若、佛窟不仅是佛教信仰的一部分,亦是建设聚落的公共场所。位于本村坊的兰若、佛堂是村邻、宗族的公共场所,也是凝聚村邻、宗族的重要象征。前述北大195《重修唐家佛堂院记》有“五邻礼忏,常住年深”,说明唐家佛堂是民众共同活动的场所。一些兰若的命名有浓厚的宗族色彩,S.6583V(1)《常年设供转帖抄》有“宋家兰若”,S.86《淳化二年(991)四月廿八日为马丑女回施疏》记“城西马家、索家二兰若共施布一匹”,可知宋家、马家、索家都有本宗族的兰若。社邑活动的集合地点除在寺院举办外,多在兰若、佛堂举行,亦证兰若、佛堂为村坊活动的公共场所。
(三)推行社会教化
以耆寿为代表的乡族势力负责基层社会教化,P.4660《节度押衙敦煌郡耆寿张禄邈真赞》记载敦煌郡耆寿张禄为“龙沙豪族,塞表英儒。忠义独立,声播豆卢。仁风早扇,横亮江湖。有德有行,不谓不殊。闺门孝感,朋友言孚。家塾文议,子孙徇德。事君竭节,志守荣枯。洞归(赜)政法,安然不徂。夜泉忽奄,悲云四颫。神剑溺海,过隙潜驹。千秋美誉,应同玉壶。时咸通十二年(871)季春月蓂生十五叶题于真堂”[12]467。张禄为归义军初期的敦煌耆寿,赞文通篇称赞其忠义仁孝且重视家塾教育,符合耆寿德高望重、教化社会的形象。S.2113《唐沙州龙兴寺上座马德胜和尚宕泉创修功德记》记载马德胜和尚亡父为“敦煌县耆寿,讳太平,字时清。孝悌承家,闲居得志。履谦恭于乡闾,慕直道于前贤。风向许由,不趋名利”,文书写于唐乾宁三年(896),马德胜的父亲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耆寿,“履谦恭于乡闾”(以身作则教化乡邻)。
郝春文先生考察了敦煌私社的教育与教化功能,儒家文化方面宣扬尊卑之礼、朋友之义、忠孝,佛教文化方面宣扬佛与佛法的功德、信仰佛教、佛教教义,指出私社中尊卑之礼的教育是最普遍的[13]。作为社邑活动的组织者和贯彻者,三官是尊卑之礼的重要宣传执行者。S.6537V(3-5)《十五人结社社条》(文样)载:“窃闻敦煌胜境,凭三宝以为基;风化人伦,藉明贤而共佐。居(君?)白(臣?)道合,四海来宾,五谷丰登,坚牢之本,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宜(义),恐时侥伐(代)之簿,人情以往日不同,互生分(纷)然,后怕各生己见……且三人成众,赤(亦)要一人为尊,义邑之中,切籍三官钤辖,老者请为社长,须制不律之徒。”[4]49-50社邑强调尊卑孝义,此十五人结社的目的即是怕“人情”生疏,此处的“人情”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礼义。“不律之徒”指不遵守尊卑礼义者。以老者为社长,就是要规训不践行尊卑礼义者。Дх.11038《索望社案一道》载:
盖闻人须知宗约宗亲以为本,四海一流之水,出于昆仑之峰。万木初是一根,分修(条)垂枝引叶。今有仑之索望骨肉,敦煌极传英豪,索静胤为一派,渐渐异息为房,见此逐物意移,绝无尊卑之礼,长幼各不忍见,恐辱先代名宗。[14]
索家同宗因怕分“房”居住导致宗族成员忘记长幼尊卑之礼及宗约,故结社以谨守尊卑礼仪。Дх.12012《清泰二年(935)投社人王粉子状抄》记载:“投社人王粉子,右粉子贫门生长,不识礼仪,在于家中,无人侍训,情愿事奉三官。所有追凶逐吉,奉帖如行。伏望三官社众,特赐收名。”[15]文书明确说明王粉子入社是因其不识礼仪,家中无人教导,愿入社遵循三官教诲。
(四)调解民事纠纷
家族社会网在互帮互助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影响广泛,在家庭重大事件的决策中,亲邻是重要的见证者和部分决策者,如遗书、分家书、放良书、放妻书中就有亲邻见证的传统。P.3146《年代不详残凭》记载:“小小家业屋舍,被苟苟母子回日,对诸亲行巷老大,具立文书,抄录分付诸亲。”[16]“诸亲行巷老大”为宗族领袖。S.2174《天复九年(909)神沙乡百姓董加盈兄弟分书》记载董加盈兄弟三人分家时,有“今对亲姻行巷”“右件家业,苦无什物,今对诸亲,一一具实分割,更不许争论”。在这起分家纠纷中,亲姻行巷是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文书记有“见人耆寿康常清”。乡族势力在基层纠纷中常常充当调解人,S.2385《年代不详阴国政卖地契》有“见人耆寿”。P.4525《年代不详留盈放妻书》记载:“今亲姻村老等与妻阿孟对众平论,判分离别遣夫主留盈讫。”耆寿、村老皆是乡村中有威望者。S.4374《从良书》是“从良书”的样式文书,可以反映当时从良事件解决的一般性,签押人名处有“亲保、亲见、村邻、长老、官人、官人”。《通典》记载:“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8]63-64亲保、亲见、村邻为亲戚邻居,长老是一聚落中有威望者,官人指行政官员。
S.5816《寅年(834?)节儿为杨谦让打伤李条顺处置凭》记载:“寅年八月十九日,杨谦让共李条顺相诤,遂打损经(胫)。节儿断,令杨谦让当家将息。至廿六日,条顺师兄及诸亲等,迎将当家医理。从今已后,至病可日,所要药饵当直及将息物,亦自李家自出,待至能行日,算数计会。又万日中间,条顺不可,及有东西营局破用,合着多少物事,一一细算打牒,共乡闾老大计算收领,亦任一听。如不稳便,待至营事了日都算,共人命同计会。官有政法,人从私契,故立为验,用为后凭。僧师兄惠常,僧孔惠素,见人薛卿子。”[16]413-414此文书虽为吐蕃时期文书,但考虑到乡族势力在乡村中的顽固性,亦能反映归义军时期的情形。杨谦让之名又见于S.5788《社司转帖》、S.5831《社司转帖》、S.5823《寅年杨谦让牒》、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在杨谦让与李条顺相诤事件中,除两方当事人外,出面的还有节儿、乡闾老大、条顺师兄及诸亲。节儿为官方代表,乡闾老大是控制乡村事务的乡豪。文书很好地反映了乡村中个体对官方、亲邻及乡豪的依赖,从“又万日中间,条顺不可,及有东西营局破用,合着多少物事,一一细算打牒,共乡闾老大计算收领,亦任一听”句可知,官方对乡族势力在基层社会中的权威是认可的。
(五)参与政治活动
P.3633《辛末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圣天可汗状》记载:“遂令宰相、大德僧人,兼将顿递,迎接跪拜,言语却总□□。狄银令天子出拜,即与言约。城隍耆寿百姓再三商量,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和断若定,此即差大宰[相]、僧中大德、敦煌贵族耆寿,赉持国信,设盟文状,便到甘州。”{1}面对回鹘军队兵临城下,沙州百姓上状请求投降,此次投降谈判敦煌派出了宰相、僧中大德、贵族耆寿,宰相代表节度使和俗官力量,僧中大德代表佛教力量,贵族耆寿代表大族乡族力量。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记载“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唐长孺先生认为此件文书是曹议金于同光二年(924)上于后唐的求授旌节的表文[17],说明耆寿在重要政治事件中传达民意、参与政治活动,以耆寿为代表的基层势力是敦煌社会的重要力量。
另外宴设司会支出一部分财物以招待里正等乡村官吏,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载“二十一日,准旧十乡里正纳毬场胡併(饼)四十二枚,用面二斗一升”“十乡老面二斗、油一升”[6]283、285,由“准旧”可知此种活动已为惯例。曹议金上台后修建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第98窟供养人题记中有“节度押衙知沙(洪)池乡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王富延供养”“节度押衙知慈惠乡官银青光禄大夫检国校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王弘正”“节度押衙知赤心乡官银青光禄大夫檢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进供养”[18],说明作为一乡之长的乡官是归义军政权内部结构中的重要一员。
乡族力量在基层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是官方不得不联合的对象,对基层社会治理有着积极作用,但也有消极面。P.2595《赤心乡百姓令狐宜宜、氾贤集等状》载:“赤心乡百姓令狐宜宜、氾贤集等。右宜宜等总是单身,差着烽子。应著忙时,不与帖户。数谘乡官,至与虚户。总是势家取近,不敢屈苦至甚,免济单贫。伏请处分。”[9]309令狐宜宜等单身,需承担烽子的差役,农忙时数次请求乡官,想以典押物品代替差役,却遭豪强大户欺压。赋税差科义务中,乡官等基层官吏会袒护豪强大户,乡官时常与乡豪联合,共同治理基层社会,这种联合是基层治理中出现腐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冯培红. 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D]. 兰州大学,2004:237-250.
[2]李浩. 论唐代乡族势力与乡村社会控制[J]. 中国农史,2010(1):88-94,53.
[3]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
[4]宁可,郝春文. 敦煌社邑文书辑校[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50.
[5]孟宪实. 论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的组织形态[J]. 敦煌研究,2002(1):59-65.
[6]唐耕耦,陆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351,359,361,363.
[7]陈国灿. 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J]. 敦煌研究,1989(3):49.
[8]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8:63-64.
[9]唐耕耦,陆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289.
[10]刘进宝. 敦煌归义军赋税制的特点[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49-154.
[11]王谠. 唐语林[M]. 北京:中华书局,1987:62.
[12]郑炳林,郑怡楠. 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205.
[13]郝春文. 中古时期社邑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73-188.
[14]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敦煌文献:第15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44-145.
[15]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敦煌文献:第16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
[16]沙知.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18.
[17]唐长孺. 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C]//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4.
[18]敦煌研究院.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