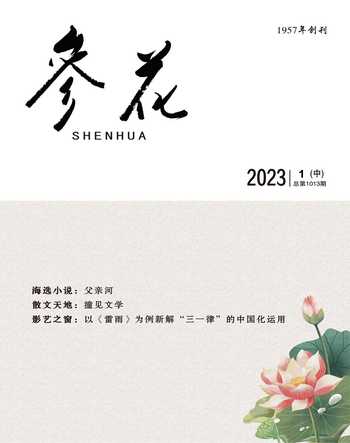浅析科诨在传统曲艺中的应用
2023-05-30皇甫宇鹏
一、引言
“科诨”一词,泛指戏曲中的各种喜剧性穿插,主要由戏剧人物滑稽的动作和搞笑的语言来促成喜剧效果。“科”多指滑稽的动作,“诨”多指喜剧性的语言。相声是源于生活、被广大群众喜爱的曲艺表演形式。科诨与相声都是通过搞笑的语言动作为大众带来欢乐的,二者具有关联性。科诨是一种民族艺术形式,在感情渲染方面体现了一定的民族性。将科诨艺术运用到传统曲艺表演中,可以增强作品的“喜剧性”效果,本文对此展开详细研究。
二、科诨概述及其在戏曲中的作用
科诨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两汉“优”的表演,唐代参军戏已经发展得十分繁盛,参军戏有两个角色,即参军与苍鹘,表演时,参军着绿衣假扮官员,苍鹘手执磕瓜击打参军,或问答、或打斗,使观众发笑。在宋金杂剧院本中,参军戏中的“参军”与“苍鹘”两个角色变成了专门用来科诨调笑的“副净”和“副末”两个脚色。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卷二十中说:“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副净色装傻充愣、发呆,做出滑稽可笑的样子;副末色打诨,逗乐取笑观众看客。戏曲中的科诨在宋金杂剧、院本科诨表演的基础上,发展成一种重要的喜剧手段。
清代戲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结构第一里指出,“填词一道,文人之末技也”,在科诨第五里又说,“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这么看,文人认为科诨是上不了台面的,是“末技中的末技”。然而,科诨作为戏曲艺术中一种重要的喜剧性手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在明代,戏剧理论家就对科诨艺术给予了高度关注,王骥德认为:“大略曲冷不闹场处,得净、丑间插一科,可博人哄堂,亦是戏剧眼目”,[1]他将插科打诨比喻为“剧戏眼目”。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评品《玉蝶记》《金合记》等剧本时说,“程君工于曲,而科诨之妙,犹未深晓,故少洗脱之工,便觉意为词掩”,[2]提出了要“深晓科诨之法”,方可编剧。清初戏曲家李渔更是在《闲情偶寄》中对科诨的重要性做了形象的论述:“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之人参汤也。养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观乎?”[3]李渔一边说科诨是“末技之末技”,一边又说“可作小道观乎”,戏曲作品的成败都在于此,能当作小道来看待吗?这句反问式的回答,显然驳斥了插科打诨是末技的观点,“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更是突出了科诨的重要地位。那么,科诨在戏曲中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首先,在于养精益神,使人不倦。《闲情偶寄》云,“戏文好处,全在下半本。只消三两个瞌睡,便隔断一部神情,瞌睡醒时,上文下文已不接续。”大众也编有戏台对联:“要看早些来好文章先争入手;须观完了去真结果还在后头”,一部戏曲作品无论好坏,从创作到搬演,其初心就是让观众来看的,如果观众在看戏的时候想要瞌睡,或者看一部戏,睡了半部戏,都是剧组成员不愿看到的,所以必须给观众提供一种叫作“科诨”的参汤,时不时让观众一乐,养观众之精神,让观众时时保持着一个清醒的看戏状态,能够让观众看完整部戏才是最重要的一步。
其次,在于调笑逗趣,活跃气氛。例如在《张协状元》里,张协与贫女在破庙结婚时,没有桌子摆设,小二便用两手撑地,用背部做桌子。正当新郎新娘开怀对饮时,小二却突然大叫:“做桌底,腰屈又头低,有酒把一盏与桌子吃!”贫女问:“小二在何处说话?”小二说:“在桌子下!”[4]观众知道小二在戏曲舞台上充当了桌子,这种科诨穿插,能取得令人捧腹的效果,还活跃了剧场气氛。其实调笑逗趣,活跃气氛的目的也是使人不倦。
最后,在于劝诫。讽谏与科诨可以理解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将讽谏放在科诨中,寓庄于邪。失去了深刻的思想内容,科诨就失去了灵魂,要寓讽谏于调笑娱乐之中,在捧腹大笑之余有所醒悟,达到一定的劝诫目的。正如李渔《闲情偶寄》贵自然里的例子:“刘备执掌蜀国时,天大旱禁酒,有官员向一人家查收酿酒的工具,简雍与刘备一起游玩时,看见男女各自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简雍就和刘备说他们想行淫,请把他们抓起来,先主刘备说,你怎么知道?简雍说,与想要酿酒还没有酿酒类似。先主大笑,于是就把准备酿酒的人放了。”[5]简雍没有直接对先主说这样做不对,而是通过科诨的方式让先主刘备自己认识到做法的错误,从而自觉更正自己的做法。在哈哈一笑的同时,不需得罪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就达到了提意见、劝谏的目的。另外,对反面人物的揶揄也可以反衬正面人物的美好品质。科诨通过夸张、变形的表演,无情地嘲弄、揶揄反面人物,把恶展现给观众看,从而与作品想要赞扬的正面人物形成鲜明对比。在关汉卿的杂剧作品《救风尘》中,周舍依靠权势,诱娶宋引章,娶前百般迎合,娶进门后对其暴力相加。关汉卿运用科诨的喜剧技巧,把周舍处理成一个被揶揄的对象,在赵盼儿与周舍的斗智斗勇中笑料百出,让人直呼过瘾。在第四折中,赵盼儿骗取周舍对宋引章的休书一段,周舍已经进入了赵盼儿设下的圈套,还逞威风,实在可笑,用自己的行为否定自己,观众也发出会心的笑声。周舍奸猾到底,宋引章轻信到底,赵盼儿机警到底,将三人的不同性格做对比,凸显了戏剧冲突,表现了讽刺的对象和赞扬的对象。
三、科诨在相声艺术中的应用
我国古代观众在观剧方面,有着最为朴素的观剧心理,如果有庙会、有戏看,能给辛劳一天的劳动者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戏曲艺术里的科诨段子便承担了这项功能。发展到今天,喜剧方式多种多样,载体千变万化,科技的加入更是为大众送去了源源不断的欢声笑语。科诨在本质上与喜剧是相通的,但由于喜剧作品的形式不同、表现的生活不同,科诨的形式也就相应不同。相声作为喜剧艺术中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已经被认为是一种行业。相声肇始于1870年前后,历经150多年的发展,已广为大众接受并变得越来越受人喜爱。就相声的渊源、发展及现存主要形式而言,它与古代戏剧里的科诨不无关联。
首先,相声的捧、逗角色与插科打诨的人物设置有关联。按照表演方式划分,相声分为单口、对口、群口。现在最流行的是对口相声,对口相声指表演中捧、逗两人交替说些有趣的话,做些有趣的动作,抖包袱、说笑料,以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一般情况下,逗哏居于说话的中心位置,主要的包袱都由逗哏抖出,主要的笑料都由逗哏讲出,捧哏处在配合逗哏的位置;而在相声界又流传着“三分逗,七分捧”这么一句话,这又强调了捧哏处于二者中的重要地位。捧、逗之争也常常拿来编成相声段子,两人互相争抢、互不相让,从而引发观众的笑声。相声《论捧逗》《捧逗之争》《大话捧逗》等都是在争论捧、逗重要性中引发无数笑料的。《大话捧逗》更是通过琼瑶版、武侠版、宫廷版三个版本改编了捧逗之争,在语言上风格多样,在动作上夸张搞笑,以此来实现角色对立,增加笑料的目的。捧、逗的角色定位依据相声演员的不同风格而表现不同,捧、逗在舞台表演和角色扮演上互相调侃、相得益彰,形成强烈的滑稽感。
相声里的“一捧一逗”构成二人对打成戏的主体结构:表演中,逗哏和捧哏既要相互配合,又要互相调侃、戏弄,互补又对立。从历史上看,这种表演结构早在唐代参军戏的参军和苍鹘组合中已经成熟。参军戏里,参军如逗哏者,扮演“智者”,机智聪明,性格略刚;苍鹘如捧哏者,扮演“愚者”,迟钝愚笨,性格略柔。当然,在后世相声发展中,也不必严格按照参军如逗哏,苍鹘如捧哏的绝对对应来发展,二者常常灵活变化,比如在王声与苗阜的相声《满腹经纶》里,就是参军如捧哏,扮演青年大学生;苍鹘如逗哏,扮演装呆充愣的文盲。到宋金院本里,参军戏中的“参军”与“苍鹘”两个角色变成了宋金杂剧院本中专司科诨的“副净”与“副末”二色,副净色发乔,发呆装傻,表现出滑稽、可笑的样子;副末色打诨,逗乐取笑。现如今,相声的捧哏、逗哏与副净、副末两个脚色的分工是不完全对应的,而是既有对应又有相反,既有发展又有补充的关系。总之,经过唐代参军戏里的参军与苍鹘,宋金院本里副净与副末以及元杂剧里净、丑插科打诨,发展成了对口相声里固定的捧哏与逗哏的人物设置。
其次,相声同科诨一样,都有劝诫的作用。相声属于曲艺艺术,起源于北京,以幽默滑稽为艺术特色,这种强烈的劝诫功能让相声极具现实意义,借助大众乐于接受的表演形式,在博得观众哈哈一乐的同时,又使观众有所反思,在让观众解压放松的同时,也起到了惩恶扬善、传递正能量的积极作用。例如在群口相声《五官争功》中,通过拟人化的表演形式,在产生笑料的同时,劝导人们要团结协作,不要互相拆台。相声《马路情歌》,通过呈现出租车司机违反交规被交警查住的情节,在二人斗嘴的表演中,让人有所思考,其真正的主题内涵是倡导人们在争执时要换位思考,互相理解。这与科诨的劝导、讽谏功用是异曲同工的,科诨的讽谏功能从一开始便存在,楚国优孟巧谏楚王重人轻马、照顾忠臣等都属于讽谏劝诫。明代戏曲家徐复祚的讽刺喜剧《一文钱》,刻画了一个吝啬鬼形象卢至,他非常富有,却极其吝啬刻薄,作家通过刻画许多其他角色的科诨对吝啬鬼进行调笑,烘托出卢至刻薄丑陋的一面。可见,相声里强烈的劝诫引导作用与科诨的讽谏功能不无关联。
最后,相声的“说学逗唱”与科诨艺术相承袭。相声是语言的艺术,由说学逗唱构成,虽说相声在定义上讲求語言功底以及语言的运用,但在实际表演中也离不开相声演员滑稽夸张的表情、逗乐搞笑的动作。例如相声演员岳云鹏在台上站定,手拖住下巴,这种卖萌搞怪的标志性动作一出,观众就会哈哈大笑;在相声《大话捧逗》中,通过不同风格的表演,把相同的台词用不同的表演方式呈现出来,给予生动搞笑的再现,如果不配合场上夸张的动作演绎,单凭语言,有时也很难达到想要的效果;在相声《两个弄潮儿》中,两人在场上又唱又跳、又哭又闹、又走模特步,这种夸张搞笑的动作配以引人逗乐的语言,引得观众捧腹大笑。相声里的语言可以对应科诨的“诨”,相声里的动作表演,如捧哏与逗哏在场上打闹可以对应科诨的“科”,这么看,相声“说学逗唱”配以打闹表演的动作与科诨是有关联的,因此,相声的本质可以说就是科诨。
四、科诨在喜剧艺术中的应用策略
从我国传统戏剧到现代最受欢迎的相声艺术,都离不开科诨,如何更好地发挥科诨的作用,如何运用科诨也已成为研究喜剧的重要课题。王骥德、祁彪佳、李渔等戏剧理论家都对科诨有过探讨,在总结李渔《闲情偶寄》中科诨理论的基础上,试提以下几点策略。
第一,科诨要讲求“自然”之法。在喜剧作品或者喜剧表演中,必不可少地要加入科诨,但科诨并不是想加就加的。为了搞笑而搞笑,生搬硬套地插入某科诨一段,只会让人感觉不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科诨要贵自然:“科诨虽不可少,然非有意为之……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6]《张协状元》作为早期南戏作品,有不少调笑逗乐,甚至闹剧式的科诨,虽能引来了一些笑声,但脱离了剧本的思想内容和人物性格,为科诨而科诨,是索然无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按照李渔的观点,就是不自然的。现在有一些相声在逗乐观众时也脱离了实际,脱离了表现主题,就容易走上硬搬噱头、故作忸怩的道路,给观众带来不自然的感觉,从而降低了相声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如果喜剧演员丢弃了自己的人物风格,去模仿别人的风格,也会显得生硬、不自然,违背观众的期待,也许能暂时逗乐观众,但长时间模仿别人,必定丢失自己,给观众不自然的感觉。现如今,相声演员大部分都有自己的人物特色,这些人物特色是在实践中不断打磨出来的,并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根据自己的风格去设定情景、创作段子会取得极大成功;如果看到别人的风格搞笑就去模仿,无疑是为搞笑而搞笑。所以,喜剧创作要以“自然”为宗,力求自然而然,以达到“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境界。
第二,科诨要“又俗又不俗”。戏曲、相声等深受大众喜爱的表演形式本来就是亲近大众的,不俗则不受大众喜爱。《闲情偶寄》忌俗恶中言及:“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7]因此,科诨的最佳状态就在于“又俗又不俗”,这是喜剧创作者应该努力追求的方向,避免腐儒之谈,也要有文人表达。科诨应是适合剧中人物性格的幽默表达,在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看来,都能捧腹开怀,而不应是为了取悦观众而对粗俗词汇、恶俗语言进行的堆积。综上所述,在传统曲艺中应用科诨的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喜剧性情境,通过滑稽的艺术加工使观众发笑,满足其精神上的愉悦,在传统曲艺表演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骥德.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曲律(第四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2]祁彪佳.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远山堂曲品(第六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3][5][6][7][清]李渔,著.张萍,校点.闲情偶寄[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4]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作者简介:皇甫宇鹏,男,硕士研究生在读,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
(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