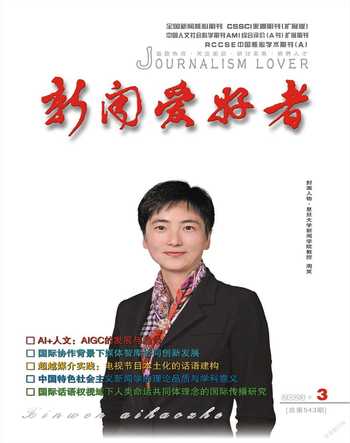吸纳与创新:建设性理念的基层融媒体实践与探索
2023-05-30邵鹏王晟
邵鹏 王晟
【摘要】作为理论舶来品,西方建设性新闻理念已在中国完成了理论的引介与本土化实践。在此过程中,研究和探讨对西方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吸纳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方法,以宁波鄞州区融媒体中心为个案进行剖析,发现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本土化实践极具中国特色。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明确导向的同时,在实践中完成了对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吸纳、融合与创新,并在新闻理想与媒体生存之间获得平衡。西方建设性新闻框架经过基层媒体的磨合与调适后,逐渐形成了更具生命力、包容性和中国特色的建设性问政监督的实践逻辑与操作模式。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县级融媒体;问政监督;鄞州样本
近年来,一种融入了积极心理学元素的西方新闻理念——“Constructive Journalism”进入了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的视野,国内学界将其译为“建设性新闻”或“建构式新闻”[1]。在理论引介的同时,将其定位为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生产形式和理念。“国外主流媒体在建设性新闻领域的实践已取得不菲的成绩,学术界研究方兴未艾。”[2]而且通过文献计量梳理海外学术界相关领域时还发现,“建设性新闻研究不断拓展内涵,逐步走向世界,不仅具有清晰的理论轮廓,而且有广阔的学术视野”[3]。然而,十余年来,西方学术界同建设性新闻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献总量却不足百篇。对比西方,国内学界对“建设性新闻”却抱有高度的热情与期待。在2019—2022年间,国内发表相关领域论文将近400篇,学科核心期刊都以设立专栏、编辑专刊等方式关注和探讨了该领域研究。同时,《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凤凰网、石家庄广播电视台、苏州广播电视台等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响应,积极开展建设性新闻探索和实践。在很短时间内,“建设性新闻”完成了从理论引介到落地实践的过程,从学术边缘迅速走到了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的“舞台中央”,可谓速度惊人。当下,我们需要正确对待西方新闻学理论的本土化借鉴、吸纳与实践,也需要在与西方进行学术交流时处理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4]的关系,从而实现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建设性新闻的溯源与特征
建设性新闻的概念肇始于西方媒体实践,旨在改善负面报道过度泛滥的状况。[5]狭义来看,建设性新闻指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类新闻实践的新探索,可与“解决之道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相提并论;广义来看,建设性新闻则是此类新闻实践凝炼与抽象而成的新闻理念,将“解决问题与否”作为新闻优劣的评价标准,强调提供立体完整的新闻报道,寻求并建立一套可以付诸行动的解决方案[6],为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开拓路径。
建设性新闻理念承袭和涵盖诸多积极元素和价值特征,被称为新闻报道的“伞式”理论。[7]根据报道策略划分,建设性新闻存在对策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四大分支。[8]实际上,建设性新闻集成了各类新闻报道的焦点及技巧,包含了“方案性、未来导向、多元包容、赋权公民、解释新闻及语境、协同创作”六大特征要素,但始终将“解决特定问题”作为核心诉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建设性新闻突破了消极报道的传统批判,传承与凸显了新闻的社会公共责任,有助于直面与突围当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危机。总体而言,建设性新闻是对西方新闻传统的检视、纠偏与补充,由此掀起了一轮新闻领域的理论热潮,并顺势进入中国新闻界。
(二)实践本土化:建设性与正能量的在地结合
中国传统的正能量传播思想、当代新闻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实践为建设性新闻的本土化提供了理论根基和实践路径,以发挥“媒体积极自由”和“记者主动角色”的功能。新闻实践中正在形成一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传播正能量为导向,面向未来和寻求媒体生态平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理念。[9]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正是融入建设性新闻理念的重要领域。根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思想,“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10],两者的出发点和目标均是为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改進工作。由此可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并非西方式的“揭黑”和“扒粪”,而是重在为国家“建言献策”,为党政部门“分忧解愁”,为社会群体提供一种由治理参与者向治理主体者转变的机会[11],以推进社会治理为价值目标。
与此同时,为了坚守舆论主阵地,打通新闻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县级融媒体建设如火如荼,已经从全面覆盖转向纵深发展,从机构融合迈向社会融合,对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12]可以说,县级融媒体既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鼓励民众参与治理的重要工具,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从舆论监督角度来看,一方面,县级融媒体贴近基层政府和民众,具备地缘上的天然优势,有利于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建设性舆论监督有助于县级融媒体替民众立言、与政府协同,促进问题切实解决,从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因此,县级融媒体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具备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值得进一步的基层实践和创新探索。
二、研究对象
宁波市鄞州区融媒体中心成立于2019年6月,在成立伊始就明确提出“以建设性问政监督作为改革方向和工作重心”,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融媒体中心建设性问政监督的开展,推动了新媒体应用平台下载量、活跃用户数的大幅提升;相关新闻栏目获得了省市区各级宣传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节目取得的相关成果获得了省部级领导的批示;更重要的是,由于建设性问政监督,所在辖区政府的民主评议成绩得到显著提升;地方政府也因此对融媒体中心给予了政策、经费和编制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同时,学界评价认为“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性新闻报道特色鲜明,效果显著,是政府运用媒体促进自身工作的典型案例”。[13]2021年,宁波市鄞州区融媒体中心又因其建设性问政监督的特色,入选了中宣部县级融媒体典型案例的调研项目。因此,作为建设性新闻理念在中国新闻媒体本土化实践的考察案例,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确实具有管中窥豹的现实价值,而且作为经济发达城市宁波的基层媒体,鄞州区融媒体中心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以该个案作为样本展开剖析,无疑更具普遍性意义。
研究团队在2021年至2022年间多次前往鄞州区融媒体中心进行实地调研及深度访谈,全面了解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发展脉络、实践路径以及“建设性问政监督”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基于访谈与调研所获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结合网络文献资料,剖析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的新闻理念,挖掘和梳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演进关系,从而为全国范围内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与方案。
三、研究发现
(一)建设性问政监督的政治方向
鄞州区融媒体中心介绍,早在2018年该中心就已经接触到建设性新闻理念,开始将其融入新闻业务实践,通过舆论监督参与社会治理。从具体的新闻实践来看,鄞州区融媒体中心打造了“鄞响”全媒体发布平台,并构建了舆论监督的五大品牌矩阵。至此,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性问政监督实践已经形成了多样化的主题报道和问政监督形式,结合融媒体新技术,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问政监督全媒体矩阵,成为提升其影响力的一张“金名片”。
建设性问政监督不仅提升了县级融媒体的影响力,而且在宏观层面改变了媒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问政监督所关注的不仅包括日常民生中的大事小情,也包括政府施政中的各种决策。融媒体中心的管理者不断强调,问政监督的努力方向与政府的施政方向是高度契合的。媒体管理者能够以“局内人”的身份参加各种政府工作会议,与问政监督的对象长期平等交流,甚至本身就归属于同一体系,而媒体问政监督也可以被视为政府施政行为与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主流媒体被当作“党委政府执政资源和工作平台”[14],使区域治理更加高效顺畅。就媒体角色而言,议程设置下建设性的问政监督使媒体角色从传统的“耳目喉舌”“传声筒”转变为“思想库”“智囊团”。基层治理与政府施政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问政监督的方式被抛出,在联系群众、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导下,媒体成为政府解决问题、寻找智慧、探索路径、求得理解与认同的重要手段。
由此看来,鄞州区融媒体中心所秉持的建设性问政监督与西方主张的建设性新闻理念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对于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强调,其核心是对于自身过度商业化、市场化所导致的“破坏性”的“自我救赎”;而中国“建设性问政监督”背后的历史性意涵则更容易被各层级政府所理解和接受。因为“这里的‘建设是有明确社会理想和政治方向的词汇,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辩证过程,其内涵包括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5]。因此,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不存在“谁来建设?建设什么?为谁建设?”的疑虑,党的新闻工作者不仅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伟大进程的忠实记录者,而且也是积极参与者、切实推动者和不可或缺的建设者。
(二)建设性问政监督的解困之术
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性问政监督拥有五大品牌。其中,周播电视舆论监督栏目《鄞视聚焦》紧扣民生小事,推动相关问题的整改落实;报纸专栏评论《钱湖走笔》以小見大,围绕鄞州新近发生的热点舆论事件,平均每月发表5—6篇评论文章;电视问政类访谈节目《民情面对面》,深度报道社会热点、难点,监督和质询干部们相关的工作问题,促进诸多“疑难杂症”的有效解决;广播新闻节目发挥舆论监督“轻骑兵”作用,速度快、数量多、力度大,曝光类评论作品在每年的省、市政府奖中屡次获奖;新闻专栏《鄞响聚焦》则连续追踪曝光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的典型问题,在社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对不文明现象、行为的监督热潮。这五大品牌栏目矩阵是融媒体中心“报、台、网、微、端”的立体呈现,构成了多元、立体、完整的新闻内容传播模式。
同时,鄞州区融媒体中心还充分利用不同传播平台的特色,通过“鄞响”客户端的即时性,电视台黄金时段的聚焦,报纸显著版面的联动,以及鄞州新闻网的跟进,从“一次采集,多方发布”到整合媒体资源,加强舆论监督的影响力。在首轮曝光后,无论是报纸、电视台还是“鄞响”客户端,都会开展“回头看”的追踪,继续以媒体联动形式跟进报道整改所取得的成绩,曝光整改不力等问题。
基于建设性新闻理念,新闻业不仅需要揭示问题,同时也需要提供“问题解决导向”的报道框架。[16]相应的,建设性舆论监督的重点是杜绝“一曝了之”的现象,通过追踪问效、回访反馈等方式,推动社会治理问题的及时整改和督办。[17]在此过程中,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确实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譬如,举办“民情面对面——局长问政公开赛”,在公开问政之后,鄞州区融媒体中心及时开设《立行立改》新闻专栏,针对各自涉及的问题,跟踪报道相关部门的整改行动。因此,建设性问政监督的解困之术的核心在于,其不仅要关注当下存在的问题,更要着眼于未来的解决之道,甚至要以忧患意识和长远格局去深度思考,并共同推动政策出台和机制改革。而在此过程中,新闻媒体和从业者的主动谋划、积极参与,甚至精心安排都变得必不可少,更具主动性与积极性成为基层融媒体实现建设性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发力点。
(三)建设性问政监督的聚力之道
在访谈和调研中,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管理者普遍认为,解决融媒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财、物资源匮乏的现状,是当前基层媒体做大做强的核心问题。新媒体的崛起不仅直接影响了传统媒体自身的造血能力,限制了其拓展空间和获取物质资源的能力,更导致了在人才资源更替方面的难以为继。如何应对以上这些在基层媒体融合进程中广泛存在的问题,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的经验是聚合行政、媒体、用户、社会的多重力量,做大做强“‘鄞响客户端”,以此作为建设性问政监督的主阵地。
(1)聚行政之力,联结政府工作。这是从鄞州区党政工作人员入手,让党政工作人员养成每日必看“鄞响”的习惯。一方面,“鄞响”客户端开设专题类栏目,发布大量的本地资讯,使客户端成为区委区政府政令通达的窗口、政情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多途径收集市民、企业关心的问题,整理后由政府在“鄞响”平台进行精准回应、即时推送,形成强烈的社会反响,强化了“鄞响”客户端的权威性。
(2)聚媒体之力,推进深度融合。融媒体中心正式运营以来,鄞州区报业和广电融合,人力资源得到快速扩充,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度融合,反映在“鄞响”客户端上的就是图文音频综合呈现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尤其是在电视媒体的加持之下,客户端平台的短视频内容迅速发展成为亮点。设立“鄞响V视”,以20秒短视频形式呈现时政新闻;开设“直击一线”,将电视新闻节目拆解重塑、按需投放;推出“鄞视频”“鄞响记者VLOG”等系列短视频,更具新媒体传播特色,优化用户体验感。
(3)聚用户之力,鼓励自媒体创作。融媒体中心与自媒体展开合作,充分挖掘用户资源,鼓励和推动用户生产内容的UGC模式,让内容信息逐渐摆脱原来留给用户的“呆板”印象。由客户端推动的UGC内容《新疆做馕姑娘》《鄞州青年节》《复工第一天》《一起聆听城市复苏的声音》等爆款短视频作品在全网总计流量过亿,并且被央媒选用和转载。
(4)聚社会之力,吸纳第三方力量。通过激活和利用社会资源、第三方力量,拓展新内容,打造新品牌。针对区委区政府的不同工作重点,“鄞响”客户端与其他区部门单位合作,开设各类专题共计21个。例如,与区教育局合作推出“空中课堂”,将区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在云端分享,累计上传200多个课件,累计点击量突破180万次;与区人社局合作开设“千企万岗”网上招聘频道,持续吸引就业群体的密切关注。
对于基层融媒体而言,“聚力”无疑是一种谋求生存发展的积极策略;对建设性问政监督而言,“多方聚力”则践行着呼吁和引导政府、企业、公众共建美好社会的建设性新闻理念。[18]换言之,媒体不仅自己成为改变社会的积极记录者、参与者,而且还将更多的社会主体纳入共创美丽中国的伟大进程之中。
四、结论与探讨
通过本文对鄞州区融媒体中心建设性问政监督的个案研究,不难发现,中国基层媒体的在地实践已经调适出逐渐清晰的实践逻辑与操作框架,进而勾勒出的则是更具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理念。
首先,建设性新闻理念虽然在理论界被视作西方新闻界学术和实践的产物,但在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中建设性新闻则被视为对西方学术话语的借鉴、吸纳、融合和创新。建设性新闻理念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从学术版图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施于实践,一方面无外乎其核心理念始终仍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框架之内,与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宗旨和原则不仅是并行不悖的,而且因为党的历史和党的新闻事业史本身就是一部建设史,建设性新闻理念自然而然地被吸纳与融合。另一方面,应对新媒体的挑战与冲击,媒体融合仅能在有限的层面上解决中国传统主流媒体所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仍需通过理念的创新与变革为新闻生产实践注入更多活力,不仅要守住舆论主阵地,更要在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上寻得新突破。
其次,鄞州区融媒体中心将建设性新闻理念与中国问政监督相结合,无疑在完成一轮媒体角色和新闻从业者身份上的重新设定。媒体与新闻从业者要成为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引导者”与“行动者”,他们需要面向未来,号召公众以交流、沟通、合作的方式直面问题、共谋出路、携手共进,共创美好社会。在此过程中,建设性新闻的“介入性”取代了传统的“客观性”[19],为媒体和新闻从业者提供了与新媒体、自媒体同等的主动权与话语空间,使其能够在社会治理、改革与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甚至主导型的角色。
再次,无论是建设性新闻所追求的共建美好社会,还是中国当下所追求的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共创美好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成这些目标都需要打破不同圈层和群体之间的漠然、冲突与割裂,都需要大众在物质与精神层面汇拢与凝聚。而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所尝试的,就是要不断前瞻和描绘彼此共同的未来愿景,给予公众期待、信心与希望,它不是简单地提供积极、乐观与正能量,而是提供方法、路径与行动方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传播秩序重建研究”(18BXW062)研究成果]
參考文献:
[1]徐敬宏,郭婧玉,游鑫洋,胡世明.建设性新闻:概念界定、主要特征与价值启示[J].国际新闻界,2019(8):135-153.
[2]晏青,凯伦·麦金泰尔.建设性新闻: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对凯伦·麦金泰尔的学术访谈[J].编辑之友,2017(8):5-8.
[3]邵鹏,虞涵,张馨元.新闻正能量:建设性新闻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94-110.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9(2).
[5]Mast J,Coesemans R,Temmerman M.Constructive journalism:Concepts,practices,and discourses[J].Journalism,2019,20(4):492-503.
[6]殷乐.并行与共振:建设性新闻的全球实践与中国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S1):33-41.
[7]金苗.建设性新闻:一个“伞式”理论的建设行动、哲学和价值[J].南京社会科学,2019(10):110-119.
[8]McIntyre K,Gyldensted C.Constructive journalism:An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y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echniques to news production[J].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2017,4(2):20-34
[9]邵鹏,叶森.疫情报道中我们需要怎样的新闻与新闻业:兼论中国建设性新闻理论的构建[J].当代传播,2020(3):46-50.
[1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88.
[11]王建新.国家治理视角下党媒监督的实践逻辑[J].新闻大学,2021(5):81-94+124.
[12]张昱辰.从机构融合迈向社会融合: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路径再思考[J].中国出版,2019(16):10-13.
[13]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用建设性新闻拓宽社会治理新思路[EB/OL].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1786165.
[14]褚银良批示肯定《鄞响聚焦栏目》[EB/OL].http://www.nbyz.gov.cn/art/2021/8/31/art_1229108276_59148622.html.
[15]李彬.建设性新闻之辩[J].学术前沿,2021(9):116-126.
[16]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J].新闻记者,2019(9):32-39+82.
[17]赖薇.建设性舆论监督:党报参与社会治理的“重头戏”:以北京日报《政府与市民》的实践为例[J].新闻与写作,2020(4):94-97.
[18]Hermans L,Gyldensted C. Element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Characteristics,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udience valuation[J].Journalism,2019,20(4):535-551.
[19]常江,田浩.建设性新闻生产实践体系:以介入性取代客观性[J].中国出版,2020(8):8-14.
(邵鹏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王晟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