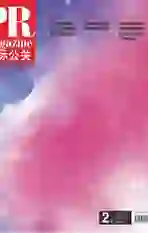理性选择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的行为研究
2023-05-23韩晓宇
韩晓宇

摘要: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加速外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孝道文化受到冲击,削弱了以往以配偶和子女为主的家庭养老。发展互助养老成为弥补农村家庭养老弱化、增进农村老年人福祉的必然选择。本文以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选择互助养老是基于资源获得和偏好满足的一种理性行为,互助双方理性地考虑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并遵循一定的规则。
关键词:理性选择理论;农村互助养老;理性诉求;行为逻辑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已达26402万,20年间增长了13405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上升了8.3%。[1]农村是中国老年人最多的地区,积极应对农村老龄化,提高老年人福祉是乡村老龄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而农村养老的现状是家庭规模缩小、居住安排和生活方式较传统模式发生了变化,对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造成了极大冲击,使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趋突出。在农村倡导与发展互助养老,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缓解养老压力的重要措施,受到国家与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一、互助养老的动因
(一)农村养老场域发生变化
农村家庭资源有限、风险抵御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互为反馈的社会交往,这种交往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帮助” 和“回馈”,但基本上是出于个人的责任和感情,不会理性计算收益。从伦理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村是以“己” 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农村的帮助和回馈是从离差序格局最近的中心出发,先是家庭;后是亲属、邻里、朋友,这种基于伦理和情面的依靠血缘或地缘关系结成的互助纽带,在一定的场域内稳定地发生,一旦超出这种由人情伦理体系构建的场域,互助行为便很难被信任。
而在现代农村中,由于年轻人去城市打工,差序格局处于中心位置的亲子关系所带来的资源和链接由于距离过长,脱离了农村老年人养老的场域,以往依靠子代和亲属的非正式支持的家庭养老格局发生了改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子辈能够提供的只是基础的经济资源,服务照料和精神慰藉提供不足,老年人需要离开家庭这个场域,寻找新的养老资源的代替。农村的人口流动使得农村的封闭性发生了变化,以往出于人情考虑的互助行为变成一种出于利益考虑的工具理性行为,脱离亲缘和地缘的互助,需要发生在可持续的循环互助组织中。农村互助养老需要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小农道德伦理发展成为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新的利益共同体,守望相助,抵御养老风险。
(二)政府的大力扶持赋予合法性
自2008年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前屯村建立农村互助幸福院以来,农村互助养老成为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良方,在各地政府的推动下各地开展了农村互助组织试点。在国家有关农村社会养老的部署中,均提出要发展互助养老,并且从最初的组织建设发展到服务供给。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提出要重点建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人活动中心、互助式养老服务中心等社区养老设施。[2]2016年《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强调,要大力支持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建设。[3]2019年4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促进农村、社区的医养结合,大力发展政府扶得起、村里办得起、农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的农村幸福院等互助养老设施。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开辟失能老年人照护单元,确保有意愿入住的特困人员全部实现集中供养,逐步将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转型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4]
(三)农村老人有参与互助养老的能力和闲置资源
农村互助养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低投入,利用内部资源是实现互助养老存续的关键。实际上,农村的资源缺乏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缺乏现代管理的组织框架,对于村庄内部闲置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动力。[5]
农村老年人并没有像城市老年人或是西方老年人那样有明确的退休时间,大部分老年人都会依据身体情况继续进行劳动,因此无须也不应该将老人看作是无能的被照料者。无论是依靠政府组织集中入住的农村幸福院;还是根据无组织的村民的松散自助养老;还是依靠时间计量劳动付出的时间银行,对于健康的老年人来说,都是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提供帮助,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人来说,时间资源和人力资源实际上是闲置资源,也就是说,互助养老所需的主要资源在老年群体中并不是需要竞争的稀缺资源。相反很多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健康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欠缺,在老年时期逐渐退出社会生活,对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信心不足。因此,激发村庄内部的资源,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服务的过程中动态地获知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资源的供给是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基础的,这样的资源提供可以最大效率地被利用,既能满足现阶段农村养老的迫切需求,又能够实现农村老人的积极老龄化。
二、农村互助养老的理性诉求
(一)资源互换:养老需求的最大化实现
理性行动理论认为,行动者可以通过控制资源实现自身需求的实现,并实现利益最大化。[6]在社会行动系统内双方因为有一定的目的,依赖对方所控制的资源获取利益,并且可能因为这种交换产生进一步的依赖关系。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中主体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养老服务的供需双方。供需双方可以通过资源的互换实现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最大化实现。
农村互助養老生发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基础上,对于无法实现家庭养老的老年人来说,即使子女可以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支持,却无法弥补家庭的情感支持功能。而参与互助养老能够扩大老年人的社交活动,通过集体娱乐、服务参与等手段,丰富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增强老年人的社会资本,有效解决老年人的孤独问题,增加老年人的自我社会价值。因此,农村互助养老主要是依靠家庭之外的社会力量满足养老需求,服务方主要是低龄老年人、邻里、朋辈等群体;被服务方主要是需要照料及需要精神慰藉的失能、半失能老人。从行动系统来看,服务的提供方所拥有的资源包含时间、服务照料、精神慰藉;被服务方所拥有的资源包含时间、政府补贴、情感,可以从服务提供方得到满足的需求包括服务照料、精神慰藉。互助养老能够满足老年人日常的服务照料和情感慰藉。
(二)偏好实现:短期付出与长期利益的权衡
老年人的需求主要分为三大类:物质的、服务的、精神的。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需求被分为五个等级:老年人对物质需要是最基本也是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老年人对服务的需要是满足安全的需要,而对精神的需要则是比较高层次的对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目前,互助养老的主要服务提供者是低龄老人或志愿者。健康的低龄老人虽然具有比较好的健康资本,即可以劳动,但是并没有固定的收入,未来面临生存的风险,通过互助养老的方式短期内付出劳动虽然无法实现当下的利益最大化,但从长远来看,进入老年期后,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必定会增长。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直接目的是期望未来能够换取等价的自我养老需求的满足,虽然这种回报不是即时的,但这是一种基于利益考量的理性行动。虽然面临信息不对称,劳动无法货币化等问题,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可持续的循环互助养老可以使自己未来能够得到养老服务照料而不必付出高额的花销,这对于自身未来的养老选择是十分有利的,选择互助养老也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得到对应的服务。
三、互助养老的行动逻辑
(一)价值规范:以情感为主导的尊老互助的文化规则
规则是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通过实行奖惩措施,可以促使人们按照规则行动。[7]包含正式规则,也包含文化规则、社会规则等非正式规则。在传统农村社会内一直存在着适合互助养老发展的内在文化规则,这种规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守望相助;二是尊老敬老。
农村社会本就是熟人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宗族观念和血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瓦解,但是农村社会的乡土底色没有发生变化,血缘和地缘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消失,原来的养老道德规范和互助规范依然具有很强的认同感。互助养老模式发挥了农村的地缘优势,打破了以往只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养老格局,聚集养老,将分散在村落各处的老人集中在农村幸福院内,缩减老人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既节省了互助的成本,又能够拉近老人的心理距离,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在幸福院内随着交往距离的缩短,互助网络也变得紧密,从而使互帮互助的文化规则得到强化,构成新的利益共同体,有助于农村重焕敬老爱老和守望相助的文化传统和底蕴,无疑为发展农村互助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础和社会支持。
(二)行动规范:以理性为主导的等价互惠的社会规约
人情规则是农村社会维持秩序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农村封闭而资源分散,人们之间不依靠利益关系守望相助,它依赖于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成为一种由文化价值支持的社会规范,约束着人们之间的交往。[8]人情规则通常适用于以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情感共同体中,承载着道德内涵。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现代化观念涌入农村,人们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蕴藏着伦理情感的人情规则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在规则下选择更加理性的策略来应对。[9]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不再是基于道义的帮助与回馈,正在向社会互惠规则转变,具体表现为人们比起交往的情感表达与获得,更加注重互助的成本与获利是否对等,这也是在农村熟人社会日趋衰落的情况下,互助养老得以发展的保障。
在平等互惠的社会规则的约束下,这种在区域和群体间相对公平的养老服务交换进一步提升了由于过去熟人社会瓦解而逐步衰减的农村的信任感和凝聚力,使得社会成员更加愿意从事到互助养老的服务中。群体之中的平等互惠规则同时也会提升未来服务提供方与被服务老人的获得感和体验感,促使其为未来满足养老需求目标而努力,继而加入到互助养老的队伍中来。这两类人群都以利益最大化下的平等互惠原则为行动逻辑,引导着人们互助养老的服务行为。在互助行动中,老年人除了受到孝道、尊老以及互助文化规范的约束外,还受到社会中人情的平等交换的互惠规约。这是一种基于市场价值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遵循的是平等互惠的社会交换规则。
四、总结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互助行动是一种理性行动。作为理性行动者,老年人会理性分析如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文化规则和行为规则的鼓励与限制下,农村老年人通过控制自身的资源分布,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互助养老选择,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理性行动者,农村老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取决于其资源价值是否能够合理交换。因此,农村老年人在试图控制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源来获得长期养老服务的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是即时的,也可能是未来的回报,这是微观层面上农村老年人选择互助养老的行动策略;在宏观层面上,个体的理性行动在文化规则、社会规则以及制度化规则的影响下理性分析,规避风险,选择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因此,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之内理解和讨论如何实现农村互助养老行为的循环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EB/OL].[2021-05-10].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
[2] 国务院办公厅印.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EB/OL].[2011-12-17].http://www.gov.cn/zwgk/201112/ 27/content_2030503.htm
[3] 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EB/OL].[2016-07-06].http://www.gov.cn/xinwen/2016—07/06/ content_5088745.htm
[4] 国务院.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EB/OL].[2019-04-1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4/16/content_ 5383270.htm
[5] 張彩华.村庄互助养老幸福院模式研究:支持性社会结构的视角[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7.
[6] 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 李凤翔.理性选择理论述评[J].经济研究导刊,2014,(36): 302-303.
[8] 杜鹏.“面子”: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探究[J].社会科学文摘,2017,(7):65-67.
[9] 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