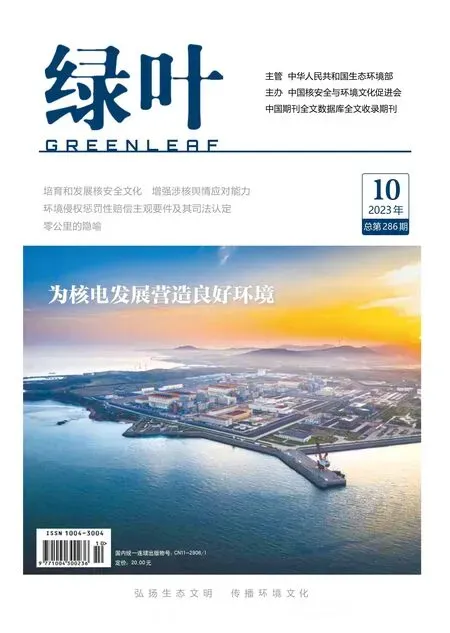回望
2023-05-10◎杜柯
◎杜 柯
记得更多时候是在暮春或初夏,家里就我和母亲,每天,有种日久天长的清宁、安寂、平和的调子。岁月无恙,冬去春来,春艾夏生,人老了一岁,又像年轻了一轮……
——适逢此时,开启了那段美丽的日子。想想看,风清月明,草木蔚然,阳光明媚,川溪润朗,空气中微微颤动着一丝超越云翳之上的清响……万物欣悦,丰饶生长,每样生物都自立自足于浩瀚的王国,大地蕴藉深远,世界灿烂明亮,而我们仿佛需要一种语言——超越语言之上的语言,需要一种情感的归宿和灵魂的召唤,因而总是那么不动声色又深情有致地酝酿着什么……
面对如此静谧的、清明的,宛如锦瑟一般美好的时光,真不知该如何度过一分一秒,怕把它生生虚耗、浪费了。
这时候,我就忍不住要做点什么。
但做什么才有意义呢?结末是四处走一走。常常是出了家门,往山野里跑,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没个固定路径,随心所欲——“道”法自然。
我妈呢,这时也忍不住要做点什么,因为天气实在太好啦——其实她一直在做着各种家务,目下就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洗衣服,树冠和阳光斑驳错落投影于地,院子里清晰生动。
我给妈妈打了声招呼,便出门去。路吸引着脚,脚把我带向东面一个山坡,那山的坡体庞大,雍容,意境舒展,可以登高望远,主要是离家又很近,能够适可而返。
我身不由己地走着,好像腿脚可以单独行动而不受我指使。这蜿蜒的羊肠小径,穿过田地,穿过丛林,穿过溪流,穿过沟壑、崖根,穿过梁峁、山坡、草地,在我眼里永无尽头,顺着任意一条岔路仿佛都可以把自己走到消失,走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迷离处……这条土路,永远是一副淡漠表情——从来没见它热闹过,有人走时就恍惚生动一点,人走后又迅速陷入一种博大自足的沉寂。它仿佛是有生命的,但是进化太慢,且俨若修行的隐者活了几百年,是个快要成精的老道,看起来什么都漠不关心反应微茫,可内在却有宏大的定力和智慧。
有时候是春天,路把我带向这草长莺飞的三月天。春色丰艳,天空瓦蓝,视野里满目是令人舒悦、灵魂轻盈、肌肤润泽的清辉。燕子在天空剪剪地飞,像在裁布,蝴蝶穿着花裙子,醉心于舞蹈,路旁的每一株草,每一蓬荆棘,都焕发出无限生机,空气鲜净纯美,穹宇明蓝动人。有时候是夏日,道路两旁嘉树成荫,幽凉若梦,某处隐秘的山谷正流着翠玉一般的溪水,听起来使人觉得清新脱俗……这水,好像流进了人的心田里。坡田上玉米已初显长势,一排排,秀色林立,山风吹拂过一面面绿色旗帜,随风动荡,掀起窈窕的翠浪……此时,即便是一个从未从事过稼穑之人,亦可和这群植物做心灵的对话和共晤……一种秘密的会意,造成了心灵的柔情冲击,愉悦包围了心脏,扩大成眼前绵绵浩浩的风华。
而有时是秋天,气候清和干爽,天空素净淡雅,万物宴然、庄严,一切清晰如画,为气韵生动的丹青妙手,一气呵成的浑然天成之作。还有老鹰,孤傲地,施了魔法般螺旋形盘旋于高空之上,以上帝的锐眼默然检阅人间,做凌厉简练的速写——悟透了世间千年轮回不过是它的一个盘旋缩影。这种桀骜和洒脱,唯属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孤勇者。
依稀记得,很多时候我去爬山,而母亲正在家里做家务,我徜徉在这样的意境里,一刻就是一万年,一万年也是一瞬呵,我多次走向那面青翠的山坡,永远浓缩和凝结在时间的舍利腹内。
命中注定,那些时候,我走啊走,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似乎要从自己躯壳里走出来,走成一个赤裸的、全新的、非俗世间的生命。从家里出发,到那个山坡,不过二十分钟脚程,我在走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变得更加自由,像一只蝉蜕壳似的——换句话说,每次出行,无异于一场禅修之旅……
一次我途中去吃桑葚——那条溪谷的沟壁上寂寞地生着几株桑树,到了季节,桑葚已经成熟,油黑光亮地缀在枝头。地面还撒落下斑斑点点,没人吃,除了蚂蚁和鸟雀。这天可把我吃美了,那种鲜甜,来自天地日月的菁华孵育,成为我独享的盛宴。
当吃到不想再吃之后,去沟溪里洗手净唇,对着亮闪闪的水镜看清自己已洁净如初,重新缓缓起身,漫步而行。
涉过溪沟,攀爬进入了一片树林,白杨、桦树、栎树,各类落叶乔木杂生,那哗哗的流水声,分明是“安静”另一种改头换面的喧嚣。山风林籁,鸟啼蜂鸣,便在其间幽幽回荡,如同一个巨大风箱——里面发出的声音,丰富和单纯、现实与梦幻杂糅。树林里,尤其是夏日的树林有多么盛大的情绪!那种蒙鸿浮动,生命芳华一并礼献、祭出,静静地燃烧且释放巨大能量,令人近乎疼痛地感动着。它们清晰而强烈的阴影里滋生出秘密空间,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前尘往事就在里面沉淀,回荡……
路旁草丛,不时有覆盆子、羊奶泡,和一种叫“救命粮”的红色小果——像豆子似的,不知道学名叫什么,据说当年红军战士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吃它救过命,也有民众吃它充饥,所以叫“救命粮”;不过它毕竟不是粮,这玩意吃着酸甜可口,吃多了会引起便秘。
天气实在太帅了。天空蓝得能刺激出人的眼泪。苍崖翠壁,修林茂竹,远依白云,令人目迷神摇。对面舒缓的山坡,坡腰上散漫地丛生有各类香花野果,随手可以拾掇。香甜的浆果,微辛而芳馥的野花,是大山娟美的笑颜和诚意待人的礼物。
如果走乏了,途中随便找一处草甸、一块石头坐下来,身心顿歇,物我相融。有的岩石面貌冷峻,有的面目和善,但无论多么冷峻,一屁股坐上去,一会儿也焐热了。而面目和善的,亦是样貌多样:有如天然沙发,有如胖硕面包,有似老头慈祥的脸,有若山羊嶙峋的头。那些石头我每经过一次,仿佛都会记我一次,所以后来我看到它们,都怕它们突然要伸出手来与我打招呼。
说起这面山坡,其实与我家的直线距离不到一千米。它微微地倾斜——那是一种充满了柔情和浪漫的倾斜,宛如少妇娇慵的衣裙,可以看到起伏之曲线。其实这山坡也是牧童经常光顾的地方,有时候,我会在这里遇见他们。但遇到的他们也是安静的,牛羊安静地啃草,牧者安静地跟随……这里没有热烈欢腾、喧哗聒噪,静宁安逸是永远的主题。
坐在山坡上,就沐入了山野自然的清光之中,心旷神怡,视野阔大。远处是一层层起伏的山峦,犬牙交错割据着,颜色深浅明灭;近处山上,可以看到一畦畦修洁整饬的田地和随势赋形结庐而居的人家。有人在门前的地里劳动,镐锄一扬一落挖掘着什么;有人在院场晃悠,还能看到小孩子撵鸡——大约是偷吃了晾晒的粮食;有人去井栏挑水,慢慢移动,从容不迫……啊,这种生活总是给人天长日久的感觉,也不知多少年多少代就这样过去了,也许,爷爷和孙子过的是同一种生活,不过在年岁上有了轮回,内容却是重复的,大家都习惯成自然,无怨无尤乐天知命地过下去。
有时候不免去想:难道多少年后我不在了,我的某个后代子孙也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观望,并且观望的情景一模一样吗?又或者,多少代之前,我的一个无名祖先正坐在我现在的位置,甚至坐在同一块石头上向对面张望,是否看到的也和我现在差不多?这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话:时间是静止的,流逝的是我们。
对于臀下的石头,我诞生出一种联想:自然的风化演绎中,石是可以变成土的,而土也可以变为石,比如土能生木,木又能生土,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天地构成五行的元素都可以互生——恒常的变中有不变,大的不变中有永久的变……这正是世界的构成与解析,阴谋与阳谋吗?
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仿佛可以无限放大我的身体。仰望高空,碧宇深远,一丝不苟,清朗得像万年前就在储蓄这清朗;这蓝天永恒的染料虽也随时调整变化,但却无不以极致的单纯而见长,使人为之感动。
天空有巨大的云块在缓缓移动,如同一摊瓷实的棉团飘浮于头上。我迫近那朵白云,想象将其拥入怀中的暖意和温柔。那团云有野性,也散发着母性,甚至就像一袭棉被、一个大枕头,要我躺上去深深地睡眠吗?
环视四周,山野浩荡,花草烂漫,长风无尽。思绪在这时自由翻转、飞扬,适性任情,坐久了人会感到孤独,却又觉得无比宁静,乃至渐渐沉寂下来。最后,这平淡祥和的喜悦渐渐被稀释了,那是因为坐久了,想回家。
家在哪里呢?就在咫尺之遥。坐在山坡上,可以望见我家的院子,和在院子里做家务的母亲,从门口进进出出的情景。从她弯腰的动作可以看到衣服已经洗毕或第一遍已结束在倒洗衣水,有时她在择菜,身边放着竹篮,有时正在喂鸡,有时扫院……可以闻到母亲的气息和家中的日常气息——但这其实是闻不到的,而是条件反射,心里蓄存的记忆信息在视觉触及的一刻自然挥发。
我家的院子和房屋轮廓,望上去低低的,只能看到一个侧面山墙,院子也只能看到大半个,其间绿树掩映,杂花生树,把我家的庭院烘托得极富情致。
然而,当我回望的时候,虽然只隔着几百米空间纵深的距离,却像在眺望另一世界,而且是不可沟通的——我知道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妈妈一定不知道我在望她,从她那个角度看来,我是渺小到不可寻觅,因为山野的浩大浓绿稀释了我身影;当我回望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它安静得无以言传,怎么讲呢?仿佛电影中的镜头,也许就是侯孝贤的蒙太奇,那种安静像不存在似的,不真实,像下一秒就会消逝……
这个时候,我有点难过,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甚至会忍不住泪水长流,世界是多么悠久、宏大,不动声色,而我是多么渺小、脆弱。一大一小的衬托,令人备觉孤单。我深深地感觉到孤独的力量多么深重,不可摧毁。我似乎已离开家很长时间了,家的熟悉在减损,俨然好久没见到母亲,母亲的气息在变弱。这时,我会迫不及待地想回去,回到那个熟悉环境中,仿佛回去迟了便成南柯一梦,沧海桑田,找不到母亲,找不到回家的路,找不到我的家园了。
于是,我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草梗黏土,心怀无限忧伤,仿若刚经历过多么伤心的事,急不可待又忧心忡忡地往回走。这时,山坡背后,忽然转出来一个面目清癯、留着撮山羊胡的老人,我认识他,是山那面一户人家。看到我急匆匆往回走,他说:“就要回去哪,不再耍一会儿?”
我没有停止脚步,嘴里咕哝一句“不了”。我的声音很弱小,他也许勉强可以听到;也许,我的话刚出口就被风吹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