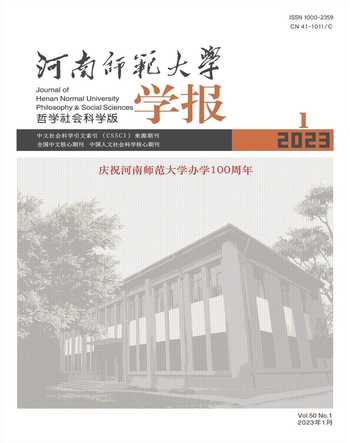唐《高宗谥议》读释
2023-04-29李思语陈飞
李思语 陈飞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3.01.16
摘要:《高宗谥议》是唐代皇帝谥议文中颇为独特的一篇。唐代皇帝谥号主要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等部门官员集体议定,上奏朝廷确认。《高宗谥议》的作者涉及执笔者、身份作者、精神作者等多重关系,虽以中宗口吻表达,实反映武后的意志。其按语关于“天”“皇”“大”的解释,或循旧例,或据经典,或为新创,与武后及官方的习惯说法不尽一致。高宗谥号“天皇大帝”应理解为“天皇”“大帝”的合称,文中关于高宗谥号的解释及其“九德”的过度虚美,杂糅诸家思想学说,大抵以儒家为根本,以道家为归宿。武后将高宗神圣化,与其特定的现实背景和政治用意有关。
关键词:武则天;唐高宗;天皇大帝;虚美
中图分类号:I20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1-0114-08收稿日期:2022-05-16
“谥议”是关于谥号的评议。“谥号”是为死者所加称号,一般要通过评议来确定,故就谥号议定规则及过程而言,属“制度”范畴;将议谥的内容撰写成谥议文,则属于“文学”的范畴。谥议集制度与文学于一体,是较为典型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关于文学的制度,包括文学本身的制度以及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制度,笔者于此拟另文论述,这里不多涉及。之一。古人死而有谥,起源甚早,一般认为西周时期已形成制度,秦朝短暂废止,汉以后复行,至唐代更加完备而规范。谥号有官谥和私谥之别,国家层面的官谥又可分为“君谥”和“臣谥”。前者包括皇帝、后妃、太子等;后者一般为高阶(三品以上)大臣。唐代皇帝谥号的确定过程,通常是先举行“南郊请谥”的礼仪,然后议定,将议定结果上报朝廷最终确认,然后以“谥册文”布告天下,有的还刻成类似图章的“谥宝”随葬。相关制度和仪式流程学者多有论述如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王岩:《唐代太常博士考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赵雪梁:《唐代皇室谥号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白雪兵:《唐代皇帝谥号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徐路:《隋唐官员谥法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但大都属史学的研究,很少从文学制度视角进行考察。目前可见的唐代皇帝谥议文共有八篇,《高宗天皇大帝谥议》(以下简称《高宗谥议》)是颇为独特的一篇。相关论著虽有所涉及,但较简略或语焉不详。本文拟就其中几个问题试作解说,以期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
一、作者的多重关系
《高宗谥议》的独特之处,首先是其作者。目前所见明确标署有二:一为《唐大诏令集》,题曰《高宗天皇帝谥议》,下署“武后”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中华书局,2008年,第75页。案:据文义,前者标题应有“大”字。本文所引《高宗谥议》文皆据《唐大诏令集》。又文中所引古代文献皆酌加标点。。一为《全唐文》之《中宗》二,题为《高宗天皇大帝谥议》董诰:《全唐文》,卷17,中华书局,1983年,第208页。。如此便有武后、中宗(李显)二说。据《唐会要》载:“高宗天皇大圣大宏孝皇帝讳治……宏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崩于东都贞观殿(年五十六)。文明元年八月庚寅,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县界)。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哀册文(天后武氏撰),谥册文(阙),谥议(阙)。”王溥:《唐会要》,卷1,中华书局,1955年,第3页。案:括号内原为小字注文。“高宗天皇大圣大宏孝皇帝”为天宝十三载(754)所加尊号,“天皇大帝”为最初的谥号,“高宗”为庙号。王溥(922—982)为五代至宋初的四朝宰相,也是著名学者和文人,当时他已不详高宗谥议文和谥册文(迄今未见)的作者为谁,可知《唐大诏令集》《全唐文》所署作者大概为后人(编者)所加。两个署名皆有其合理性,也有其不确定性,这须要联系当时议谥的实际情况来解读。《旧唐书·高宗纪》载:“(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是夕,帝崩于真观殿,时年五十六。宣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群臣上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刘昫:《旧唐书》,卷5,中华书局,1975年,第112页。“群臣上谥”就是群臣议定谥号上报朝廷,据此可知“天皇大帝”这个谥号应为群臣所议定,其谥议文的写作也应是群臣所為,至于具体执笔者为谁,尚不得其详,不论是谁,都表明《高宗谥议》的作者还有第三者的可能。
文献关于唐代“臣谥”制度的记载较为详明,如《唐六典·太常寺》:“太常博士掌辨五礼之仪式,奉先王之法制;适变随时而损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礼,则与太常卿以导赞其仪。凡王公已上拟谥,皆迹其功德而为之褒贬。(议谥:职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佐史录行状,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拟谥讫,申省议定奏闻。)无爵称‘子。……养德丘园,声实名著,则谥曰‘先生。大行则大名,小行则小名之。(旧有《周书谥法》《大戴礼谥法》。又汉刘熙注《谥法》一卷,晋张靖撰《谥法》二卷,又有《广谥》一卷。至梁,沈约总集谥法,凡有一百六十五称)”李林甫,陈仲夫:《唐六典》,卷14,中华书局,1992年,第396页。案:括号原为小字注文。学者或据此认为“太常卿和太常少卿负责拟定皇帝谥号”白雪兵:《唐代皇帝谥号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第17页。,此说可能并不全面和准确。实际上唐代参与“臣谥”的部门和人员尚不止此,如《唐六典·尚书吏部》载:“考功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其谥议之法,古之通典,皆审其事,以为不刊。(诸职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其佐史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任勘校,下太常寺拟谥讫,覆申考功,于都堂集省内官议定,然后奏闻。赠官同职事。无爵者称‘子。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奏赐谥曰‘先生。)”李林甫,陈仲夫:《唐六典》,卷2,中华书局,1992年,第41-44页。案:括号原为小字注文。可知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也有参与谥号议定的职能。
至于唐代的“君谥”,除了太常寺,还应有鸿胪寺的参与。《唐六典·鸿胪寺》载:“鸿胪寺:卿一人,从三品。(《周官》:‘大行人掌大宾客之礼。秦官有典客,掌诸侯及归义蛮夷。汉改为鸿胪。景帝中二年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隋初鸿胪寺卿一人,正第三品,统典客,司仪、崇玄等三署。开皇三年省并太常,十二年复旧。炀帝降卿为从三品,皇朝依焉。龙朔二年改为同文正卿,咸亨元年复曰鸿胪。光宅元年改为司宾寺卿,神龙元年复旧。旧属官有崇元署,开元二十五年,敕改隶宗正寺。)少卿二人,从四品上。……鸿胪卿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而供其职务;少卿为之贰。……凡皇帝、皇太子为五服之亲及大臣发哀临吊,则赞相焉。凡诏葬大臣,一品则卿护其丧事;二品则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仪,以示礼制也。”李林甫,陈仲夫:《唐六典》,卷18,中华书局,1992年,第504-505页。案:括号原为小字注文。又载:“司仪令掌凶礼之仪式及供丧葬之具,丞为之贰。(若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为五服之亲举哀,本服周年者,三朝哭而止;大功者,其日朝晡哭而止;小功已下,及皇帝为内命妇二品已上者、百官执事及散官一品丧,皇太后、皇后为内命妇三品已上丧,皇太子为三师、三少及宫臣三品已上,并一举哀而止。)”李林甫,陈仲夫:《唐六典》,卷18,第507页。案:括号原为小字注文。可知自汉以来诸侯王的谥、诔、策(册)皆为鸿胪寺职掌。唐制多沿前代,大抵亦当如此。又“凶仪”主要指丧葬礼仪,应当包括谥、诔、策(册)之类。据此推之,唐代皇帝、后妃、宗室,以及三品以上大臣的谥、诔、册等议定施行,皆当有鸿胪寺的参与。尤可注意的是,《唐会要》载:
元和十五年四月,礼仪使奏:群臣告天,请大行皇帝谥。准礼及故事,合集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于南郊告天毕,议定,然后联署闻奏。王溥:《唐会要》,卷2,中华书局,1955年,第18页。
“群臣告天请大行皇帝谥”应为此奏文的“事由”(主题),然后说按照礼仪制度和以往惯例,“群臣”先举行南郊告天请谥礼仪,然后议定谥号,然后“联署”“闻奏”。参加请谥和议定的“群臣”包括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及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联署”应为各部门长官联合署名;“闻奏”则是将议定的谥号(包括依据、理由等)上报朝廷(新嗣位皇帝)确定。由此逆推唐前期皇帝谥号的议定,大概也应如此。也就是说,高宗谥号的议定,应是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以及太常寺、鸿胪寺等相关部门官员组成的“议谥小组”来具体负责,议定后各部门长官联合签署,然后“闻奏”(虽然嗣君为中宗,但决定权在武后),最后确认。如果武后没有异议,那么这个“闻奏稿”应该就是最终的定稿;如果武后有不同意见或新的指示,则以武后满意的“修改稿”为最终定稿。总之,不论是闻奏稿还是修订稿,都要由“某人”来执笔完成,这个“某人”当然必须是官职、威望和文学水平都举足轻重的大臣,姑且称为“执笔者”。
然而这个执笔者未必就是《高宗谥议》的“身份作者”。所谓身份作者,是指文章所代表的“主人公”的身份,也就是以谁的身份和口吻来说话。在古今中外的官府文书中,执笔者和“身份作者”的不一致是普遍情况。如文臣为皇帝拟写诏敕,就必须以皇帝的口吻来说话。诗文中经常采用的“代言体”,也属于类似的情况。《高宗谥议》所代表和代言的身份主体为中宗(李显),文中称:
顾以虚菲,夙承乾荫。既忝彰明之地,常怀辅佐之诚。荐萤烛以助光,引鹤露而添海。而圣德虚受,无来不应。每听览余暇,侍奉话言。论道德则洞启元枢,语忠孝则广通心极。叙轩顼之淳化,积若神交;述尧禹之清风,宛成晤对。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第76页。
“乾荫”一般指父亲,如《梁书·袁昂传》载:“昂幼孤,为(从兄)彖所养,乃制期服。人有怪而问之者,昂致书以喻之曰:‘窃闻礼由恩断,服以情申……孤子夙以不天,幼倾乾荫,资敬未奉,过庭莫承,藐藐冲人,未达朱紫。从兄提养训教,示以义方。”姚思廉:《梁书》卷,中华书局,1973年,第452页。“幼倾乾荫”,即谓父亲早逝,幼年便成孤儿,由从兄抚养教育成人。唐人敬让《请致仕侍亲表》云:“臣未登壮岁,乾荫先倾。逮于强仕,母氏为育。欣欣而就禄者,希禄养之及亲也。”李昉:《文苑英华》,卷640,中华书局,1966年,第3132页。是说自己很早父亲就不在了,由母亲养育长大,出仕为官。至于“过庭”,更是人所熟知的子受父教的熟典。“冲人”则多用作儿子的自称谦辞,这里显然是指新即位的中宗。总的来看这段文字大意是说:自己资质一般,但一向承蒙父皇(高宗)的慈爱恩荫,被置于显要的地位。自己常怀感恩忠诚之心,愿为辅佐父皇尽微薄之力。父皇虚怀若谷,经常和自己交谈,从道德修养,到忠孝礼义,自己受益无穷。尤其是在谈到黄帝和颛顼的治化、尧舜及夏禹的成功时,父子之间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无疑都是以昔日皇子、当下新君的姿态和口吻在说话,可证《高宗谥议》的“身份作者”为中宗无疑,这应是《全唐文》将《高宗谥议》置于中宗名下的主要依据。
这段文字紧扣父与子、先皇与嗣君的双重关系来叙写,重在以情动人。或者说《高宗谥议》中的“感情”部分是与中宗相对应的,但其“精神”部分却未必出于中宗。这里的“精神”是指主旨、原则、基调及用意等,略同今人所说的领导讲话或上级文件的“精神”。《高宗谥议》的“精神”应主要出自武后,因为高宗谥号实质上就是高宗的盖棺论定,在当时朝廷权力格局下,即便是当朝宰相乃至嗣君中宗,都没有资格来作最终结论,而必须听命于武后。据《唐会要》载,早在“显庆五年(660)十月已后,上(高宗)苦風眩,表奏时令皇后(武后)详决,自此参预朝政,几三十年。当时畏威,称为‘二圣。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称‘天后。”王溥:《唐会要》,卷3,中华书局,1955年,第24页。《旧唐书·高宗纪》亦载:“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刘昫:《旧唐书》,卷5,第100页。《资治通鉴》述其事于麟德元年(664)《资治通鉴》,卷210《唐纪》17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司马光,胡三省:《资治通鉴》,卷210,中华书局,1956年,第6343页。)。大抵自麟德以后,武后便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及高宗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更加名正言顺地独揽军国大权。这段时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先是弘道(亦即永淳)元年(683)十二月四日晚高宗崩逝;十一日中宗即位,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则此前中宗虽有嗣君之名,尚无“宣敕”的资格;此后则一切仍取决于武后。次年正月一日改元嗣圣(684),二月六日便废黜中宗,次日改立睿宗(李旦),改元文明,除了“政事决于太后”,还“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于是武后正式临朝称制。八月葬高宗于乾陵,九月改元光宅,全面改易旗帜服色及官号,拉开了“革命”(以周代唐)的序幕司马光,胡三省:《资治通鉴》,卷230,中华书局,1956年,第6415-6421页。。总之,武后不仅早已实权在握,高宗死后更是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高宗的盖棺论定,在当时可谓国家头等大事,以武后的性格、地位及野心,决不可能不闻不问、任由他人,必然要深度介入、操控始终。况且按照制度和惯例,群臣议定后也必须“闻奏”,由武后最终确认。也就是说,高宗谥号的议定,不仅必须遵照武后的指示精神,而且必须经过武后的审核同意,才能最终完成定稿和授予。因此可以说武后是《高宗谥议》的“精神作者”。但《高宗谥议》应撰写于中宗被废之前,故又须显示中宗的存在。
由此可见,《高宗谥议》由群臣议定后联署上报,则“群臣”是“闻奏稿”的最初作者;“闻奏稿”由某位大臣执笔撰写,则执笔者为“闻奏稿”的写定作者。“闻奏稿”如果须要修改后定稿,那么“修订稿”的执笔者既可能是“闻奏稿”的写定者,也可能另有其人,此人则为最终执笔作者。撰文时用中宗的身份和口吻,则中宗为“身份作者”。议谥自始至终都遵循武后的旨意,则武后为“精神作者”。这些复杂因素的糅合,形成了《高宗谥议》的文本,同时也形成微妙的“作者”关系。在现存的唐代皇帝谥议文中,只有《高宗谥议》的署名(武后或中宗)如此“特殊”(其他都是文臣署名)白雪兵《唐代皇帝谥号制度研究》统计:“唐代皇帝谥议文撰者姓名或官职可考者共16篇,其中由太常卿或太常少卿等太常寺官员撰写的谥议文为11篇,占比为68.75%;由礼部侍郎撰写的谥议文为4篇,占比为25.0%;只有高宗的谥议文不是由太常寺或礼部官职(员)所撰,而是出自皇后武则天之手。”(白雪兵:《唐代皇帝谥号制度研究》,第17页。)案:武则天此时已为皇太后,不应称“皇后”,《高宗谥议》由武后亲自撰写的可能性不大。又“官职”疑为“官员”之误。,然则《高宗谥议》作为一篇议论文,其“精神”部分无疑是最重要的。其开篇称“窃闻星回日薄,悬象著明之谓‘天;龙跃凤翔,握镜乘时之谓‘圣”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第75页。,“悬象(日月)”“龙凤”皆有高宗和武后相提并论的隐喻,意在显示武后的突出地位和对《高宗谥议》的精神主导。参考高宗哀册文为武后所撰的记载,甚至也不排除武后亲自(或令人代笔)撰写《高宗谥议》的可能。因此将《高宗谥议》视为武后所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二、谥号的多源取义
《高宗谥议》为高宗所定的谥号也很独特,其结论部分称:
谨按:自然覆育曰“天”,明一合道曰“皇”,无所不包曰“大”。谨状上议曰:“天皇大帝”,庙称“高宗”。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第76页。“高宗”既为庙号,则“天皇大帝”就是谥号。但这里没有直接用“谥号曰”或“谥曰”,而是用“谨状上议曰”。“上议”是谓上报所议结果,亦即“闻奏”。可知这篇《高宗谥议》实为“闻奏稿”,至于是否为武后的最终确认定稿,或是否还有别的最终确认定稿,目前尚未见证据材料。从这段关于谥号的表述来看,其按语与后面的称号并不完全吻合。“谨按”以下是交代后面所定称号的取义根据和含义解释,但是只交代了“天”“皇”“大”三个字,既没有交代“帝”字,也没有涉及“高”“宗”或“高宗”。庙号问题暂置勿论,仅就“天皇大帝”这四个字而言,一般以为高宗的谥号只有“天皇大”三個字,“帝”即皇帝,没有交代的必要如白雪兵谓“其谥号应为‘天皇大,计三字。”(白雪兵:《唐代皇帝谥号制度研究》,第39页。)。虽然可备一说,但未免有些简单。
李唐诸帝的谥号,高宗之前,高祖李渊初谥“大武皇帝”,太宗李世民初谥“文皇帝”,咸亨五年(674)八月十五日分别追尊为“神尧皇帝”“文武圣皇帝”。此番追加谥号当然是武后的主意,她同时还给“今上”(高宗)加尊号曰“天皇”,给自己加尊号曰“天后”王溥:《唐会要》,卷1,第24页。,从而与“二圣”形成匹配,以显示自己与高宗“平起平坐”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可知“天皇”之称在高宗生前就已使用,高宗崩逝之后,官方文书往往将“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与“高宗天皇大帝”相提并论,或称“天皇大帝”“大帝”如武后《乾陵述圣记》云:“高祖神尧皇帝,晦电凝祯,流虹降祉……太宗文武圣皇帝,资灵宝纬,挺睿金英……(阙)高宗大帝焉。……(阙)大帝之怀紫翼锦鳞,与常有异。……大帝莫能自安……(太宗)令大帝总知军国……太宗命大帝承旨玉阶……太宗抚大帝颊而言曰……”(《全唐文》,卷97,《高宗武皇后(三)》,第1005页)又如《减大理丞废刑部狱制》云:“高祖神尧皇帝,披图汾水……太宗文武圣皇帝,负日月而膺运……高宗天皇大帝,云房诞睿。”(李昉:《文苑英华》,卷463,中华书局,1966年,第2361页)。大抵在武后那里,“天皇”“大帝”是作为两个整体概念使用的,既不是“天皇”修饰“大帝”,也是不是“天”“皇”“大”修饰“帝”。“天皇”意谓高宗比一般世俗皇帝更加高超神妙;“大帝”是说高宗比一般世俗皇帝更加广大无限;而“天皇”与“大帝”意义相近相通《说文解字》云:“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段玉裁注:“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92页。),可以互训为义,总归是要把高宗天神化,从而也间接地将自己(武后)天神化,隐然有超越太宗、高祖,乃至以往所有皇帝的“野心”。然则高宗谥号“天皇大帝”中的“天皇”,当是其生前尊号“天皇”的直接沿用,而“大帝”则为武后(或根据武后旨意)所加,故完整地说,高宗谥号应是“天皇大帝”四个字。《高宗谥议》“按语”不从“天皇”“大帝”两个称谓上加以解释,而是将“天”“皇”“大”拆分开来解释,并且忽略“帝”字,大约是为了贴合传统谥法的表述形式,如“一人无名曰‘神”“德象天地曰‘帝”“静民则法曰‘皇”“仁义所在曰‘王”黄怀信,张懋鎔,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27-630页。之类。另外可能还有用此公开的正式的官方“新”解释来替代和统一朝野上下的认识,消除人们对于“天皇”的误解和非议,同时也可以掩盖上述“野心”,赢得更广泛的接受和认同。
谥号特别是官谥的议定,一般是根据死者的德行事迹、参酌权威的谥法典籍(如上引《唐六典》注文所说的《周书谥法》《大戴礼谥法》,刘熙注《谥法》、张靖撰《谥法》《广谥》,以及沈约总集的《谥法》等)来进行综合审议评定,皇帝的谥号大抵亦当如此。《高宗谥议》的按语虽然采用了传统谥法的表述方式,但其所谓“自然覆育曰‘天”,却不见于传统的谥法典籍,应是武后所“新创”,然并非无据。《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卡:《老子》,卷2,中华书局,1993年,第101-103页。“人”“地”“天”“道(大)”“自然”都是道家学说的重要概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法”有“效法”(而生成自身)之义,反过来说就是自然生道,道生天,天生地,地生人。而“天下母”尤能显示“覆育”之义。《高宗谥议》谓“自然覆育曰‘天”,将“自然”与“天”结合起来,可见其与老子学说的渊缘关系。《礼记·中庸》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卷5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94-895页。《论语·阳货》曰:“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6页。则高宗谥号的“天”也吸取了儒家思想。
“皇”,《逸周书·谥法解》曰:“静民则法曰‘皇”,“静民”即“安民”黄怀信,张懋鎔,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6,第629页。。“静民则法”有“不扰匹夫匹妇”“虚无寥廓,与天地通灵”等义班固:《白虎通德论》,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页。。《高宗谥议》所谓“明一合道曰‘皇”,与此不尽相合。《管子·外言》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房玄龄注云:“一者,气质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随世立名者也,其实则一也。”管仲,房玄龄,刘绩:《管子》,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9-110页。《高宗谥议》之“明一合道曰‘皇”盖取义于此。《管子》的学说,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兼容并蓄,就这段文义而言,则更近于儒家。尤可注意的是,房玄龄为太宗朝名相,与高宗、武后都有过交集,《高宗谥议》的“皇”字取义于《管子》,或与房玄龄注《管子》的影响有关。
“大”,亦不见于传统谥法。《高宗谥议》所谓“无所不包曰‘大”,应主要取义于道家。上引《老子》“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已见其义。河上公注云:“不知其名,强曰大者,髙而无上,罗而无外,无不包容,故曰‘大也。”“其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复逝去,无常处所也。”“言远者,穷乎无穷,布气天地,无所不通也。”“远曰反,言其远不越绝,乃复在人身也。”王卡:《老子》,卷2,第102页。可见“大”不仅指“无不包容”,还有变化无形、无所不在、无所不通的含义。《尔雅注疏》云:“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闳、博、介、忳、夏、幙、?、赎、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以其数字皆训为大,故引之也。周公作诂,必以‘始也‘君也‘大也居先者,始者无先之称,君者至尊之号,大则无所不包,故先言之。一曰此三者天也、人也、地也。《易·乾卦》云:‘万物资始。《坤卦》云:‘直方大。《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故以此三者为先,乾坤相对之物,而以地在人后者,以人居天地之中,且尊尚人君,故进之。”郭璞,邢昺:《尔雅注疏》,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页。显然是兼取儒家和道家之所说。孔颖达释《周易》“大哉乾元”曰:“乾之四德(元亨利贞),无所不包。”王弼,魏康伯,孔颖达:《周易正义》,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6页。孔颖达为太宗朝大儒,所主持编修的《五经正义》,颁行于高宗永徽四年(653),作为官方定本,为全国学校和科举的“统编教材”,对武后的影响不言而喻。武后自撰《臣轨》曰:“夫道者,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注云:“言道之广大,无所不包。故上覆于天,下载于地,高而不可穷其际,深而不可测其原。”武后:《臣轨》卷上,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与《高宗謚议》的“无所不包曰‘大”的意义基本一致,此可为武后“精神”之一证。
以上所引述的文献材料,只是作为理解《高宗谥议》“天”“皇”“大”含义的主要参考,并不一定就是当初撰文时的具体依据。但由此不难看出,《高宗谥议》的谥号选字取义来源比较广泛,有对传统谥法的参用,有对经史诸子的酌取,也有自己的改造创新。而在酌取古代经典方面,主要是道家要素和儒家要素的糅合,前者的意味更加浓重;当然还有现实因素的考量,而这些都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武后的“精神”。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既没有援引佛家“诸天”“上帝”之类的义理,也没有附会道教“天皇大帝”之类的仙说,这反映出武后(及高宗)虽然平时颇好佛道,但在《高宗谥议》如此重要的官方文告中,并没有将其作为取义根据,当是出于政治考量的有意规避。二是《高宗谥议》关于“天”“皇”“大”的解释,大抵只是这种特定场合的一种官方辞令而已,未必就是武后内心的真实用意,也未必就是当时普遍认同的取义。即如《高宗谥议》开始说“悬象著明之谓‘天”“握镜乘时之谓‘圣”,就与篇末的“自然覆育曰‘天”并不一致。而从武后及朝廷的文书来看,更多采用“天皇”“大帝”的称谓。也就是说,在武后及时人的心目中,仍将高宗视为“天皇”或“大帝”或“天皇大帝”,而不是割裂孤立的“天”“皇”“大”,也不是三字合成的“天皇大”或神仙传说中的“天皇大帝”。
三、谥主的过度虚美
谥议文的主题和主体都在于表彰赞美谥主的德行功绩,《高宗谥议》也是如此。其开篇即称:“营窟橧巢之代,犹昧典章;如云类海之君,方崇号谥,所以阐扬功美,荣镜古今。”明确表示要“阐扬”高宗的“功美”,使其荣耀古今。随后称高宗:“以大圣而乘圣,克昌宝历之基;由至德而纂德,载广金图之运。对日之岁,穷象外之微言;弄田之辰,尽天下之能事。”可谓是天赋异禀,圣上加圣,德上加德,无以复加。此可视为总体评价,具体表现在九个方面,亦即所谓“九德”。因总评中已言及早年禀赋和德行,故“九德”从高宗为太子时说起,称其“恒侍禁中,问安之道斯极;长居膝下,候色之诚逾励。因心隆于爱敬,率性感于神明”,此为九德之一,即“先圣之孝德”。及至君临天下,称其为“追夏禹之焚甲,袭殷汤之解网。一物有违,则满堂兴虑;一夫弗获,则推沟寘怀”,此为九德之二,即“先圣之仁德”。在军国政事方面,称其“无幽不察,观六合于目前;无远不昭,视八纮于掌内。循机授政,则旁烛于九围;命将出师,则坐知其万里”,此为九德之三,即“先圣之明德”。在敬事祖先方面,称其“寅畏上元,肃雍清庙,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提衡均驭朽之危,履石同蹈冰之惧,虽处泰罔泰,休而勿休”,此为九德之四,即“先圣之恭德”。在日常自奉方面,称其“卑宫菲食,土簋茅檐,身好弋绨之衣,手无金玉之玩,翚裘必烬,袂安彻”,此为九德之五,即“先圣之廉德”。在文章制作方面,称其“荣河绿错,授宸鉴而生知;温洛丹清,澡璇襟于性与。汾水秋风之唱,仰天翰而扶轮;妫汭丛云之歌,钦睿词而拥篲”,此为九德之六,即“先圣之文德”。在内外关系方面,称其“驾狄攻“攻”字《唐大诏令集》阙。《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杨州大都督英贞武公李公之碑》云:“出车青徼,申谋绛宫;驾狄攻狄,驱戎伐戎。”李勣为太宗名将,高宗名相,此碑为“御制御书”,故据以酌补。(王昶《金石萃编》,卷59,中国书店,1985年,第6b页。)狄,无远而不怀;以戎伐戎,有征而必伏。提封所亘,拓地位于邹“邹”字《唐大诏令集》阙,据《全唐文》补。瀛;正朔所通,辟境踰于亥步”,此为九德之七,即“先圣之威德”。在道德修养方面,称其“损之又损“损之又损”,《唐大诏令集》注云:“阙四字”。《全唐文》,卷361,《卢重玄》之《〈冲虚至德真经〉序》云:“傥因此论以用心,去情智以归本,损之又损,为于无为,然后观《列子》之书,斯亦思过之半矣。”(第3666页)重玄即卢藏用之弟,(清)徐松《登科记考》,卷4,景龙三年(709)下列“抱器怀能科”及第人有“卢重玄”之名(董诰:《全唐文》,卷361,中华书局,1984年,第149页),姑据以酌补。,为于无为,事于无事。鸣銮访道,敬拜小童之言;修己就闲,载感大庭之梦”,此为九德之八,即“先圣之元德”。在人格的最终成就上,称其“体至道而调一气,舒卷阴阳;运冲和而契两仪,发挥风雨。将百灵以交际,与“与”字《唐大诏令集》阙,据《全唐文》补。万物而通诚。珍瑞普彰,休征毕应”,此为九德之九,即“先圣之神德”。总之这九德层层递进,不断扩展和升华,最后将高宗描绘成与“至道”“阴阳”“两仪”“百灵”“万物”同化如一、超越时空的全能之“神”。这些德行功绩应是参与议谥的群臣根据武后的授意“议”出来的,在取义上与上述关于谥号的解释基本一致,也是兼采经史诸子思想学说,但九德从“孝”“仁”说起,中间经过“明”“恭”“廉”“文”“威”,最后达到“玄”与“神”,这样的叙事显示出高宗是以儒家德行为根基,广泛吸取各家,最终归结于道家,似乎有意避开佛教和道教(仙家),这也应是武后“精神”的体现。
对“大行皇帝”歌功颂德、不吝赞美,既属人之常情、史之通例,也是丧葬文學的普遍现象。但像《高宗谥议》这样将所有美谥集于谥主一身而且无所不用其极的过度虚美,还是比较罕见的。《旧唐书·高宗本纪》总评说:“大帝往在藩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刘昫:《旧唐书》,卷5,第112页。除了登基前尚有可称道之处外,登基之后的所作所为乏善可陈,甚至遗患无穷,几乎可与亡国之君相提并论。《新唐书·高宗本纪》的指责尤为痛切:“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袵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中华书局,1975年,第79页。直接称高宗为“昏童”,痛斥其“毒流天下,贻祸邦家”。显然,这些切责都间接或直接地指向武后,也就是说,武后才是那个“毒流天下,贻祸邦家”的罪魁祸首。这当然都是从李唐政权的立场和视角而作的评价,但也是当时及后世较为普遍的看法和态度,如众所熟知的骆宾王“讨武瞾檄”所言:“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骆宾王撰,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这样的人心向背,武后当然会有更强烈的了解和感受。实际上,武后的越权干政,朝野上下的不满和抵制一直不断,至高宗崩逝前后,更是危机四伏,甚至酝酿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徐敬业起兵“讨武”)《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载:“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大帝崩,皇太子显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既将篡夺,是日自临朝称制。庚午,加授泽州刺史、韩王元嘉为太尉,豫州刺史、滕王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绛州刺史、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相州刺史、越王贞为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纪王慎为太子太保。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生变,故进加虚位,以安其心。……九月,大赦天下,改元为光宅。旗帜改从金色,饰以紫,画以杂文。改东都为神都,又改尚书省及诸司官名。初置右肃政御史台官员。故司空李勣孙柳州司马徐敬业伪称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刘昫:《旧唐书》,卷6,中华书局,1975年,第116-117页。)。《高宗谥议》如此过分地虚美高宗,应是武后对这种人心向背的一种反应,也可以说是一种策略,意在通过对高宗的高度评价和赞美,树立和维护高宗的神圣形象,最大可能地安抚和笼络人心;同时也间接地将自己神圣化,为其临朝称制提供合法性、合理性及合情性的支持,稳定和巩固统治地位,并为实现更大的野心做舆论准备。这可以从武后紧随《高宗谥议》之后发布的《改元光宅诏》中得到反映,其文云:“高宗天皇大帝,云房诞睿,虹渚降灵,受绿错之祯符,应朱绨之景命。飞车乘毳,臣轩、顼之不臣;没羽浮金,服禹、汤之未服。开边服远,更阐宇于先基;富贵宁人,重增辉于前烈。抚璇当宁,调五气于明堂;考瑞升中,朝百神于日观。茫茫众俗,宁知覆焘之恩?蠢蠢庶萌,孰辨陶甄之力?固已千年启旦,三圣重光,历选前书,无闻往载。”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3,中华书局,2008年,第15页。此时武后已直接称“朕”,以皇帝的身份和诏制的形式发布文告,态度口气果然不同,更加明确强调(虚美)高宗大帝的天赋、德行、功绩和恩惠超越以往所有帝王,对“茫茫众俗”不知“覆焘之恩”和“蠢蠢庶萌”的“不辨陶甄之力”非常不满,提出严厉质问。然则“茫茫众俗”“蠢蠢庶萌”的这种反应,正透露出武后对高宗的过度虚美亦即间接地美化自己,在当时遭到普遍的怀疑乃至反对,而越是这样武后越是要极端美化高宗及自身。
由以上简要的解读可知,《高宗谥议》的独特性是由当时诸多特定要素杂糅合造成的。在制度上,既要依循帝王议谥的礼法和通例,实际上又受到武后的操控;在名分上,既要照顾嗣君中宗的身份,又必须服从皇太后(武后)的旨意;在文本上,既有群臣和执笔者的参与,更有武后的最终确定;在文体上,既要符合传统谥法的体例,又要体现武后任性好奇的风格;在定号上,既要沿用高宗生前的尊号,又要考虑与武后的关联;在取义上,既要突出道家的主导倾向,又要体现儒家的根本地位,还要兼顾或规避其他思想学说。这些都与当时特定的国家权力结构、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朝野人心的向背等密切相关。《高宗谥议》的执笔者将如此复杂而微妙的要素糅合起来撰作成文,可谓煞费苦心,亦属“难能可贵”。由于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执笔者“糅合”起来难度很大,使得其文本呈现出某些不和谐,如作者题署的分歧、谥号字数的多少、按语的解释与其他表述的不一致等。这既是《高宗谥议》的难点,也是其他的特点,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皇帝谥议的普遍现象。
InterpretationofGaozongShiyiinTangDynasty
LiSiyu,ChenFei
(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
GaozongShiyiisaveryuniqueoneamongthearticlesoftheemperorsShiyioftheTangDynasty.TheShihao(thenameofdeadnobleman)oftheemperorsoftheTangDynasty,ismainlydiscussdandchoosedbytheofficialsofZhongshusheng,Menxiasheng,Shangshusheng,Yushitaiandotherdepartments,thentheyreportittothecourtforconfirmation.TheauthorofGaozongShiyiinvolvesmultiplerelationshipsincludingwriter,identityauthorandspiritualauthor.AlthoughitwasexpressedinGaozongstone,itactuallyreflectedWuhouswill.Thisarticlesinterpretationof“Tian”,“Huang”and“Da”iseitherbasedonoldexamples,classicsbeforeTangDynasty,orinnovations,whichisnotquitethesameasWuhouandtheofficialscustomarystatement.TheShihao“TianHuangDaDi”Shouldberegardedasacollectivetermfor“Tianhuang”and“Dadi”,thearticlesinterpretationofGaozongsShihao,andhighglorificationonhis“JiuDe”,ninevirtues,istheresultofcombinationofvariousideologicaltheories,whichprobablytakesConfucianismastherootandTaoismasdestination.ThereasonwhyWuhousanctifiesGaozong,liesinthespecificbackgroundofrealityandherpoliticalintentions.
Keywords:WuZetian;TangGaozong;TianHuangDaDi;highglorification[责任编校海林]
作者简介:李思语(1993—),女,河南驻马店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唐代丧葬制度与文学;陈飞(1957—),男,江苏睢宁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代文学制度的教学与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