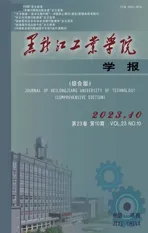音乐疗愈的心理机制研究
——以音乐诱发情绪为例
2023-04-23张苇杭
张苇杭
(澳门大学 社会学学院,澳门 999078)
一、音乐疗愈与音乐诱发情绪
作为艺术疗愈的一部分,音乐疗愈(music healing)与音乐治疗(music therapy)并不等同。治疗(therapy)仅包含使创伤消退的过程,疗愈(healing)一词则指使得个体的身心恢复完整的过程,它是使个体身心在治愈创伤的同时能恢复到更加完整的状态,从而达到治疗疾病乃至陶冶情操、提升身心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于音乐的作用包括疗愈功能早有记载。儒家经典文献《礼记·乐记》一方面阐明了音乐的本质在于“人心之感于物”,强调“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另一方面也突出了音乐的教化作用,“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而其中的“平好恶”,便带有了音乐疗愈的理念。《荀子·乐论》中也有相关记载,在荀子看来,音乐“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因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2]他说:“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2]强调音乐可以调节情绪、提升修养,从而改变人的内心。
叔本华认为,音乐这一形式在艺术中有特殊地位,因为其不依赖于“文字的阐述”,与其他艺术形式需要将认知功能具象到某个特定主题不同,音乐以其流畅的表达方式以及准确的信息传递,使得欣赏者可以跳过集中注意力的认知过程,从而诱发个体普遍的情绪体验。他说:“从一切美得来的享受,艺术所提供的安慰,使艺术家忘怀劳苦。”[3]由此,音乐通过强烈且直观的情感体验,最终可以实现疗愈的目的。符号论美学创始人苏珊·朗格认为:“作曲家不仅仅是表现,而是努力表达了微妙而复杂的情感,这些情感甚至不能用语言命名。”[4]情绪作为个体心境的重要外在体现,可以高度反映个体的心理状态与心境变化,情绪一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根据复杂程度分为基本情绪和复杂情绪,另一种则根据情绪的强度、速度、紧张度、持续性等指标分为三类——心境(Mood)、激情(Intense emotion)、应激(Stress)。而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会使用音乐进行交流、相互影响并且用其表达情绪(Zatorre,2001)。Juslin等人认为音乐诱发情绪主要是通过六种心理机制:音乐期待(Music expectancy)、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评级性条件反射(evaluative conditioning)、脑干反射(brain stem reflexes)、视觉意象(visual imagery)(Juslin,2003)。Koelsh等人通过fMRI确定情绪处理的神经相关因素,用愉快与不愉快的音乐片段作为实验材料唤起情绪从而证明了杏仁核、海马结构和腹侧纹状体可以被不同类型的音乐激活(Kolesch,2010)。那么音乐所诱发的情感是否可以具有疗愈作用?音乐是否可以作为一个高效的手段帮助个体的内在疗愈?这是需要论证及解决的问题。
二、音乐诱发情绪对于个体的调节及疗愈作用
1.音乐所诱发的情绪对个体起到调节作用
赵莉通过情绪诱发实验及Beck的负性认知图式,得出抑郁倾向大学生对于音乐诱发的悲伤情绪存在认知偏向[5];张婧通过音乐诱发积极以及消极情绪及AX-CPT修改范式,发现音乐诱发的积极情绪促进了认知控制灵活性的加工,并且降低了认知控制的灵活性[6];马夕汐通过研究发现,在音乐诱发了积极情绪的情况下,被试在握力测试中的表现高于控制组,同时个体在中度衰竭以下的情况下,积极情绪可以有效地缓解自我衰竭并加强自我控制[7];马晴则发现,音乐诱发的积极情绪对高三学生的认知执行功能存在促进作用,音乐诱发的负性情绪会阻碍学生认知信息刷新的能力[8]。以上研究可以证明,音乐诱发情绪对个体的认知水平与认知功能产生影响,进而产生对个体的调节,这种调节不一定是正向的。例如抑郁症倾向的个体在听到有负向情绪引导的乐曲时,会产生更强烈的抑郁情结,节奏较快或声音较大的音乐也会占据认知资源从而使个体认知能力下降,进而引发焦虑、愤怒等负向情绪,最终导致降低认知任务(如Stroop测试)的表现,因而正确使用音乐诱发情绪的调节作用,是将音乐作为有效疗愈手段的前提。
另外,也可以通过实验证实,音乐还可以通过影响大脑的枕叶皮层从而控制人的情绪。Hou等人(2019)通过价值—转换图表将音乐分为四组:“平静”“悲伤”“欢乐“愤怒”,听到“悲伤”的音乐时,枕叶区域的α波段表现出更大的活动范围;听到“欢乐”的音乐时,枕叶皮层的θ和α波段能量较高,额叶的β波段能量较高;当被试听到“安静”或“愤怒”的音乐时,额叶的各波段能量增高。在被试聆听喜欢的音乐时,额区的θ波段能量增加,聆听不喜欢的音乐时,额区β波段能量增加(Balasubramanian et al,2018)。而诱发α波段的脑波可以有效缓解负面的情绪并使被试感到愉悦与放松(卢英俊,2012)。可见,从神经活动层面也可以证明音乐能通过影响大脑活动来诱发情绪。
2.音乐诱发的积极情绪对个体产生疗愈功能
音乐对于个体生理方面的治愈能力被定义为音乐治疗(Music Therapy),我国对于音乐治疗学的定义是:“是研究音乐对于人体机能的作用,以及如何运用音乐治疗疾病的学科。属于应用音乐心理学范畴。”[9]Bonny(1986)认为音乐治疗是在音乐治疗师的指导下,系统地运用音乐来改变患者的情绪和/或身体健康。因此,“它强调音乐的功能,而非它的美学价值”,而音乐的美学价值则可以激发人类的情绪并让人类与乐曲旋律产生高度共鸣,从而通过情绪来从精神层面治愈并一定程度上强化个体,从美学角度出发治愈并强化个体精神的过程则被认为是音乐疗愈(Music Healing)。
情绪对于个体的疗愈作用早有研究。Kathleen早于1986年就提出积极情绪可以增强个体免疫力,这主要体现在唾液免疫球蛋白A(Salivary immunoglobulin A,lgA)的水平在观看幽默录像后相比于观看说教录像后显著提高。Fosha(2009)认为情绪是心理治疗的核心,并在包括二元关系、身体调节、创伤、分离、社会参与等个体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Susan M.(1998)研究发现以情感为中心的婚姻疗法可以促进婚姻关系中的积极情绪产生,从而以相对稳定的方式治愈双方的心理创伤。
三、音乐诱发情绪对于个体疗愈作用的机制
目前研究中,音乐诱发情绪的机制主要学说是Juslin(2008)的心理机制学说,该学说认为人的情绪由音乐通过六种心理机制——脑干反射、评价性条件反射、情绪感染、视觉意象、情景记忆、音乐期待产生,但鲜有研究者探究音乐所诱发的情绪是否具备疗愈作用以及产生疗愈作用的机制是什么。下文将探讨两个理论模型并且指出其作为作用机制的合理性。
1.扩展——构建模型(broaden-build theory)
扩展——构建模型由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Fredrickson)于2004年提出,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如幸福、期待、快乐)拓宽了一个人的意识,并且鼓励新颖的、探索性的思想与行动,芭芭拉认为这些积极的情感拓宽了一个人的思想——行动库(thought-action repertoire),例如,快乐会激发游玩的冲动,兴趣会激发探索的冲动,满足则激发品味与整合身边事物的冲动,爱激发了这些冲动在安全、亲密关系中的循环往复。对于音乐诱发的情感,其在生理表现上与通过其他途径诱发的情感没有明显差别,因此音乐所激发的积极情绪对于个体的认知与行为的可能性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提高,这是符合拓展——构建效应的,具体表现为音乐诱发的积极情绪会为个体提供额外的心理资源以进行认知加工。
拓展——构建理论同样拥有其进化心理学的意义,即积极情绪虽然无法直接增加个体的生存率,但是通过积极情绪拓展得到的资源会长久地存在并且通过这些资源,个体将得以拥有更高的存活几率,例如对于风景的好奇会促成地理知识或航海知识的增加,陌生人间愉快的交谈会形成一段长久而相互扶持的友谊,兴奋的体育竞技使得个体拥有强健的体魄(Brown,2006),等等。这些获得的资源——根据弗雷德里克森(2001)的说法——是长效而可以积累的,并且将积极情绪带来的行为扩大的技能会随着时间增强,这将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个体因得到资源而提高幸福感,产生积极情绪,积极情绪又将拓展个体的行为与思想从而促进个体获得更多资源。
音乐疗愈中同样可以适用该模型,研究表明音乐所诱发的情感相比于其他艺术形式更加剧烈,与个体当前的情绪状态有很高的一致性(Stefan,2005),根据此研究的另一项fMRI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指出除了海马体外,在音乐刺激呈现期间,颞极(temporal poles)、杏仁核(amygdala)等大脑区域以及Rolandic鳃盖(Rolandic opercular)、前上岛叶(anterior superior insula)以及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形成的运动回路的激活均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使得个体不断并且越来越快地拓展自己的行为,这与弗雷德里克森的研究结果相呼应,并且证明了拓展——构建模型在音乐激发情绪的疗愈作用中从生理层面上存在。
2.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Emotions as Social Information Theory)
传统的社会影响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劝说、妥协、服从和认同,Van Kleef(2009)在达尔文功能性情绪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关于情绪与社会功能的思考,并指出情绪是人际交往中社会影响的主要来源。该模型区分了情绪发挥社会影响功能的两条途径:情绪反应路径和认知推断路径,前者是情绪的输出过程,即个体向外界输出自身情绪以及情绪所联结的行为,例如,一个人生气时会声色俱厉地说话、开心时会发出笑声等等;后者则是根据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并推断的过程,是根据环境输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者会根据自己的情绪提取关于情绪表达者的情感、态度、倾向以及行为意图的信息,之后观察者会加工信息并完成推理过程,继而影响观察者的行为。在Van Kleef的理论中,情绪不仅是作为个体心境的外在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交互过程中的重要信息,即个体通过感知他人情绪而接受关于周围环境的信息,进而产生对于外界的反应。
基于以上过程,情绪可以切实地改变个体对于外界的认识。产生积极情绪的音乐也可能通过该过程影响个体对于外界的归因,从而使个体拥有更加积极的心境面对外界。
在刘小禹的文章中提到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中包含情绪感染理论(Emotional contag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情绪可以从一个个体传染到另一个个体,音乐对于个体的情绪唤醒可以作为传递情绪的作用,同时音乐唤起的情感与个体的情感状态又具有高度一致性(张婧,2014),因此音乐可以有效地唤起情绪。积极的情绪会使个体对于周围环境产生正面的归因与认知,从而对环境表现出友好,进而形成正向情绪的正反馈循环,从而达到疗愈的目的。
音乐的疗愈作用在20世纪早期就有记录,当时埃文·奥尼尔·凯恩(Evan O′Neil Kane)在JAMA上发表了他关于在手术室内使用留声机的报告。其后的第二年,WP Burdick在美国麻醉和镇痛年鉴中发表了对该实验更详细的描述,他回忆道:“凯恩医生在康复病房看到留声机的有益效果后,将其搬进了手术室,发现几乎所有患者都能更好地耐受麻醉诱导,并且在经历“恐怖的手术”之前也减少了焦虑(Conrad,2010)。一些临床研究也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音乐疗法可以作为治疗抑郁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的替代疗法(Lin et al,2011)。
音乐可以有效地诱发多种情绪,既可以作为未来的研究角度进一步探究音乐疗愈激发情绪后的神经活动与大脑变化,也可以作为情绪疗愈的一种方式,即通过音乐来诱发情绪,从而通过情绪对多种心理疾病进行治疗。但音乐中仍有许多变量,如听音乐的姿势、音乐的节奏、不同个体的人格以及对于某种音乐的个人喜好,“这些变量是多样的,人们对音乐的品味是多样的,习惯性地听曲姿势与音乐刺激对身体、思想和精神的最终影响有很大关系”[10](Bonny,1986)。本文通过举出音乐所诱发的情绪对于个体的多种影响以及对于多项神经科学领域的总数,论证了音乐诱发情绪的过程是音乐疗愈的内在机制之一,该内在机制可以用于未来对于音乐与个体心理改变的影响以及音乐对于个体的疗愈作用,即是否可以存在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模拟音乐来诱发情绪,从而达到更高效的疗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