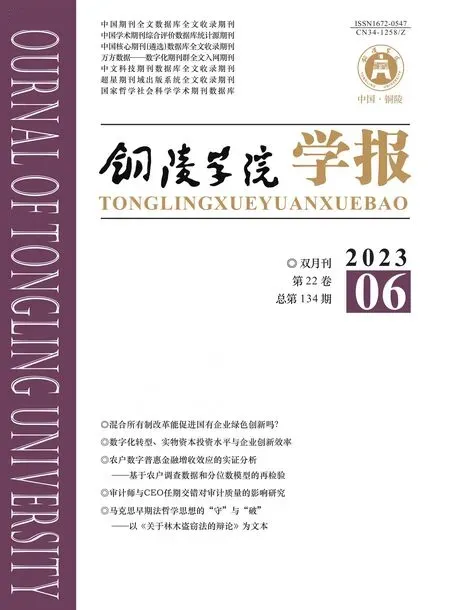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守”与“破”
——以《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为文本
2023-04-19蔡佳钰赵悦悦
蔡佳钰 赵悦悦
(1.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0;2.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莱茵报》时期,普鲁士政府专制腐败,德国城邦林立,国家四分五裂。 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等级分化严重,贵族阶级腐败贪婪。 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意图塑造的“理性国家”与实际的现实状况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反差。 受到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影响的马克思面对“理性国家”为何沦为维护私人利益工具、 贵族的特殊习惯为何能成为国家认可的习惯法、 贫民的习惯法为何不能成为国家认可的普遍法等问题,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莱茵报》后期的重要著作,也是马克思法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里充满了关于自由主义、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重要的法哲学思想,也是马克思第一次对“物质利益”发表看法,这被看作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重要转折点, 为马克思后面法学思想的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对《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法哲学思想的再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早期法学思想的演变过程:马克思既有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继承, 也有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突破。
一、国内研究情况
马克思的早期法哲学思想是马克思法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从80 年代开始就对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展开了丰富的研究。 第一,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相关研究:俞吾金通过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 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马克思影响重大[1];刘俊祥认为马克思政治思想起源于对黑格尔政治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并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关于政治国家的思想[2]。 此类研究大多关注马克思从黑格尔那继承了什么、批判了什么为主、内容多样,且不仅仅局限于法哲学思想。 第二,从刑法学角度对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研究:李希慧等学者从对《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本考察,分析了文本中蕴含的刑事立法、犯罪客体与犯罪构成、刑罚的基本问题等思想[3];章辉对马克思法学思想中蕴含的刑法学思想进行了分析, 并认为可以从本质上认识剥削阶级刑法的反动性[4]。 此类研究探讨了法哲学思想中的刑法思想,但未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刑法思想的继承性和突破性进行研究。 第三,对马克思法哲学中某一具体思想的分析:龚廷泰、吕波对马克思的新理性自由法思想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新理性自由法思想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和主要内容等问题[5];林进平则收集整理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在莱茵报时期的文章,并对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进行了探究[6]。 此类研究虽内容具体且解读清晰, 但是其思想内容较窄,不能全方面展现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 第四,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的研究:陈学明梳理了马克思进入大学到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法哲学思想发展历程,并对其早期法哲学思想中人民主权、理性法、自由法等思想进行了研究和探讨[7];马东景对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的理论背景、历史演进、思想主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分析[8]。 此类研究重点分析了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继承和突破并没有进行分类总结。
综上所述,以上学者们运用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的早期法哲学思想、 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继承与延续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本文以《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为文本,具体考察并详细论述马克思在文本中的法哲学思想,通过重点分析和分类,讨论并总结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继承与突破, 为读者清晰展现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转变的发展脉络。
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文本分析
19 世纪初, 莱茵省在普鲁士专制的统治下,广大人民生活极端艰苦,不得不依靠拾捡枯枝、采摘野果维持生计。 但是贫苦农民的这种谋生手段却被认为违反了法律。 仅1836 这一年,因擅自砍伐和盗窃林木的案件就高达15 万件。 面对这种情况,“莱茵省议会经多年沉寂后于1841 年5 月23 日至7月25 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 会间就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案在内的多项法案进行了辩论”[9]。马克思就是在此背景下创作出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在文中,马克思探讨了国家和法的本质,分析了关于贵族利益与贫民利益的关系。 他用辛辣尖讽的语言抨击莱茵省省议会的行政官员,指责官员们利用国家作为工具为林木占有者谋取利益,使国家沦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 此时,马克思对国家和法的探讨虽遵循了黑格尔理性国家的思想,但却也能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为贫苦大众发声,对普鲁士特权阶级进行抨击。 文章闪耀着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光芒,且在对于物质和联系的看法中彰显了其唯物主义思想,这显然是对黑格尔理性法哲学思想的突破与发展。
(一)基于国家和法的本质探究
第一,质疑林木盗窃法立法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强调立法权基于国家制度产生,是国家权力的体现,而省议会却越权,竟“以第二立法者的资格与国家立法者并肩行事”[10]。在马克思看来,立法权是国家最根本的权力,省议会只是政府机关,没有任何权力取代国家行使立法权。 马克思直接提出司法程序不公正使得私人利益践踏法律程序、破坏司法公正。 马克思此时质疑:难道国家不应该是“绝对精神”,代表普遍利益以及最高自由的表达吗?
第二,质疑盗窃罪的认定问题。 针对贫民捡枯枝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森林法这一问题, 贵族没有从犯罪的客观要件来讨论拾捡枯枝的行为是否触犯刑法。 贵族代表认为,如果不把拾捡枯枝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的话, 那么拾捡枯枝的行为就会经常发生。 显然,贵族阶级为了追求特权、保护自己利益而置贫民利益于不顾。 马克思讽刺道“这种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的做法……必然会把许多不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10]。在文中,马克思对“拾捡枯枝”和“盗窃林木”行为作了具体区分。 马克思认为,林木是活的机体,砍倒林木就是要把林木暴力砍断、使林木分解,这样盗窃林木才是伤害了林木所有者权益的行为。 然而,捡枯枝同盗窃林木在本质上存在不同, 由于枯枝已经从林木机体上脱离,已不属于林木本身,此时林木占有者也就不再占有从林木上落下的树枝。 法要合乎事物的本质规律,违背事物本质规律的法就是“不法”。 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10]。
第三,讨论“贵族的习惯法”和“贫民的习惯法”问题。 黑格尔理性法学强调国家是特殊利益和普遍的利益的统一,国家制定法律,是要给权利活动以肯定的范围,而不是限制权利的范围。 “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处理私权方面, 只限于把已有的权利固定起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而在没有这些权利的地方,它们也不去制定这些权利”[10]。贫民拾捡枯枝、采集野果,是自然对他们的馈赠,已成为他们维持生计和生活的一部分。 贵族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损害贫民的习惯,就像动物世界里的野兽利用弱肉强食去欺压弱小,这就是动物的兽性。
第四,阐述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黑格尔把国家认定为一个活的有机整体,人民是国家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强调“国家应该把森林条例违反者看做一个人, 一个和它心血相通的活的肢体,……而最主要的是应该把他看做国家的一个公民”[10]。 此处可以看出,马克思是认可黑格尔的。 人民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每个人都与国家息息相关。 然而,在现实的利益冲突中,省议会的代表只看到了私人利益,看不到贫困农民的利益, 这使黑格尔在理念中构筑的理性国家受到极大的冲击。
(二)基于利益关系问题的讨论
尽管贫民已经穷困潦倒, 可是莱茵省议会的各阶层还是极力偏袒林木占有者的利益, 对贫民利益视而不见。 马克思此时已经看到利益关系对国家和法的影响,他提出“在问题涉及森林条例违反者的利益时,它抹杀这些行为之间的差别,认为这些差别并不决定行为的性质。 但是当问题一旦涉及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时,省议会就承认这些差别了”[10]。
第一, 面对省议会提出的对盗窃林木行为的处罚,马克思提出应依据事物价值来判断惩罚的标准。马克思认为“犯法的一定内容就是一定罪行的界限。因而衡量这一内容的尺度也就是衡量罪行的尺度。对于财产来说,这样的尺度就是它的价值”[10]。事物的本质能够为判断提供客观的标准, 对犯罪行为定罪处罚也要有客观的标准。 在给盗窃林木的违法者以处罚时,应以事物的价值作为一种衡量标准。 然而,省议会代表态度“轻率”,还提出了“特殊补偿”。 对“价值”问题置若罔闻,对他们有利的就是合法的,对他们不利的就是有害的,只有“利益”是他们的衡量标准。
第二,针对林木看守者的监督,马克思认为这是对林木占有者利益的维护,对贫民利益的损害。 贵族代表认为“监督”可以使林木看守人忠诚,使林木看守人可得到林木占有者的信任。马克思却认为给予林木看守人以监督,实际上就是让林木看守人更加坚定地站在林木占有者的立场,维护林木占有者利益。可是,谁来维护贫民的利益?连代表正义的法和理性国家都是利益的工具,成为贵族阶级的奴仆。“使国家的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觊觎、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10]。
第三,针对林木占有者提出的“特别补偿”,马克思给予严厉的抨击和讽刺。 委员会首先提出,要传讯看守人就得让贫困的农民另外再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这实际上是剥夺了贫民与看守人对质的机会。 贵族代表提议,除了罚款外,还应给林木占有者以补偿,那么林木占有者得到的可能“就是4 倍、6 倍以至8 倍的罚款, 最后是损失的特别补偿”[10],这就是林木占有者获得的“额外价值”。 林木盗窃者变成了林木占有者获得收益的渠道,“罪行变成了彩票”成为林木占有者的纯利润,罚款没有归于国库却落入私人的腰包。
此时, 马克思虽还不具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也没有认识到经济关系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当时正值青年的他在思想上已经有了重大转变。
三、马克思“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思想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守”
虽然《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莱茵报》期间后期作品,然而整个《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在国家和法理论上都是赞同黑格尔国家理论和理性法思想的。 也正是因为遵循着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 马克思才会对现实的利益问题产生苦恼和困惑,督促着他自己继续深入研究。
(一)理性是国家和法的本质
首先, 马克思对国家和法的定义与黑格尔是一致的。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从法的本体论出发,认为意志是法的起源,他指出“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 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 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11]。同样,马克思在《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都有过“法是理性自由”的表达。 他还主张,出版物是人类精神的特权,赞扬书报出版法是真正的善法,抨击书报检查令是对意志自由的惩罚。 他强调“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肯定的善”[10]。因此, 马克思认为, 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和天性,是人与其他物种最根本的不同。 法起源于人的主观意志,国家没有权力剥夺人的自由,不论是活动自由还是精神自由。 出版法是精神自由的外化表现,因此对出版物的限制就是对精神自由的剥夺, 就是对法的否定。
黑格尔认为国家是 “伦理理念的现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实体”[11]。 他指出“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 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11]。 因此,黑格尔构建的理性国家,是在理念中自为地发展的国家,具有自由、独立和永恒存在的特性,具有与神一般的光芒色彩。 马克思坚守着这种国家理念, 坚定地站在理性的立场审视现实问题。 所以,当他面对普鲁士政府对出版自由的限制、对贫民利益的无视、对贵族利益的维护的现实状况下,马克思曾坚守的理性从哲学的高度降为现实斗争的武器并为其所用。 随后,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以及维护自由报刊的思想取向也都脱胎于此[12]。
其次,国家和法遵循的普遍性原则是一致的。 黑格尔强调国家是作为一个有机体存在的, 是建立在普遍性原则之上,并认为“政治制度是国家组织和国家内部关系的有机生命过程”[11]。 马克思也同样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有机机构, 个体和有差别的等级具有特殊性,不能代表普遍利益,只有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才具有理性。 所以,马克思强调“国家不但有把事情办得符合于自己的理性、 普遍性和尊严的手段, ……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拥有这些手段并加以运用”[10]。 林木占有者的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等级特权的维护,均代表着特殊性。 而这正是私有利益对国家普遍性的否定,是对理性国家权力的损害。 因此, 马克思将个人贪欲与国家之间的斗争看作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13]。
(二)自由是理性国家的现实表现
首先,自由思想一直贯穿马克思法学思想的始终。黑格尔认为,自由存在于意志当中,自由首先是精神的自由。 他认为“说到自由,和意志也是一样,因为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 意志而没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11]。 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中洋溢着关于自由主义的法学思想。 马克思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写作和阅读,出版物是个人精神最本质的存在方式,“书报检查制度”是对人类精神自由的限制和剥夺。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虽未用具体的语言涉及自由问题, 但是他内在的驱动力——自由主义思想, 驱使他审视这个现实世界,让他认识到现实的世界与理念构筑的世界截然相反。 马克思让自由思想反观现实,通过考察农民贫困的生活,认为农民贫困并不是因自然等其他因素造成,而是由于政府一味维护贵族阶级利益的腐败等原因造成。
其次,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进一步意识到“客观关系”对国家和法的影响。 他认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略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10]。因此,当他发现普鲁士政府不论是面对“拾捡枯枝的贫民”还是“穷苦的葡萄酒酿造者”,普鲁士政府都成为了“近视患者”,选择对人民的贫困视而不见。 立足于法的本体论,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是抽象的、脱离于现实的自由。 当马克思依据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将抽象的自由与现实的自由统一起来去思考现实问题时,他认为,既然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国家是绝对理性、伦理理念的化身,那么国家就应该化身理性和正义, 担负起实现单个人的特殊利益和民众的普遍利益的职责, 这显然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三)刑罚是对法的恢复
首先,马克思坚持罪行应与刑罚相均衡。 上面已经分析过, 马克思否定那些不加区分的将 “拾捡枯枝”的行为与林木盗窃罪混为一谈,这是对罪与非罪的界定,并且提出“衡量罪行的尺度”是财产的价值判断,也即对刑罚尺度的界定。 黑格尔的“刑罚报复主义”认为“犯罪的扬弃是报复”,“犯罪具有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11]。 可见, 马克思此时是遵循黑格尔“刑罚报复主义”思想。 在质的方面,要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的客观要件;在量的方面,对于罪行的处罚,要与犯罪行为相均衡,这个判断标准就是物的“价值”。 此处的“价值”,并不具有政治经济学里的“一般等价物”的抽象概念,只具有衡量财物的尺度意义。
其次,马克思强调刑罚权属于国家司法权,是国家运用法律对犯罪的惩罚,专属于国家。 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司法权是国家行政权中的一部分,国家具有独立审判权。 国家权力高于个人,私人无法染指国家司法权力。 马克思用“公众惩罚”来确定国家权力,强调国家权力不能转让给私人。 “国家对犯人的任何权利,同时也就是犯人对国家的权利。 任何中间环节的插入都不能将犯人对国家的关系变成对私人的关系, 惩罚却由公众的惩罚变成对私人的金钱赔偿了”[10]。 文中的“公众惩罚”旨在强调国家的理性和普遍性,以国家身份惩罚犯罪。
再次,马克思提出“惩罚本身作为法的恢复”与黑格尔认为刑罚是对不法的否定的思想是一致的。按照黑格尔的刑罚理念逻辑, 刑罚是对法的否定之否定,也即“恢复法的原状”。 因此,黑格尔认为“刑罚是自在自为的正义”,是以恢复法的原状来实现理性和正义。 然而,省议会官员却让惩罚变成了罪行,把没有罪行的地方变成了有罪行。 人民看到的是惩罚,看不到自己的罪行,这就是把法变成了“不法”。 如果法成为不法,那么刑罚如何让法恢复原状,又如何代表正义和理性。 因此,普鲁士专制政府恣意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制定的“恶法”,不仅仅会使惩罚毫无效果,……同时也就消灭了法本身[3]。
由此可见, 马克思关于犯罪与惩罚的思想同样是遵循黑格尔的罪与非罪要有界限、 罪行与刑罚相均衡以及国家专属司法权的思想。 虽然马克思对“国家为何维护私人利益”没有较为成熟的思考,但文中的质疑和尖锐的抨击却为马克思发现国家和法的本质奠定了基础。
四、马克思“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思想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破”
(一)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
黑格尔所在的国家观虽然承认人民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但是他又贬低人民,认为人民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 将人民与国家对立起来。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观极具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使他无法看到人民的利益高于国家, 无法形成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思想。 马克思在考察现实社会时,体会到了农民的疾苦,突破了黑格尔的国家思想,认为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高于国家。 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 中, 马克思提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10];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强调刑罚应是“公众惩罚”;在《论离婚法草案》中,他强调优秀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10]。 马克思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认为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人民的意志才能代表国家的普遍意志。 “马克思把法的合理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则正是为了论证人民的国家和人民的法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7]。 可见,马克思在此时已初露人民主权的思想,不再局限于“德国庸人”的俗气。
(二)“法”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马克思高度赞扬出版法对思想自由的肯定, 反对书报检查法对思想的禁锢和限制;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他痛斥普鲁士政府“毫无心肝”,对私人利益极力偏袒;他肯定“贫民的习惯法”,认为贫民是代表人民的普遍意志,否定“贵族的习惯法”,认为贵族是代表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他认定国家和罪犯的关系不能因私人的身份而改变,这是国家的责任和精神;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他站在穷苦葡萄酒酿造者的立场,讽刺普鲁士政府对人民的贫困 “保持怀疑” 并推卸责任。 他句句讽刺,尖锐批判,发起对贵族和贫民等级严重分化的抗议。
什么是公平正义? 在黑格尔所设计的立法权里,有三个等级包括贵族地主等级、 普遍等级以及私人等级。 这些等级包含贵族地主、行政官员、工商业代表,却唯独没有工农劳动群众。 相反,马克思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深刻地批判现实社会,无情地揭露普鲁士政府的腐败。 马克思要求国家能够平等对待每一位公民,取消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划分;要求国家能够维护人民的普遍利益, 处理国家问题时能够一视同仁, 体现人民的普遍意志; 要求法合乎理性,司法机关能够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要求判案,审判结果公正廉洁。 也正是由于马克思看到了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局限性和矛盾, 才有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批判。
(三)物质利益制约国家和法
马克思一直恪守着理性国家的思想, 认为国家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有机整体。 然而,基于对现实问题的考量让马克思看到了普鲁士政府的腐败与无能。马克思发现,法不是绝对自由意志,而是受制于客观的现实关系。 马克思在看到普鲁士政府极力维护林木占有者利益时, 这些利益的问题不断冲击着他所坚持的理性法思想。 “黑格尔式的‘国家和法’同物质利益关系的理论应然与资本主义世俗世界中 ‘国家和法’同物质利益关系的实然之间的分裂,引起了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论求索”[14]。此刻,马克思并不清楚这种客观现实关系就是经济关系。 由于没有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 他还没有看到国家和法背后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但是物质利益已经让国家和法沦为了私人利益的奴隶。 “政府当局本身存在的以及政府当局同特权等级勾结谋利的制度性腐朽关系”[12], 这使马克思坚守的国家理论和理性法思想逐渐向意识与现实相统一的唯物主义法学思想转变,并促使他更进一步探究社会存在的各种关系对国家和法的意义。
五、《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在马克思法学思想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法学思想史上最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 文中的经典论断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虽然文中关于国家和法的本质、利益关系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罪与罚相适应、刑罚是对法的恢复等问题的讨论, 还存在唯心主义法哲学思想的局限性, 但这些讨论却给读者清晰地展现了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本质和特征。
马克思在面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纷繁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时,他始终没有回避,而是直面问题本质。 通过对现实问题本身的考察和批判,他自觉地接受了自己坚守的“理性国家观”的缺陷,并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发出了直接抨击和挑战。 也正是由于遇到“物质利益”的难题,引发了马克思对国家和法进一步思考, 并清晰地意识到客观关系对法的本质、法的内容的决定作用。 总而言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端。 正因如此,马克思“退回书房”,在克罗茨纳赫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