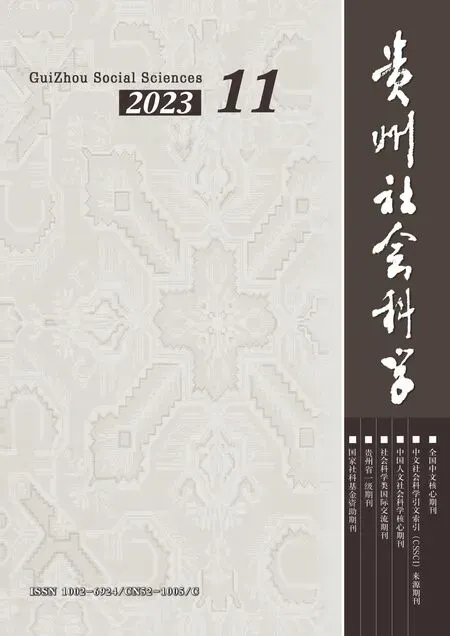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历史逻辑
——列斐伏尔《论国家》第二卷研究
2023-04-17张一兵
张一兵
(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3)
在《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后,时隔两年,列斐伏尔写下了四卷本的《论国家》(1976—1978)。①在这里,我们主要集聚于列斐伏尔在《论国家》第二卷中对研究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历史性回溯,进行一些初步的梳理。
一、现实抽象与异化:研究国家问题的方法论思考
在《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后,列斐伏尔为什么会突然想到研究国家问题?依我的推测,这应该是空间生产在更大尺度上的必然延伸,他自己用中文的拼音“Guo-Jia”构境来表示更大空间中的“国—家庭”,②并且,这个大的国—家正在走向征服全球的世界化空间。这是他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直接干预的思考,这也生成了所谓国家生产方式的全新概念。在这里,我们主要集聚于列斐伏尔在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对国家理论的历史性回溯和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前进式探讨。
1975年,列斐伏尔发表了这四卷书的写作提纲《现代世界的国家》,③明确提出他将研究和思考的对象并不是一般的国家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及其最新发展。我觉得,这一提纲完整呈现了此时他头脑里构想的写作计划。在这份写作提纲中,此书的第一卷为《论国家:现代世界中的国家》,列斐伏尔从国家体系和问题式(problématique)入手,将分别对民族与国家(L'Etat et la Nation)、国家的全球布展(l'extension planétaire)、国家的世界体系(le système mondial)、来自各国的报告、现代国家与经济增长(croissance économique)和国家与社会生产剩余的提取(le prélèvement du surproduit social)等问题进行讨论。可以看出,这一卷正是触动列斐伏尔思考神经的焦点,即当下资本主义世界中越来越突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问题,这应该是他在《资本主义的幸存》和《空间的生产》二书写作中逐步形成的新认识,即如果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空间生产获得了苟生,那么这种空间生产的显著特征,则是以国家生产方式的形式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扩展到全世界。显然,这里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卷为《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列斐伏尔将从现代国家问题式历史生成的回顾开始,首先辨识现代国家的概念和他眼中的研究方法,然后再分别讨论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经典表述及后来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线索。列斐伏尔这一卷的目的,显然试图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方法论路径,以及标示他自己在这一思考线索上的独特视角。第三卷为《论国家:国家生产方式》,在这一卷中,列斐伏尔将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入手,分别讨论现代国家的基础(Les fondements de l'Etat moderne)、国家的物质交换(L'échange matériel)、国家的具体抽象(abstraction concrète)、国家的积累过程(processus cumulatif)、作为国家装置中政治职业的分工(La division du travail politique)、增长与发展(Croissance et développement)、现代国家的扩张(Extension mondiale de l'Etat)、国家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L'Etat et 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sociaux) de production]等问题。这一卷展现了列斐伏尔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基本看法,这包括了马克思原先已经讨论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物质生产与市场交换、分工与资本积累,以及经济增长与扩张等方面的问题,只是将其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来,当然,其中的核心还是在今天资产阶级国家层面上那个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第四卷为《论国家:现代国家的矛盾——国家的辩证法》,列斐伏尔站在战略与逻辑(Logique et stratégie)的高度,将分别讨论现代国家在减少冲突(réducteur des conflits)中的作用、现代国家自身存在的基始问题和本质性矛盾(Le premier problème et la contradiction essentielle)、大写的知识与权力(Le Savoir et te Poutroir)、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L'Etat-nation pris entre les différences)、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Valeur d'échange et valeur d'usage)和国家与空间(L'Etat et l'espace)等问题。这一卷中,列斐伏尔的思考重点已经转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具体矛盾上来,这包括了他所关心的知识与权力的同谋性关系、空间的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取代等问题,并将这种思考与自己的空间生产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列斐伏尔完成和正式出版的四卷《论国家》,基本上实现了他自己原初制定的这一计划。在这里,我们先来看列斐伏尔自己设定的研究现代国家问题的方法论,然后着重分析作为列斐伏尔国家问题基础的黑格尔—马克思的国家观,最后集中于列斐伏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创性的观点——国家生产方式问题中的一些具体分析。
列斐伏尔认为,在今天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问题的思考上应该有这样一些大的原则:一是“分析应该尽量被确定在一个全球的水平(niveau planétaire)上”。④这是他目前最关心的方面。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土地,而是更大范围中的世界性空间生产。这是一个不断世界化(mondialisation)的进程。Mondialisation(世界化)这一概念,是列斐伏尔经由阿克塞洛斯⑤获取的海德格尔的观念。⑥二是要细微地看到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空间生产中那种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层级形态学”(morphologie hiéarchique stratifiée),即从个人生活的家庭空间到社会关系场境的群体活动空间,再到国与国之间的作用关系,这是一个从日常生活批判到全球层面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链接。三是关注不同层级空间之间的转换,比如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空间关系生产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的转换,民族国家向世界等级的突变(有如美国成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资本跨国公司对世界的征服等。四是观察不同层级空间的历史缘起、平衡发展和突变状况。这会是一个历史认识论的视角。⑦这是列斐伏尔希望强调的一般理论原则。然而更加重要的方面,必然是国家问题研究中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这些方法主要表现为:
首先,在现代国家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上,列斐伏尔明确主张坚持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的抽象法。这是一个很高的方法论台阶。依列斐伏尔的看法,抽象是概念的本质,相对于现实的存在来说,“抽象(l'abstraction)就是分隔、扼杀、解剖”。⑧这是一个很哲学的说法。为此,他还引用斯宾诺莎“狗的概念不会叫”(Le concept de chien n'aboie pas)的例子,因为从实际存在的狗到“狗”的概念,已经分隔和扼杀了会叫的生物存在,可是,狗的概念却捕捉到了所有感性生存的狗的抽象本质。这正是古希腊哲学开端中那个从“杂多”的感性实存向“一”的抽象存在的本质性过渡。可能,这种抽象也是所有文化历史发生的前提性基础。当然,列斐伏尔也注意到抽象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在他看来,一切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抽象是社会性的(socialement,自有工具和语言时起);在法律中,在鉴别中,抽象又是政治性(politique)的”。⑨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主观抽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客观抽象的区分。因为,他这里提及的工具,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是劳动者技能的客观的现实抽象且重新物相化于工具的结果了,这种客观现实抽象并不是发生在主观意识中,而是劳作活动重复中的现实提炼。这与法律条文的观念抽象是异质性的。不过,聪明的列斐伏尔察觉到,在抽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量,正是在劳动理论之中,抓住了设想和实际之间的一个首要关系”。⑩这是对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科学抽象的现实前提,即“19世纪在这方面的伟大发现,就是抽象化的(l'abstraction,因而也是实践的,de pratique)社会存在(l'existence sociale)”,所以,马克思科学抽象方法的现实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存在的“抽象化的”l'existence sociale(社会存在)。这种判断,立即使列斐伏尔的思想显得深刻起来,因为,抽象化的社会存在当然已经不再是人的主观观念抽象,而是客观的社会活动和关系的现实抽象。这就进入到一个深刻的思想构境之中。并且,列斐伏尔指出,在马克思之前,首先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是古典经济学家和黑格尔。
黑格尔与首批经济学家一起,曾经指出,劳动和需要作为社会关系(rapports sociaux),是现实和自然、有机活动和欲望很久之前的一些抽象化。后来,马克思指出了,商品是怎样把物质性(作为被产生的物体,qu'objet produit)和抽象性(作为被交换的物体,qu'objet échangé)统一起来的。
这当然是正确的理论直觉。因为,在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斯密那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劳动分工的出现,已经使人的劳动本身碎片化,产品成了社会化总体劳动的结果,这种历史性发生于资产阶级组织的工业实践中的抽象化的社会存在,实际上是劳动分工基础上客观生成的劳动一般,这与上述工具生产中出现的现实抽象是不同的。黑格尔敏锐地体知到这一现实抽象化进程,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逻辑之中。而马克思则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了物质性的商品交换活动中发生的抽象劳动价值关系生成的现实抽象,及其颠倒实现出来的货币(资本)关系的“抽象成为统治”。由此可以看到,在列斐伏尔那里就混乱地呈现了他自己也没有厘清的马克思思想中的三种现实抽象:一是工具生产中的劳动技能的现实抽象,这是有人类生产工具使用以来就出现的抽象。之后,这又将在科学技术的抽象构序中反射对象化为机器;二是历史地发生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分工之后的社会劳动一般的现实抽象,这是列斐伏尔此处所意识到的斯密—黑格尔的抽象化;三是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中历史生成的价值关系的现实抽象,之后这种抽象会颠倒式地事物化为货币和资本。在后来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中,他同时提及作为现实抽象II-III的“技术的抽象、商品世界所属的抽象”问题。我觉得,这是列斐伏尔在方法论讨论中无意识获得的重要认识。因在他看来,“黑格尔所说的需要和劳动的体系,马克思认为的商品世界,尼采的金字塔的等级,都是一些具体的抽象化(abstraction concrètes)”,它们不过都是“概念的社会运用(l'usagc social du concept)”。不是概念的社会运用,而是他们对客观的社会关系现实抽象的观念反映。
我发现,列斐伏尔所理解马克思科学抽象方法时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他明确指认出,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承认“生产性活动(l'activité productrice)”的观念背后,发现了创造财富的“劳动、劳动者、剩余价值和资产阶级剥削的机制”。这是对的。列斐伏尔说,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是一个自然事实”,因为,“在它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劳动延伸自然,出自自然,然后,向自然作斗争,向后者夺取‘东西’、财富”,由此,“劳动造就人和人类世界。因此,劳动处于历史的中心和确定历史意义的地位。劳动在两个方面创造财富:交换和使用(échange et usage),而后者是本质”。应该说,列斐伏尔的理解基本上是对的,但不够精准。马克思最早意识到劳动的重要性,是在1844年的《巴黎笔记》对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次系统研究的进程中,他分别在“经济学中的路德”(恩格斯语)斯密的《国富论》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看到了社会财富背后的对象化劳动,并生成了人本主义话语构境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虽然在1845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革命中,劳动通过物质实践进一步深化为第一层级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但在马克思1850年代进入到自己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后,他的确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中的重要变化,即从一般物质生产过程背后再一次突显劳动过程的主导性,并且再一次将劳动重新置于自己整个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地位上。由此,创立全新的劳动价值论和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正是在这个科学理论革命中,马克思完成了一种科学概念上的科学抽象。依列斐伏尔的看法,马克思的发现在于,
劳动力的使用和由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生产,都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劳动时间的方法(社会劳动定量)引到一个粗暴的等价(équivalence)之上。劳动这种自然的能量,通过劳动时间的转换,变成了商品。交换价值与自然决裂,交换价值本身是一种抽象(abstraction),它把劳动又变成了一种抽象:劳动力与产品同时被用钟点计算,抽象变成了社会的力量和形式(L'abstraction devient force et forme sociales)。
应该说,列斐伏尔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所描述的马克思的经济学逻辑构序,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中最深的思想构境。只不过,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粗暴等价”,商品交换中现实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是自发地出现在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之中的,劳动时间的“钟点计算”不是一种资本家的主观故意,而是交换活动发生时物品获得的特殊经济质性,“交换价值”本身是一种商品交换活动中价值关系现实抽象的结果,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客观的现实抽象在货币和资本关系中才历史性地成为一种统治性的force et forme sociales(社会力量和形式)。马克思的原话为:“抽象成为统治。”列斐伏尔的下述描述同样是极其深刻的。他认为,马克思
从一个实践(例如交换,l'échange),到一个概念——不是从一个内部运动,而是作为迎接实际和收集事实的方法来发展概念。因此,马克思构思了一些概念(范畴),以及构成其理论的这些概念的连贯:从交换价值(la valeur d'échange),经过商品世界、社会劳动(手段)、剩余价值、资本的有机组成等,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
这基本上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科学抽象法的正确分析。这里,马克思最重要的发现,恰恰是那个商品交换的实践本身中发生的现实抽象,这是理解整个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本质的关键,也是马克思整个经济学批判话语逻辑构序的基础。列斐伏尔认为,在现代国家问题的科学研究中,同样要坚持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方法。在他看来,今天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
在一个漫长的路程中,抽象(反自然,l'anti-nature)使一个第二自然(nature seconde)出现:自动装置(l’automate),它取消劳动。这个第二自然的模式和象征在机器上,在城市里,在思想里,在国家里,出现了。在这个戏剧性的路程中,社会人的创造力量通过了一些可怕的考验。它变成了要消失的抽象——商品、资本、死劳动(机器、厂房)、资本家的财产(死人抓住活人,le mort saisit Je vif!) 以及国家——中的最强有力的一个抽象。
这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中,黑格尔所指认的那种人创造的社会力量表现出异己性的第二自然,已经是马克思所揭露的取消劳动的抽象l’automate(自动装置),有如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世界中出现商品、货币和资本,特别是这些经济事物(金钱、机器、劳动对象和厂房等)背后所遮蔽起来的“死劳动”(对象化劳动),现在,这种自动装置通过城市和国家实现了一种新的抽象,这是一出人创造出来的社会力量反过来奴役和支配的“死人抓住活人”的悲剧,这一切,在今天都是由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一“最强有力的抽象”体现的。
其次,研究现代国家问题不能遗忘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的方法。这是列斐伏尔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反复强调的批判方法论问题。列斐伏尔说,“异化(L'aliénation),这个‘概念’从被人们遗弃的黑暗之中,从它搁置的哲学的阴暗之中浮现出来,已有三四十年了。今天,人们可以沿着它那闪烁的轨迹,提出许多有关它的问题”。言下之意,把异化观念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遗弃中拯救出来,这一“闪烁的轨迹”中他自己当然是有贡献的。这应该是事实。也是在这里,列斐伏尔再一次批评阿尔都塞,因为后者将异化概念仅仅看作是早期青年马克思使用的“意识形态”话语,而粗暴地无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和《资本论》等重要的经济学论著中同样坚持了批判的异化思想。列斐伏尔坚持说,“在马克思的思想里,异化并不在科学性面前消失。恰恰相反”。这是正确的判断。显而易见,对于阿尔都塞式的“新教条主义”(néo-dogmatique)对异化概念的否定,列斐伏尔是深恶痛绝的:
20 来年前即以清晰感到,“异化”挡了它的道,这种倾向,在这个词儿里包含的批评的打击之下瓦解了。因此,必须搬开障碍。人们曾想向异化要它的“身份证”和“户籍”(papiers d'identité et son état civil)。当概念或隐喻的异化在继续它在现代世界中的闪亮轨迹,同时激起对各种不同条件(被殖民者、被压迫者、女入、儿童、黑人、青少年,且莫说劳动者)的认识和意识的时候,人们向它要求哲学-科学“护照”、理论地位的证明。真是凶恶、粗野的学究!人们不去承认这个辞格的实际情况、它所起的催化剂(catalyseur)作用,而将它置于认识论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lit de Procuste de l'épistémologie)上,割去它的翅膀和双脚。
由此可见列斐伏尔的愤怒心情。他看到,正是在多年以前,阿尔都塞出版了《青年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宣判了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不具有科学的身份,简单剥夺了异化批判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出生证明,而当异化概念在今天的学术界对殖民主义奴役关系、女性和其他边缘人群的特殊的被支配关系的思考中大发光芒时,却又被勒索出示来自于马克思那里的通关“护照”。他怒斥阿尔都塞等教条主义的做法,简直就是一种腌割学术的现代lit de Procuste de l'épistémologie(认识论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问题上,阿尔都塞的做法的确存在着形而上学般的简单化。因为,他虽然正确地证伪了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主义话语,但却简单地否定异化概念在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中的客观存在和重要意义。其实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也是对错兼半,因为他固然正确地看到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后期经济学研究中的重现,但他并没有十分自觉地区分客观地存在于马克思思想中两种异化批判理论的异质性基础:人本主义话语基础上的劳动异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劳动异化理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但却异常重要的理论界划。
列斐伏尔主张,在我们面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问题的思考中,在马克思思想方法论中起到catalyseur(摧化剂)作用的异化批判的方法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思想工具。列斐伏尔甚至认为,在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武库中,异化概念,
它比剩余价值或生产力有计划增长(d’nccroissemcnt planifié des forces productives)概念的真正的——必须重复一遍,精辟的—一理论更有意义。由于有了这个词,遭受的痛苦就转变成清醒的力量。凡是拥有这种清醒力量的人,就会知道为什么而斗争,应该反对什么,反对谁,依靠什么,依靠谁。
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可能真的是异化理论此时在列斐伏尔心中的逻辑地位。因为他认为,比之于马克思在经济学中所揭露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预想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科学的异化批判能让人成为有明确斗争方向、拥有“清醒力量的人”。对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除去革命的摧化剂作用之外,列斐伏尔还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即异化批判就像冲洗相片中的显影剂(révélateur)那样,会让现实生活中那些被隐匿起来的罪恶显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比喻是深刻的。由此列斐伏尔才会认为,在批判的方法论构境中,它的意义更大。比如在面对资产阶级的国家问题上,列斐伏尔就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的政治异化(l'aliénation politique)批判的观点,这恰恰是他能够超越“国家拜物教”(fétichisme de l'Etat)的前提。实际上,政治异化的问题只是出现在青年马克思的早期学术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之中,这里列斐伏尔所指认出来的政治异化构境中的“国家拜物教”显然已经是他自己的理论逻辑演绎了。也是这里,列斐伏尔愤愤地谈及,阿尔都塞一类“结构功能—结构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正是十分敌视“政治异化”的观点。列斐伏尔分析说,国家拜物教是拜物教现象中的一个高级产物。一般而言,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话语是指,
每当社会活动的产物趋向于一种自治的存在(existence autonome),似乎在摆脱社会关系,表现出一种具有立时就要影响所考虑到的关系的特有活动的现实的时候,也就有了拜物教(fétichism),也就是说,极端的异化(aliénation extrême)。因此,这个广义的产物,在包含着生产活动的同时,又掩盖着它。所有大的“产物”——思想及其产生、艺术、技术、爱情、经济活动、商品和货币,最后还有国家——无不如此。
在讨论国家拜物教时,列斐伏尔同时涉及了马克思科学批判话语中两个最重要概念拜物教与异化的复杂关系。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构境层。在他看来,当一种人们的社会活动产物畸变为某种超出社会关系的existence autonome(自治存在),并开始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时,也就产生了对这种异己力量的拜物教现象,拜物教是aliénation extrême(极端的异化)。说拜物教本身就是极端的异化,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特别是在他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中,较晚出场的三大经济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批判话语,只是在经济学语境中描述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和异化的主观表象,而非现实异化本身。至于艺术、技术、爱情和国家现象中出现的拜物教批判,已经是列斐伏尔自己的逻辑延伸了。
列斐伏尔说,在对异化与拜物教现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只有中介才能被偶像化(Seutes les médiations peuvent se fétichiser)”。这是一个深刻却不够精准的判断。因为在列斐伏尔看来,直接性的对象似乎是不易被偶像化的,但其实最早的拜物教却是以原始部族生活的图腾文化中的物神方式出现的,比如对一种具体的动物或自然对象的直接崇拜。可列斐伏尔认为,往往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中介关系会是产生偶像化的基础,这应该是后来社会发展中逐渐复杂起来的社会关系异化中的现实。有如费尔巴哈指认的人的类关系中介异化和偶像化为上帝、马克思指认的商品交换中的价值中介关系的异化和事物化颠倒为货币等。列斐伏尔告诉我们,
中介和抽象(Les médiations et les abstractions)有着密切的关系,中介对社会实践进行抽象(la médiation effectue une abstraction de pratique sociale);它使之变为实践;它使之具体化(concrétise)。中介和抽象在表面上和实际上同时脱离直接性,是自立的(s'autonomisent)。它们有,或者不如说似乎有一种固有的存在。包括知识、语言等也是如此。
在列斐伏尔的表述中,往往出现的情况会是深刻与不准确并存。在思考中介与偶像化的关系中,列斐伏尔想起了上面讨论过的现实抽象问题,然而,现在变成“中介对实践进行抽象”,如果这里的中介意指作为社会生活本质的社会关系,那么,并非是中介关系对实践进行抽象,而是实践活动本身中现实抽象出关系,有如劳作实践中技能关系的抽象,商品交换活动中价值关系的抽象等。列斐伏尔说,中介与抽象都脱离了直接性,这是对的,抽象出来的关系更有可能表现出仿佛s'autonomisent(自立的)虚假固有存在。这正是拜物教生成机制的核心。列斐伏尔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像中介的经济关系被偶像化一样,资产阶级的“国家自此表现为在某个领土上抓住了各种中介一一城乡之间、农工之间、知识(脑力)和生产(包括体力)之间——的那种最普遍的中介”。这个掌握了各种中介的偶像化的国家,“盖过并统治着其它所有的偶像”,这就生成了政治异化关系中的现代资产阶级fétichisme de l'Etat(国家拜物教)。
最后,也就是列斐伏尔自己的回溯—前进法(régressif-progressif)。在这里,列斐伏尔再一次表明,他的回溯—前进法缘起于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的历史观察方法:
人们能够通过从往昔(passé)重新找到现在(présent),以目前的形象回想往昔的方法,笨拙地行事,可偏偏总是从现在、从眼下出发。于是,入们便满足于通过类似或相象,或者甚至通过重言式的简单重复和统一,把现在投射于往昔(projeter le présent sur le passé)。可马克思建议,把历史性的往昔作为它包含有未来的萌芽但尚未发展来加以分析。
这是一个双向透视,一是马克思提出的人体是解剖猴体的钥匙,这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发展回溯式的分析;二是社会初始阶段的发展总是已经内含着“未来的萌芽”,这是一种前进的发展眼光。列斐伏尔说,“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把两种方法——历史发生和回溯分析(l'histoire génétique et la régression analytique)——协调成一种对全部事实的灵活的和全面的科学。”这也意味着,将马克思的l'histoire génétique et la régression analytique(历史发生和回溯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正是列斐伏尔的“回溯—前进法”。由此,在资产阶级现代国家问题的研究中,既要研究这种国家理论的历史缘起,也必须面对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我们先来看列斐伏尔眼中,现代国家理论从“回溯”黑格尔那里的历史缘起,然后再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新“前进”。
二、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历史发生逻辑
列斐伏尔认为,对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历史认识,缘起于黑格尔。因为,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恰恰在于客观发生于社会历史中现实“抽象的巨大升级(colossale promotion),即财产(私有财产、动产)——法律和法典——国家和民族(l'Etat et la nation)”。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列斐伏尔将黑格尔哲学最后出场的理性主义国家与法,视作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实践中现实抽象的“巨大升级”,这倒是对黑格尔哲学新的解读。这是列斐伏尔上面所强调的科学抽象法的实际运用。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时候,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虽然马克思深刻地提出“拜物教的理论(商品的、货币的、资本的)指出了社会的抽象(l'abstraction sociale)是怎样在社会上存在和起作用的。商品和交换价值以及物质交换,都有一个既是精神的又是实践的存在方式”。这一概括是深刻的。但是,列斐伏尔同时认为,“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论战使理论模糊了”,因为,这种简单的唯物主义立场并没有真正透视黑格尔国家概念的主体性能动本质。我以为,列斐伏尔的这种判断显然是非历史的。因为,青年马克思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写作时,他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主谓颠倒,根本还没有深入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语境之中,自然也谈不到看到经济拜物教背后的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中发生的“社会抽象”问题,但当马克思后来在《大纲》中完成对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活动的科学认识之后,他不会再简单否定“抽象成为统治”的资本主义逻辑,虽然马克思没有来及完成自己在计划中的“国家”问题研究。在《大纲》中,马克思曾初步拟定过一个可能性中的经济学理论阐释的“五点构想”,即1、经济学理论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3、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形式”;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从《大纲》到《19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马克思的思考始终都是集中于第一个专题。
列斐伏尔说:“黑格尔在革命中看到的是行进着的理性(la raison en marche),而不是血腥暴力和历史的偶然事件。朝着什么行进?朝着国家的完善形式(la forme achevée de l'Etat)。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中以及在革命之后,民族国家出现了,并显现出,它在‘其自身和为其自身’,有着自己的基础、意义、起源和目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因为,正像黑格尔将拿破伦视作代表资产阶级历史趋势的“马背上的绝对精神”一样,在他的眼里,当时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理想化的普鲁士王国),正是超越了仍然处于经济必然性王国中的市民社会且实现绝对精神的自由王国。这样,在黑格尔唯心论的理性主义国家观的背后,却隐匿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逻辑。依列斐伏尔的看法,黑格尔眼中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仍然处于一种“精神动物界(Le règne animal spirituel)”和“事物本身(chose elle-même)”之中。这个Le règne animal spirituel(精神动物界)和chose elle-même(事物本身)”,都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著名说法。在市民社会里,
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范围里活动,并在抽象地实现一个局限而客观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在实现类似动物的他性生活(analogue sur un autre plan à la vie animale)。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和经济学家们的世界(monde de l'économie bourgeoise et des économistes)。每个人都在按照他认为实际的和唯一实际的利益行事,只寻求“事物本身”(chose elle-même),即财富、金钱。说实在的,每个人都在为他自己打算。然而,这个事物是有欺骗性的,因为“事物本身”隐藏着他性物(autre chose),包括超越它的时刻。实话实说;每个人在相信事物的同时,都在自己欺骗自己。
这是一段极其重要的思想复构,深刻而精准。因为,虽然黑格尔接受了斯密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也透视出这种由看不见的手支配下的自发经济过程的非主体性特征,此处列斐伏尔指认的类似动物界的他性生活,即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动物界”,意喻在资产阶级的经济世界中,人所创造出来的经济事物却表现为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二自然”的他性存在,人们还处在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生存关系场境(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之中。“每个人在相信事物的同时,都在自己欺骗自己”,这几乎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原话。
列斐伏尔说,在黑格尔那里,从市民社会到国家超越性的过渡有三个环节:
a) 需要的和个人通过劳动以及通过其他所有人的劳动和满足而满足的中介,这就确定了需要体系;
b) 包括在该体系之中的自由因素,这就确定了在司法之中(个人的)自由和所有权;
c) 通过机关对因此而合法化了的利益进行保卫,一种是国家外的机关,亦即行会,另一种是国家内在的机关,亦即行政。(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8节)
第一个环节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建构的经济的市民社会话语,其核心是以市场交换中介为转换关系的“需要体系”,原子化的个人需要的满足依赖于他人的劳作,这里的需要体系是个人盲目生产和利益冲突中自生成的;第二个环节是内嵌在市场交换中的自由因素与私有制的矛盾,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场的本质是自由竞争,可是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却使这种自由畸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发生前提;而第三个环节则是协调这些不同力量关系中复杂冲突的“行业公会”和国家。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黑格尔的“行业公会”和国家的本质,正好是扬弃“第二自然”状态中经济必然性的能动主体性。这种能动的主体性直接体现了绝对观念的自我觉醒和解放。这一点,将很深地关联于下面列斐伏尔提出的国家生产方式概念。然而,国家与法是如何扬弃市民社会的呢?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列斐伏尔分析说,在黑格尔眼里的市民社会中,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需要是连在一起的,它们互相之间紧密相连,组成一个体系。方法、工具和生产活动、劳动也是一样。劳动、特殊化(分成小块)和同样日益扩大的抽象(abstraction)作用也同样出现分裂和扩大。需要同劳动一样,因与自然界和在一种具体的,也就是积极的和生产的抽象作用的地位中的直接性的关系而产生。没有什么比一个需要比一种劳动更具体的了;但这种“具体性”(concrétude)作为巳经历过的直接性和表面的满足,那只是幻想而已。需要和劳动依赖于他性需要(autre besoin)、他性劳动(autre travail)以及所有的需要和劳动的既普遍又个别的关系。
这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对斯密市民社会理论的需要体系的批判性解读,在列斐伏尔自己理解构境中的展开。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斯密那个劳动分工条件下,“个体的劳动随着户品的大量增加而变得日益简单和抽象(在这里,黑格尔触及了实业的问题)。在手段(工具、技术、劳动组织)和能力的社会抽象作用的水平上,单个人和为了满足他们的那些小组之间的相互依赖”。这是说,劳动分工将总体性的劳动切分成小块的作用,劳动只是在一般社会劳动的层面上被现实抽象和整合起来,这造成了原子化个人之间的需要与劳动直接关联的消解,人们需要的实现只能通过非我的autre besoin(他性需要)、抽象的autre travail(他性劳动)的外部市场关系重新联结起来。这种经过市场抽象关系中介的
相互作用使得一系列的需要和一系列的劳动(如同一系列的言论和事物)回到它们自身来,互相确认。真正的具体存在于整体——每一个系列以及它们的联系——之中。这就把抽象纳入具体之中。作为“主体”——社会的单个人——的确定状态的每一个需要,坚信能够遇到与之相联系的,也就是通过确定的劳动产生的、能使之满足的客体。
当然,这种个别的劳动和需要之间的“相互确认”,是经过了市场交换,每个原子化的个人能够找到满足自己需要的客体,都是通过抽象的外部力量重新纳入到具体生活中来。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经济的市民社会仍然处于“第二自然”的必然性之中。在这里,这种在市场交换关系中出现的消极的抽象力量,本质上是绝对理论的“狡计”(看不见的手)。
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需要一种超越仍处于黑暗的经济必然性王国中的市民社会的主体性能动力量,除去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的初级干预,这就是体现了绝对精神自我觉醒中的国家与法。在黑格尔这里,国家被设定为一种主体性的“行动的哲学”(philosophie en acte),它体现了对消极的“第二自然”的市民社会经济王国的超越。然而,依列斐伏尔判断,在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中,经济必然性里异化关系被消除了,他并不承认在国家与法中仍然存在着“政治异化(aliénation politique)”。这应该是对的。因为在黑格尔心目中的普鲁士王国,已经是扬弃市民社会中“第二自然”异化后的绝对理念的自由王国的实现。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基本原则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就不同了,在1843年他最早遭遇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与法时,他仍然在政治领域看到一个颠倒的(renversement)世界,
他把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消失了的异化运动(le mouvement de l'aliénation)又加进来了。他结束了逻辑至上、逻辑对辩证的统治,恢复了辩证对逻辑的领先地位,因此,找回了被这位哲学家弃之于国家哲学中的现象学的运动(le mouvement de la Phénoménologie)的运动。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正是在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中,重新将政治异化置于社会批判话语的“首位”,“恢复否定的和建设性的辩证运动”,从而开启了对资产阶级政治与法权的批判。由此,“马克思从对异化的哲学批判走向对国家和政治本身的政治批判。这显示出了政治断裂”。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这里,国家不再是黑格尔奉作“神明”的终极结构,而只是一定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随着社会关系而变化。因此它没有永久性。它诞生了,将在衰弱之后消亡”。如果说,列斐伏尔以上的观点,主要是概括了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一直到《论犹太人问题》前后的思想,大的方面是对的。可依我之见,马克思此时并没有在面对国家与法的政治批判语境中自觉地“加进”le mouvement de l'aliénation(异化运动),固然他看到了政治领域中的法人与市民社会中现实个人之间“双重生活”的分离。并且,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自觉地使用异化观念,是对赫斯金钱异化观的简单挪移。在之后的思想发展中,马克思也没有谈及列斐伏尔这里所指认的发生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的aliénation politique(政治异化)。
列斐伏尔明确提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所以他说,“如果有人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国家理论,也就是说想寻找一种连贯和完全的国家学说体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这种学说体系是不存在的”。不过列斐伏尔也承认,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关注国家问题,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斗争中,马克思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问题。这里,他提及马克思在1858年2月写给拉萨尔的的那封信,在信中预想的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批判的六本书中,就包含有“国家”,但后来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这一完整的写作计划。这一“六册计划”,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大纲》中“五点构想”的进一步修订。列斐伏尔指认说,在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思考中,有着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历史性地认识国家的历史发生、发展和灭亡。
马克思从未停止过思考和证明自人类社会开始以来,国家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各种实际的斗争,而宗教的历史则可以归结为各种理论的斗争。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什么比一种包含着它的产生斗它的历史、它的形成和它的发展的国家理论更为重要的了。
这是对的。自国家出现以来,它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并随着这种斗争而消亡。这应该也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国家观的理论前提。在列斐伏尔看来,在国家的历史消亡问题上,也应该理解“马克思在国家问题上的犹豫和动摇”。这是因为,他认为,一方面,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倾向于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焦虑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必须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国家问题上的思考可以有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经济上,然后是政治上的,économiquement, puis politiquement)工具(instrument)”。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和控制被压迫阶级的暴力工具,这是我们熟知的观点,可是,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讨论过国家是作用于économiquement(经济上)的统治工具,这是列斐伏尔故意留下的逻辑伏笔。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列斐伏尔说,在马克思的眼里,“国家只是上层建筑。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久将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方面,努力去确定这一个词的含意和意义。他们将不去理会另一方面——机构方面,只是在关系到法时,偶而提一提它”。意思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都将国家归属于上层建筑,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只是涉及了上层建筑中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问题,基本上没有关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组织机构。可是在这里,列斐伏尔的判断似乎有一些改变,因为,他开始认为,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工具时,同时意味着,资产阶级的
国家是一种装置(appareil),是根据主要的生产和交换资料方面变得宽松的阶级的需要而改组历史的结果,而国家又能使这个阶级由经济上的优势变成为在政治上拥有霸权(hégémonie),甚至可以实行专政。这种国家权力还能保证这个阶级在经济方面(économique)和社会方面(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再生产。
这里的显著变化是,列斐伏尔在讨论马克思的国家观时,刻意突出了资产阶级的国家装置在政治统治之外对生产与交换的économique(经济方面)所进行的“改组历史”的作用,而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显然不存在这种关注的目光。这是列斐伏尔的过度诠释,他是依从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的逻辑,重构了马克思国家观念中的主体能动性,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导引出他后面将要提出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问题。列斐伏尔还特意指认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观点,
什么是现代国家?在恩格斯看来,它是现代社会为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条件而自行产生的组织(L'organisation)。现代国家,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机器,即资本家的国家,集体资本家(le capitaliste collectif),一个资产阶级的大行政管理委员会(le grand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可以看到,列斐伏尔这里突出强调了资产阶级现代国家新的本质特征,国家并非仅仅只是一种受经济关系支配的上层建筑,而它本身就是主体性的le capitaliste collectif(资本家集体),这显然也是列斐伏尔自己刻意的放大。首先,正像前面他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指证的那样,资产阶级不是一座死去的“雕像”,它通过国家形式直接干预着社会生活,并且,这种主体的能动干预在今天已经“发展到顶点”。
其次,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的统治力量。列斐伏尔说,马克思的“这种理论把国家看作是竖立于整个社会之上,既表现出寄生性,又表现出掠夺性,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它能够掠夺整个社会的成果”。这里的寄生性,不仅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还表明通过税收等方式,“国家的整个机器是靠社会生产的财富来供养和维持的”。我觉得,这里列斐伏尔特别想强调的方面,恰恰是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的资产阶级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掠夺性。因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能动的阶级主体(资本家集体),它又会表现出对社会财富(剩余价值)直接的掠夺和支配生活的强暴性。在今天,资产阶级“能够把政府和国家变成掠夺社会的工具”,并逐渐地生成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国家生产方式。
再次,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直接管理着生产力。这当然是列斐伏尔这里最关心的问题。在他看来,国家“无论是由于它具有一种经挤能力而承担各种行政管理的职能,还是它在表面上继续竖立在社会之上,但实际上,国家政权直接管理着生产力”。这当然已经是一个新的判断。依列斐伏尔的说明,马克思并不是一开始就看清这一点的,而是在后来关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中,才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因为在那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鉴于控制水所提出的大量问题,国家就要负责各种各样的大工程:修筑堤坝、排水和灌溉设施等”,并且,“修建这些水利网还必须配以修建连结各个生产单位的道路,以便供民用、军用,有时还要供宗教方面使用”。这就出现了一种国家对生产力本身的直接管理和控制。我觉得,列斐伏尔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这种东方式的国家直接控制生产活动,会不会是封建经济的本有特征,因为在欧洲的中世纪,土地上的神授皇权依神性—宗法关系,同样是直接支配和控制所有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列斐伏尔认为,正是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才使得马克思开始注意到已经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相类似的情况。列斐伏尔进一步延伸说,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国家并非是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在同各个阶级的关系中也并非处于中立状态”,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通过国家实施“一种经常性的压力以便把劳动当作一种商品纳入交换的轨道之中,也就是说,通过把劳动时间估价为货币而纳入交换的范围之中”,这样做,是“为了把地方市场和各生产单位纳入国家市场”。这是表明,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本身,必然是通过国家统一的交换制度和货币度量,包括国家银行来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更重要的是,
一旦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永恒不变的规律,即供求规律运转失常,一旦市场(特别是劳动力的市场)失去规则,国家就得介入并起作用(l'Etat entre en action)。它阻止各种危险倾向,阻止在繁荣时期劳动交换价格的上涨和平均利润的下跌,等等。
我以为,这当然不会真是出现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所谓“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的主要现象,这已经是列斐伏尔用今天的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去反注历史的做法。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根,就是重农学派对皇权和国家力量对生产的主体性干预,让商品—市场中的生产和交换自发地生成自身的“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的客观支配,这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安身立命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劳动力进入市场,商品交换中现实抽象出的价值关系颠倒为货币,以及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一个国家的货币单位,都不会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自觉主体意志。资产阶级国家突破“自由主义原则”,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直接干预的主体性作用,这应该是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
列斐伏尔告诉我们,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比如,“在各个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向了垄断(la libre concurrence se convertit en monopoles)”,列斐伏尔没有注意到,恩格斯此处提及的经济垄断并非是发生在国家层面上的主体性,而是资本利益集团的主体性。即便如此,恩格斯也只是将这种经济垄断现象其视作向社会主义 “计划生产”(la production planifiée)的客观逼近。恩格斯并不会设想,“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国家以及资产阶级本身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组织”,在未来资本主义当代发展的现实中,资产阶级竟然会将这一计划经济机制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
在列斐伏尔看来,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的理论进展,出现在卢森堡的经济学思考之中。这应该是列斐伏尔在自己的“历史回溯”中的新发现。列斐伏尔说,国家问题虽然并不是卢森堡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但在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评论中却无意识涉及到了资产阶级现代国家作用的另一面。列斐伏尔说,
罗莎·卢森堡在她的《政治经济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économie politique)中指出(并非直接攻击马克思),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流通和周转相互重迭,而马克思并没有从历史上和理论上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资本论》中,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是以实现剩余价值没有问题为前提的。
具体而言,在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上,卢森堡认为,“剩余价值并非是在资本主义‘内部’(à l'intérieur)实现(这个‘内部’主要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在外部(au-dehors)实现,扩大积累首先是以输出为前提,这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外围地区逐步遭到损害”。我的看法是,卢森堡提出的观点是对的,但马克思并非不知道资本积累中资产阶级对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疯狂掠夺和不平等交换,马克思也不可能将剩余价值的实现仅仅局限于资本对本国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上。这一点,马克思在1947年的《居利希笔记》中已经开始有所观察,在已经可以看到的1850年前后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还专门做了殖民主义专题摘录。只是,在从《大纲》《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集中于理论化的民族国家内部“资本生产总过程”的思考中,并没有来得及真的完成自己包括了“世界市场”(国与国之间贸易、殖民主义关系等)的写作计划。这是上述马克思自己的“五点设想”和“六册计划”中共同的结尾部分。在这里,列斐伏尔直接引述卢森堡在《政治经济学导论》中的一段表述:
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经济中,必然存在与纯粹的商品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明显,只有一个国家拥有对另一些国家的经济支配权,才能正常地从这些国家获得更多的产品,而它本身并不会给这些国家提供同等的报酬。这种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丝毫也不是两个平等的伙伴之间的交换。
列斐伏尔让我们注意卢森堡这段文字中的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不平等交换”,这是指资本在本国之外通过不平等交换和掠夺实现的资本积累与另一种方式的剩余价值实现形式;二是在这种发生在“一个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经济支配权”中,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资产阶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是列斐伏尔所需要突显的国家主体能动性特征。由此,列斐伏尔还进一步得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与卢森堡同时代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列斐伏尔认为,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l'impérialisme est contemporain du capitalisme),而不是如列宁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如果不向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区输出,剩余价值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对其它地区的掠夺,没有同较远的国家的贸易,没有工业产品的大量输出,就没有积累。
在列斐伏尔的眼里,列宁同样“轻视了19 世纪到20 世纪通过征服、掠夺、各种贸易的联系和最初的殖民化而形成的世界市场”。我认为,这当然是列斐伏尔在偷换概念的基础上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曲解。列宁所指认的帝国主义,是特指20世纪初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世界性的战争争夺和瓜分整个世界的现代资本主义列强,这一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特殊历史形式的帝国主义,是以区别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关系为本质的。与马克思一样,列宁从来没有忽略从14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通过殖民主义的方式侵占和掠夺世界的历史,而只是突出强调了在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生成,以及必然产生的国家垄断资本不可抑制的新型对外扩张和侵略。并且,在列宁所处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他得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最高阶段,应该说是有其客观现实基础的,随之而来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真正的问题在于,谁都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后来通过“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实现的重要改变。在这一点上,我们显然无法非历史地苛求他们。
实际上,列斐伏尔此处想要突出说明的方面,正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显著的能动性主体特征,这似乎直接确证了黑格尔那个超越“市民社会”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当然,这已经不仅仅是列宁20世纪初所指认的垄断资本的对外暴力扩张,而更主要的表现为今天资产阶级国家主动的自我调节性(Régulateur)。这个自觉的主体性的Régulateur(调节性),正是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核心,也是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在改变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盲目经济发展状态之后,出现在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的“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生产和经济运行,然而,这种主体性的自我调节,竟然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力量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也是在这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转换为资产阶级国家伸向全部社会空间的看得见的手。在列斐伏尔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原先那种
竞争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concurrentiel)的各种自发的、盲目的和‘自动的’的调节(Régulations spontanées, aveugles et automatiques)——各种社会的平均值(les moyennes sociales),例如平均利润率,由各种被计划好的、被预测到的(calculées et prévues)和严格研究过的平均值所代替,这就保证了一种按照意愿(volontairement)来维持的严密性”。
在列斐伏尔这里的问题域中,这是一种客观发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新的现实。前述黑格尔在唯心主义思想构境中,明确指认的有自觉主体性意愿的国家(与法)对“第二自然”状态中的市民社会的超越突然成为现实。关键还在于,马克思和列宁预想在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那种盲目的、无政府生产后,本应出现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calculées et prévues(计划和预测)的生产,现在竟然直接出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中,资产阶级不可思议地通过自己的主观volontairement(意愿)所实现的国家调节,直接作用于经济过程。
当然,列斐伏尔这里通过对国家问题的“历史回溯”,目的是要更好地、“前进式”地理解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家问题中出现的新情况。在此,列斐伏尔让我们聚焦于今天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极端的重要性:一种国家的空间支撑物的生产(la production d'un support spatial de l'Etat)和各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la recon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今天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极端重要?因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获得垂而不死的幸存,就在于资产阶级通过国家的生产方式拓展了社会空间中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就将20世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内嵌到自己的空间生产理论逻辑构序之中来。他兴奋地说,
按照这种图式,人们可以研究新资本主义(néo-capitalisme,这就是说各种大组织的资本主义包括各种所谓跨国公司)。人们同样可以研究新帝国主义(néo-impérialisme)和它的各种特定的现象(例如,各工业大国从不发达国家大量输入劳动力,这是一种剩余价值生产的新的方法)。
人们要研究发生在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列斐伏尔围绕国家生产方式中的空间生产的论述值得参考,这是科学说明以跨国公司为模式的国际资本组织和国际化劳动公式中新的剩余价值盘剥方式的有效路径。
注 释:
①Henri Lefebvre ,De l’E'tat, I.L’E'tat dans le Monde Moderne.Paris: Union Générale d’ Éditions.1976;De l' E'tat, II,Théorie marxiste de l'état de Hegel à Mao, Paris : Union Générale d’ Éditions,1976;De l’E'tat III.Le Mode de Production Etatique.Paris: Union Générale d’ Éditions.1977;De l' E'tat , IV,les contradictions de l'etat moderne.la dialectique de l'état ,Paris : Union Générale d’ Éditions,1978。
③Lefebvre Henri.L'État dans le monde moderne.In: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37—38, 1975.Sociologie politique et culture théorie sociale et linguistique.pp.3—23。
⑤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los ,1924—2010):法国思想家。代表作有:《作为技术思想家的马克思》(1961)、《未来思想导论》(1966)等。
⑥ Lefebvre, "Marxisme et technique;' Esprit no.307 (1962): 1023-1028.此文为列斐伏尔关于阿克塞洛斯的著作《作为技术思想家的马克思》(Kostas Axlos, 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De l'alienationde l'homme a la conquete du mond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61)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