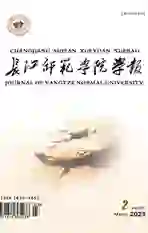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乌江航道文化遗产的特征及价值
2023-04-12林婵娟李然
摘要:文化线路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遗产表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借助文化线路理论,通过文献整理与田野调查,对乌江航运系统进行遗产识别。研究发现:乌江航运系统具有类型丰富的遗产构成,具备文化线路的基本特征,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线路,可称其为乌江航运。通过探讨乌江航运的特征与价值,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拓宽文化线路的遗产视角。
关键词:乌江流域;文化线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652(2023)02-0062-10
DOI:10.19933/j.cnki.ISSN1674-3652.2023.02.00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ISD):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土司文化遗产比较研究”(20FMZB005);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乌江航运文化线路遗产研究”(BSY21034)。
文化线路遗产是国家与地方互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历史遗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线路宪章》认为,“文化线路是水路、陆路或其他形式的交流路线,有明确地理界线、独特的动态和历史功能以及特殊而确定的服务目标。它源于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在时空中涉及的所有文化之间的交流互惠在其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构成之中得以体现,并将相关联的历史关系与文化遗产整合为统一动态系统”[ 1 ]。文化线路遗产的挖掘、整理、阐释及保护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的文化线路遗产研究大多集中于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线路“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走廊的路网”,或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海上丝绸之路、灵渠、蜀道、万里茶道,以及西南丝绸之路、北京中轴线、茶马古道、川盐古道、武当神道等大型文化线路,还有许多流域性水运文化线路遗产亟待挖掘与整理,乌江航运文化线路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线路之一。
乌江是武陵民族走廊最西侧的通道[ 2 ]。它发源于贵州乌蒙山脉,于重庆涪陵汇入长江,流域范围涵盖今渝、黔、滇、鄂四个省级行政区。乌江是长江右岸最大的支流,其干流中下游部分及郁江、石阡河等支流组成的航运系统从西南辐射华中500余公里,连接着中原、荆楚、巴蜀、滇黔等地域文化区,覆盖了汉、苗、土家、仡佬等多民族文化区,可以称其为乌江航运。
乌江航运兴起于战国时期,反映了中原、荆楚、巴蜀、滇黔等多地域人群的政治、商贸与文化互动往来。乌江航运的形成与发展受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影响,其所联通的不同文化和人群的交往互动充分反映在沿线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这种互动影响以航运为主要方加强中原地区和乌江流域各民族地区的交往,既体现了历代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治理不断深入的过程,也体现了乌江流域各民族不断吸收中原文化,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龚锐等的“盐油古道”研究[ 3 ]已经触及乌江航运线的文化线路特征。从文化线路遗产的理论背景出发,结合乌江航运历史与航运遗产现状,对乌江航运文化线路遗产的构成、特征及价值进行初步探讨,期望推动乌江流域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丰富我国流域性水路文化线路遗产的类型。
一、乌江航运文化线路的遗产构成
乌江航运依托航运而形成,是沿岸不同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通过航运沟通,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商业、民俗等各人文领域内互相碰撞而产生的,其遗产构成可以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种类型。
(一)物质文化遗产
1.航道。航道是乌江航运系统最核心的物质文化遗存。乌江航运因两岸时有岩崩阻塞河道,通航路线有所调整,在不同历史年代有不同的线路分布,主要有涪思段(重庆涪陵—贵州思南)、思湄段(思南—湄潭沿江渡)、郁江段(郁山—彭水)、石阡段(思南两江口—石阡)四段。
2.渡口。渡口是航运基础设施,见证了乌江航运上不同区域的人员往来与商贸交流。乌江航运上的渡口遗址众多,仅铜仁地区的乌江渡口就有118处[ 4 ]。见诸历史文献较多的渡口有河闪渡(仡闪渡)、马骆渡(马骡渡、马洛渡)、沿江渡(袁家渡)、德江上渡(蛮夷司上渡)、廻龙场渡等,但多数渡口仍未受到足够重视,仅彭水、沿河两地的红军渡与余庆廻龙场渡口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助航类遗产。(1)纤道。有学者将乌江纤道开凿的时间追溯到战国初期的巴人南迁。见诸于史籍最早的是清道光十二年(1832)思南知府杨以增在镇江阁悬崖处修建纤道[ 5 ] 169。乌江沿岸古纤道大多被淹没,彭水万足、思南两江口等几处尚存零星遗迹。(2)绞关站。绞滩指用绞盘或绞滩机绞拉船舶通过急流滩。乌江航运的上水船每过险滩,人必上岸,货物依靠人力搬运过滩,船则由船工打帮“换综”拉纤方能过滩。绞滩始于明朝,经历了搬滩、人力绞滩、机械绞滩三个阶段。随着水电开发后乌江水位的上升,众多绞关站已被埋没水下,绞滩也退出历史舞台,仅剩贵州德江县境内潮砥滩上的绞关遗址。
4.码头型古城镇。乌江航运及其伴随的政治军事资源、人口、商贸与物流的汇聚,孕育了两岸众多码头型古城、古镇。航路上的古城主要是思南、彭水、涪陵等历史文化名城。航路上的古镇较多,如龚滩、羊角、郁山、潮砥、洪渡等。但随着现代的经济运动和水电建设,目前只有淇滩和龚滩(异地复建)相对完整,且龚滩古镇已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5.古建筑。乌江沿岸城镇分布着许多与航运相关的古建筑遗存,其中以会馆、祈福庙宇和盐业仓储最具代表性。会馆建筑多是清时受川盐之利吸引,从陕西、江西、四川和两湖等地区迁居乌江沿岸贩盐运盐的商人所建立。现存会馆建筑中,陕西会馆仅酉阳龚滩古镇西秦会馆一处,两湖会馆也只有石阡禹王宫,江西会馆有彭水万足万寿宫、思南万寿宫、石阡万寿宫,四川会馆有彭水万足万天宫、酉阳龚滩川主庙、思南川主庙等。航路沿线还遗存了与乌江航运密切相关的宗教场所——王爷庙。王爷庙多系木船时代船工及家人祈求航运平安的庙宇,现仅思南、石阡保留有其建筑遗存。清以后川盐入黔行销时期的仓储遗存有思南周和顺盐号、龚滩“半边仓”等。
6.石刻。石刻是乌江航运历史上政府、士绅、商人与民众关于航道开发、航运管理的社会契约,是航运民间公产、商业管理制度的雏形。摩崖石刻中,以德江潮砥的“黔中砥柱”最有代表性,1958年便被列为贵州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有关乌江渡口管理的碑刻内容也十分翔实,如《湄潭沿江渡政德碑》《桶井严禁舟楫贪揽重载碑》《仡闪渡兴渡碑》等;还有记载疏凿乌江河道的碑刻,如《通木坪修河碑汇》;航运码头、场市管理碑刻,以《龚滩签门口永定成规碑》最有代表性,2009年被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乌江航运有密切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饮食、民俗、号子、航运有关古代诗词、“歪尾船”建造技艺、民间传说等方面。彭水郁山的鸡豆花和三香等制作技艺、德江土家族炸龙和傩堂戏、思南花灯戏和上元沙洲节、石阡布偶戏和仡佬族毛龙节等非遗均与乌江航运带来的文化交融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古代黔地陆路不畅的情况下,乌江航运成了历代移民携带各种文化因素的传播孔道。以德江土家族炸龙为例,其中充斥着汉民族舞龙习俗、土家族“火神崇拜”与傩文化的交融性。炸龙是德江土家族春节的重要民间活动,其本质实为“舞龙”“龙灯”,只因炸龙是其高潮环节,所以民众统称为炸龙[6]。清道光《思南府志》载“祈年则上元龙灯、社会、神会及各庙斋醮,均此意也”,说明至少两百多年前龙符号就已经被拥有白虎崇拜的土家人所接受,而这应与明清时期沿乌江航运进入该地区的大批汉人有着密切关联。这种舞龙习俗与土家族悠久的“火”崇拜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扎龙、出龙、送帖、舞龙、游龙环节后的“炸”龙高潮。同时,炸龙与“冲傩”有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与“冲傩”的转运动机一致,即当事人主动要求在炸龙活动中“被炸”,以此驱除霉运;二是与“冲傩”中的“还愿”要求一致,即一旦参与炸龙,便要连续参加三年,否则会遭报应。
乌江航运上的船工号子,生动地反映了航运与船工、纤夫等的生活状况。乌江船工号子以沿河乌江山峡一带最典型,川江号子(乌江号子是其组成部分)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思南船工号子已被列入贵州省非遗名录,武隆羊角船工号子也被收录至重庆市非遗名录。历史上“歪尾船”常年航行在涪思段航路,沿线民间造船业也曾十分兴盛。据记载,德江新滩附近的侯家坨的“水木匠”中曾保留有“歪尾船”的土法建造技艺[ 7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歪尾船”的建造技艺随着1964年最后一只“歪尾船”的拆解,逐渐消失在漫漫江流中。
许多政治家、文学家或生在乌江沿岸,或经航路求学、任官、贬谪而驻足乌江两岸怀古凭吊或感时伤世,留下的大量诗文增添了乌江航运的文化底蕴。其中,以刘禹锡、黄庭坚等发扬光大的乌江竹枝词最具特色。前人对这些文学作品多有整理,如黄节厚曾专门收集乌江古代诗词350首[ 8 ],为进一步认识乌江航运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关于乌江航运的传说有《乌龙辟江》《乌老汉要江》《狮吼洞》《鲥鱼堆的传说》《玉龙架桥》《仙人造船》《送龙归大海》等。
二、乌江航运的文化线路特征
1994年的马德里会议指出了文化线路的四点判别标准,即空间特征:长度和空间的多样性反映了文化线路所代表的交流是否广泛,其连接是否足够丰富多样;时间特征:只有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文化线路才可能对它所涉及的社区文化产生影响;文化特征:是否包含跨文化因素或产生了跨文化影响;角色和目的性特征:它的功能[ 9 ]。
(一)空间特征:山水相间,空间繁复
乌江航运是一条水路通道,以今重庆涪陵为起点,溯乌江而上,从四川盆地延伸至云贵高原,在长度上跨越500余公里。从线路分布、地貌形态和地理空间看,它有明确的地理范围,具有山水相间、空间繁复的空间特征。
乌江航运具有明确稳定的线路走向。它涵盖涪思段、思湄段、郁江段与石阡段四条线路,其中又以涪思段为主体。其线路分布为第一,涪思段:从重庆涪陵至贵州思南长约395公里的乌江干流航线,是乌江航运的主体线路。龚滩是古代川黔界点,自明万历年间凤凰山岩崩后,涪思段愈发明确地以龚滩为界,分为涪龚段和龚思段两程。从船只上水角度讲,涪龚段的线路是今重庆涪陵—羊角碛—武隆—江口古镇—彭水—洪渡古镇—龚滩,龚思段一线主要是龚滩—思渠古镇—沿河—淇滩古镇—新滩—潮砥—桶井—思南城。第二,思湄段:从思南到湄潭沿江渡的干流航线,全长约60公里。乌江思南以上的河道通航历史较短,至1915年左右,思湄段河道可自思南上行至沿江渡附近。船只若由思南城上行,线路是思南城—镇江阁—邵家桥—两江口—文家店—河闪渡—通木坪—梁家渡—沿江渡。其中,思南—河闪渡为稳定线路。第三,郁江段:从郁山古镇到彭水城的乌江支流郁江段航线。该航运段落线路大致为峡口塘—蔡家坝—郁山镇—观音岩(彭水县城乌江口),长约112公里。第四,石阡河段:由石阡城至思南塘头镇两江口的乌江支流石阡河航线,全长约62公里。石阡段的线路为两江口—雷家屯—浮桥口—石阡城。
从地貌形态看,乌江航运四条线路共享山水相间的特征。乌江航运集中分布在乌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河道多险滩,两侧多峡谷。思湄段与石阡河段地处乌江中游,此段航道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主要夹行在大娄山脉与武陵山脉之间,多为二三百米深的V字形峡谷,崩石堆积,以鱼子三滩最著名。涪思段与郁江段地处乌江下游,此段航道宽窄相间,河面相对开阔,但仍有潮砥、新滩、龚滩、羊角碛四大滩王。乌江航运联通了云南高原、贵州喀斯特山地和四川盆地,其间既有低山丘陵,又有山间盆地(坝子),还有河流阶地与岩溶平原[ 10 ],横切武陵山脉和大娄山脉,串联起梵净山、佛顶山、八面山、白马山、仙女山、金佛山等自然山川,跨越了多样的地貌形态。
乌江航运所连接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呈现显著繁复性。从地理空间看,乌江航运连接了众多不同的地理区域。航路两端分别是四川盆地的东南边缘和贵州高原西南部分的中低山地,其主体线路涪思段可由涪陵北接长江动脉直连祖国东部平原,石阡河段线路继续深入贵州高原东部地区,郁江段尽头峡塘口转入陆路直达鄂西南山区,思湄段延长路线则可转接乌江上游流域云南高原的东延部分,这种因航运而生的地理空间交往繁多而复杂。从文化空间看,乌江航运沟通了中华大地上多层级文化区域。覃德清将中华民族地域文化分为15个文化区[ 11 ],从乌江航运的覆盖范围看,它至少连接了中原、巴蜀、荆楚与滇黔四大文化区,甚至可以通过与长江航线的联动,与东南沿海的吴越文化区产生联系,这种因航运而生的文化空间互动多样而复合。
(二)时间特征:历史悠久,赓续千年
乌江航运的历史起源有三种观点:其一,将历史追溯至传说时代的“廩君之土舟”[ 12 ];其二,追溯至巴国对乌江水道的开发利用[ 13-14 ];其三,追溯至信史记载的公元前316年的秦国“司马错自巴涪水,伐楚国黔中郡”[ 26 ] 23。从最早的军事航运记录看,乌江航运距今至少已有2 300余年历史。乌江航运的发展大致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隋唐以前为初始阶段。自秦“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 12 ]始,乌江航运开始登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舞台。三国时期,晋欲伐吴,蜀郡益州刺史王澹修官船,派遣李毅自涪陵取武隆,行军路线也与司马错类似[ 16 ]。这一时期涪思段线路大致为涪陵——黔东北地区。此外,由于郁山盛产盐、丹砂,“郁盐东以济楚,西入武陵,还需要郁江外运到彭水”[ 17 ],秦汉以后的丹砂运输也依赖郁江,因此郁江段在先秦时期也应有所开发。
第二,隋唐宋元时期为发展阶段。唐时,乌江已可通航至费州(今思南)。航路通畅加强了中原王朝对乌江流域的管理,唐朝在乌江干支流沿岸屡设建置,宋时也曾在龚滩等地设转运仓。唐宋以后,乌江沿线多次崩石,逐渐形成了龚滩、潮砥、新滩三大断航滩。元时于涪陵、新滩、羊角、龚滩等地设水驿,供船只分段周转。经过历代水上开发,涪思段线路开始明确地发展为涪陵—武隆—彭水—洪渡—龚滩—潮砥—思南。
第三,明清时期为繁荣阶段。这一时期,乌江航运在涪思段主体线路的基础上,于明万历年间形成了延伸线路石阡段,清中期时又形成了思湄段。明嘉靖十八年(1539),时任四川按察使的田秋倡凿乌江,船只从此由涪陵出发,过龚滩,越新滩、潮砥,几易舟楫可航至思南。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石阡知府郭原宾首倡疏凿石阡河,由此从石阡城至思南塘头两江口的石阡段线路开始形成。民国二十六年(1937)所立的《湄潭沿江渡政德碑》载,“我境沿江渡,地界黄、余、湄、瓮,水接遵、筑、思、沿。前二百年码头热闹,近三十载市镇萧条”[ 18 ],说明至少清中期时思湄段线路也已开始形成,只不过后期年久失修,只能断续通航。
第四,民国至抗战时期为再繁荣阶段。民国时期,川盐入黔政策的继续施行,推动了思湄段线路的再次疏通。1914—1915年,思南商民刘维章等人在余庆县通木坪继续上行,开凿了梁家渡、鱼子三滩等处,使乌江干流河道可再次通航至湄潭县沿江渡,直抵瓮安江界河[ 5 ] 32-33。至此,思湄段的完整线路再次形成,乌江航运的四条线路也最终定型。抗战时期,1938年10月宜昌沦陷长江水运中断后,乌江航运在西南大后方物资运输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第五,20世纪后期为分段通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多次整治,涪思段以及思湄段内的文家店至大乌江河道实现了机动船全线通航。这标志着乌江航运木船时代的结束,拉纤、盘滩退出了历史舞台。新中国的陆路交通建设,使水上客货运输竞争力渐衰。随着1969年乌江渡水电站的修建,构皮滩、思林等电站也纷纷破土动工,乌江航运的完整性遭到破坏。20世纪90年代末,渝怀铁路通车,乌江流域梯级水电站渐次开发,乌江干流航道完全处于分段通航状态,通江达海被中断。
乌江航运绵延赓续,在两千余年的时间跨度里沟通着古川黔大地,航运架构起的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交往互动从未间断。21世纪初,乌江航运仍被纳入《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①中长江水系高等级航道布局“一横一网十线”的“十线”之一。随着2020年乌江白马航电工程正式开工,乌江航运将全面复苏,乌江航运将与长江黄金水道重新联通。
(三)文化特征:交融共生,多元一体
王铭铭曾用文化复合性概括西南文化面貌,认为其意指不同社会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内部结构生成于与外在社会实体的相互联系,其文化呈杂糅状态[ 19 ]。乌江航运辐射地区恰处于历代中央王朝经略西南边疆的必经之路,其文化复合性更加明显,构成了乌江航运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
这种复合性以中原文化为基底。历史上文人官员的贬谪流迁使大批中原人士沿乌江航运进入滇黔外缘,加速了中原儒释道文化向乌江流域的传播。自李唐以降,乌江航运便成了流人的必经之地。唐时李承乾、长孙无忌等被流放黔州,李白、刘禹锡等也因政治牵连流放黔地;宋元时期,程颐、黄庭坚等被贬后也谪居于航路沿岸;明清时期流任更多,王阳明、孔子后裔孔文山等[ 20 ]也均被贬至黔地。皇亲国戚的到来使黔州(今郁山)在历史上出现了紫云宫、开元寺、文昌宫等“九宫十八庙”的佛、道宗教建筑,也产生了鸡豆花、三香、擀酥饼等精致的宫廷饮食。一众文人骚客谪居期间,吸取了巴人竹枝歌的体裁,创作了大量诗词作品;同时广办儒学,如程颐在涪州(今涪陵)创北岩书院,思州(今思南)建鸾塘书院、设文庙,致使沿线地区文教日盛,思南府甚至出现了“文教覃敷,民俗渐化”,“取科第、登仕版,可方中州之盛”[ 21 ] 52的兴旺景象。
乌江航运带来的“他者”地域文化的流动性与“自我”民族文化的栖居性深刻体现在沿线的会馆建筑中。禹王宫是湖广移民聚会之所,集中展示了湖广人的大禹信仰。贵州石阡禹王宫的戏台木雕以西汉李陵抗击匈奴为主题,借李陵部下“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 22 ]表达荆楚文化中的爱国之情。石阡仡佬族先人在参与修建万寿宫时,将飞檐翘角的仡佬民居特点融入传统建筑[ 20 ],将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成功融入了江西会馆建筑。川主庙是四川商人集会之所,亦是古代四川百姓祭祀川主李冰的宗教场域。航路沿线的贵州地区亦是川主庙密布,思南居民甚至“盛装神像,鼓行于市”[ 21 ] 108,岁祭川主。其本质是受川民入迁影响,接受川主信仰,意借川主神力变乌江“天险”的水患为水利。封火墙建筑特色也多见于航路沿线,龚滩古镇鳞次栉比的土家吊脚楼之间有封火墙相隔,沿河淇滩古镇的封火统子更是胜似徽州民居。封火墙这种源于吴越地区的文化特质,是早期徽商在沿线经营淮盐的文化产物,是乌江航运与长江航线联通互动的文化结果。
因乌江航运而产生的“内外”互动在漫长的“上下”历史中构成了沿线地区的文化复合性,这种复合性也体现在一种“傩”民俗传统中。乌江航运沿线的黔东北地区傩戏盛行,傩文化元素在思南花灯戏、石阡布偶戏等非遗中有迹可循。如德江傩堂戏演出内容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交融性。在开坛仪式中,“我祖你原是湖南、湖北,来在云贵显威灵”的唱词说明其源自古代楚地,说明傩堂戏与“信巫鬼、重淫祀”的楚文化有着深厚渊源;从傩堂戏跳神看,“施法者”土老师(也称端公)在当地土家人中拥有较高威信,其演出内容也大多是原始宗教,充斥着土家族文化;《九州和尚》《十州道士》《梁山土地》《梁祝》等剧目内容又体现出儒、释、道文化与中原地区民间故事、历史演义的身影。高伦认为,贵州傩戏的形成受到先秦时期巴、楚巫文化和汉唐以来中原汉族移民习俗的影响,明确指出沿河、德江、思南等地“信巫屏医,专祀鬼神”的习俗是涪州杂剧等通过乌江水路进入的影响结果[ 24 ]。傩活动产生于原始社会,本是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现象,是华夏文明因子,但如今在中原地区消失不见,而在僻处一隅的贵州民族地区完整保存下来,这种文化表现也十分符合威斯勒的“文化年代学说”[ 25 ]。
乌江航运沿线的文化面貌中,既有中原儒释道的文化底色,又有多地域文化因子的存在,还有巴楚巫文化的身影,加上当地民族文化的浸润,构成了一种多元一体的复合性。这种复合性以乌江航运(尤其是木船运输)为主要的动力学类型,是周边诸文明体系在其推动下的内外互动中产生的。经过两千余年未曾间断的上下交往,其文化内部的交融状态在航运文化遗产中呈现出来,使乌江航运呈现出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
(四)功能特征:走廊通道,枢纽整合
第一,军事走廊。乌江航运北连长江,南达云贵,是古代中原、巴蜀连接黔中大地的必经之路。乌江航运用于军事运输的案例数不胜数。如秦多次通过乌江伐楚;隋开皇二年(582),田宗显奉旨征讨乌江沿岸,在黔地开疆辟土刻石记功;宋大观元年(1107),田宗显十四世孙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内附,继而沿乌江平服湘地叛乱;明洪武十四年(1381),傅德友率30万大军从四川、湖广远征云贵,大量的粮草运输也取道乌江;抗战时期,乌江航运又肩负起了运输军事储备物资的后勤任务,成了抗战生命线。
第二,商贸通道。乌江航运贸易的运输物资以食盐为大宗。南宋绍兴年间,乌江航运上就已出现官船、民船并行运输食盐、贡赋和粮食的现象[ 26 ] 46。夜郎、原川东、黔东北等地,也向来依托乌江航运,实现食盐与沿岸丹砂、煤、茶、漆、桐油等的物资交换。明洪武年间,“令商人输粟于边,给以盐引,令其赴场支盐自行贩运”[ 27 ],大批食盐沿乌江航运销往贵州。清乾隆年间,川盐入黔“涪岸”设立,使得自涪陵上水时大批运进四川井盐,下水时运出沿岸的生漆、桐油、五倍子等土特产品的运输模式开始成型。民国时期,为降低米粮等大宗物资运费,沿线商民致力于开凿乌江上游航线,如思南商人刘云开等成功开通思湄段航道后,“印江布疋、思南雄精,由水运至江界河以达于省。瓮安、余庆之米,原船运至思南,每场河下码头米船常有三四百号”[ 26 ] 174,贸易极盛。
第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路。随着历代乌江航运的发展,大批汉人的进入使沿线地区人口剧增,经济相对繁荣,致使民族结构和居住格局逐渐改变,风气习俗趋向同一,各民族交往交流日益增多,并逐渐呈现交融态势。以明为界,沿线地民族人口结构呈现从“夷多汉少”向“汉多夷少”的转变。明以前,沿线人口多为苗、土家、仡佬等世居民族先民,进入的汉人较少。先秦时期沿线属巴子国,多巴人;汉唐时为荆楚与巴蜀交错地带,土家族与苗族先民“武陵蛮”“五溪蛮”“涪陵蛮”等多繁衍于此;宋时黔中一带亦“多是蛮僚”,分布有仡佬族先民。乌江航运所带来的人员往来、食盐流销与丹砂外运,催生了古思州(黔东北地区)相对繁荣的经济,也奠定了永乐年间贵州建省的物质基础。黔地建省后,明王朝愈发重视对乌江航道的开发,四川、陕西、江西等地的商人、流民等纷纷迁入,“汉不入境”的局面被进一步打破。《思南府志》载,“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移入境”[ 21 ] 103,“自佑恭克服之后,芟荑殆尽”[ 24 ] 19,明中期时“土著之民无几,而四方流寓者多”[ 21 ] 152,其中又以“陕西、江西为多”[ 28 ] 19。到民国时期,民族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已是“合属烝黎,全系汉族,并无杂居之苗”[ 5 ] 41。土家、苗、仡佬等民族先民从“化外之民”变成了“编户之民”,其民族身份在长时间的改土归流中发生了转化,从而逐渐形成了汉人占多数的人口结构。沿线各民族与入迁汉人逐渐呈现出交错杂居的民族居住格局。汉民大量进入之前,沿线世居少数民族本就处于一种杂居状态,《太平寰宇记》称黔州所辖者“杂居溪洞,多是蛮僚”[ 29 ] 89,费州亦“地同黔中,尤杂生僚”[ 29 ] 116。到明时,随着汉人大量进入,思南府“蛮獠杂居,居东南者若印江郎溪曰南客,居西北者若水德江蛮夷,沿河、婺川者曰土人”[ 30 ] 82,已呈现一种“五方杂处”的居住格局。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各民族风俗也逐渐趋向一致。明以前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较少,在风俗上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史书多载“苗、僚、土、客,人民则异”[ 21 ] 159,各族之间“语言各异”,“其性犷悍,其风淫祀”[ 29 ] 89。但随着明朝贵州建省后,大批汉民的迁入,当地风俗大变,原本“民性质俚,俗尚简鄙”的思南府,已是“渐被华风,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悍劲之性,靡然变易也”[ 30 ] 82,“夷僚多效中华,务本力穑”[ 31 ];石阡府仡佬族亦“渐染中华之教”,“其民端庞淳固,以耕殖为业。天资忠顺,悉慕华风”[ 30 ] 108。在与汉人的长期交往中,当地民众法律意识也逐渐浓厚,如思南府境内务川县人持丹砂之利多殷富,“善告讦难治,长吏多不能久比以罪罢去”;印江郎溪土家人,亦“善持长吏之短”[ 30 ] 19-20。
三、乌江航运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文化线路的价值构成可以是多元的、多层次的[ 32 ]。乌江航运见证了乌江航运对沿线地区贸易的贡献,推动了历史上多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具有显著的经济、文化交流与现代旅游价值。
(一)资源交换、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
乌江航运是沟通沿线各民族生计的纽带,使不同经济文化区域之间的资源交换成为可能,汞矿等矿产资源的外运和明清时期大规模的盐油贸易,凸显出乌江航运资源交换、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
乌江航运的发展,率先打通了黔地北入中原的经济走廊,为贵州古代经济的初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明嘉靖《思南府志·地理志》记载,思南府“产朱砂、水银、棉、蜡、漆诸物,皆中州所重”,“上接乌江,下通楚蜀,舟楫往来,商贾鳞集”。航运的发展打破了乌江流域相对封闭的状态,外地人口尤其是汉人的大量迁入,增加了开发乌江流域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农作物引进乌江流域,有力地促进了乌江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经济的形成。
乌江沿岸因航运兴起了众多航运市镇,如武隆羊角、酉阳龚滩、沿河淇滩、思南等,这些因航运兴起的码头市镇为附近民众提供了必要的贸易场所和生存空间。到了清代,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乌江成为“川、贵贸易之咽喉”,主要行销川盐入黔。险滩处城镇居民将传统的耕作方式转变为以搬滩、商贸为生,航路的发展改变了航路沿线民众的传统生计方式。盐的输入也改变了乌江沿岸人民的饮食结构,并形成特色食品产业。贵州素不产盐,境内许多民族都有“望盐生咸”的谚语。明代推行川盐入黔,乌江航运盐运运输兴盛,乌江流域各民族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改变,如榨菜、咸菜、水盐菜、咸鱼、甜酱瓜、盐茶汤等盐制食品也逐渐成为主流。
(二)美美与共、文明互鉴的文化交流价值
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在乌江航运的起点涪陵交汇,通过航路远播乌江中下游地区,沿途不同的商帮又将原籍的地域文化带入航路的码头节点城市,一路与黔、鄂、川、湘边区的土家、仡佬等少数民族先民文化碰撞,最终与位于黔中腹地的古夜郎文明交融。各类人群借助航运之力,构成了乌江航运平等互利、文明互鉴的文化交流价值。
乌江航运在历史上是一条移民通道。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政策性大规模移民和航路上盐运的发展,为乌江流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使不同民族的商旅在沿线贸易与沿岸城镇定居生活,人口和商品的流动带来了盐文化、商贸文化、建筑风格、生产技术、宗教信仰、审美理念、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大量移民涌入形成了许多帮派组织及其聚会活动空间场所。乌江航运沿岸码头型古城镇中兴建起许多地域性的会馆建筑。木船从业者也曾经修建王爷庙祈求船只平安,彰显着乌江航运带来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兴起和互鉴。这些人类文化价值的互鉴充分体现在乌江航运沿线码头型古城镇、会馆、渡口、船工号子等文化遗产上,如思南县有思南府文庙、华严寺、万寿宫、永祥寺。乌江沿岸既有古代土著的悬棺葬、洞棺葬,也有三国蜀汉涪陵太守庞宏墓、唐长孙无忌墓,明四川按察使田秋墓、明理学家李渭墓、明督察院金御史肖重望墓、明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田仰墓等官员墓葬。
乌江航运是沿线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渠道。乌江航运沿线为多民族地区,巴人后裔土家族与濮人后裔仡佬族、苗族为世居民族。土家族先民大部分居住在思南、沿河、德江、印江等县,仡佬族先民主要居住在思南,苗族主要集中居住在黔东北一带。随着乌江航运的发展,汉、彝、苗、布依、侗、白、瑶族等众多民族也不断地进入航路沿线地区,航路带来的人口流动和商贸往来增进了各民族的了解和互信,实现了各民族的团结,乌江航运成为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手段,乌江航运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三)文景合一、历史厚重的旅游价值
乌江航运沿线具有山水旅游的绝佳自然条件。正如民间所道:“乌江两岸山连山,乌江河中滩连滩。”武陵山脉与大娄山脉两大地质板块上亿年的碰撞挤压,形成了乌江鬼斧神工的“V”字峡谷景观。恰处于我国第二与第三阶梯过渡处的崎岖地形,又造就了乌江多险滩、多巨浪的河道环境。但伴随着乌江流域大规模水电建设的尾声,“天险”乌江的湍流恶滩已被驯服为两岸青山、一江碧水的温顺模样。沿岸由夹石峡、黎芝峡、银童峡、土坨峡等众多峡谷串联而成的乌江百里画廊景观不逊于长江三峡。
乌江航运拥有以多民族民俗与区域历史文化调整形成的特色人文资源。沿线为汉、苗、土家、仡佬等多民族聚居区,嗜酸喜茶的饮食习惯、繁杂多样的民族服饰、干栏式的居住方式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共同织就了灿烂的民族风情。受古代航运交通影响,聚落多依乌江而建。大规模水电移民后,羊角、郁山、龚滩等古镇旅游势头正盛,异地复建后的龚滩古镇已经“由自生自长的乌江水埠码头、边贸集市和建制镇行政中心逐渐成长为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存地和渝黔乌江画廊景区核心景点”[33],成了一个具有民族特色和乌江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旅游古镇。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红军的南渡乌江、强渡乌江等血色战役,在乌江航运沿线留下了许多红色文物,如重庆彭水的红军渡、贵州沿河淇滩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遗址、余庆的迴龙场渡口等,均是乌江航道上宝贵的红色旅游资源。
四、结语
乌江航运是一个贯穿川(渝)、鄂、滇、黔边区的民族情感走廊、自然生态走廊和旅游文化走廊,它绵延于川黔之间,带动了我国西南地区大片空间范围的人类交往与流动,为该地区在商品、思想、知识、文化等方面带来了持续不断的交流与互惠。乌江航运跨越武陵山区、大娄山脉崎岖不平的自然地形地貌区域,其间大小险滩密布,纤道、绞关站等助航遗存充分反映了沿线的各民族群众对恶劣河流交通条件的适应和利用方式,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杰出见证与典范。乌江航运具有真实而完整的遗产构成,完全符合马德里会议所提出的文化线路的四个判别标准,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线路。
大运河等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已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已列入《“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①。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视察扬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时指出,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34 ]。乌江航运不仅拥有厚重的航运历史文化,其线路上还存留有大量的渡口、战斗遗址等红色文物,是黔、渝携手两地文旅深度合作的重要人文资源,是沿线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文化支撑。当下应以长江、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立即开展对乌江航运文化线路遗产现状的调查和保护,以避免“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尴尬处境。同时,应增强乌江航运的各界认可度和社会知名度,塑造乌江航运特色文化品牌,推动沿线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使之成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1] CIIC. 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e Route[EB/ OL].(2008-10-04)[2022-05-21]. http://interna-tional. icomos. org/quebec2008/charters/cultural_routes.
[2]黄柏权.武陵民族走廊及其主要通道[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16-21.
[3]龚锐.乌江盐油古道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22-29.
[4]《铜仁地区通志》编纂委员会.铜仁地区通志:卷1地理[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5:196.
[5](民国)思南县志稿[M].马震崑,修.陈文燽,纂.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
[6]徐浩,周惠萍.德江土家族“炸龙”与文化认同[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8(3):96-99.
[7]田永国,罗中玺.乌江盐殇[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173-175.
[8]黄节厚.乌江古代诗词译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9] CIIC. Reports of experts[EB / OL].(1994-11-09)[2022-05-21]. http://international. icomos. org / ma? drid1994/cultural routes.
[10]黄健民.乌江流域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24-27.
[11]覃德清.中国文化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7.
[12]彭福荣,李良品.乌江流域文化概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51.
[13]王绍荃.四川内河航运史:古、近代部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0.
[14]夏述华.涪陵港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16-17.
[15]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194.
[16]政协思南县委员会.思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G].思南:思南县印刷厂,1986:97.
[17]何延应,高仲,冉光明.古镇郁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63.
[18]汪育江.乌江流域考察记[M].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00:152.
[19]王铭铭,舒瑜.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9.
[20]张世友.变迁与交融:乌江流域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08.
[21]嘉靖思南府志:第2册[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
[22]司马迁.史记英选[M].李算,编选.李淑芳,凌朝栋,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28.
[23]余继平.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506.
[24]高伦.贵州傩戏[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2-12.
[25]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91.
[26]夏鹤鸣,廖国平.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
[27]赵斌,田永国.贵州明清盐运史考[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40.
[28]嘉靖思南府志:第1册[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19-20.
[29]乐史.太平寰宇记:第29辑[M].影印本.南京:金陵书局,光绪八年(1882年).
[30]赵瓒.弘治贵州图经新志[M].沈庠,修.赵平略,邢洋洋,赵念,等点校.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31]谢东山.(嘉靖)贵州通志[M].张道,编集.张祥光,林建曾,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138.
[32]李伟,俞孔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J].城市问题,2005(4):7-12.
[33]刘安全.少数民族古镇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实践与逻辑——以酉阳龚滩建设特色旅游小镇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131-138.
[34]袁媛.大运河是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N].新华日报,2021-01-26(17).
作者贡献声明:林婵娟负责撰写与修订,李然负责指导。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Wujiang Waterway Rout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Ex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LIN Chan-Juan, LI R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Abstract:Cultural route is the heritage expression of ethnic exchange,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it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build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ith the theory of cultural route,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heritage of the shipping system of the Wujiang rive through literature colla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hipping system of Wujiang river is composed of rich types of heritage and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routes. It is a cultural route worthy of the name, which can be called Wujiang waterway. By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Wuji? ang waterway,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heritag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outes for the research of inter-extensive promotion of ethnic ex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Key words:Wujiang river basin; cultural route; ethnic ex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赵庆来)
①交通运输部,发改交运〔2007〕1370号:《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
①国院办公厅,国办发〔2021〕43号:《“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