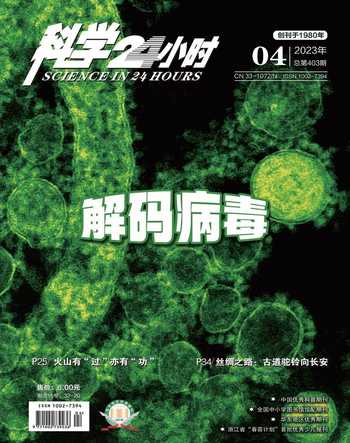与病毒共存
2023-04-07一宁
一宁
提起与病毒共存的观点,不少人都觉得不现实。病毒的存在就是为了繁衍和传播,而这一切都是要以破坏宿主细胞为基础的。对人类而言,病毒的流行不仅会导致个体的死亡,而且还会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
尽管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进步,我们对病毒的认知在不断深入。而医药卫生领域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遏制了病毒对人类的影响,但是,诸如艾滋病病毒、新冠病毒、狂犬病毒等病毒,仍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健康风险。而现阶段,由于缺乏有效的针对性药物,我们仍无法在短期内战胜这些病毒。因此,与病毒共存的话题也在不断被热议。
理论基础
病毒的进化历程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的种类数量是巨大的,在自然环境中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呼吸的空气、触摸过的物体,就连我们的体内都有病毒。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病毒都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构成威胁,它们也有“好”与“坏”之分。其中,对人类和动物有害的病毒,只占非常少的一部分。
与病毒共存是有理论基础的。无论你愿意与否,自人类起源至今,已经和病毒打了至少25万年的交道。在这些时间里,病毒始终在不断变异。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病毒的存在促进了物种进化。科学家发现,病毒能将基因整合到宿主的细胞中,其中部分核酸链为DNA的病毒基因片段可以成为宿主核酸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基因的功能还不明确,但是从进化学的角度来看,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有观点认为,人类与黑猩猩之间存在着5%的基因差别,这差别有可能源于在进化过程中二者感染的病毒存在差异。还有研究发现,在人类的基因链中存在着病毒基因的片段,这或许就是病毒与人类博弈时留下的痕迹。
病毒的存在完善了人类的免疫系统。病毒感染人体后,多数情况下会在一定时间内被清除,这个过程的实现得益于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的发挥。免疫系统是有“记忆能力”的,它会对感染的病原体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免疫记忆,下次再遇到相同的病原体,就可以快速识别,合成免疫细胞,分泌免疫因子,并最终将病原体消灭。尽管这种免疫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但就如同温室里的花朵是无法经受住风雨的洗礼一样,人体的免疫系统只有在病原体的不断锤炼下才能够更加成熟和完善。
现实选择
就现阶段人类的医疗科技水平而言,想要在短期内战胜并消灭病毒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病毒划分“三六九等”,针对不同类型的病毒,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一方面,人类已学会利用病毒。研究者用完全活性的病毒制作疫苗。人类通过接种疫苗,刺激免疫系统产生针对病毒的武器——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这对于降低那些高致病性的病毒的危害性有重要的作用。18世纪,天花病毒肆虐,100年间欧洲因天花死亡的人数高达1.5亿。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明的牛痘疫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疫苗。

1915年,英国科学家从痢疾康复患者的粪便中分离的噬菌体,成功治愈了2名痢疾患儿,这是人类首次利用病毒战胜细菌。由于噬菌体具有特异性强的特点,近年来逐渐被用于对付“超级细菌”。利用病毒喜欢钻入宿主细胞的特点,腺病毒、逆转录病毒、慢病毒等病毒还被作为载体应用于医学领域(被称为“病毒载体”)。在病毒载体的基因中“插入”某种目的基因,让它们“运输”目的基因到细胞中,使插入的目的基因能够在细胞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一方法在基因治疗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某些病毒还被作为精确制导药物的载体和特效杀虫剂。病毒的应用领域正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人类尽力遏制有害的病毒,减少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每一种病毒都有特定的传播规律,这个规律既包括了传播途径,也包括了流行趋势,以及造成的危害。我们对病毒了解得越少,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就越大。反之,我们越熟悉它,就越能掌控甚至消除它的影响。
《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中曾有记载:“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这段文字阐述了传染病对人群普遍易感,在人际间可以互相传染且症状相似的特点。传统的传染病预防措施通常有两种:一要“正气存内”,即增强身体免疫力;二要“避其毒气”,即避免接触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现代流行病学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又总结出了一套防疫策略,例如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这些防疫策略在对抗病毒流行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疫苗的出现,为人类最终战胜病毒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尽管现阶段人类在这方面能做的工作十分有限,但已经成功地消灭了天花病毒。
人类与病毒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新型病毒不断出现,对人体健康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如果想要实现共存,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要学会敬畏自然。在目前已知的可以导致人类感染的病毒中,有75%来自其他动物,通过物种间的各种交互,病毒很容易在物种间迁移。其中,蝙蝠是“最大的病毒库”。一方面是因为蝙蝠的数量巨大;另一方面,同为哺乳动物,蝙蝠与人类的基因序列比较相似,因而蝙蝠携带的病毒更易于在人群中传播。此外,自然栖息地的破坏,导致野生动物进入人类社会,狩猎、宰杀、食用野生动物,也会造成人类感染病毒。例如令人闻之色变的埃博拉病毒,最大的可能来源是灵长类动物或蝙蝠。而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减少接触野生动物和未知动物,以及给易患人畜共患病的家养宠物和牲畜定期注射疫苗,降低病毒向人类迁移的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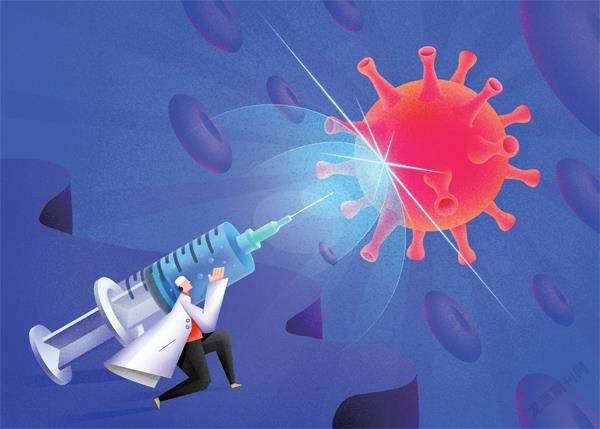

二是充分掌握病毒的流行病學规律,做好新型病毒的监测。对于病毒来说,传播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自然选择在病毒毒性和传播之间进行了平衡,最终那些毒性足够大但又不会杀死原始宿主的病毒会生存下来。因此,我们应对的关键点,就在于对已知的病毒做到充分的了解,包括它的天然和可能的宿主、传播的途径、易感人群,以及季节和地区的流行特点,监测每年病毒流行趋势的变化和新型病毒的情况。然后,利用这些数据提早作出预判,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和早治疗,降低其影响。
三是积极做好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尽管人体的免疫系统在对抗病毒感染方面已经非常出色,但是病毒变异逃逸与人体的免疫系统,就像是一场永恒的“猫鼠游戏”。病毒在自然流行的过程中发生的突变,可能是在感染人体的过程中,与免疫系统相互抗争的过程中发生的,也有可能是病毒本身在适应人体的过程中引起的突变。所以,要想做到有效制衡它们,还是要靠疫苗和特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