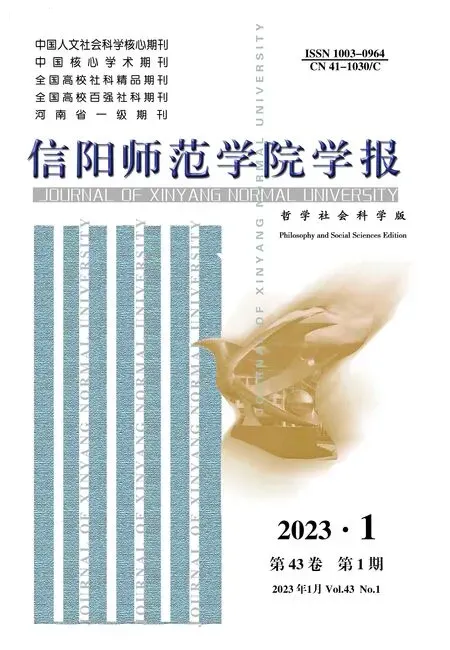炎黄学学科化建设又添力作
——《炎黄学》序
2023-04-06王震中
王震中
(1.信阳师范学院 炎黄学研究院,河南 信阳 464000;2.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霍彦儒先生大作《炎黄学》即将面世,尊嘱作序,我深感欣慰。一是感到从炎黄文化走向炎黄学,符合 “新文科”发展的时代需求;二是感到建设炎黄学需要学者们多方面的努力,霍先生的《炎黄学》是一力作;三是感到《炎黄学》问世也是霍先生对自己几十年从事炎黄文化研究的一个总结和升华。
说到炎黄学学科建设,就会使我们想到提出创建炎黄学的事情和信阳师范学院于2017年12月成立炎黄学研究院的事情。
提出创建炎黄学前后有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霍彦儒先生于2007年4月初在西安召开的一次“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炎黄学”这样一个概念(参见霍彦儒《炎黄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朱恪孝、谢阳举主编《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页);随后于2010年6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陕西黄帝陵基金会、湖南炎帝陵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主题为“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的学术研讨会,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新时期以来炎帝与炎帝文化研究扫描》一文中,霍先生又一次提出了创建“炎黄学”学科的建议,并在大会发言中,对创建“炎黄学”学科的意义做了说明(参见霍彦儒《新时期以来炎帝与炎帝文化研究扫描》,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论坛组委会学术组编《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2010年版,第64页)。在此会上,还有一位陕西学者也提出了创建“炎黄学”的议题(参见李养民《炎黄文化研究的哲学思考》,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论坛组委会学术组编《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2010年版,第79页)。这是关于炎黄学概念的提出。这时霍先生所说的“炎黄学”只是学问之学,还没有涉及“学科化”的议题。
提出创建炎黄学的第二个阶段,是与信阳师范学院2017年12月成立炎黄学研究院联系在一起的。2017年12月23日,在原河南省委书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徐光春先生的支持下,在时任信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宋争辉、校长李俊等领导的主导下,信阳师范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炎黄学学科建设暨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炎黄学研究院,旨在推动以炎黄学为代表的国学学科化进程。信阳师范学院在成立炎黄学研究院之后的第2年开始,即从2018年9月新学年开始,以大学本科二、三年级必修课的方式开设了“炎黄学公开课”,并着手编写《炎黄学概论》,《炎黄学概论》还获批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炎黄学概论》分“学术版”和“教材版”两种,由李俊和王震中主编的学术版《炎黄学概论》,于202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教材版的《炎黄学概论》初稿已成,正在加工完善之中。正如我们在《炎黄学概论》的《绪论》中所说的那样,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建设的“炎黄学”是“学问”之“学”与“学科”之“学”的结合;这种“把传统文化学科化的做法,使教与学、教与研有机统一,使炎黄文化研究真正进入高等教育课程体系,迈开了把传统文化从‘学问’之学转为‘学科’之学的坚实步伐,推动了以炎黄学为代表的国学学科化进程”。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成立之后,霍彦儒先生被聘为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参与炎黄学学科建设之中,并承担《炎黄学概论》两章的写作,为炎黄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现在,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在李俊校长的直接领导下,已建成河南省特色优势学科,继《炎黄学概论》出版之后,正在组织撰写一套颇具特色的“炎黄文化研究丛书”,力争使以炎黄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科化建设又上新台阶。
设立炎黄学、让炎黄文化走向学科化的举措,是重要的、必要的,也恰逢其时。就其重要性和必要性而言,正像我们在《炎黄学概论·绪论》所指出的那样:
炎黄文化研究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炎黄文化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三种类型:一是对部分资料的整理,例如,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两位原副会长李学勤、张岂之主编的八卷本《炎黄汇典》;二是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授、学者以及地方上的研究人员进行的带有学术性的研究;三是被称为“民科”的民间文化人的研究。上述第一类属于资料性的基础工作。第二类虽然说多数是带有学术性的,但这些研究与教学脱节,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各地的研究是散点式的,缺乏总体规划,很多成果无法得到系统性的总结,无法将不同成果内在地联系成一个整体。
多年来,上述这些问题属于结构性的,它们在炎黄文化研究的旧有的模式与框架下只是反复出现,不断重演,而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要求我们从结构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我们找到了在大学创建炎黄学学科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炎黄学学科的建设,以学科为依托,通过学科平台,这些顽症才能得到解决。这是创立炎黄学的一个重要意义与价值所在。
炎黄学学科建设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把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建立在文化自知的基础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了“文化自信”,并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富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我们知道,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知。炎黄学学科建设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自远古而来的文化特质,是一项基础性的建设,也就是说,炎黄学学科建设有利于我们把炎黄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炎黄精神与中华精神的关系、炎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讲清说透,从而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来达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诚然,在由“文化自知”而达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一点上,以往的炎黄文化研究也有近似的作用,然而它远不如利用炎黄学学科建设这种方式更有意义。炎黄学与炎黄文化研究这两种方式,在培养和增强文化自信、自觉上,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炎黄学是把我们对炎黄文化的自我认识,放在科学的、系统的学理基础之上,来进行学术建树、学科建设和文化弘扬的。所以,炎黄学凸显了炎黄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只有在科学性和系统性基础之上,才能实现从“文化自知”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也是我们把炎黄文化研究提升为炎黄学的另一价值所在。
我们说的恰逢其时,是说炎黄学走向学科化建设有时代契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2014年,习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2015年2月,习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说:“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轩辕黄帝陵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对历史文化要注意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学术交流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2019年,习总书记在《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9月27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讲到“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在讲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时说,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意见》,提出“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公开课”等。显然,习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两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意见》吹响了包括炎黄学在内的国学学科化的集结号和动员令,成为炎黄学走向学科化建设的时代契机。
在这样可喜的形势下,霍彦儒先生完成了他的《炎黄学》著作的写作。在书中,霍先生满怀热情地阐述了炎黄学学科研究的设想、内容与方法,并把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炎黄学涉及的所有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排比和鉴别,既包括地上的文献资料、民间传说,也包括地下的考古学资料。第二个层面是在各种资料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炎黄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思考、研究和建设。第三个层面结合时代之需要,进行炎黄文化的“转化”和“发展”,使蕴含其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为今天的现实服务。我认为这样的划分是科学合理的。
为此,霍先生设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两个中心”,即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二是建立“两支队伍”,即专业研究队伍和业余研究队伍;三是搭建“两座平台”,即社会普及炎黄文化平台和大、中、小学校普及炎黄文化平台。
炎黄学研究是一项长期的科研工作,需要有两个中心来支撑。有了研究中心或基地,才能将各方面研究人员组织起来,使研究工作长期有序开展下去。霍先生说,河南信阳师范学院依托本校文学院,挂牌成立了炎黄学研究院,并邀请全国十多位从事炎黄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组成炎黄学学术委员会和研究队伍,多次召开座谈会,启动了炎黄学的研究工作,完成并出版了《炎黄学概论》一书,还在信阳师范学院的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的本科、研究生中讲授炎黄学公开课,在“两个中心”建设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霍先生希望今后应着手建立资料库,收集古今以来有关炎黄及与炎黄有关的所有资料,包括文献、考古、民俗、民族以及近现代以来有关炎黄文化研究的论著等,并建立炎黄学数据库。当然,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
之所以要建立“两支队伍”,即专业研究队伍和业余研究队伍,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实践表明,炎黄文化的研究需有两支队伍:其一是专业的,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为基础,以从事学术、理论研究为主;其二是业余的,即民间的,是以炎黄文化传播地的专家学者和民间爱好者组成,是以民俗和应用研究为主。业余的民间的这股研究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后,各地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更多的是由地方业余专家学者和民间有关人士较早介入,开始研究、宣传,并逐步扩展至专业人士的研究介入。所以,在炎黄学研究中,虽则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理论研究,但也不能离开民间的民俗、传说等的应用性研究。
关于搭建社会普及炎黄文化平台和大、中、小学校普及炎黄文化平台,可以是举办“炎黄论坛”的形式,也可以是讲座的形式。“炎黄论坛”不仅是开展炎黄学研究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而且也是普及炎黄文化的有效形式和途径。近年来,一些地方如陕西黄陵、宝鸡,河南新郑,湖北随州,山西高平,湖南炎陵等地依托炎帝、黄帝祭祀活动,多次举办炎黄论坛和讲座,向当地机关干部、大中小学生和群众普及炎黄文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把炎黄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炎黄文化是指炎黄二帝及其时代所创造的文化;广义的炎黄文化是既包括炎黄时代亦包括炎黄子孙所创造的文化,这就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通观《炎黄学》全书,前八章是站在狭义的炎黄文化的角度写的,后五章是站在广义的炎黄文化的视角写的。前八章是:第一章炎黄与炎黄族的起源、时代和生态环境,第二章炎黄二帝的生葬传说,第三章炎黄二帝的称谓、族姓和形象诸问题,第四章炎黄二帝的谱系传说,第五章炎黄与“三皇五帝”暨司马迁“五帝观”,第六章炎黄与炎黄族的迁徙,第七章炎黄时代与中华文明之起源(上),第八章炎黄时代与中华文明之起源(下)。后五章是:第九章炎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肇端,第十章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第十一章炎黄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第十二章炎黄祭祀与历史现实意义,第十三章炎黄与炎黄文化研究概述。在这十三章中特别是前八章中,霍先生在充分叙述前人研究或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研究,也汇聚了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这样做是可取的:既尊重了别人的研究成果,又阐述和论证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这是著书立说最基本的要求。我对霍彦儒先生在炎黄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对炎黄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努力、对炎黄文化和炎黄学的情怀,深表敬佩,并以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