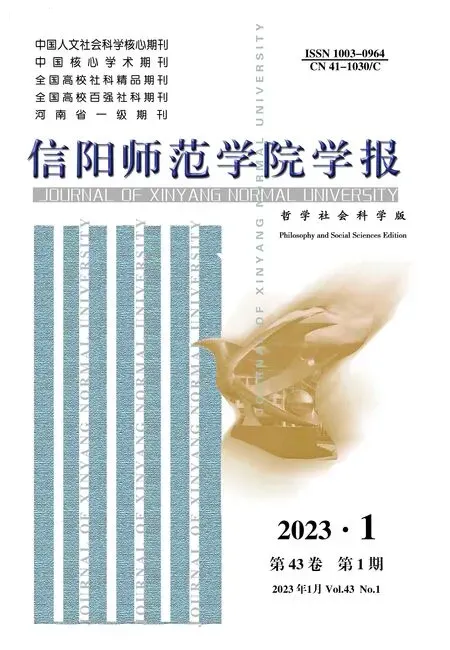从接受美学看鲁迅小说创作
2023-04-06董琼
董 琼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新文学开始于晚清,发展至五四时期蔚为壮观,这种变化与这一期间读者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的。“重要的并不在于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文学诉求是什么,而是这种文学诉求是否拥有广泛的接受主体”[1]100。现代接受美学着意突出读者的接受意识与再创造在文学价值实现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鲁迅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重视读者接受的作家之一。在他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2]73这里强调了“读者”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否则,作者的一番辛苦只能化作孤芳自赏。鲁迅复出文坛,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是因发生在S会馆中有关“铁屋子”的争论,“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3]441,在这声“呐喊”中,我们分明感受到文学创作主体(隐含的作者)欲与潜在的读者交流的姿态。
一
文学作品离不开读者接受,而读者对作品的基本态度和评价又取决于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作家在创作作品时应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而期待视野在每个年代,标准又都不同。拿现代文学期刊来说,它的读者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一般读者,其购买与阅读,乃纯粹的文学消费;另一种则是理想读者,不只阅读,还批评、传播、再创造。如果举例,前者为上海的店员,后者则是北京的大学生。”[4]119在文学传播中,传播的内容不能过高于读者的接受习惯和能力。在一个觉醒者尚不能达到一定数量的时代,很难实现传播的有效性。对此,鲁迅有着深刻体会,如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就因没有引起读者“共鸣的心弦”,以致销售冷落,无法再版。时间到了五四前夕,读者主体的悄然变化[5]20,作为鲁迅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尽管其“独白”式的心理描写跟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结构相去甚远,然而“这种几乎没有故事情节、全凭个人心理分析来透视社会、历史、人生的‘独白’,对于急于宣泄情感、表达人生体验及社会理想的年轻一代,无疑是最合适的”[5]117。应该承认,鲁迅小说“独白”体创作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而且其带浓厚抒情色彩的表达也打开了现代作家和读者沟通与交流的新渠道。
在鲁迅小说中,以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题材为主,这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独创”。但我们也注意到,鲁迅对乡村及乡村生活并不熟悉,不仅小说中有关乡村生活的描写少之又少,而且鲜有乡村生活的气息,其笔下的乡村人物,如七斤、闰土、阿Q、祥林嫂等,基本与鲁迅同龄,无法涵盖农民群体,甚至几乎没有一个乡村青年主人公。这确实是鲁迅创作的“硬伤”。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他深切认识到乡村对于现代中国变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久居在外的生活,故乡对于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事实上,自年少在外求学,后久居城市,他无缘涉足乡村,自然也就无缘涉足真实的乡村生活及无法真实地进行乡村青年人物的塑造。那为什么鲁迅会毅然决然选择此类题材呢?“时代精神逐渐转化为审美的潜在的读者,不知不觉地进入作家的心灵,暗中制约着他的创作动机。换言之,时代精神不是直接支配作家的,而是通过某些中介环节间接地决定创作过程的,潜在的读者当是最重要的中介之一”[6]205。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的选择。五四新文学的主人公虽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但潜在的读者却不是普通农民(以农民为主要读者,以小学为平均接受能力的文学,是从延安以后开始的)。鲁迅笔下的乡村是写给五四青年读者及知识分子看的。有学者将鲁迅小说视为“民族寓言形式”的写作,它原本就是基于知识分子的立场,为知识分子而写的小说,是为城市读书人而构筑的现代乡土中国的生存图景。
然而,1919年的鲁迅已38岁,“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3]441,“寂寞”与“沉寂”构成他生命的底色。可是面对青年读者,“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7]54。正是对读者的重视,他声称,虽然“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但仍“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于是乎“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8]469。如他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3]441。如果说初入文坛,“光明的尾巴”是鲁迅告慰读者的方式,多少还带有象征的意味,那么在后来的作品中,鲁迅则更多传达出一种“怀疑一切”的姿态,他甚至对绝望也提出了质疑,直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相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所以,在他“离开-归来-再离去”,抑或“置身其中,边走边看”,鲁迅以一种“行走”的姿态传达出作家个体自我的生命体验以及“反抗绝望”的力量。然而鲁迅也直言“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9]301,但他也不相信所谓的青年的“前辈”和“导师”,他只确定人生的终点——坟,至于在从此到那的道路,包括他自己也在寻求。鲁迅从不以长者自居。他不仅把批判的目光指向庸常大众,甚至也指向了“我”——城市读书人。如果说《新青年》的其他同人崇尚振臂一呼式的绝对“言说”,鲁迅的姿态显然要低得多。他以呐喊者的身份,以小说的方式切入,更注重从现实现象或事件引申到国民性问题,这正是鲁迅的深刻而伟大之处。纵观鲁迅的创作,不论是封建礼教的问题、头发的问题,抑或“一件小事”,他都从读者的视角,理性的目光来审视现实,鲁迅在小说中很少宣教,他以医生的解剖式的方式让读者一点点接近事实真相、人性的本质。从这一点上看,鲁迅更像一个启蒙者,然而和五四时期所崇尚的先知者对后知者的思想教化的启蒙不同,鲁迅更接近于康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去“启蒙自己”。“人内心中最重要的革命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状态中走出’。他不再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别人为他思维,他则只是模仿或者让自己依靠襻带被引导,现在他敢于用自己的双脚在经验的地面上向前行走,虽然还摇摇晃晃”[10]223。这就是启蒙,任何时候都遵循自己思维的准则就是启蒙。鲁迅没有选择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启蒙者”来启“被启蒙者”,而是引导读者用一种启蒙的眼光,敢于在习以为常的庸常中,在人生终点的思索中,用理性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有学者在研究冰心创作的影响时,对当时的读者有过这样一段分析,“她是以什么建筑了自己在读者间的根基呢?这是可以分作两点说的。其一,当然是由于思想上的原因。……她的倾向是反封建的,但在她的观念形态中,依然有封建意识的残余。这情形,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青年中普遍的情形。在旧的理解完全被否定,新的认识又还未能确立的过渡期中,青年对于许多问题是仿徨无定的,是烦闷着的。冰心作品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情形,她抓住了读者的心”[11]400-401。如果说冰心以贴合同龄读者的方式创作,那么作为年长者的鲁迅,面对早已隔代的读者,又是采用何种方式来启迪他们用理性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的呢?从这一思考出发,不难发现,鲁迅小说中普遍采用的“看/被看”“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小说模式显然更贴合读者观察现实、深思自身的需要。如在“看/被看”的模式中,《示众》颇为典型。全篇只有一个看犯人的场面,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看别人”与“被别人看”,烘托出具有象征意味的氛围,而对读者来说他们都是被看的内容。因此,不仅有叙事者所讲述的小说人物的看与被看,而且有隐含的作者与潜在的读者的看。隐含作者借叙事者冷静客观的直视,向潜在的读者传递出看客们的麻木与残酷,让后者直逼病态的社会现实,在心灵的震撼中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深入的思考。事实上,鲁迅有很多小说是从《示众》中“看与被看”模式中生发出来的,所以不论是作为被看者的祥林嫂、孔乙己与作为看者的庸常大众之间的“看与被看”,还是先驱者与群众、“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看与被看”。透过叙事者有距离的旁观叙事,读者体会到隐含作者情感的真挚与思想的深刻,由小说外在的理性与冷静感受到一种内在的深刻与苍凉,进而启发他们用理性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一切。
同样,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中,也暗含隐含作者与潜在读者的交流。一方面前面我们也提到,鲁迅作品的潜在的读者基本是五四青年与城市知识分子,他们和鲁迅相仿的求学经历,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即使多年离乡,仍满怀着对故土的反思与追忆,这无疑是鲁迅作为隐含的作者与潜在的知识分子读者不约而同的叙事选择。另一方面在叙事结构上,这类小说由他人故事与“我”的故事所共同营造出的复调小说形式,也更便于向潜在的读者传达出隐含作者的所思所想。小说既写的是他人也写的是“我”自己(包括隐含的作者及潜在的读者)。如在《祝福》中,小说中祥林嫂和鲁镇的关系是叙述者讲述的重点,它向世人揭示了“礼教吃人”的主题。除此之外,小说也展开了“我”和鲁镇的故事。“我”清醒于跟鲁镇不再相容,早已“决计要走”,但“我”与祥林嫂的相遇,后者无意中对“灵魂有无”的拷问,让作为归乡的知识者的“我”不得不在支支吾吾中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由此深刻反思“我”与鲁镇精神上的内在联系——“我”的逃离何尝不是一种逃避?这显然是鲁迅通过隐含作者的反思向潜在的读者要传达的信息。
二
文学活动的展开,离不开文学创作主体与潜在的读者(隐含读者)的交流,同时也只有经过读者的接受,才能形成审美对象并实现作品的价值。
看鲁迅小说,不论是“狂人”、阿Q、祥林嫂等主要人物,还是杨二嫂、卫老婆子等次要人物,还是诸如“老东西”“小东西”这样符号化的人物,他们无一例外的性格鲜明,极富表现力,然而有关他们的来历、生平及籍贯,甚至姓名,读者却一概不知。小说对人物有距离的观照,它不是通过人物生平事迹,而是通过典型事件及人物情感状态,也包括景物、场面、细节等方面的对应关系的建立,由此激发起读者心灵中与主体相一致的情感形态。如在《药》中,不管是直接出场的华老栓一家,还是借茶客言谈出场的革命者夏瑜,对读者来说,他们的性格是非常模糊的,然而却丝毫不影响由作品情感氛围的清冽逼人所感受到阴冷逼仄。不仅如此,这种主体情感的确立不是以一种“大胆的自我暴露”“忧郁感伤的自我抒怀”表现出来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含蓄内敛的情感力量。读鲁迅小说,仿佛有个自己对他笔下的人物深沉思索的创作主体,虽然表面上是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却熔铸着创作主体刻骨铭心的生命印迹及审美感悟。然而,这也为他的读者在解读他的作品时带来了困扰。一方面为强化作品主体情感的投射,小说势必淡化情节,减小形象描写的密度,从而导致形象自身以及形象与形象之间的“空白”增大,产生类似于古典诗学中“象外之象”的审美功能,而这需要读者调动超越形象自身限制的想象,弥补这一空白。另一方面在意义上的内敛含蓄,意味着主体意义被隐藏于形象的深层,尽量不让意义脱离形象直接表达出来,而这需要读者透过形象本身来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而这两方面势必对读者的阅读经验及审美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在《示众》中,仅仅是庸众看客看犯人的场景;在《头发的故事》中,仅围绕着头发问题发生的争执;在《离婚》中,也仅是对爱姑离婚事件的描述。然而,这些描写却深深蕴含着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这类作品感到不知所云是不足为怪的。
前面我们也提到,普通读者并非鲁迅关注的重点,鲁迅自己也深知,“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12]70。但面对作品与普通民众难以互应的情况,鲁迅不媚悦大众并不意味着放弃大众。基于不同层面的读者,鲁迅通过设定不同层面的叙事结构,来实现不同层面读者的阅读接受。以《狂人日记》为例,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狂人的十三则日记,却忽略了小说开头的文言序文。事实上,在这段序文中,隐含着作者对潜在的读者不同层次的预设。在一般读者看来,这段序文是告诉大家,《狂人日记》全篇语无伦次,是狂人思想的意识流,有悖于传统文学的审美规范。小说透过自剖式的心理“独白”与亦癫亦狂的话语呈现,无疑向读者表达出对现实世界的颠覆,以此“揭露封建家族和礼教的弊端”。但小说除了这一层面的读者,作者更寄希望于后者——医家。当然这里的“医家”并非指医学工作者,而是有志于探讨“国民性改造”的潜在的读者。在序文中提到本文对狂人日记“撮录”并“一字不易”,但二则变十三则,在编选上,存在着一个怎样选择的问题。狂人因发现封建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而被庸众甚至家人视为“狂人”,在读者来看,狂人越来越清醒的时候,却是叙述者笔下庸众视其为愈来愈癫狂的时候。狂人与庸众互为偏执,谁也没办法改变对方。然而,鲁迅既不是站在狂人的立场上去抨击众人,也不是站在众人的立场上来抨击狂人,而是透过所谓冷静客观的“撮录”,表现出对狂人与庸众的双重否定(序文提到狂人愈后“候补”就是叙述者“余”对狂人的否定)。与此同时,小说也暗含着隐含的作者对“余”的否定。在文言序文中,只有“余”的声音而狂人沉默,而在白话正文中,只有狂人的声音而“余”沉默;在文言序文中,“余”称狂人愈后赴某地候补,而在白话正文中,狂人的清醒在庸众来看是愈加的癫狂。况且,“余”归来时狂人已离开,俩人唯一的交集只是那两册日记。“余”所谓的狂人“正常”是真的正常吗?即便“正常”了,这个正常的过程“余”却丝毫没有交代。小说所呈现出的两种叙述、两种观点暗含着隐含的作者对叙述者“余”的否定,也正是在否定与颠覆中完成与“医者”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应该说,小说由文言序文与白话日记所构成的并不完全吻合的叙述隐藏着作者对不同读者寄寓着不同的叙述意图。对一般读者而言,隐含作者通过狂人之口痛斥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并借庸众对狂人的压制隐喻“铁屋子”的万难破毁,由此完成对一般读者揭露封建礼教弊端的目的;而对“医者”,即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城市读书人而言,隐含作者通过叙述者“余”文言和白话的并不完全吻合的叙述,暗含着对叙述者本身的否定,从而与智性读者完成有关启蒙者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在《孔乙己》中,小说的多层主题意蕴同样透过孔乙己、叙述者咸亨酒店的小伙计即“我”以及掌柜、众酒客等三类人物所构成的多重叙事结构的“否定之否定”得以展开。文中那个满口“之乎者也”又懒惰迂腐的孔乙己形象,很容易引发一般读者对封建科举制度及封建教育制度对人的戕害的思考,同时小说通过酒店小伙计“我”的视角来观察酒馆的一切,不仅穿短衣帮的众酒客对孔乙己遭遇的冷漠与讥讽,而且在否定孔乙己的同时也否定了一般民众的“苦人的凉薄”,而本应童真无邪的“我”对孔乙己及众酒客事不关己的冷静直视,儿童视角沾染上成年人世界的冷漠无情,对这一视角的否定同样揭示出民众荒芜冷漠的看客心理以及国民性改造的艰难。应该说,鲁迅小说正是透过叙述者对人物的否定以及隐含作者对叙述者的否定的否定,有效地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体验。对一般读者而言,叙述者对故事人物的否定,以此揭示封建礼教的弊害,从而激发读者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而对智性读者而言,隐含作者对叙述者的否定的否定,则是和智性读者进一步探究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不仅如此,这一否定之否定不仅指向他人,更指向自身。就如在《一件小事》中,隐含作者对“我”对车夫行为的否定的否定;在《祝福》中,隐含作者对“我”对祥林嫂的否定的否定;还有在《伤逝》中,隐含作者对涓生对子君忏悔的否定。鲁迅以一种彻底否定的精神,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所以,鲁迅基于“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可以说是对城市读书人灵魂的巨大拷问。
鲁迅执着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13]631,然而另一方面,“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4]163。鲁迅在“顾念读者”与“抒写自我”之间矛盾与纠缠,实际上也是启蒙理性与个人情感的碰撞与纠结。于是,我们看到,当启蒙理性居于主导地位时,对国民劣根性及奴性的抨击与嘲讽占据上风;而当个人情感溢出理性的范畴,感伤悲悯的人伦之情悄然冲淡了批判的锋芒而趋于低回缠绵的哀婉彷徨。“呐喊”与“彷徨”共同构成了鲁迅小说的艺术基调(由这一点来看,从《呐喊》到《仿徨》也表现了在理性批判之后,鲁迅对现实处境及精神情感关系更深切的感悟)。而不论是哪一种形态,理性精神与文化情感的同时存在,它们的碰撞与融合,使其小说叙事呈现出双语对话结构,它以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和隐含作者的意识结构为主导,透过作家(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读者)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的介入,或偏重于启蒙理性的审视,或包蕴着对传统人伦之情不由自主的留恋,然而这却是鲁迅作为一个以文化批判与思想革命为己任的现代知识分子所必然做出的叙事选择。“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5]338,这声音不仅仅是鲁迅的,也是一个以文化批判与思想革命为己任的现代读者所必然面对的真实。
鲁迅曾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历史中间物,“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9]301。在积习与新知面前、在庸俗与开化之间,“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在希望与绝望的矛盾冲突中,“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9]302。作为历史的中间物,鲁迅不愿做应者云集的英雄也不愿做替人引路的导师,他的小说与五四时期一代人最深刻的焦虑与思索联结在一起,他更愿意在旧壁垒中引出希望的种子,从庸常大众中滋生出理性的力量。总之,鲁迅小说印刻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五四时期一代人最深刻的焦虑与思索,其作品闪烁着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光芒和真挚热诚的情感力量,无疑是现代中国民族和文学进入历史青春时必有的情感标记和心理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