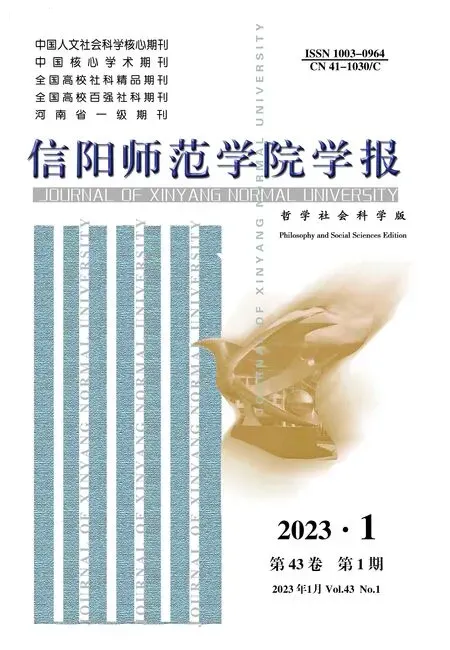明清小说中的夜读书写探析
2023-04-06许中荣许中康
许中荣,许中康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一、引言
夜读作为古代文人的日常活动,在各类典籍中记载较多。史书中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故事,至今我们仍耳熟能详。这一日常活动进入文学领域,也成为文人咏叹、追忆与想象的对象,有着较为丰富的文学表现。“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颜真卿《劝学诗》),是苦志勤学的典型场景;“耿耿一灯明,虚室意潇洒”(朱霞《寒夜读书》),构成别有韵致的文人夜间生活图景;“怜我青灯常寂寞,泥他红袖细商量”(管斯骏《题查履光〈红袖添香夜读书图〉》),寄托着古代文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独特文化心理;“青灯有味似儿时”(陆游《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充盈着古代读书人对童年夜读生活的美好回忆。
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中的夜读书写已有关注。莫砺锋的《陆游“读书”诗的文学意味》认为陆游擅长写夜读情景的奥秘,在于“并未把目光局限于书斋之内,而是注视着书斋四周的整个环境”,让“读书”诗“具备了声响、色彩”而呈现出勃勃生机[1]。夜读离不开书灯,“再挑灯火看文章”,薛涓的《宋诗书灯意象研究》等文章对书灯意象的源流,特别是宋诗中书灯意象凝聚的功名情结、居家自适、人生失意、生命流逝等人文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林雨鋈的《王安石的读书诗与书斋生活》则通过剖析王安石“将仕途失意寄托于苦读生活”的夜读诗创作,探讨其以“青灯”勾勒夜读情境的审美趣味[3]。张含的《蒲松龄的夜读书写及其苦乐传达》从诗稗互渗的视角对蒲松龄诗文与《聊斋志异》中夜读书写的苦乐差异进行了颇有新意的解读,特别是就《聊斋志异》对诗歌夜读书写“化苦为乐”所传达的幻象救赎取向的讨论,是当前为数不多的对古代小说夜读书写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4]。当然,上述散点化的研究对于古代文学中丰富的夜读书写而言尚远远不足。夜读书写的源流、各体文学中夜读书写的异同与互渗、夜读书写的性别差异及其表现、夜读书写蕴含的文人心态等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明清小说中有大量的夜读书写,如《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中的关羽夜读、第四十七回中的庞统夜读,《红楼梦》第四十五回中的黛玉夜读,《儒林外史》第十六回中的匡超人夜读、第二十一回中的牛浦夜读等,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情节。文言小说中的夜读书写更加普遍,如《聊斋志异》中的《绿衣女》《鲁公女》《聂小倩》等有十余篇涉及夜读书写,其中志怪者,有《陈锡九》《青凤》;遇艳者,有《连琐》《聂小倩》《小谢》《鲁公女》《书痴》《青梅》《绿衣女》《白秋练》等。《子不语》中的《鬼魂觅棺告主人》《匾怪》《汤翰林》《狐鬼入腹》《阿龙》《狐生员劝人修仙》等6篇涉及夜读书写,均为志怪故事。《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卷四“陈执礼”、卷六“徐编修”、卷十一“戈廷模”、卷十三“郭彤纶”、卷十三“王觐光”、卷十七“杨槐亭族叔”、卷十九“慧灯和尚”、卷二十三“严先生”等多则故事以夜读作为叙事的关键或核心情节。不仅夜读书写在篇幅与数量上相当可观,而且它作为“有意味的”叙事单元在小说的艺术呈现上也常起着重要作用。如《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夜读、《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夜读,直接推动了小说故事的发展。此外,夜读也常是摹写人物的点睛之笔,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夜读、《红楼梦》中的黛玉夜读。夜读书写还是“红袖添香夜读书”文化心态的艺术表达,潜藏着丰富的文人群体的文化心理。总而言之,夜读书写是明清小说中值得引起重视的文本现象。据笔者所见,当前关于古代小说中夜读书写的讨论文章并不多。本文拟从夜读与小说叙事、夜读与人物塑造、夜读书写与文人的情感补偿及情理之争几个角度略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二、夜读与小说叙事
暮夜赋予了夜读神秘气息,通过夜读营造与渲染所读之书的神秘感是明清小说中的惯用技法。例如,《英烈传》第十七回中刘伯温夜读周颠所授“天书”;《前七国孙庞演义》第二回中孙膑从鬼谷子处求得三卷天书“燃灯夜读”等。典型的是狐精夜读天书的情节,如《醒世恒言》卷六《小水湾天狐诒书》中的王臣夜行途中见到“两个野狐,靠在一株古树上,手执一册文书,指点商榷,若有所得,相对谈笑”,出于好奇,飞弹击伤二狐夺得“天书”,由此引出“天狐诒书”的系列故事。天狐夜读的神秘气息,令窥见者充满好奇,进而谋夺天书,从而形成了“夺书——索书——争斗——报复”的故事链。
夜读作为引出故事的契机,读书声和灯光这两个要素在推动叙事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三国演义》第四十七回中“连环计”得以实现的契机,缘自庞统在西山背后草屋中夜读,引诱蒋干中计:“是夜星露满天,(蒋干)独步出庵后,只听得读书之声。信步寻去,见山岩畔有草屋数椽,内射灯光。干往窥之,只见一人挂剑灯前,诵孙、吴兵书。干思:‘此必异人也。’叩户请见。”[5]594-595《人中画》第二卷《柳春荫百磨存气骨 商尚书慷慨认螟蛉》中,商尚书“沿着长堤一带步月赏玩。忽步到柳春荫门前,听见里面书声朗朗,便立住脚细听。听他读了一回,又放声痛哭,哭了又读,读了又哭。商尚书听了半晌,心下惊讶道:‘我听此人如此哭,如此读,其人决非寻常!胸中定有大冤大苦之事。’”[6]37夜读作为商尚书与柳春荫相遇的契机,绾合了两条叙事线索,直接推动了柳春荫故事的转向与发展。《儒林外史》第十六回《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中的匡超人“读到二更多天,正读得高兴,忽听窗外锣响,许多火把簇拥着一乘官轿过去,后面马蹄一片声音,自然是本县知县过,他也不曾住声”[7]212。不料他的这番夜读恰触动了知县的怜才之念,在县令的提携下,其命运发生了重要转折。如此种种,夜读不仅是引出故事的契机,而且常利用夜读的灯光或读书声这两种在夜间易于得到凸显与放大的要素作为引导叙事的线索,实现特定叙事场景的聚焦或不同叙事场景的切换与贯串。
就情节模式而言,夜读见怪、夜读遇艳是明清小说夜读书写中常见的两种。虽然小说中的“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怪”的一种特殊形态,但两种情节模式的创作取向与小说意趣却有着显著不同。
其一,夜读见怪。这一情节模式主要叙述书生夜读时目睹的神怪妖异情状,在志怪小说中相当普遍。《聊斋志异》卷一《青凤》中的耿去病“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8]124;《子不语》卷四《七盗索命》中的“夜交三鼓,一灯荧然,汤方看书,窗外有无头人跳入”[9]57;《子不语》卷二十四《鬼魂觅棺告主人》中的姜静敷“月夜读书,窗户轰然打开,棺盖低昂不已”[9]379;《阅微草堂笔记》卷六中的徐编修“每夜读书,则宅后空屋中有读书声,与琅琅相答。细听所诵,亦馆阁律赋也,启户则无睹”[10]77;《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中的王觐光“半夜灯光忽黯碧,剪剔复明,见一人首出地中,对灯嘘气”[10]213;《夜雨秋灯录》卷二《应声蓝面鬼》中的“一夕,正把卷,忽闻梁间有窸窣声。异而睨之,则一巨鬼”[11]45;《夜谭随录》卷五《大眼睛》中双丰将军“夜坐读书。忽见一物类蝙蝠,直扑灯来”[12]159等,均是掌故形式的炫奇志异。
其二,夜读遇艳。这一情节模式在《太平广记》卷三八六《刘长史女》中已有“一夜,高氏子独在船中披书。二更后,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丽,直诣高”[13]3081,其往往呈现为狐鬼花妖幻化的美女冒夜私奔夜读书生。与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偏好夜读见怪的情节模式不同,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夜读书写更多与“遇艳”有关,呈现出鲜明不同的创作旨趣。比如,《子不语》卷十四《狐鬼入腹》中的李鹢“灯下读书,忽两女子绝美,来与戏狎,李不为动”[9]212,这一故事,仅从开头看似有极强的向“夜读遇艳”发展的趋势,然而后文却只是单纯的怨鬼报仇故事演绎,分毫未涉艳情;《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中的江宁书生“宿故家废园中,月夜有艳女窥窗。心知非鬼即狐,爱其姣丽,亦不畏怖。招使入室,即宛转相就,然始终无一语,问亦不答,惟含笑流盼而已”,虽涉艳情,但女子却仅“取笔作字”而“终无一语”,且终以佛家消业结尾,使小说由遇艳转向了志怪[10]13。这在《聊斋志异》的故事建构中是很少见的。在《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中,记“怪”是其创作旨趣,即使女鬼“绝美”也鲜涉艳情,“艳”只是凸显“怪”之奇趣的修辞手段。而《聊斋志异》的夜读书写虽也常由“怪”发端,但“怪”却往往是“艳”的铺垫,并以男女艳情为旨归。例如,卷三《鲁公女》中的张于旦在鲁公女亡后“极意钦想”,“一夕,挑灯夜读,忽举首,则女子含笑立灯下。生惊起致问。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遂共欢好”[8]295;卷五《绿衣女》中的于璟“夜方披诵,忽一女子在窗外赞曰:‘于相公勤读哉!’因念:深山何处得女子?方疑思间,女已推扉笑入,曰:‘勤读哉!’于惊起,视之,绿衣长裙,婉妙无比。于知非人,因诘里居”[8]700,均是由“怪”入“艳”的叙述程式。
推究其因,《聊斋志异》中的夜读书写之所以对“夜读遇艳”倍感兴趣,缘于蒲松龄试图以“遇艳”的梦幻来抚慰“寂寞荒园明月夜,蕉窗影里度清霄”(《读书效樊堂(其二)》)的寂寥苦况,以及满足“对于‘知遇’的期许和想象”[14]。这也与《胡四姐》《莲香》《林四娘》等篇中的“夜独坐,有女子搴帘入”[8]289情节模式,是同一心理的产物。而《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夜读书写更青睐“夜读见怪”,是古代读书人以“志异”的掌故消遣平淡夜读生活这一传统的延续,流露的更多是仕途亨通的士大夫好奇尚异的文化心态。这也是《聊斋志异》与《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在处理同一题材时,之所以呈现出“写心”与“志异”别趣的根源所在。
三、夜读与人物塑造
王嘉在《拾遗记》中载:“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恐辞说繁广忘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15]153由此衍生出的燃藜图,也成为劝勉后进发奋苦读的熟典。由此可以理解《红楼梦》第五回中,当“愚顽怕读文章”的贾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不看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16]69。明清小说常通过夜读表现人物的勤苦好学,比如,《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王景隆“整日读书,晚下读至三更方才睡”[17]341;《平妖传》第十五回中的皇太子“聪明好学,虽然夜深,兀自秉烛而坐”[18]102;《情梦柝》第八回中的楚卿“发愤读书”“读至四更,犹吟哦不绝”[19]108;《谐铎》卷三《读书贻笑》中的徐登“宵分苦读,常至达旦”[20]41;等等。不过,明清小说这一层次的以夜读写人,往往仅是简要陈述人物的夜读行为,以渲染人物焚膏继晷的苦志勤学,文学意味相对较淡。
值得关注的是,明清小说惯用读书灯为人物聚焦生色。例如,《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中的关羽夜读:“胡班潜至厅前,见关公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班见了,失声叹曰:‘真天人也’”[5]337。关羽“灯下凭几看书”的儒雅与威严,透过胡班的近距离窥视得以聚焦和彰显。《三国演义》此处并未言及关羽所读为何书,很大程度上小说只是通过关羽的夜读彰显其儒将风采。“清夜读《春秋》,一点烛光灿古今”“青灯观青史”云云,只不过是杂糅了史传中关羽好读《春秋》的典故与小说中关羽的夜读的典故,把关羽夜读的书籍附会为《春秋》而已,赋予关羽的夜读行为更多“忠义守礼”的深层寓意[21]。《水浒传》第六十四回中,“帐中灯烛荧煌,关胜手拈髭髯,坐看兵书”[22]820;《东西晋演义》东晋卷之三《殷浩兴兵去伐燕》中的姚襄亦“在中军燃灯读书”[23]440。将军夜读也成为古代小说建构儒将形象的程式笔墨。
除此,小说也常借助夜读的书籍为人物摹神刻骨,如《五代史平话》中的郭威“每夜读诵《阃外春秋》《太公兵法》”[24]215,通过酷嗜兵书凸显其雄才大略。在这方面,以《红楼梦》第四十五回中的黛玉夜读为典型:
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16]607-608
与《三国演义》凸显夜读者的读书神态不同,林黛玉的夜读更多着眼于其所读书的内容。《秋闺怨》《别离怨》等感伤诗作无疑契合了“秋霖脉脉,阴晴不定”的自然环境,“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而令黛玉“心有所感”。谢肇淛《五杂组》中“凄风苦雨之夜,拥寒灯读书,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亦殊有致”[25]1768,读者、环境、书籍,共同建构了带有浓郁感伤情调的夜读情境。这一情节与冯小青夜读《牡丹亭》有很强的“文本间性”。《女才子书》卷一《冯小青》曰:
一夕,风雨潇潇,梵钟初动,四顾悄然,乃于书卷中捡出一帙《牡丹亭》,挑灯细玩。及读至“寻梦”“冥会”诸出,不觉低首沉吟,废卷而叹……援笔赋成一绝云:冷雨幽窗不可聆,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时已夜半,但闻雨声淅沥,乱洒芭蕉;风响萧疏,斜敲窗纸;孤灯明灭,香冷云屏。[26]6
在上述的夜读书写中,书籍的内容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起着关键作用。小说通过书籍内容与读者现实境况的“互文”,借此实现书与人在行为或精神上的贯通,从而为夜读者写心图貌。
夜读,并非总是默读。“夜半梅花春雪里,小窗灯火读书声”(汤显祖《与李太虚》)。明清小说中的夜读书写还常格外凸显读书声,如《情变》第八回中“但听得四壁厢虫声、蛙声,与那木鱼声、磬声相应。忽然又听得一阵读书声,入耳声音很熟……顺着那读书声寻去。走进了一个院落,只见一所客房,内中透出一点灯光,那书声正从那里面出来”[27]166-167。即是特意把读书声置于众声喧哗的“虫声、蛙声,与那木鱼声、磬声”之中并格外凸显出来的。凸显夜读者的读书声,是明清小说中的常见叙事程式,如《隔帘花影》第二十三回中的严好礼:“念的书声且是好听,到了半夜,凄凄楚楚,如泣如诉的,常念到好处,双泪俱下。”[28]387《合浦珠》第十回中的钱生:夜夜诵读,如鹤唳,如蛩吟,声声感入肺腑[29]318。《醒风流》第六回中的梅公子:“初时诵读,留心收敛,不敢高声。以后渐渐惯了,读到忘怀处,便高声朗诵起来。一夜冯公睡醒,忽听得书声朗朗……仔细听时,愈觉声音悲切,不禁披衣起坐。再听时,那书声竟从木荣房里来的,不胜骇异。遂缓缓启扉,一路步到木荣房边。但见月明如水,树影横空,吟唔之声与风声上下,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宛如孤鹤唳空,幽闺泣妇,书声中又带有凄楚之意。”[30]45
正所谓“声如其人”。明清小说通过着意摹写读书声,以在夜间相对于形貌而言更具身份辨识度的声音来描摹人物,以“耳朵”写人而非以“眼睛”写人,是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上颇具文心之所在。而且明清小说中的夜读在声音场景的建构上,对于成年人而言,多带“凄楚之意”。这一小说情调的创设,既源于光照不足的情况下,人物情感内缩而易生悲感;同时也与小说人物的命运遭际直接相关,夜读者在小说中往往是身世坎坷、命途多舛的形象,“凄楚”的读书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其内在情感的外化,即“有此人,有此声”。
稍值一提的是,明清小说中的夜读书写不仅常常通过读书声来以“声”写人,而且读书声特别是童子的读书声,作为声音景观,本身也创设了别具意趣的小说情境。例如,《歧路灯》第一回中谭孝移在丹徒本家“一日晚上,孝移同绍衣夜坐,星月交辉之下,只听得一片读书之声,远近左右,声彻一村”[31]7-8;《隋唐演义》第六十二回中“天色傍晚”“两人赶进村中,这村虽是荒凉,却有二三十家人户,耳边闻得小学生子读书之声”[32]550;《飞花艳想》第一回中的“夜间燃灯,杨氏就课子读书,那咿哦之声往往与牙尺剪刀声相间”[33]1,均着意凸显童子夜读的声音景观。这一小说修辞,是与翁承赞《书斋漫兴二首(其二)》中的“官事归来衣雪埋,儿童灯火小茅斋。人家不必论富贵,唯有读书声最佳”,陆游《夜出偏门还三山》中的“到家夜已半,伫立叩蓬户。稚子犹读书,一笑慰迟暮”,以及吴学礼《郭外夜归》中的“近郭不妨归近夜,到门犹有读书声”,曹耀珩《放舟夜归》中的“谁家茅屋近,隐隐读书声”等诗词创作一脉相承的文学表达。童子的琅琅夜读声,不仅是和谐而富诗意的夜间音景,也象征着年轻一代的勤勉好学,犹如暮夜中茁壮成长的读书种子,诗书绵绵继世长。
四、夜读书写与文人的情感补偿及情理之争
“红袖添香夜读书”是明清小说夜读书写中的重要话题。例如,《飞花艳想》第十一回中的“风清月白夜窗虚,有女来窥笑读书”[33]64;《狐狸缘全传》第三回中的“窗明几净读书堂,斗转星移漏正长。独坐含情怀彼美,相思有约赋高唐”[34]44。如此种种相近的表述,流露与呈现了孤馆青灯的读书人对“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想象。虽然明清小说中不乏如《三门街全传》第二十三回中的蒋逵“在灯下读书,秀英一旁刺绣”[35]90这般“绩麻夜伴读书灯”式温馨浪漫的夜读场景。但无论是就艺术表现,还是意蕴呈现,这一话题主要集中在“有女来窥笑读书”的美人“夜奔”情节模式建构上。
孤馆青灯的夜读生活对于读书人而言是枯寂而孤独的,此时如果有一“添香”的“红袖”,无疑让夜读变得香艳、浪漫起来。宋代无名氏在《沁园春·冬至日娶》中希冀新娘“短檠灯火,伴读书郎”,清代端木埰在《齐天乐》中也说“添香红袖伴高咏。书城相对万卷,比金籯万卷,风味须胜”等,都曾把“红袖添香夜读书”作为理想生活形态加以吟咏。这一情结对常年离家在外坐馆的蒲松龄来说感受尤为深切,并在《聊斋志异》中有着深刻表现。无论是《聊斋志异》卷三《连琐》中的连琐与杨于畏“与谈诗文,慧黠可爱。剪烛西窗,如得良友”[8]338-339的情事想象;还是《聊斋志异》卷十一《书痴》中的郎玉柱“一夕,读《汉书》至八卷,卷将半,见纱剪美人夹藏其中。骇曰:‘书中颜如玉,其以此应之耶?’心怅然自失”[8]1489的遇艳心理,其对“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无限憧憬则是一致的。更能直接表现这一心理的是小说中大量的“夜读遇艳”故事,如《聊斋志异》卷三中的《鲁公女》、卷四中的《青梅》、卷五中的《绿衣女》等,美女深夜来奔读书人的故事情节,无疑是蒲松龄枯守书斋夜读“此际凄凉不啻僧”(《合浦珠》第十回)时浪漫幻想的艺术呈现。
当然,这一情节模式与心理,并非蒲松龄的草创,而是有着悠久的文学与文化传统。《搜神记》所载的谈生故事,虽已基本囊括了“夜读遇艳”的所有情节要素:“有谈生者……常感激读经书,通夕不卧。至夜半时,有一好女……来就谈生,遂为夫妇。”[36]388-389但其却只是一较为单纯的志怪故事。《括异志》卷五《李参政》中“二女子”的到访虽是“夜读遇艳”情节模式,但其作用更多体现在“女仙指路”[37]而非精神慰藉。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七《毕令女》中的士人“半年前夜坐读书,有女子扣户曰:‘为阿姑谴怒,逐使归父母家。家在城中,无从可还,愿见容一夕。’泣诉甚切,不获已纳之,缱绻情通。自是每夕必至”[38]238的故事虽更近似“夜读遇艳”情节模式,只不过在此故事中“异”的属性远大于“艳”,且小说中的女子也是以“无从可还,愿见容一夕,泣诉甚切”的面目博取同情,而非以美貌打动书生。《龙图公案》卷六《金鲤》中的精魅“变成小姐形迹,到真读书馆所叩其门户”[39]121,迷惑“好男子”刘真则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读书人对“夜读遇艳”故事的心理设防——“艳”为精魅所化。
不过,夜读书生对于“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妙幻想仍驱动着这一故事的不断生成,并把“艳”的成分逐渐纯化与美化,精魅的邪恶属性淡化,而往往以和蔼可亲的“人”之属性呈现。例如,《艳异编》卷三十四《舒信道》中“方盛秋佳月,舒呼灯读书。忽见女子揭帘而入,素衣淡妆,举动妩媚,而微有悲涕容。缓步而前曰:‘窃慕君子少年高志,欲冥行相奔,愿容驻片时,使奉款曲。’舒迷蒙恍惚,不疑为异物,即与语”[40]466;《艳异编》卷三十五《金友章》中的“友章每夜读书,常至宵分,女亦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执卷,而女不坐,但伫立以侍。友章诘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其就寝。女曰:‘君今夜归房,慎勿执烛,妾之幸也。’既而,友章秉烛就榻,揭被乃一枯骨耳。友章惊骇,惋叹良久,复以被覆之。须臾,乃复本形……涕泣呜咽,倏尔无见”[40]475-476。在此,来陪伴夜读书生的女鬼已没有了早期故事中浓郁的厉气和诱惑意味,而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红颜知己”或“腻友”。别有意趣的是《子不语》卷十三《张光熊》中的张光熊“七月七日,感牛郎织女事,望星而坐,妄想此夕可有家婢来窥读书者否。心乍动,见帘外一美女侧身立”,小说并未渲染艳情的香艳,而着意于“居年余,张渐羸瘦”的妖媚惑人的结果。这篇小说的特殊意味在于,张光熊与狐精日久生情,相约“二十年后,华州相见”,既而果然。袁枚以“或曰此狐仙感情欲而托生也。语从前事,恰不记忆”结尾,“狐仙感情欲而托生”,是耶,非耶?“语从前事,恰不记忆”突破了两世姻缘的旧套,赋予了小说无限的流波余韵和想象空间[9]203。
当然,在此情节类型中,夜读书生面对“来奔”的女子,恰如《合浦珠》第十回《咏雪诗当垆一笑》中申屠丈警诫钱九畹“或遇闲花野草,亦须屏却淫邪,以存阴鸷,庶几功名可成,而遐龄可保”[29]315一般,尽管心存艳想,却鉴于干涉“功名”“遐龄”,必须克制欲望。甚至诸多小说把夜读拒艳作为“未遇时”的阴德,使读书人的“遇”与夜读拒艳形成某种因果关系。如《聊斋志异》卷四《青梅》中,当青梅“夜诣”张生时,“生正色却之”:“卿爱我,谓我贤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夫始乱之而终成之,君子犹曰不可;况不能成,彼此何以自处”[8]473。有趣的是,小说中青梅却以张生的夜读拒艳,作为“决其必贵”的前提之一。
不过,相比之下,情欲与礼法的冲突才是构成这一情节模式的核心要素。或许也可这样认为,“夜读遇艳”情节模式实是在儒家伦理规约下,夜读书生面对诱惑如何“慎独”以及“克己复礼”的文学演绎。具体演绎思路,主要有二:一是把夜半来奔的女子淫化或妖魔化,以危险抑制欲望的泛滥。例如,《混元盒五毒全传》第十二回《假佳人花园觅偶私效鸾凤》:
(谢廷)在房看书,此刻已交二更时分,忽听得窗外扣门之声。谢廷仔细侧耳一听,却是个女人的声音,竟不睬他了。伏自挑亮了灯,仍然看书。不多一刻,又听得扣门声响。谢廷听得烦恼,设或开了门,惟恐是女人,岂不男女有授受不清。没奈何,只得起身开门看视,只见果是一个女子……谢白春道:“岂有此道理!况你家小姐乃是翰林之女,千金之体,怎么今夜叫尔前来请我?我又是个读书之人,何敢越礼犯分?男女不相授受,有关闺阃之风,坏我的远大前程,此事断断不能的!请姐姐早回,好好回复小姐。若在此地缠绕,我就叫书童去禀你家老爷,叫你性命难保!”[41]78-82
二是着意凸显夜读书生以礼自持,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克制诱惑。例如,《合浦珠》第十回《吟雪诗当垆一笑》:
(蕙姑)悄悄走至窗下窃听,欲推门而入,门是关的,只得轻轻扣响。钱生听了,忙掩卷问谁?却又寂然。未几,将欲展卷,又闻扣响,如前。生平素畏鬼,亦呼紫萧,而紫萧已垂头熟睡,乃执灯自起启扉。只见蕙姑静立于扉外,惊避进房。蕙姑亦尾后而入。钱生愕然道:“小娘子寅夜至此,有何见谕?”蕙姑道:“闻君静夜读书,特来作伴耳。”钱生道:“小生自有圣贤为伴,请勿进内,男女之间,嫌疑不便。”蕙姑剔了灯煤,翻弄书帙,含笑而问道:“君乃风流名士,曾阅《西厢记》否?”钱生正容道:“此乃艳曲淫词,岂入我辈之目。”蕙站又杂以谐谑,多方诱生,而生终不能动。乃双脸晕红,含愠而退。[29]318
沈起凤《谐铎》卷三《两指题旌》:
一夕,秉烛读书,闻叩户声。启而纳之,主人妇也。叩所自来,含笑不言。固诘之。曰:“先生离家久,孤眠岑寂。今夕好风月,不揣自荐,遣此良宵。”蓉江正色曰:“妇珍名节,士重廉隅。稍不自爱,交相失矣。汝请速回,人言大可畏也!”妇坚立不行。蓉江推之出户,妇反身复入。蓉江急阖其扉,而两指夹于门隙,大声呼痛。稍启之,脱手遁去。[20]46
小说极力夸大女性的主动、体态与语言上的魅惑,以凸显夜读书生所面对的诱惑之强大,从而与书生的“克己复礼”形成力量上的呼应——诱惑越大,守己愈难。然而,在这一情节模式中,我们仍可见到夜读书生面对引诱时的脆弱,《混元盒五毒全传》中的谢廷虽然义正辞严地拒绝引诱,却在狐精变化的女子面前不堪一击,在其脸上轻轻“一抹”就“迷迷糊糊,身不由己跟了前去”,以至“面如黄土,骨瘦如柴”,幸亏张天师现身除妖,才侥幸逃过一劫;《合浦珠》中的钱九畹面对蕙姑时是畏惧、“惊避”与“愕然”的,相对蕙姑挥洒自如的“含笑而问”“杂以谐谑”,钱生在诱惑面前全力以拒之的“正容”总是显得局促不安;而《两指题旌》中的赵蓉江“急阖其扉”时的仓皇失措,无疑也可视作惊乱内心的外化。由此可见,夜读书生以“礼法”为武器来抵御“情欲”的诱惑时往往显得手忙脚乱、力不从心,虽然最终经受住考验,却也甚是狼狈。但也正是夜读书生在以礼法抑制情欲时的艰难,才使小说人物跳出了情理交锋的单纯概念演绎而变得鲜活起来。
综上所述,夜读书写是明清小说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明清小说中的夜读书写与古代文学夜读书写传统一脉相承,它作为古代文学夜读书写的创作形式之一,在小说叙事、人物塑造、音景创设以及文化心态的呈现上具有多重价值。目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中的夜读书写传统关注尚少,如何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角度梳理古代文学中的夜读书写,发掘其中蕴含的独特文学价值和文化内涵,从而深化对这一特殊文本现象的认识,本文即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