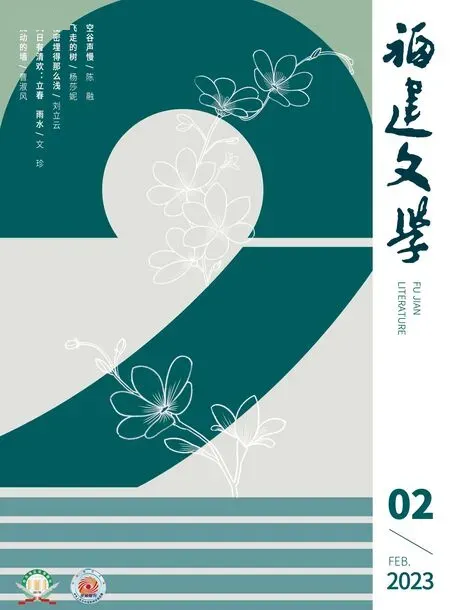山河与故人
——读施晓宇历史文化散文
2023-04-06龙潜
龙 潜
1
施晓宇出版了《洞开心门》《都市鸽哨》《思索的芦苇》《直立的行走》《大美不言寿山石》《闽江,母亲的河》《秋水文章不染尘》《走陕北》等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散文集。特别是散文集《施晓宇说史——一个人的另一面》《文人文话》和近年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散文选刊》等刊出的作品,更是显示了施晓宇对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
施晓宇用他的散文,讲叙在社会现实的高歌猛进中,不应忘却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他的散文无论是地域范畴、内容题材还是作家个人的文学观念、审美理想和精神诉求,都在当下中国散文中表现出别样的表述形态与价值系统。
施晓宇的散文在文学追求上是古典主义的。宁静肃穆的古典主义文学是人类黑暗中温暖的光亮。充满悲悯情怀的作家所关注的是受苦受难的人们,他们在善与恶之间,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表现出良知、见识、勇气和高尚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崇高人格。他们对恶的诅咒,对一切被怜悯的人的深切同情,覆盖和引导了人们心底潜在的美好渴望。
施晓宇的散文以非虚构方式,用从容的语言和客观的理性态度,力图再现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在这样的叙述中,他的书写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始终站在客观的立场去还原历史,挖掘历史背后的现实社会意义,遇见人被社会赋予的一切。在时光中,在中国社会的进步中,施晓宇相信历史永恒。
现代化背景下,我们没有靠近真正的现代,我们却又似乎忘记了历史,我们成为一种处于历史与现代夹缝中的被异化的“过渡性”的人,对于现代的核心要义知之甚少。施晓宇的散文通过历史文化和人物的书写,让历史记忆和现实同时呈现,形成连接,创造了一个个具有张力的镜像。他的散文串联起大量的人和事,构建起别具一格的文本结构,用叙事来表达历史中的各方姿态,从历史的角度探求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
施晓宇的散文将福建独特的人文历史纳入自己的文学书写之中。在现代性语境中,地域文化逐渐边缘化和陷落。而对于施晓宇来说,福建不仅是地理空间、物理空间,还是心灵空间,他从中获得了精神的引领。他的散文书写,唤起人们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唤起人们思考这片土地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唤起人们思考融合与冲突、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在发展与进步中的化解之道。
施晓宇的散文于叙述中始终有一种自我审视,这使得他的散文节奏舒缓,有着淡淡的忧伤。沈从文曾提到自我审视,大致说过这样的话:离开自己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活人中很少那么做,因为这么做不是一个哲人便是一个傻子。施晓宇的散文是历史的“个人经验”的复活,具有沈从文说的“生活”之上“生命”的意义。如果说关于历史的书写是在温习过去,那么施晓宇的散文已展现了强大的还原能力。他的书写又不止于历史,他念兹在兹的是文学在广阔的时代中保存历史的痕迹。
2
历史是故事的发生地,它以自身的古老性和包容性鬼魅般吸引写作者。施晓宇的《秋水文章不染尘》《走陕北》这两部散文集,为我们展开了地域历史的想象与建构。在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地理空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寻求地域文化认同与自身归宿。其实,中国大地上的每一地域都承担着这一重要的使命。一个地域的兴衰命运反衬出百年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历史趋势,也折射出历史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价值。如同巴赫金所说的“道路”时空体,他说:“社会性隔阂在这里得到了克服。这里是事件起始之点和事件结束之处。”
施晓宇的散文中还展示了底层民众的群像。这些文字向我们展现了生气勃勃的人文风貌,是作者对故乡和朋友的回望。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人们白日短行,施晓宇的散文对那些人的亲切描写,不仅表现出对小人物高尚精神的赞扬,还是自我的一种精神返乡,即在生活中生活着。或许他们是平凡的人,但他们生活的困境其实是中国之困境,对他们生活迷惘的记叙其实是对中国的展望。
施晓宇是一个十分注重叙事技巧的作家,他的散文运用互文性结构,通过不同文本之间的联系相互映衬、互为补充,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这种橘瓣式结构,从多个视角对叙事空间展开观察与叙述,打破了线性叙事的时间,使多个空间并置,从而在空间与场景的不断变换中推进叙事进程。他散文中的“互文性”即读者在阅读完一个文本后,可以在其他文本中找到这一文本的补充或延续,使不同人物有自己开口说话的可能,自身形象与特点也因此更加饱满。
时间是笼罩在空间纬度之上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历史中那些往事和人物作为一种文学文本的表达,在被阐释的同时也被想象。在当下与过去、保守与激进、传统与现代的比较中,历史的时间体验得到强化。巴赫金在谈到歌德作品中的时间问题时,认为歌德能在物体身上看到不同时间的存在及其背后所蕴藉的思想内涵。某种程度上,历史的遗迹体现为时间的痕迹。历史辉煌的过去以及因地理、政治等原因而逐渐衰落的现状,提供给施晓宇的更像是一种时间性的远距离想象,而非一种叙述元素那么简单。《龙阳之癖》《谒司马迁墓》《辜鸿铭祖地回望》等篇章证明了这一点。这些遗迹为时间所渗透,其意义超越了事物本身,在时间的流年中,展示了时间的绵延性。
时间是一种较为抽象的存在,而空间是一种较为具体的存在。从外在艺术结构形态来说,《访蒲城三陵》《朱仙镇里谒岳飞》《一代宗师宋慈》这些篇章大都以“地点·人物”的方式进行命名。按照陈平原的观点,不同空间场景的并置、对比、组合,可以使文本获得另外一种较为特殊的美感效果。这样的布局其实隐藏着施晓宇对散文的整体构思以及对历史的理解和想象。约瑟夫·弗兰克指出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的作品是用“同在性”取代了“顺序性”,因而是“空间的”。显然他所指的空间是抽象化的、符号化的空间,也即是文本的空间形式和空间结构。在施晓宇的散文中,其主要体现为时间的淡化和时间的凝固,从而赋予时间以精神内涵、文化内涵甚至是生命内涵。从施晓宇选取的意象看,不管是《屹立的马尾》还是《杜陵四苏》这类作品,其本身就体现出时间的空间化特征;书中的场景的描绘,即弗兰克所谓的空间描写,就像电影里面的定格画面一样,时间在这里被凝固、被定格、被停止,使事件表现为一种空间形态,这跟图像叙事有了共通性。
施晓宇对历史文化的写作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构建,而是试图通过不同时空的拼接和并置,把历史真实地展示出来。而这种异时性并置的书写方式,有效地突出了知觉上的同时性。《秋风秋雨感业寺》《马嵬坡与杨玉环》《他乡遇故知》等作品因此成为充满立体感的空间图景。历史的异质性、非理性、边缘性和陌生感更多来自作家自身的体认。所谓历史想象,离不开历史的文学性感知、体验和表达。古人就常常在想象中构建“天下”的概念。
施晓宇散文中的时间叙事是寻找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重要手段,他善于用时间的穿越去强调一种历史的时间体验。历史时间在施晓宇散文中并不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也作为一种行文逻辑或者写作策略。其中,时间的空间化以及多重空间的并置是施晓宇散文呈现空间形式的最主要手段,前者使时间被淡化,空间由此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后者使其散文能够容纳更多的共识性场景,由此展露出对空间化效果的追求。
3
在中国散文发展历程中,“真实”作为传统散文的基石一直被不断强调。然而,众多散文作家尝试在散文中加入想象的成分并因此获得了成功,如余秋雨《道士塔》就将许多虚构的场景和情节引入文中,余光中《年轮》就在写实与想象之间来回穿梭。施晓宇的《空海:中国取经》《屹立的马尾》《杜陵四苏》等作品,同样也是由于涉及大量的想象成分才显得丰满。虚实结合一直是中国艺术的特点之一,文学艺术要求从虚与实的结合和统一中寻找艺术的美。很大程度上,文学对历史的想象是对历史空间的一种重塑,不仅能够反映作家的情感与态度,也影响读者对历史的解读。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想象”是文学的核心词。近几十年文学想象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种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考察文学的想象问题,很大程度上将文学想象与形象思维等同起来,如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和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第二种是从语言艺术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想象,认为文学语言能够实现“想象力的振奋”,倡导从文学话语中寻找文学的“表现链”,如童庆炳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和杨守森的《艺术想象论》。
施晓宇散文的想象,本质上是自由性、超越性和创造性三者的统一。其自由性表现为施晓宇笔下的想象具有既包含某种在场的东西,又包含某种不在场的东西,是用有限的在场来表示无限的不在场;其超越性表现在施晓宇对于表象的想象既能够突破自身,又能够突破客观现实以及时空限制,这是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的升华;其创造性表现为施晓宇散文既能创造出新的文学形象,又能把新形象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对历史想象所具有的表现性、象征性和创造性的综合呈现。特别要指出的是,虽然施晓宇散文对历史的想象是基于历史特有的地理空间、历史变迁和文化形态,但作为一种文学创造活动,这具体又涉及到对历史的感知、筛选、描述和意义赋予,表达的是对历史的认识、回忆、期待,因而无法避免作家主观色彩、审美情感和心灵启悟的浸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