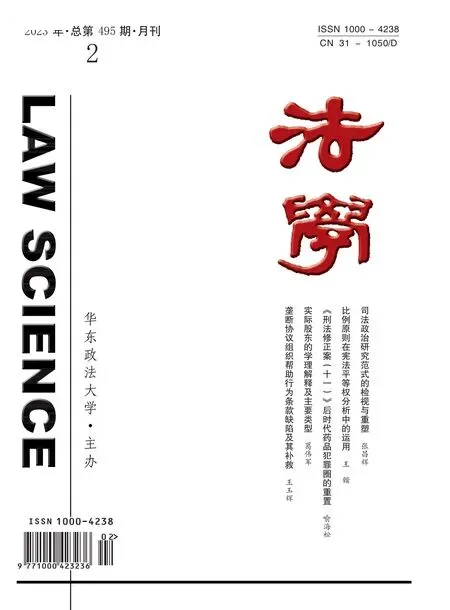一身专属性理论视角下的数字遗产继承
2023-04-06张挺
●张 挺
自然人死亡后,其财产依法由继承人继承。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私人生活也全面数字化,手机成为“终身伴侣”,出现了全新类型的财产。人们在电子邮箱、搜索引擎、社交平台、购物网站、游戏娱乐程序等多种互联网服务中产生了大量的个人数据,一般通过账号密码的方式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产生关系。自然人死亡后,这些个人数据即所谓数字遗产便面临可否继承的问题。〔1〕例如,自Facebook公司(2021年10月已正式宣布改名为Meta)出现后的8年时间内,已有超过三千万的用户死亡,有研究者推测到21世纪末,至少有49亿的用户会死亡。See Carl Ohman & David Watson, Are the Dead Taking over Facebook? A Big Data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Death Online, 6(1) Big Data & Society 1-13(2019).此外,在大量个人数据积累于相关企业平台的现状下,如果允许企业毫无节制地使用而不允许继承人处理,从情理上与法理上均无法接受。因此,有必要从内容规制的层面考虑数字遗产的处理问题。
我国《民法典》已经对数据信息的保护作出了部分回应,〔2〕参见梅夏英:《〈民法典〉对信息数据的保护及其解读》,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26-31页。那么其能否解决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以《民法典》继承编为中心的私法是否有必要回应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从司法实践来看,国外已经存在数字遗产继承的多个判例,例如2005年美国“数字遗产第一案”、2018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Facebook继承案”以及英国的“Apple ID继承案”。〔3〕参见杨勤法、季洁:《数字遗产的法秩序反思——以通信、社交账户的继承为视角》,载《科技与法律》2019年第2期,第75-76页。另外,随着技术、社会以及经济要素的相互作用,复杂、交错的数字遗产法律问题不仅对继承法、人格权法、合同法等私法领域产生冲击,还对各国平台治理的法律传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鉴于此,本文从一身专属性的角度分析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首先探讨财产、人格二分化的现行范式能否解决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继而提出一身专属性理论及其在数字遗产继承上的运用,最后就数字遗产继承的完善进路提出若干建议。
一、数字遗产的属性争论并非能否继承的关键
(一)数字遗产的定位
1.数字遗产的概念及司法实务现状
与数字遗产概念紧密关联的是数字财产概念。数字财产是指“未附着于任何形体之上的无形财产,以账户、股票、选择权、知识产权等形式呈现,包括呈现或储存于电子设备中的信息,如云端、网页、电子邮件、社交媒体、拍卖网站、在线支付,再如照片、影音频道、游戏网站、音乐网站等”。〔4〕See James D. Lamm, Christina L. Kunz, Damien A. Riehl & Peter John Rademacher, The Digital Death Conundrum: How Federal and State Laws Prevent Fiduciaries from Managing Digital Property, 68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388 (2014).与此相对,数字遗产主要是自然人死后遗留的数字财产,通常是指自然人死亡时以数字信息形式存储在一定载体或网络中的物品,或者在网络环境下以数字形式存在的自然人死亡后未被继承的所有虚拟财产。〔5〕参见陈奇伟、刘伊纳:《数字遗产分类定性与继承研究》,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79页。但是,数字遗产并不是一个严谨意义上的学术术语,“而是作为死后关于数字财产所产生的法律问题总称而使用”的概念。〔6〕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の登場により法律はアップデートを必要とするか(1)」立命館法学389号(2020年)176頁。正如德国学者指出的,并不存在一种家庭亲属对于非财产权利的独立权,数字遗产甚至是带有误导性的。〔7〕参见[德]马蒂亚斯·施默克尔:《德国继承法》(第5版),吴逸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数字遗产也不是继承法上的概念,而只是描述性、说明性的名词,更合适的表达甚至应当是“数据遗物”或者“数据资产”。因此,数字遗产是包括被继承人所有数据财产的概念,包括被继承人对数据服务提供者的权利或请求权以及有经济价值的电子数据。
我国的虚拟财产纠纷较多,但数字遗产继承相关案例并不多,其中涉及金钱的数字遗产(如金融账号)纠纷比较少,而涉及社交网络、电子邮件等数字遗产的纠纷相对较多。进入司法程序的相关纠纷不多,即便诉至法院,大部分也会被法院以各种理由拒之门外,从诉讼利益的角度而言,这显然是不合理的。〔8〕参见陈奇伟、刘伊纳:《数字遗产分类定性与继承研究》,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78页。对于数字遗产能否继承,法院明显未形成一致的裁判思路,持有肯定与否定两种立场。〔9〕参见李雅男:《民法典视野下社交网络账号的继承》,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129页。有的法院认为其可以继承,“网络社交账号因用户的注册而设定并排他性地直接支配使用,因其使用而产生网络影响力,具有一定的价值,是一种网络虚拟财产,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10〕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5899号民事判决书。有的法院则否定网络账号的支配权,继而否定数字遗产的继承。例如,有法院认为相关游戏账号的封号是网络游戏秩序管理的合理范围,对此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约定。〔11〕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民(2020)粤0192民初4109号民事判决书。总体而言,随着我国相关立法及法院逐渐肯认虚拟财产保护,数字遗产纠纷将逐渐进入司法程序,但是能否继承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依然争论较大,主要争议是数字遗产的性质问题。
2.数字遗产的属性争议
上述司法纠纷主要集中于数字遗产是否属于财产以及属于何种性质财产的分歧。若答案是肯定的,则需解答数字遗产是否均可继承以及数字遗产性质之争议是否直接影响继承结果等问题。
关于数字遗产属性的学界观点大致可以分为“物权说”“债权说”“复合财产说”三大类型。首先,“物权说”认为数字遗产属于物权的客体或者准用物权的规定,由其“所有人”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益。该说已非主流学说,因为批判者认为,数字遗产相比有体物遗产,数据内容一般更具人格属性,在数量上也更为膨胀。〔12〕参见程啸:《论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5期,第13页。无论是德国法〔13〕原田弘隆「ドイツの『データ所有権』論争に関する序論的考察(3·完)」立命館法学397号(2021年)163-164頁参照。、日本法〔14〕臼井豊『電子取引時代のなりすましと「同一性」外観責任』(法律文化社,2018年)「はしがき」Ⅶ頁参照。还是我国法,大都不承认所谓数据所有权,“虽然数据具有财产上的价值,可以承认数据资产在无形财产上的某种权利,但是将这种权利称之为所有权显然是不妥的”。〔15〕塩原俊彦『サイバー空間における覇権争奪個人·国家·産業·法規制のゆくえ』(社会評論社,2019年)198頁。但是,数字遗产关乎“特定的人对该归属数据的链接权”,这恐怕没有疑问。其次,“债权说”认为数字遗产附着于作为网络账户法律基础的合同关系之上。该说认为,网络账号既不是民法上的物,也不构成知识产权的客体,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分和识别用户的技术标识,是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同关系或者说债上关系。〔16〕参见申晨:《虚拟财产规则的路径重构》,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84-94页。最后,“复合财产说”则是根据不同的类型将数字遗产认定为不同权利的对象。比如,储存于物理载体的数字遗产被认定为物权对象,有知识产权的则被认定为知识产权的对象,而未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普通数据则是债权保护对象。〔17〕参见王琦:《网络时代的数字遗产、通信秘密、人格权——以社交通信网络账户的继承为焦点》,载《财经法学》2018年第6期,第90页。该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债权属性,但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物权化的结果。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债权化的物权。〔18〕参见马一德:《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探析》,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5期,第77页。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数据本身没有特定性和独立性,亦不属于无形物,不能归入民事权利客体,不宜将其独立视为财产。〔19〕参见梅夏英:《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第167页以下。故而数字遗产的纠纷实质上是对争议账户的一种网络操作权,解决了操作权问题也就解决了问题本身。〔20〕同上注,第167页以下。
从以下两个方面而言,关于数字遗产属性的争议对其能否继承的要件事实影响不大。首先,按照《民法典》第1122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无论是“物权说”“债权说”还是“复合财产说”,不可否定数字遗产是自然人的财产,既然是财产自然便存在继承的可能性。其次,可能有人对数字遗产是否属于财产提出疑问,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财产本来就不仅仅指的是有形物,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财产的意义和范围都是社会需求和互动的结果。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法已经成为“财富法”,数字遗产自然是网络社会中的重要财富。另外,鉴于财产涵盖了所有权、债权和其他复合型权利,无论将虚拟财产界定为物权、债权还是知识产权或其他新型权利,其均应在财产范畴之内当无疑问。〔21〕参见梅夏英、许可:《虚拟财产继承的理论与立法问题》,载《法学家》2013年第6期,第84页。也就是说,在认定数字遗产属于财产范畴的情况下,按照《民法典》第1122条第1款判断数字遗产可否继承的关键已经不是其属于哪种财产,而是数字遗产是否存在法律特别规定或者按照其性质不得继承。
(二)分离理论之批判
关于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问题,目前国内外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当根据数字遗产财产性之有无决定是否可以继承,即只有财产性的数字遗产才可以继承,没有财产利益尤其是具有人格属性和身份属性的数字遗产,不应纳入继承范围。〔22〕参见马一德:《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探析》,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5期,第77页。有的学者进一步将数字遗产分为财产性数字遗产、人格性数字遗产和混合型数字遗产:财产性数字遗产属于公民可继承的财产;当数字遗产主要体现为主体人格利益时,则视情况而定,对于主要体现为人格利益的应该保护其人格权;财产、人格混合型数字遗产中的财产性权利则可以继承。〔23〕参见陈奇伟、刘伊纳:《数字遗产分类定性与继承研究》,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81-83页。以上按照数字遗产财产属性之有无的区分理论可以称为分离理论。
但是,分离理论在以下方面难以自圆其说。第一,认为人格权益不可以继承的理论前提并非牢不可破。从作为我国人格权理论渊源的德国法发展历史来看,人格权本身虽然并非财产权,但是部分人格权包含财产权的要素,从而具有转让性和可继承性。自“Marlene Dietrich案”以来,德国法院认为含有“财产价值构成要素”的人格权益可以继承。虽然有观点将人格权分割为高度人格部分和财产权部分,只有后者才可以继承,但也有观点认为两者一体不可分,人格权中的利用权能可以转让。在德国,“人格权非转让说”已非主流,人格权益的可继承性在理论上并非没有争取空间。〔24〕米村滋人「人格権の譲渡性·相続性——ドイツ人格権理論の展開を契機として」東北法学会会報30号(2012年)1-2頁参照。人格与财产双重保护的人格权保护模式同样见诸于美国法上“公开权”与“隐私权”的分立、日本法上“商品化权”与传统人格权的分立。总之,已有不少理论反思了人格权益不得继承的理论前提,提出了所谓“财产性人格权”的观点。〔25〕参见黎桦:《民法典编纂中的财产性人格权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8期,第15-18页。
第二,在现实中并不能将数字遗产截然分为财产属性的数字遗产与非财产属性的数字遗产。虽然部分数字财产易于区分,比如金融账号、网店账号、客户信息等明显带有财产属性,但是更多的数字财产兼具财产属性与非财产属性(或人格属性),尤其是大多数账号对继承人而言并不具有财产属性,只有由众多账号形成的大数据才可能有财产价值,此时又如何认定其是否有财产属性?财产性与非财产性(或人格属性)难以区分的理由还在于,具有财产价值的内容与没有财产价值的内容往往是交叉、重合的。〔26〕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の登場により法律はアップデートを必要とするか(2)」立命館法学390号(2020年)257-258頁参照。按照《民法典》概括继承的规定,继承人承继了被继承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这是为了整理遗产所必要的法律行为,继承人可以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附随性义务。
第三,在处理无财产价值的纯粹个人数据的情况下,分离理论明显存在困境。纯粹个人数据大多并不具有财产属性,按照分离理论似乎不在继承范围内,但是这显然不合常识,特别是在允许继承个人信件等实体物件的情况下却不允许继承“数字书信”,其依据又何在?首先,作为纯粹个人数据的电子邮件到底是财产性权益还是非财产性权益,这一问题需要依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回答。其次,区分个人数据与其他内容将产生实务上的困难。例如,该如何区分电子邮件中财产性的内容和纯粹个人数据,在法律上到底由谁予以认定。再如,我国有司法判决认为,通讯工具号码属于广义的虚拟财产,手机号码随着被继承人的使用逐渐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但是手机号码的使用权同样具有财产权益,故而根据《民法典》第1122条第1款可以继承。〔27〕参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2018)黑0111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书。
第四,分离理论不符合我国继承法上的概括继承原则。《民法典》第1122条第1款规定了继承标的的概括继承,除非存在该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情况。这是因为尽管《民法典》继承编对遗产范围的界定采取概括式规定,没有在遗产范围中明文列举新型财产,但由于《民法典》总则编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新客体和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因而这些有形的或者无形的新型财产都可能成为遗产。〔28〕参见杨立新:《我国继承制度的完善与规则适用》,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100页。而且,目前我国法律并无数字遗产不得继承的相关规定。
二、一身专属性理论下数字遗产可继承性之证成
(一)一身专属性的意义与解释
1.继承法上的一身专属性原理
在分析数字遗产可继承性的问题上,过往研究几乎都被“束缚”在其性质认定与分离理论中难以自拔,但似乎缺乏对我国《民法典》继承编相关规定的规范分析。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都规定了概括继承原则,即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其遗产作为整体转移给继承人(我国《民法典》第1122条)。〔29〕参见[德]安雅·阿门特:《德国继承法》,李大雪等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二宮周平『家族法(第4版)』 (新世社,2013年)311頁参照;冯乐坤:《限定继承的悖理与我国〈继承法〉的修正》,载《政法论丛》2014年第5期,第114页。对比《民法典》第1122条与原《继承法》第3条可以发现,前者对后者进行了重大修改,将遗产范围之规范由“概括+列举”的立法模式修改为“概括+排除”的立法模式。按照新规则,只要是属于自然人的合法财产,在其死亡时全部转化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对比关于继承范围的立法可以发现,在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民法中,继承的对象是“权利、义务”,〔30〕参见《日本民法典》第896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48条。而在有些国家则是“财产”或“遗产”。〔31〕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922条。两者都是以概括继承为原则,在例外情形下需要考虑“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这就是“性质解释问题”。
此处的“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是相对比较模糊的表达,立法者认为这是与人身密切相关的财产权利,〔32〕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解读》(第5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337页。有的学者认为这指的是与被继承人的人身有关的专属权利或者与自然人人身不可分离的具有抚恤和救济性质的财产权利。〔33〕参见杨立新:《我国继承制度的完善与规则适用》,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90页。但也有学者认为以上权利是客观上“不能继承”的权利,而不是依性质不能继承的权利。〔34〕参见马新彦:《遗产限定继承论》,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91页。本文认为,比照国内主流观点以及比较法的规定,此处的“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指的是权利、义务或法律关系具有“一身专属性”而不得继承。所谓一身专属性指的是与个人的人格、才能以及法律地位密不可分,难以由他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属性。〔35〕一身专属性,也称人身专属性。二宮周平『家族法(第4版)』(新世社,2013年)312頁参照;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6页;梁慧星:《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争论——兼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两个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15页。在继承法上,我国学者也基本认为人身权利与一身专属性债权、债务不能继承。〔36〕参见马忆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0页。在比较法上,例如《日本民法典》第896条规定:“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起,继受属于被继承人财产的一切权利、义务,但专属于被继承人本人的除外。”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专属于被继承人本人”便是学理上的“一身专属性”。〔37〕二宮周平『家族法(第4版)』(新世社,2013年)311頁参照。再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48条第1款规定:“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除本法另有规定外,承受被继承人财产上之一切权利、义务。但权利、义务专属于被继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此但书中的“专属于被继承人本身”就是“一身专属性”。〔38〕参见陈棋炎等:《民法继承新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117-118页;戴炎辉等:《继承法》,自印本2013年版,第121-123页。
一身专属性并非继承法特有的规定,而是广泛存在于我国《民法典》之中,比如代理制度(第169条)、债权转让(第545条)、委托合同(第923条)、合伙合同(第977条)等。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法律解释上被认为符合一身专属性的情形,比如劳务合同中的当事人、难以替代的债务、亲权人的地位、扶养请求人的地位等。一身专属性可以分为归属的一身专属性与行使的一身专属性,前者只有特定的人方可行使,没有代位的人;而后者虽然在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行使,但是限定于特定资格的人方可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可以由特定的人代位行使。继承法上的一身专属性为归属的一身专属性。那么,何种权利、义务以及法律关系具有“归属的一身专属性”?在权利方面,包括三种类型:(1)身份权、人格权等非财产权;(2)虽为财产权,但与被继承人之人格或身份相关,如扶养请求权、赡养费请求权等;(3)以特别信任关系为前提的权利,比如因雇佣或委托合同产生的权利。在义务方面,也包括三种类型:(1)以被继承人身份为基础之债务,如扶养义务;(2)债务履行需要被继承人特殊技能或人格的;(3)以被继承人特别信任关系为基础的债务,如职务保证、信用保证。在法律关系方面,只要不以被继承人的地位、身份、人格为基础的,皆可继承。〔39〕参见黄诗淳、张永健:《一身专属性之理论构建》,载《“中研院”法学期刊》第25期,第294-295页。
2.数字遗产的一身专属性及其判断标准
数字遗产中涉及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是否具有一身专属性?这需要根据不同的数字遗产作出不同的判断。一般而言,基于金钱给付内容的权利、义务,比如以银行电子账号、网店等为内容的权利、义务,均是可以继承的;可以转化为金钱给付的权利、义务,也应当允许继承。〔40〕同上注,第317-318页。但是,因人格关系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也因人格消灭而消灭。〔41〕参见程啸:《论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5期,第15页。如此截然分开的做法显然又陷入了上文所批判的分离理论,值得商榷。
本文认为,一身专属性并非简单基于金钱与非金钱或者财产与人格的二分法,而是须根据数字遗产的特征进行调整。数字遗产在许多情况下包含了人格属性,因人格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因人格不存在而消灭,人格权并非完全不可以继承。对于人格权被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如受害人未行使则无法继承,但是如因起诉或依契约承诺的,则已转化为金钱债权,显然是可以继承的,〔42〕参见黎桦:《民法典编纂中的财产性人格权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8期,第15页。这也得到了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判例的支持。〔43〕参见黄诗淳、张永健:《一身专属性之理论构建》,载《“中研院”法学期刊》第25期,第313页。可见,人格权本身虽然不是财产权,但是部分人格权包含财产权要素,以此为根据可以继承部分人格权,也就是说人格权还可以分为高度人格部分和财产权部分,后者存在继承的可能。从人格权发展历史来看,现代私法并不一律禁止人格权通过转让或继承进行转移。〔44〕米村滋人「人格権の権利構造と『一身専属性』(1)」法学協会雑誌133巻9号(2016年)1314頁参照。对于数字遗产尤其是以社交账号为代表的数字遗产,网络服务提供者大多只是平台运营者,其给付主要是技术而非内容,因此所承担的义务并不具有一身专属性。〔45〕在德国“Facebook账号继承案”中,法院即以此为理由否定合同当事人义务的一身专属性。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訴訟のゆくえ(2)」立命館法学383号(2019年)228頁参照。但是,有些数字遗产可能涉及被继承人的交往关系、敏感的兴趣或取向、政治信条、宗教观点甚至网上的信口开河、“毒舌”等,只要在未违法的情况下,都是个人隐私,死者并不想为外人所知,这些内容可能构成一身专属性。书信、日记等虽然也涉及隐私,但一般认为是可以继承的。因而需要明确一身专属性的机能及其判断标准,如此才有利于在数字遗产继承中避免“被继承人的隐私权”和“继承权”之间发生冲突,防止出现“一刀切”和过于模糊的判断。
关于一身专属性的判断标准,有学者认为,主要根据数字遗产的继承是否对被继承人“人格的生存造成困难,存在定型化的危险”,只要不存在这种危险,非财产权部分的人格权也存在继承可能性。只是对于现实中非财产性的数字遗产,上述危险性相对比较多。但是,一身专属性主要是为了保护权利人,并且为了保证整齐划一处理的权利内容的明确性,除了对人格权造成危险的情况之外,都应该认可数字遗产的继承。〔46〕米村滋人「人格権の権利構造と『一身専属性』(5)」法学協会雑誌134巻3号(2017年)461頁以下参照。当然,也有学者对于通过一身专属性尽可能扩大数字遗产继承范围(扩大解释)的做法表示警惕,认为这可能存在损害非财产价值中人格权最根基部分的危险。〔47〕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訴訟のゆくえ(3·完)」立命館法学384号(2019年)151頁参照。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数字遗产是否具有一身专属性需要结合信任、能力或技术属性进行判断。〔48〕参见黄诗淳、张永健:《一身专属性之理论构建》,载《“中研院”法学期刊》第25期,第298页以下。
综上,本文认为一身专属性的分析可以按照如下两个步骤展开。第一步,除非有特殊理由,在被继承人生前发生的金钱或可转化为金钱的给付请求权或者义务,均应认定无专属性,但是如涉及人格权或者身份关系而发生金钱给付义务的除外。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涉及金融账号、网店等相关数字遗产的继承中障碍较少,但是对于不涉及金钱给付的社交账号并不因此否定其继承性。在此基础上,一身专属性的分析需要进入第二步,即该数字遗产所涉基础法律关系是否具有信任、能力或者技术属性,如有则不继承,如无则可继承。关于被继承人与数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一般认为数字服务提供者并不是因为信任与被继承人缔结网络服务合同,即不是专门为某个自然人而订立,〔49〕参见程啸:《论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5期,第16页。甚至相关账号的继承可以继续保持账户活跃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数字服务提供者是有利的,故而两者之间并非因信任而建立关系。但是,如下文所述,对此还需要结合不同的互联网服务合同中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至于被继承人的能力以及技术问题,在互联网利用过程中恐怕并不存在门槛,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未达成年的被继承人或者部分数字遗产的使用会存在技术壁垒等。因此,最终还是要结合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判断是否具备一身专属性的问题。
(二)网络账户利用行为的一身专属性分析
以一身专属性为视角分析数据遗产的可继承性,关键在于探求网络服务合同的本质。因此,下文将通过分析网络利用行为的性质及其对继承的影响,探讨网络服务合同是否具有一身专属性。
1.利用网络账户的合同关系属性
用户的账户密码是链接数据的途径,因而数字遗产中的核心问题是用户账号的可继承性,而这种链接建立在用户(被继承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合意的基础之上,即网络账户的法律属性是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合同关系的履行方式。实际上,用户在开设网络账户时,形式上也会存在用户协议,用户只有点击同意才可以正常开设相应账户。那么这种合同关系的性质如何?是否会影响合同权利、义务的继承,从而成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抗辩理由?
目前的研究多认为,网络服务合同是一种复合型合同,具体属于哪种合同类型取决于网络账户的功能和用途。同时,网络服务合同尤其是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服务合同大多是无偿合同。其中,社交平台网络账户的主要功能是信息传输与展示,具有承揽合同或服务合同的性质,同时具有数据储存空间的功能,所以又展现租赁合同的属性;网络游戏账户等伴随额外可以自由买卖的游戏物品又具有买卖合同的元素;而电商平台则明显具有中介合同的元素。〔50〕参见王琦:《网络时代的数字遗产、通信秘密、人格权——以社交通信网络账户的继承为焦点》,载《财经法学》2018年第6期,第89-90页。德国学者认为网络服务合同混合了使用租赁、承揽以及雇佣合同的要素。〔51〕同上注,第89-90页。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无偿委托合同,应考虑到网络服务合同的无偿性,这对合同类型定性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受托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将数据交给网络用户的义务。
如果该数字遗产利用涉及委托、中介等合同,则需要判断该合同的一身专属性,存在难以继承的可能性;而如果是雇佣、承揽等合同,则雇佣者、定作人等的死亡不影响该合同的继承。另外,作为委托人的网络用户负有偿还委托事务费用的义务,双方对使用合同的性质并没有意图,也没有期待,因此对合同性质的解释应当重视网络用户(被继承人)的意思。虽然继承的对象是合同关系,实际上重要的是数据链接的合同法律性质,决定是否承认该链接的关键在于该网络服务合同本身。如果偏向使用租赁要素的话,站在租赁人的立场,网络用户死亡的,该利用关系并不当然归于消亡,除非该使用租赁存在特别权利继承的约定,否则应按照继承法概括继承。无论是使用租赁还是委托,有偿合同自不在话下,如果重视无偿要素,就不能忽视使用租赁的告知权以及委托的解释规定。当然,如果将其界定为使用租赁,那么在使用期限内出租人就没有任何理由限制继承人登录账号。
网络服务合同虽然大多是无偿的,但是作为交换用户也提供了个人数据,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此为基础可以通过广告等方式获取利益。基于这种现代商业模式的复杂情况,明确该合同及其背后的“当事人(含该服务所涉及的第三人)的意思以及利益”,从而处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双方在遗产继承上的问题。在大多数涉及数字遗产继承的案件中,在利用者死亡后,需要考虑被继承人是否存在让继承人继承并使用该账户的意思,以及运营者是否也有这种真实意图。
2.另一个视角:网络账户与书信、日记等现实私人物件的异同
在数字遗产可继承性问题上,可能会将其与现实中带有隐私属性私人物品的继承相比较,尤其是将其与书信、日记等纯粹个人物品的继承相比较。《德国民法典》第2373条规定,家庭文书以及图片(家庭肖像)不得买卖,第2047条第2款同时规定,与被继承人个人或家庭或全部遗产有关的文书,由继承人共同所有。既然书信、日记等纯粹个人物品可以继承,是否可推导出数字遗产的继承?书信、日记等纯粹个人物品与数据有其相似性,但是两者还是存在明显差异,因而不少学者对两者作相同处理提出了质疑。
第一,互联网上所遗留的数据明显具有更高的敏感性。相较于数字遗产,继承人可以通过物理手段较好地控制日记、书信等信息载体,但是对链接数字遗产的账号而言,其更加敏感,也可以更快复制、传播,且其记录在互联网上难以完全删除。虽然在法律上希望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现象尽可能得到相同的处理,但在遇到数字遗产继承问题时显然是存在差异的。〔52〕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の相続性に関する批判的考察(1)」立命館法学395号(2021年)126頁参照。
第二,书信、日记等在继承结束后,其传递过程也就结束了,通信保护可以发挥作用的过程便随之结束。网络账户上的相关信息并不等同于书信、日记的电子版,两者的本质差异在于,书信在邮政服务者送达后通信内容便无法复制,而网络账户作为即时通讯相关数据得以保存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器上并可以反复长期提取,而且与书信相比,网络数据是在双方之间不断往返的。
第三,从个人信息泄露的“刹车”功能出发,网络账户中的内容显然更为隐秘,侵权的心理障碍更低。在日记、书信等情况下,继承人只能在现实中获取,而在数字遗产的情况下,通常是双方双向交流过程,因此信息读取也更为便捷。
(三)纯粹个人数据的一身专属性问题
关于数字遗产中非财产的纯粹个人数据的可继承性解释问题,存在以下两种学说。第一种是限制解释说。该说认为,可以根据数据有无财产价值区分可否继承,即有财产价值的数据可以继承,而不具有财产价值的数据在内容上具有一身专属性或者具有人格属性的数据则不得继承。同时,前者可以由继承人概括继承,后者只能由关系最近的亲属进行保护。第二种是扩大解释说,该说认为继承法上概括继承的对象包括上述非财产的纯粹个人数据内容。目前,在德国此为通说。〔53〕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の法的処理に関する一考察(2·完)」立命館法学368号(2016年)206頁参照。但是,也有学者对上述理由表示质疑,认为应当区分财产权部分和非财产权部分,只有前者可以继承(即限定解释说)。〔54〕同上注,第206页。与书信等仅限于通信机能不同,网络账户具有现代交流功能,比如有的利用者使用实名,但是只有得到许可的人方可浏览。例如,被继承人会将电子邮件的内容保存在已发送的邮箱里,除非写信人对往来书信刻意复制、留存,一般而言,邮政通信无法单方面对投递的信件进行保存。也就是说,不仅是死者通信对方的秘密,死者本身的秘密也可能成为数字遗产。
对此,本文支持后者的观点。与上文对分离理论的批判一样,按照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的标准确定是否可以继承纯粹个人数据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如下。其一,作为继承法上的根据,原则上书信等都是可继承的遗产,我国《民法典》只是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外,都是可继承的财产,并没有相关规定按照财产价值的有无对能否继承进行区分。在数字遗产的继承中,应当保存或者销毁什么,应当由继承人独立判断,与价值无关。〔55〕参见[德]马蒂亚斯·施默克尔:《德国继承法》(第5版),吴逸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另外,由与死者存在共同纽带的继承人或者近亲属继承纯粹个人数据无论如何也是人之常情。因此,上述划分与继承法的体系与价值判断是存在矛盾的。其二,着眼于数据内容,将其按照有财产价值和非财产价值进行区分本身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现实的。以社交账户为例,其中哪些具有财产属性,哪些不具有财产属性,显然并不能严格区分。而且即便是以财产性权益为原则的概括继承,对于死后人格保护以及通信秘密等隐私权的保护,也需要探讨不同情况的应对之道。其三,区分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法律评价并没有客观根据,从保持法律统一性的视角,数字遗产的法律处理应该尽可能与现实遗产相同。比如,书信、日记等现实世界的遗产当然允许继承人查看,也不可能根据其是否具有财产价值分别进行调查。
三、数字遗产继承的抗辩
如前所述,我国《民法典》一改原《继承法》对遗产定义所采概括加列举的立法模式,采用了概括加排除的立法模式,为遗产的概括继承及数字遗产等新事物打开了口子。故而,原则上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遗产都属于我国继承法上的继承对象。判断数字遗产是否具有可继承性取决于是否符合归属上的一身专属性。那么,在哪些情况下数字遗产可能具有一身专属性而例外地否定其可继承性呢?
(一)合同法上的抗辩: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解释
1.格式条款的抗辩
关于数字遗产继承在合同法上的抗辩,需要分析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在债权债务概括继承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合同格式条款中“不得继承”约定的问题;二是被继承人转让网络账号是否足以影响合同的订立。
按照“债权说”的理解,数字遗产的链接是数字服务提供者与被继承人之间缔结合同的给付。这种链接(即账号与密码)是否可以继承本身也可能是合同约定的内容。因此,几乎在所有数字账号注册阶段,网络服务提供者都会与注册人之间缔结协议约定相关事宜,当然如果用户想要注册账号,该协议一般没有协商余地,即所谓格式条款。调查互联网服务注册协议可以发现,对于涉及金钱类的网络账户(比如金融理财账户),网络服务提供者一般提供完善的继承流程。〔56〕以腾讯旗下理财通账户为例,开户人身故的账户只需要提供逝者死亡证明、火化证明、销户证明之一以及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即可继承亲人离世财产。而同样是存在财产性价值的游戏账户,则几乎不允许继承。对于视频网站的账户,有些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纪念账号,社交网站则几乎都是在注册协议中明确表明不允许继承,且只能由注册人使用。〔57〕例如,《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第7.1.2条规定:微信账号的所有权归腾讯公司所有,用户完成申请注册手续后,仅获得微信账号的使用权,且该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通过受赠、继承、承租、受让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用微信账号。那么,这些不允许继承的格式条款能否成为数字遗产继承的抗辩理由?
传统观点认为,格式条款限制可能成为数字遗产继承的主要法律障碍之一。对于这个障碍的解决,过去的研究多从格式条款无效的角度出发,认为用户大多不会注意或无兴趣阅读不得继承的条款,或难以精确了解其法律意义,因而其不具有正当性,导致该条款无效(或不存在),〔58〕参见黄忠:《限制数字资产流转条款的效力论》,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48-62页。或者从限制解释论上认为死亡继承属于账号转移的合法事由。〔59〕参见梅夏英、许可:《虚拟财产继承的理论与立法问题》,载《法学家》2013年第6期,第86页。关于“不得继承”条款的效力,德国法院在著名的“Facebook账号继承案”中明确提出,“禁止向他人转让或传达密码”之条款不过是为了保证网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为了规制遗产处理,由此条款不能推断出不得继承账号的结论。〔60〕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訴訟のゆくえ(1)」立命館法学384号(2019年)208-210頁参照。另外,关于死者生前能否将账号密码转移给继承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网络服务提供者与被继承人的账号转移性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还是难解的,毕竟即便约定了转移无效的条款,也是对网络用户及其继承人的不利益处理。
“不得继承”条款毕竟是当事人双方约定的条款,虽然按照以上分析不会成为继承的实质障碍,且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限制继承的情况下,这一矛盾确实处于难以调和的状态。但是,权利继承性原则与网络账户的转移还是应当以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解释为中心,而不是按照“不得继承”条款“一刀切”。
2.排除债权转让的抗辩
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可以通过排除债权转让的方式进行抗辩?按照《民法典》第545条,被继承人可以将合同转让给继承人,除非按照债权性质或者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那么,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可以以该网络服务合同性质(即一身专属性)为由主张不得继承?如果被继承人生前将网络服务合同转让给继承人,当事人的特别约定是否可以排除继承?关于网络账号利用合同是否包含一身专属性的问题,肯定者认为继承法上的概括继承只是原则,因此并非所有的数字遗产都可以继承。对此,德国著名的“Facebook账号继承案”判决认为,许可继承人得到被继承人的账号链接可能实质上改变了《德国民法典》第399条(禁止债权让渡)的类推适用,必须排除继承的合同内容的,应以利用关系中的特别关联性(特别信赖关系的一身专属性)为理由,排除继承的可能性。〔61〕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訴訟のゆくえ(1)」立命館法学384号(2019年)201頁参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排除债权转让性推导出排除继承的可能性。社交账号的利用往往与网络用户本人密切相关,是网络用户为了自己而注册使用的。但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签订的网络服务协议显然不只是针对该注册用户的特别的、个性化的安排,大部分网络账号都可以让注册人无偿使用服务,出于商业目的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该网络服务从而放大商业利益。尤其是对于社交账号,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会排除他人与自己缔结合同,因为其商业模式是希望与所有的网络用户缔结合同,也就没有达到排除继承的程度。
反之,如果互联网服务本身不以追求用户数目为目标,而是注重注册者本身的信用、能力或技术的资格审查,则该债权可能是不得转让或继承的。在此情形下,就像医生与患者、律师与当事人之间一样,有些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信赖关系和保密义务,此时两者之间的债权可能是不可转让的。在网络服务过程中,某些网络用户相当于社团中的成员,而社团成员的继承性以及转让性受到严格限制,故而可以不承认其继承性。〔62〕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の登場により法律はアップデートを必要とするか(2)」立命館法学390号(2020年)274頁参照。对此,有反对者认为,将互联网平台视作一个团体的前提本身是值得质疑的。实际上在缔结服务合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详细审查注册者的情况而自动生成网络账号。〔63〕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の法的処理に関する一考察(1)」立命館法学367号(2016年)155頁参照。
总之,关于格式条款是否构成抗辩的问题,在要件事实上法院应判断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信赖关系等因素,而这有赖于两者之间真实意思的探查,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二)通信秘密的抗辩
在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会以保护通信秘密为理由提出抗辩。保护通信秘密的规范依据是我国《宪法》第40条,通信秘密即通信内容和其他通信信息不为其他人知悉或获取的权利。〔64〕参见张翔:《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第45页。宪法学界一般认为通信秘密是一个基本权利。〔65〕玉蟲由樹「ドイツ憲法判例研究(215)一般的平等原則の私法への照射」自治研究95巻4号(2019年)158-159頁参照。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保护通信秘密,不得将包括被继承人在内的互联网个人信息转移给第三人。有人认为,死者的通信相对方也可以请求通信运营商保守秘密,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向继承人许可登录网络账户可能侵害通信相对方的通信秘密。在美国的“In re Facebook Inc.案”中,在Facebook用户死亡后,其母亲要求Facebook公司提供死者的通讯记录,法院认为“公司在民事案件中不能被迫交出账户内容”,在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愿也没有义务提供私人账户记录。〔66〕参见赵自轩:《美国的数字资产继承立法:争议与启示》,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7期,第37-38页。
继承权也是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其与通信秘密保护的基本权利在数字遗产的继承上便产生了冲突。此时,在不同的情形下要确定何种基本权利更为强势就需要考量具体情况进行利益衡量,主要思考以下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向继承人转移网络服务提供者积累的通信内容是否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依据《电信条例》第65条第2款,电信业务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向他人提供电信用户使用电信网络所传输信息的内容。那么《电信条例》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122条第2款所指的法律另有规定?此处涉及对“擅自”要件的理解,一般认为侵害通信秘密的过程应该仅限于传达服务层面,通信相对方的信息内容已经在生前交付给他人,实际上与侵害通信秘密无关了。〔67〕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の相続性に関する批判的考察(2)」立命館法学396号(2021年)152頁参照。“继承权”是“侵害通信秘密”的正当化事由。正如宪法保障继承权,保护继承人的利益通常大于通信秘密。他人对纯粹个人数据的链接需要正当化的“适当的法律上的介入规范”,继承权是一项具有高度人身性质的权利,在被继承人死后归其继承人享有,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第三人的任何干涉都是对遗产的侵害,甚至有德国学者认为法院都没有权利对其作出决定,法官不得有选择地同意或者拒绝进入网络账号。〔68〕参见[德]马蒂亚斯·施默克尔:《德国继承法》(第5版),吴逸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页。故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存在“擅自”向继承人传输信息的行为。
另外,此处还涉及条文中“他人”一词的解释。由于继承权具有合法基础,继承人是被继承人过世后其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的继承者,可以认为就是被继承人本身,因此继承人不属于此处的“他人”,不构成对“他人”提供网络数据传输信息的内容。同时,本文所指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真的构成提供电信服务的业者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意见,即从被继承人的通信相对方角度来看,继承人完全就是“他人”。而且通信相对方完全不知道继承人范围以及继承的安排,也不会想象与被继承人以外的人发生关联,不会也没有打算继续与继承人交流。也就是说,很难想象继承人代替被继承人具有事实上一身专属性的法律地位。
第二个问题是将网络账号移交给继承人是否需要通信相对方的同意。这是因为通信相对方一般不会知道谁将继承数字遗产。基于以下理由,未经通信相对方的同意将网络账号移交给继承人,一般不能成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抗辩事由。首先,想要所有的通信相对方同意网络账号转移本来就是不现实且不必要的,在解释上“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在人格上是同一存在”。实际上,在涉及隐私不愿意公开的情况下,选项应当从通信相对方同意继承转换为其有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继承人删除相关内容。其次,被继承人的通信相对方在社交网络上活动,其本身也应当预料到其通信的网络账号内容为继承人所知的情形。最后,即便按照前述分离理论,正如书信、日记无需得到通信相对方的同意而当然可以继承一样,没有必要区别对待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数字遗产继承也无需得到通信相对方的同意。
(三)死后人格权的抗辩
在数字遗产继承中常有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用户隐私的抗辩,既往研究已表明虚拟财产继承并不侵犯被继承人和第三人的隐私。〔69〕参见黄忠:《隐私是阻碍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理由吗》,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4期,第50-63页。那么,网络服务提供者可否以死后人格权为理由抗辩继承人提出的网络账号链接请求呢?
目前关于死后人格权的抗辩是否成立,存在正反两说。肯定说认为,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未交付网络账号密码,网络账号链接的继承人可能会限制或妨碍死后人格权,理由是被继承人出于各种原因可能不想把个人数据移转给任何人,作为一种权益在死后也应该继续得到保护。死后账号数据免受无限制链接的保护依据在于个人信息决定的基本权利以及数据信息系统的机密性与不可侵性。〔70〕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の相続性に関する批判的考察(1)」立命館法学395号(2021年)135頁参照。换言之,近亲属或者继承人对于死者个人数据的处理虽然享有财产法上的权利或者控制,但是这种权利或控制不得超出维系死者生前身份构建的边界,一旦超出死者生前的身份构建,对死者人格利益造成妨碍,其正当性便是值得质疑的。〔71〕参见陆青:《数字时代的身份构建及其法律保障: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的思考》,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21页。死后人格权保护的问题真正存在于继承人想要继续利用被继承人网络账号的情况,死者的近亲属可以依据侵权请求权以及不作为请求权守护死者的人格权。
否认说认为,在具体案件中,由于继承人往往是被继承人的近亲属,或者说是人格权的代位行使者,因而从网络服务提供者处获得通信内容的链接并不会侵害死者的人格权。同时,继承人或近亲属显然比网络服务提供者更适合作为被继承人人格的保护人。但是,其隐含的意思是死者人格本身并无保护的意义,而此时近亲属本身又不可能侵害死者人格权,因而数字遗产继承也就不存在侵害死者人格权的可能性了。而且在意定继承的情形下,两者之间显然存在信赖关系,书信、日记等纯粹个人物品也可以继承,所以并无争议。但是,鉴于目前被继承人对作为数字遗产的账号信息并不关心,而死后人格权侵害的正当化依据在于被继承人的同意,而本人同意规则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在法国法中,对于侵害肖像权、私生活等情形中“人格权人的承诺”,应该尽可能尊重其意思,承诺的要件包括明确性及特定性,在其范围的解释上必须尊重承诺的目的。〔72〕石尾智久「人格権侵害における被害者の承諾の判断枠組——フランス法における人格権の保護法理との比較」法政論究119号(2018年)426頁以下参照。在德国法中,学理上也认为必须存在数字遗产被继承人对“死后人格权侵害的同意”。如果没有被继承人的这种意思便将其与日记、书信等作相同处理是不合理的。〔73〕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の相続性に関する批判的考察(1)」立命館法学395号(2021年)140頁参照。
本文认为,死后人格权对数字遗产的抗辩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因为在所谓人格塑造的过程中,数字遗产具有重要的作用,且被继承人并不愿意自己的数字遗产被继承。有研究表明,在Facebook的点赞分析中,每个账号月均点赞150次,只要有70个以上的点赞,专业人士就能分析出用户的人格特征,可见数据对人格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以色列的一项网络调查,有31%-36%的用户明确拒绝其他人对自身“数字遗产”的任何访问权。〔74〕参见顾理平、范海潮:《作为“数字遗产”的隐私:网络空间中逝者隐私保护的观念建构与理论想象》,载《现代传播》2021年第4期,第140-146页。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继承人虽然没有留下如何处理数字遗产的遗言,但实际上对于一些涉及个人“人设”的隐私性内容,其本身并不希望包括继承人在内的其他人知晓,也就是说对于该类数字遗产继承的意愿不高。人在生前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人格,死后也有必要继续保障其纯粹个人生活领域不受干扰。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证明数字遗产的继承将明确侵害被继承人的死后人格设定及其意愿的,则可以此为抗辩拒绝继承人继承。至于是否妨碍死后人格保护取决于是否“重度侵害”作为人的尊严的核心部分而存在的人格。在具体案例中,该数据的保密性程度尤为重要,保密性程度越高,则侵害性越强(即所谓相关关系判断)。综上,纯粹个人数据在死后亦应受到人格保护。
四、余论:数字遗产继承纠纷的预防及制度展望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数字化社会的推进,将产生更多数字遗产继承纠纷。从现有法律框架来看,死后数据处理并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定义务与责任。面对海量数据的继承问题,应该考虑纠纷预防的制度安排。
第一,关于立法补缺问题,虽然不少德、日民法学者认为传统民法典足以应对数字遗产继承的问题而无需修改,只需要在个别问题上新设特别规定即可,〔75〕臼井豊「デジタル遺品の登場により法律はアップデートを必要とするか(1)」立命館法学389号(2020年)168頁以下参照。但是为了更加顺利地处理数字遗产纠纷,有必要通过立法明确以下两个问题。首先,立法者应该明确通信秘密不适用于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通信相对方之间的关系。其次,欧洲以及德国的数据保护法都明确了概括继承原则凌驾于第三人(即被继承人的通信相对方)的潜在数据保护问题之上。
第二,应鼓励网络用户(被继承人)利用现有的遗嘱继承制度。被继承人可在生前通过遗嘱对数字遗产作出明确安排。有了被继承人同意的基础,便可极大破除隐私保护或死后人格权的抗辩。对此,应区分以下三种情况进行处理。首先,死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将数字遗产转移给第三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权拒绝第三人提出的继承请求。其次,如果死者生前转移网络账户的意思表示是真实、明确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拒绝继承人转移网络账户的请求。〔76〕参见李雅男:《民法典视野下社交网络账号的继承》,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139页。最后,涉及第三人的,则应该尊重第三人意愿,但仅在其明确表达自己与被继承人之间的相关信息不愿意被他人知晓的情况下,才可以请求删除相关信息。
第三,应鼓励企业提供和扩充关于数字遗产服务的选择。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合同采取预防性手段,从法律和技术层面提醒用户处理数字遗产的链接问题。目前已经有不少互联网企业正在摸索用户死后账号利用规则,除了设置追悼账号,有不少互联网企业还增加了继承条款,并逐渐改变“不得继承”的格式条款。数字遗产的立法趋势是加强对死后个人数据的保护,促进信息的自由决定,强化数据主体的信息自我决定权。〔77〕See Kristin Nemeth & Jorge Morais Carvalho, Digital Inherit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6 Journal of European Consumer and Market Law 253 (2017).此外,如何在技术上区分死后人格权保护范畴内的纯粹个人数据与财产权数据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任务之一。
第四,可以考虑建立数字遗产信托制度。数字遗产信托制度是国外的一种数字遗产转移模式,允许个人为数字遗产设立信托从而加以控制。特别是在我国《民法典》新规定遗嘱信托的背景下,可考虑建立数字遗产信托的相关制度,鼓励网络服务提供者自主开发数字遗产信托的技术方案。有些企业也进行了相关创新。例如,谷歌推出了“非活跃账户管理器”,该程序允许用户从谷歌的每一项服务中指定最多10位受信任的联系人,共享、接收与下载该用户账户至停止使用前的所有数据。Facebook也曾推出遗产联系人制度,允许用户指定联系人在其去世后负责管理后续资料。〔78〕参见顾理平、范海潮:《作为“数字遗产”的隐私:网络空间中逝者隐私保护的观念建构与理论想象》,载《现代传播》2021年第4期,第144-145页。
数字遗产继承是数字化时代的大势所趋,《民法典》第1122条已经为数字遗产的继承提供了请求权基础,但是在具体适用中应该从一身专属性理论出发,而非将数字遗产简单分为财产性法益与非财产性法益,并在承认数字遗产可继承的基础上细化例外情形下的抗辩理由。此外,对于死者个人数据,应在其尊重人格权以及财产权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保护死者的数据自我决定权,这也是相关制度设计的根本出路。正如日本著名民法学者铃木禄弥教授所言:“继承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哪些属于遗产,而是在于继承人之间以及继承人与非继承人之间的衡平,以及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思。”〔79〕鈴木禄弥『相続法講義(改訂版)』(創文社,1996年)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