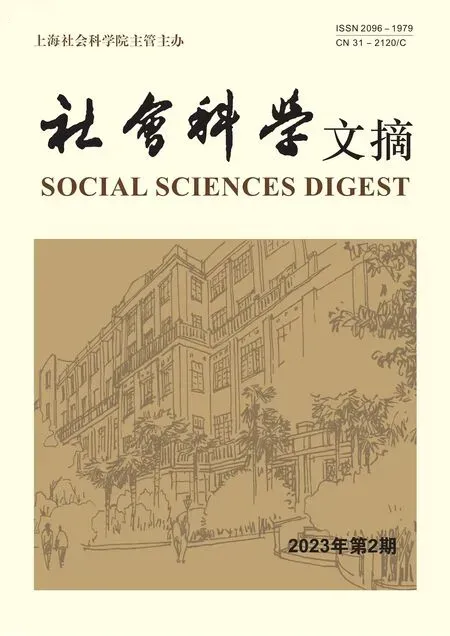《庄子》中的良好生活:形式与内容
2023-04-06黄勇王振钰
文/黄勇 译/王振钰
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令人瞩目的复兴,对一直主导现代伦理学话语的义务论伦理学和功利论伦理学形成挑战。在亚洲思想传统的研究中,包括印度教、佛教以及最重要的儒家思想在内,传统儒学中的美德伦理学潜力也被不少学者所探索,但对道家特别是《庄子》的美德伦理学潜能却关注甚少。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长期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庄子》并非伦理学著作,甚至不包含伦理学思想,如果说包含的话,也不过是问题重重的道德相对主义。近来有学者注意到,虽然《庄子》在很多问题上持怀疑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立场,但《庄子》里面包含着某种良好生活观,因为《庄子》明确赞扬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类生活。但他们强调,《庄子》所赞扬的人类生活,只是由于这种生活的形式,如庖丁在解牛时所体现的轻松自在,而不涉及这种生活的内容。还有学者由《庄子》蕴含良好的生活观就简单认定《庄子》也有美德伦理学。然而若《庄子》真的只关心人类生活的形式而不关心其内容,就会出现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问题,如把像庖丁“解牛”一样轻松自在地“解人”的职业杀手的生活,也看作是良好的、具有美德的生活。事实上,良好的人类生活应当有其内容向度,而这种内容一定与人之为人的特性即人性有关。在我看来,《庄子》不只关心人类生活的形式,即轻松自在;也关心行动的内容,即对他者与己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这种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作为道家美德伦理学所推崇的最高美德,不仅是我们熟悉的其他美德伦理学类型所忽略的美德,也是生活在这个全球化、多元化时代的我们所必需的美德。
良好生活的形式:轻松自在
各种类型美德伦理学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有德之人生活自然、轻松、优雅、快乐、自在。例如,丹尼尔·斯塔特曼(Daniel Statman)声称:“有美德的人‘自然地’做正确的事情,不需要与情感、倾向或性格做斗争,不存在‘精神’与‘身体’或‘理性’与‘激情’之间的任何冲突。”这与康德主义和后果主义伦理学形成了对照。前者突出遵循道德原则,后者强调行动的后果,至于遵循道德原则或产生最好后果的行动本身是否轻松、优雅、快乐、自在等并无道德价值。
在这种背景下探索《庄子》美德伦理学的可能性,人们自然会被其中所谓的技艺故事所吸引。用艾伦·福克斯(Alan Fox)的话说,在这些故事中,各种大师像自动驾驶仪一样非常轻松地执行各自的任务。庄子通过“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木匠梓庆”等技艺故事告诉我们的关于自发性、优雅、轻松、快乐等所有这些道家圣人的特点,使一些《庄子》的研究者误以为这些故事中描述的生活已经体现了道德上的美德。例如,福克斯声称庄子的伦理学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它所要求的不是遵循伦理规则,而是发展品格”。在福克斯看来,正如在庄子道德认识论中唯有真人才能有真知,在美德伦理学中只有善人才能有善行。葛瑞汉(A.C.Graham)、艾文贺(Philip J.Ivanhoe)等也认为:“这些故事使人们相信庄子并非道德怀疑论者,他认为有些人不仅理解一种更好的方式,而且理解道本身。”显然,所有这些技艺精湛的人在这些技艺故事中都是作为积极的、堪称典范的人物出场的。问题是:他们仅仅是在各自的行当之内称得上典范,还是在一般的人类社会当中也能如此?他们所领悟的道仅仅是在各自的行为中所践行的道,还是普遍的伦理之道?
不同于上述几位学者对我们问题的肯定回答,文策尔(Christian Helmut Wenzel)抱怨说,这些技艺故事“仅仅教导我们如何在目标设定后达到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接受什么目标并将其设定为自己的目标”。在文策尔看来,《庄子》或许也可以教会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小偷或职业杀手,就像它教会我们成为一名好厨师一样;也就是说,它会教会我们如何轻松、快乐、自然地去偷窃和杀人。陈汉生(Chad Hansen)基于他所主张的弱版本(即不只是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也认为《庄子》的伦理学不允许我们谴责希特勒,尽管也不允许我们说希特勒的视角和我们的一样好。因此,亚瑟·丹托(Arthur Danto)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老庄的哲学要求“瓦解了使道德成为可能的条件,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违背了道德。所以他们应该受到同样的指责”。
我同意艾文贺等人的观点,即《庄子》中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也同意文策尔等人的观点,当我们单独阅读这些技艺故事时,它们是道德中立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阅读这些技艺故事的同时阅读其余的文本,特别是一组我称之为“差异故事”的文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庄子式的道家美德伦理学,它特别强调道家最重要的美德,即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一种为我们所熟悉的任何美德伦理学版本中所忽略的美德。
良好生活的内容: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
庄子强调要认识和尊重道德行为者与道德接受者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道德接受者之间的差异。不仅我们出于自我利益做伤害他者的事是错误的,为了自认为出于他者利益而对他者做的事也可能是错误的。原因在于,我们认为对他人有益的东西并不一定被他者所认可,而被一个他者认为是好的东西,也有可能不被另一他者所认同。由于我们行动的接受者是特定的他者,他们可能与作为行动者的我们或其他任何人不同,我们必须采用我们行动的实际接受者的标准,而非其他任何人的标准来评估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认为对我们有利的东西也必然对他人有利,从而将我们的善的标准强加于他人,灾难就可能随之而来,这正是《庄子》中“浑沌之死”故事的寓意。
在“浑沌之死”中,倏、忽二帝出于“善意”为浑沌凿出缺失的七窍,其结果却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不明白,世间之物不仅不同,而且具有平等的价值。他们没有意识到,要使事物平等,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使他们完全相同,特别是与我们自己相同;而是承认与我们不同的并且相互之间也各不相同的他者都有同等价值。这个观念在《庄子》的“鲁侯养鸟”“伯乐驯马”等故事中也有生动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庄子》的差异故事虽然常以动物作喻,其落脚点却在人。比如,《庄子·齐物论》讨论适合不同动物的居所、食物和美色各不相同以后,马上就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论:“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肴乱,吾恶能知其辩。”很显然,这是针对儒、墨用某个(些)统一的仁义是非标准来规范所有人的行动,而不是所有动物的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庄子》阐释不同物种的不同特性需要不同对待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以类似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在《庄子》看来,我们要看到不同人的不同之性,并根据他们各自的不同之性去对待他们。
庄子通过这些差异故事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伦理信息呢?有些学者依据《庄子·天下》篇中的“常宽容于物,不消于人,可谓至极”,认为庄子在这里所提倡的就是重要的现代价值“宽容”。在我看来,用宽容来概括这些差异故事的伦理蕴含,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现代语言中的“宽容”意味着宽容的对象中有我们反对的东西,而《庄子》这里并无此意;二是宽容在这里只能表达不干预他者差异性生活方式的被动性伦理思想部分,无法展示《庄子》伦理思想中尊重他者差异化生活方式的能动部分。因此,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而非宽容,更能综合反映《庄子》的伦理信息。
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美德与良好生活
从《庄子》差异故事中表达出来的对差异性的尊重到底是一种道德义务还是一种美德,这牵涉到我们如何看待《庄子》的差异故事与技艺故事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庄子》的差异故事与技艺故事应该结合起来理解,因为它们传达了同一伦理信息的两个不同方面。差异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合乎道德的生活的内容:尊重他人的不同生活方式。技艺故事则告诉我们从事道德行为的形式:自发、自然和不费力。把这两类故事结合起来看,我们就能发现,《庄子》所强调的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不能做义务论的解释,而应该做美德论的理解。换言之,《庄子》里的尊重不是道德原则,而是美德。具有这种美德的人能够自然、自发、毫不费力地尊重具有同等价值的他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具有这种美德的人能够将他(她)的天性与道德对象的天性相匹配(以天合天)。另一方面,我们也就不必担心,这些技艺故事会让我们以为,职业小偷和杀手的生活也可能是良好生活。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职业小偷和杀手等不尊重道德行动的接受者。换言之,这些人虽然具有《庄子》所推崇的有德者相同的生活形式即轻松自在,但与有德者的行动的内容不同甚至相反。这种内容要求我们尊重与我们不同的他人的生活方式,认为其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从逻辑上讲,它就不能容许任何不尊重具有同等价值的其他生活方式的存在。
方克涛(Chris Fraser)认为单独从技艺故事中就能理解庄子的良好的生活观。因为,庄子的良好生活观主要关心的就是如何过一种生活,具体来说就是作为形式的“游”。然而,在我看来,如果这种良好生活观之“好”只涉及生活的形式而不涉及生活的内容,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职业杀手,只要他们在杀人时像庖丁解牛时那么游刃有余、自然、轻松、优雅,也就可以看成是在过一种良好生活,而这显然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良好生活观。另一方面,离开生活的内容来看生活的形式,我们无法确定这种生活的好坏。要理解“良好的人生”中的“好”的意思,需要理解什么是人生,它与别的动物和植物的生命的差别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人性。
良好的人生就是充分体现了人性的生活,良好的人生不只涉及如何生活,更重要的还涉及什么样的生活。差异故事中表达的对差异性的尊重的美德,正是《庄子》里面蕴含的一种说明何为良好的人生的恰当的人性观。必须注意的是,《庄子》里面全面而复杂的人性观至少包含两个虽不相互隐含却并不相互矛盾的方面。其中的一个方面是将人作为行动对象时应该特别注意的。不同的行动对象由于有不同的性格,对于什么是良好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一个行动主体不但不能将自己认为是良好生活的所有方面看作也是其行动对象的良好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且也不能将一个行动对象的良好生活的所有方面看作是另一个行动对象的良好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个复杂的人性观的另一个方面则是所有的行动主体,按其本性,都没有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他人的倾向,而有关心和尊重他人生活独特性的倾向。如果前一个方面强调的是不同行动对象之殊异性,后一个方面强调的则是所有行动主体的共同性。至于现实中人们缺乏认识和尊重我们的行动对象的差异性的自然倾向,则在于成心并非本心,因而有待于人类通过“心斋”与“坐忘”来克服成心,以恢复本心。
心斋与坐忘:培养尊重差异的美德
尽管成心不是人与生俱来之物,也非至德之世的人们所拥有的美德,但事实上,庄子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也一样),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成心,几乎没有人拥有尊重与己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美德。因此,要摆脱成心,恢复对他者的尊重这种美德,人们有必要开展道德方面的修养功夫。《庄子》提出了许多道德修养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庄子·人间世》的“心斋”和《庄子·应帝王》的“坐忘”。
《庄子·人间世》中说:“虚者,心斋也。”心之空虚也即心胸开阔。“心斋”的目的就是要清空心中所有的偏见、意见和先入为主的思想,即成心的内容。因此,庄子常用明镜来比喻圣人或完人能不加褒贬地反映事物本来面目的心灵,所谓“至人之用心若镜”(《庄子·应帝王》)。固执己见的心则如同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与此有关,庄子也用水喻来描述圣人或至人的心灵,“平者,水停之盛也”(《庄子·德充符》)。庄子试图用水喻来说明本心的这一特征,就是心不与他人争论,而总是顺从于他们,这就是圣人与人交往的方式(顺人)。同样地,圣人也不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庄子·应帝王》)。
与“心斋”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坐忘”是返性修德的另一种修养方式:“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应帝王》)“坐忘”与“心斋”密切相关。“心斋”,如我们看到的,就是要把心中的先见去除,而“坐忘”则是要将这些东西忘掉,实际上是一回事。因此徐复观说:“心斋的‘未始有回’,坐忘的‘堕肢体,黜聪明’,都是‘无己’、‘丧我’。而无己、丧我的真实内容便是‘心斋’;心斋的意境,便是坐忘的意境。”
无论是在庄子所处的时代,还是今天,要培养尊重不同生活方式的美德,都需要开展恰当的修养功夫,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心斋”和“坐忘”,它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要去除成心,恢复本心,即尊重不同生活方式之心。由于这种尊重与人性有关,因此,良好的人生就是人之为人的性得以充分实现的生活,真正的良好人生就是对人们的不同生活方式加以尊重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