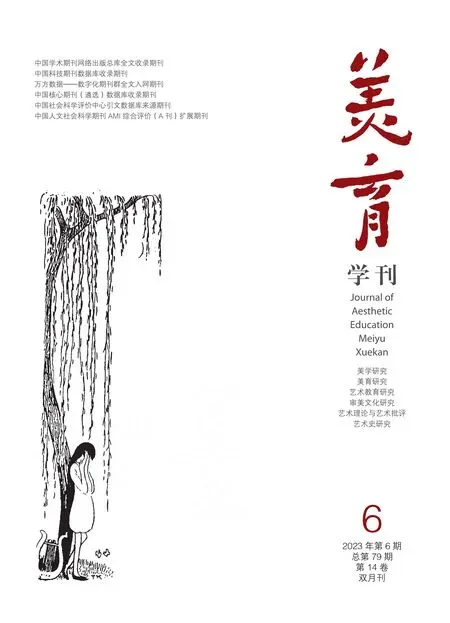戏剧美育在新时代人格涵养中的作用
——以古希腊悲剧经典为例
2023-03-24桑丹,陈敏
桑 丹,陈 敏
(中央戏剧学院 a.戏剧文学系;b.戏剧学系,北京 102209)
康德将人的内心全部能力区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总目的是在知情意(即在哲学、美学、伦理学)三方面都要达到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调和”[1]300。知(知识)帮助人认识客观世界,而情(审美)与意(道德)则生成于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关系。知与意从属于因果律,而情因其主观经验性而不受因果律的制约。知与意是逻辑的、有限的、约束的,而情是直觉的、无限的、自由的。知与意的既定秩序与人类自由意志的冲突不仅永恒存在,而且这种冲突所激发的人类生存情感即普遍人性正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性的具体表现。知与意两层面对于人的自由意志所构成的困境与其说是一种冲突,不如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正如马拉美所言,“戏剧最根本的主题是人和宇宙的对抗”[2]。对于悲剧来说,最奇妙的不是痛苦,而是人物对待痛苦的方式;引起人们振奋的不是灾难,而是人物的反抗。命运可以摧毁个人,却无法摧毁人的伟大与崇高。当生活中知与意的既定秩序与介入其中的人的自由意志的冲突被显现于舞台之上时,戏剧性冲突则能激发观众的情感,进而令观众开启对困境中的人物形象的审视与反思。正是人类生存情感被悲剧激发,人身处知与意困境中的现实受挫才得以慰藉与参照,进而反思内在的主观世界,确证其与存在的关系并指导实践——认识和改造外在的客观世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从知、情、意的角度探究古希腊悲剧经典,不难发现,知(知识)和意(道德)的困境来源于悲剧诗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与悲剧诗人的主观情致化合最终呈现于舞台中央,形成一个个不泯的戏剧人物。它是一种依托于知与意的困境中的人类生存情感的符号创造,其戏剧性是戏剧中人物和情境的契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由此实现知、情、意的调和。古希腊悲剧经典显然没有完全独立于日常生活,审美与哲学、政治、宗教、伦理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希腊悲剧经典作为西方古典美学的范畴,具有他律性特征。中国美学基于主客一体到主客二分的中国哲学转向继而发生从自律到他律的现代性内部变革,同时受到西方现代美学从他律到自律的反向外部影响,因而显得更加独特与复杂。随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入,中国现代美学才呈现出美学他律性的主流特征,强调审美的功利性、艺术的政治性和趣味的大众化。据此,不难发现古希腊悲剧经典作为西方古典美学范畴与中国现代美学在美学特征上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同构性,这也是其能成为当代中国美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要介质的根源。
一、戏剧审美机制:知、意困境激发情感、塑造人物
戏剧是以演员塑造的舞台人物为核心的融合了艺术的各个门类以及文学的一门视听综合性剧场艺术。它不仅是一种制造快感的娱乐与技艺,更是重要的、真实的和普遍的文化媒介。戏剧美育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戏剧美在哪里、其审美对象是什么。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剧作家阿瑟·米勒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视古希腊戏剧为典范,“因为其人物都是以追寻自由理想为目的的感性生命的存在,所以都是呈现‘美’的‘完整的人’”[3]。这里“完整的人”指的是人性的完整。塑造“完整的人”的审美人物,是戏剧艺术的美学使命,而审美人物就是戏剧审美的对象所在。
古希腊悲剧经典在审美人物的塑造上,凸显人类生命的尊严和意义,更强调对完整的人的追求。“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人性的尊严靠的是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悲剧作家们给了我们确定的回答。”[4]戏剧是总括的艺术,其揭示人类多面性的特质决定了戏剧性形式中人的生命存在与知、意既定秩序的密切关联。戏剧从来都不会离开生活,尤其不会离开那些卡在知与意困境中的生活。“悲剧是人类试图摆脱无法克服的窘境与社会、与他人及自我进行的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5]正是介入知与意的困境,拓展了戏剧的表现手段,显化了戏剧冲突,强化了舞台艺术与观众所处当下现实的关联,丰满了审美人物的生命形象。“对于心智相关的秩序和越界的兴趣,确实是古希腊悲剧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6]292悲剧诗人描绘伟大的、不愿接受人之为人局限性的个体,以此与知的困境抗争。当然,这种界限也包括别林斯基所说的在每个悲剧的内容里都有美学上允许的道德问题,即意的困境。韦尔南所提出的“悲剧时刻”的概念,“也是围绕着英雄、传统的规范与流动的社会中新出现的法制和公共价值之间的张力展开”[6]225。概言之,无论是知识还是伦理、道德、法制所建构的令雅典城邦骄傲的既定秩序,悲剧诗人总是在他们的戏剧艺术作品中试图将这些状似完满的知与意的既定秩序的确定性撕开一条裂缝,注入不确定性的、异于常理的混乱,将知、意的困境以戏剧情境的形式显明地摆在戏剧人物所处的当下,令其在种种两难的、撕扯的绝境中向着知、意秩序的既定界限试探、冲撞。情的无限性冲破了知与意的有限性,自由的狂飙注入秩序的井然,为人类与人类社会的向前迈进拓展了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空间。观众将自我完全沉浸于悲剧人物立足的情境,在和人物情感共鸣中沟通了自身生活现实的知与意,完成知、情、意的互动交融。达成了观演关系中的慰藉与参照,所谓美的观照,指“我们把其他一切的诱惑加以断绝,而专一地陶醉于对象生命里面”[7]。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即人类的生存情感,是从杂多具体的情感中抽象的概念,具有本质性。正是在审美人物所处的知与意的困境中通过戏剧行动激发的人类生存情感,实现了人物对现实既定秩序的审美超越,令观众与审美人物一道在戏剧人物的生命体验与感受中迸发出强烈的追求真理、正义与至美的愿望,内在心灵也在戏剧鉴赏中实现审美超越。通过以上关于戏剧审美机制的阐述,不难理解悲剧缘何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古希腊文艺的最高形式并承担着公民教育的社会功用,悲剧诗人亦被视为公民的教育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到悲剧的功用,即通过引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使情感得以净化(即卡塔西斯)。卡塔西斯所针对的是作为观众的人,所依托的则是作为戏剧审美人物的人,归根结底,反映社会现实的悲剧艺术是为了寓教于乐、审美教化。
戏剧“创造了一种虚幻的经验和历史”[8]21,所表现的正是人类情感的本质。苏珊·朗格不再将直觉与理性对立,而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直觉交融了情感、想象、感知,成为理性思维的起点。人类思维的发展,就是在直觉与逻辑的共同作用之下才能得以完成。而古希腊悲剧经典的美育价值就在于实现了审美直觉与逻辑思考的联系与调和。戏剧审美的过程,同样成为理性思维的起点。悲剧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太多人类固有的局限性,当观众体验到戏剧人物所处困境中的压抑、焦虑、困惑、痛苦与迷茫时,悲剧诗人就将观众引向人类生存情感的天光中,戏剧中心人物在承担起自己命运的同时也真正意识到了人的有限性与世界的无限性,并成为一个“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9],承担自己的责任、承受自己的命运的真正的理想的人。
黑格尔将希腊古典艺术视为精神内容和物质形式的完美契合。他把独立自足性视为理想的人物性格所必有的主要特征,在他看来,理想的人物性格只有在理想的环境中才能形成,理想的环境即英雄时代。“就个人对社会的关系而言,他一方面依存于社会,接受社会的理想。另一方面不受社会限制,……能凭自己的意志去实现这种理想。”[1]436古希腊悲剧经典在舞台上的呈现,可以说是英雄时代的理想环境。英雄时代所赋予舞台上的知与意的困境会体现为更为压缩的时空环境、更为激烈的事件冲突、更为复杂的人物关系。悲剧人物,即便身处命运之神搅动的湍流漩涡中也不失其高贵与庄严,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这残酷的命运,昭示了黑格尔所说的真正的悲剧精神。“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人,不能成为真正的悲剧主角,凡是不计成败、奋起斗争、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人物才最富于崇高严肃的悲剧精神。”[10]以死亡落幕的悲剧人物却在观众心目中成为永恒不泯的英雄,流芳千古。在黑格尔看来,“他个人虽然毁灭,他所代表的理想却不因此而毁灭。所以悲剧的结局尽管是一种灾难和苦难,却仍是一种调和或永恒正义的胜利”[1]441。可见,古希腊悲剧经典在展现理想的审美人物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亦是审美和美育的理想介质。
二、知、意困境激发情感:以《俄狄浦斯王》为例
正是在索福克勒斯所处的时代,戏剧创造了一种人民与国家互动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评价其作品《俄狄浦斯王》为:“希腊悲剧的典范,十全十美的悲剧……剧中的悲剧冲突、悲剧性格、悲剧效果都足以代表古希腊悲剧的最高水平。”[11]俄狄浦斯所陷入的知、意困境表现在人神之争,即人的自由意志与神谕的对抗。弑父娶母的神谕,无论之于俄狄浦斯还是舞台下的观众都是戏剧开场后人人皆知的秘密,而俄狄浦斯则是通过选择背井离乡、不见父母,在三岔路口杀死老王,破解斯芬克斯之谜,拯救忒拜成为新王,玷污母亲床榻等一系列戏剧动作极力声言:知命而不认命,也就是即便我知道我是谁,但我偏偏不想成为我。悖论在此发生,正是俄狄浦斯自由意志驱使下的人的理性与神谕的对抗,反而助推神谕在其身上的依次显现。这显然是一个隐喻,人类自由意志一直在对抗且受限于现实世界,这种冲突从人类起源至今从未停止。然而古希腊悲剧经典则可以将这种冲突以及冲突所激发的情感呈现到一个至今似乎都难以企及的高度。索福克勒斯残酷地将俄狄浦斯置于神谕与谜题席卷的属于知、意困境的风暴眼中,将俄狄浦斯的知与意层面的自信撕得粉碎。西格尔称:“希腊戏剧中没有哪一个角色比俄狄浦斯更强烈、也更悲剧性地体现了人类文明力量的诸多悖论。”[12]
戏剧开场,凭着过人的智慧赢得第一公民称号的俄狄浦斯王,在众人眼中就是智慧卓然的“最高贵的人”[13]348,是智慧与德行的典范。“我们是把你当作天灾和人生祸患的救星”[13]347,在城邦人民的拥戴与厚望中,无论是知还是意,他都显出异乎寻常的自信,甚至志得意满地认为自己是“幸运宠儿”:“我认为我是仁慈命运的宠儿,不至于受辱。幸运是我的母亲。”[13]375这显然是具有反讽意味的,一个一直在神谕阴影笼罩下的逃亡者,却在理性的对外延伸的行动中走向膨胀与迷失,而这也预示着他终将沦为“一切污染”[13]354、沉堕自造的耻辱。于是,俄狄浦斯种种与神谕对抗的行动,状似自由意志驱使的理性选择、无往不胜,实则凸显了他的刚愎自用、对旁人狐疑满腹等人性的缺陷。弑父娶母的命运神谕,反而成其不断对外归因、向外攻击的最大借口。
具体而言,俄狄浦斯作为戏剧人物的复杂性,在于他时刻摆荡于知与盲、高贵与耻辱的两极。他可以凭一己之力破解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谜题而拯救城邦、承袭王位、走向伟大;然而另一面,他一直是那个每分每秒提心吊胆的弃婴,那个永远被阿波罗神谕封印的命运的逃犯。而缉凶和自查两个戏剧行动线内外交织,向外的缉凶(查找杀死老王的元凶),向内的自查(我是谁),二者有时间线上的前后承续,在观众眼中却是双流交织的一体两面。含蕴哲学意味的斯芬克斯之谜,用脚的意象象征人的行动性。它代表人以一生为尺度的向外延伸、对外探索宇宙真相即人对自然的科学探索(知)、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建构(意)。俄狄浦斯,这个名字一语双关,本意是脚肿的人,同时意为知道脚谜语的人。他之所以能够猜出谜底,恰好因其一直以来信奉与坚持的自由意志驱使下的不断对外延伸的行动力,这恰是西方理性文明走向科学探索的集体无意识。缉凶与自查行动线交织,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最佳的发现”,即“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14]而俄狄浦斯的发现与突转极力声言的正是在进步和知识获取的叙事中人对自身认识与控制的不确定性。诺克斯对这种探究用语的分析值得玩味:“悲剧中的这一行动,不计后果、坚持到底追查痛苦真相的行为,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科学探索。”[6]343
俄狄浦斯最终陷入了“你虽然有眼却看不见你的灾难”[13]357的自我认知困境,母亲成妻子、子女成兄妹的道德伦理困境。知、意困境所激发的人类生存情感——一边是对外界高扬的剑所指代的无所不能的自负,一边是刺瞎自己双眼的母亲的金别针所代表的对自造困境无能为力的自卑——将观众引向沉思:何谓理性?理性为何?或许能给这一悬思以启发的是剧中的另外一个隐喻——瞎子,曾是俄狄浦斯面对先知忒瑞西阿斯将元凶的线索逐渐指向自己时回击的最为恶毒的语言暴力,曾被其自负地视为无知的象征,而在戏剧落幕前,俄狄浦斯以自戕双目承认了其对于自身的本质性无知,并通过自我放逐的方式实现自我惩罚,进而实现了对理性悖论的审美超越。
伯格森认为,人类理性的狭隘功利活动,根本不能形成对生命的真正认识。克罗齐则认为,只有直觉认识才是一种完善的、无所不包的认识形式。克罗齐的直觉理论对艺术表现了强烈的反理性主义。19世纪末以来,科学家们才渐渐习惯把他们的规律和理论看作近似的知识。如梅洛-庞蒂所说,“科学的任务——去澄清具体之物、去澄清感性之物——是个无穷无尽的过程,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完成”[15]。因此,面对知、意的困境,悲剧艺术显然不会将解决问题的出路诉诸知识的研讨与伦理的思辨,而是以艺术特有的审美方式,通过戏剧人物的命运体验激发人类生存情感,为那些人类既有秩序中的不可解之谜,打开一扇窗,照进美的天光。
三、古希腊悲剧经典审美机制的美育启示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不仅因为它是人类最高智慧和最高美感的结晶且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在时间长河中经过洗练且持久恒远,不断地形塑着人类精神。“马克思每年要把埃斯库罗斯的原著读一遍。他始终是古希腊作家的忠实的读者。”[16]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17]古希腊悲剧经典,之所以迄今为止仍然在全球范围享誉不衰,从戏剧美学角度探因,就在于通过情境与人物的完美契合,实现了知与意的困境中所激发的审美人物的人类生存情感即普遍人性与观众现实当下体验共鸣的永恒性。换言之,人类从起源开始就一直承受着自由意志与现实世界冲突所带来的痛苦。自由意志有无限可能,现实世界却处处受限。人类自有生命开始,其终极目的就是获得自由和解放。因此,人类产生了一种创造艺术的迫切需要,只有艺术才能冲破现实世界的重重限制进而使人们缓解内心的痛苦。于是,我们在鉴赏古希腊悲剧经典时,沉浸于那些英雄人物拼尽全力与知、意困境对抗的生命流变中,将戏剧审美人物作为理想的永恒对象讴歌与传颂。
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目标。在马克思心目中,人类解放的标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8]。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深受席勒影响,曾称席勒是“新思想运动的预言家”[19]。美育一词便是席勒最早提出的。他明确界定美育即情感教育。席勒认为,人性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本性:感性与理性。他肯定感性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价值。美育能够使人的感性和理性趋向平衡,进而恢复人性的尽可能的和谐。黑格尔称赞席勒敢于超越康德的思想界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20]。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正是席勒所提到的“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在满足游戏冲动的道路上去寻求人的美的理想”[21]。美,能将分裂的人变成自由、完整的人。审美教育可以使艺术美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实现于生活。这开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审美的生存的新人文精神路径重塑,关系到人类长远持续美好的生存。
艺术活动作为一种集中而复杂的以创美为中介的审美活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统,“创造—作品—接受是这个独特系统中的三个主要环节”[22]。冯友兰先生把通过审美还原驻留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格称为风流,同时认为“风流是一种所谓人格美”。[23]冯友兰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构成真风流的条件:必有玄心、必有洞见、必有妙赏、必有深情,强调了审美的超越性、直觉性、人情化、无目的性。冯友兰把风流当作一种人格美,可以启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风流同审美人生之间的关系。他把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被其视为人生境界中的最高者,又称同天境界即天人合一。实现大全的人生境界,成为冯友兰境界论及美育思想的最高目标。人格和境界的提高,从更深远的层次讲,需要通过审美来解决。把冯友兰风流人格美的阐释、席勒的美育观点,与古希腊悲剧经典知与意的困境激发情感展现审美人物的戏剧审美机制相结合,会发现,一切教育形式中都应该渗透审美教育,而美育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这是美育最根本的理念。美育需要内外兼修,对内强化和谐人格的培养,对外理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朱光潜先生认为:“心有知、情、意三面,教育求在这三方面同时发展,于是有智育、德育、美育三节目。”[24]科学、道德都具有既定秩序的边界性,科学只能研究与解决具备客观现实基础的问题,凡与人的情感、意志相关联的问题,都难以用科学方法加以解决;而道德往往难于突破地域、民族、习俗的范畴,局限在特定历史阶段,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却难以约束人的内心世界。而科学的真与假、道德的善与恶,又具有时移性,彼时的真或是此时的假,此时的善或是彼时的恶。而只有人类生存情感却能跨越时代、跨越种族、跨越国界一直以生命存在的形式影响着人类精神活动与情感活动的深层心理结构。艺术就成了“为表达基本生命而发展了的可塑形式”[8]62。古希腊悲剧经典,正如席勒在《美育书简》里言称的,有映象生命的能力,把生命和形式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活的形象,一种生命形式,艺术因而具有强烈感染力。古希腊悲剧经典作为古典主义美学范畴,具有美学的他律性特征。据此,戏剧美育可以成为智育、德育的中介进而实现知、情、意的沟通互融。诚然,戏剧美育不仅是戏剧教育,更是通过戏剧审美的方式提升受育者的审美体验能力,进而产生一种高远的人生追求,提升自我的人格境界。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我们心中不可没有诗意、诗境,但却不必定要做诗”[25]。
戏剧美育贵在戏剧审美,而戏剧审美则需要美育者带领受育者通过戏剧赏析来实现传播与育化,最终使受育者在戏剧艺术中感受美、欣赏美、陶冶美,以达成戏剧的美育之功。植根戏剧本体论,通过戏剧美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升美育者的戏剧赏析能力是戏剧美育的当务之急。戏剧审美,美在人物,而人物和情境的完美契合,是戏剧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戏剧人物在戏剧情节所建构的知与意困境中所呈现出的独特丰富复杂的个性情感命运,则是需要美育者进行戏剧赏析的重点与核心。以此为抓手,戏剧美育要培养观众在鉴赏时能在戏剧情境呈现的复杂人物关系中找到人物行动背后的幽微动机的能力,通过对人物动机和行为的判断,对情绪或情感的性质进行体验式识别,进而把握人物的个性情感特征,通过情感共鸣实现审美超越,实现知、情、意的沟通,使直觉、感知、情感、想象成为理性思维的起点。通过审美体验、反观自省、心灵觉悟,进而丰富和提升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待人处事的能力。
“欣赏如果不‘再造’出作者所‘创造’的东西,它就会成为被动的接受,就体会不到艺术作品的真正的妙处。”[1]568。戏剧美育以创美、审美的巨大动力,强化人的创造力、想象力,进而推动科学与道德向更高维度开疆拓土,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戏剧赏析,既赏又析,赏偏感性,析偏理性,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谓赏中有析,析中有赏,彼此依托互为提升。然而,作为戏剧审美核心内容的戏剧赏析,却时常受限于赏析主体对戏剧本体的把握不明、戏剧美学观念的偏狭、意识形态的矛盾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状况。因此,提升戏剧美育水平,前提是需要提升戏剧美育工作者的戏剧美学理论水平与戏剧美育的业务能力,重点在于提升其戏剧审美能力和戏剧赏析水平。欠缺戏剧审美能力的育人者很难达到戏剧育人的目的,而没有科学规范的戏剧赏析方法和有效的戏剧赏析传播,戏剧审美就只能成为育人者的独美。
除了专业能力,更要重视戏剧美育工作者正确的历史观、时代精神与自身人格境界的提升。克罗齐认为,历史的透视是文艺赏析的一个重要条件,“不置身于作者的历史情境,就无从了解作者以及他和他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不结合到自己的当前历史情境,也就不能凭实际生活经验去体会作品,不能使作品对自己发生正当的作用”[1]568。新时代的中国戏剧更强调戏剧艺术的人民性。戏剧艺术既要满足人民的审美趣味,又要不断提升人民的审美素养。戏剧艺术本身就承担了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和美好情操的时代新人的目的与使命,向来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美育方式。然而,过去在戏剧美育中往往过于强调知识灌输、技能培训、道德批判,轻视心灵育化与人格培养,不注重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求索进而影响人生境界的提升。美育,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它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我们身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应该立足新时代,创新与发展当代中国戏剧美育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虽是国家发展之本、当务之急,但切忌急功近利,更不能违背创新规律。面对中西方不断涌现的戏剧美学新思潮,我们在与时俱进的同时,更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保持学术定力、审慎对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明辨其背后潜隐的意识形态。对于中西方文化与美学经典,应该在经典以及经典产生的时代厚壤中,继续深入探研、比较分析、发现规律、把握精义、行稳致远。
古希腊悲剧经典作为戏剧艺术的明珠,其赏析正是在高度压缩的时空中对英雄人物情感命运的集中体验过程。当悲剧走向世界的时候,悲剧精神就开始发光,社会的现实也将被揭示。观众在剧场里实现了情感共鸣,他们走出剧场投身社会实践时,能够更加坦然地正视自身缺陷,接受可能的失败,书写和承受自己的人生,担当自己的职责,为挑战人类极限而奋起行动,进而真正成为理想的、自由的、完整的人。所以说,悲剧不悲,它是极致的美。
舞台人物根植于剧本人物,二者合称为戏剧人物。通过戏剧性形式中完整戏剧人物的塑造,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是戏剧独具的优势。以完整戏剧人物塑造为核心,依托戏剧性形式,融通古今、并蓄中外、博采众长,展现最新最美的时代旨趣,培育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是当代中国戏剧美育必须把握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