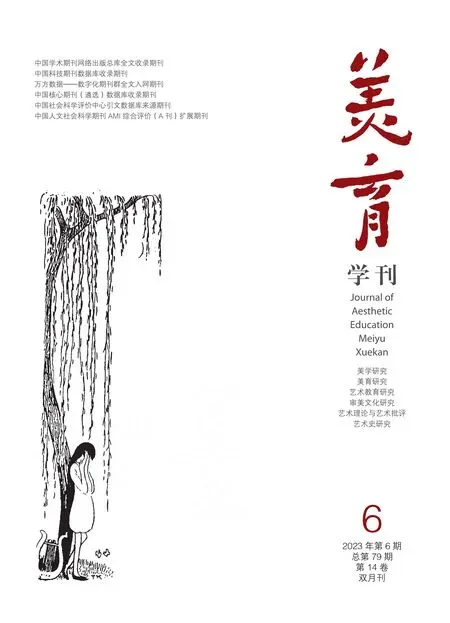本雅明与齐泽克艺术思想的汇通
——基于绘画作品《新天使》的解读
2023-03-24许锦煊单小曦
许锦煊,单小曦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瓦尔特·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又译《论历史的概念》)中,以一种近似梦幻隐喻的写作方式,展开了对历史的探讨。在第九节中,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弥赛亚救赎的角度对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进行了解读。即使“天使”的概念与形象已然将自身诉诸神学的形而上学意义以及某种超越历史性的超验存在,但此处本雅明在描述完画作的构图和布局之后,仍转而将新天使与其哲学体系中的“事件”“历史”与“进步”概念相联系,我们不得不将其视作某种断裂与突兀。作为画作的《新天使》与本雅明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着联系?
若干年后,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其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中,以某种融合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学的方式,对《历史哲学论纲》进行了阐释。然而吊诡的是,向来被认为是《历史哲学论纲》最著名选段的第九节,在齐泽克这里被忽略了。此处我们无法知晓齐泽克出于何种原因对第九节避而不谈,但可以肯定的是齐泽克选择回避了第九节,而笔者认为第九节中的画作《新天使》恰恰最能体现出本雅明主义与齐泽克主义的汇通之处。
针对该问题,笔者基于对《新天使》的解读,试图挖掘出本雅明艺术思想与齐泽克艺术思想之间的暗合与呼应,以及此种殊途同归的意义。
一、天使与新天使:对于概念与文本的梳理
若要对《新天使》进行解读,首先必须了解本雅明与该画作的关系,并将“新天使”置于“天使”的神学序列之中进行概念梳理。
1920年5月至6月,保罗·克利的《新天使》在汉斯·格尔茨的画廊展出。1921年6月,本雅明的好友舒勒姆在慕尼黑用重金替他买下这幅画作,后舒勒姆为《新天使》作诗一首,这首诗即是《历史哲学论纲》第九节开头的那首:
我的双翅已振作欲飞
我的心却徘徊不前
如果我再不决断
我的好运将一去不回
[1]269
11月时画作寄给了本雅明,这幅画始终挂于本雅明的书房。1940年法国战败后,躲在巴黎的本雅明决定离开巴黎前往美国,可惜他最终在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自杀。在此之前,他把《历史哲学论纲》的手稿交给了阿伦特,把《新天使》交给了巴塔耶,后来又由阿多诺保管。依照本雅明的遗愿,画作最后回到了舒勒姆的手里,在舒勒姆去世之后被捐赠给了以色列博物馆。
在《历史哲学论纲》的第九节,本雅明是这样描述新天使的:
保罗·克利(Paul Klee)的《新天使》(AngelusNovus)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张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他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致他再也无法把他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1]270
根据舒勒姆的诗歌和本雅明的描述,结合其历史唯物主义和弥赛亚主义救赎观,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历史天使的停留之处是灾难事件发生的地方;第二,天使在这幅画作中,似乎站在了天堂的对立面,但实际上二者关系是扑朔迷离的;第三,在第二点的基础上,我们也不禁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和弥赛亚主义救赎观与文本中所提的“进步”之间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种解释。一是新天使意欲停留在灾难与事件发生之处,并且试图拯救这个破碎的世界,但最终因天堂的干扰而失败;二是新天使留恋着过去,试图拯救这个破碎世界时,却陷于这种困境,来自天堂的风暴恰恰是把新天使解救出来了。
倘若根据第一种解释,新天使的形象顺承了整个《历史哲学论纲》文本脉络和主旨,因为“历史地描绘过去”[1]267在本雅明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1]267,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1]267。由上下文可知,本雅明始终站在被压迫阶级一边,反对那种伪善的“进步”,即以某种“进步”的名义去压制被统治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式“进步”。齐泽克指出拉康在《精神分析的伦理》中认为,“进化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总是暗示了对至善的信仰,对终极进化目标的信仰。这样的终极进化目标从一开始就指引着进化的进程。换言之,它总是暗示隐蔽的、极力否认的目的论,而唯物主义总是创伤化的,它总是包含着回溯性运动:最终目标并不铭刻在开端身上;事物总是事后才获得意义。秩序的突然创造会回过头来将意涵赋予先前的混沌状态”[2]206。可以说,齐泽克的解读比较符合《历史哲学论纲》呈现出的直观意义。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认为天使学可与人间的官僚体制相对应。“在末日审判之后,当上帝的选民被带入天堂时,以及所有的有罪者被送入地狱时,一切的治理活动都停止了,并且天使的等级制度也被剥夺了它们所有的功能。但除了一个功能:荣耀,他们将继续不知疲倦地向上帝唱赞歌,直到永远。荣耀是天使—治理功能得以自我生存的形式”[3]。而《历史哲学论纲》中的新天使恰恰相反,新天使站在与天堂相对的一边,放弃了对上帝的赞美,不再等待神学意义上弥赛亚的降临,而是选择反抗,选择直面事件和灾难,选择让历史唯物主义的弥赛亚降临,历史唯物主义者审度着“为了被压迫的过去而战斗的一次革命机会”[1]275,“以便把一个特别的时代从同质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把一种特别的生活从那个时代中剥离出来”[1]275。
以上即是第一种解释的内容,但是第一种解释除了渲染出一种新天使的悲壮感之外,似乎并不能解释结果论意义上的“失败”。换言之,基于何种理由,本雅明要让进步的风暴最终吹走天使。这不得不让我们审视第二种解释,并思考为什么“进步”最终发生了。倘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考虑新天使,考察本雅明论述之实在界基底,我们似乎可以发现第二种解释何以可能。
二、新天使:反崇高的崇高
若要对第二种解释进行论述,则必须首先重构并分析画作《新天使》,通过拉康—齐泽克式的精神分析学视角去审视《新天使》在何种程度上最初吸引了本雅明,以使得他将其作为艺术、历史、神学的联结点。
克利的新天使一反自中世纪以来的天使形象,一反神学上的崇高,将天使极简化,甚至是卑俗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新天使占据了观者的原质(das Ding/la chose,又译原物)位点,我们可以将它当作是后现代主体。
原质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曾有过不同的含义,本节所说的原质是在其“不可能的”意义上说的。要理解这一含义,我们不得不考察其在精神分析学中的概念区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德文中,表示“某种事物”意思的有“原质”(das Ding)和“事物”(die Sache)两个单词。此处我们结合这一点,并考察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学中“词表象”(Wortvorstellungen)与“物表象”(Sachvorstellungen)的区分。根据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分析的地形学,这二者在前意识—意识的划分中紧密结合;在无意识的界限中,只能发现“物表象”(Sachvorstellungen)。于是容易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词表象”(Wortvorstellungen)与“物表象”(Sachvorstellungen)在精神分析学的地形学中似乎并非完全同一,而“事物”(die Sache)也被弗洛伊德用来指称无意识中的“物表象”(Sachvorstellungen)。
但拉康在象征层面上协调了“词表象”(Wortvorstellungen)与“物表象”(Sachvorstellungen),而在象征层面与实在层面将“事物”(die Sache)与“原质”(das Ding)相对立——“‘事物’(die Sache)与‘原质’(das Ding)相对,它意指某种事物在象征秩序中的表象呈现,而原质是这种事物在其自身‘无法言语的现实’中的,在其实在界中的,那种超越所指的东西”[4]207。简而言之,“事物”(die Sache)属于象征界,而原质(das Ding)属于实在界。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无意识层面“事物”/“物表象”也是一种语言现象,正如拉康名言——“无意识像语言一样结构”[5],“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6];原质外在于语言和无意识,被“不可能的”实在界赋予了同样“不可能的”特性,而之所以称之为“不可能的”,是因为实在界和原质无法被想象、无法被象征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康式的原质(das Ding)与康德式的物自体(Ding an sich)有一定程度的暗合。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对象小a”(object petit a)的概念逐渐替代了原质。由此我们可以说在超越象征化的意义上,原质即为“对象小a”。二者的区别在于:原质是从精神分析的地形学角度说的,“对象小a”是从欲望的角度说的。
结合这一点,我们又能在享乐(Joissance,又译痛快)的意义上理解原质。原质(一如“对象小a”)是欲望的对象,而快乐原则维持着主体与原质的距离,若是主体过于接近原质,那感受到的不会是快乐,而只能是痛苦。于是可以说原质在实在界中是一个位点,主体围绕着原质做着循环运动,却永远无法真正得到它,否则就会直面实在界。
齐泽克将该意义上的原质概念应用于艺术哲学的崇高论中,对此我们可以做以下梳理。
如果对艺术史进行大致的分期,那么可以说在前现代的古典艺术时期,遵循着再现论(representationism)的路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都试图将实在界中的原质予以象征化(符号化),试图以某种美好的事物去填充空无的原质,正如齐泽克在《易碎的绝对》中所言,“传统(前现代)艺术的问题是,如何以一个足够完美的对象来填补崇高物的空无(纯位置)——如何成功地将一个普通的对象提升到物的高度”[7]24。
到了现代主义时期,随着艺术观念和伦理的变更,我们开始质疑一切占据原质位置的事物的合法性,我们逐渐认识到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于艺术品本身的直接物质性,而不过是因为它占据了原质的位置,于是“人们不再能够指望有一个(神圣的)位置空无存在那儿供人类的人工品占据,因此要做的事情就是照原样保持在这个位置以确保这个位置本身将会‘发生’——换句话说,问题不再是可怕的空虚及填补这个空无,而毋宁说首先要创造这个空无”[7]24。在此基础上,一种“缺席的美学”诞生了。
而到了后现代主义时期,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美学的商品化与商品的美学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原质空无的位置愈来愈难以维持,于是“自相矛盾地,似乎维持这个(神圣)位置的惟一办法就是用垃圾、用可鄙的排泄物来填补它”[7]28-29。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杜尚的《泉》,作为现代工业产品,展示用的小便器与厕所里的小便器、商店在售的小便器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它之所以为艺术品,除了杜尚的身份加持之外,仅仅是因为它占据了人们的原质之位。同样的例子还有曼佐尼的大便,在罐头中的排泄物之所以能被拍卖出高价,除了人们的猎奇心理之外,只能用卑俗之物占据原质之位来解释。
虽然看上去似乎是先有了实践与观念上的变化,才产生了精神分析意义上人们对原质看法的变化,但事实上,二者的发生逻辑是同时的,并无先后之分。
回到克利的《新天使》,结合拉康—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理论,不难发现,一反古典想象的新天使能够被人们视作艺术,正是因为它占据了观者的原质,它是对传统的反讽。与前现代的崇高相异,它带给观者的震惊感是因为“它摆脱了统一的宗教话语控制,使得人们的审美意识偏向于自然中那些未被文化所污染的事物,从而展开自我反思”[8]。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反崇高的崇高”中两个“崇高”的含义有所不同。“反崇高”意谓一反康德意义上的崇高,亦即数学上的崇高和力学上的崇高。前者表现为数量上的无限,如丁托列托《天堂》给人的观感或许可以归入此类崇高;后者表现为力量上的无限,如米开朗琪罗《创造亚当》给人的观感或许可以归入此类崇高。而后一个“崇高”意谓某种位置关系,是莫比乌斯环的两端,是卑俗和与之相对的崇高之间的辩证转换。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克利的《新天使》是一种“反崇高的崇高”。也正因如此,《新天使》吸引了本雅明,使他将其作为艺术、历史、神学的联结点。
三、斜目而视:“事件”与“对象小a”
放眼看去,《新天使》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定是新天使的“斜目而视”。本雅明是这样描述新天使眼睛的——“他凝视着前方”[1]270,“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1]270。如此,我们不禁疑问为什么新天使看到的是“事件”和“灾难”?
结合精神分析理论,这一点不难理解。齐泽克通过对莎士比亚《查理二世》第二场第二幕的解读,阐释了“斜目而视”概念。这场戏涉及国王的仆人布希与王后之间的对话:
布希 每一种悲伤的实质都有二十个影子,它们表现出来的像悲伤本身一样,但其实不然;因为悲伤的眼睛,涂上致盲的泪水后,会把一个完整的事物分成许多物体;就像凹凸镜一样,从正面看过去,除了模糊外只有空无;而斜目而视,却能看到清晰的形状:所以尊敬的王后,对于国王的离开,您斜目而视才发现了悲伤的形状而不是他自己的轮廓;其实从正面看去这除了幻影并无他物。仁慈的王后啊,不要因为离别以外的事情而感到难过:您其实什么也没看到,即使看到了,这也不过是透过悲伤的眼睛看到的错误幻象,它常常把想象的东西当作真实的东西,且为之哭泣。
王后 也许确实如此,但我内心深处的灵魂说服了我,让我觉得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停止伤心,那伤心如此之重,即使在我不去想它的时候,空虚的重压也使得我喘不过气。
布希 那不过是一种信念罢了,尊敬的王后。
王后 那决不是什么信念;信念常会从某种久远的悲伤中产生;而我的不是,空无导致了我的悲伤,或者有什么东西导致了我的悲伤:在我确实拥有的回归中;但它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是某种我无法命名的东西;是一种无名的悲哀。[9]
在这里,布希所说的“从正面看过去,除了模糊外只有空无;而斜目而视,却能看到清晰的形状”,“您其实什么也没看到,即使看到了,这也不过是透过悲伤的眼睛看到的错误幻象”,“那不过是一种信念罢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齐泽克意义上的“斜目而视”概念。
一般而言,直视某个事物,我们能直观地看到它的“本来面目”;如果是通过被欲望和焦虑缠绕的“斜目而视”,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事物扭曲和模糊的轮廓。但齐泽克意义上的“斜目而视”,倒转了日常经验:直观事物反倒只能看到轮廓模糊的斑点,而只有从某个角度去进行一种被欲望缠绕渗透的、扭曲的观看,才能看到事物的清晰形态。
要注意的是在《新天使》中,“斜目而视”的并不是作为接受主体的我们,而是画中的新天使,也即原本作为被观看对象的新天使在此刻转成了观看主体。他斜着眼睛向画面的右侧望去,在那里他发现的是“对象小a”(objet petit a)。作为被欲望设置出来的客体,纯粹的“客观”凝视无法察觉出“对象小a”存在,所能发现的只有空无,而只有借助于被欲望缠绕的凝视才能察觉其存在。“对象小a”无法超越扭曲而“自在地”存在,它是这种扭曲的化身,是焦虑的物化。
要了解“对象小a”的这种性质,我们必须从“对象小a”在拉康理论体系中的流变开始说起。“对象小a”中“a”的概念是最初诞生的。“a”源于法语“autre”的第一个字母,该词通常被译为小他者、小客体。“与呈现出彻底的、无法简化的异己性的大他者不同,小他者是‘那种根本不是另一个人的他者,因为它本质上是与自我配对的,在某种关系中是永远有反射性和相互交换性的’。”[4]128简而言之,这个小他者并非我们一般意义理解上的区别于自我的另一个人,而是在想象秩序中具有“自反性”的自我,因此在早期拉康的理论中“a”属于想象界。1957年拉康引入了幻象公式后,原本的“a”开始有了“欲望的对象”的含义,它变成了一种想象性的、局部性的客体,它此时指称与自我之身体相分离的元素——于是他正式提出“对象小a”的概念。1960年至1961年的研讨班上,拉康把“对象小a”与“agalma”相联系,这个词语出自柏拉图的《会饮篇》,一种祭祀用的神像。珍贵的神像藏匿于不起眼、不值钱的小盒子中,拉康借助这个词语类比“对象小a”也如“agalma”一样,是我们在小他者皮囊之下欲望的对象。而1963年以后,如前文所述,原质概念逐渐被“对象小a”替代,于是“对象小a”有了实在界的含义,但事实上它从未失去过想象性的性质,拉康到了20世纪70年代还说它是想象的。既然它是实在界的,它就开始指称某种永远得不到的对象,进而可将其称为“欲望的原因”。和原质的定义相仿,“对象小a”同样被冲动环绕,但无法被冲动接近,因而它事实上又成了焦虑的对象。在之后的研讨班上,拉康认为“对象小a”是实在界入侵象征界后,象征界对其进行未完全的符号化而形成的剩余、残渣,又是在主人能指试图缝合一切能指的过程中产生的剩余,又和剩余享乐相挂钩。70年代后,拉康把“对象小a”置于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中心点。
在梳理完“对象小a”的概念流变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本雅明与拉康式精神分析的一个暗合之处,这可以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新天使的“对象小a”作为其“欲望的客体—成因”,意味着新天使欲望着画面右侧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又是欲望的原因,他欲望它,但并不理解它,也不需要理解它。另一方面,“对象小a”是实在界入侵象征界的结果,实在界的入侵,意味着创伤性经历的回归,这相当于是在说“对象小a”具有创伤性。之所以说它有创伤性,一是因为它不可想象,二是因为它抵抗符号化。
因而,精神分析式的解读与本雅明的解读相呼应:这一连串的事件,这单一的灾难,这堆满的尸体和破碎的世界,无不宣告着新天使的创伤。如此将“事件”与“对象小a”对应,那本雅明解读的突兀也就被消解了。
四、嘴、翅膀与风暴:修补世界的幻象性
既然天使看到的“事件”/“对象小a”是创伤性的,那么“风暴”的含义也就不言而喻了——那是“实在界的应答”。“创伤性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实在界对现实的入侵,意味着主体的现实感的丧失,意味着主体的全然的无能为力。”[10]310
但此处应注意“实在界”(the Real)、“现实”(reality)与“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三者之间的区别。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实在界(the Real)是非想象性的、非符号化的、前主体的“心理现实”。实在界在前镜像阶段中,被用来指称某种个体的本原状态,在生命之初与母体紧密结合的状态。现实(reality)则是象征界试图对实在界的入侵进行符号化后的残余,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为保持现实与实在界的清晰界限,必然地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主体。这种现实即为某种关于包含人物、事件、场景等要素的图景。而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是一种幻象空间。我们总是用某种幻象空间来填补实在界的黑洞,这种填补总是溢出的,溢出后的剩余部分,就构成了这种想象性的现实感。
在知晓了三者的区分之后,回到“实在界的应答”。面对想象性的现实感的消失,“主体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自己当成高高扬起的‘阳物’,摆出‘阳物性’的姿态,重建已经丧失的现实感,并把自己的‘无能’转化为‘全能’。就其具体表现方式而论,就是为实在界的入侵承担全部罪责”[10]310。天使摆出的这种“阳物性”姿态即为张开的嘴和翅膀。
这种阳物(phallus)的概念既是从想象的意义上去谈的,又是从象征的意义上去谈的。
之所以说它是想象性的,是因为在前俄狄浦斯时期(也有人认为这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一个时期),母亲在孩子之外还欲望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想象性的阳物,这个第三项始终介于母亲与孩子的二元关系之间,因而这种二元关系是非纯粹的。此时,孩子会认识到自己和母亲身上的某种缺失:这种缺失在母亲身上的表现,即她作为最初的大他者却不完整,所以她才能有欲望;这种缺失在孩子身上的表现,即他无法满足母亲的欲望。于是这样的过程形成了一种双向奔赴的关系——“母亲欲望着她缺失的阳物,而孩子试图成为她欲望的对象,试图成为这个缺失的阳物以填补她的缺失”[4]131。孩子必须献出实在界的某种东西(拉康始终认为实在界仍有物质性蕴含,表现为隐藏于想象界和象征界之下的物质基础,因而“实在的阳物”也是作为身体器官的阴茎),但他的性器官还太弱小,面对作为最初的大他者的母亲,显得那么无力,于是孩子会有焦虑(所以焦虑与实在界挂钩)。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后续阶段中,父亲的介入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种焦虑。但这种想象性阳物的意义对于天使来说,实际上是要躲回到那种前俄狄浦斯的阶段中,以逃避实在界入侵导致的象征化失败的事实(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表现为父亲介入的未完成和阉割的未完成,以导致从想象界跨入象征界的失败)。
之所以说它是象征的,是因为孩子借由想象性阳物完成的第一个辩证法(俄狄浦斯情结中想象性阳物自身的否定之否定)与能指象征形成的方式类似,阳物于是成了一个能指。这个能指是作为最初的大他者的母亲永远缺失的东西,于是齐泽克对拉康“大他者”概念阐释之一会有“大他者不存在”[11]一句,其实这句话意谓作为和谐统一的象征秩序是不存在的,因为永远都有这样一个能指是缺失的。所以新天使的象征性阳物姿态(直观呈现给我们的姿态),事实上是为了试图摆出与大他者中缺失相一致的姿态,即新天使试图去恢复一种关于大他者完整全能的虚假愿望。这种虚假愿望的本质其实与上述的躲回前俄狄浦斯阶段的行为如出一辙。
回到前述问题,第二种解释得以被辩护:正是因为新天使留恋于过去,为了承担全部罪责,才试图去修补世界,亦即去重建那种业已丧失的现实感,以期用幻象来掩盖创伤。然而这种尝试是必然失败的,因为不仅现实感本身是一个幻象,甚至“主体”这个概念也是镜像阶段后建立的幻象,这种修补、重建行为从而也必定是幻象。所以新天使试图去修复世界的行为会令他必然地陷于某种困境,舒勒姆的诗歌也因此得以解释。
幻象与欲望挂钩,因为幻象就是被设想为实现主体欲望的场景,它“只是一个空洞的外表,一个屏幕,用来供人投射其欲望。它的实证内容(positive contents)的迷人现身,目的只有一个,即填充空白”[10]13——幻象所展现出来的就是欲望本身。而如上文所述,主体与作为欲望的“客体—成因”的“对象小a”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可能的”。于是,“正是幻象这一角色,会为主体的欲望提供坐标,为主体的欲望指定客体,锁定主体在幻象中占据的位置。正是通过幻象,主体才被建构成了欲望的主体,因为通过幻象,才学会了如何去欲望”[10]9。
然而根据欲望的悖论,即“我们以为‘事情本身’在不断地拖延,其实不断拖延这个行为,正是‘事情本身’;我们以为自己在寻觅欲望,在犹豫不决,其实寻觅欲望和犹豫不决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欲望的实现。也就是说,欲望的实现并不在于它的‘完成’和‘充分满足’,而在于欲望自身的繁殖,在于欲望的循环运动”[10]11,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为了拯救现实(感)而采取的行动本身就否定了现实(感)。修补的未完成,才是我们的欲望,一旦修补成功,欲望就消失了,就会陷入焦虑,与实在界相遇。
所以,那场进步的风暴,又能产生与精神分析的呼应——进步是必然的。但我们不能忘记这里所言的“进步”是本雅明本人所反对的法西斯主义式“进步”,所以这种“进步”在实在界中有了某种“大屠杀”意味,从而也确实解释了《历史哲学论纲》第九节的现实指涉性,可以说本雅明在奥斯威辛之前就已经“预见”了“奥斯维辛”。而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谈论《历史哲学论纲》的这两节中,把斯大林主义与本雅明主义相对立。因此虽然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并未提到《历史哲学论纲》的第九节,但能够看得出这种“不在场意味”的“在场”。
如此这般,似乎能够使第二种解释得以拓展,即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天使在精神分析中似乎成了一个“恶人”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与天堂的表面对立性完全被解构为了内在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新天使对于事件、历史的看法,以及他对于进步风暴的处理方式,经过了想象化和象征化的包装,相较于直接的、直观的实在界入侵而言,更具有伪装性、迷惑性,所以对新天使形象的解读更充满了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关系到在实践论意义上的主体选择方向,也关涉规范伦理学意义上对“什么是善”与“什么是恶”的讨论,甚至能够延伸到一种元伦理学上对于道德事实的探讨。
五、本雅明、精神分析与康德的遗产
至此,本雅明艺术思想与齐泽克艺术思想的暗合汇通之处,通过精神分析式的解读可以说已经融洽了,这种融洽性表明二人艺术思想在实在界层面的某种一致性,亦即出于同样的某种实在界之思,二人在象征界中以不同的符号化方式去表述一种历史可能性的回溯性定义。而笔者在本文中针对《历史哲学论纲》第九节中《新天使》,给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解读,然而正如实在界入侵象征界给主体带来的创伤性一般,这种激进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本雅明与齐泽克最初的理论设想。
这种激进的解读事实上仍激荡着一种康德的回响、一种对康德遗产的应答,正如前文中多次联系到康德一般。之所以在此提到康德,是因为他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方面的矛盾态度。
一方面,他对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极其反对,他认为“服从当前立法权力所制定的法律是一种义务,不论它的来源是什么……如果违背了平等法则去分配政治负担,臣民对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可以提出申诉和反对意见,但不能积极反抗”[12]154,并且“对人民来说,不存在暴动的权利,更无叛乱权……人民有义务去忍受最高权力的任意滥用,即使觉得这种滥用是不能忍受的。理由是,对最高立法权的任何反抗,只能说明这与法理相悖,甚至必须把它看作是企图毁灭整个法治的社会组织”[12]155。不仅如此,他放大了当前统治者的权力,认为“以统治者的名义所作的一切必须被认为都是根据必需的权利去做的”[12]156。由此,他在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方面的理论似乎就能为法西斯的行为辩护,而民众亦不能对此存有异议。更进一步地,基于其道德哲学理论,尤其是根据《论所谓的出于博爱关切而说谎的权利》中所举之例,当一个人的朋友遭到追杀而躲到自己家中,杀手正好找上门来时,这人有义务不说谎,即使这可能葬送朋友的性命,因为“诚实是一种义务,必须被视为以契约为基础的一切义务的基础”[13]612-613,“如果你严格遵守诚实,那么无论不可预见的后果如何,公共正义都不能对你有所指摘”[13]612-613。这样的例子在一百多年后的德国真实再现了,根据康德,当法西斯搜查犹太人和异见者时,民众有义务诚实地配合。由此,在《新天使》中呈现的那种人间灾难,是不应被阻止的,至少是不能进行暴力反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天使与天堂的态度只是在遵守一种康德式的实践。康德在《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一文中提到了一种预告性的历史叙述,这种历史叙述是先天可能的。之所以它是先天可能的,是因为“预告者本人就制造了并布置了他所预先宣告的事件”[14]150,正如犹太先知们所做的那样。如此,新天使与天堂的态度便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本就知道一切理应如此。
但正如上文说的,这其中存在一个吊诡之处。同样是在《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这篇文章中,康德把人类历史观分为了三种,分别是恐怖主义的、幸福主义的和阿布德拉主义的。关于恐怖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即沦落为恶的历史观,不具有持续性,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必然是自我灭绝的。这是因为人们会愈发感觉到事情已经如此之坏,以至于不能变得更坏了,于是便只剩下等待末日审判的来临,更有甚者会期待在此世界被烈火消灭后,迎来一个更新的世界。但这些被康德当作批判的话语,似乎恰恰能为《新天使》中所发生的辩护,仿佛世界确实向着这个方向前进了。然而,在接下去的论述中,康德肯定了人类是朝着改善前进的,因为这给人类带来的收获是“合法性的产品在合义务的行为中的增多,无论它可能是由什么动机所促成的。这就是说,人类朝着改善而努力的收获(结果),只能存在于永远会出落得更多和更好的人类善行之中,也就是存在于人类道德品质的现象之中”[14]164。
吊诡之处就在于:按照康德对革命与反抗的态度来看,如果世界向着《新天使》中的方向,即任由灾难发生的方向,任由新天使被风暴卷走的方向前进,世界就会掉入恐怖主义历史观的深渊,这能很好地适配第二种解释,新天使与天堂的“恶”之形象也能得以辩护;但如果按照康德认为的人类最终能向善前行来看,只要对上述之“恶”冠以“善”之名,便能消解其中的血腥,因为这是“理应如此”的,这是新天使与天堂的计划。而后者恰恰是各类极权主义为自己行为辩护的最常见理由。简而言之,康德的矛盾在于,他一方面认为人民应该服从当前统治而非反抗,即使要改变什么,也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改良而非自下而上的革命;另一方面却认为人类向善改进。但若是当前统治以善的名义做了严重的恶,导致了人民陷入灾难,又该怎样处理?
回到第九节上,结合上文论述生发的思考,我们不难发现第九节在《历史哲学论纲》的整个文本中,本身就构成了突出的“畸形”或者说某种“黑洞”,抑或说第九节之于读者而言,正如《新天使》之于观者而言,二者都是我们的“对象小a”。如若要使自身不陷于创伤的深渊,那么强调并融入某种神学意义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抚平这种创伤。
因而,如齐泽克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所言,“在他的理论(与物质)活动终结之时,神学问题突然出现。只有‘借助于神学之力’,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大获全胜”[2]195,于是我们又能回到《历史哲学论纲》第一节中那个著名的命题:
据说有一种能和人对弈的机械装置,你每走一步,它便回应一手。表面上看,和你下棋的是个身着土耳其服装、叼水烟筒的木偶。它端坐在桌边,注视着棋盘,而一组镜子给人一种幻觉,好像你能把桌子的任何一侧都看得清清楚楚。其实,一个棋艺高超的驼背侏儒正藏在游戏机里,通过线绳操纵木偶。我们不难想象这种诡计在哲学上的对应物。这个木偶名叫“历史唯物主义”,它总是会赢。要是还有神学助它一臂之力,它简直战无不胜。只是神学如今已经枯萎,难当此任了。[1]265
齐泽克在书中提到了本雅明的一段话:“在Eingedenken(追忆)时,我们获得了一种体验,这种体验禁止我们以基本上是非神学的方式设想历史。”[2]196或许,这就是神学之于本雅明之意义,亦即悖论式的新天使身上所承载的意义。而人类能做的,就其自身而言,或许仅仅只有等待,等待那“最末的日子”——“在永恒之中是任何事情都不再进行的,而那种事情便是有关人类在其全部生命时间中的行为的清算。那就是审判的日子;因此,世界审判者之降福的或惩罚的判决才是万物在时间中真正的终结,同时也是(福或祸的)永恒状态的开始,在那种状态中已经降临于每个人的命运就停留在宣判(定案)时刻所分派给他的那种样子”[1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