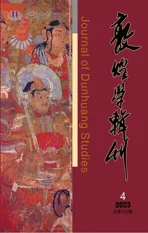论敦煌占卜书中的天人观念
2023-03-22李艺臻
李艺臻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00)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古代人们思考天人关系的问题,其用意往往在于如何体察天意,从而更好地把握个人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作为一种古老的天人沟通方式,占卜在人类生活中曾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科学的世界观形成以前,人们惯常以占卜来作为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决策依据,占卜行为可说是人类文化历史中最早出现的人类意图把握自身命运的尝试之一。《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1)《尚书·洪范》,参见屈万里《尚书集释》,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124页。《礼记·曲礼》:“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2)《礼记·曲礼上》,参见[汉]郑玄注《宋本礼记》(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45-46页。《易经》本来只是蓍占吉凶休咎的记录,后来被赋予了“权舆三教,钤键九流”的地位,成为人们理解宇宙天地万物的重要依据。
作为认知天人关系的基本方式,占卜活动本身即承载了古人关于天人观问题的深刻思考与丰富认识,故而关于占卜的研究可谓理解我国古代天人思想所不可忽略的关键。尽管自《周易》的时代直到中古时期,占卜理论及实践方法在不断发展,然而历史上官方禁忌、学者轻视等诸多原因所造成的文献材料的匮乏,影响到了今天人们关于我国古代占卜文化的系统认识。直到敦煌占卜文书的陆续发现,这一状况方才得以改观。
敦煌占卜文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天人观念的发展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文献集中于唐五代时期,反映了中古时期占卜活动的大量细节情况,填补了中国古代占卜历史的一个空缺,也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乃至自古以来所流行的天人观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依据。研究分析这些文献,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对古代占卜视域中天人观念的发展流变形成更为系统而完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从占卜术数的独特角度出发来深入古代人们的生活实际,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从而更加理性客观地认识、评价占卜的社会功能及历史作用。
一、敦煌占卜书所产生的社会背景
敦煌占卜文献所成立的社会背景,根植于晚唐五代特殊的时代环境与敦煌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归义军政权是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半独立政权,所管辖的区域是多民族的居住区,故敦煌地区是多种文化、宗教交汇的地区。因此人们对人生命运等问题的思考,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种思想传统及文化习惯的影响,体现于当时所流行的占卜活动中,形成了富有晚唐五代敦煌文化特色的天人观。唐五代的敦煌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祸乱频仍。晚唐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初,所面临的是一个在经历了吐蕃统治破坏后内外交困“四面六蕃围”的生存环境,终其一朝,其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在这种背景之下,占卜的流行似乎成为一种必然。郑炳林指出:“不但一般民众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就是当权的政府官员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人们不得不产生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认为只要不违背神的意愿,了解神的意思,做事就会一帆风顺。因此除了信仰佛教多做功德外,就是通过阴阳杂占来了解神的意思。敦煌文书中的《西秦悬像占》等一大批占卜书,就是敦煌文士在这种背景之下撰写的。”(3)郑炳林《敦煌写本梦书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页。
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统治者不但自身信仰占卜术数,将其应用于行军、择日、祭祀、建造等一系列活动中,还将阴阳占卜之学渗透到职官设置与官方教育之中。如节度使幕府参谋要求“必以阴阳技术者处之”,归义军幕僚同时往往担任州学教师,负责教授阴阳占卜之学。此外又有伎术院之设,伎术院“是张承奉建立金山国时新成立的机构,是掌管归义军的典礼祭祀、占卜阴阳、天文历法之事的职能部门”(4)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第39-47页。。这些条件都十分有利于数术知识的发展与传播,与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之风的盛行息息相关。
正如唐代刘禹锡所言:“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5)[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5《天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24页。动荡的社会环境,无常的前途命运,使人对自身的力量产生了怀疑。由于丧失了自信力,人们只得把命运寄托在所谓的“天”上,意图求取神灵的庇佑。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人们一方面渴望利用各种手段来获取天意,计算出某种确定的结果来求得心理安慰;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远未能发展至可以解释万事万物的程度,因此建立在天命论观念上的种种计算方法,就必然导向阴阳术数而非系统的科学理论,敦煌占卜文书之形成,即普遍受此种观念的影响支配。
占卜之风的广泛流行,一方面可以促进阴阳术数之学的传播,而在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为官方所垄断的占卜之学变得民间化,这一特点在敦煌占卜书中十分明显。(6)黄正建指出:“敦煌占卜典籍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民间性。广泛流传在民间的占卜典籍,除少量是官方著录的著作外,大部分都是‘下俚斗书’,这应该是占卜类典籍流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75页。与占卜文书的民间化相对应的,是其思想内容的世俗化,体现在天人观念的方面,敦煌占卜书所谓的“天”,不是理论化、抽象化的“天理”“天道”,而往往是神秘化的决定吉凶祸福的“天命”“天谴”;而所谓的“人”,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一般的“人”或者“人性”,而是现实生活中具体存在的个体的人。敦煌占卜书内容虽然不离天人关系问题,但民间性、世俗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是从理论化的角度来概括人如何来沟通天,而是通过关注世俗社会中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现实问题来体现其所理解的“天意”。
文化来源的多元化是敦煌占卜文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三教融合作为重要的社会思想背景,对当时人们观念的支配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其中儒家思想作为汉唐王朝的意识形态主体,对占卜之学的影响巨大。陈于柱认为:“由于儒家思想文化以及特有的思想内涵和行为规范深深地融入于传统中国民众意识之中,并决定和影响着民众宗教意识的走向,因此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为了迎合社会和民众既已认可的价值观,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自身的基本价值取向建筑在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之上或与之相贴合。”(7)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因此,体现在敦煌占卜书中,不仅有P.2574《周公占法》,S.2578《孔子马头卜法》,P.3908、S.5900《新集周公解梦书》等托名儒家先圣的著作,而且儒家思想的道德伦理观念也被吸收于内。如CH.87《许负相书》:“眉上骨高,名九(犮)[反]骨,为子不孝,为臣不忠。”(8)CH.87《许负相书》,参见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361页。以不孝不忠之相为恶相。又如P.2859《五兆卜法》:“假令戊己日卜得木兆,名为君子利吉,小人则凶。”(9)P.2859《五兆卜法》,参见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研究》,第210页。以“君子”“小人”区分同一卜兆之吉凶。郑炳林认为,敦煌写本相书“主要是儒家的理论为基础,《许负相书》称‘夫积善于庆,则众相自然,积恶头(显)扬,表其深现。’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新集文辞九经钞》,……孔子曰:吉凶由人,祸福由己,行善则吉,行恶则凶。为由己也而由人乎。……俗谚云:终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即有余。必须行善,恶不可作……左传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10)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1期,第10页。可见敦煌占卜类文书普遍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思想观念。
儒家关注现实人生问题的入世倾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思想,以及《周易》之“阴阳”、《尚书》之“五行”“九畴”等概念奠定了传统占卜术数之学的理论基础,而其后随着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思想的传入,其中的一些固有观念亦随之发生了变化。唐五代敦煌的社会风俗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对于敦煌占卜书而言,在佛教理论当中,又以因果报应论与轮回转世说的影响尤为突出。郑炳林在考察敦煌占卜行为决定论产生的背景时提出:“佛教提倡因果报应,所谓前世因,现世来世果。这种因果关系对占卜行为决定论及其二重行为决定论有直接影响,占卜行为决定论及其二重行为决定论实际上是佛教因果报应论的翻版和变形,行为就是因,而面相和梦象征兆是果。”(11)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第7页。P.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未生羊相人,命属武曲星,……其人本是安国人,前世为破斋,遂来至此生。……酉生鸡相人,命属文曲星,……其人本是天陀罗国人,前世为破斋,遂来至此生。”(12)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第218页。可见敦煌占卜已将佛教转世说融入其内。
佛教思想对敦煌占卜天人观念的影响主要有:首先,关于“天”的性质的认识有所变化。传统占卜的天命论认为天是人间吉凶祸福的来源与主宰,天意既不可抗拒,又无法更改,这实际上是一种宿命的视角,将一切可能的偶然祸福都归于命定,归于一种想象的必然。佛教理论则强调无“自性”(“自在天”),否认主宰吉凶祸福之“天”“上帝”的实存性,而代之以“因缘合会”的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传统占卜的理论根基;其次,关于“人”的定义亦有所变化。在传统占卜视野中,不论是作为侦问天意的认识主体的“人”,还是承受天命的对象的“人”,都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而佛教三世因果之说,则仅将现世的人视为在三世轮回过程中因业力假合而成的阶段性存在。既然连“我”之存在亦非实有,那么求神问卜的行为又能有何意义?
因此,在佛教广泛流行的唐五代敦煌地区,占卜术士面对以上问题,不可能不作出回应。从敦煌占卜文献内容来看,一方面,敦煌占卜书在编纂时往往借用佛教名号,宣传佛教信仰,如P.4778《管公明卜法》,管公明即三国术士管辂,他并非佛教徒,然而《序》中却要求卜者“专心念卜,又称七佛名字。”又如P.3908《新集周公解梦书》专设“佛道音乐章”,称“梦见礼佛,得贵人力。梦见入寺行,主喜事。梦见菩萨者,主长命。梦见金刚,得人力助”(13)P.3908《新集周公解梦书》,参见郑炳林《敦煌写本梦书校录研究》,第173页。。又如S.5614B《摩醯首罗卜》称:“志心烧香念佛,恳苦发愿,恶事自消,所愿从心。”(14)S.5614B《摩醯首罗卜》,参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实际上是通过宣扬佛教信仰来回避与佛教教义相冲突的问题。另一方面,敦煌占卜书亦吸收了佛教理论尤其是因果轮回的思想来完善自身理论。正如陈于柱所言:“各式佛教理论的融入,特别是佛教因果报应论和轮回观念,进一步完善了占卜理论,增强自身的变通能力,使得原本属于民间宗教的占卜,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成熟宗教的韵味,借助于此,经不起理性检验的占卜方术在社会的生存力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15)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第222页。
除佛教外,道教文化对敦煌占卜之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自汉魏以来,道教即在河西地区流行,而之于占卜活动而言,其意义尤为重要。正如李零所说:“道教文化是以术数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表达,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16)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4页。此种特点决定了道教文化与占卜术数在思维上共同的底层逻辑以及在实用技术层面上的互通共享,在敦煌文献中有所体现。《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说张义潮“上明乾象,下达坤形,觏荧或(惑)而芒衰,知吐蕃之运尽……六甲运孤虚之术,三宫显天一之神”(17)S.6161、S.3329、S.6973、P.2762、S.11564《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参见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第32页。,表明他既通星相,又明阴阳术数,其中所谓“六甲之术”“天一之神”既是星名(18)如《史记·天官书》云:“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27《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90页。,又是神名(19)如郑玄注《乾凿度》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清]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易乾凿度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5页。,同时也是占卜符号,术数学称为“用神”(20)如《黄帝金匮玉衡经》云:“天一贵神,位在中宫,据璇玑,把玉衡,统御四时,揽撮阴阳,手握绳墨,位正魁罡。”《道藏》第4册《黄帝金匮玉衡经》,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002页。按:“天一之神”,在六壬式中即为“天一贵神”,在遁甲式中即为“天乙直符”。。
道教思想对敦煌占卜中天人观念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消极的方面来说,道教神灵系统将原本属于自然现象的事物神秘化、宗教化,使人们对天的认识依赖于神秘的存思冥想等宗教修炼途径或是斋醮符咒等宗教仪式,敦煌占卜文献中保留了大量符箓咒语的内容,即为道教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从积极的方面而言,道教文化渗透于占卜术数之中,在无形中又将原本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天”具象化、符号化,使人们对于“天意”的显现更易把握,因而才能产生诸如厌胜灾禳等改变“天意”的行为尝试。虽然其形式仍然不出乎宗教信仰的范围,但试图以人力而改变天意,如《抱朴子》所谓“我命在我不在天”(21)《抱朴子·黄白》,参见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7页。,同时也意味着相较传统宿命论的天人关系而言,“人”的地位其实已有所提高。
二、天人关系问题思想进路与敦煌占卜文献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说是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两条基本思路。自古以来的占卜之术始终以“天人合一”论为其思想基础,并在历史上“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概念不断对立转化的运动过程中发展演变出新的理论形式,这些演变的痕迹在敦煌占卜文书中得以大量保存,为今人系统了解中古时期占卜之学的发展以及占卜视野下天人观念的流变提供了依据。
上古时期,人们在对世间万物尚未形成理性的认识之时,往往将自然现象归结为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于是有鬼神的说法,其后又创造上帝的观念,作为一切现象活动背后的根源与主宰。上帝鬼神观念的成立,源于人们对自然规律、自然意志的人格化想象,是一种以人类自身为中心来认识天道,富于主观色彩的“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宗教信仰的基础。其后,随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进化,人们开始尝试从宗教鬼神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转而从自然气化以及人性生成的角度来理解天人之际的问题,带有客观冷静的特性。
自西周末年“变风变雅”之作,不少人开始对“主宰之天”的存在表达怀疑,春秋时期“天道远,人道迩”等重人重民思想之提出,以及“六气”“五行”等自然气化说的流行,使传统的天命鬼神观念被动摇。孔子继而提出“仁”“礼”的观念,强调以人的理性为基点来认识万物,以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老子则主张“无为”“自然”之说,强调“天地不仁”的客观真相。自此以后,人们对天命的认识已大不同以往。徐复观说:“西周及其以前之所谓命,都是与统治权有关的天命。到了春秋时代,扩大而为‘民受天地之衷以生,所谓命也’的一般人的命;这是天命观念划时代的大发展。‘天地之衷’所命于人的,在孔子、在子思的《中庸》便称之为‘性’,在老子、在《庄子内篇》便称之为‘德’。这是一般人生的道德要求上所新建立起来的道德关系,可以说是道德自主性的觉醒。”(2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4页。
孔子的“仁学”思想以道德修养作为落实天命的基本方式,其后孟子进一步以“性善”说作为人性修养的内在理论依据,并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人性论之“天人合一”途径。老子以倾向于自然规律性的“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其后庄子则进而发展为“德”“得道”之概念,庄子一方面提出了人可以经由修炼得道而成为“真人”从而“复归于天”的“天人合一”论,另一方面又强调“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23)《庄子·大宗师》,参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5页。的划分天人之间界限的主张。再后,荀子发挥庄子的观点,完全从自然生成化育的角度来理解天人关系,明确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至此,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
在宗教的传统中,以人所禀受上天的祸福赏罚作为天命实施的直接呈现,以精神信仰作为“天人合一”的根本途径,而此时所欲“合”的作为对象的“天”,即为“信仰之天”“主宰之天”。春秋时代以来的人性论学说,如《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4)《礼记·中庸》,参见[汉]郑玄注《宋本礼记》(下),第189页。,《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25)《周易·系辞上》,参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459-460页。以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作为天命实施的根本体现,以道德修养作为“天人合一”的根本途径,而此时所欲“合”的对象即为“义理之天”。战国以来,以荀子为代表的自然生成论,强调“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26)《荀子·天论》,参见[清]王先谦集解《荀子集解》,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529-530页。,以天地自然的生成化育作为天命实施的根本体现,以物质生产作为“天人合一”的根本途径,而此时所欲“合”的对象即为“自然之天”。随着人们对天人关系认识的分化,以“天人合一”论作为理论基础的占卜之术,从形式到思想内容亦均随之而发生变化。
上古时期人们受上帝鬼神观念的支配,将所观察到的一切现象看作神明的启示。《说文》:“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27)《说文解字·示部》,参见[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第21页。“示”的实质是天命的呈现,占卜的作用即在解释天命开示的具体用意,而其所依据的即是“象”。所谓的“象”,指包括各种自然人事现象在内的对象性存在,《易》书称为天地人“三材”。《周易参同契》论观象之法,云“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心,参合考三材”(28)《周易参同契·卷上》,参见[清]陶素耜集注《道言五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2页。。即是观察天文、地理、人事“三材之道”种种之象。具体如何观之?《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9)《周易·系辞下》,参见[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释文《宋本周易》,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62页。可知即是以参观比较之法,连类而通其义。所以《系辞》又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所谓的“像”不仅指“现象”,更有“想象”“类像”之义,如《说卦》所列举“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等例,是为典型。
分析《易传》可知,最初的占卜所依据的即是象,而象占的方法即在发挥“比类合谊”的类象思维方式,寻找不同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关联,从而得出结论,如中国古代所流行的龟卜、梦占之法,即属于象占的范畴。类象思维的本质是一种依赖感性直觉的形象思维(insight)方式,而其后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进展,人们开始将逻辑抽象思维应用于占卜,因此而有数占之法,筮占即为典型(30)李零认为,中国古代的占卜体系可以用“象”与“数”二者来概括。“‘象’是形于外者,指表象或象征;‘数’是涵于内者,指数理关系和逻辑关系。它既包括研究实际天象历数的天文历算之学,也包括用各种神秘方法因象求义、见数推理的占卜之术。”《中国方术考》,第35页。。
以筮占为代表的数占体系之成立,反映出在早期文明中人们的天人、命运观念已经悄然发生改变。《易传》论易数及数占的产生,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31)《周易·说卦》,参见[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释文《宋本周易》,第177页。又说:“成象之谓乾,效法之为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32)《周易·系辞上》,参见[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释文《宋本周易》,第148页。可见数占之形成,同时是将“象”纳入其中的,用“象”来演绎“数”,用“数”来归纳“象”,二者相辅相成。虽然如此,在数占的系统中所假定求解的“天意”,已与象占有着明显的不同。象占将“象”作为占卜中沟通神人、预示吉凶的中介,其所悟出的只能是“神明”(inspiration),天意即“神明”;数占虽然也利用象,如“卦象”“爻象”等等,但是可以用理性思维来把握的数,才是占断的关键。故其所依据数而计算得出的“天意”,就带有了客观规律(law)的意味。考察《系辞》所论筮法一节,如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33)《周易·系辞上》,参见[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释文《宋本周易》,第152-153页。,可知数占背后是有一整套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总结作为基础的。
数占的出现同时意味着关于人们命运的认识变得复杂了。如果说之前人们用难以捉摸的偶然性的“象”来表示恩威不测的天意,视命运取决于造化的奇迹,那么数占在占卜中加入具有确定性的“数”,则体现了命运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之特点。正如《荀子·正名》所言:“节遇谓之命”,“节”犹今所谓“必然性”,“遇”犹今所谓“偶然性”(34)章太炎说:“荀子必言‘节遇’者何哉?节本作卩,命本为令,令者集卩,其义谓合符因果,酬业历然不爽,比于合符,故谓之卩。然人心违顺,本无恒剂,其有乍发决心,能为祸福者,非必因于宿业,而受之者,诚为遇也。”《章太炎全集·菿汉微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页。。偶然的背后是必然,因此数占之卦象由策数所确定;必然之中又有偶然,因此数占虽有确定的运算程序,但每次计算的结果却都是随机数。可见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命运观问题的思考已经相当深入。
理性思维的进化,天命观念的革新,使得人们对冥冥之中主宰祸福赏罚的所谓“司命之神”的存在越来越感到怀疑。荀子就说:“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35)《荀子·天论》,参见[清]王先谦集解《荀子集解》,第540页。认为占卜不过是一种装饰表演而已,不足以用来预测决断大事,所反映的是在经历理性主义启蒙之后占卜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面对这一生存危机,占卜自身不得不寻求新的天人关系论,作为其“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之,即是将决定吉凶祸福的来源、主宰由神秘主义的“信仰之天”过渡到气化论的“自然之天”,与此相对应的是占卜体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较大的变化。
从占卜形式来说,春秋战国以降的占卜形态逐渐趋于数术化。从《左传》《国语》中所记载的占例来看,在春秋时期,以龟卜为主的象占已基本被以筮占为主的数占所替代。其后数占与战国秦汉时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互为影响,发展渐趋符号化、格式化、复杂化,并最终形成了式占这一特殊的数术形式。式占是以式即一种模仿宇宙结构的工具进行占卜,李零说:“它模拟天象,模拟历数,目的是想创造一种可以自行运作的系统,以代替实际的天象观察和历术推步。特别是它使用的图式和符号系统具有很大的抽象性,使占卜者可以利用其方、色变换和配数、配物,将天地万物森罗其中,宛如一部内存容量很大,可以自由输入输出的信息处理机,有求必应地回答各种卜问之事。”(36)李零《中国方术考》,第40页。式占的出现标志着占卜术数化发展的新阶段。
从占卜内容来说,春秋战国之后的占卜内容逐渐趋于经验化。以象占为例,传统的龟卜虽然日渐衰落,乃至绝迹;但相法却迅速兴起,大行其道。相法的流行,一方面因其基本理论建立在两汉以来所通行的自然命定论之上。如王充《论衡·骨相篇》说:“禀气于天,立形于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实也。”(37)《论衡·骨相》,参见黄晖撰《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页。又说:“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38)《论衡·骨相》,参见黄晖撰《论衡校释》,第116页。汉代的天人感应论以及自然命定的元气化生论,无疑为相法乃至整个占卜体系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合理依据。另一方面,相法虽然没有像式法那样复杂的天文历法背景,但因其内容多来源于经验总结,有一定的统计样本作为支撑,所以其中的一些说法容易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验证,从而获取人们的相信。传统卜筮的衰落以及式占、相法的兴起,反映出占卜之术的内容及方法逐渐从神秘性、意象性到逻辑性、具象性,从依赖直觉灵感到注重逻辑推理、经验归纳的转化。
需要指出的是,占卜体系的革新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但这种理性化、经验化的转变却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且并不彻底。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自身理论的原因,如占卜之术所依据的“天人合一”观念虽然从倾向神秘体验的“主宰之天”过渡到“自然之天”,但其所依据的阴阳五行学说本身就保留了大量宗教信仰的成分,而气本论的天人思想也始终未能脱离宿命论的范围;也有一些外在的原因,如式占虽然有系统性以及逻辑思维方面的优势,但因其演算过于复杂,所以虽在汉代盛行一时,但其后流传却并不广。因此,直到唐代,一方面不断有新的占卜术出现,另一方面旧有的占卜形式也往往得以保留,从而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占卜门类。
《唐六典》记载:“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动用之事;丞为之贰。一曰龟,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39)[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14《太常寺·太卜署》,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2页。可见唐代太卜令的职掌除了沿袭传统的“龟”(龟卜)“易”(易筮)外,还增加了后起的“兆”(五兆)与“式”(式法)。又说:“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焉。”(40)[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10《秘书省·太史局》,第303页。其中所包括的占卜术数涉及《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的“天文”“历谱”类,以及“五行”类中的“阴阳五行时令”“灾异”等类目。此外,在民间还流传着种种“杂占卜”,其主要内容有:阴阳、占梦、相宅、九宫、禄命、葬术、相术等。(41)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161页。
以上占卜之法,如相宅、禄命之类在后代流传广泛,不断发展;如占梦之流,则渐趋式微;还有一些如五兆、九宫等,则早已失传。而以上种种内容在敦煌占卜文书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为今人全面系统地了解唐五代时期占卜文化的整体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其中所涉及的门类,郑炳林、陈于柱《敦煌占卜文献叙录》将其分为“易占”“卜法”“式法”“天文占”“宅经”“葬书”“禄命书”“发病书”“梦书”“相书”“婚嫁占”“鸟鸣占”“逆刺占”“走失占”“杂占”(如“占怪书”“藏文景教占卜书”等)“其他”(如各类厌禳之术)共十六类。(42)郑炳林、陈于柱《敦煌占卜文献叙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则将其分为“卜法”“式法”“占候”“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杂占”(如“身体占”“鸟鸣占”“占怪”等)共十二类。(43)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目录”部分。
敦煌占卜文书传承发展了传统占卜的数占、象占体系。如《易三备》继承发挥了京房易学的八宫六十四卦系统,敦煌五兆占法类文献反映出五兆占法将天干、地支、五行生克等引入筮法体系,且计算程序复杂化之特点,可谓传统数占的发展,而《孔子马头卜法》《周公卜法》《管公明卜法》等则相较传统筮法,其流程大为简化,故有利于数占的传播。又如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关于相法、梦占的内容,涵盖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唐五代时期以经验性为主要特点的象占体系的成熟。
考察敦煌占卜的主要理论基础,尤其是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天人观念,可知:一方面,汉代以来流行的“天人感应”的天人关系论,自然气化的天人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说占据了重要地位。如敦煌文献P.3589《日月五星经纬出入瞻吉凶要决》论天象与人事之间的关联,说:“日者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有瑕,必露其虐,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国则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宁。”(44)P.3589《日月五星经纬出入瞻吉凶要决》,参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第162页。此即“天人感应”论的谴告之说。又如Fragment58(756)(IOL.C.118)《先贤周公解梦书》序云:“盖闻解梦者,二气已分,三才列位,五行头缘,天地交泰。阳为日,阴为月,□乾三思,坤将三母始。”(45)Fragment58(756)(IOL.C.118)《先贤周公解梦书》,参见郑炳林《敦煌写本梦书校录研究》,第238页。即以阴阳五行气化的观点来解释天地万物的形成,作为其占梦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宗教鬼神说的天命观念仍然在占卜体系中得以大量保留。其中一个典型是敦煌占卜书所记录的占卜仪式的内容,多为祷祝神灵之说。如P.4048《灵棋经》:“每卜占之时,皆须清净烧香,安作少时,然后执棋而咒之曰:‘卜兆臣某乙,谨因四孟诸神、四仲诸神、四季诸神、十二辰官,上启天地父母、太上元老、日月五星、北斗七星、四时五行、六甲阴阳、廿八宿、岁得(德)明堂:某乙心有所疑,请为决之。’”(46)P.4048《灵棋经》,参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第65页。另一典型是敦煌占卜书中十分常见的厌禳鬼神之术。如P.3908《新集周公解梦书》专设“厌禳噩梦章”,云:“凡人夜得噩梦,早起且莫向人说,虔净其心。以黑(墨)书此符安卧床脚下,勿令人知。乃可咒曰:赤阳赤阳,日出东方。此符断梦,辟除不祥。读之三遍,百鬼潜藏。急急如律令。”(47)P.3908《新集周公解梦书》,参见郑炳林《敦煌写本梦书校录研究》,第177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道德命定论的天人观念在敦煌占卜书中被予以强调,并赋予了新的内涵意义。以“义理之天”为本的“天人合一”论认为,人只有通过道德修养的途径,才能实现、扩充由上天所赋予的仁义礼知之性,达到“与天地参”的“大人”境界,此即天人关系问题的道德决定论。陈来指出:“筮占的正确性,要求筮问者具备基本的德性,要求所问之事必须合乎常情常理。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无论筮占的结果如何,事实的发展和结果必败不吉。这样一来,‘德’的因素成为占卜活动自身所要求的一个重要原则。”(48)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6页。然而此种观点基本上是指向问卜者与占卜者的,即对占卜的人的道德素养作出一定要求,而对占卜体系本身的理论建构作用其实有限,而在实际占卜活动当中,术者亦不以此作为判断吉凶的主要依据。(49)正如陈于柱所言:“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占卜的道德感化并不能掩盖其自身天然的功利性以及所带来的非道德的一面。如敦煌本宅经P.3594中的《推出入逐急不得吉日随时所去门》言:‘会门在子远行吉。兵门在丑攻罚(伐)吉。贵门在卯见官长吉。阴门在巳奸私吉。阳门在午求利吉。狱门在未鱼(渔)猎吉。解门在申祷祀吉。男门在酉求男吉。女门在戌求女子吉。蔡门在亥求物吉。’”《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第232页。
而在敦煌占卜中,这种状况则有所改变。如Fragment58(756)(IOL.C.118)《先贤周公解梦书》序言中反复论及“妖祥不胜善政,怪梦不胜善行”(50)Fragment58(756)(IOL.C.118)《先贤周公解梦书》,参见郑炳林《敦煌写本梦书校录研究》,第238页。的占梦原理。P.2572《相法》说:“凡相之法,看其所作,虽有好相,由(犹)需好行。行若不善,损相毁伤也。”(51)P.2572《相法》,参见郑炳林、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6页。将判断行为善恶作为看相之法的关键。P.4522《推镇宅法第十》说:“埋镇之后,百日内不煞生,不行大(淫),不出恶语,慎之大吉。”(52)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第203页。规定在厌胜法术完成后,问卜者只有严格遵守以上禁忌,镇宅才会收到实效。据此可知,敦煌占卜不仅在占卜理论中强调道德的原则,而且将行为善恶的判断纳入占卜实践当中,从而形成了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行为决定论”同时体现了敦煌占卜中天人观念的理论特色,兹将在下节之中予以讨论。
三、“二重行为决定论”的天人观念
“行为决定论”即认为在占卜活动中占卜结果是由人的行为所决定的。郑炳林指出:“敦煌占卜文书中提出了‘行为决定论’,这是敦煌写本占卜书对占卜活动的贡献。所谓行为决定论就是好相好梦的实现主要取决于自己行为的好坏。‘人好自疑,勿为恶行’,‘妖祥不胜善政,怪梦不胜善行’。这样就把梦书里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存在的矛盾全部变通。”(53)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第1页。简要言之,即解决了“占辞预兆与人事实现之间不统一”的问题。
行为决定论主要体现在敦煌写本解梦书与相面书中。Fragment58(756)(IOL.C.118)《先贤周公解梦书》序言称:“凡龟卜梦兆,并是神□吉凶,然后依经占之,吉凶善恶,消息可知。相梦所作,心同龟兆,是以检书知之,各辨吉凶。……值诸梦相,皆有神在傍前,□对即吉,愿(怨)嗔即不吉,万不失一。……善恶并无要征,后世之人,宜当慎之。梦善即向姓明人前说之,梦若恶,则减(缄)口勿说之,经三日说明之,神明欢喜,即为除灭灾祸及成福。人好自疑,勿为恶行,事当灭刹(杀)。”(54)Fragment58(756)(IOL.C.118)《先贤周公解梦书》,参见郑炳林《敦煌写本梦书校录研究》,第238页。
敦煌本梦书的行为决定论其中包含了这样的内在逻辑:首先,占梦吉凶实际上是由神所决定,而不论是龟卜或是梦兆,从本质上说都只是人与神沟通的一种手段。其次,梦相都有神在其旁,神具于人心,人心善恶,神皆知之,而以梦相示其喜怒之情,为之谴告。最后,神明福善祸淫,故行为之善恶,可以决定神意之喜怒,从而决定吉凶之结果。可见,敦煌本梦书的行为决定论虽以行为作为吉凶的关键,但又认为行为并不能直接决定结果,而是以行为影响神意,神意转化为现实,所体现的是一种天人交互影响的天人关系论。一方面,人事吉凶由天命神意所主宰,而另一方面,天命却并非凭空而来,它主要取决于人的行为之善恶。因此,人又可以积极干预天意,以善行感动神明,“神明欢喜,即为除灭灾祸及成福”,从而自己决定其命运之吉凶。
行为决定论在敦煌写本相书中,进一步发展为“二重行为决定论”,体现出关于天人交互影响关系的更加深入的认识。CH.87《许负相书》说:“夫积善余庆,则众相自然。积恶头(显)扬,表其深现。”(55)CH.87《许负相书》,参见郑炳林、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第27页。P.2572《相法》说:“凡相之法,看其所作,虽有好相,由(犹)需好行。行若不善,损相毁伤也。”(56)P.2572《相法》,参见郑炳林、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第206页。郑炳林解释说:“外部面相是以前行为的表现,人的好相和恶相是由其行为善恶决定的,以前有了善行才会有现在的好相,以前的恶行才决定现在的恶相,陷入了宿命论的观点之中。……如果将《相法》中提出的好相的后天行为决定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即行为—好相或者恶相—行为,又从消极转往积极进取方面转化,这就是敦煌相面术上的面相二重行为决定论。敦煌占卜法的二重行为决定论实际上是一永无止境的轮回过程,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因果关系。”(57)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第6页。
敦煌本相书的二重行为决定论包含了这样的内在逻辑前提:首先,人相的好坏是来自天生的,也是命运吉凶的体现。其次,人行为的善恶直接决定了面相的好坏,因此,人的行为可以决定命运的吉凶。所谓“二重行为决定论”的“二重”,至少有三层含义:其一,是时间先后的二重性:即过去的行为决定现在的面相,而现在的行为又决定未来的相。其二,是逻辑关系的二重性:行为之因决定面相之果,而面相之果又是行为之因的反映。行为为因,则面相为果;行为吉凶为果,则行为动机善恶又为因。最后,是命运观及其天人关系的二重性:人相源自先天,其所禀赋的相的好坏,已为以前行为的善恶所决定。“如果仅仅根据先天行为决定论这一点看是非常消极的人生哲学,有了好相剩下的只要等待好的预兆实现就是了,有了恶相只有安于现状等待报应就是,不求积极进取”(58)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第6页。,虽然如此,即使有了好相,仍需要借助好行乃能令其得以实现,若行不善,则相貌仍然会变为恶相,即所谓“行若不善,损相毁伤也”,又将命运的决定权落实到人自身的行为之上。可见“二重行为决定论”虽也主张天命,即天对人的规定性,但同时又强调人的积极行为即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可以反过来改变天命,这就跳出了传统宿命论的窠臼。
“二重行为决定论”相较“行为决定论”,其天人思想的进步性表现在:首先,是天人互动联系更加直接。敦煌本梦书的行为决定论虽然主张行为善恶可以决定梦兆吉凶,但是仍然带有“神道设教”的意味,以神明的喜怒作为善恶动机与吉凶结果的中介,而敦煌本相书的二重行为决定论则不再假托神灵的权威,而是将人的行为善恶与面相好坏直接联系起来,在天与人的互动关系中,人的主体性更为明确。其次,是因果逻辑性更加严密。二重行为决定论通过在逻辑上设定因、果、缘的概念,以及划分先天、后天,如行为是因,则面相为果;行为动机是因,则面相吉凶为果;先天行为为因,后天吉凶为果,而后天行为则为助缘,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具有辩证思维的特点,对于命运以及天人关系的认识更加复杂、准确。
敦煌占卜书中行为决定论及二重行为决定论天人观念的思想价值与理论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行为决定论通过引入行为这一变量来解决占辞预兆与人事现实矛盾的问题,其高明之处在于:“行为是无法用量化标准衡量的,好行为是什么样的程度,谁也无法确定这个标准,因此相对数量标准法来说出现更宽的回旋余地。”(59)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第6页。对天命的认识具有灵活变通的特点。第二,行为决定论将道德定命的思想引入占卜决断的理论实践之中,“是一种积极的占断方法,提倡人积极行善行,为善政,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作用和意义很大”(60)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第5页。。二重行为决定论则吸收佛教果报因缘以及“众生无定相”等占相之说,同样强调善恶行为对面相的决定作用,鼓励人们多积善行,合于自然。第三,行为决定论及二重行为决定论继承唐代中期以来“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61)[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68《列传第九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39页。的重人事、轻鬼神,重人为、轻天命的时代思潮,在占卜理论实践中强调天命人事的互动作用,重新定义天与人的关系,提升了人的地位,凸显了人主观能动行为的主导性作用,使得长期以来为迷信观念所笼罩的占卜活动具有了理性的色彩,并为宋代及之后以善恶来观察吉凶而认为命运可变的占卜理论的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
四、结论
若提起占卜,人们便容易想到被称作“群经之首”的一部占卜之书,即《周易》,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周易》书中不止有占卜天象人事的内容,甚至连关于占卜自身的预测也已包含在内。占卜数术在易卦中用“巽”来代表,李零说:“卦名有三种读法:一读卜算之算,二读选择之选,三读逊,指伏藏。”(62)李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75页。《巽》九二曰:“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无咎”,似乎早已预言了占卜术数的命运。“巽在床下”之“巽”可读为“筭”,即“算筹”之意,马王堆帛书本《周易》“巽”即作“筭”。古人有“庙算”之说,作为决策大计所用的算筹,本应陈列于太庙,受香火供奉,为何却被置于床下?既然“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63)《周易·蒙》,参见[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释文《宋本周易》,第18页。,为何却又要“用史巫纷若”?“巽在床下”这一象,暗示了后代史巫之流的命运,正如司马迁所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64)[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梁]萧统编《文选》卷41《书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12页。巫卜之士曾经是君王的座上宾,到后来却只能沦为与倡优相提并论的地步,再后来甚至欲求倡优之畜且不可得,只能纷纷流入民间,而成为江湖术士一类的人物。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占卜术数在历史上的没落呢?其实原因仍不出乎一“巽”卦。占卜的目的在于探测神秘的天意,而如果天意可以凭借计算的方式得出明确的结果,那么又何必依赖“朽骨枯草”呢?计算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计算的日渐精密,所反映的是人类逻辑思维的不断进化,而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越是进化,占卜术数这样的建立在高度随机不确定性上的类似于赌博性质的决策方式,就越是难以经得起理性的检验,以至于出现“频巽”即频繁占算的情况,此即“用史巫纷若”的第一层含义。
理性逻辑思维的不断进化,将人的思想观念逐渐从宗教天命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而人们对天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分化。社会思想观念中的“天”,不再仅仅是信仰性的“主宰之天”,同时有了道德性的“义理之天”与物质规律性的“自然之天”的明确概念。天人观念尤其是“天人合一”思想,是占卜术数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新的天人观念的产生、流行以及“天人合一”论的分化,一方面动摇了长期以来占卜所依据的神秘主义与宿命论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占卜自身出于生存的需要,亦不得不吸纳新兴的理论,从而相应地发生分化,体现在占卜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不但史、巫分化,巫、卜分化,而且占卜也分为“象占”与“数占”两大流派,并形成了以式占、相法为代表的高度数术化与经验化的占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占卜决策的抽象逻辑性与经验验证性的需求,此即“用史巫纷若”的第二层含义。
可见,占卜的没落虽然早已注定,但并不意味着它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系统的科学理论产生之前,占卜术数曾经有着相当长时间的发展期,而这些发展演变的历史遗迹在敦煌占卜书中得以大量保存。敦煌占卜的门类繁多,内容丰富,思想来源复杂,其中既讲宗教神秘的体验,又有经验的总结与理性的观察,所反映的是以占卜的形式所传承保留的历史上各个时期人们的天人观念。敦煌占卜既有传承性的一面,也有创新性的一面,以“二重行为决定论”为典型,它重新发掘儒家传统中道德定命论的思想,吸收佛教因果、占相等说,形成了占卜理论关于“天人合一”论的新的解释,通过强调人的道德行为的作用,提升了由占卜活动所体现的天人关系中人的地位,顺应了唐中期以来理性主义的时代思潮,为在人文理性思想不断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之下的传统占卜术数合理性以及有效性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