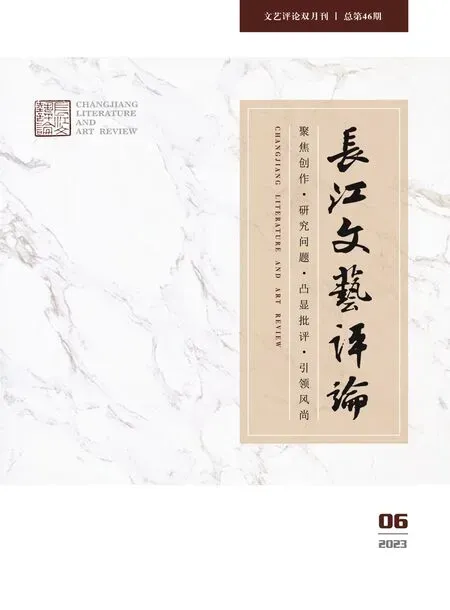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浪漫主义书写
——论叶梅小说的创作特色
2023-03-22◆杨彬
◆杨 彬
叶梅走出大山、走出土家山寨之后,她的神思常常回到家乡恩施,回到那片神奇的土地。她以对那片土地的由衷热爱,以对土家文化的深深领悟,返回到恩施先民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返回到恩施那片神秘秀美的山水之中。叶梅小说在“返回”的过程中,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土家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
“当人们又重新拾起旧日的宗教和局部的及地方的旧有的民族风格,当人们重新回到古老的房舍、堡邸和大礼拜堂时,当人们重新歌唱旧日的歌儿,重新再做旧日的传奇的梦,一种欢乐与满意的大声叹息、一种喜悦的温情就从人们的胸中涌了出来并重新激励了人心。在这汹涌的情操中,我们最初并没有看出一切心灵中所引起的深刻而不可改变的变化,这种变化有那些出现在明显返回倾向中的焦虑、情感和热情给它作证。”[1]这是克罗齐对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描述,它指出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冲动是以“返回”为特征的。当我们仔细阅读叶梅的小说时,那种强烈的返回故土鄂西山乡的情结,使叶梅的创作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一种混合着诗人心灵变化多端的想象和轻快、洒脱、飘逸的幻想,在同一部作品中将近处和远方、今天和远古、真实存在和虚无飘渺结合在一起,合并了人和神、民间传说和深意寓言,把它们塑造成为一个伟大的象征的整体”。[2]叶梅小说就蕴涵着勃兰兑斯所描述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内在特征。故乡在叶梅心中熔铸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使叶梅小说在故事情节、自然描写、文化内涵等方面蕴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叶梅回到故乡那片神奇山水之中,在土家族的历史时空中漫游,把恩施山水塑造成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浪漫主义整体。
一
传奇,是浪漫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最后的土司》《山上有个洞》《回到恩施》中土家山寨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传奇性人物、历史环境及其语言氛围,构成了叶梅小说的传奇特色。叶梅小说的传奇故事在土家山寨中展开,恩施土家山寨对于叶梅来说,那方故土犹如曲波的林海雪原、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从而成为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一种独特的浪漫主义文化艺术氛围。土家山寨已成为叶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成为她永远的故乡情结。叶梅同时也明确地看到土家文化和汉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状态,她描写着鄂西山村土家人的特色,也描写土汉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进程。
叶梅的《最后的土司》《山上有个洞》《回到恩施》讲述了一个个土家山寨的传奇故事。《最后的土司》将两种文化碰撞和交融描写得惊心动魄。小说采用土家人和汉族人对比写法,描写土家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态。《最后的土司》中覃尧是龙船河的最后一代土司,李安是闯入土家地区的汉族人,两种文化的冲突导致一系列悲欢离合的故事。汉族人李安因避祸战争闯入了覃尧的领地,因为冒犯了舍巴日的祭祀活动,被覃尧砍去了一条腿(实则是腿已受伤腐烂,砍去腿是为了保全李安的生命),覃尧派最美的土家妹子伍娘去细心照料李安,伍娘爱上了李安,但是土家族的初夜权造成了李安、伍娘、覃尧三人的人生悲剧。作品对覃尧行使土司初夜权的处理颇有技巧,覃尧行使初夜权,不是土司对属下的权力占有,而是男人对女人真正的爱情。但是,伍娘却不爱覃尧,覃尧希望通过初夜权得到自己喜欢的女人,而淳朴、虔诚、单纯的伍娘只是把土司当作神,在她的意识中,初夜是献给神的,对于世俗中的覃尧她并不喜欢。因此,她坚决回到她爱的李安身边。汉族人李安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将伍娘作为羞辱土司的工具肆意折磨。伍娘生下了孩子,覃尧为了得到自己的儿子,按照李安的要求割掉舌头。伍娘失去了孩子,这个对神最虔诚却命最苦的土家女子在舍巴日祭祀活动中跳舞直跳到气绝。作品通过这个悲壮的故事,将土家文化和汉族文化的碰撞描写得惊心动魄。作品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土家人舍巴日的祭祀活动,也描写了土家人和汉人的文化差别,伍娘的悲剧就是这样的文化碰撞造成的。虽然作品尽量客观地描写文化碰撞给男女双方带来的伤害和影响,但是作为土家族作家的叶梅在情感上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土家族文化。从作品看,土司覃尧比起李安要爽直、宽厚得多,对女人,土司覃尧比李安也要好得多。李安对伍娘的折磨以及最后带走孩子导致伍娘之死,主要是汉族文化在李安身上的凸显。虽然两人都对造成伍娘之死负有主要责任,但从作品可以看出作者情感上倾向于土司覃尧。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在描写文化碰撞和民族融合的同时,保持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追求。少数民族文化不能只是在自己封闭的传统和环境中发展,必须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在特定情况下就是学习汉族文化,因为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碰撞、融合是趋势,已经势不可挡。表现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趋势和特有的历史现实途径,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叶梅创作以来一直的追求。
《山上有个洞》运用时空交叉的手法,描写了最后的一个土司和他儿子的传奇故事,田土司在历史命运(改土归流)前所做的特殊举动,在大敌当前为儿子在山洞操办婚事后引颈自杀的壮举,田土司儿子田昆和牟杏儿的浪漫爱情故事,被叶梅描写得神奇而迷人。《回到恩施》是叶梅最具有“返回”特征的小说,叶梅又以一个外乡汉族人父亲的视野,返回到50 年代的恩施土家山寨野三关,在那里演绎了一段革命历史传奇故事,外乡人父亲、区长张赐和土家人谭驼子、谭青秀、沈先生的纠葛在神奇的恩施土家崇山峻岭中展开,如同野三关山水的神奇一样,他们的故事也具有神秘的传奇色彩。谭驼子的死、九姨的疯、沈先生的世事沧桑以及在历史巨变前的个人悲剧色彩,在叶梅笔下一一展开,汉族父亲终于成为了一个恩施人,一个汉族干部在土家族地区工作,最后把土家族地区当作自己的家乡,他最后回到了恩施,叶梅也回到故土,以深情的浪漫主义笔触描写恩施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传奇故事。叶梅带领我们返回到恩施土家山水之中,让我们深深沉浸在恩施土家山水的历史内涵和土汉文化的融合状态,也让我们看到民族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态。
叶梅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采用土家族和汉族对比描写的方法,既描写土家族的民族特色,又描写土汉民族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撒忧的龙船河》中的覃老大、覃老二和巴茶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龙船河的土家人的代表,而莲玉则是山外汉族人的代表。他们之间对万事万物、对男女之情的看法有很大差别,他们之间的爱情悲剧、人生的悲欢离合,其原因就在于土家和汉族人巨大的文化差别。两种文化的相互碰撞,给覃老大和莲玉都带来迷惑、带来麻烦,也带来一生的悲剧。覃老大和莲玉两人的结合,象征着两种文化的交融,两种不同文化交融的最初碰撞、相融,总会有不适应,甚至会带来悲剧,但是,民族文化的融合是必然的,就如同覃老大和莲玉有了儿子、孙子,他们二人的后代实则就是两种文化融合的象征。叶梅在作品中虽没有明确说两种文化的优劣,但作为土家族作家的叶梅,字里行间对土家人的淳朴、善良、蓬勃的生命力以及那基于两情相悦的相处方式、那与大自然搏斗的力量和智慧都有掩饰不住的赞美。《撒忧的龙船河》中对土家人宗教信仰有详细的描写,土家人的宗教信仰和回族、藏族有所区别,土家族的宗教信仰是图腾崇拜、超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土家族的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合二为一,对生死的看法、对情爱的观念都在土家人的生活中展现出来。《撒忧的龙船河》中第一次在用文学的笔法描写土家人的丧葬习俗,描写了土家族著名的跳“撒忧尔嗬”,土家人对生死具有独特旷达的看法,当人死去后,土家人认为他只是走向另一段路程,亲朋好友不用悲伤,应该跳起“撒忧尔嗬”欢快地将他送走。作品中覃老大去世,妻子巴茶没有哭天喊地,而是在场坝里掌灯,十几个土家汉子为他跳起“撒忧尔嗬”,“笑逐颜开的气势非凡地为覃老大送行。”[3]丧事喜办、哀而不伤,是土家人独特的丧葬习俗,也展现了土家人旷达的生死观。
二
叶梅是恩施人,对于故乡——恩施土家山寨那方山水她怀着特殊的感情。如果说传奇故事是她对土家先辈们的神话崇拜,那么对土家山寨的自然描写则是对土家山水的诗化写意。让故乡从背景走向前台,把故乡作为主人公,把自然性灵化展现了浪漫主义的又一明显特征。叶梅小说的中的故乡,已不是一般的风景、风物描写,它是热烈的情感宣泄,是安妥作者灵魂的一方圣土。叶梅的故乡既是土家山寨本色的展示,又是其心灵的抚慰和情感的寄托。在叶梅作品中,故乡已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和背景,而是从背景走向了前台,成为了叶梅小说的角色和主人公。
《山上有个洞》中的“洞”,不仅仅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场所,也是叶梅故乡山水独特的代表,是叶梅心中的一块圣地:“应该说土家人从他们的祖先巴人开始就对洞穴有着深刻的感情。那时在清江之畔的武落钟离山,有着赤穴、黑穴两个山洞,住着五姓族人。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其他四姓生于黑穴,起初的时候不分君长,俱事鬼神,后来相约掷剑于石穴,说明中者,则奉为君。巴氏之子务相独中……五姓人于是心悦诚服,共立巴务相为廪君,廪君就是土家人供奉的祖先,死后化为白虎,受到子孙万代的景仰。土家人因此对祖先住过的山洞敬仰有加,田土司……把高高山上的通天洞当成儿子的学堂,考虑不能不说有他独到之处。这洞与世隔绝,风光秀美,本是一个让人断绝尘念修身养性的绝妙所在,且紫气东来,冬暖夏凉,真所谓洞天福地。”[4]
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出,叶梅对“洞”的描写绝不仅仅把它作为普通的自然景物来描写,它饱含着叶梅对“洞”的土家文化意韵的热爱和崇拜之情,既充分展示了洞在土家族文化中的深刻历史内涵,又包含着作者对故乡山水无比热爱的圣洁之情。
故乡山水在叶梅作品中成为角色,成为精神实体,它被灵性化了。它的灵性化包括“人化”和“神化”两个方面。如评论家王又平所说:“所谓‘人化’,即把自然理解为一个可解人意、与人声息相通、心灵相同的世界”。“所谓‘神化’,则是把自然理解为一个不言不语、神秘莫测,具有崇高感的威严世界”。[5]
叶梅作品中的故乡,即土家山寨的山山水水:龙船河、清水河、通天洞、野三关,不仅仅是人物和环境的装饰和道具,它自身就是角色,甚至是主人公。土家山寨的山水具有自己的灵性、性格、意志和力量,它自身就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用俄国形式主义的术语来说,故乡山水(自然)被置于前景,对于整个作品的审美起着支配作用。故乡山水是一个可解人意、与人声息相通的世界,它能抚慰心灵、寄托情感,甚至具有人所不具有的超意志力量。
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长江三峡沿岸高低起伏的大山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溶洞,它们是崇山峻岭中一只只睁大的眼睛,长久地不动声色地凝视着天和地,是是非非,风风雨雨,爱恨情仇,沧海桑田,一代又一代。……人老洞未老……[6]
这是《山上有个洞》中的一段话,在这里溶洞不仅仅是作品主人公生存、栖息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自然已经从背景走向前台,它和田土司、田昆、田快活一样,是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代又一代土家人的历史见证,也和作品中的土家儿女一样,是作品中的重要角色,一起展示着故乡土家山寨的文化内涵。
叶梅小说从特定的土家文化和恩施土家山水情境出发,塑造了一个个性格突出而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
《最后的土司》中的伍娘就是一个充满了浪漫主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是土家山水的化身,是土家文化的精魂。伍娘的出生就充满神秘色彩:“李安后来才知道,同龙船河许多解不开的谜一样,女子伍娘的身世也是一个谜,十八年前的一个早晨,桡夫子在龙船河的旋涡里发现一只转动的木盆,不管水流如何冲击,木盆只是在那里打转,两个时辰过去了还在原地。更让人惊异的是,一个小小的婴儿裹着一件红绸衣,安安静静地躺在木盆里随那波浪打转,一个劲儿地对天空奇异地微笑。土司看了说:‘河水都打不走,那就养在龙船河吧。’她随土司姓了覃。覃伍娘从生下来就不会说话,她高兴或者生气都只会呵呵地叫。可她长成了龙船河最美妙的女子,她吃百家饭长大,自小便学鸟飞兔跑,树摇草动,将山水天地间的灵气都采到了心里,她会用身体的动作表达一切,龙船河的人从来也不觉得伍娘不会说话……”[7]这个漂亮、美妙充满灵气的土家女子,是土家文化的精魂,她用生命护卫爱情,也用生命诠释土家的神灵。她用生命舞蹈,用恩施山水所有的灵气舞蹈。当神灵和爱情发生矛盾时,她用舞蹈和生命完成了对舍巴日的祭祀。可以说,伍娘是土家族奇异秀美山水的化身,是土家文化的精魂。
《山上有个洞》中的田土司是一个具有传奇性的英雄人物,他在土家山寨面临灭顶之灾时,以土家人特有的胸怀,为儿子田昆在山洞里当着汹汹来犯之敌操办婚事,为了免除全族人的杀身之祸而引颈就义。《回到恩施》中的沈昌舜,这个参加过武昌起义的土家绅士历经沧桑,身世传奇。在土改和剿匪斗争中他深明大义,力劝匪首投降。叶梅用神秘的笔调描写了他因历史变迁而难以违抗的悲剧结局,但无论如何,沈昌舜确是一个具有传奇性的人物。
叶梅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具有浪漫传奇色彩,如《最后的土司》中的土司覃尧;《山上有个洞》中的田昆、田红军;《回到恩施》中的谭驼子。这些土家山寨养育的人杰,有情有义,血气方刚,敢做敢为,活得光彩照人,死得惊天泣神。他们既是恩施土家山水养育的儿女,也是恩施土家山水的精魂。
三
叶梅小说蕴涵着独特的文化意韵,那是土家文化特有的浪漫主义内涵。那土家山寨的传奇故事,那土家山水的自然情韵,都深深包含着土家的文化意韵和文化氛围。在她小说的很多地方,都表现了土家文化和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浪漫主义意韵。
“土家族女作家叶梅便是这样一位有着强烈本民族文学意识的作家。她以本民族文学作为自己的支撑点,把创作思想和文化价值取向指向土家族文化传统所蕴涵的美德,通过对土家人生活的挖掘和人生意义的揭示,讴歌新时代新生活,展现民族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也传达着土家人在同社会命运、个人命运搏斗中的力量和坚强。”[8]这是吉狄马加在为叶梅小说《五月飞蛾》所做的序中对叶梅小说的评价,他看到了叶梅小说所蕴涵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叶梅小说的民族文化内涵具有土家人特有的浪漫主义内涵。土家人崇尚自然,崇尚神灵,张扬生命激情,他们把自然和神灵一样看待,从自然中去感悟生命的本质。《最后的土司》中,叶梅用充满浪漫主义的笔调,描写了伍娘用舞蹈表达对自然的崇敬、对神灵的崇敬,同时也展示伍娘那深入骨髓的土家人特有的情结,那就是把生命奉献给神灵,完成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完成对舍巴日的祭祀:“她一次次舒展双臂向空中呼唤,充满迷惘的渴望。她泪流满面,同时又灿烂的微笑,她的舞蹈像龙船河水飘然而过,像天边的月亮冉冉升起,像树丛中飞过的精灵,她像是忍受着烈火的煎熬,又像是在烈火中找到了归宿。”这段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文字,充分展示了土家文化的浪漫主义本质。
土家人在巴山秀水中生活,在山的熏陶和水的浸染下,土家女子温柔美丽,清醇得如同恩施那美丽的清江水,为了神灵为了爱情可以舍弃一切。而土家男人则轻财重义、守信重诺,豪放豁达、乐观自信。
土家文化的浪漫主义内涵被叶梅用充满激情的文字描写出来,让我们在她那深情的描写中感受土家文化的浪漫主义本质。叶梅一直提倡多民族文学观念,她的小说以描写土家族的民族特性为主,但她深刻认识到聚居于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的土家族人民是通过不断与汉文化、楚文化、蜀文化、黔中文化、夜郎文化进行交流兼容,从而形成了土家族独特的开放包容的文化样态,她的作品都是在土家族、汉族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中,进行人物塑造、故事设置和情感表达。
叶梅已经走出了大山,走出了土家山寨,因为走出,所以她的眼光才那么独到和宽阔,她的作品才具有超越大山的胸襟。因此她的小说也不仅仅是返回式的模式。其他作品如《五月飞蛾》就是走出大山、走出土家山寨的另一种描述,是走出大山后对当下的思考。叶梅小说既返回土家山寨,又走出土家山寨,既立足于土家文化,又真切地描写鄂西这块土地上各民族交流、交往、交往的图景,用文学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叶梅不同于那些纯粹返回式浪漫主义小说家的长处,也是叶梅小说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