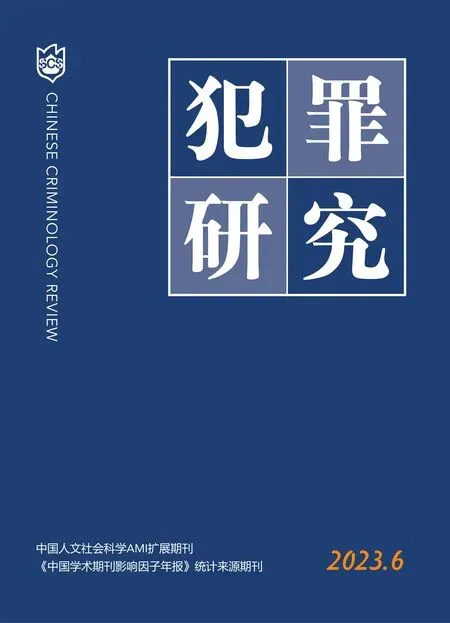环境刑法中的预防原则与累积犯
2023-03-22川口浩一著陈俊秀夏杉青译
[日]川口浩一著 陈俊秀 夏杉青译
一、前言
近年来,由于塑料垃圾的产量持续增加,微塑料引起的海洋污染问题凸显,可能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带来不良影响。(1)关于这种对生态和人类产生不良影响的机制,参见《プラスチックごみは何が問題なのか?:有害物質の運び屋であるマイクロプラスチックが世界の海をただよっている》,《NEWTON》2020年第40卷第1号,第102页。该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高度关注,与全球气候变暖并列为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然而,“关于海洋塑料污染,塑料垃圾的流出量和入海路径、海洋中塑料循环的实际状态、微塑料对海洋生物和人类的影响等尚不明确的内容还有很多”。即便如此,仍有学者强调法律迅速应对的必要性,他们指出(2)参见铃木良典:《海洋プラスチック汚染の現状と対策》,《REFERENCE》2020年第829号,第3页。“考虑到塑料流出到海洋后不易分解和回收,在明确各项内容后才开始寻找对策可能为时已晚”。(3)关于国际趋势,参见铃木良典:《海洋プラスチック汚染の現状と対策》,《REFERENCE》2020年第829号,第3页;辻昌美:《海洋プラスチックごみに関する国際的動向》,《Governance研究》2020年第16号,第101—173页;岩泽聪:《米国における一般廃棄物処理の概況とプラスチック規制の現状》,《REFERENCE》2020年第829号,第29—59页;远藤真弘:《廃プラスチックの輸出入をめぐる状況》,《REFERENCE》2020年第829号,第61—71页;滨野惠:《EUの海洋ごみ対策及び循環経済への転換に向けた取組:特定のプラスチック製品による環境への影響を低減する指令》,《外国の立法》2019年第282号,第45—74页;中西优美子:《EU環境法の法的枠組と措置の構造解説:EU の使い捨てプラスチック製品規制指令を例として》,《環境管理》2019年第55卷第9号,第33—39页;高田秀重《マイクロプラスチック汚染の現状、国際動向および対策》,《廃棄物資源循環学会誌》2018年第29卷第4号,第261—269页。在德国,也展开了有关海洋塑料污染的刑法应对问题的讨论。(4)Vgl. Martin Heger/Markus Hower, Gewässerverunreinigung durch Kunststoffpartikel in Kosmetikprodukten, NuR (Naturund Recht) 2014, 470ff.; Klara Malberg,Gewässerverunreinigung ( §324StGB) durch Einbringen fester Stoffe in Gewässer: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Rechtsgutslehre im Umweltstrafrecht, Hamburg 2018;Regina Michalke, Die Gefahr für die Umweltmedien-und die (bescheidene)Rolledes Strafrechts bei deren Feststellung und Eindämmung, in: Thomas Fischer/Eric Hilgendorf (Hrg.), Gefahr, Baden-Baden 2020, S.209 ff.与全球变暖相同,应对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时,所谓的“预防原则”或“事前考虑原则”(5)参见大塚直:《環境法》,有斐阁2020年版,第55页。“防患于未然原则”是指“应防止威胁环境的物质或活动给环境带来不良影响”。不同于前者,“预防原则(预防性方法)下物质或活动与环境损害的联系不能得到确定的科学证明,即以科学不确定性为前提”。同时,预防原则的特征有三:一是伴随着“科学不确定性”;二是以可能发生“严重的或不可逆的”损害为前提;三是强调“不能将具有科学的不确定性而延期对策作为理由使用”。与此相对,德国的“事前考虑原则”是“涵盖预防原则和防患于未然原则的概念”,包括 “危险防御”“风险事前考虑”以及“将来考虑”三个方面。在环境刑法中的适用成为问题。如后文所述,从传统刑法学的立场来看,很多学者对在环境刑法中导入预防原则持慎重意见。另外,在立法中,如《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1998年法律第117号)中没有将“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本身作为惩罚对象。对此,也可以考虑对部分经营者施加总量规制,对违反者根据情况实施不同的刑事制裁。若在某些领域中预防原则性规制是必要的,则环境刑法学要求包括从立法论层面探讨刑事规制应该如何起保障作用。
柳宪一郎先生撰写了预防原则的适用等与环境污染问题相关的大量文章。(6)参见柳宪一郎:《化学物質管理法と予防原則》,《环境法研究》2005年第30号,第35页;朝贺広伸:《英国のリスク管理と予防原則》,《环境法研究》2009年第154号,第129页。近期,与预防原则相关的“累积犯”(Kumulationsdelikt)的讨论再度受到日本学界的关注。虽然这篇文章还不够成熟,但仍想在本退职纪念号上献给先生。
二、关于德国环境刑法中累积犯的讨论
德国环境刑法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主题:一是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7)关于对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论的批判,请参见拙稿《環境刑法総論の基本問題》,《関西大學法學論集》2015年第65卷第4号,第109页。二是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8)行政从属性问题讨论的概观,请参见拙稿《環境刑法の行政従属性について》(收录于井田良编《山中敬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下巻]》,成文堂2017年版,第397页)。亦可参见近期的德国专著:Maximilian Lenk, Die Bedeutung verwaltungsrechtlicher Entscheidungen und Rechtsbehelfe im Strafrecht: Zugleich eine konzeptionelle Betrachtung über die Berücksichtigung rechtlicher Rückwirkungsfiktionen im Strafrecht, Berlin 2020.三是洛塔尔·库伦(Lothar Kuhlen)提出的累积犯理论。(9)Vgl. Hanna Sammüller-Gradl, Die Zurechnungsproblematik als Effektivitätshindernis im Deutschen Umweltstrafrecht, Berlin 2015, S.144-151.具体而言,主题三的累积犯理论是对《德国刑法典》第324条(§324 Gewässerverunreinigung)的水域(水体)污染罪(10)关于该条,除了各种评论之外,还可参见Frank Saliger, Umweltstrafrecht 2. Aufl.,München 2020, Rn. 328 ff.; Paul Krell, Umweltstrafrecht, Heidelberg 2017,Rn. 195 ff.; Michael Kloepfer/Martin Heger, Umweltstrafrecht, 3. Aufl., München 2014, Rn. 171 ff.另外,丸山雅夫在《環境媒体汚染》(收录于町野朔编《環境刑法の総合的研究》,信山社2003年版,第442页)一文中将Gewässer译为“水域”;浅田和茂在《ドイツの環境刑法》(收录于中山研一编《環境刑法概説》,成文堂2003年版,第62页)一文中将该词译为“水体”。的解释,该条规定:“水域(水体)污染罪(1)未经许可污染水域或恶化水质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2)犯本罪未遂的,亦应处罚;(3)过失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弗兰克·萨利格(Frank Saliger)提供了以下事例来解释此规定。
事例1:A、B和C三人在短时间内分别按照A、B、C的顺序朝一个小湖的不同位置丢弃家庭垃圾。三人丢弃的垃圾量均在轻微性的界限以下,但这些垃圾的总量达到第324条第1项的结果标准。A、B和C是否需要因违反该条规定而承担刑事责任?(11)Vgl. Frank Saliger, Umweltstrafrecht 2. Aufl.,München 2020, Rn. 220.
若将本罪视为侵害结果犯,着眼于个别行为和个别结果判断“污染”和“水质恶化”,则在这个事例中的A、B和C都是不可罚的,这是一贯的结论。与“个别行为说”相对的是“全体行为说”。立法者也是基于后一种学说,设定“全体结果”,并将这个结果分别归属于A、B、C的个别行为。然而,“全体行为说”在刑法解释论上并没有充分的法理基础。洛塔尔·库伦的“累积犯”(12)Vgl. Lothar Kuhlen, Der Handlungserfolg der strafbaren Gewässerverunreinigung (§324 StGB), GA 1986, 389 ff.正是为了从理论上奠定该学说的基础。在累积犯理论中,不要求个别行为与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险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欠缺刑罚威慑时,多数行为会反复发生,从而使受保护的水体功能发生障碍。累积犯理论将反复发生的行为犯罪化,其重点在于回避因果关系问题。(13)Vgl. Frank Saliger, Umweltstrafrecht 2. Aufl.,München 2020, Rn. 244; Paul Krell, Umweltstrafrecht, Heidelberg 2017, Rn. 70ff.与此相对,弗兰克·萨利格主张“区分方法”,(14)Vgl. Frank Saliger, Umweltstrafrecht 2. Aufl.,München 2020, Rn. 246 ff.根据与信赖原则结合的自我答责性原理,区分第一行为者和后续行为者的答责领域。首先,第一行为者(上述事例中的A)对由其引起的部分结果负责,不承担刑事责任;后续行为者可能对全体结果负责。由于B的行为结束后垃圾丢弃量还没有超过轻微的范围,所以B也是不可罚的。最终只对C根据其具体的认识状态以故意(第324条第1项)或过失(同条第3项)进行处罚。(15)Vgl. Frank Saliger, Umweltstrafrecht 2. Aufl.,München 2020, Rn. 250.然而,这个结论为个别行为的发生时间这一偶然因素所左右,相较之下基于累积犯理论(全体行为说)得出的结论似乎更为妥当。下文将参照日本的讨论,探讨引入德国环境刑法的累积犯在理论上是否妥当。
三、日本累积犯的肯定论与否定论
(一)平野龙一提出问题
1978年,平野龙一在国际比较法学会第十次大会的报告《环境的刑法保护》中提出“当一种物质的排放只有在累积之后才产生危险时,或当它与其他地方的排放物或外部条件竞合之后才产生危险时,或在现有的科学知识中难以认定该物质对人类健康有害时”(16)平野龙一:《環境の刑法的保護:第10回国際比較法学会大会での一般報告》(同《刑法の機能的考察》,有斐阁1984年版,第90页),初载《刑法雑誌》1970年第23卷第1、2号,第164页。,法律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并对危险概念作了阐述:“危险这个概念一般是不明确且难以证明的。特别是在污染行为的情况下,危险不是由一个污染行为引起的,而是由污染行为的反复发生造成的。每个污染行为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危险性,但行为的累积会危害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另外,行为在偶然的情况下,即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是否可能造成危害也是不确定的。”(17)平野龙一:《刑法の機能的考察》,有斐阁1984年版,第111页。对此,长井圆表示,平野龙一“虽没有使用‘累积犯’这个词,但其很早就指出了累积犯的要点”,洛塔尔·库伦的累积犯理论是对平野龙一提出的问题进行的理论回应。(18)参见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50页。
(二)长井圆的见解
1.累积犯的意义
长井圆对累积犯的界定是:“虽然各个别犯罪行为不需要达到法益侵害或危险化,但只要该犯罪行为反复进行,就需要专门属于引起法益侵害或危险化的行为形态的犯罪类型。”(19)同上注。这本身就暗示了狭义上真正的“环境犯罪的处罚依据”并非“保护法益的侵害、危险化”(20)同上注。。易言之,“极多数行为者的自身行为不构成‘传统的财产犯’(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但这些行为‘给环境带来负荷’,反复‘累积’后能造成‘环境法益的侵害、危险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各行为者不一定成立‘共同犯罪’,但各单独行为能够因果性地构成累积结果(法益危害)或有构成结果的危险,可以作为‘特殊的抽象危险犯’予以惩罚”(21)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51页。。对此,长井圆认为,传统犯罪论中广义的共犯是指“造成同一法定结果(既遂、未遂)的复数行为者,根据共谋、意思联络等对因果关系的加功,各自成立犯罪”,而累积犯“这种共犯或特殊共犯没有法定或理论上的构成依据,(22)在德国,也有人认为累积犯参与了类似于共同犯罪的全体行为,导致累积的全体结果,如水体污染。参见葛原力三、川口浩一译:《Claus Roxin?Günther Jakobsドイツ刑法学の過去(きのう)?現在(きょう)?未来(あす)》,《関西大学法学論集》2020年第50卷第1号,第168页以下、第212页。是所谓时间性的‘同时犯’(单独正犯)的一种,是独特的‘遥远的抽象危险犯’的一种类型。并且累积犯作为环境犯罪的重要理论依据,其不同于公害犯罪(公众危害犯),即使不危害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传统的个人法益,也会对革新的、综合的环境法益(公益、集体法益)造成危害,在性质上是与‘保护未来世代的环境’不可或缺的预防原则相关联的‘具有不确定风险的特殊抽象危险犯’”(23)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51页。。
2.作为抽象危险犯的累积危险犯
长井圆认为“累积危险犯”是“仅凭自己的单独行为不能造成法益的侵害或危险化,只有通过与同类他人的多数单独行为的‘竞合’才能危害法益的犯罪类型”,是“抽象危险犯的一种”(24)同上注,第63页。。在累积危险犯中,“每个人仅因自己的单独行为(行为的因果贡献)受到处罚”,即使是同时犯,“每个单独行为并不需要在时间上同时进行,也可以前后进行,只是要求其多数行为的累积结果有导致法益危害的可能”。易言之,该累积结果“从法益危害来看具有近似于纯粹的‘客观处罚条件’的性质,但未被法律的肯定为犯罪成立要件”。以法益危害为依据的累积结果并不构成各行为人的“罪责本身”,而只是作为“确认可罚性的立法依据”,尽管这些行为本身是轻微的行为。(25)同上注,第64页。同时,累积危险犯只对自己的抽象危险行为造成的“法定结果”负责,承担相应的“法定刑”。(26)同上注,第66页。上田正基在《その行為、本当に処罰しますか:憲法的刑事立法論序説》(弘文堂2016年版,第146页)一文中也提道:“累积犯和预备犯的行为规范,在达到所设想的抽象危险的过程中,以他人或自己的后续行为的介入为前提,所以相对于行为规范所描述的行为本身,累积犯和预备犯中行为人的答责性较小。”“多数人的协作行为既遂造成的危险”,没有成为明示的犯罪成立要件,所以“对这种危险的认识也不能成为犯罪成立的要件”。易言之,“在累积危险犯(真正的环境犯罪)的认定中,只要求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大量重复、累积与自己相同的犯罪行为带来的‘抽象危险’有概括性认识即可。各行为者根据其行为的一般性质,通常能认识到上述情况”(27)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66页。。另外,累积危险犯的要件不限于“同一种类行为”的累积,若其定义包括“同一目标的其他行为样态”,则累积危险犯理论的适用领域还将扩大到非法制造或持有武器、药物,伪造货币、信用卡和交通危险犯的超速驾驶等犯罪。(28)同上注,第64页。
3.累积危险犯处罚的界限
长井圆认为,累积危险犯是“抽象危险犯的一种”,但“法理并不允许对所有造成环境负荷的行为进行无限制处罚”,如“人类呼吸时进行的气体交换——吸入维持细胞、组织活动所必需的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即使是粪尿的排出,也不能以造成环境负荷为由认定违法”。“人类生存、生活所必需的排出行为,属于《日本刑法典》第35条的正当行为,其违法性受到排除。”另外,根据《废弃物处理法》禁止非法丢弃的规定(第16条),“任何人不得随意丢弃废弃物”。这里所说的“随意”的要件,意味着丢弃行为应符合“可罚的违法性”,如“一些家庭将蔬菜鱼肉的废弃物混合发酵成肥料,减少了一般废弃物的排量,有益于环境保护”。此外,“即使将必要的排出行为称为‘社会性相当行为’,其是否构成实质上违法仍需要借助常识判断”(29)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73页。,以下举例加以说明。(30)同上注,第74页。
事例2:X朝便利店放置的垃圾箱内随意丢入店外购得物品的垃圾。长井圆认为,事例中X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倾倒罪。当垃圾量达到一般废弃物的收集范围时,X应成立《轻犯罪法》第1条第27号规定的“丢弃污物或废物”行为从而受到处罚(拘留或罚款)。(31)同上注。
事例3:X从海岸向大海投下一个塑料瓶。针对这种向海洋和河流乱丢塑料垃圾的个别行为(即使是少量垃圾),考虑到塑料对海洋的“累积”性以及“预防原则”,这种情况究竟应该肯定其具有非法抛弃罪的可罚的违法性,还是应该认定其为《轻犯罪法》上的犯罪尚待商榷。如果把非法抛弃罪解释为“累积危险犯”,那么便可成立该罪。
4.与累积侵害犯的区别
长井圆提出“必须区分累积(危险)犯和与此不同的类似犯罪”,并列举了如下事例。(32)同上注,第65页。
事例4:X把一杯水倒进水库后,修学旅行中同行的99名同学Y1-99也相继半开玩笑地把各自的瓶装水倒入水库。仅有X的行为还不能导致现住建造物等侵害罪(33)现住建造物等浸害罪,参见《日本刑法典》第119条规定:决水浸害当前有人居住或是当前有人在其中的建造物、火车、电车或矿坑的,处死刑、无期或三年以上徒刑。——译者注(《日本刑法典》第119条)的结果,但与Y1-99的行为相加、累积足以造成水坝决口。(34)参见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65页。上述情形可以称为“累积(侵害)犯”,但认定为“累积(危险)犯”显然“似是而非”。长井圆在该事例中表示,“作为法定结果的‘侵害结果’的罪责受到了质疑”,“X的危险行为和法定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客观归属关系),X只要在行为时认识到在水库的现状中加入X的行为就会达到法定结果,就会成立故意的既遂犯”。不过,X如果对Y1-99行为“连概括性的认识都不存在,就不可能对水库决口引起的浸水结果(因果关系)存在认识,因而X的故意不成立”。但“只要有竞合原因及认识,X对于自己的同一行为就成立单独犯(同时正犯),因而没有必要讨论X与Y1-99的共同正犯(意思的联络·《日本刑法典》第60条)是否成立”。(35)同上注。正如长井圆明确指出的,这个事例的问题在于累积性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累积犯,所以对该事例的“累积侵害犯”解读是错误的。
5.预防原则与累积犯
最后,长井圆在与上述预防原则的关系与防患于未然原则的对比中指出,“传统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或公共危险犯,结果发生风险的增加即为行为危险的实现。只要判断危险时依据‘统计因果法则’或‘确实的科学证明’,就符合‘防患于未然原则’的要求”(36)同上注,第72页。。而“与抑制不确定风险的‘预防原则’相对应的抽象危险犯是‘累积危险犯’”(37)同上注,第73页。。
事例4:这样的“累积侵害犯”是“仅仅是因果关系竞合的一个事例”,而“累积危险犯”则是“即使累积很多人的行为,行为与法益侵害(如全球变暖这一结果)的因果关系的预测本身也有不确定的风险”。“尽管如此,只有援引‘预防原则’,才能对这种个别行为(环境负荷)的累积导致的‘风险增加’进行对应且正当的处罚。”(38)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72页以下。但是,“预防原则的适用仅限于存在‘不可逆的重大法益侵害’风险的情况”。(39)同上注,第73页。
(三)嘉门优的见解
上文中长井圆强调了预防原则与累积犯的联系,对此部分学者也提出了将防患于未然原则与累积犯联系起来的见解。例如,嘉门优认为,“累积犯确实是指,该行为本身不侵害法益,但通过与其他同样的行为方式的共同作用,能够导致法益重大侵害的行为方式,如禁止乱扔垃圾等为了保护环境而制定的惩罚性规定。为了将惩罚犯罪的行为正当化,要求严格验证人类生存将会遭受怎样的实际危害”(40)嘉门优:《法益論の現代的意義》,《刑法雑誌》2011年第50卷第2号,第12页。。针对开头列举的逐渐得到验证可能对人类产生实际危害的海洋塑料污染问题,如上述事例3中的个人向大海或河里乱扔塑料垃圾是否具有可罚性的问题,我们期待该见解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四)北野通世的见解
北野通世也持同样的立场。他认为,“累积犯是以保护环境、各种制度、一定的社会关系为目的,本身很难单独认定是侵害、危险化法益的行为,是为了防止同样的行为反复发生,效果累积造成法益侵害、危险化而设置的,被解释为抽象危险犯的一种类型”。然而,“问题在于,此种个人行为难以单独认定为侵害或危险化法益,对该行为的处罚如何正当化”。也就是说,在社会上,个人所承担的义务不仅限于“不要给任何人带来伤害”,还包括为确保“公平分配”而协助他人的义务。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处罚可以从两方面来正当化:一是累积效果足够现实;二是从规范角度来看具有特殊的可罚性。(41)Andrew von Hirsch/Wolfgang Wohlers, Rechtsgutstheorie und Deliktsstruktur-zu den Kriterien fairer Zurechnung In: Roland Hefendehl/Andrew von Hirsch/Wolfgang Wohlers (Hrsg.), Die Rechtsgutstheorie: Legitimationsbasis des Strafrechts oder dogmatisches Glasperlenspiel? Baden-Baden 2003, S. 196 ff., 207ff.累积犯的处罚正当化的第一个要素是“内容的重大性,即该法益对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共同生活非常重要,当该法益受到危险化和侵害时,受害对象重大并不确定地扩大,且恢复代价巨大”。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可以进一步地说,“作为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根据,行为与法益之间的无价值关联必须得到实质性承认。即法益侵害、危险化的机制明确,且该行为造成部分法益侵害、危险化结果,即形成了法益侵害发生所必需的因果性条件之一”。易言之,“在满足这两个要件的情况下,累积犯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法益危险化构造的一种特殊的抽象危险犯”。(42)参见北野通世:《抽象的危険犯における法益の危殆化構造》,《山形大学法政論叢》2014年第60、61号,第7页、第43页。同时,该见解的持有者认为有必要确认“已明确构成发生法益侵害所必需的因果条件之一”。如嘉门优所言,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来看,可以认定累积犯是“抽象危险犯的一种类型”。(43)北野通世在《抽象的危険犯における法益の危殆化構造》一文提道,一般认为累积犯的概念是洛塔尔·库伦提出的,但实际上威廉·加拉斯(Wilhelm Gallas)早已提出了同样的理解和想法。Vgl. Wilhelm Gallas, Abstrakte und konkrete Gefährdung, in: Hans Lüttger (Hrsg.), Festschrift für Ernst Heinitz zum 70. Geburtstag, Berlin 1972, S. 171 ff., 181.
(五)批评累积犯的见解
1.伊东研祐的见解
伊东研祐将累积犯界定为,“各个别的犯罪行为不需要达到法益侵害或危险化的地步,但如果该犯罪行为大量发生的话,必须要专属于会引起法益侵害或危险化的行为形态”,并批评说:“从责任主义的观点来看,累积犯这一范畴的正统性并不值得肯定”(44)参见伊东研祐:《環境刑法序説》,成文堂2003年版,第23页注41。。这种批判是对累积犯的一般批判,但正如长井圆所暗示的那样,其“忽视了环境犯罪的处罚正当化的‘理论根据’(环境‘法益’危害的事前抑制必要性这一立法理由)”(45)参见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66页。。该见解的持有者有必要释明具体何种情形会违反责任主义。
2.斋野彦弥的见解
首先,斋野彦弥认为洛塔尔·库伦的累积犯概念是指“个别行为的实施不会造成犯罪结果,但大量进行就会造成一定的法益侵害、危险化的行为”。他认为,“你的污染行为不会危害到现在某人的健康,但如果大家都做和你一样的事情,将来就会造成损害”。其次,“水质污染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健康的责任,是否能超越可罚的违法性界限而使惩罚正当化?如果盗窃别人地里一个苹果的行为缺乏可罚的违法性,就不能以可能发生同样的盗窃为由,让个别行为人承担多数人盗窃整个苹果园的(被稀释的)责任”。(46)参见斋野彦弥:《公害刑法と環境刑法》,收录于町野朔编:《環境刑法の総合的研究》,信山社2003年版,第67页以下。
长井圆反驳道,“第二点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斋野彦弥对累积犯的曲解或认识混乱”。长井圆认为,“水质污浊罪是指当事人应对自身的污浊行为(单独犯)承担‘相应’的责任,进而承担刑罚,而不允许将其他多人的污浊行为的责任转嫁给该当事人”,“同样,不能因当事人盗窃一个苹果的行为,而将其他多人的盗窃整个苹果园的责任转嫁给该当事人”(47)参见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66页。。不过,斋野彦弥认为“环境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仅因个人法益之间的关联性薄弱,就否定一切环境侵害行为的可罚性”,相较于“累积这种单纯的数量上的问题”,为了应对关联性薄弱带来的问题,更应该从“法益侵害增加的主要原因”上寻求答案。其中主要包括“侵害的不可逆性、不可回避性”,“足以危及人类存续”的“严重损害后果的严重性”,模仿性、诱发性,“与其他因素、原因综合而产生结果的复合性”四个原因。(48)参见斋野彦弥:《公害刑法と環境刑法》,收录于町野朔编:《環境刑法の総合的研究》,信山社2003年版,第68页。对此,长井圆表示“最终肯定了累积犯的当罚性”。参见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66页。因此,斋野彦弥否定累积犯概念,但从预防原则的角度肯定了提前处罚本身的合理性。
3.金尚均的见解
金尚均更为全面地批判了累积犯概念。(49)参见金尚均:《環境刑法における蓄積犯罪:水域汚染を中心に》,《龍谷法学》2001年第34卷第3号,第319页。他认为,累(蓄)积犯概念扩大了结果概念,失去了其所具有的界限意义,降低了构成要件的自由保障功能,使得国家对市民生活过度干预。易言之,“如果不能认定某一事态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就不能对其处以刑罚”,“危险判断也必须实质化”,“在没有实质危险的情况下处以刑罚,可能会使得给人贴上罪犯标签成为国家控制的手段”。他批判道,“根据洛塔尔·库伦的累积性思维,对环境造成负担的‘轻微’行为也会被认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这样一来,扩大了环境刑法中的结果概念,使其失去了原有的限缩功能。洛塔尔·库伦的这种见解与抽象危险犯的一般理解没有太大差别,这降低了构成要件的自由保障功能,等于允许国家对普通国民生活的过度介入”。金尚均认为,“与人的死亡或窃取他人财物等客观明确的结果不同,在保护超个人或集体法益的刑法规范中,构成要件的结果有抽象化的可能,在保护社会法益时,不以危险发生为要件的抽象危险犯之构成要件,实质上与行为犯没有任何区别”。他接着论述,“行为人多次的、独立的行为本身只是产生轻微的污染(环境负荷),通过同类行为的积累才产生结果的情况下,由个别行为产生的事件和现象本身(导致轻微污染),难以在刑法上被认定为结果”(50)同上注,第17页。。
对此,长井圆表示,“但从水质污浊罪的成立要件来看,特定水域的水质污浊化是构成结果犯(既遂犯)的‘法定结果’(水质超标排放),这并未降低‘构成要件的自由保障功能’”。他反驳道,“只要水质标准、排放总量基准在经验法则规定的合理范围内,便不构成‘国家对市民生活的过度干预’。把污染水体(危害生态)作为违法行为,是为了防止‘熊本水俣病事件’(51)即1953—1956年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的公害事件。后查明为日本窒素公司将含有甲基汞的工业废水排放到水俣湾和不知火海中,致数百人汞中毒。——译者注危害健康的悲剧发生,‘保护国民生活所必要的国家干预’”(52)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67页。。
4.谢煜伟的见解
谢煜伟也认为,累积犯正是社会风险控制的一个环节,是风险概念逐渐融入刑法理论的象征。谢煜伟批判道,累积犯以消除人们对不可预测风险的“不安、不信任”为名,简单地将国家过度的预防性介入行为正当化。(53)参见谢煜伟:《抽象的危険犯論の新展開》,弘文堂2012年版,第138—139页。易言之,“必须从抽象的危险犯解释论中全面排斥累积犯概念,因为这不仅违反了刑法的基本原理,而且是过度的社会风险管理……独立的个人所做的个别行为,即使其本身很轻微(例如对环境介质的负荷),也会因同种行为的累积产生危险化结果,而被视为构成要件上的结果”(54)同上注,第138—139页。。谢煜伟还批判道,“我们几乎不知道后代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兴趣和愿望,人的价值观、思考方式、生活方式,即使在同一代中也是多种多样的。探寻与几百年、几千年后的世代之间共通的环境伦理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主张照顾后代的见解实际上是当代对后代的‘家长主义’”(55)同上注,第170页。。
针对上述批判,长井圆从预防原则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反驳。首先,长井圆认为,如果没有以熊本水俣病事件、丰岛事件以及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经验性事件”为现实依据,这种批判是“过于概念性的论述”,“应该再次确认的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只不过是‘不确定的风险’,虽然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预测的因果关系,但不够确定。因此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直面‘地球环境的风险’。在目前情况下,‘未雨绸缪’是唯一可行的‘社会风险管理’。这是根据‘预防原则’得出的逻辑结论”(56)长井圆:《未来世代の環境刑法2:原理編》,信山社2019年版,第67页。。其次,对于“家长主义”的批判,长井圆认为,“这种批判也是异想天开的,违背了环境法的基本理论共识……在当事人自我实现能力欠缺或不充分的情况下,以当事人的自由意思为基准,帮助其实现自己的意思决定(自助)。‘家长主义’是一种善意的思想,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互惠利他行为’。不能把‘正确的家长主义’和‘不必要的干涉’混为一谈”(57)同上注,第68页。。长井圆还认为,谢煜伟的“抽象危险犯论”本身“误解了‘风险社会论’的主旨,误以为‘抽象危险犯’是空洞的处罚扩张论”。易言之,越是追溯到“侵害重大法益”之前的“法益危险”(具体的危险结果)以及“遥远的法益危险”(抽象的危险结果),危险就越稀薄,处罚范围也不可避免地前置化、扩张化。“相较于‘覆水难收’,累积犯更能有效地保护环境,避免修复所需要的巨大费用负担,避免分担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害结果。相应地,累积犯中分配给每个人的处罚分量(法定刑)也会减轻。”“鉴于能够同时避免重大侵害和重罚化,累积犯对社会和行为人来说都是合理的”,不能忽略这一理论可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价值。(58)同上注,第68页。
5.石亚淙的见解
石亚淙(59)参见石亚淙:《環境犯罪の処罰範囲に関する試論——日中の刑事法制の比較から―》,早稻田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基于以下7点对累积犯概念展开了彻底的批判:(60)同上注。(1)刑法和行政法的规制对象的混淆。“使用累积犯概念会混淆刑法和行政法的限制对象。刑法的规制对象是对国民的具体利益造成具体侵害的行为。因此,即使通过累积作用预见将来可能造成侵害,只要该行为本身不具备具体危险性,就不能处罚。通过累积作用可能造成侵害的行为,正是行政规制的对象。行政部门应该建立预防系统,以预防将来可能造成重大侵害的个别行为,并通过行政处分来限制这些个别行为,这正是行政机关的责任。在刑法中增加对这种行为的限制,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责任的转换。因此,当对人体健康的危险停留在抽象阶段时,应该通过行政措施来阻止危险的具体化,只有发生了具体的危险,刑法才有介入的可能。”(2)欠缺与法益侵害的因果关系。“刑法只能在具体的个别行为与法益侵害或其危险具有因果关系时介入,不能因将来的类似行为而肯定其与法益侵害或其危险的因果关系。易言之,不应该将将来的不确定的行为也加入其中来判断现在行为的可罚性,应该只追究具体行为的可罚性,不能以他人的行为为根据来认定其刑事责任。因此,累积犯只是提供了研究现行规定的工具,只能说明立法背景,不能提出具体行为可罚性的具体标准,也不具有立法批判功能。概言之,处罚累积犯是让实施某种行为的人承担类似行为的全部结果,这有违反责任主义的嫌疑。”(3)行为和刑罚的比例。“刑罚的分量应该与造成的损害成比例,所以在行为本身轻微,积累后才会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对这种轻微行为的刑罚,对应的是积累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二者不能成比例。”(4)危险的稀薄性。“围绕累积犯的性质,在是否属于危险犯的问题上存在对立,因此很难确定认定标准。既然其性质模糊,就不可能明确其构成要件。另外,即使将累积犯解释为危险犯,由于累积犯只具有比抽象危险犯更稀薄的危险性,在认定累积犯时,也有可能超出抽象危险犯的范围,甚至可能成为单纯的行为犯。”(5)对行为者的处罚过于提前。“对累积犯的处罚依据在于,行为者的行为与他人的‘可能’类似行为相结合,会引起将来‘可能’的法益侵害。也就是说,不仅他人的类似行为是‘可能’实行,而且法益侵害结果也仅是‘可能’的。只能说仅凭‘可能’的假设性状态就处罚行为者尚且太早。”(6)新的法益侵害的可能。(61)关于这一点,至少在德国的讨论并不主张累积犯理论坚持传统法益论的观点。Vgl. Lothar Kuhlen, Der Handlungserfolg der strafbaren Gewässerverunreinigung, GA1986, S. 389 ff.“提倡累积犯的动机在于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法益论。”但是,“除了传统法益以外,法律还有可能认可新的法益。即使某个行为对人的生命、身体没有抽象的危险,若侵犯了别的新的法益,则其处罚可能可以正当化。如果没有侵犯其他新的法益,根本就不存在处罚的必要性”。(7)防患于未然原则及预防原则与刑法不符。“累积犯说主张的环境污染和侵犯人的传统法益的关联性,只是防患于未然意义上的。但笔者认为,防患于未然原则不能适用于刑法。在环境领域采用防患于未然或预防原则是没有争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环境刑法上也必须采用该原则。防患于未然或预防原则,是在风险被承认,但危险的存在不能被证明的情况下适用的原则。在不能证明危险存在的情况下适用刑罚是刑法的过度介入。在适用刑罚时应该考虑的问题是,某行为是否侵害了法益或引发了危险,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加以规制。虽说是防患于未然,但并不意味着在危险不确定的阶段就可以适用刑罚。刑法只能介入能够确证行为和结果的因果关系以及危险存在的领域。”石亚淙的彻底否定说受到日本其他否定说的深刻影响,基本上是站在环境刑法消极说的立场上,形成以保护个人法益为中心的法益论、行政法和刑法作用的严格区别论、对处罚早期化的批判论的定位。
四、今后的研究课题:刑法中预防原则的适用范围
综合上述比较研究,日本的肯定说(62)参见神例康博:《廃棄物処理法違反の罪をめぐる解釈論的諸問題:不法投棄罪を中心に》,《臨床法務研究》2014年第13号,第126页。该文提道:“累积犯理论的意义在于阐明了‘累积’方法也是侵害环境介质的方法之一。易言之,在考虑对环境介质的侵害行为时,不仅要考虑一次性的行为、一时性的破坏,还要考虑行为的‘累积’也可能引起对环境的侵害。行为的累积作用,是确定作用于环境的个人行为的允许范围时,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不同于洛塔尔·库伦的见解,(63)Vgl. Lothar Kuhlen, Der Handlungserfolg der strafbaren Gewässerverunreinigung, GA 1986, S. 389 ff.多数将累积犯认定为抽象危险犯的一种。但正如弗兰克·萨利格所言,(64)Vgl. Frank Saliger, Umweltstrafrecht 2. Aufl.,München 2020, Rn. 244.洛塔尔·库伦所关注的是被通说和判例认定为侵害犯(结果犯)的《德国刑法典》第324条水域污染罪中“全体结果归属”的问题。(65)Vgl. Thomas Fischer, StGB 67. Aufl., München 2020, § 324 Rn. 2o BGH NStZ 1987, 323.因此,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累积犯的问题应该是关于环境犯罪结果的评价,特别是关于其轻微性的判断。例如,在对非法丢弃罪的构成要件“随意丢弃废弃物”(《废弃物处理法》第16条、第25条第1项第14号)进行轻微性判断时,应考虑行为的累积性。另外,在与预防原则的关系上,本文基本认同长井圆“一定领域中,环境刑法中不能否定该原则适用”的见解。笔者认为,此时累积犯的概念在解释论和立法论中都将会是有益的工具。然而,对上文中列举的具体事例的解释,特别是在立法论中如何展开,都将成为今后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