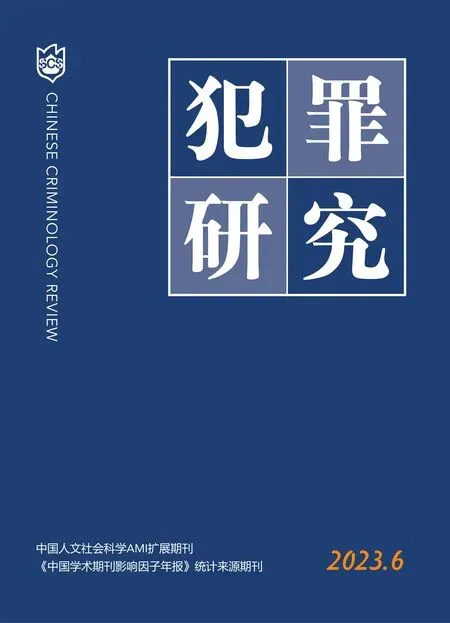“轻罪”理论研究中若干观点的商榷
2023-03-22汪明亮
汪明亮
近些年来,理论界关于“轻罪”的研究如火如荼。毋庸置疑,相关研究成果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改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之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理论界对轻罪的研究时间不长,部分研究成果所提出的若干观点(包括对策建议和学术论断)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内含的科学性要求还存在差距,尚有改进与完善空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和国家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需求而提出的时代命题,犯罪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有之义。(1)参见黄石:《推进新时代犯罪治理现代化建设》,载《人民法院报》2022年9月22日,第5版。科学性是犯罪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科学性表现在真实性、全面性和逻辑性三个方面。在学术研究领域,无论是提出轻罪治理对策建议,还是给出相关学术论断,都必须从真实、全面和逻辑等视角满足科学性要求。易言之,学术研究引用的实践资料要真实、考虑的视角要全面、归因推理要符合逻辑。
一、“‘轻罪时代’选择以宽为主刑事政策”的建议
有学者认为,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正从自然犯转向法定犯,犯罪形势日趋缓和。在此判断之上,进而提出“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应该彻底摈弃严打重刑思维,从宽严相济转向以宽为主的刑事政策,刑罚应整体趋轻”之建议。(2)参见卢建平:《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期,第51页。该建议是以“‘轻罪时代’意味着犯罪形势缓和”之判断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该判断难以成立,以该判断为基础的刑事政策选择建议值得商榷。
学界认为我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的依据有二:一是近年来8类严重暴力犯罪的犯罪率逐年下降,其在全部犯罪总量中的占比也在下降;二是刑事案件中判处3年以下刑罚比例达80%以上。(3)参见卢建平:《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期,第51—55页;周光权:《“轻罪时代”呼唤社会治理方式转型》,载《上海法治报》2023年5月26日,第B7版。以上两方面理由并不足以证明当前的“‘轻罪时代’意味着犯罪形势缓和”之判断。主要理由是:其一,虽然近年来8类严重暴力犯罪的犯罪率逐年下降,其在全部犯罪总量中的占比也在下降,但由于8类严重暴力犯罪绝对数量较大,即便犯罪率与占比率呈下降趋势,其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给民众带来的恐惧感亦非常明显。以故意杀人案件为例,近20年来已经下降近40%,但近些年每年的绝对数量还有7000起左右,(4)以公安机关故意杀人立案数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6522起、2020年7157起、2019年7379起、2018年7525起、2017年7990起、2016年8634起、2015年9200起、2014年10083起、2013年10640起。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3年7月31日访问。一些故意杀人案件动机极其卑鄙、手段极其残忍,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社会恐慌。其二,判处3年以下刑罚的罪未必都是真正的“轻罪”,仅以法定刑作为区分重罪与轻罪的标准过于简单、不尽科学。(5)应该以实质危害性,而不能以法定刑作为“轻罪”的认定标准。理由很简单,由于受立法者的观念、立法技术等因素影响,法定刑配置并不能与行为的实质危害性相对应,也即立法上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例如,理论界大多认为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轻罪(其法定最高刑是拘役),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数据分析,交通死亡结果与醉驾之间存在正相关,在危险驾驶入罪后,特别是在“零容忍”司法政策指导下,交通死亡人数与伤害人数随即下降(死亡人数降至年均5万人以下、伤害人数降至2万人以下),但近几年来,随着司法认定上的松动,交通死亡人数随即上升(近几年死亡人数都在年均6万3千人左右、伤害人数在2万5千人左右)。(6)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3年7月31日访问。如此说来,危险驾驶罪能算是“轻罪”?又如,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最高法定刑是3年有期徒刑,但自江苏“铁链女”事件发生后,要求提高该罪法定刑的呼声不断。如此说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能算是“轻罪”?其三,若干经济犯罪自然犯趋向显现。一般认为,经济犯罪主要是法定犯。“其危害性更多地体现在违反经济活动规则……与主观道德评价没有必然联系,伦理性色彩相对较弱。”(7)杨书文:《理解经济犯罪的三个关键词》,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5页。但从近些年发生的若干类型经济犯罪来看,伦理色彩却越来越明显,其不仅违反了经济活动规则,而且还严重侵犯了他人的财产、健康甚至生命权利。例如,一些犯罪人为了谋取暴利,不顾他人生命、健康权利,大肆生产、销售假药、有毒有害食品;(8)依据裁判文书网的数据,2015年至2021年,每一年的生产、销售假药、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基层法院审理案件均在2000件以上。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029CR4M5A62CH/index.html,2023年2月24日访问。一些犯罪人没有最基本的怜悯情感,实施集资诈骗犯罪、证券犯罪,骗取退休老人养老金、(9)参见《检察机关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https://www.spp.gov.cn/xwfbh/dxal/202206/t20220617_560065.shtml,2023年2月17日访问。收割中小散户(10)参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https://www.spp.gov.cn/zdgz/202209/t20220909_577066.shtml,2023年2月24日访问。;一些犯罪人不顾及基本的友情与亲情,实施组织传销活动犯罪,骗完熟人骗亲人(11)参见《骗同学骗亲友 疯狂传销致人跳河跳楼》,http://yz.jsjc.gov.cn/tslm/dxal/201801/t20180116_251413.shtml,2023年6月10日访问。等。其四,法院判决的刑事案件呈现上升趋势,犯罪量居高不下。(12)以人民法院审理刑事一审案件收案数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1277197件、2020年110761件、2019年1293911件、2018年1203055件、2017年1294377件、2016年1101191件、2015年1126748件、2014年1040457件、2013年971567件。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3年7月27日访问。
既然“‘轻罪时代’意味着犯罪形势缓和”之判断与较严峻的犯罪现实不相符,那么建立在该判断之上的刑事政策选择建议亦有商讨空间。因此,在当前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必须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具体来说,一方面,采用科学的方法筛选出真正的“轻罪”(而非仅按法定刑判断),该宽则宽;(13)真正“轻罪”的筛选,需要采用比较的、实证的方法,而非简单的法定刑。限于篇幅,笔者将另行撰文论证。另一方面,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严则严,不能以所谓的“轻罪时代”为由放弃对严重犯罪的严惩。此外,即便是对真正的“轻罪”,在依法从宽处理时也应有限度。要充分考虑“轻罪”的生成机理,特别是理性选择犯罪原因论的启示,警惕因处罚过宽而使刑罚失去威慑力,进而使从宽成为间接促使轻罪生成的社会因素。(14)理性选择理论把犯罪人假设为“理性人”。犯罪人能认识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并能对自己行为成本和后果利益进行比较,只要有可能,都倾向于以最小的行为成本去换取最大的后果利益。简言之,犯罪是一种利益与损害之衡量。理性选择理论是刑罚威慑论的重要理论依据。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轻罪”大多可以通过理性选择理论予以归因。因此,在考虑对轻罪从宽的时候,应有底线。刑罚之苦必须超过犯罪之利,一个不足的刑罚比严厉的刑罚更坏。(15)参见[英]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孙力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0页。
二、“应该废除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建议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与人大代表建议“应该废除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遏制效果不佳;二是附带了不利后果。详言之,一是该罪没有起到有效遏制此类行为的效果。该观点认为,将醉驾行为入罪并没有起到有效遏制此类行为的效果,该类案件数量仍在攀升,已高居刑事案件数量首位。二是行为人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将面临一系列附带的不利后果,如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影响子女报考公务员等。(16)参见《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我为何建议取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6941365,2023年7月27日访问。把以上两个理由作为应该废除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理由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荒谬的。依此逻辑,盗窃罪也应该废除。原因很简单,一是该罪没有起到有效遏制此类行为的效果。从数千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将盗窃行为纳入犯罪范围并没有起到有效遏制此类行为的效果,盗窃罪一直大量存在着,曾经长期高居刑事案件数量首位。二是,因盗窃被认定构成犯罪后,行为人除了需承担刑事责任外,也将面临一系列附带的不利后果,如会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公职人员将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甚至影响其子女报考公务员、警校、军校。实际上,依此逻辑,所有的罪名都应该被废除。遏制效果不佳与附带了不利后果两个因素难以成为废除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理由。一旦建立在此理由上的建议影响刑事立法,则可能不利于犯罪治理效果的实现。更何况,该观点认为“该罪没有起到有效遏制此类行为的效果”的理由本身也是不成立的。该理由只是简单地看每年的涉罪数据,没有分析涉罪之外的数据,特别是减少伤亡事故方面的数据,论据过于片面。大量数据表明,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后,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累计减少数万起醉驾带来的伤亡事故,避免了数万家庭因交通事故破碎、返贫,充分体现了“醉驾入刑”坚持生命至上的立法初衷。(17)具体而言,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驾驶人数分别达到4.06亿辆、4.92亿人,同比2012年分别增加1.6亿辆、2.27亿人的背景下,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指数持续向好,重大以上交通事故从2012年的25起下降到2021年的4起,已连续33个月未发生特别重大交通事故,1次死亡3人以上较大事故降幅达到59.3%;每排查100辆车发现的醉驾比例比“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参见高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指数持续向好》,载《人民公安报》2022年7月26日,第3版。评价醉驾入刑的效果,不能仅看涉罪数据,更要考察其对生命健康的保护状况。
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后,为什么没能彻底消灭此类行为,反而每年有近30万人涉罪?这需要从犯罪学角度进行分析。“醉酒驾驶行为纳入犯罪范围并没有起到有效遏制此类行为的效果”的观点是违反犯罪学常识的。从犯罪学角度考察,危险驾驶犯罪是行为人因素、自然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如酒文化、汽车产业、法律处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8)参见汪明亮:《严惩“酒驾”肇事犯罪观念之反思》,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第5—8页。我们消灭不了这些因素,自然也就消灭不了该犯罪。在此意义上说,一旦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其必然长期存在,这正是迪尔凯姆所说的“犯罪正常论”。而且,只要导致危险驾驶犯罪的各种因素没有太多变化,该犯罪每年发生的总量也不会有太多变化,这正是菲利所说的“犯罪饱和论”。可以预测的是,随着驾驶人员与汽车数量的持续增长,如果不改变危险驾驶罪的入罪标准,该类犯罪总量将会持稳定上升趋势。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刑法消灭不了醉驾行为,为何还要将该行为入罪?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通过改变社会因素(加大法律处罚力度),尽可能把该行为控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公共安全,实现生命至上目标。从立法论角度考察,醉驾行为有无入罪必要,关键要考察以下四方面因素:即有无可罚的社会危害性、民众的态度、域外经验以及有无其他有效控制手段。醉驾型危险驾驶是导致重大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人为风险的重要来源,具有可罚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民众支持酒驾入罪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域外经验也是支持入罪的;其他手段难以发挥效果,现行的行政处罚模式难以有效遏制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19)参见叶良芳:《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证成和规范构造》,载《法学》2011年第2期,第15页。
虽然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不宜废除,但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入罪门槛低,导致打击面过宽;二是附随不利后果较重。对此,我们的建议是改良而非革命。具体改良路径学界已有较成熟观点,值得相关职能部门参考。例如,通过立法提高该罪的入罪门槛,诸如增设“不能安全驾驶”要件;通过司法裁判标准的科学化设计,实现司法出罪功能,或者发挥现有刑事诉讼制度框架内的相对不起诉制度功能,并激活我国《刑法》第37条定罪免刑条款;建立前科消灭或者前科封存制度等。(20)参见周光权:《论刑事一体化视角的危险驾驶罪》,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期;李翔:《论微罪体系的构建——以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研究为切入点》,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期;梁根林:《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交互审视下的危险驾驶罪》,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4期;等等。
三、“刑罚轻缓化是世界刑法发展趋势”之论断
学界以“刑罚轻缓化是世界刑法发展趋势”之论断来支持“当下轻罪时代刑罚应该宽缓”之观点,是一种常规视角,也是重要的依据。该视角或依据是不完全符合世界各国刑法发展实践的。“刑罚轻缓化是世界刑法发展趋势”论断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真理。从应然看,该论断是成立的;但从实然看,则未必。对多数轻罪而言,该论断是成立的;但对多数重罪及少数轻罪来说,则未必。实际上,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呈现出的是“刑罚严厉化趋势”。根据美国纽约大学大卫·加兰德(David Garland)教授对美英等国犯罪政策历史演变规律的研究,发现其犯罪政策历经了刑罚严厉化—刑罚轻缓化(刑罚人道主义)—刑罚严厉化的演变。详言之,在18世纪中后期之前的传统社会,犯罪政策凸显了刑罚严厉化倾向,强调严刑峻法;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后期的100多年时间,受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权观念影响及当时缓和的犯罪形势,在犯罪政策领域,以美英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场所谓的刑罚人道革命(humanity revolution),即强调给予犯罪人人道的待遇,而不是严厉的惩罚。(21)See Jonathan Simon, Sanctioning Government: Explaining America′s Severity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Vol.56, No.1, 2001, p.217.然而,到了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曾经引领刑罚人道革命的美英等国对犯罪问题所采用的控制政策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犯罪控制和刑事司法领域内朝向理性化与文明的刑罚现代化进程长期趋势已彻底改变。(22)See 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3.这些转变令专家感到意外,违反了历史预期。这些变化意味着刑罚人道革命的终结,刑罚严厉革命(severity revolution)的到来(23)See Jonathan Simon, Sanctioning Government: Explaining America's Severity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Vol.56, 2001, p.217-254.;意味着人道主义理念的退让,刑罚严厉化趋势显现。
以美国为例,刑罚严厉革命主要体现在:在刑事立法方面,制定了诸多特别法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既有法治规则,利用法律对抗法律(law against law)策略,(24)所谓法律对抗法律,就是通过违反法治的法律,以减少或规避在预防犯罪时可能遇到的程序上的障碍,其目的在于违反法治程序以拯救社会秩序。See B. Bebenton,T. Seddon,From Dangerousness to Precaution: Managing Sexual and Violent Offenders in an Insecure and Uncertain Age,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49, Issue 3, 2009, p.343-362.严厉打击特殊类型的刑事犯罪,如《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梅根法》(Megan′s Law)等。在刑事司法方面,限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制定强制判决、强制最低刑期判决、推定判决、量刑指南、“三振出局”判决等法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受到限缩和制定预防性羁押法。在行刑方面,恢复执行死刑,且数量呈稳中有升之态势,(25)据统计,1977年执行死刑1人,1987年为25人,1997年为74人,2007年为42人。See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Executions by Year,https://deathpenaltyinfo.org/executions-year.有些州的死刑执行还采取了示众与电视直播方式;(26)参见高一飞、张金霞:《围观杀人:美国死刑执行的示众与电视直播》,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36页。开始限制服刑罪犯的权利,取消假释委员会酌情假释权,结束监狱的奢侈设施等。除美国之外,研究表明,其他一些国家与地区20世纪中后期也同样出现了刑罚严厉化倾向。例如,根据托马斯·马蒂森(Thomas Mathiesenn)、尼尔·克里斯蒂(Nils Christie)与华康德(Loic Wacquant)等学者的研究,欧洲国家越来越倾向模仿美国的刑罚严厉化犯罪控制模式。(27)See 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reface.又如,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反战后刑事立法中所坚持的“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倾向,在刑事立法上开始走向犯罪化、重刑化与早期化,(28)参见黎宏:《日本近年来的刑事实体立法动向及其评价》,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6期,第103页;张明楷:《日本刑法的发展及其启示》,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1期,第9页。如性犯罪的立法修改;(29)日本性犯罪的立法修改,不仅涉及刑法、刑事诉讼法,而且还新增了特别立法。在刑法方面,大幅修改了强制性交罪和强制猥亵罪的条款,并将罪名修改为不同意性交罪和不同意猥亵罪。其一,列举了8种在外观上为不同意的行为,并明确规定性犯罪的实质要件是使被害人陷入“难以形成、表达或实现不同意的状态”,或利用被害人的此状态。其二,修改了性同意年龄,从13岁提高到16岁。其三,扩大了严重性犯罪的行为范围。其四,确认配偶或伴侣之间也可实施不同意性交罪和不同意猥亵罪。其五,将针对未满16岁未成年人以猥亵为目的要求或实际会面行为入罪。在刑事诉讼法案方面,将公诉时效在原来基础上延长5年。此外,还新制定了《偷拍性姿态等处罚法》,处罚拍摄性姿态,提供、存储以及传播性行为图像的行为。参见《讲座综述:日本刑法中性犯罪的修正》,https://law.fudan.edu.cn/09/7a/c27189a592250/page.htm,2023年11月3日访问。在刑事司法方面,严罚案例、死刑执行案例也日渐增加,例如,日本一男子从厕所偷窃价值2元的厕纸,被判刑7个月;(30)参见《日本一男子从厕所偷窃价值2元厕纸 被判刑7个月》,载搜狐网站2018年7月12日,http://www.sohu.com/a/149130333_114731。又如,日本奥姆真理教13名死刑犯已被全部执行死刑。(31)参见《日本奥姆真理教13名死刑犯已被全部执行死刑》,载环球网站2018年7月26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aLWs。
大卫·加兰德的研究表明,“刑罚轻缓化是世界刑法发展趋势”之论断是相对的,该趋势是世界刑法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其过程是曲折的,并不会一帆风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刑罚轻缓化还是严厉化,一定要考虑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条件,而不能仅凭理论界的“一厢情愿”。(32)参见汪明亮:《守底限的刑罚模式》,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页。20世纪中后期的美英等国犯罪政策转向对当今中国的犯罪政策立场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33)同上书,第67页。虽然当下我国处在“轻罪时代”,但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当前犯罪形势依然严峻,尚不具备全面刑罚轻缓化的现实条件。在此背景下对刑罚轻缓化的过度强调不仅难以降低犯罪率、缓解公众的犯罪恐惧感、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还可能带来诸如犯罪被害人的权利被忽视、引发被害人及其家人上访甚至复仇、不利于刑罚威慑效果的实现、导致司法权威日渐下降以及引发更严重犯罪的发生等负面后果。(34)参见汪明亮:《守底限的刑罚模式》,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13—118页。
因此,“刑罚轻缓化是世界刑法发展趋势”论断不能成为当下刑罚轻缓化的理由,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对多数轻罪可以考虑轻缓,但对重罪及部分轻罪还需考虑刑罚严厉化的现实意义。
四、“犯罪化有违刑法谦抑性”之论断
一些学者以“犯罪化有违刑法谦抑性”为由批判犯罪化,特别是轻罪立法。(35)参见韩轶:《刑法更新应坚守谦抑性本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为视角》,载《法治研究》2020年第5期;石聚航:《刑法谦抑性是如何被搁浅的?——基于定罪实践的反思性观察》,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该理由是难以成立的。首先,刑法谦抑性与犯罪化并不是对立的。谦抑性强调的是最后手段性,即如果通过其他手段能够抑制某种危害社会行为时,就不必动用刑罚手段,但如果该种行为已达到严重程度而其他手段难以发挥抑制作用时,刑罚就该及时介入。刑法谦抑性与犯罪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36)参见汪明亮:《刑事立法刑罚模式化——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64页。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例,“修改的多数内容是为了与其他部门法相衔接,属于前置法修改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37)周光权:《刑事立法进展与司法展望——〈刑法修正案(十一)〉总置评》,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9页。。其次,刑法谦抑性只是一个抽象的学术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具有不确定性,以其作为刑事立法原则不仅不科学,而且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在此意义上讲,刑法谦抑性只能发挥“对立法者审慎立法的温情提示”(38)陈璐:《论刑法谦抑主义的消减》,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9期,第123页。的作用,是否需要设立轻罪,依据的“绝非单向度的谦抑主义”(39)孙国祥:《反思刑法谦抑主义》,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1期,第85页。。
实际上,当下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适当保持犯罪化趋势、设立轻罪,不仅不违背刑法谦抑性,而且实为必要。首先,这是刑法使命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类在向前迈进的同时,也面临着人类进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危害,进入所谓的“风险社会”(40)风险社会理论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为代表。风险社会理论家认为,风险概念是当今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 风险社会是对当下社会形态的最佳表征。他们认为,“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秩序与方式,提供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物质便利,也创造出众多新生危险源,导致技术风险的日益扩散。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各种人为风险,从电子病毒、核辐射到交通事故,从转基因食品、环境污染到犯罪率攀升等。风险社会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状态。”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02 页。,中国亦不例外。(41)参见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 年第1 期,第48页。在“风险社会”,不仅新的实害行为增多,而且可能带来严重风险的危险行为亦频发。刑法作为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把严重危害社会的实害行为纳入其规制范围实属必需,把可能带来严重风险的危险行为设为轻罪能防重患于未然。其次,我国现行刑法采取的是一种定性加定量的犯罪立法模式,通过《刑法》第13条设置了较高的犯罪门槛,将大量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之外,这为犯罪化趋势提供了可能,特别是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对大量本来由劳动教养制裁的违法行为予以刑法规制势在必行。最后,犯罪化还是消解道德恐慌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各方面的道德恐慌。(42)参见汪明亮:《过剩犯罪化的道德恐慌视角分析》,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9期,第76页。道德恐慌一旦形成,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反应,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加强社会控制手段,包括“制定更多的法律、判处更长的刑罚等”(43)E. Goode, N. Ben-Yehuda,Moral Panic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cience, Blackwell,1994,p.30.。由此,犯罪化不可避免。当然,必须严格限制犯罪化,特别是设立轻罪的条件,即确立严格的犯罪化原则,以避免过剩犯罪化。这些原则包括:基于当前及今后惩罚犯罪的实际需要;基于当前刑事立法的罪刑规范不能满足惩罚犯罪的实际需要;符合法秩序统一原则;顺应刑事立法的国际潮流等。(44)参见肖中华:《轻罪的范围界定、设置原则与认定规则》,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89—90页。
值得说明的是,与“犯罪化有违刑法谦抑性”论断相似的是,有学者提出了“轻罪立法的指导思想是积极刑法观”之论断,(45)参见何荣功:《轻罪立法的实践悖论与法理反思》,载《中外法学》2023年第4期,第959页。并对该刑法观进行反思。该判断也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必须是刑事立法所依据的,反映立法的根本方向、目标,决定立法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把积极刑法观界定为指导思想是不合适的。积极刑法观只是一些学者自立、自认的一种观念,远远达不到指导思想的程度与境界。另一方面,指导思想只能先于刑事立法而存在,是决定立法根本方向的理论基础。而积极刑法观则是学界在刑事立法之后,对立法背后的价值趋向的一种概括。也就是说,不是积极刑法观指导刑事立法,而是通过刑事立法推演出积极刑法观。实际上,近些年轻罪立法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已有官方的解读。例如,《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指导思想包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坚持创新刑事立法理念。(46)参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说明》,载中国人大网站,http://www.npc.gov.cn/zgrdw/npc/lfzt/rlys/2014-11/03/content_1885123.htm,2023年11月2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