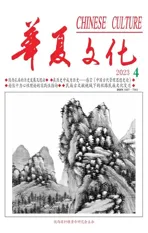在历史中成为历史
——感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
2023-03-22□韩巍
□韩 巍
我与刘文瑞老师的交往是先见其文,再见其人,一见如故。会上碰面,私下热聊,其乐融融。多年前回西安参加学术交流,还专门去他家讨过一碗面吃。刘老师专长史学,涉足管理既是个人喜好也是他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的职责之所在。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很多中国历史的典故、轶事,也时常听他谈及对当代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最重要的是彼此对管理学界的诸多困扰和“解决之道”持有十分相近的看法。
有机会为刘老师及合作者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上下卷)(以下简称《思想史论》,也以刘文瑞代替“刘文瑞等”)写上几句感悟,是我莫大的荣幸。刘老师了解我的性格,他乐于看到的文字一定得是由衷之言。半年前收到刘老师的大作,并没有很快着手阅读,那时及以后一段时间都忙于与现代诠释学进行“对话”,试图展示诠释学对管理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当然,刚拿到《思想史论》,第一时间就曾随手翻阅。刘老师用八十多万字“对古代管理思想进行理性思考,梳理其类型,发掘其奥秘,认知其逻辑,判断其得失”,意图“从学术角度对‘中国特色’给出深层解释,写出有分量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原本就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刘文瑞 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页)读者也需要用足够的时间、精力去揣摩和领悟。然而,正是导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概论”中的三个关键词:“把握”“框架”“机制”,让我对本书瞬间产生了一种“疏离感”。伽达默尔诠释学里有一个“完满性前把握”的说法,我是不太信的,“把握……思想”也不可取;哪怕是刘老师谦称的“大体框架”也让我心生抵触;而“作用机制”四个字让我对《思想史论》近乎失去兴趣。面对几千年厚重历史积淀下来吾国吾民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对日常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现于洒扫应对的点点滴滴,让我很难想象引入作用机制这种(后)实证主义概念的必要性。以自己对刘老师的了解和猜测,他头脑中的管理思想图景似乎不该是这般模样。
相较于历史(思想史),我对(历史)哲学的兴趣更浓。作为一个实证主义的敌视者,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早就进入了自己的视野,其间我还读过奥克肖特的《经验与模式》,加登纳的《历史解释的性质》。三年疫情期间,我还阅读了安克斯米特的《历史表现》,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历史诗学》和《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不难想象,这些学者的思想都在不同维度、程度上强化了个人对人类世界包括历史(观念史、思想史)的另类看法。简言之,就是对人类生活之“规律”“因果”学说的排斥乃至对“真实”“真相”的疑虑和保留。
坊间总有人讲“走进历史”“走出历史”。在现代诠释学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那里,基于诠释循环的先在性,所谓走进、走出都像是无稽之谈。历史不是被认知的客体,我们也无法成为认知历史的主体。只有效果历史中“假扮”认知主体的我们看见历史,也只能是“历史地看见”(通过前见“看见”)且不断生成新的历史(成见、偏见)。历史是一条河,浩浩荡荡,从不停歇,我们身在其中,“岸边”不过是人类的虚构,以便于我们从事独有的思想实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就是刘老师思想实验的一份报告。
一部《思想史论》可以带给读者什么?诠释学有“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三种取向。 我做不到也不打算遵循中国传统“注经”释义的套路:“即便是注释,也要守持‘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规范”(《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214页)。我是一个倾向于“读者中心论”的读者,《思想史论》文本已成,就不再属于刘文瑞老师。作为读者和诠释者的我“遭遇”《思想史论》,一如多种古代文本“遭遇”作为读者和诠释者的刘老师。这是一种诠释循环的处境。刘老师面对的那些古代文本是伽达默尔所谓“历史的实在和历史诠释的实在”(洪汉鼎:《实践哲学 修辞学 想象力: 当代哲学诠释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3页),这就是《思想史论》文本的“命运”和意义。效果历史效应发生在刘老师和我的身上,显现于彼此的“前见”“视域”,我们以相近或相异的问题意识与文本进行一场对话,那里有一种先在的“问答结构”。从而,“思想史”只能是人为选择、建构的产物,刘老师一定是依循他的问题意识选择部分历史的实在和历史诠释的实在为他所用,为当下所用形成文本。答案不在别处,就在《思想史论》。我向《思想史论》提出问题,那里有我想要的答案,而我的问题和答案应该就在这篇感言之中。可以说,《思想史论》是一个强化“主体间性”“皆为诠释”意识的范本,读者能了解什么,领悟什么,不仅仰赖刘老师的文本,更取决于读者自己的精神世界!
一、对《思想史论》的总体印象
我不可能“重演”“重现”刘老师的思想轨迹,更不可能比他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理解得更好。依从伽达默尔的说法,“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这就够了”(《实践哲学 修辞学 想象力: 当代哲学诠释学研究》,第80页)。不可避免地,我对《思想史论》的理解和诠释,注定更符合自己的前见、视域和问题意识。
如果单看《思想史论》导言“概论”归纳、提炼的三个方面,即其一,刘老师援引葛兆光先生的看法,稍加变通,增加国家治理,勾勒了中国古代一般思想的“地图”,涉及“汉字和思维”“伦理和社会”“官民之分和君臣之道”“信仰的合一和分立”“阴阳和五行”“中华和四夷”;其二,建构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大体框架,涉及“人性假设”“组织原理”“角色定位”“动力与激励”“决策机制”“君臣之道”;其三,探索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作用机制,涉及“不同思想的殊途同归”“互相砥砺的左右互博”“行为路径上的内圣外王”“作用方式上的教化领先”“实施方法上的有经有权”。应该说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但这并非我的兴趣所在,刘老师所呈现的这幅理性化、体系化的概念“画卷”与我的期待不同。我更好奇在波澜起伏的历史长河中看见——不只是(管理)思想被言说成什么,而是(管理)思想被践行成何物?落实于何时、何地、何事、何人?要言之,我希望从《思想史论》中不只看到古代思想家的晦涩文本被刘老师如何注释和解读(理解和诠释),更想感受、领悟他意图把读者引向何方?他的处境意识,他的理解和诠释,他的困顿和挣扎,他的“被抛”和“筹划”,最终是那个我熟悉的、亲切的能与之对话的刘老师的身影。于此,我推测他最想表达的内容远不是“把握”“框架”“机制”这类总体性、同一性的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结论”。
暑假期间,我用一段完整的时间认真拜读了《思想史论》。我终究看到了我想看到的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思想史论更多的“可能性”。私下以为,阅读《思想史论》最好不要以导言为“向导”,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直奔章节,无论是“孔子”“老子”“鬼谷子”,还是“六条诏书”“颜氏家训”“吕氏乡约”。每一章的第一段都像是论文的摘要,提纲挈领,不乏真知灼见。像一张思想草图,要点突出,可谓“偷懒”阅读的捷径。我忍不住摘录如下,一口气读完,行云流水,酣畅淋漓:
“心学针对程朱的‘天理’内化,主张‘人心’外化。从陆九渊到王守仁,心学成为同程朱理学抗衡的主要学说。陆九渊主张简易工夫,即个体心智的自我觉醒。从管理角度看,陆九渊的所谓‘本心发明’,实际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反思。心学的治国之策,人心在制度之上,从而对前人‘有治人无治法’的管理思想给出心学新解。陈献章主张天理即自然,强调‘学贵自得’,由自然进而自信、自立、自重、自乐、自为、自主。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强调理气合一、理心合一、理欲合一、知行合一。到王守仁揭示‘致良知’之教,成为古代儒家思想阐释演绎的又一个高峰。王守仁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以其平定南赣‘山贼’、宁王反叛、广西民变三个事功闻名,由龙场悟道到创立致良知之教,反抗官定程朱理学的僵滞教条,启发人之主体善心,以良知良能实现人人自主。王守仁对朱熹的批评,明面是学术分歧,底里是治道分歧。心学将程朱的化良知为天理,转向化天理为良知,把外显的至善归根于人心,给自治提供理论依据。至此,中国古代的组织学习思想最终成型。阳明心学的关键,在于追寻‘作为人,何为正确’的终极之问,回归人的自主性。阳明心学在嘉靖万历以后传播极广,尤以王畿和王艮为代表。他们不但追求人心自主,而且追求人性舒展,突出个体价值,体现人格独立,颇近于自我实现理论。其后的心学支绪致力于突破礼教束缚,则被统治者视为离经叛道。”(《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671页)
作为读者,对于特定文本的认同越多,也不必只顾击掌叫好;反而对于“疑难”“不解”之处,可以更加用力。比如,我对“至此,中国古代的组织学习思想最终成型”,“颇近于自我实现理论”的论断就心存疑问。刘老师是读者间接“领悟”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管理思想的理想向导。读者可以从章节中大量的叙事和解读入手,知道很多趣闻,重温不少典故,虽详略偶尔不如预期,但读来的确兴味盎然;尤其是从那些比较生动、鲜活的人和事上产生共鸣,获得启发。换言之,刘老师原本就栖居在《思想史论》的叙述和阐发之中,不像他导言中的“把握”“框架”“机制”的抽象性,而是在细节上的娓娓道来,在诠释上的小心翼翼的字里行间,尤其是那些点到为止,那些欲言又止,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方。
刘老师对古代思想者的包容在《思想史论》里是贯彻始终的,用语温和、委婉,是对陈寅恪“同情的理解”的最好践行;他对当权者也算宽容,略有选择,毕竟关乎历史进程,遂让他“寄望”更大,苛责难免。比如“魏徵的步步退让,也活灵活现地衬托出唐太宗的以势压人,甚至有点死皮赖脸”(《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487页);他对“个体”“自我”,民间社群有足够的期待,“自治”“家训”“乡约”虽然效果不彰却表述得不厌其烦,比如“《吕氏乡约》的实施状况几乎没有史料记载,其生命力主要表现在文本流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90页)。他对史学界讲了一些话,重要与否,我难以判断;也对管理学界讲了一些话,中肯、平实,绝不咄咄逼人。总体看来,他既不太左,也不太右,在历史与当下之间站得“不偏不倚”。可以说,这是一个文本世界里的刘文瑞,远不像他津津乐道的古代先贤那么恣意妄为(史官“修理”皇帝,《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488页),少有声色俱厉,剑拔弩张。作为一个历史和管理的“跨界”学者,他的表达方式或许可以被看作一种关于“如何表达”的隐喻。
二、个人的看见和领悟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早已浸透于我们的血脉之中,作为信念、准则、智慧甚或“技术”,广泛、深入地实践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语言中,无论是诸子思想、庙堂高论,还是“旁门左道”、民间俗语,每每应时应景,可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却常常相互抵牾,“左右互搏”;在行动中,彼此的所想、所言、所行总在一致与不一致间摇摆,也总与各种“版本”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纵横家们(经由刘老师的文本大概都能找到那些“渊源”)的“正”“奇”,“诡”“诈”纠缠不清。我们在“国家治理学说”中看到“做人的道理”,也能在“家训”中看到“治国理政之要义(人才)”。庙堂也好,民间也罢,看起来是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秩序井然,实际上更可能是上下同构,相互参照,彼此复制。几千年过去了,依然纠结于“天道”“民意”“君子所为”“小人行径”等等。
我究竟从《思想史论》领悟到什么?没有框架,只有议题。
其一,治学
我读过的史学著作有限,对史学的治学了解不多。管理学研究“实证主义化”以后,常有人以规范学术自居,轻视思想之辨。“编撰”文献综述,也多是为我所用。
刘老师在后记中特别提醒:“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研究应该有三重追求:其一、必须具有坚实的基础,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从史料学意义上做到知古以求真;其二,必须具有思辨的内核,能够给人以启发,从观念史意义上做到鉴古以知今;其三,必须坚守学术的本位,从学术史意义上做到正学以闻道”(《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735页)。而且对于史料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重视传世文献……;第二,重视正史记载……”(《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736页)。可以说,《思想史论》就是最好的践行,凡争议、分歧、存疑之处,少有孤证立论,旁征博引,恪尽周全。
不妨以一条注释为例:“‘横渠四句’的版本极多,文字稍异,最常见的有二: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另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兴趣考订文字者,可参阅对比朱熹、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南宋《诸儒鸣道》之《横渠语录》,真德秀的《西山读书记》,南宋末吴坚刻本《张子语录》,明版《张子全书》之《语录抄》,晚明冯从吾的《关学编·自序》,清代《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黄百家案语”(《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649页)。没有皓首穷经、博览群书,哪儿来的“真相”可言?于是,凡《思想史论》中的历史“事实”、典故,甚至“八卦”,都让我大长见识,深以为然。
“治学”不可能没有争议,习惯了二元对立的“非黑即白”,争议就容易催生“敌意”。刘老师在《思想史论》中常用“有人”“有些人”“有的学者”(不加引用)引入质疑、批评的某些“史学”观点,作为一份思想记录,也是意味深长。“有人会指出,法家也重民。……法家所说的民萌众庶,无非‘王资’而已。至于有人把法家的重民思想同西周以来的各种重民思想相提并论,存在的问题更为明显。法家彻底否定了西周以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迟早会走到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道路上去,而法家绝不允许这种念头出现。还有的学者把‘重民’与‘重农’混淆,以法家(尤其是商鞅)的耕战政策显其重农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163页);“从此,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有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体系。当代有些人把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思想根源归结到儒家而放过了法家,有点南辕北辙,找错了对象。秦晖把这种批判的错位喻为‘荆轲刺孔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168页)。
刘老师的批评也尽显其宽厚之风:““利出一孔”…… “把‘利出一孔’观点命名为‘管仲陷阱’有所不妥。既然商鞅明白无误地表达过这种思想,为何不把它命名为‘商鞅陷阱’?仅仅看到《管子》有此记载,就把商鞅的思想嫁接到管仲头上,从学术角度来看过于粗疏。提出这一命名的学者,其思考角度和批评精神值得赞赏,但是,不实的东西无法奠定坚固的理论立足点,这需要引起学界注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240页)。
当然,对史学研究他也说过重话,却通常并不指名道姓:“在王充的言论中寻找自然科学知识,相当于把茅盾的《白杨礼赞》和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当作植物学著作;在王充的言论中寻找唯物论和无神论,相当于把高阳的《慈禧全传》和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当作历史学著作。仅仅就知识而言,把《论衡》中所列举的资料,以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医学和药物学、生物学、昆虫学归类而论(而这种笔法相当普遍),用现代知识加以解释,其偏颇显而易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385页)。为陆贽平反“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往往拘泥于一个僵化的公式: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是历史的进步,陆贽反对两税法,所以陆贽的反对就是抗拒历史潮流,而全然不看陆贽在两税法问题上的具体辨析。这种简单化、概念化的所谓研究,难免厚诬古人,误导读者”(《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19页)。
一个例外是通过引文才能确定他的批评对象:“有不少人拿出其中‘知为力’的观点,声称王充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比英国的培根早一千多年,全然不顾王充与培根思想内涵的不同。类似这种偏差,需要引起管理思想史研究的高度警惕。”(《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388页)
其二,中国式思维
诠释学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中文的独特性自然源于中国人生活体验的“共同性”。刘老师有自己敏锐的问题意识,也不乏启发读者的洞见。言及孔子的教学方式,“奠定了中国教育传统中的感悟性整体理解方式,不主张那种把文字掰碎揉烂的分析理解方式。孟子把它概括为‘大而化之’。所谓大而化之,本义与现在常见的用法相反,并非说那种模棱两可的马马虎虎,而是说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高屋建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5页);“中国的道理是感悟出来的,而不是析解出来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6页);“比喻是汉语文化中特有的论证方式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思维和拼音思维的差别。……西方的学说,往往需要‘理解’,而中国的学说,往往需要‘领会’。……对于中国的管理者来说,领会、感悟、比照,有可能比推理、分析、演绎更重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68页);“中国古人论事有个特点,就是省略分析过程直述结论,以归纳和洞察直奔主题。……这种分寸拿捏看似简单,实则需要信念、智慧与经验的高度嵌合,难度极大”(《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244页)。
在《思想史论》下卷第二十五章之“中唐文坛的管理奏鸣曲”,刘老师有言:“柳宗元以文人论管理,是古代文学与思想智慧交织的典范。探究柳宗元的管理思想,可以为当今管理学的非实证研究提供参照”(《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23页)。他还不忘提及马奇教授领导力的“文学”取向:“可见,从文学中获得管理研究的灵感和洞见,古今一理,中外同途”(《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44页)。
可惜,在主流实证主义那张大网的遮蔽下,行文中道的刘老师并没有借“语言转向”“叙事转向”之风展开深入的讨论。自个人彻底走向诠释主义以后,在我看来,语言之于思维,文学(艺术)之于管理,在管理实践中那些具体的事项和人际互动所发挥的影响恐怕远远大于“实证研究”“科学研究”的成果。所以,读到下面这段文字也就不免感慨良多:
“文人论证的思想火花,不能与分析缜密的学术构建相提并论。以享有盛名的柳文为例,柳宗元的管理思想与当代的管理学说相比,灵动有余而缜密不足,富有洞见却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证检验。所以,不能看到柳宗元提出了某种想法,就断言某某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更不能用柳宗元的例证贬低当今管理学界的学术成就。柳宗元毕竟是文人,是失意官员,而不是管理学家,构建管理学理论体系和提出管理学系统观点的任务并非他能承担。但是,这并不妨碍读者从柳文中获得启示。”
其三,人才
刘老师专门研究过古代“人力资源”问题,著有《继承与变革——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的发展历程》,于是在《思想史论》中也用心颇多:在用人识人方面(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吕氏提出了八观、六验、六戚、四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282页);“王充以命定与偶合的关系来讨论人力作用的机制,对‘遇、幸、偶、适’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是古代应用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研究人力资源的先驱。在人性问题上,王充辨析了性命关系,强调人性的可变性,推崇教化的作用,又以先天禀赋和后天修炼来贯通人性研究,对人才测评落脚于相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383页);刘劭在《流业》中提出人才之“三材十二种”,并“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讲人才划分为五个层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428页);苏绰《六条诏书》涉及“反对门资”,“‘官二代’问题,是抑制人才的关键。”“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省官简政”的诠释也十分有趣(《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473-474页);在一个从上至下的权力社会,分享了古人“管理”上级的心得:“陆贽的贡献在于把‘治乱之本,系于人心’的大道理变作戴在德宗头上的紧箍咒,具体咒语有三:‘罪己、改过、纳谏’”,也是可圈可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15页);还包括借柳宗元《梓人传》包工头杨潜的“领导才能”推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要各在其位,各尽其能”(《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39页)。这些对中国古代“人力资源”的探索,在类型性、系统化程度上至少让我大开眼界。
其四,国家治理
我不得不请求刘老师的谅解,虽然他对中国古代各路国家治理(管理)思想着墨不少,却并非我的核心关注之所在。我也相信偏爱“设计”“框架”“系统”的读者定能从中受益。从《吕氏春秋》“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262页);以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配套,建构大一统国家的治理模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326页);再到苏绰“他的‘六条诏书’构成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框架,实现了顶层设计和基层操作、体制建构和习惯演化的结合,从而完成了由秦汉到隋唐的治理思想过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465页)。
坦白地讲,我的注意力更在于:“中国传统的民间管理思想往往可以看到理性与迷信并存,逻辑与神秘共在,经验与灵异交错”(《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327页);“《颜氏家训》是家训之祖,其文直白浅显,是把儒家思想用于生活实践的杰作。……它的管理思想,体现在人情世故之中。……尤其是学术中难以表达的生活分寸和为人窍门,在该书中得以充分展示。……《颜氏家训》可以反映出理论逻辑与生活体验的不完全重合,进而使人们从更为实在的层次理解管理实务的内涵”(《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49页);“颜之推劝学,不讲道德性命之辩的大道理,只讲现实功利的私家语,这种劝学路数,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使用最广泛的方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60页)——那个更具社会学、人类学色彩的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三、视域融合:契合与分歧
从本文一开始,我就不接受刘老师导言中的“把握”“框架”“机制”。我用“议题(主题)”化而不是“体系化”方式形成对《思想史论》的理解和诠释,那么,我与刘老师究竟有没有视域融合?我非常确定彼此的契合之处,也会指出我们的“分歧”,而且我更乐于相信部分的分歧并非刘老师的“本意”。
以下引述的观点,背后多涉及比较重大的理论问题,原本值得展开讨论,但考虑到刘老师表达的“隐忍”和自己“洞见以下皆为修辞”的武断,我只想说,无论是隐含的问题还是昭然的答案,我都完全认同:
“熟读历史就可能发现,那些掌握了所谓历史规律的人,出于真理在手的自负,有可能会走进错得离谱的房间”;“在历史上,凡是声称自己掌握了某种规律的人,往往会依仗所谓的规律改造世界,不撞南墙不回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123页);“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不少人以战争喻商业,然而,战争与商业是有区别的。‘兵凶战危’是进入军事领域的警告牌,战争与增进社会福利的工商业具有本质区别。如果真按战争方式指导经商,那么,商业就会失去它的美好一面,只剩下令人战栗的惨烈。了解兵家思想,掌握古代兵法的思辨路数,目的在于使人们更清楚、更冷静地看到战争的逻辑,而不是把它照搬到工商领域”(《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145页);“凡是津津乐道于令个体为组织作出牺牲者,往往会推崇这种法家式的组织体系”;“组织强大化,目标单一化,成员蚁族化”(《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170页);“法家思想从管理角度来看,其利显赫,其弊也昭著。强大化的同时是没有退路和缓冲,简单化会导致失去利益协调机制,工蚁化会泯灭个体价值。这些都是法家管理思想的致命伤”(《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170页);“秦国的耕战政策,能够培育出辛勤劳作的农夫和慷慨赴死的战士,却不能培养出游走吟唱的诗人和仰望星空的智者”(《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171页);“管理思想的真正贡献,往往在洞见之中而不在计量之中”(《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290页);“建设新型民间社会,应当从《吕氏乡约》中寻找社会自治的‘精气神’。当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从‘乡约’角度解读,则会发现真正的内涵。如果企业家的‘在商言商’,不是冠冕堂皇地为政府分忧解难,而是以独立的自治姿态承担社会责任,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才有可能真正诞生,企业家阶层才会成为真正的社会中坚”(《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49页)。
刘老师是我的前辈好友,我从他那里受教已久。借助《思想史论》,开眼界、长见识,感念之余,还是要说出我与“文本中的他”的分歧。概言之,主要有三点,即人性假定(assumption,他习惯用“假设”)、逻辑与“事实”。关于人性假定,当年他曾委婉地批评过我对和谐管理理论“去人性假定”的鲁莽。所谓人性假定,无外乎为逻辑推演的自洽性提供保障,我还是觉得没有那么重要,这或许是我对管理“理论”及其严谨性的某种轻慢;《思想史论》不时强调“逻辑”与“事实”(事实验证、实证检验),我则有点儿不以为然。管理更是实践,援引布迪厄(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 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的话:“实践有一种逻辑,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这样才不至于过多地要求实践给出它所不能给出的逻辑,从而避免强行向实践索取某种连贯性,或把一种牵强的连贯性强加给它”。我相信“历史研究”“思想史论”依然可以从中加以借鉴。至于“事实验证”“实证检验”这样的说法,作为一个诠释主义者,我就不想再作解释了。
我对刘老师在《思想史论》中不时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当代西方管理学者的思想观点(理论)类比(比附)也不大认同。正如他自己所言“当代对《人物志》的研究,多数沿用西方视角,从心理学、人才甄别、人才测评等角度入手进行科学式分析,由此导致西方学术范式主导下忽略或者埋没中国智慧,没有去探究真正的本土文化资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440-441页)。回想本文“中国式思维”中刘老师的那些洞见,这种附会大可不必。毕竟它们不仅分处全然不同的语言世界、经验世界,特别是“意义之网”更是大相径庭。
当然,我对刘老师最大的抱怨是《思想史论》中有太多没有注释的生僻字,似乎唯一的例外出现在第441页:“注解(个别古代字义难解者,加括号用今义说明)”,对于非史学读者或如我这种识字有限者而言,阅读体验不算美好。
四、个人的处境和选择
历史是“流”(flow),生生不息。人类生活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至于“思想史”,无论是仰望星空,还是反求诸己,都是人类少数“精英”或“幸运”之士审视自我留下的文本片段——它可以被理解、解释、说明、批判,反反复复,最关键的是“应用”于个体。我想在《思想史论》中寻找的答案,是关于“自我”的光亮,助力自己省思来处,探寻去向。说到底,就是如何直面个人的处境和选择。
“完成”与现代诠释学的对话之后,我对概念化世界,尤其是对今日管理的知识形态(生产过程)已兴致索然。我特别关注那些生活中显现出来的生动、细节、质感的东西,无论是被当作学术知识还是被看作实践智慧。显然,在某些管理研究者的眼里那些“叙事”“思辨”不像“学术”,但我却以为管理知识不必是理性分析,不必是逻辑自洽,不必是系统条理……它只要足够诚恳,蕴含个人努力,最重要地,能有好的结果就可以了。
因此,我特别喜欢“夹缝中的坚守”的陆贽,打动我的不是他“与现代组织学习理论类似”的“以诚求信、以信求治的管理方式”,而是他“不仅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和探索作出了贡献,而且也是历代宰相中最富有学者气质,也最能坚守道义准则的人格典范”(《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03页);我也特别喜欢柳宗元“长安药材商人”的故事,“这位商人宋清似乎不追求赢利,到他那里买药的人可以赊账,到了年终,他查看堆积的欠条债券,揣度不能收回的就一烧了事。而且他还特别注重药材质量,用他的药见效快,所以医生也乐意让病人上宋清这儿来买药。尽管宋清不以发财为意,但他却能获得大利”(《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540页)。
我相信大多数《思想史论》的读者不过是某个组织中的普通人,没有机会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圣人”“枭雄”或“奸佞”。我们也不必太过纠结于“君子”“小人”之辩,心向君子应该是多数人的理想,但于现实世界,论及具体生活,则难免小人之心,小人行径,谁能例外呢?君子不是人格,它更是一种“秩序”期待中的理想行为。在个体层面的差异需要在主体间性(群体)中得以释放,但是否存在共识,恐怕就无法断言。世易时移,我们看到很多“君子”“小人”在不同时代、空间视角(近乎共识)下的不同影像,时而君子,时而小人,只能由他人、后人评说。我无意于相对主义化,只是不愿意铁口直断,把复杂的人生标签化为“触目惊心”的真君子或真小人。我内心的确向往张载“横渠四句”的那份壮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最多甘于韩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那份平凡。其实哪有什么平凡,早已难上加难。
刘老师恐怕很难想象,当我读到他老家的那副对联时,才终于看见一幅久违的画面,那是整本书最能打动我的文字:“笔者年少时,曾在乡间的窗户上看到这样一幅对联:‘月照西窗诸葛亮,日出东山左丘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第461页)。那才是我们的生活,那才是历史与我们最紧密的关联。我耳边仿佛又回响起父亲爽朗的乡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阅读文本就是理解和诠释文本,这是一场无法完结的对话,但愿刘老师听到了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