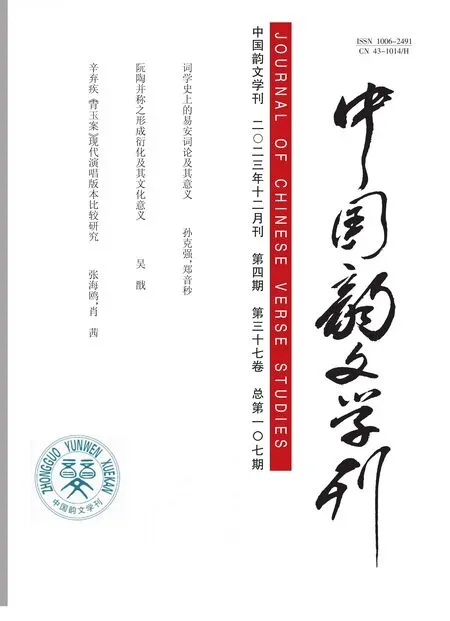论陈维崧中期词体创作的转变与词体观之建构
2023-03-22王毅
王 毅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创作风格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整合统一后在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是“作家所擅具的或一艺术美的外部印证”[1](P1)。黄霖先生曾言,文学风格的内质就是人的生命意味[2](P292)。由于创作主体的生活经历、个性情感、政治立场乃至习惯爱好均具有独异性,那么不同作家的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态度与精神体验就截然不同。抒发情志的艺术形式各适其用,最终所表现出来的文学风格迥然相异。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行难为状……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3](P67-68)“体”就指的是文学风格,“为体也屡迁”讲的就是作家创作风格具备可变性因素。创作主体的生活经历具有阶段性,其一生可能存在着多种社会身份的转变。不同的遭际与心态会影响到作家文体观的重新架构和艺术技法的自我反省。因此纵观作家的创作生涯,他们的创作风格并非从一而终,而是有着自我否定与转变的特色。对此,我们不能够采取知性的研究方法,因为知性无法真正认识事物的总体,不懂得一切事物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不断地发生、发展乃至死亡,因此,必须以理性的视角与研究方法予以具体探究。
陈维崧(1626—1682)是清初词坛名家,其《迦陵词》在流播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时而被提及却未深究的论题:陈维崧词体创作风格转变于何时、为何转变及转变期的艺术风貌又如何。论者通常将陈维崧词风转变期定为其创作的中期阶段。需要明确的是,词风的转变不代表一个人的创作风格完全改变,而是词体创作内部一些元素有机整合方式的规律变化。陈维崧词才超拔,词心醇厚,是千年词史中创作力最为强盛的词人,其词体创作前、中、后期既有一脉相承、具有延续性的因素,又有与“少作”截然相反、具有自我否定色彩的异质加入,还有一些处于风格转变时期内创作主体的审美情趣摇摆不定、新变与惯性缠连包裹的作品[4]。本文试以陈维崧词为基础,加之对前辈学者结论的辩证思考,对陈维崧词体创作中期的总体艺术风貌予以阐述。
一 陈维崧词体创作转变期的界定: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一年(1661—1672)
目前学界关于陈维崧词体创作的转变期往往以严迪昌的结论为准。严迪昌先生在《阳羡词派研究》一书中作出以下论断:
迦陵词的创作中期是个词风转化、风格初成时期。其时间上下界限大致自顺治十五年(1658),到康熙七年(1668)年底结束短暂的“京师弹铗”转去中州为止。这前后十年的重心是“如皋八载”,这是一个湖海漂泊的困顿阶段。中期创作的标志是《乌丝词》的结集面世。[5](P182)
台湾学者苏淑芬在论述陈维崧的词学历程时也说:“中期作品是从顺治十三年(1656)秋冬起到康熙七年(1668),这一期以‘如皋八年’为重心的湖海漂泊期,所著《乌丝词》中怀旧悼往之篇占三分之一,也有早岁优游贵族生活的追忆,更有陵谷变迁的追忆。”[6](P47-48)对陈维崧创作中期开始时间的判断虽有不同,但总的来看,二人分期的原则与判断基本一致。一者,以“如皋八载”的漂泊生涯和《乌丝词》的刊刻发行为重要依据,二者将陈维崧康熙七年(1668)由北京至中州这一行迹作为词风转变完成的标志。那么,首先来看陈维崧在如皋、宜兴等地漂泊流离的遭际是否给他带来思想上的重大变化以及《乌丝词》是否已经有了陈维崧后期词作的艺术技巧。
陈维崧之父陈贞慧于顺治十三年(1656)五月十九日病逝,同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曾在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左右致书家道沦落、科场失利的陈维崧,邀其至如皋读书生活。同年十一月初七,在安排完庶母时氏下葬与送别四弟宗石返商丘的烦冗事宜后,陈维崧至如皋,冒襄馆之宅东留耕堂。(1)陈维崧《小三吾倡和诗序》:“戊戌十一月,陈子自娄江拿舟访先生,先生馆于小三吾,而日与赋诗饮酒焉。”又冒襄《同人集》卷六收录陈维崧诗《己亥冬赠冒巢民先生为太母七十寿》云:“昨岁仲冬日初七,陈胜蹑屩初入门。”从以上二例可证陈维崧至如皋的时间。参见周绚隆《陈维崧年谱》上册,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页。康熙三年(1664),陈维崧由于科考两战两败,欲上京另谋出路,因此决定离开冒家。其诗《将发如皋留别冒巢民先生》将这种久困场屋、淹骞流离而又彷徨无端的愁闷挥诸笔端:“嗟予业未精,岁月忽以逝。两战两不收,霜蹄一朝蹶。我闻长安街,连云矗扶荔。金张许史家,敝裾尚堪曳。逝将舍此游,愿言一谒帝。”[7](上册,P563)除了应邀游玩或者返家探亲,陈维崧这七年来行迹基本不出如皋冒家。(2)严迪昌等学者所说的“如皋八载”指的是顺治十五年到康熙四年(1658—1665)。但考索陈维崧行迹,他在康熙三年(1664)就已经离开了如皋,康熙四年(1658)二月随毛师柱、王士禛等人在水绘园修禊唱和,六月随王士禛再次离开如皋另谋出路。总的来看,陈维崧馆于冒宅仅七年,冒襄《朴斋诗集》卷五《六集和其年留别原韵,兼寄阮亭先生》序云:“其年读书水绘庵七载,昨岁下第,决计游燕,坚留不得。”见冒辟疆著《冒辟疆全集》上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页。将陈维崧此阶段的词体创作作为转变期的标志是不合理的。瑞士学者皮亚杰指出:“一个刺激要引起某一特定反应,主体及其机体就必需有反应刺激的能力。”[8](P60)创作主体需要外部环境与主体精神两个维度的刺激与反思才能真正改变创作风格。从外部环境来看,陈维崧虽家道中落,但是寄居在冒家能保障衣食无忧,贵公子的习气并没有多大改变。冒襄为友人之子提供了广泛交游的人脉、资金与场所,连收录了陈维崧明末至顺治十七年(1660)诗作的《湖海楼诗稿》也是冒氏为之资助刊刻。据周绚隆《陈维崧年谱》及相关可考诗文资料来看,陈维崧单在顺治十五年(1658)底刚到如皋的两个月内就至少参加了大小聚会11次。由于结识的斗方名士多为诗人,因此在交游的场合陈维崧也常用诗来应酬唱和,词体创作不多。而这一时期的词作多是在扬州与邹祗谟、董以宁和王士禛等年轻文人交往时所作,受到广陵词坛词风影响甚重,很难在词体次韵唱和中大展身手,局度有限。从主体精神来看,按赵月瑟所说,我们“不应当根据人的意识来解释人的行为,而应当根据人的行为来解释人的意识”[9](译者的话,P2),词人的行为结果就是词作,研究者还是应当以词的文本去探寻主体精神。这一时期的词作大多收录于《倚声初集》中,总的艺术风貌呈现出绮才艳骨与雄浑之气兼容,以真情取胜。词作虽受云间词派影响极深,但咏史词和五首《满江红·怅怅词》这样的少数作品已隐约透出一个事实:奉唐五代为圭臬,同时瓣香北宋诸家,以小令为主,创作主题多为闺阁艳情与时令感伤,艺术风格早期多呈浓艳纤软的云间词风已经不适宜陈维崧抒情的需要了。但这种在词体文学观念上稍纵即逝的反思并没有能带动词体风格整体的转变。综上,外部环境并没有能够给予创作主体强烈的刺激,陈维崧这时期词作的主题内容和整体艺术风格可以作为例证。
黄天骥先生曾分析总结了陈维崧后期词作的艺术风格,“喜欢捕捉‘历乱烟村’、‘断壁崩崖’、‘柴门栗椽’、‘野鸭’、‘狂涛’、‘残碑’、‘月黑枫青’的形象;爱使用的动词是‘吼’、‘裂’、‘啮’、‘怒卷’、‘颠踬’之类;他经常创造的是‘黑’、‘幽’、‘险’、‘古’、‘野’、‘粗硬’的气氛。就像扬州画派那样,用破笔焦墨,在纸上挥洒皴刷。大处气势磅礴,小处藏而不露,给人以强烈的刺激。”[10](P68)《乌丝词》中的作品是否具备了陈维崧后期词作的典型风格或者演变痕迹呢?《乌丝词》共四卷,收录141调,词作266首,刊刻于康熙五年(1666),康熙七年(1668)被孙默刻入《国朝名家诗余》。“乌丝”一名取黄庭坚《往岁过广陵值早春,尝作诗云:“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今春有自淮南来者,道扬州事,戏以前韵寄王定国二首》诗“想得扬州醉年少,正围红袖写乌丝”[11](上册,P185)之意,即少作,集中较多作品书写了陈维崧身为年轻贵公子时期在江南声色犬马的艳冶生活与浪子心境。
从题材内容来看,《乌丝词》主要包括了三方面。第一,闲情之作及应酬交游词占到了《乌丝词》的近三分之一。如史惟圆《沁园春·题其年〈乌丝集〉》所言“拟向红楼寄此身”[12](第二册,P783),恣意书写与狂朋怪侣在红楼中灯红柳绿、莺歌燕舞的艳冶生活体验的词作仍占《乌丝词》很大的比例。部分旖旎纤软之作如《长相思·赠别杨柳》《点绛唇·咏枕》极尽浮艳,品格未比《花间》《草堂》高出多少。第二,感伤故国之作是明清鼎革的时代产物。陈维崧此类题材的词作虽有比兴寄托,但陈维崧毕竟是年轻遗民,对亡国之恸体认不深,没有如陈子龙等抗清义士或者吴伟业这样的贰臣闻人在词中所透露出来对故国的留恋与动息无措、歧路徘徊之怅惘那么深沉与强烈。如《杏花天·咏滇茶》“异乡花卉伤心死,目断昆明万里”[13](P380)一句,借茶花在异乡凋谢之事嗟叹南明永历帝在昆明被吴国贵绞死之事。该词虽融入了陵谷变迁的兴亡之感,但字里行间并没有流露出陈维崧在这场异变中亲身感受到的悲慨,略有“隔”之嫌。前两类作品受限于创作主体的眼界与情感积淀,不仅词作中根本看不到“狂涛”“残碑”之类的幽涩奇诡的意象,艺术风格距“气势磅礴”“藏而不露”尚远。第三种是陈维崧将身世之感融入倚声的感伤怀旧之作,是这一时期创作主体不平而鸣的艺术结晶,在小令与长调中均有出色作品。《乌丝词》中有“对君家,两世湿青衫,吾衰丑”(《满江红·陈郎以扇索书,为赋一阕》)这般英雄迟暮、容颜衰丑的妄自菲薄;有“向泉台泣数一年间,飘零状”(《满江红·乙巳除夕》其二)如此对漂泊流离、居无定所的无奈与感伤;也有“江上斜晖,弟作归人兄未归”(《减字木兰花·广陵旅邸送三弟纬云南归》)此类骨肉相连、兄弟情深的流转情悲。但是从词人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来看,词作流露出的是一种阴结郁悒、难以消解之愁闷,情感真切深挚,但与陈维崧在中州时期及其后的词作表达出的睥睨一切、横绝千古的傲情明显不同。前者是内敛,后者则极为外放。正是这种情感基调的差异,《乌丝词》中作品常营造的是落日楼头之幽凉氛围,塑造的是一位江南游子的抒情人物形象,给读者的是一种痛彻心扉、哀婉同情的阅读体验。而这种阅读观感也远不及黄天骥先生所说的“强烈的刺激”那般发人深省与酣畅淋漓。综上,《乌丝词》的刊刻确为陈维崧词体创作生涯的重大事件,但将其作为陈维崧创作中期的标志,此观点仍可商榷。
陈维崧词风之嬗变是可以从他本人及友人的相关文字材料中找到印证的,如陈维崧弟子蒋景祁所作《陈检讨词钞序》:
其年先生幼工诗歌,自济南王阮亭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学,其上有吴梅村、龚芝麓、曹秋岳诸先生主持之,先生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然刻于《倚声》者,过辄弃去,间有人诵其逸句,至哕呕不欲听,因厉志为《乌丝词》。然《乌丝词》刻而先生志未已也。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伤邹、董又谢世,间岁一至商丘,寻失意返,独与里中数子晨夕往还,磊砢抑塞之意,一发之于词,诸生平所诵习经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于词见之,如是者近十年,自名曰《迦陵词》。[7](下册,P1831-1832)
“《乌丝词》刻而先生志未已也”表明,康熙五年(1666)所刊行的《乌丝词》并不能作为词风嬗变的标志。蒋景祁毕竟是作为后辈记述老师词学创作的脉络,难免会有记忆上的偏差。陈维崧“倦游广陵归”大致是在康熙五年参加“广陵唱和”之后,他在这个时期并没有放弃诗的创作。陈维崧完全“弃诗弗作”要到康熙十二年(1673),因此“遂”这个逻辑关系并不存在。除此之外,综合这篇序中的信息,可以得到以下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康熙五年(1666),《乌丝词》刊行,陈维崧有意识地自我革新,但是在这本词集中并没有能够完全落实,找到一种真正只属于他自己的抒情方式和思想美与艺术美高度统一的倚声技法。二、康熙五年陈维崧参加广陵唱和活动,曾作唱和词《念奴娇》八首,均未收录于《乌丝词》。三、康熙八年(1669)董以宁逝世,康熙九年(1670)邹祗谟又亡,倚声同道之友人相继离世。四、康熙十一年(1672)陈维崧自中州史逸裘幕失意返乡,之后开始了与“里中数子”寄情山水、恣意唱和的生活。总的来看,自《乌丝词》刊刻传播到《迦陵词》的自度成型,大致在康熙五年至十一年(1666—1672)之间。另外,陈维崧在与王士禛、邹祗谟、董以宁等人顺治十八年(1661)“题扬州女子余韫珠所绣诸图”与“题《青溪遗事》画册”两次词体唱和中的作品均未收录于《倚声初集》中,而收录于《乌丝词》集内,和词中已然显现出了对广陵词坛词风的脱离。如果我们再将《乌丝词》中词作的系年纳入考量,那么陈维崧的词体创作中期可以划定为顺康之际至康熙十一年(1672)从中州返乡这段时间内,这是创作主体在词体观和艺术风格论两个方面自我反省、否定与创新的漫长转变过程。
根据蒋景祁的这篇《陈检讨词钞序》所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陈维崧创作的实际呢?陈维崧曾在康熙十年(1671)左右作《任植斋词序》论及对其少作之反思,他声称:“顾余当日妄意词之工者,不过获数致语足矣,毋事为深湛之思也。乃余向所为词,今覆读之,辄头颈发赤,大悔恨不止。”[7](上册,P53)陈维崧在康熙五年(1666)刊行《乌丝词》后,正因为他“志未已也”,所以又有了续刻词集的计划。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手稿本《迦陵词》第八册中完整地收录了《乌丝词三集》和《乌丝词第三集》,《乌丝词第三集》是《乌丝词三集》的一个补集,两个集子中的词作也毫不相同。其中《乌丝词三集》中就收录了陈维崧康熙七年(1668)北上京城路上和到了北京与龚芝麓、钱芳标等人交游唱和乃至赴中州期间的词作,如《齐天乐·骥沙旅店纪梦》《黄河清慢·清江浦渡黄河》《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即用其题乌丝词韵》《点绛唇·夜宿临洺驿》《西江月·过冯唐故里》等。《乌丝词第三集》中的词作系年也止于康熙十一年(1672)最后一次至中州时期。而本应该计划先于《乌丝词三集》刊刻的《乌丝词二集》在手稿本中未能得见其面目,但我们可以推测出该集大致收录的是康熙五年(1666)《乌丝词》刊行后至康熙七年(1668)出发赴京这段时间的词作。严迪昌先生等前辈学者因为条件有限,未能得见手稿本《迦陵词》,因此能够得出他们的结论已实属不易。今人应该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结合能够看到的新材料得出目前最能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白静在其论文中说:“《乌丝词》的结集和出版是陈维崧中期词创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它不仅是陈维崧湖海漂泊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陈维崧转变词体观念、确立独特风格的初步探索,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3)白静《手抄稿本〈迦陵词〉研究》,南开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转引自刘伟《康熙年间手稿本〈迦陵词〉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92页。此论断是很有见地的。“阶段性成果”也表明了《乌丝词》确实无法代表陈维崧中期词作的整体面貌,但向词坛宣告了词体创作自我革新的开始。
陈维崧词体创作中期大致为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一年(1661—1672),这是他创作风格的转变期。这一时期,由《乌丝词》到《乌丝词二集》《乌丝词三集》《乌丝词第三集》,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沉淀的过程。《乌丝词》仅是词风转变的初步探索,陈维崧经由康熙五年(1666)广陵唱和、康熙七年(1668)京师唱和及之后的中州之行的情感积淀,到康熙十一年(1672)第三次中州之行结束返乡,最终在词体观和倚声技法两方面完成了词风的转变。
二 抒情方式的调整和倚声技法的创新:广陵唱和与北京、中州之行
如果从风格批评的角度来看作家的创作风格,按照严迪昌先生的定义,“文学风格则是批评家从所品评的某一作家的作品中把握住的只有他这一个才擅具的美的境界的概括”[1](P11-12),那么,“这一个”,即独异性就是创作风格转变的必然追求和最终目标。仅仅贴合广陵词坛创作风格的词体创作注定是千篇一律的,这只会使得陈维崧成为王士禛、邹祗谟、董以宁创作群体中平凡的一份子。而后世无论是陈廷焯将他尊为“古今五家”(4)陈廷焯《词坛丛话》“古今五家词”条:“古今词人众矣,余以为圣于词者有五家。北宋之贺方回、周美成,南宋之姜白石,国朝之朱竹垞、陈其年也。”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20页。之一,还是胡薇元推崇他为“清初三家”(5)胡薇元《岁寒居词话》“清初三家”条:“倚声之学,国朝为盛,竹垞、其年、容若鼎足词坛。陈天才艳发,辞锋横溢。”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38页。之一,抑或是我们今天视他为一代词宗、阳羡词派领袖,都是针对陈维崧中后期词风而言。纵观陈维崧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一年(1661—1672)的创作过程,结合他的行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广陵唱和”和北京、中州之行所带给陈维崧词体创作极为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抒情方式和倚声技法两个方面。
陈维崧曾作词《采桑子·吴门遇徐崧之问我新词,赋此以答》论及抒情方式之转变:“当时惯做销魂曲,南院花卿,北里杨琼。争谱香词上玉笙。 如今纵有疏狂兴,花月前生,诗酒浮名。丈八琵琶拨不成。”[7](中册,P996)由“销魂曲”到“疏狂兴”,可以粗疏地说是在风格上从婉约转向豪放,但从根本来说是受到稼轩词的影响,抒情方式由内敛式转向外放型。歌德曾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14](P39)风格的变化体现在抒情方式的转变,也必然是词中反映的创作主体思想的变化。陈维崧后期词在内容上借助词体酣畅淋漓地抒发一己之愁闷与睥睨千古的豪情。康熙五年(1666)的“广陵唱和”对陈维崧词在抒情方式的转变起到了启发与促进作用。(6)沈松勤指出:“‘江村’与‘广陵’两大唱和是引领并推进陈维崧词风新变不可或缺的一个契机与环节,从中也宣告了其以‘飞扬跋扈’为特征的‘变调’风格的成熟与确立。”见沈松勤《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36页。需要注意的是,陈维崧所作“江村唱和”和词为事后所作,他本人并未实地参与到“江村唱和”之中,王士禄见到陈维崧《满江红》和词也应该是点评《乌丝词》时。另外,陈维崧词风转变应该是一个持续性事件,而非一蹴而就,几首词作就能简而概之的。因此综合考量,陈维崧到了康熙五年“广陵唱和”才真正在大众视野中开始改变抒情方式并有数量可观的词作作为实践的依据。“广陵唱和”共有十七人参加,由多组小型唱和组成。此次唱和调寄《念奴娇》,是康熙四年(1665)“江村唱和”后稼轩风进一步扩大影响的证明。“从内容和风格看,调寄《念奴娇》唱和词或抒发词人内心抑郁不平的愤慨,或表现词人旷达超脱的态度,或兼而有之,主要表现为悲慨激宕的稼轩风,兼有超脱旷达的苏轼词风,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15](P203)曹尔堪开场词中即有“平山堂下,但含烟衰草,旅愁千斛”[16](P80)的羁旅之愁,宗元鼎和词中更有“纵饮千杯休惜醉,莫负酒酉农人熟”[16](P87)的旷达宽慰之语。且看陈维崧和词《念奴娇·小春红桥燕集同限一“屋”韵,时有鱼校书在座》:
霜红露白,借城南佳处,一餐秋菊。更值群公联袂到,夹巷雕鞍绣轴。一抹红霞,三分明月,此景扬州独。挥杯自笑,吾生长是碌碌。 且喜绝代娥媌,玄机娣姒,风致偏妍淑。(7)《陈维崧集》以康熙二十六年患立堂刻本《陈迦陵文集》为底本,而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广陵倡和词》中该词题为《念奴娇·小春红桥燕集同限一“屋”韵,时有鱼校书在座》,过片句为“且喜绝代娥媌,鱼玄机娣姒,风致妍淑。”陈维崧填该词限“屋”韵,为《念奴娇》正体,《广陵倡和词》系临场发挥,有不合格律之嫌,当以“患立堂”本为准。见王士禄编《广陵倡和词》,南京图书馆清抄本,见《扬州文库》第5辑第83册,广陵书社2015年版,第84页。恼乱云鬟多刺史,何况闲愁似仆。小逗琴心,轻翻帘额,一任颠毛秃。倚阑吟眺,云鳞坟起如屋。[17](下册,P1328)
“挥杯自笑,吾生长是碌碌”,“何况闲愁似仆”,“一任颠毛秃”,陈词中满目皆是牢骚语。该词在情感表达方面有一个极强的特点,就是自我意识十分突出,以我口抒我怀,愤懑无奈之情喷薄而出。我们不妨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歇拍句“吾生长是碌碌”已定下感情基调,下阕四句均表述了主体的动作或内心思绪,在情感表达上,每一句均有一个内含的“吾”作为主语。“广陵唱和”活动中的大部分词作都表达了强烈的个体情感,但如陈维崧词有如此明晰之自我意识的,则极为少见,如王世禄对该词的评价:“掀髯长啸,致足空群,读一结可识词家造语法。他人郎有此意,断无此句也。”[16](P84)“掀髯长啸,致足空群”意指陈词个体情感之强烈,“他人郎有此意,断无此句”则是称赞陈维崧抒情方式之独异。在“广陵唱和”之后的词作中,由“吾”变“我”,“我”在其词中出现频率极高。第二,上阕歇拍句加上下阕除结拍句外的三句,这四句正是由于词人刻意地安排篇幅来抒发情感,而导致语句中没有一个意象的出现,且语言逻辑关系明畅。这两种倾向相互配合,以自我意识为主导,强调不借助意象自然流畅地抒发一己之苦闷,这样的抒情方式极易形成以文为词的倚声特色,这也与“广陵唱和”所推行的稼轩风相契合。如陈维崧的论词词《念奴娇·读曹顾庵新词,兼酬赠什,即次原韵》上阕:
老颠欲裂,看盘空硬句,苍然十幅。谁拍袁绹铁绰板,洗净琵琶场屋。击物无声,杀人如草,笔扫夋兔毫秃。较量词品,稼轩(8)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广陵倡和词》中该词题为《念奴娇·读曹顾庵新词,兼酬赠什,即次原韵》,歇拍句为“较量词品,梦窗白石山谷”,此处当以“患立堂”本为准。见王士禄编《广陵倡和词》,南京图书馆清抄本,见《扬州文库》第5辑第83册,广陵书社2015年版,第84页。白石山谷。[17](下册,P1329)
此等表达,在《倚声初集》所收录的陈维崧词及《乌丝词》中绝无仅有。词中议论,如平地而起,扶摇直上,“裂”“拍”“净”“杀”“扫”“秃”一系列的重字给人以排山倒海、无可辩驳的议论之势。“较量词品,稼轩白石山谷”,稼轩首当其冲,不仅可以形容曹尔堪之词风,更涵盖了“广陵唱和”的整体艺术内核,同时也蕴含了陈维崧自身的词学宗尚。这首词不仅加强了上述的两种倾向,并且自我意识更强,通篇无一个意象,情感的宣泄在重字的加持下如飞湍直下,激烈跳荡。
词风的转变既有独异性,又有稳定性,陈维崧在“广陵唱和”中将这种直接外放的抒情方式一以贯之并不断加强情感宣泄的力度,如“无数狂奴,一群荡子,屯守倡家屋”(《念奴娇·送朱近修还海昌,并怀丁飞涛之白下,宋既庭返吴门,仍用顾庵韵》)。王士禄感叹道:“诵‘无数狂奴’一下三语使我叹,作此寂寂,灵山一会,故自不易”[16](P84),“我与浯溪曾有约,采入文钞篇幅。细写千行,高吟百遍,音响崩崖屋”。(《念奴娇·红桥倡和集成,索李研斋序、孙介夫记,作词奉柬并呈冒巢民先生》)孙枝蔚如此评价此词艺术特色:“意态傀俄,笔力夭矫,雄奇顿挫,直令南北两宋诸家气尽。”[16](P85)情感的肆意宣泄并不妨碍陈维崧造语之奇,“薄命余同鞠。鞠兮惜汝,一生长被人蹴”[16](P86)(《念奴娇·广陵客夜却忆吴门同吴梅村先生暨叶讱庵、盛珍示、王维夏、崔不雕、李西渊、范龙仙、王升吉饮钱宫声宅,时有新王、赖凰两较书在座》),道古人之未道。“蹴鞠”二字分押,押韵极为妥帖,情感颇为深挚。
北京、中州之行对于陈维崧词风转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倚声技法方面。康熙七年(1668),久困场屋的陈维崧上京另谋出路,在龚鼎孳的帮助下,同年便前往河南学政史逸裘幕求职。一方面,“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17](P247),河南中原地区也是造就古今英雄志士声名的热土,苍凉广博的北方大地给了陈维崧极大的视觉冲击,名胜古迹与英雄文化也对他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层面的震撼,这些无一不被化为语言素材,融入《乌丝词三集》《乌丝词第三集》中。另一方面,龚鼎孳倡导发起的京城唱和极大地鼓励了陈维崧词体创作的积极性,并且在大量的同调次韵应和中明晰了自己的定位。
首先,从康熙七年(1668)陈维崧前往北京始,残颓怪诞、光怪陆离的自然意象接连出现于他的词作中,配合重笔,营造出壮美孤秀之氛围,这也成了他后期词作的显著特色之一。如他北上过程中所填之词:
落日古郯城,一望秃碑苍黑。怪底蜗黄虿紫,更藓痕斜织。[7](中册,P1005)
(《好事近·郯城南倾盖亭下作》)
乱峰怪石甃围墙。墙里人家一半枣花香。[7](中册,P1064)
(《虞美人·过青驼寺旧寄示冒子青若》)
乱碑没入寒芜里。[7](中册,P1095)
(《渔家傲·羊流店怀古》)
在北京时所作:
堪愁成往迹,缭垣败甃,满目残秋。[7](中册,P1229)
(《满庭芳·过辽后梳妆楼》)
看水面、怒涛似屋,巨鱼如阙。[7](下册,P1532)
(《贺新郎·席上赠芝麓先生》)
中州旅途所作:
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风卷怒涛。[7](中册,P1059)
(《南乡子·邢州道上作》)
雄关上郡,看城根削铁,土花埋镞。[7](下册,P1327)
(《念奴娇·巨鹿道中作》)
朝来急霰,似千层浴铁,一军都白。何事严装偏早发,鞭指荒台阏伯。万籁悲号,六花狂舞,归骑疑冲敌。[7](下册,P1337)
(《念奴娇·梁紫有和予〈百字令〉词,因用前韵酬之,送其暂返锦池,兼促即来梁苑》)
陈维崧词在意象经营方面的改变可谓得“江山之助”,《礼记·中庸》孔疏论述了南北地域特色所造成的人性格上的差异:“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18](P1626)孔尚任在《古铁斋诗序》中也讲到了风土人情对作诗填词的影响:“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19](第二册,P1180-1181)在康熙七年(1668)之前的词中,这类意象偶有出现,但是在陈维崧北行之后,则屡屡成为词作中塑造的典型意象。由江南行至齐鲁大地,目之所及,词中所见还是苍黑的“碑石”,到了北京、中州占据词文本篇幅的就是“怒涛”“酸风”“铁城”“荒台” 等更为丰富且气势雄浑的意象了。加之“卷”“削”“狂”等重字,整个画面充满着生命抗击的意味。这些自然意象本就在江南地区极为少见,而在经由北京、中州之行后,它们就成为陈维崧词中经常化用的语言素材来强化词人情感的力度。即使是在康熙十一年(1672)后词人回到了家乡宜兴,他也经常将身边的山石枯木刻画出阴森奇诡的形象,这就与北京、中州之行创作技法上的实践有着直接联系。
其次,陈维崧在北京、中州期间使用以文为词的手法更为娴熟,出现了对话体的词体创作。对话体即两个人一问一答的形式,这在汉大赋中极为常见,通过主客对话,达到突出中心、劝百讽一的效果。后来辛弃疾、刘过将对话体引入词体,这成为以文为词手法的一个样板。但辛、刘二人仅将其作为一个尝试,相关词作数量并不多,对后世影响有限。到了陈维崧手中,对话体词才成为创作主体耗费心力并大力创作的体裁之一。这一体裁在《乌丝词》中虽有简单的涉足,但在中州期间陈维崧才开始投入心力,将对话体不断深化并拓展篇幅。这表现在从一首词的上下阕的问答关系拓展到两首词形成对话关系。前者如《乌丝词》中收录的中调《摊破丑奴儿·纪艳》:
隔帘挼碎相思苣,斜著乌云,漾著红巾。袅袅亭亭一段春。是耶,难道是、昨宵人。 戟门阖却葳蕤锁,花气氤氲,月色缤纷。墙角猧儿吠夜分。非耶,谁道是、昨宵人。[13](P398)
此词尚属闺中女子的自问自答,但上下阕之间的问答关系已经非常明晰了。上下阕形成对话,这种倾向在陈维崧后期词中更为强化,如《风入松·苦暑戏与客语》中上阕直言“客言”,下阕即为词人“答言”,《洞仙歌·乞巧同蘧庵先生赋》中上阕为词人问天孙,下阕为天孙作答。这些词均是陈维崧对话体词体创作的持续性实践。
将问答分赋两词始于康熙十年(1671)陈维崧寓居在商丘侯方闻家中,见其兄侯方岩沉迷于斗鹌鹑,友人田兰芳作书劝谏,于是他将田氏书信中话括入词中,又戏代侯方岳作词回应。
沁园春·叔岱先生雅有鹌鹑之癖,友人田梁紫作书止之,戏括书语为词
客语先生,唶汝鹌鹑,才乎不才?纵遇敌争能,差强燕雀,为人穿鼻,终是驽骀。尽日啁啾,一身眇小,只合充庖佐酒杯。因何事,却烦人把握,费尔安排。 王褒僮约新裁。更每日奔驰一百回。要新魁就浴,甫令东去,故雄觅粒,旋遣西来。樊笼盈庭,屠沽入座,恐累先生盛德哉。驱之便,算豢龙非计,好鹤为灾。
沁园春·又戏代叔岱先生答
先生得书,再沥余杯,敬谢客言。叹古往今来,几场蚁斗,山林朝市,到处蜗涎。卿论自佳,仆狂殊甚,枉费相如谏猎篇。吾衰也,只短衣射虎,便拟终焉。 此虽鸷愧鹰鹯。看猛气雄心非偶然。正霜天袖手,试观其怒,中原赌命,肯受人怜。藉尔骁腾,消予磊块,长日浮沉里闬间。公休矣,姑从吾所好,以待来年。[7](下册P1498-1499)
前词代表以田兰芳为代表的世人观点,“樊笼盈庭,屠沽入座,恐累先生盛德哉。驱之使,算豢龙非计,好鹤为灾”,这种无益的爱好不仅成为侯方岩的污点,甚至还可能如春秋时期的卫懿公一般,因为痴迷鹤,从而生出祸端,亡国亡身。后词虽是代人所答,实乃夫子自道,“仆狂殊甚”“吾衰也,只短衣射虎,便拟终焉”“中原赌命,肯受人怜”都是词人自身写照。作答之词自我意识极强,运用“仆”“吾”自称及“此”“正”此类转折的虚词使得全篇宛如散文,文笔清爽,情感表达顺畅。对话分赋两词作为一种创格,并不是陈维崧创作生涯中的昙花一现,后期词作中有《菩萨蛮·和龚伯通寄于生用原韵》和《菩萨蛮·代于生答伯通仍用前韵》形成书信问答,代龚士稹书“红烛奈他何,相看泪孰多”之相思愁绪,又代于生表达“郎口似隋河,相思谎最多”[7](中册,P989)的娇嗔回应。在《氐州第一·诘鼠戏同云臣赋》和《氐州第一·鼠对》更是构造出了一组人鼠对话。由此可见,辛弃疾、刘过等南宋词人涉足但未深耕的领域确实被陈维崧苦心经营,并以丰富的创作实现了,这样的创新最早发生于康熙十年(1671)中州时期。
再次,陈维崧在北京、中州期间开始尝试创作叠韵联章体词。出于交游应酬的需要,陈维崧曾在康熙七年(1668)八月初六至八月十六日与北京作《念奴娇》叠韵词十首,词末限字“绝”;康熙十年(1671)冬在中州再填《念奴娇》叠韵词六首,词末限字“拾”。组词的创作对词人的倚声能力是一个考验,限韵则使得难度更加提升。但陈维崧能够迎难而上,因难见巧,浪子心绪和落魄愁恨在叠词形式下凸显得愈加强烈,这也得到了当时及后来许多词人的关注与青睐。康熙七年(1668)的陈维崧作《念奴娇》词后有龚鼎孳、钱芳标、陈维岱、陈至言、董元恺、董儒龙等人追和,季迈宜、王霖更是效仿陈维崧以日作题的方式作词七首及八首。康熙十一年(1672)陈维崧返乡后更是挥洒才情,填《蝶恋花》四月词、五月词、六月词每组八首,共二十四首,吸引了阳羡徐喈凤、史惟圆、史可程等人与其唱和,凌立仁[20]、曹寅、戴鉴、沈朝初等后辈词人均有追和。由此可见,不仅陈维崧自身对叠韵联章体词一直保持着创作的热情,当时乃至后世的词人均以陈维崧词作为创作范式倚声唱和,这种模拟创作又反向提升了陈维崧的创作积极性。这类组词对陈维崧词在清代的经典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在部分词作中陈维崧有意使用重字。这里的“重字”非重笔,而是重复之字,在传统的诗歌批评理论中本是竭力避免的现象。《文心雕龙·练字》篇中刘勰提出了“权重出”的命题,认为遣词造句需避免重字:“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21](P351)但陈维崧反其道而行之,词中“我”“吾”此类指代自身的字频出,康熙七年(1668)所作《贺新郎·徐竹逸招同几士兄阁上看梅》一词中单“花”字出现了8次。前代词人词作中也并非没有重字,如晏几道《御街行》(街南绿树春饶絮)中总共76字,重字11个,并不影响词格,梁启勋所说“读之不但不觉其赘,弥觉其美”[22](P2978),正是从情感表达方面认可了词中重字的使用技法。
三 词体观念之自觉:以《今词苑序》为中心
陈维崧在康熙五年(1666)的广陵唱和中受到稼轩风的影响开始转变词中的抒情方式并逐渐成熟,在北京、中州的求仕旅途中创新倚声技法,受到了龚鼎孳、钱芳标等名词人的追捧和后世词人的追和。陈维崧词风的转变与他主体意识中词体观念之自觉有关,从顺康之际至康熙十一年(1672)的陈维崧的书信、为友人词集作的点评、序跋,乃至论词词中可以看出一条词体观念转变的大致脉络。大约于康熙十年(1671)为自己与吴逢原等人选《今词苑》所作的《今词苑序》(又名《词选序》)是陈维崧词体创作生涯词体观的高度凝练,真正标志着他在创作实践与词体观念两个维度上的蜕变,词体创作开始进入后期。
(一)词体观之逐渐自觉
明末清初,词相对于诗仍然处于文体的弱势地位。但是在文网密布的清王朝统治下,文人们担心遭遇文字之祸,于是将创作视野拓展到了词文学。如陈衍《小草堂诗集序》中所说:“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咏物、咏史以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镬类然也。”[23](P684-685)词体的特质意内言外,言近旨远正符合这一时期文人们抒情言志的需要。顺康之际江南地区的士子因“奏销案”“通海案”营造的恐怖文化氛围而人心惶惶,惊怖不安,王士禛主张以“羚羊挂角”之法借倚声寄托亡国之恸:“释氏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古言云羚羊无些子气味,虎豹再寻他不着,九渊潜龙,千仞翔凤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24](卷一,P4481)王士禛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元年(1662)在扬州任推官时曾作为原唱发起了五次词体唱和活动,尤以《浣溪沙》调寄“红桥怀古”、《菩萨蛮》调寄“《青溪遗事》画册”两次唱和规模最为宏大,作品留存数量最多,吸引了陈维崧、邹祗谟、董以宁在内的一批年轻遗民词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顺康之际的广陵唱和活动所体现出的“尊体”理念对陈维崧在创作中期过程中词体观的建构是有直接影响的。
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顺治十八年(1661)之前陈维崧没有涉及词的理论文字,而在参与到王士禛主持的词体唱和活动后,他由点评词集入手,继而在信札、序跋以及词作中阐发自身的词学观念。陈维崧品评他人词作多是从遣词、声律、取境等艺术论层面入手,如“广陵唱和”中评陈世祥《念奴娇·小春红桥宴集同限一屋韵》“写景、用事、炼句、造字无一部极矜隽”[16](P98),评邓汉仪《念奴娇·抱琴堂与戴云极司李夜集,因怀王阮亭祠部兼柬西樵司勋》“俯仰之间,情思苑结,用笔倩艳,几于着纸欲飞”[16](P93)。到了康熙六年(1667)尤侗的《百末词》中,陈维崧除品评字句外,兼及整体的画面感与意境,如评尤侗《海棠春·晓妆和阮亭韵》“一幅晓妆图,美人云气缭绕纸上”[25](P665)。而在康熙七年(1668)陈世祥的《含影词》中,陈维崧的点评不单是鉴赏只言片语,而且开始触及“尊体”的核心问题。陈维崧对于陈世祥《沁园春·浣手绣观音》的评语为:“其波折处有《龙门》章法在,其顿挫处有杜陵字法在,孰谓词为小道哉。小儿不得无理。”[26](P93)以文体地位相对较低的词比附文体地位高的诗,从而获得文体层面的认可,是词“尊体”的必要途径之一。
陈维崧在创作中期摸索出两条途径树立“尊体”观念,一是与明末清初许多词人一样,通过比附诗从而获得文体上的认同。另一条途径是肯定由《花间》一脉相承的艳丽词风,借男女间的悲欢情事来写词人自己的忧患交迫之悲与百端交集之哀,是谓之“哀艳”[27]。陈维崧康熙七年(1668)为友人所作词序中可以清晰看出这种倾向。陈维崧首先针对鄙弃《花间》词风的看法予以抨击,他在《叶桐初词序》中说:“曾闻长者,呵《兰畹》为外篇;大有时贤,叱《花间》为小技。十年艳制,坐收轻薄之名;一卷新词,横受俳优之目。……然而结习宁志,鄙怀有在。遇成连与海上,情终以此而移;见美丽于中山,口遂不能无道云尔。”[7](上册,P386)借伯牙学琴与中山君失礼亡国两个典故阐述艳词的两个特征,能移人情且不失礼制。词中的情多是关于个人遭际之愁闷,《钱宝汾词序》谈到的“柳郎中小令,丽句虽多;牛给事新声,愁端不少者矣。仆类楚狂,偶来燕市。一声河满,怜司马之青衫;三叠阳关,羡尚书之红杏”[7](上册,P367)正是此理。而这种个人情感的表达是符合礼制的,常以比兴寄托取代直抒胸臆,陈维崧在《杨圣期〈竹西词〉序》将哀艳之词的两个特征融为一句:“楼头扇底,颇多托兴之篇;花下尊前,大有言情之制。”[7](上册,P394)每一个词人拥有抒情方式的多元选择,以艳词的表达技巧婉转地表达款款情思是他们的词心独具。因此,陈维崧得出结论:“讵言小道,亦曰多能。”[7](上册,P395)总的来说,这两条“尊体”途径是明末清初许多词学家理论阐释的共通点,但是千篇一律的文体比附观点和崇尚艳词的审美终究会走向词体创作和鉴赏的枯竭,没有一位词学家能够如陈维崧一般以“飞扬跋扈”之气魄在“尊体”的大理论框架之下将词直接等同经、史的地位,将之推至文体的至高之位。
(二)《今词苑序》的词体观建构
陈维崧不仅仅是清初词坛名家,他还是清代骈文发展的标志性人物[28]。陈维崧《今词苑序》词体观念的建构借鉴了他与冒襄二子禾书、丹书顺治十八年(1661)所编《今文选》的骈文理论架构。
比较《今词苑序》和《今文选序》,我们可以发现两篇序的写作思路大体一致。两篇序文均以对话体开篇,指向性与批判性极强。《今文选序》指出清初的骈文写作存在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的问题。外部存在着“错综者以迁、固为专家,整炼者以庾、徐为极则。更相调笑,莫能同同”[29]的问题,内部问题则是很多骈文创作者徒事夸饰、言之无物的写作倾向。因此清初很多作文者将散文与骈文看作互不侵犯、相互对立的两种文体。陈维崧则引刘勰《文心雕龙·情采》“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21](P288)立论,言明骈文与散文在写作立意上是一致的,均需要“情”“文”“理”“辞”各要素的相互配合,主张骈文的写作也需要思想、情感为本,反对只追求外在美的形式化倾向。由于散文均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这类史书作为写作模板,骈文通过比附散文,很容易就能达到文体地位的高地。再加之陈维崧卓绝的骈文创作,使得骈文在清初确实获得了主流的认可。
鉴于在骈文领域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成功,陈维崧在推尊词体的理论阐释中不再选择以词比附诗的策略,而是在形式上以词比附骈文,内容上以词比附经、史,从而达到“为经为史”的文体高度。《今词苑序》的开篇与《今文选序》基本相同,以主客问答的方式引出部分作者认为倚声会导致“损诗格”的问题。陈维崧在对此偏见进行批驳时,并非就词论词,而是将词与骈文一概而论:
客亦未知开府《哀江南》一赋、仆射在“河北”诸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前此史迁、班椽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而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上下古今,如刘勰、阮孝绪以暨马贵与、郑夹漈诸家胪载文体,仅部族其大略耳,至所以为文不在此间。鸿文巨轴固与造化有关,下而谰语卮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辄也。[7](上册,P54)
这段文字的基本立论是“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中心在后半句。每一种文学体式就如人一样有不同的艺术特点,是不应该将之分高下的。徐庾骈文较之《史记》《汉书》更得《庄》《骚》遗韵,苏轼、辛弃疾词无事不可入,不逊于杜甫之“诗史”。由此来看,作文的初心是相通的,表达方式则是不同的,此观点与《今文选序》大致相同。在此基础上,陈维崧主张打破刘勰《文心雕龙》、阮孝绪《七录》、马端临《文献通考》和郑樵《通志》中文体分类无“词”之定式。“鸿文巨轴固与造化有关,下而谰语卮言,亦以精深自命”就是声明每一个文体自有它本身存在的价值,“鸿文”与“卮言”无形之间被拉到了同一个高度,共通点就是“精深”。“精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词并非轻易可完成的,需要精通,即创作主体需要苦心经营去钻研它。二是词本身所具备的“深”的艺术特质。不论是表达诗无法开辟出来的内心世界的隐秘忧思,还是继续在诗的抒情境界中捕捉曲折隐逸的情丝,抑或是开疆辟壤营造或是唤醒两性情味悠长的情感体验,词都具备了意内言外的双重性。词具备了和其他文体相同的可挖掘性和独异的艺术特质。因此,陈维崧又提出了“思”“气”“变”“通”四项对于创作主体倚声的基本要求,前两者是艺术论的角度,“通”是创作论的角度,“变”则是兼及创作论和鉴赏论两个角度,这是所有文体创作的共同点。总之,词与诗不具备地位孰高孰低的争辩,骈文与五经、史书也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只要以性情为本,苦心经营,即使表达方式有所差异,也仍是与“造化”相关的“精深”之作。一言以蔽之,词与经、史、诗有相等的文体地位。
陈维崧《今词苑序》中所体现出的“尊体”观念有两个特点。第一,《今词苑序》中骈文的援引仅仅作为词体“尊体”的借鉴与参照。明末文体地位低微的骈文在陈维崧的号召下得到了当时文人的注意与青睐,如毛际可所说:“昭代人文化成,骈体之工,无美不备。自陈检讨其年一出,觉此中别有天地。”[30](卷六,P790)吕双伟指出,康熙时期宜兴地区“俪体” 的相对盛行,无疑与陈维崧俪体文集的刊行与成就的召唤有关[28]。陈维崧想要将骈文领域的经验转移至词领域,因此《今词苑序》中并没有凸显出词与骈文过多的相似性,而是将两种文体置于同样的、被鄙弃的地位,以骈文文体地位的上升提升词体“尊体”的可行性,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比附。第二,正是由于陈维崧的策略是强调词体与经、史等文体既有创作根本的相通,又具备艺术特质的独异,因此《今词苑序》的词体观建构打破了以往以词比附诗的逻辑怪圈。明末清初的词学家往往以“诗余”为切入点,将词作为诗的一脉传承或者功能上的补充物,甚至建构词统序列,以此抬高词的文体地位,如王士禛《倚声初集序》中所言:“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31](P164)阳羡派另一代表词人任绳隗在康熙六年(1667)所作《学文堂词选序》也说:“夫诗之为骚,骚之为乐府,乐府之为长短歌、为五七言古、为律为绝,而至于为诗余,此正补古人之所谓备也,而不得谓词劣于诗也。”[32](P576)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比附于诗的最终效果仅仅会让词得到一个等同或略低于诗的地位,只有在真正意义上探索到词与《五经》的共通点才能获得“为经为史,曰词曰诗”的地位。不破不立,不从根本上破除词比附诗的逼仄路径,是无法真正令词取得极高的文体地位的。陈维崧骈文领域的经验与超越卓绝的文学视野让他的《今词苑序》成为清代词体文学“尊体”理论体系中一面最为鲜明的旗帜。
四 总 结
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一年(1661—1672)是陈维崧词体创作的中期,是他词体创作的转变期。《乌丝词》的刊刻发行标志着陈维崧词风转变的开始。康熙五年(1666)的“广陵唱和”促进了他在词作中抒情方式的转变,自我意识更为凸显,以议论与直抒胸臆取代了传统诗歌中借助意象寄托情志的婉转抒情手法,表达出的情感更为豪宕狂放。在北京、中州之行中,陈维崧开始逐步创新倚声技法,包括词作中添入大量奇诡怪诞的意象、创作对话体词和叠韵联章体词以及有意使用重字,形成了话语上与众不同之特色,这是他后期词体创作重要的前提。陈维崧在创作中期词体观的自觉是相对落后于倚声实践的,但依然能够从中看到一条理论渐趋成熟的清晰脉络,康熙十年(1671)所作《今词苑序》中“为经为史”观念是词体观的核心命题,是他词体创作转向后期的旗帜。由此可见,艺术风格的创新既是理论架构的必要条件,又是理论指导后的必然结果。康熙十二年至十四年(1673—1675)陈维崧无一首诗作,康熙十五年至十六年(1676—1677)共作诗13首。陈维崧自中州返乡后,全身心投入词体创作,用词体唱和的方式将徐喈凤、史惟圆、曹亮武、任绳隗、董元恺、储福宗等一批词人拉入创作阵营,既而形成“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9)此命题由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卷八中首次提出,严迪昌将之用于阳羡词派的评价。见严迪昌著《清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1页。,整体创作风格如山呼海啸、凄苍清狂的阳羡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