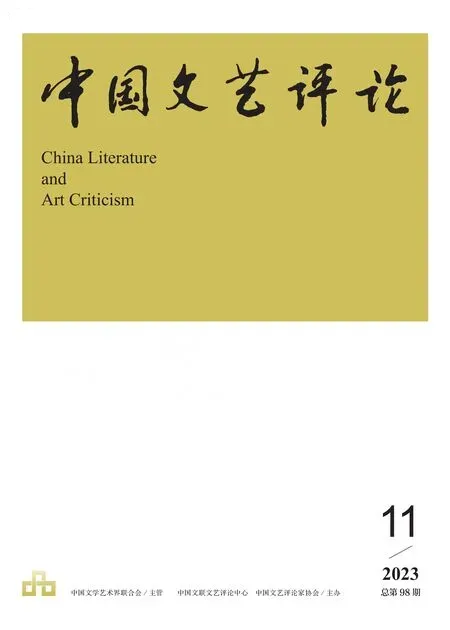浅析朗诵艺术的仪式性表达
2023-03-21■李艳
■ 李 艳
朗诵艺术的文献记载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可将“诵”理解为读,随着历朝历代的发展,朗诵的含义逐步扩展,在近现代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被确定下来。朗诵是相对于朗读而言的一种舞台表现形式,朗诵者在舞台上需要有腔调、有感情、有声调、会背诵,其创作过程中可以加入音乐、化妆、服装、肢体语言、舞台效果等多种视听艺术元素。[1]参见高原:《朗诵的“前世今生”:朗诵词义的历史变迁探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第161—162页。随着时代的发展,朗诵艺术的表现方式更加丰富多样,人们欣赏朗诵艺术作品时不仅能够从感官上得到身心的愉悦,更能给人以无限的憧憬,勾起人们感恩、崇敬、怀念等复杂的情感。符·阿克肖诺夫在对朗诵艺术本质进行探讨时认为,朗诵艺术是戏剧艺术的变体,主要表现在使用更接近自然的、口语化的舞台语言。[2]参见[苏]符·阿克肖诺夫:《朗诵艺术》,齐越、崔玉陵译,北京:广播出版社,1984年,第4页。在他看来,朗诵艺术源于戏剧艺术,但是朗诵艺术更加强调对语言文字的再创作。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朗诵艺术会通古今、融贯中外,已成为当今重要的语言艺术表达形态之一。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培育时代新人、促进国家文化繁荣[1]参见吴岩:《积势蓄势谋势 识变应变求变——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第9页。,也对当今的朗诵艺术提出新要求。这也意味着对新时代朗诵艺术的解读需要融入新的视角,促进朗诵艺术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发展。面对朗诵艺术表达中出现的思维定式问题,需要通过多元视角打破旧有的、僵化的理念。为此,本文重新思考朗诵艺术的源流、表征,从仪式性的角度出发,并对朗诵艺术的仪式性进行思辨分析,希望能为朗诵艺术的新文科建设提供思路。
一、巫术与传播:朗诵艺术仪式性的成因
朗诵作为源远流长的语言艺术之一,往往与诗歌相伴而生,我国的诗歌历史可以追溯到《诗经》,那时的诗歌是唱出来的,所以在当时人们所认知的朗诵更加偏向“吟诵”的范畴。[2]参见冯媛媛:《舞台朗诵艺术的审美意蕴探析》,《新闻界》2014年第6期,第70页。关于朗诵艺术的起源,虽众说纷纭,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艺术的起源学中得到启发,将朗诵艺术的起源回溯到史前文明。通过对朗诵艺术的深耕发现朗诵艺术具有较强的仪式性,从巫术起源开始到传播的仪式观都可以发现朗诵艺术仪式性的踪影。
(一)仪式与巫术:朗诵艺术的源流新解
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就曾提出过“巫术说”的观点,他们认为早期造型艺术、原始歌舞等艺术形式都与巫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3]参见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32页。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最早提出了“巫术说”的观点,他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方式是“万物有灵”,世间万物都能够与人产生交感。[4]参见[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13—415页。这种交感是源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并通过仪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巫术与艺术之间具有强烈的相似性与接近性,巫术活动中也经常能看到舞蹈、唱歌、绘画和造型等艺术表现形式。[5]参见[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王至元、陈华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7页。因此,在艺术表现过程中,“仪式性”作为一种隐匿的属性潜藏于各个艺术形式中。朗诵艺术的仪式性也不例外,朗诵者居于特定的场所,有腔调、有感情地将文学作品通过语言艺术表现出来,形成具有较强表演性、观赏性、宣传性等特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以仪式性引发文学作品与观众的情感共鸣。
当我们从“巫术说”的角度出发,也许可以将朗诵艺术追溯到原始社会。在那时朗诵艺术表现在贯通神与人界限的“巫师”身上,其目的是为了完成某项仪式、祷告天地,希望来年能够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巫师的角色身份会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进步而发生变化,原始社会中的祭司、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君主,都可以认为是巫师这一角色的代言体。这一代言体往往被人为赋予了沟通天地的职能,且具有较强的仪式色彩。《礼记·祭统》也记载了“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602页。,由此阐明了祭祀礼仪对于管理百姓、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也说明在我国进入文明阶段后,原始社会的祭祀宗教仪式活动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我国的祭祀礼仪往往还与“乐”相伴而生,如《礼记·乐记》所言“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2]同上,第1530页。。并且我国古代的祭典用以奉天地、祖宗、先王之德,沟通神人两界,必须献祭献乐,以求礼乐中和。[3]参见王志峰:《祭祀·仪礼·戏剧:中国民间祭祀戏剧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第37页。中国古代君主也有封禅的传统,这也是在礼乐中和的背景下诞生的一种传统祭祀仪式。《管子·封禅》中记载无怀氏(中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成汤、周成王都曾有封禅的表述。[4]参见[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6页。因而古代君王祭祀时的场景便可以浮现于脑海中,以规范的礼仪、肃穆的形态、礼乐齐鸣向天地先贤祷告,以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其中向天地先贤祷告时朗诵的祭词,便可以将其归为官方正式场合下的朗诵表达。从君主主持祭祀活动来说,其明显带有强烈的宗教神秘色彩,其中祭祀祝祷时的朗诵行为更多偏向的是实用、功利属性,而不能完全地将其称之为朗诵艺术。
从实用性、神秘性以及宗教目的逐步发展为具有娱乐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艺术,是随着思维的逐步进化,对于超自然力量的认知发生变化,从而改进某些仪式、放弃某些仪式的过程。[5]参见[美]奥斯卡·G.布罗凯特、弗兰克林·J.希尔蒂:《世界戏剧史》上册,周靖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1—2页。因此,对朗诵历史发展的考察还需要转到艺术视角中,也许我国历史悠久的、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祭祀戏剧可以带给我们新的启发。祭祀戏剧是戏剧的主要分类之一,它区别于传统的观赏性戏剧,是一种对于神灵或祖先崇拜而赋予浓厚戏剧成分的祭祀活动。麻国钧曾就祭祀戏剧的概念进行探讨,他认为祭祀戏剧与传统戏曲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祭祀戏剧的表演以巫师作为主要的代言体,恪守仪式礼法,且不以娱人为主要目的,祭祀戏剧的演出空间往往围绕传统祭坛展开,并呈现出参与者观演不分的特性。[6]参见麻国钧:《中国传统戏剧的分类与戏曲剧种层次新论》,《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9—11页。代言体在表演祭祀戏剧时会产生明确的角色认知转变,他们从个人转变为所扮演的神灵角色,通过化妆造型、焚香沐浴等方式表现出对于祭祀戏剧表演时的尊敬。其中尊敬便是源于祭祀活动的礼仪与规范,而一系列的化妆造型、扮演神灵等行为也是艺术创作与想象力生发的过程,当面对观众进行超脱于独立个体的表演过程,便使得祭祀戏剧具备了审美娱乐功能。
朗诵艺术的发展便是一种在祭祀戏剧化的衍生中不断螺旋式地上升的过程,朗诵艺术发展至今,逐步舍弃了祭祀戏剧中的宗教神秘色彩,但其所蕴含的仪式性仍然保留其间。为了实现更好的演出效果,朗诵者在朗诵时会实现角色认知转变的过程,我既是我又是文章作者的代言体,为了更深刻地揣摩其中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需要通过朗诵者的声音语言与音乐、神态、动作相结合来完成二度创作。这种表演仪式性既包括肢体语言对于作品内容的表达,也包含了创作者的内心认同。角色身份的转化是对于创作者、作品、作品的背景等内容的敬重,同时也是为了能够用语言使观众内心泛起对文学作品的涟漪。尤其是朗诵赞颂革命先烈、缅怀抗战烈士、团结奋斗力量等作品时,朗诵者内心必然要经历某种“仪式”。这也意味着朗诵艺术的表达实现了对于祭祀戏剧的嬗变,将仪式性赋予了时代价值与意义,使得朗诵艺术既表现出了祭祀戏剧的传统又具有相对独立性。
(二)仪式与传播:朗诵艺术的社会意义
朗诵艺术一定是为了追求某种传播效果,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诚然,朗诵艺术的表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内心的情感,同时也能让人们在朗诵者的表达中体会文学作品的意蕴。然而,朗诵艺术的背后还表现出通过仪式起到不断维系社会纽带的作用。詹姆斯·凯瑞曾提出过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这两个对于传播的定义。前者主要是源于地理和运输上的隐喻,把信息传给他人,“以达到控制空间和人的目的(有时也出于宗教的目的),更远、更快地扩散(spread)、传送(transmit)、撒播(disseminate)知识、思想和信息”[1][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页。。传播的传递观认为传播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效果,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这种传播行为或方式究竟会对受众(接受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凯瑞看来,传播的过程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某种效果,还存在某种意义。因此,他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信息在空间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指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2]同上,第18页。。传播的仪式观强调的不是所谓信息对于个人的控制或影响,而是强调个人获取这些信息时所产生的满足感以及文化共享,通过某一团体组织把人们召集起来,共同实现信息的交流。当我们在观看朗诵艺术时,一系列精彩的语言艺术表演不仅仅能够为个体带来思想观念的冲击,更在于朗诵艺术活动让以社会关系联结的人在同一时空下共同感受文学作品的魅力这一重要作用。当观众观看朗诵作品时,是以朗诵者的表述参与到文学作品中的。观众并非仅仅通过欢呼、掌声来表达自己对于朗诵作品的喜爱程度,其间还反映了文学作品、朗诵者、观众三者的互动过程。观众无论是无动于衷,还是真情流露,都满足了传播仪式观中以参与者的身份参与到朗诵艺术作品的共情之中。
此外,传播的仪式观也贯穿于朗诵者的前期准备过程。前期的准备活动也称“备稿”,它是让朗诵者从文学作品中来、再到文学作品中去的过程,这种活动过程本身就是具有仪式性的。朗诵者从作品中独立吸收内容的过程能够带来满足感,这是由于对文艺作品的整体把握而产生的。有学者指出,这种满足感不是因为获得了什么,而是源自连续性、重复性的实践所形成的一套固定模式。[1]参见冯梦瑶:《“传播”与“仪式”如何相遇:詹姆斯·凯瑞传播思想的宗教视角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3期,第34页。这里所指的满足感并不是认为朗诵艺术的备稿是没有意义的,仅仅是一种程序化的产物,而是揭示了广义备稿的意义。文学作品的数量是庞杂的、多元的,朗诵者在初次拿到稿件时很难完全把握其中的所有内容,因此会运用过去已有的一些知识去解析文本并重构大致的作品表达样态,这与满足感的形成有异曲同工之处。当大致掌握了朗诵艺术作品的表达时,后续面临的狭义备稿则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学作品的认知程度提高后所进行的具体把握。
凯瑞也对传播进行了定义,他认为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ed)、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改造(transformed)的符号化过程。[2]参见[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页。这意味着传播是一个符号互动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功能构建的方式。[3]参见刘建明:《“传播的仪式观”的理论突破、局限和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16页。在朗诵艺术的表达过程中,朗诵者通过声音、动作、神态等表现方式阐述文学作品的深层次内涵,这本身不具有特别的意义,更多是一种人体的运动,但是正因与人类社会相连接才令这些行为变得具有特殊的情感和意义,才能促使仪式性的表达。朗诵艺术的仪式性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的双向互动过程。这也解释了朗诵艺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认知下缘何表达会呈现出差异的问题,正是由于内心对于文学作品仪式性的感知不同所带来的结果。同样地,对于朗诵艺术的评价不同,也是对个体而言的符号互动的差异。当然,朗诵艺术是与社会连接后所形成的艺术表达形态,也具有明显的时间偏向性。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会倾向于表达不同主题的文学作品,这既与文学作品的写作背景有关系,也与朗诵的时代背景有关联。在二度创作过程中促成了文学作品与当下社会关系的联结,说明了朗诵艺术的仪式性赋予了表达的时代意义。
在传播过程中,朗诵艺术的仪式性在于将混乱无序的表达向结构化、系统化转变,这在朗诵艺术的教学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仪式性的产生会让朗诵者过度依赖外部技巧(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的运用,但仍然需要注意对稿件作品深层次的理解以及对内部技巧(情景再现、内在语、对象感)的使用,如此才能进一步提高朗诵艺术作品的艺术表现能力。
二、外在与内在:朗诵艺术仪式性的表征
朗诵艺术仪式性的产生与社会相连接,并且具有特定的符号互动功能。同时,朗诵艺术的仪式性也是以文学作品为核心的内外兼修的产物,它不仅体现在朗诵者的造型、表达、妆容、动作、神态、语音面貌和舞台设计等外在因素上,也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写作创作背景与朗诵者的内心世界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认识、态度,以及朗诵者所处的社会背景、社会节日氛围等隐含的内在因素上,这些都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朗诵艺术的效果。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之间相互交融,最终为朗诵艺术作品服务,以达到感染人的目的。
(一)外在因素:多元交感与融合
朗诵艺术的各种外在因素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内部的传播过程,这一传播过程是多元的、融合的,并最终以舞台的形式传递给观众。朗诵者的服装、道具、动作等外部表现方式的核心都是为文学作品本身服务的,同时也是仪式性的重要表现方式。在朗诵艺术表达的过程中,朗诵者好似扮演了一个角色,为了进一步符合角色的身份,通过各种造型以使外在层面与作品不断通感。此外,当朗诵者并非一人(对诵或集体朗诵)时,仪式性的表现方式也会有所差异。朗诵者之间的交感会更为频繁,包括表达的作品分配、声音艺术设计、服装间的配合、手势动作、眼神间的互动等,这些都是表达仪式性的重要方式,仪式性正是在一系列舞台内部的传播过程中逐一展开的。此外,朗诵作品的呈现方式因舞台技术的发展而逐步提升了外在因素的表现力,并通过各种技术的融合增强了朗诵艺术仪式性的张力,电子显示屏、灯光、音乐音响、麦克风等也都增强了朗诵艺术表达的创造力和创新性。
仪式性还会随着媒介空间的拓展而发生变化。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当下,朗诵艺术的形态出现了线上线下共同发力,直播、录播相结合的表现方式。无论形态发生何种改变,都需要以舞台作为传达朗诵艺术作品的支点。对于舞台的理解需要通过多角度观察,舞台不再是过去单一的、传统的形式,而是一个具有多元艺术综合的表现形态。它变成了由朗诵者把控并以作品为核心的“场”,此时除了需要考虑舞台技术因素对仪式性的影响外,还需要了解其媒介传播方式及表现形态。线下的朗诵艺术创作是常规的、传统的朗诵表现形式,也是仪式性体现的重要方式之一,此时观众观看朗诵艺术作品往往会受限于座位、视野等因素,这也导致了观众的参与方式更多是与稿件的共鸣。当朗诵艺术在新媒体平台上线时,直播与录播的媒介形态差异则会使朗诵艺术仪式性程度发生变化。当直播时,朗诵者不仅仅担任着艺术创作者的角色,也兼具作品传达与介绍、直播内容把控、与用户互动等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朗诵者与观众之间是一个近距离的交感过程,朗诵者的表达也会因观众的互动而产生内在因素的变化,因时长所带来的生理状态的差异等因素,使得朗诵艺术的仪式性发生波动性变化。在录播时,朗诵者需要意识到视听语言的运用对朗诵艺术表达的影响,构图、镜头语言、蒙太奇等都会改变朗诵艺术作品仪式性的体现,同时现场环境也将影响朗诵者自身对仪式性的感悟。
(二)内在因素:社会认同与感知
除了语音面貌等外在因素以外,朗诵艺术的呈现效果差异大多源于朗诵者自身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程度和对社会认知程度的差异。朗诵艺术表达的内在因素是否会存在仪式性,或者说朗诵艺术的表达有没有在心理上产生对于作品的理解、尊重与认同,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目前,为了实现更好的朗诵艺术效果,越来越多的朗诵者开始执着于对外在因素进行巧妙的加工,以期能够呈现更佳的视觉效果和感官效果。但是朗诵艺术的重心不能仅仅放在外在因素上,优秀的朗诵艺术作品是内外兼修的结果,当朗诵者忽视了内在因素的仪式性就会导致作品只有技巧、没有灵魂。
朗诵艺术内在因素的仪式性主要体现在朗诵者与文学作品的符号互动中。实际上在朗诵艺术的表达过程中会产生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既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对出现或不出现的人物的认可,也表明了朗诵者能够通过身份认同感知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并与之产生联系。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主要包括四大类,分别是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1]参见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第37页。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上述四类身份认同方式会差异化出现,并影响着朗诵艺术仪式性的产生。这种身份认同是朗诵者在二度创作前、初步接受文学作品时,由自身的认知结构和认知框架所决定的。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2]E.Goffman, 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p.21.这也使得过去的生活经验会影响到朗诵者前期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认知。
在朗诵艺术表演时,朗诵者需要赋予文学作品中出现或不出现的人物以灵魂。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作是作者笔下所描绘的社会中的人,人物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社会化互动的过程,从而综合把握住人物的主我(i)与客我(me)的关系。米德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主我”是有机体对其他人的态度作出的反应;“客我”是一个人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3]参见[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霍桂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当我们在把握朗诵人物时,忽视了主我与客我间的关系,仅仅认知人物其中一面就会导致人物表达得不完善,人物性格不够饱满。因此,有必要对主我与客我进行分析,有效探讨人物的社会互动关系与社会互动过程,深入了解人物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当然,朗诵者作为社会的一员,也不能仅仅考虑文学作品的社会环境因素,还需要注意到文学作品、朗诵者、观众三者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朗诵艺术表达的初衷。
三、悦己与悦人:朗诵艺术仪式性的辨析
朗诵艺术仪式性的诞生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下逐步规范化而形成的,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朗诵艺术仪式性是以朗诵者为核心的艺术表现行为。在探讨时不能将仪式性看得非常狭隘,或通过各种条条框框将其定义,说明什么情况是满足了仪式性的要求,又或是不满足的情况有哪些,这些都丧失了朗诵艺术的本真。朗诵艺术的仪式性是在悦己与悦人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一旦脱离了朗诵艺术纯粹的目的,那么仪式性就变得毫无意义。
(一)悦己:朗诵者的精神解放
朗诵艺术的仪式性并非要求朗诵者约束自身,实则是朗诵者自身的精神解放活动,是具有仪式性的。在舞台上,朗诵者就是把控舞台的人,同样也是可以突破自我的人。朗诵者在表达文学作品时,既是作者的代理人,也是作者笔下人物的代言人,其言行举止已经不再是以个人名义发出的,而是在继承了作者和作者笔下人物的精神意志之后实现的自我人格的解放。马尔库塞曾言:“美学形式是一个既不受现实的压抑,也无须理会现实禁忌的全新的领域。它所描绘的人的形象和自然的形象,是不受压抑性的现实原则的规范和拘束的,而是真正致力于追求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甚至不惜以死为代价。”[1][英]布莱恩·麦基编:《思想家:与十五位杰出思想家的对话》,周穗明、翁寒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3—74页。当朗诵者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深入分析,深层次地进行不受压抑的精神解放活动,完完全全地将自我投入到文学作品中时,这种潜意识的行为所具备的仪式性,往往才是朗诵艺术仪式性的本真。
朗诵者的精神解放同时具有复杂性的一面。朗诵艺术对于朗诵者而言是非功利的精神解放活动,但是朗诵艺术的行为却会因为朗诵者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产生联结,无法跳脱出朗诵行为所带来的功利性。换句话说,朗诵者本身就是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矛盾结合体,朗诵者很难将这两者相互剥离。与其批判功利性、赞扬非功利性,不如辩证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结合朗诵艺术仪式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来看,其中既包含了更好地实现朗诵艺术呈现效果的功利性的一面,又包含了朗诵艺术与文学作品之间纯粹的精神交流的非功利性的一面。对于朗诵者而言,功利性与非功利性都是追求舞台上精神解放的方式,也都表明了朗诵艺术悦己的一面。
(二)悦人:观众的艺术启迪
朗诵艺术仪式性的体现使得观众在观看艺术作品时具有较强的愉悦感,同时能够通过多种朗诵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了解文学作品所传达的意涵。在朗诵艺术的表达中,悦人并非只与朗诵的艺术表达行为有关,还包括对文学作品的印象与感知。观众在欣赏朗诵艺术作品时对艺术有了深入的体验,进一步了解了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意涵,同时也令自我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以及对美的感知。从艺术的功能而言,艺术兼具了认知、娱乐、教育功能,为观众构建了强有力的精神世界。仪式性既能通过表面的设计赋予其意义,又能因朗诵者的思想境界对其予以把控,可谓是内外兼修的产物。观众在观看朗诵艺术作品时,不仅仅通过外部设计对作品定调,同时也能通过自我的艺术感知能力为作品定性。在观看朗诵艺术作品时,对观众而言,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交流活动,同时也是一次回顾历史、回看先贤的时机。“艺术的交际——信息功能可以使人们交流思想,有可能使人们研究时代久远的历史经验和地理遥远的民族经验”[1][苏]鲍列夫:《美学》,乔修业、常谢枫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213页。,并逐步实现思想启迪,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朗诵艺术的仪式性看似是对观众的刻板规训,但是却在耳濡目染下实现了语言艺术教育。朗诵艺术的何种方式是可以被观众接受的,又是怎么呈现的,这都是教育的过程,通过印刻认知框架,将朗诵艺术的表达烙印于人们的内心深处。由于朗诵艺术是源于对语言的艺术化探讨,所以它能够用口述的方式传播优秀文学作品及其精神内核,实现群体意义上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诚然,现在越来越多的朗诵艺术作品希望从外在因素上打破传统朗诵艺术的枷锁,力求创新出现反仪式性的表现行为,但是其本质上仍然无法脱离朗诵艺术仪式性的范畴。情感的表达倘若没有深入到文学作品中,充分感受并尊重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仪式性的内在因素,那么就很难把握作品的内核,这样也就很难谈论朗诵者的表达是否可以归为艺术的范畴。因此,仪式性对于朗诵艺术而言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观众而言也是理解作品的重要表现手段与艺术启迪方式。
结语
笔者通过综合多元的学术体系对朗诵艺术进行探讨后,发现仪式性作为重要的纽带贯穿于朗诵艺术表现行为中。从巫术起源说到传播仪式观,从仪式性的艺术表征到符号互动论,都能够说明朗诵艺术所蕴藏的仪式性色彩。朗诵艺术的仪式性研究是从另一个视角去发现朗诵艺术的理论意义与价值,并且明确了朗诵艺术的本质是悦己与悦人的结合体。朗诵艺术的仪式性表达,拉近了文学作品与朗诵者、观众之间的距离,让文学作品不再是普通人难以琢磨的“空中楼阁”“镜花水月”,从而让文学作品有迹可循。文学作品也为朗诵艺术加持,成为其仪式性表达的灵魂。[2]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吴文璟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