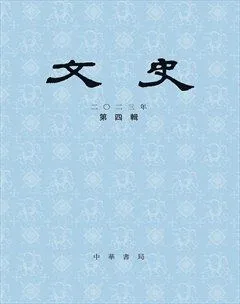六朝南方“俚”“獠”的書寫變遷史
2023-03-17張兢兢
提要:六朝政權對南方地區統治的推進,改變了華夏士人對南方土著族群的認知,
“蠻”“越”概念的縮小與“俚”“獠”概念的擴大,是最爲顯著的現象。三國時代隨着吴蜀政權對南方邊地的開拓,“俚”始見於嶺南的西江流域,“獠”始見於嶺南西部與南中東部相連區域,與“夷獠”同義,皆屬專稱。在最初的華夏識别者眼中,“俚”與“獠”的地域文化特徵存在明顯的差異性,是兩種狹義族類。東晉南朝對嶺南統治的深化,使嶺南地區的族群分類獲得較爲清晰的界定,主體族群“俚”遍布嶺南,仍是專稱。與此同時,獠人入蜀後巴蜀統治的弱化,模糊了華夏知識界對“獠”概念的認知。“獠”之布滿巴蜀者爲泛稱,見於嶺南西部者爲專稱;“俚獠”遍及嶺南,與“俚”同義;“夷獠”之稱泛於西南、中南廣大地區,逐漸成爲南方蠻、俚、獠等族群新的總稱。從“百越”“南蠻”到“夷獠”,南方土著族群主要泛稱的書寫轉换,也揭示了南方華夏化運動由長江中下游地區向西、向南滲透的基本方向。關鍵詞:六朝 嶺南 巴蜀 俚 獠
秦漢以降,“蠻”除了廣義地指代南方土著族群,逐漸縮小範圍,狹義地專指長江中游流域的諸蠻群體;同時“越”亦作爲南方土著族群的泛稱外,概念也漸次壓縮,至漢末局促於長江下游的揚州地區,即所謂“山越”。這種族類觀的演變,是華夏政權對南方土著社會認識加深的結果。無論“蠻”還是“越”,皆未形成明確的族群邊界和族群認同,與其糾纏於類似
“山越”族屬問題的争論,毋寧回歸歷史文本的形成與書寫之中,。
(1) 重新認識這些族群的内涵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古南方邊地族群變遷與國家治理研究”(20CZS024)階段性成果。
(1)“蠻”“越”概念書寫的代表性研究,參吕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3期,2005年,第 1—26頁;呂春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 2006年,第 29— 56頁;魯西奇《釋“蠻”》,《文史》 2008年第 3輯,第 55— 75頁;魯西奇《“越”與“百越”:歷史叙述中的中國南方“古族”》,《東吴歷史學報》第 32期,2014年,第 1—63頁;羅新《王化與山險 —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歷史研究》 2009年第 2期,第 4— 20頁。
立國江南的孫吴政權苦心經營山越與武陵蠻的同時推進了對嶺南邊地的統治,割據巴蜀的蜀漢政權亦加强了對南中邊地的控制,促使南方地區的族群分類發生重大變化,其標誌是“俚”和“獠”的出現。“俚”“獠”雖爲漢語文獻中的稱謂,但按照現代語言學和民族學的研究,可能都源自相應人群自稱的音譯(1),並非完全出自華夏知識界的憑空演繹。然而中古史籍有關
“俚”“獠”的各種叙述顯得雜亂難理,尤其是二者的關係晦暗不明,則表明當時族類識别的限度。遲至南宋時居嶺南多年的周去非對“俚”“獠”的認識尚較有限,他在《嶺外代答》中稱:“俚人,史稱俚獠者是也。此種自蠻峒出居,專事妖怪,若禽獸然,語音尤不可曉。 ”(2)陳寅恪進一步推論:“凡史籍之止言獠或夷獠聯文,而屬於梁益地域者,蓋獠之專名初義。伯起書之所謂獠,當即指此。至屬於廣越諸州範圍,有所謂獠,或以夷獠俚獠等連綴爲詞者,當即伯起書之俚也。”(3)陳氏以空間界定人群,將《魏書·司馬叡傳》列舉的南方各種人中之“俚”對應嶺南、“獠”對應巴蜀。此説深刻影響了後來學界對六朝“俚”“獠”關係的認識(4),但其未注意到族類與地域的聯繫常隨時間推移而變遷,稽諸史籍,其説不盡爲然。
“俚”“獠”進入正史之前,散見於類書中所存六朝地記。這些早期“俚”“獠”史料雖然大都爲已散佚文獻的片段,且限於不同作者的主觀因素,很難説在同一時代一定對某些族類概念形成共識;但經全面梳理,並比對稍後成書的相關正史,綜合分析後,仍可發現:
(1)民族史學界從民族語音角度解釋“俚”“獠”,一般認爲二者同出“越”語族群的自稱,參白耀天《“俚”論》,《廣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 2期,第 52— 64頁;李艷峰、王興宇《中國古代僚人研究的回顧和反思》,《思想戰綫》 2012年第 6期,第 105—106頁。有學者甚至以爲“俚”“獠”語音相似,可能是相互關聯的族群,參[加]蒲立本著,游汝傑譯《上古時代的華夏人和鄰族》,《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 1輯,1998年,第 356頁。這類研究主要采用現代壯侗語音參照古漢語音對接越語音的方法,前提必須是越語在分化演變爲壯侗語的漫長過程中變化不大,其研究理路缺乏一定的文獻支撑,這樣的結論存有疑問。中古漢語文獻並非嚴格按照現代語言學、民族學規範來記録這些人群,即使可以從語言學、民族學方面采集到一些客觀特徵作出“分類—溯源”式的界定,也未必能真實反映當時史家的族類認知。而且同樣是使用這種民族溯源法考察“獠”的源流,在民族史學界還有“獠爲濮説”“獠爲巴説”的不同觀點,參田曙嵐《論濮、僚與仡佬的相互關係》,《思想戰綫》 1980年第 4期,第 33— 44頁;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論》,《四川大學學報》 1959年第 2期,第 33— 34頁。因爲在這種研究範式中,不同的研究者可能側重强調的文化特徵不一,所對接的族群便會發生偏差,難以取得較爲一致的意見。
(2)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卷三《外國門下》,中華書局,1999年,第 144頁。(3)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金明館叢稿初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年,第 89頁。(4)其後涉及這一問題的有:芮逸夫《僚人考》,《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2年,第 249— 292頁;徐恒
彬《俚人及其銅鼓考》,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編《古代銅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年,第 152— 158頁;張雄《六朝以來嶺南“俚”人的若干問題》,《廣西民族研究》 1985年第 1期,第 7— 16頁;覃聖敏《秦至南朝時期嶺南民族及民族關係芻議》,《廣西民族研究》 1987年第 1期,第 51—60頁;白耀天《“俚”論(續)》,《廣西民族研究》 1990年第 4期,第 28—38頁。這些研究對陳寅恪的觀點或同意或反駁,總體上囿於民族史學分類溯源的範式,對於史料的搜集考證與文本的解釋分析不足。 1990年代以後,相對於“蠻”“越”研究不斷取得突破而言,“俚”“獠”研究停留在傳統範式徘徊不前,二者的内涵與外延、分布與變遷成爲長期無法解決的難題。
如以“獠人入蜀”事件爲轉折,將六朝南方“俚”“獠”的書寫變遷史分爲兩個階段,前期與後期的叙述整體呈現出不同面貌。本文擬在陳寅恪觀點的基礎上,從族類觀念的視角對錯綜複雜的“俚”“獠”關係新作思考。
一、魏晉文獻對“俚”“獠”的早期記載
成書於三國以前的文獻裏,尚無“俚”“獠”的記載。如單看文獻内容,被認爲是“俚”之早期稱謂的“里”,最初見於記載中的東漢。《後漢書·南蠻列傳》云:“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内屬,封爲歸漢里君。”(1)按同書《光武帝紀》稱封爲歸漢里君的是“九真徼外蠻夷張遊”(2),所書當即一事。《後漢書》在稱述嶺南土著人群時使用更多的是
“蠻夷”一詞,且書中“蠻夷”還常被用來指稱長江中上游的蠻區人群。一般認爲,《南蠻列傳》將“蠻”劃分爲槃瓠、廩君、板楯三大系統,然而在該傳中,范曄加入了嶺南諸郡蠻夷,且置於槃瓠之後、廩君之前,實際上構成了“蠻”的另一系統。所以李賢在“九真徼外蠻里張游”文下注:“里,蠻之別號,今呼爲俚人。”(3)李賢認爲“里”在東漢尚屬“蠻之别號”,是對范曄所劃譜系作出的合理解釋。值得注意的是,長江中上游諸“蠻”在《後漢書》成書以前的東漢魏晉史籍中慣稱“某某蠻夷”(4),即使是後來采用了“某某蠻”稱謂的范曄,有時也仍沿用“某某蠻夷”之稱(5),表明其史料文本來源的複雜性。這反映出在東漢時代,長江中上游與嶺南地區的“蠻夷”並無後世那樣嚴格的族群分類,范曄之所以混用了單名“蠻”,恐怕是雜入了南朝時人的觀念。那麽,從《南蠻列傳》的書寫範式來看,很難説東漢時代已將
“里”當作嶺南族類專稱來使用,甚至長江中上游區域亦未形成單名“蠻”的族類專稱,他們這時仍都被視爲屬於南方族群泛稱的“蠻”“蠻夷”之支系。“俚”始見於《南州異物志》(6),《隋書·經籍志》稱此書爲“吴丹陽太守萬震撰”(7)。關於
(1)《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 2836頁。(2)《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第 60頁。(3)《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列傳》李賢注,第 2837頁。(4)參吕春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第 45—46頁。
(5)《後漢書》中“某某蠻”的表述雖多,亦常有如“武陵蠻夷”“五溪蠻夷”“武谿蠻夷”“長沙武陵蠻夷”“南郡蠻夷”“板楯蠻夷”“荆、交二州蠻夷”等稱謂,凡涉直接或間接引述前人言語、文字時,惟見“某某蠻夷”而不見“某某蠻”的表達。(6)參段公路《北户録》卷二《蕹菜》引《南州異物志》,中華書局, 1985年,第 32頁;《太平御覽》卷四九二《人事部一三三》“貪”條、卷七八五《四夷部六·南蠻一》“俚”條、卷九九〇《藥部七》“冶葛”條引《南州異物志》,中華書局, 1960年,第
2250頁下欄、3478頁下欄、4381頁下欄 — 4382頁上欄。(7)《隋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三三《經籍志二》,中華書局,2019年,第 1112頁。
《南州異物志》的成書時間,學界看法不同。向達提出:“按孫權黄武、黄龍時屢耀兵海外,比之明代,約同成祖永樂之時。又丹陽太守在黄武初爲吕範,至嘉禾三年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自吕範至諸葛恪中間相隔十餘年,未聞他人繼範爲丹陽太守者。疑萬震之爲丹陽太守,即在吕範之後諸葛恪之前,正當海外征伐甚盛之際。震在丹陽,接近國都,見聞較近,故有《南州異物志》之作,以志殊方異俗。 ”(1)而譚其驤依據《太平御覽》卷七八五引《南州異物志》所云“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之文,認爲:
按寧浦郡本吴合浦北部都尉,晉太康七年改郡,見《宋書 ·州郡志》。吴又有高興(熙)郡,太康中省併高涼,見宋志、晉志。引文言廣州南五郡無高興而有寧浦,乃西晉太康以後郡制,是萬震雖仕吴爲丹陽太守,其書則成於西晉。(2)
按《宋書·州郡志》“廣州寧浦太守”條云: “《廣州記》,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鬱林立,治平山縣。《吴録》,孫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爲合浦北部尉,領平山、興道、寧浦三縣。”(3)則寧浦郡初置於建安二十三年(218),至遲廢於永安三年(260)之前,而太康七年(286)復置。又吴高興(熙)郡約置於孫皓初年(4),故永安前“廣州南五郡無高興而有寧浦”非不可能,蓋《南州異物志》所言不必是“西晉太康以後郡制”。蓋吴世兩置廣州,首置之廣州僅存於黄武五年(226)當年(5),復置之廣州存在自永安七年(264)至吴亡(6),則廣州領有寧浦郡或在黄武五年,或至太康七年以後。又《御覽》引文言廣州南五郡中合浦僅於黄武五年初置廣州時爲其屬郡(7),其後再未隸於廣州,可證引文所書非譚氏所稱太康以後郡制。綜合
(1)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叙録》,《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7年,第 568頁。(2)譚其驤《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 —附論梁隋間高涼洗夫人功業及隋唐高涼馮氏地方勢力》,《歷史研究》 1988年第 5期,第 11頁。(3)《宋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三八《州郡志四》,中華書局, 2018年,第 1305頁。王先謙以爲《廣州記》不足據,漢末無寧浦郡,乃晉初所置,李曉傑因之(參《東漢政區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9年,第 214頁)。然《舊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輿地紀勝》《記纂淵海》諸書均載吴置寧浦郡,確係建安二十三年所置(參胡阿祥、孔祥軍、徐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三國兩晉南朝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 546頁),則《廣州記》無誤。
(4)
高興(熙)置郡時間於史無載,吴增僅認爲《晉書·地理志》總序云歸命侯所置十二郡中宜都當爲高興之誤,高興郡置於
孫皓初年,陳健梅亦同此説,參《孫吴政區地理研究》,嶽麓書社,2008年,第 255頁。(5)《三國志》卷四七《吴書·吴主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 1133頁。(6)《三國志》卷四八《吴書·孫休傳》,第 1162頁。
(7)
《三國志》卷四九《吴書·士燮傳》云:“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吕岱爲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第 1193頁)則黄武五年初置廣州,領合浦以北諸郡,而交州領交阯以南諸郡。又同書卷六〇《吴書·吕岱傳》云:
“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 ”(第 1384—1385頁)“海南三郡”顯然是指交阯、九真、日南三郡,那麽與此對應的“海東四郡”當涵蓋南海、蒼梧、鬱林、合浦、高涼、寧浦六郡,因寧浦、高涼係孫權新置,“海東四郡”蓋言漢世舊郡,如此可與“七郡百蠻”之習稱交部舊郡數目相合。然則《晉書》卷一五《地理志下》“廣州”條云:“至吳黄武五年,(轉下頁)
上考,可將向氏推測的《南州異物志》成書時間黄武初至嘉禾三年(234),進一步鎖定在黄武五年孫吴滅士氏全控嶺南之際,“以志殊方異俗”。其後西晉張華《博物志》云: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即膨脹沸爛,須臾燋煎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治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他,以其食糞故也。燋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别燋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偏鑿取以爲箭鏑。(1)
孫吴西晉廣交二州“俚”的出現,意味着在華夏的認知中,嶺南土著族群開始與長江流域狹義的“蠻”“越”族群相分離,漸成爲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族群。譚其驤指出:“秦、漢時南越國人即俚人,而俚之所以不見於《史》《漢》者,以其時中原人與俚相處猶暫,未嘗熟知其種族名,故率以泛指南人之‘蠻‘越稱之也。”(2)然則《三國志》中亦未見到“俚”稱,惟有“高涼宿賊”“鬱林夷賊”“蒼梧建陵賊”“交阯九真夷賊”等,可見“俚”作爲嶺南特定族類的專稱,在《三國志》成書的西晉時代尚不明確。但交廣諸郡的“夷賊”之别於揚州“山越”、荆州“蠻夷”,在陳壽看來則是確鑿無疑的(3),華夏政權在與嶺南土著的激烈衝突中,正在更新族類認知。
南方邊地另一土著族群“獠”,如從文獻内容看,最早見於記載中的西漢。《後漢書·西南夷列傳》云:“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 ”(4)李賢注稱此段前後所記夜郎之文多見於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該書云:“後夷濮阻城,咸怨訴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 ”(5)“濮”與“獠”的關係雖然在民族史學界分歧很大(6),但二者在
《華陽國志》中分别出現多次,明顯被視作不同的族類,且各自帶有特殊的專名,如永昌郡
(接上頁)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爲廣州,俄復舊。”(中華書局, 1974年,第 466頁)蓋《晉志》將“海東四郡”當作吴世四郡,而以同在海東的合浦、寧浦二郡爲交州屬郡,如此則與《三國志》明言交州分領“交阯以南”“海南三郡”之語相抵牾。陳健梅以爲《晉志》誤永安七年復置之廣州轄境爲黄武五年初置之廣州轄境(參《孫吴政區地理研究》,第 235頁),當是。胡阿祥等采用《晉志》之説(參《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三國兩晉南朝卷》,第 557頁),誤也。故黄武五年之廣州界域,當從《士燮傳》與《吕岱傳》記載。
(1)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卷二《異俗》,中華書局,1980年,第 25頁。(2)譚其驤《粤東初民考》,《長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259頁。
(3)《三國志》記載中,“山越”分布地區不出揚州轄域,“蠻夷”除仍用作泛稱外爲孫吴荆州與蜀漢益州所獨有,“夷賊”則被
專用於交廣二州。(4)《後漢書》卷八六《西南夷列傳》,第 2844頁。(5)常璩著,任乃强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四《南中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 230頁。(6)李艷峰《中國濮人研究的學術史考察》,《楚雄師範學院學報》 2020年第 4期,第 75— 76頁。
“有閩濮、鳩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1)。范曄將“夷濮”改爲“夷獠”,是南朝“獠”稱泛化
所致(詳下文),而非常璩、更非西漢時人的認識。
從成書時間看,“獠”與“俚”的出現大致同時,《南州異物志》云:“獠民亦謂文身國,
刻其胷前,作華文以爲飾。”(2)按其書所述皆嶺南之事,則此處之獠民當在交廣二州境内。
郭義恭《廣志》云:“獠在.
柯、興古、鬱林、交阯、蒼梧,皆以朱漆皮爲兜鍪。 ”(3)據王利
華考證,該書雖成於北魏前中期,然書中地名以漢晉地名占絶大多數,就其資料來源而言,
實際上是匯抄漢晉文獻分類編排而成的,且基本來自西晉及其以前的文獻(4)。又興古郡始
置於蜀漢建興三年(225)(5),則此條史料反映的當是三國西晉時人的認識。那麽,可知“獠”
的蹤迹不止於孫吴嶺南西部,還出現在相鄰的蜀漢南中東部,且南中之“獠”更多地見於隨
後的西晉史籍,係蜀漢開拓南中的發現。
《永昌郡傳》云:“獠民喜食人,以爲至珍美,不自食其種類也。怨仇,乃相害食耳。能
水中潛行,行數十里。能水底持刀刺捕取魚。其人以口嚼食,並以鼻飲水。死人有棺,其葬,豎棺埋之。 ”(6)該書作者無考,方國瑜認爲:“從所載爲南中七郡事,可知作於蜀漢建興三年(公元 225年)以後;而未見晉寧、興寧、河陽、建都、梁水、南廣諸郡名,則應在晉太康(安)二年(公元 303年)之前;故疑爲蜀漢、西晉時人所作。 ”(7)又同書云:“興古郡,在建寧南八百里,郡領九縣。 ”(8)興古郡蜀漢領八縣,入晉後至太康三年(282)增至十二縣(9),則此
書當成於西晉泰始元年(266)至太康三年之間。
西晉陳壽《益部耆舊傳》云:“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内
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10)蜀漢加强支配南中土著人群,用以補充蜀中匱乏的兵源,在
此背景下,南中之“獠”遂爲華夏所識。
《博物志》云:“荆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姙娠七月而産。臨水生兒,便置
水中。浮則取養之,沈便棄之,然千百多浮。既長,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爲身飾。 ”(11)劉琳
(1)《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四《南中志》,第 285頁。(2)《太平御覽》卷三七一《人事部一二》“胷”條引《南州異物志》,第 1708頁上欄。(3)《太平御覽》卷三五六《兵部八七》“兜鍪”條引《廣志》,第 1638頁上欄。(4)王利華《郭義恭〈廣志〉成書年代考證》,《文史》 1999年第 3輯,中華書局,第 151頁。(5)《三國志》卷三三《蜀書·後主傳》,第 894頁。
(6)
《太平御覽》卷七九六《四夷部一七·西戎五》“獠”條引《永昌郡傳》,第 3534頁下欄。(7)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 1卷,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 325頁。
(8)
《太平御覽》卷七九一《四夷部一二·南蠻七》“朱提”條引《永昌郡傳》,第 3509頁上欄。(9)胡阿祥、孔祥軍、徐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三國兩晉南朝卷》,第 479、674頁。(10)《三國志》卷四三《蜀書·張嶷傳》裴松之注引《益部耆舊傳》,第 1052頁。(11)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卷二《異俗》,第 24頁。
指出“荆州極西南界至蜀”之間正是牂牁之地(1),那麽此處所述當爲牂牁獠人。然則《太平御覽》所引該書此段文字不同於其他各本:“蜀郡諸山夷名曰獠子,婦人姙身七月,生時必須臨水。兒生,便置水中,浮即養之,沉便遂棄也。至長,皆拔去其上齒、後狗牙各一,以爲身飾。”(2)蒙默認爲各本俱不如《御覽》所引更足信據,而以此作爲獠人入蜀之前蜀地本有獠人的證據,並指出巴蜀土著獠人實際上就是賨人與濮人,引文中的蜀郡“獠子”當即居於蜀郡之“賨”(3)。按晚至隋以後成書的《蜀郡記》云:“諸山夷獠子任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兒出,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沉乃棄之。 ”(4)此段内容顯係抄自《博物志》,似乎印證了蒙氏所稱
《御覽》引文更加可信。但問題在於,包括“賨”在内的西南非華夏族群之泛稱爲“獠”,蓋成漢之世獠人入蜀勢力坐大後産生的現象(詳下考)。生活在魏晉之際的張華不應以“獠”指“賨”,同時期文獻中巴蜀之獠,唯見蜀漢政權所徙數量不多的南中獠人,則《博物志》所記蜀郡之獠,亦恐來自牂牁等地。又按記載魏晉獠人分布在牂牁、興古、鬱林、交阯、蒼梧等地的《廣志》也稱:“獠民皆七月生。 ”(5)而賨人不見有此特徵,可證張華所謂蜀郡“獠子”與南中之獠確屬同類。
秦漢帝國雖然統一了蠻越之地,但華夏政權在南方的統治,不過是沿主要的水陸交通綫建立了一些疏落的據點而已,郡縣政區較爲疏闊,土著人群居住的廣大山區幾乎還都是統治的空白。因此,創業江南的孫吳政權與偏據巴蜀的蜀漢政權都面臨疆土狹小和編户稀少的困境,爲增加財賦收入與壯大軍事力量以抗衡北方强大的曹魏政權,於是大力拓殖南方山地和人口資源。三國西晉之際,嶺南、南中等地“俚”與“獠”概念的誕生,意味着華夏統治向南方邊地的滲透,從而加快了對南方族類的識别和建構。
二、嶺南地區的“俚”“獠”關係
嶺南之“俚”與“獠”從一開始就區别爲不同的人群,並列出現在《南州異物志》中,因而萬震所謂“獠”非“俚”甚明。又前引《廣志》中的“獠”分布於南中與嶺南相連的五郡之地,按“俚”從未見於南中,則牂牁、興古之“獠”當即爲“獠”本身,那麽與之連帶叙述並
(1)劉琳《僚人入蜀考》,《中國史研究》 1980年第 2期,第 121頁。(2)《太平御覽》卷三六一《人事部二》“産”條引《博物志》,第 1664頁下欄。(3)蒙默《“蜀本無僚”辨》,《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 3期,第 38— 40頁。
(4)《太平御覽》卷三六〇《人事部一》“孕”條引《蜀郡記》,第 1659頁下欄。《蜀郡記》作者不詳,《隋書·經籍志》不見著
録,劉緯毅以爲隋人作,參《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 360頁,蓋其成書不早於隋。(5)《太平御覽》卷三六一《人事部二》“産”條引《廣志》,第 1663頁下欄。
具有相同形象特徵的鬱林、交阯、蒼梧之“獠”亦非指“俚”。又《博物志》所記“銅鏑”“毒箭”之俚俗,爲獠俗所無;而《永昌郡傳》所載“食人”“豎棺”之獠俗,不見於俚俗(1)。顯然,在三國西晉時代最初的華夏識别者眼中,“獠”不同於“俚”。
“俚”“獠”文化特徵有别,在嶺南的地域分布也參差不一。前引《南州異物志》云:“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 ”則俚人在吴世的活動範圍覆蓋了整個西江流域,多集中於廣州南部的西江南岸區域。又按
《博物志》所載,及至西晉交州土著亦稱俚人。而據《廣志》可知,嶺南獠人於吴晉之世出現在蒼梧、鬱林、交阯三郡,大體上沿西江—鬱江與紅河沿綫活動。蓋孫吴西晉時代廣州俚、獠皆分布於西江流域,俚人多居西江流域南部,獠人多居西江流域北部與西部;交州俚人遍及全境,獠人集中在交州北部的交阯地區。
東晉南朝嶺南“俚”稱漸多,有布滿交廣之勢,而單名“獠”者依然少見,仍可與“俚”區别開來。《南齊書·張融傳》云:“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2)按食人非俚俗,可證此“獠賊”非俚人。又《隋書·地理志》云:
“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爲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爲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别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3)及至隋世嶺南土著漸染華風已久,“俚人”與“諸獠”風俗趨同,但仍將二者分開並列稱述,可知確非同類。綜上所考,六朝交廣之單名“獠”者,絶非陳寅恪所謂之“俚”,而理應同於“獠”之專名初義。
嶺南地區在六朝時代形成了以“俚”爲主體、間雜“蠻”“獠”的族類結構,三者的族群邊界大體分明:俚人遍及嶺南而分布重心一直在西江流域(4),蠻人僅見於嶺南北部的南嶺山區(5),獠人如前所述在嶺南西部毗鄰南中一帶。衆所周知,東晉南朝南方土著族群的主
(1)俚、獠文化習俗之異同比較,參芮逸夫《僚人考》,《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第 281—282頁。(2)《南齊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四一《張融傳》,中華書局,2017年,第 803頁。(3)《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第 999頁。
(4)孫吴廣州南五郡的西江俚人發展至梁陳時代,形成了以高涼洗氏“世爲南越首領”的大規模部落聯盟,“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參《隋書》卷八〇《譙國夫人傳》,第 2025頁)。而西江督護正是南朝政府爲專事伐俚而設,參《南齊書》卷一四《州郡志上》,第 292頁。
(5)南嶺東部的始興郡是所見蠻人活動的最南界,《宋書》卷九二《徐谿傳》載始興太守徐谿上表曰:“既遏接蠻、俚,去就益易”,“中宿縣俚民課銀”,“山俚愚怯”(第 2488— 2489頁)。《梁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一三《范雲傳》稱始興郡“邊帶蠻俚,尤多盜賊”(中華書局, 2020年,第 258頁)。又同書卷三二《蘭欽傳》云:“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又破天漆蠻帥晚時得。”(第 516頁)可以推斷,始興郡的“蠻俚”連詞非一般性泛稱,蓋“蠻”與“俚”之組合,表明始興郡處於長江中游蠻區與嶺南俚區的交匯帶。
體是蠻、俚、獠(1)。相對於“蠻”“獠”而言,“俚”的分布是最清晰的,始終作爲嶺南的族類專稱而不變,主要原因在於五嶺以南在地理上自成一區,而六朝政權對嶺南的開發是一以貫之的,尤其到了南朝後期嶺南與建康之間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2)。嶺南地區華夏統治的深化,是族群分類趨於細化的前提。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嶺南地區自晉宋之際開始出現“俚獠”合稱之勢,裴淵《廣州記》云:“俚獠鑄銅爲鼓,鼓唯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 ”(3)裴淵生平無考,清人王謨認爲大抵是晉宋間人(4)。按同書云:“興寧縣,義熙四年,忽有數十大鳥,大如鶖,少焉,化爲虎。”(5)其書當成於東晉義熙四年(408)之後。又該書多次提到蒼梧鄣平縣(6),而鄣平縣不見於《永初郡國志》(7),則其書又應成於劉宋永初二年(421)之前。那麽,《廣州記》的成書時間可確定在晉宋之際。其後,“俚獠”連用之語見諸南朝正史。
《宋書·杜慧度傳》云:“循雖敗,餘黨猶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遜子李弈、李脱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 ”(8)而《資治通鑑》載此事云:“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脱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9)顯然,《通鑑》此處“俚獠”與《杜慧度傳》中的“諸俚”同義,非“俚”與
“獠”,則點校本《宋書》不當點斷“俚獠”連稱,當作“盤結俚獠”,實指俚人。又《宋書·羊希傳》云:“時龍驤將軍陳伯紹率軍伐俚,還擊思道,定之。”(10)陳伯紹在合浦地區伐俚後奏立越州。而《南齊書·州郡志》“越州”條云:“元徽二年,以伯紹爲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爲城門,威服俚獠。”(11)則又以“俚獠”指稱“俚”。那麽可證,南朝交廣之地頻見的“俚獠”,即陳寅恪所謂之“俚”。蓋“俚獠”聯詞中的“獠”,已非“獠”之專名初義,而“獠”的泛化,又與
(1)朱大渭《南朝少數民族概況及其與漢族的融合》,《中國史研究》 1980年第 1期,第 57頁。(2)劉希爲、劉磐修《六朝時期嶺南地區的開發》,《中國史研究》 1991年第 1期,第 3—13頁。(3)《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李賢注引《廣州記》,第 841頁。(4)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中華書局,1961年,第 370頁下欄。(5)《太平御覽》卷八九二《獸部四》“虎”條引《廣州記》,第 3960頁下欄。(6)參《藝文類聚》卷八《山部下》“交廣諸山”條引《廣州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第 147頁;《太平御覽》卷九八五
《藥部二》“丹”條、卷九八九《藥部六》“麥門冬”“當歸”“續斷”條引《廣州記》,第 4361頁下欄、4375頁上欄、4377頁下
欄、4378頁上欄。(7)《宋書》卷三八《州郡志四》,第 1293頁。(8)《宋書》卷九二《杜慧度傳》,第 2486頁。(9)《資治通鑑》卷一一六,晉安帝義熙七年,中華書局,1956年,第 3645頁。(10)《宋書》卷五四《羊希傳》,第 1678頁。(11)《南齊書》卷一四《州郡志上》,第 298頁。
成漢之世的“獠人入蜀”事件密切相關。
三、獠人入蜀與“獠”概念的擴散
獠人入蜀之前,最初出現於三國西晉史籍中的梁益之獠與交廣之獠,分布在南中與嶺南接壤區域,具有區別於俚人的地域文化特徵,同屬“獠”之專名初義。有關“獠人入蜀”一事,始見於蕭梁李膺《益州記》:“蓋李雄據蜀,李壽從牂柯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爲獠居,臨邛舊縣因兹置。”(1)《水經注·漾水》記載略同,並説明入蜀獠人之居處:“所在諸郡,布滿山谷。”(2)南宋郭允蹈《蜀鑑》亦同李膺之説,且進一步明確李壽引獠入蜀的時間在東晉建元元年(343)(3)。然則對入蜀獠人是否來自牂牁,唐人賈耽《四夷縣道記》有不同説法:“至李特孫壽時,有羣獠十餘萬從南越入蜀漢閒,散居山谷,因流布在此地,後遂爲獠所據。”(4)按南越之地本有獠人,多在嶺南西部,與南中東部牂牁等地相鄰,則當李壽引獠入蜀之時,南越之獠經南中與牂牁獠同入蜀地,非不可能。
成漢末年,匯聚巴蜀的獠人從山而出,對郡縣統治構成巨大威脅。《北史·獠傳》云:
“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爲益州大患。勢内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5)獠人入蜀與蜀人外遷逆轉了蜀地華夏與非華夏的力量對比,桓温平蜀後東晉政府無法遏制獠人勢力的極速擴張。及至東晉後期,荆州刺史殷仲堪上書稱:“巴、宕二郡爲羣獠所覆,城邑空虚,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謬,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 ”(6)據《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諸地志所載,成漢以至東晉,巴蜀郡縣爲獠人所没者甚多,從而導致華夏編民的鋭減與巴蜀獠人的繁殖。從漢魏之世的“沃野天府”,到晉宋之世的“蠻夷孔熾”(7),華夏政權對巴蜀地區的統治面臨嚴重危機。
南北朝時代獠人幾乎遍及全蜀,以西晉太康政區爲限,梁、益各郡在獠人入蜀後俱有
(1)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卷七五《劍南西道四》“蜀州江原縣”條引《益州記》,中華書局, 2007年,第
1530頁。(2)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二〇《漾水》,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 1722頁。(3)郭允蹈著,趙炳清校注《蜀鑑校注》卷四《李壽縱獠於蜀》,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 113頁。(4)《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九《山南西道七》“巴州”條引《四夷縣道記》,第 2703頁。(5)《北史》卷九五《獠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 3155頁。(6)《晉書》卷八四《殷仲堪傳》,第 2195頁。(7)《南齊書》卷一五《州郡志下》,第 332頁。
獠人分布(1)。據蒙文通的推算,劉宋大明時蜀中 35郡僅 5.6萬餘户,略當西晉太康時的 1/4;
而入蜀獠人自成漢末的 10萬餘落增長至北魏末的 40萬户(2)。如按陳寅恪的判斷,遍布梁
益區域如此龐大數量的獠人,即是魏晉之際出没於南中與嶺南相鄰數郡之一隅並及徙至蜀
中甚少數量的“獠”之專名初義,從人口學的角度似乎難以解釋。
馬長壽的看法則與此不同:“自 4世紀時僚之名一出,且其種類蔓延四川各地,此名遂衍爲四川蠻族之總稱。……蕭齊之世,凡非漢族之在蜀境者皆設僚郡。如越巂僚郡(今西昌一帶)、沈黎僚郡(今漢源縣)、東宕僚郡(今合川武勝等地)、甘松僚郡(今松潘一帶)、始平僚郡(今昭化以西一帶)等名,於是羅番、氐、羌、戎、賨諸族皆爲僚矣。寖假一般中國人之觀念以爲四川境内之人皆爲僚人。……當時蜀之中,固有僚,然不盡爲僚。而史書則混稱之曰‘僚。於是僚之名以泛。 ”(3)吕春盛贊同此説,認爲“獠”概念的大幅擴散是入蜀獠人勢力坐大所産生之新的族群認識,西南地區其他非華夏人群在華夏士人的認知中多被納入“獠”的範疇,遂使獠人演變成爲西南土著族群的一種泛稱(4)。相比之下,馬氏提出的這一觀
點,更能得到史料的證實。
巴蜀東北部的巴西至漢中一帶,獠人入蜀前原爲板楯蠻人活動區域。文獻記載中的
巴西獠人始見於兩晉之際郭璞之言:“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
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 ”(5)獠人入蜀之前,除上述蜀郡、漢中徙入
少量南中獠人以外,巴西地區並不見有獠人的活動。考此故事最早出自東漢應劭《風俗通
義》:“閬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鋭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鋭,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 ”(6)蜀
漢譙周《三巴記》亦稱居閬中渝水的是賨人(7),即板楯蠻。此説後經《後漢書·南蠻列傳》
采用,而廣爲人知。因此晉人郭璞所謂巴西獠人,實即漢魏時代的巴西板楯蠻。但記載郭
璞此語的裴駰《史記集解》成書年代遲至劉宋之世,此時巴西之地已爲北上入蜀的獠人侵
居,裴駰用“獠”替“賨”,正表明了當時的巴西蠻區有泛化稱“獠”的跡象。
文獻記載中的漢中獠人初見於蜀漢之世,《水經注·沔水上》云:“沔水又東逕西樂城
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諸葛亮築以
(1)張兢兢《晉隋間巴蜀僚人的華夏化 —基於政區與户口視角的討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 3
期,第 192頁。
(2)蒙文通《漢、唐間蜀境之民族移徙與户口升降》,《南方民族考古》第 3輯,1991年,第 169頁。
(3)馬長壽著,周偉洲編《四川古代民族歷史考證》,《馬長壽民族學論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84頁。
(4)吕春盛《魏晉南北朝時代的“獠族”與西南土著社會的變遷》,《成大歷史學報》第 35號,2008年,第 66頁。
(5)《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裴駰《集解》,中華書局,2014年,第 3683— 3684頁。
(6)蕭統編,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四《蜀都賦》李善注引《風俗通義》,中華書局,2012年,第 93頁下欄。
(7)《藝文類聚》卷四三《樂部三》“舞”條引《三巴記》,第 768頁。
防遏。”(1)據蒙默考證,諸葛亮在漢中築城防獠事在《益部耆舊傳》所記張嶷徙牂牁、興古獠於漢中之前,則其所防備之山谷群獠實爲漢初北遷漢中的巴西板楯蠻(2)。又漢末以降,巴西板楯蠻不斷北徙,至南北朝漢中盆地成爲其主要聚居地(3)。而《水經注》成書的北魏後期,獠人勢力也已擴展到巴漢地區,並在南北戰争中成爲影響漢中局勢的關鍵因素,甚爲北魏政權所重視(4)。《魏書》始設《獠傳》,專門記載巴漢獠人(5),當是此故。酈道元以“賨”爲“獠”,意味着漢中蠻區亦有泛化稱“獠”之勢。
由於板楯蠻人與華夏帝國接觸較早,早在東漢政府通過印綬的授予,華夏式官僚秩序已經滲透進了蠻人社會(6),蠻人君長逐漸成長爲地方豪族(7)。南北朝時代帶有蠻類背景的巴獠酋豪“嚴、蒲、何、楊”,無不出自漢晉以來的當地大姓(8),他們頗受華夏文化之薰染,“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9),與《周書·獠傳》所見
“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的獠類迥然有別(10)。因此,梁益域内之“獠”,並非陳寅恪所謂“獠”之專名初義所能包涵者。即如蕭齊所置五獠郡,亦多屬泛化層面之獠區。巴蜀北部的甘松獠郡領蠶陵一縣(11),
《元和志》劍南道“翼州”條云:“梁太清中,武陵王蕭紀於蠶陵舊縣置鐵州,尋廢。周武帝天和元年討蠶陵羌,又於七頃山下置翼州,以翼針水爲名。”(12)則蠶陵縣入梁後廢,甘松獠郡疑没於獠,北周在蠶陵故地開置翼州,李吉甫謂討蠶陵羌而置,却不言獠。按岷江上游歷世
(1)《水經注疏》卷二七《沔水上》,第 2302頁。(2)蒙默《“蜀本無僚”辨》,《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1983年第 3期,第 40頁。(3)吕一飛《板楯蠻略論》,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6年,第 232—
237頁。
(4)參《北史》卷九五《獠傳》:“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衆屯孝子谷,祉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後以元法僧代傅豎眼爲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梁兵,圍逼晉壽。……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始欣)據城南叛。梁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第 3155— 3156頁。
(5)《魏書·獠傳》早亡,今本以《北史·獠傳》補而删去魏以後事。(6)胡鴻《六朝時期的華夏網絡與山地族群 —以長江中游地區爲中心》,《歷史研究》 2016年第 5期,第 34頁。(7)中村威也《中国古代西南地域の異民族 —特に後漢巴郡における「民」と「夷」について》,《中国史學》第 10卷,
2000年,第 204— 205頁。(8)嚴、蒲二氏是閬中縣大姓,參《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一《巴志》,第 46頁;又嚴、楊二氏作爲閬中縣大姓,何、楊二氏作爲
充國縣大姓,參洪适《隸釋》卷五《張納碑陰》,影印洪氏晦木齋刻本,中華書局,1985年,第 63頁。(9)《魏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六五《邢巒傳》,中華書局,2017年,第 1568頁。(10)《周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四九《獠傳》,中華書局,2022年,第 968頁。(11)胡阿祥、孔祥軍、徐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三國兩晉南朝卷》,第 1130頁。(12)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二《劍南道中》,中華書局,1983年,第 813頁。
爲羌人居住區域,蜀漢時諸葛亮從南中遷群獠於青城山下(1),此後至隋其間除齊世短暫置有獠郡外,未見獠人蹤迹,蓋甘松之地冠以“獠”名實是泛稱。又同卷“真州雞川縣”條云:
“右昭德等三縣,並在州側近,以熟羌首領爲其令長,居無常所。”(2)而《舊唐書·地理志》“劍南道”條却稱雞川、昭德二縣“開生獠新置”(3)。按二縣所屬翼州乃蠶陵羌區,故此所謂“生獠”亦爲泛稱無疑,也表明在唐代産生了新的族群認知。
巴蜀西南部的越巂、沈黎二獠郡之地,唐代遍設羈縻州,雅州“都督一十九州,並生羌、生獠羈縻州,無州縣”;黎州“統制五十四州,皆徼外生獠。無州,羈縻而已”(4);巂州亦領諸蠻十六羈縻州(5)。據郭聲波考證,唐代巂屬羈縻州的主要族群是蠻,黎屬羈縻州的族群由羌、蠻、獠三種構成,其中烏蠻是這一地區的主體族群,而每一族群又可分爲若干部族、部落,其衆之雜難以言狀(6)。則新舊《唐書·地理志》所謂“生羌”“生獠”“諸蠻”“諸羌”仍是泛稱,然較蕭齊俱以“獠”稱,認識逐漸加深。歷史書寫中晉唐間“獠”概念的擴散與收縮,取決於華夏士人對西南土著社會的認知,認知的變遷又緣於現實世界中巴蜀地區華夏統治的衰退與强化。綜上所考,南北朝梁益之“獠”,實爲西南非華夏人群之泛稱,至唐範圍漸次壓縮(7)。
“夷獠”一詞,始見於西晉史籍中的梁益地區。《三國志·霍弋傳》云:“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静。”(8)此永昌“夷獠”當即同時期《永昌郡傳》中之“獠”,亦類於同出陳壽筆下鄰郡牂牁、興古之“獠”。
《漢中記》云:“秦白起嘗爲漢中太守,築此城以控制夷獠。 ”(9)該書作者無考,據張保見考證,成於魏末晉初(10)。然同書云:“本西鄉縣治也。自成固南城南入三百八十里,距南
(1)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五一《成都府路》“永康軍”條引《圖經》,影印岑氏懼盈齋本,中華書局,1992年,第 4067頁。(2)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二《劍南道中》,第 820頁。(3)《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四》,中華書局,1975年,第 1689頁。(4)《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四》,第 1683—1684頁。(5)《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中華書局,1975年,第 1138—1139頁。(6)郭聲波《彝族地區歷史地理研究 —以唐代烏蠻等族羈縻州爲中心》,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 431頁。
(7)唐代巴蜀族群面貌呈現出多樣性的同時,對“獠”本身的識别與分類更趨細化。《元和郡縣圖志》中有“犵獠”“戎獠”
(第 750、790頁)。《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平獠傳》出現了“南平獠”“飛頭獠”“烏武獠”“葛獠”等各具鮮明文化特徵的獠人群體(第 6325—6329頁)。儘管唐代巴蜀地區作爲泛稱的“獠”繼續存在,但同時形成多種專名的“獠”使用更多。
(8)《三國志》卷四一《蜀書·霍弋傳》,第 1008頁。(9)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九〇《利州路》“洋州”條引《漢中記》,第 4915頁。(10)張保見《樂史〈太平寰宇記〉的文獻學價值與地位研究 —以引書考索爲中心》,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 389頁。
鄭四百八十里。 ”(1)西鄉縣,按《宋書·州郡志》“梁州漢中太守”條云:“西鄉令,蜀立曰南鄉,晉武帝太康二年更名。”(2)又《漢中記》云:“興道有七女池。 ”(3)興道縣,按《晉書·地理志》“梁州”條屬漢中郡(4),成漢李雄時已省(5)。那麽據此,《漢中記》的成書時間不應在魏晉之際,而當爲西晉太康二年(281)至建興二年(314)李雄克漢中之間。按其時早於獠人入蜀,“獠”之名未泛,漢中僅有蜀漢張嶷所徙之牂牁、興古“獠”。陳寅恪在考察魏晉南北朝種族問題時,注意到一個現象:“一個種族在某地居住過,後來就把某地居民一律説是某族人。”(6)蓋《漢中記》成書之時距張嶷徙獠事已過去半個多世紀,疑是作者誤以漢中之獠爲先秦以來世居此地的土著。當然,亦有可能因後世“獠”概念擴散的影響,致使文獻在傳播中被改動。
獠人入蜀前,交廣域内未見“夷獠”之稱,則上述僅見於梁益地區之“夷獠”,應屬陳寅恪所謂“獠”之專名初義。而獠人入蜀後隨着“獠”的泛化,“夷獠”之名且更泛之,南北朝以降蔓於交廣湘等中南地區。《南齊書·州郡志》“越州”條云:“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賓,略無編户。……元徽二年,以伯紹爲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爲城門,威服俚獠。”(7)這裏實指“俚”的“俚獠”略同於“夷獠”。又《梁書·蘭欽傳》云:“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8)而《陳書·歐陽頠傳》云:“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頠預其功。”(9)陳文徹一人身兼“俚帥”與“夷獠”兩種稱謂,則“俚”可用“夷獠”代指無疑。又《陳書·陳叔陵傳》云:“四年,遷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使持節如故。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暴横,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10)是以嶺北湘州蠻區亦稱“夷獠”。
“夷獠”之稱至唐代使用更加廣泛。《通典·州郡典》云:“嶺南五府經略使:綏静夷獠,統經略軍、清海軍、桂管經略使、容管經略使、鎮南經略使、邕管經略使。”(11)則嶺南土著盡以
(1)《水經注疏》卷二七《沔水上》引《漢中記》,第 2328— 2329頁。(2)《宋書》卷三七《州郡志三》,第 1244頁。(3)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八《山南西道六》“洋州興道縣”條引《漢中記》,第 2689頁。(4)《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第 436頁。(5)《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二《漢中志》,第 79頁。(6)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録》,黄山書社,1987年,第 93— 94頁。(7)《南齊書》卷一四《州郡志上》,第 297— 298頁。(8)《梁書》卷三二《蘭欽傳》,第 517頁。(9)《陳書》卷九《歐陽頠傳》,中華書局,1972年,第 157頁。(10)《陳書》卷三六《陳叔陵傳》,第 494頁。(11)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一七二《州郡典二》,中華書局,1988年,第 4483頁。
“夷獠”概之,相反“俚”稱鋭減(1)。唐代“俚”作爲族稱已甚少使用,而更多地用作形容下層民衆低俗文化的詞彙,如“俚語”“俚言”“俚歌”“儒而不俚”“俚室”(2)。這一變化當是南朝以來俚人漸次華夏化所致,至唐所見不多的俚人也基本上以帝國編戶民的身份出現,如
《舊唐書·劉延祐傳》云:“嶺南俚户,舊輸半課,及延祐到,遂勒全輸。”(3)則唐代嶺南俚民所承擔的賦役,漸同於一般的編户齊民。又《新唐書·韋宙傳》云:“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4)此處“俚民”的族群性已經不顯,而是側重説明其婚俗的落後不合“禮”。故在唐代,作爲人群稱謂的“俚”,多指不同程度接受華夏統治與教化的嶺南編户齊民;原居嶺南西部尚未華夏化的“獠”,自南朝開始從“俚獠”到“夷獠”,便逐漸被用以泛指那些遠離帝國郡縣體系、尚能保持自身社會結構的嶺南土著人群。
隨着長江中下游蠻、越的華夏化,西南、嶺南地區的“獠”成爲唐代南方境内經略的主要對象。唐太宗有詔曰:“若南方諸州,多統夷獠,官人於彼言語不通;里吏鄉首侵漁,匹庶不勝忿怨,挺刃相讎,因是叛亡,輕犯州縣,興兵討捕,即致傷殺。 ”(5)唐代頒布的賦役令中,也常常以南方“夷獠户”與北方“蕃胡户”並列對舉(6)。蓋南北朝至隋唐,“夷獠”之稱已非陳寅恪所謂屬之梁益者爲“獠”、屬之交廣者爲“俚”,而漸作爲涵蓋蠻、俚、獠等在内的南方諸土著族群之泛稱使用了(7)。
起自西南地區的“獠化”現象,可視爲戰國秦漢以來巴蜀華夏化的逆流,其時間影響乃下延至唐,郭允蹈稱:“蜀之衣冠,流徙荆湘,而名郡樂郊,皆爲獠居矣,至唐末而患猶未已也。文物之不逮於兩京,幾數百年,職此之由。自蜀通中國以來,得禍未有如是之酷且
(1)
《元和志·嶺南道》諸卷中,“俚”止一見,“獠”“夷獠”之謂多達八處,唐代嶺南各地獠亂持續不絶,俚亂則幾乎不見。(2)金裕哲《梁陳時代嶺南統治.種族問題—‘俚........—》,《東洋史學研究》第 76輯,2001年,第 93—
94頁。(3)《舊唐書》卷一九〇上《劉延祐傳》,第 4995頁。(4)《新唐書》卷一九七《韋宙傳》,第 5631頁。(5)《宋本册府元龜》卷一五七《帝王部》,中華書局,1989年,第 315頁上欄。(6)王義康《唐代“蕃族”賦役制度試探》,《民族研究》 2004年第 4期,第 65—71頁。
(7)
唐代“獠”稱的使用,還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成爲輕賤南人之詞(參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金明館叢稿初編》,第 89頁)。“獠”的污名化,當與西魏北周以來獠人的“賤隸化”有關。《周書》卷四九《獠傳》云:“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第 967頁)又《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云:“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役夷、獠,故輕爲姦藏,權傾州縣。”(第 925頁)華夏政權從“壓獠”戰争中所獲生口源源不斷地充爲官私奴婢,從京師到邊地官僚豪强擄掠奴役獠人之風盛行,大量獠口淪爲“賤隸”。“奴”的身份與形象,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了隋唐之世華夏社會對“獠”的普遍認知,又
“夷獠”之稱泛於南方,南人之被賤視爲“獠”“獠奴”,蓋由於此。關於唐代以後“俚”“獠”概念的新變化,擬另文詳述。
(1)
久也,可不鑑哉?”其空間影響則超出西南,波及中南大片區域,“獠”“夷獠”之泛濫遂不可止,一時間大有替代“蠻”“越”之勢,成爲南方非華夏人群新的總稱。另一方面,從“百越”“南蠻”到“夷獠”,南方土著族群主要泛稱的書寫轉换,也揭示了南方華夏化運動由長江中下游地區向西、向南推進的基本方向。
結 語
“俚”“獠”最早散見於魏晉之際的地記,相關文獻多殘存在各種類書與地志之中。通過考訂魏晉地記的成書時間,排比其内容的年代先後,能推知時人對“俚”“獠”人群書寫與認知的變化。再結合相關正史的記載,六朝時代“俚”“獠”二者概念的内涵與外延、分布與變遷以及相互間的關係演進,大略可見:三國時代隨着吴蜀政權對南方邊地的開拓,
“俚”始見於嶺南的西江流域,“獠”始見於嶺南西部與南中東部相連區域,與“夷獠”同義,皆屬專稱。東晉南朝對嶺南統治的深化,使嶺南地區的族群分類獲得較爲清晰的界定,主體族群“俚”遍布嶺南,仍是專稱。與此同時,獠人入蜀後巴蜀華夏統治的弱化,模糊了華夏政權對“獠”概念的認知,“獠”之布滿巴蜀者爲泛稱,見於嶺南西部者爲專稱;“俚獠”遍及嶺南,與“俚”同義;“夷獠”之稱泛於西南、中南廣大地區,逐漸成爲南方蠻、俚、獠等土著族群新的總稱。
(本文作者爲湖州師範學院人文學院、浙江師範大學邊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1)《蜀鑑校注》卷四《李壽縱獠於蜀》,第 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