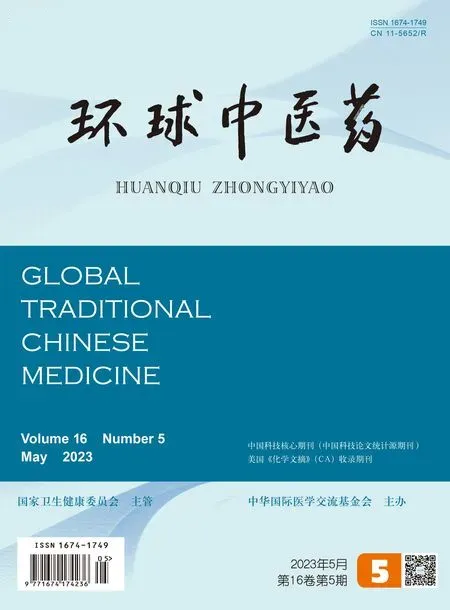基于“燥湿相济”浅析三消病机与治疗
2023-03-17王晨娄锡恩张丽萍周围王聪慧陈巧楠陶庆春
王晨 娄锡恩 张丽萍 周围 王聪慧 陈巧楠 陶庆春
中医将糖尿病归属于消渴病范畴,传统认为消渴病病机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根据消瘦、口干多饮、多食、多尿等,分为上中下三消论治。《素问·阴阳别论篇》中记有:“二阳结谓之消”,后王冰补注释文中解释二阳结,“谓胃与大肠俱热也,胃肠藏热,则喜消水谷[1]”。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候卷中提到:“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由少服五石诸丸散,积经年岁石势结受于肾中,使人下焦虚热。及至年衰,血气减少,不复能制受于石。石势独盛,则肾为之燥,故引水而不小便也[2]。”刘完素在《三消论》中亦表明消渴者乃燥热郁盛所成,热盛伤阴致消渴[3]。所以消渴病其病机多宗“阴虚燥热”。然而在临床中发现,消渴病患者阴虚火旺之象并不明显,多数体型偏胖,长期饮食不节制,损伤脾胃,脾虚则湿盛,见身体困重乏力,舌红苔白腻或黄腻。燥热这一病机又同时存在,故常见到燥湿并存之象,根据之前的思路单纯使用滋阴清热大法,疗效并不明显。故本文基于燥湿相济,针对上中下三消侧重不同提出辨治思路。
1 燥湿并存是消渴关键病机
燥与湿在中医基础理论分数阴阳水火对立,清代石寿棠首创“燥湿二气为百病纲领”,认为燥湿是百病发生的原因,其在《医原》中提出:“然天地之气,在于阴阳之气,即燥湿之气也”“往往始也病湿,继则湿又化燥……往往始也病燥,继则燥又夹湿”[4];清代周学海在《读医随笔》中提到“燥湿同形同病,燥极似湿,湿极似燥”[5],燥湿两邪可相杂共处,即如水火互济。《黄帝内经·气交变大论》[6]中对于五气的论述:湿为长夏主气,“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德溽蒸,其化丰备,其政安静,其令湿”湿邪易阻滞气机,郁滞日久则生燥热,燥性肃杀使阴气开始收敛而不外达,阴津输布失常,日久聚而成痰湿,终呈燥湿并存复杂局面。《灵枢·本藏》[6]曰:“脾脆,则善病消阐易伤。”中医认为消渴病病位在脾。且脾病多痰湿,正如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7]言:“内外所感,皆由脾胃虚弱而湿邪乘而袭之”。又《灵枢·五变》[6]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说明五脏脆弱者容易发生消瘅病,上中下三消之不同就在于脾湿夹肺燥、胃燥与肾燥。
1.1上消多属脾湿肺燥
上消以口渴多饮为主症,其病机可从脾湿肺燥论。《太平圣惠方·三消论》中记载:“热毒积聚于心肺……一则饮水多而小便少者,消渴也。”明代王肯堂于《证治准绳》中提到:“肺消者,多因心火乘肺伤其气血[8]。”清代陈复正《幼幼集成·消渴证治》[9]载:“消渴,由心火动而消上,上消乎心,移热于肺,渴饮茶水,饮水又渴,名曰上消。”心肝热炽,而肺为娇脏,火热之邪损伤肺阴,造成肺热津伤;肺主敷布津液,燥热之邪伤及肺腑,则津液不能正常敷布,常出现口舌干燥、口渴多饮、烦热多汗、舌红唇红、潮热盗汗。
临床发现糖尿病患者饮水后口渴仍不缓解,饮水过剩,超过脾胃运化之能,又易形成脾湿,痰湿上干于肺,出现口中甜腻,咳喘白黏痰,胸闷不舒,纳差脘痞等症状。燥邪郁滞水行不畅,日久生湿,湿郁久布津障碍,导致燥热再生,二者互相交叉并存,互为因果。清代沈金鳌治上消常用石膏、黄芩、白虎汤等方药,亦从侧面印证上消因于肺热,故治疗需清火润肺之品,恢复肺通调水道失常、津液失输之能[10]。
1.2中消多属脾湿胃燥
中消以多食易饥为主症,可从脾湿胃燥论。明代秦景明在《症因脉治·外感三消》[11]湿火三消篇中说:“酒湿水饮之热,积于其内……郁久成热,湿热转燥,则三消乃作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提到消渴与痰热及饮食密切相关,原文记载:“消渴病,其为病之肇端,皆膏粱肥甘之变……皆富贵人病之,而贫贱人少有也。”清代叶天士在《温热论》[12]一书中明确脾瘅舌象为苔白粘腻,是由湿热困脾而成。
长期饮食不节制,脾失运化,致痰湿困脾,出现肢倦体困,脘腹痞胀,神疲烦渴,便溏不爽。脾升胃降共同运纳,脾失健运日久则胃失纳降,脾为湿困,不能腐熟水谷,但胃有燥火,津液不能濡养,釜中无水,亦不能熟物。胃燥则见胃中灼热嘈杂,多食易饥,口干苦而黏,大便干结等症[13]。脾喜燥恶湿,脾湿赖胃阳运;胃喜润恶燥,胃阴赖脾湿濡,脾升胃降一旦失常,终成脾湿胃燥并存[14]。秦景明在《症因脉治·外感三消》[11]言“膏粱浓味,时积于中,积湿成热,熏于肺则成上消,伤于胃则成中消,流于下则成下消”,说明湿热聚于中焦日久,会上熏成肺热,下注成肾燥,导致上消与下消发生。张锡纯亦表明中焦脾胃是消渴病之关键,其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载滋膵饮和玉液汤用来治疗糖尿病[15]。
1.3下消多属脾湿肾燥
下消以尿频量多为主症[16],可从脾湿肾燥论。《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候》[2]:“下焦生热,热则肾燥,肾燥则渴,然肾虚又不能制水,故小便利。” 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中指出肥甘厚味过量、房事不节等致使人体受燥热之邪侵犯,五脏虚热内生,下焦虚热上泛则为肾消。北宋《圣济总录·久渴》[17]中:“论曰消渴之病,本于肾气不足,下焦虚热。”燥热之邪侵袭肾脏,肾不能摄纳真阳之火,浮越而外显为肾热。
先天肾精不足或者年少身体盛壮之时不知节制,极易伤肾,肾水竭,无法制约心火,日久必肾燥阴伤,症见面黑耳焦、饮一溲二、溲以淋浊,大便多秘,口渴索饮,若病久阴损及阳,阴阳两虚,出现腰膝酸软,小便清长量多,眩晕耳鸣,男子遗精,女子经少等症状,而肾固摄失司则精微物质随小便排出,可见尿如脂膏,尿中有泡沫,尿常规见尿糖、尿蛋白。“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邪重浊黏滞,胶着难化,本在中焦之脾湿未除,而病至下焦,湿邪仍存,致脾气更虚,“脾恶湿、肾恶燥”,由于水湿内聚,影响三焦的气化,津液不能正常敷布,而成“邪水”,以致面目浮肿,身肿。江丹将消渴肾病的治法概括为“温运太阴,温扶少阴”,曹子成使用滋肾阴润肾燥以摄浮火治疗此系疾病疗效显著[18]。
2 燥湿相济统筹治疗三消
无论消渴偏重上中下,其发病均与脾失运化有关, 脾之病变是消渴病发生的重点,健脾利湿,恢复脾胃运化需一直贯穿三消治疗,调整津液输布,改善代谢异常状况,清肺胃肾之燥热,可发挥标本兼治作用。
2.1清热润肺、滋肺脾胃之阴治疗上消
上消主要是火热之邪损伤肺阴,造成肺热津伤,肺为水之上源,敷布津液,肺受燥热所伤,则津液不能正常敷布,阴津耗伤更加不能敛阳,火热之象又加重,阴津亏损与燥热偏胜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土能伏火,无形之火为阳,有形之土为阴,清肺热滋肺加上滋脾阴可减轻上焦之火热。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6]中说的“少火生气,壮火食气”。糖尿病的“三多一少”症状明显是一种阳热的表现,风木与相火相煽于肺,则会出现口渴多饮,上焦火热型糖尿病的发生与肝气疏泄失常密不可分,《金匮要略》[19]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补脾后,脾气旺则肝不传脾,肝木疏泄正常,肝病好转自然无病传脾,故临床中应用滋脾胃阴法能够疏泄肝风,这从侧面说明滋脾阴可治疗上消。临床可以选用葛根、南北沙参、黄精、玉竹、石斛和麦冬等肺脾胃之阴同滋的中草药。值得注意的是若上消病变脾湿症状同时存在,要注意滋脾胃之阴药会有加重脾湿的可能,应根据阴虚与湿邪偏重选择药物使用或调整好药物比例。
2.2清胃热、化脾湿治疗中消
中消病位在中焦脾胃,胃火盛则多食、消谷易饥、口渴、小便多且黄、大便干燥。《素问·六微旨大论篇》[6]曰:“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足太阴与足阳明同居中土,燥湿相济,升降相依。壮火食气,胃火炽盛日久则脾气亏耗,脾气虚则湿邪易盛,出现脾虚湿盛之象,口渴引饮,多食与便溏并见,或纳呆、四肢乏力、面色萎黄。湿热困阻中焦会因湿与热偏重程度的差别而临床表现各异,湿重于热,病变偏于脾,若热重湿轻,病变偏于胃,胃强脾弱。当脾升胃降均正常时中焦运化方可正常,若胃气不降易出现中焦热象,脾气不升易出现水气聚集不输,故中消在泻火润燥的同时加用补脾土化脾湿之法,对于中焦土气的正常运化起到重要作用。且现代湿热蕴结的消渴越来越多发,临床中清胃热化脾湿结合西医降糖收效甚益。
2.3滋阴固肾、培补脾气治疗下消
下消病位在脾肾,肾阴虚应填补肾水,而阴阳互根,肾阳所化依赖肾水,若肾水不足或肾水寒则肾阳易外越,张景岳在《类经图翼》[20]大宝论中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说明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素问·水热穴论篇》[6]中:“肾者胃之关也。”肾阳充足,中焦阳气方可充足,只有脾胃正常运化水谷,肾水才能有所来源,故在治疗下消要同时温肾阳补肾水加之培补脾气升脾阳以祛脾湿,往往事半功倍。
3 基于燥湿相济三消分治常用药对
3.1上消:玉竹—北沙参润肺滋脾
玉竹养阴润燥,生津止渴,《中药大辞典》[21]中玉竹的记载,其主治“烦渴,虚劳发热,消渴善饥,小便频数。”可恰好对应消渴症状除之。玉竹入肺胃二经,可使津液生而燥热去,研究证明玉竹多糖具有明显降低血糖的作用[22]。沙参养阴清热,益胃生津,针对南北沙参不同,北沙参坚实,坚实者用于养阴,故针对上消常选用北沙参。清代严西亭在《得配本草》[23]记载北沙参“补阴以制阳,清金以滋水”,宜肺肾同治。临床发现玉竹养阴润燥更偏重生津止渴,北沙参入肺脾养阴而健脾补土,可更好滋生肺金,可标本虚实兼顾,两者合用,玉竹、北沙参各12 g为宜。
3.2中消:黄连—茯苓清热燥湿
黄连清热燥湿,泻火解毒,黄连主入中焦心胃,对于中消患者多食善饥症状效果较好,清代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24]认为提到:“黄连至苦,而反至寒,则得火之味,与水之性者也,故能除水火相乱之病。水火相乱者,湿热是也。”对于中焦脾胃湿热之消渴能较好的改善临床症状。研究表明小檗碱通过增加胰岛素受体表达、改善胰岛素抵抗、抑制蔗糖酶、麦芽糖酶等二糖酶的活性来降糖[25]。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清黄元御于《长沙药解》[26]中提到:“茯苓利水燥土,泻饮消痰,善安悸动,最豁郁满”,茯苓甘、淡,平,能通过健运脾肺利水,利水而不伤正。两者合用适用于胃燥脾湿之中消。若临床症状明显且血糖较高,应用西药降糖效果不理想时,黄连与茯苓可应用至30~60 g。
3.3下消:山茱萸—黄芪脾肾同调
山茱萸补益肝肾,收涩固脱,张锡纯曾言:“一味山茱萸,胜过人参当归”,山茱萸补肝肾之阴精,同时兼有固涩之功,下消久病肾失封藏固摄,可见精微物质随小便排出,尿如脂膏,山茱萸可改善“尿浊”。黄芪健脾补中,生津止渴,可用于气虚津亏,内热消渴,清·陈世铎在《本草新编》[27]中记有:“黄芪,味甘,气微温,气薄而味浓,可升可降, 阳中之阳也, 无毒……夫黄芪乃补气之圣药”。黄芪补肺脾之气,气旺则水自生,脾气健则痰湿消。孙丰雷提出黄芪健运脾胃,中焦枢纽正常,则上下通达,对于消渴病之小便混浊如脂膏者,可重用黄芪,从30 g起逐渐加量[28],同时有研究证实黄芪可提高卡托普利治疗糖尿病肾病性蛋白尿的疗效[29]。临床中山茱萸与黄芪合用,适用脾湿肾燥、阴阳两虚之下消,能够减轻患者多饮、多尿等症状。
4 小结
临床消渴病患者,常具有脾湿的特征,阴虚燥热,燥湿并存之象十分常见,常规的滋阴润燥治疗可能不尽人意。从燥湿相济入手,针对肺燥脾湿的上消,即可选用玉竹、北沙参药对清热润肺、滋肺胃之阴,若脾湿明显,要注意滋脾胃之阴药加重脾湿的可能,要调整好药物比例;针对胃燥脾湿的中消,即可选用黄连—茯苓药对清胃之热、化脾之湿,此时湿热蕴结,要避免清热化湿加重阴伤;针对肾燥脾湿的下消,即可选用山茱萸—黄芪药对滋阴固肾、培补脾气,此时可能出现阴阳两虚,更应注意阴阳燥湿不同药物的选择,应注意因时因人制宜,恢复人体整体的燥与湿、阴与阳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