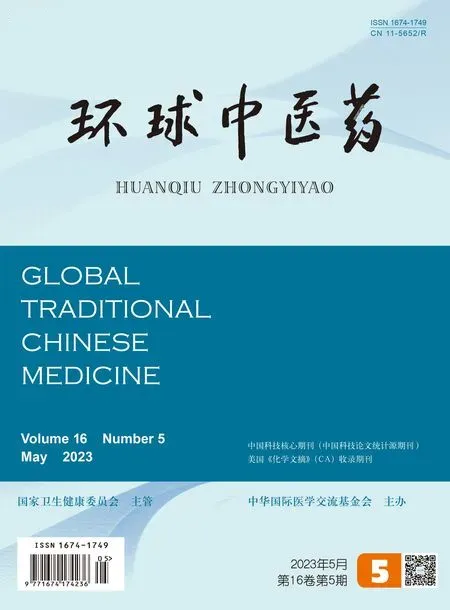李东垣、汪机和徐春甫三位医家的脾胃思想比较研究
2023-03-17李玉凤李姿慧黄辉
李玉凤 李姿慧 黄辉
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最早见于《黄帝内经》。李东垣的《脾胃论》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脾胃学说”,使“脾胃学说”达到新高度,令后世医家重视脾胃,成为了各个医学研究者对脾胃疾病研究、治疗的重要参考依据。《脾胃论》流传较广,影响颇深,汪机将丹溪学说与李东垣内伤脾胃论相融合创立“营卫论”,徐春甫是汪机再传弟子,私淑李东垣,创立脾胃元气论。笔者对三位医家脾胃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对医家研学和临床运用脾胃思想提供帮助。
1 三位医家脾胃思想的相同之处
1.1三位医家都重视元气在维持脾胃功能正常的重要性
李东垣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是维持生命活动和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内经》中提到的“真气”和《难经》所述的“原气”,实际上就是元气,这为李东垣将脾胃与元气相连打下理论基础。《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记载:“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分而言之则异,其实一也,不当作异名异论而观之。”李东垣重视元气,认为元气是人体先天之精气并依赖脾胃后天所化生的水谷之气滋养所形成的,胃气滋养元气,胃气类似元气,谷气、卫气等皆属同类。这将脾胃功能与元气直接联系起来,只有脾胃功能正常,人体元气才能充足,否则会出现“胃之一腑病,则十二经元气皆不足也”。王琳等[1]认为元气依赖脾胃滋养,所以脾胃损伤是引起疾病的起点,但脾胃之间更侧重于胃,即“人以胃气为本”。袁利梅等[2]亦主张脾胃与元气关系密不可分,当脾胃虚弱时,元气失养,不能抵御外邪,人则发病。《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云:“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以由生也。”由此可见,脾胃之盛衰,直接影响元气之盈亏,关乎机体疾病之有无。
汪机是固本培元派的创始人,主张补营气。其所处年代正是丹溪学说盛行之时,当时众多医家皆遵循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过于滋阴,重用苦寒之品。汪机认为“丹溪以补阴为主,固为补营;东垣以补气为主,亦补营也”,认为丹溪所说“阳常有余”是指卫气有余,“阴常不足”是指营气不足,故补阴即是补营;营气又是脾胃运化水谷而生成的,故其继承李东垣脾胃论,强调营气与脾胃之间的关系。汪机所述营气与东垣所述脾胃元气相近,因此补气亦是补营。赵令富等[3]也认为营气可认为是脾胃元气。《内经》云:“卫气者,水谷之悍气也”“营气者,水谷之精气”“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表明营气和卫气皆由水谷精微化生而来,所以汪机固本培元,补营气亦是培补脾胃元气。周超等[4]指出汪机在临床上运用固本培元之法,主要是用“参芪”来温补脾胃元气。
徐春甫推崇李东垣内伤脾胃论,《古今医统大全·脾胃门》曰:“春甫读东垣诸论,详明《内经》论百病皆由上中下三焦元气虚惫及形气两虚,则百病变生;东垣发挥脾胃不足而不能充实三焦,百病之所以由生也”“此春甫所以克己用功,私淑老人之旨,超脱凡俗,极登万仞,探本穷源,深得脾胃元气之妙,故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徐春甫私淑李东垣,在《古今医统大全》中多次直接引用《脾胃论》的观点,特别是对李东垣所述元气理解深刻,首次将脾胃与元气相连,创立脾胃元气学说。徐春甫认为:“不察元气,不知致病之源,而以瞑眩之药攻病之标,反伤元气,甚至脾胃大坏,谷气绝亡;恬不知觉,而犹谓病之不去是吾忧也。”脾胃元气异常是导致疾病发生的源头,一旦治疗不当反伤元气,则病甚,元气耗尽,则人死。陈瑶等[5]论述徐春甫在治未病方面,无论是未病已病还是愈后复元,从始至终都体现了重视脾胃元气的思想。
三位医家都认为对于维持脾胃功能应重视脾胃元气,李东垣认为脾胃滋养元气,补元气即是补脾胃之气;汪机主张固本培元,核心是补营气,补营气就是补脾胃元气,所以固本培元培补的是脾胃元气;徐春甫首次将脾胃与元气相连,提出“脾胃元气”一词。
1.2三位医家都认为脾胃损伤是引起其他疾病的主要原因
李东垣提倡:“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胃负责濡养全身各处,维持生命的基本保障,一旦脾胃损伤,人体失衡,百病皆至。《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曰:“岂特四者,至于经论天地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六腑,及形气俱虚,乃受外邪。不因虚邪,贼邪不能独伤人。诸病从脾胃而生明矣。”脾胃虚弱时,感受外邪侵袭,人体才会发病;脾胃俱胜时,感受外邪侵袭,人体不会发病。刘乐等[6]认为饮食失节、劳倦过度、情志失常、肝胆失疏等内因以及外感六淫,都能损伤脾胃,从而导致其他脏腑经络、四肢肌肉、五官九窍等失养而引发各种疾病。李东垣还提出“大肠小肠五脏皆属于胃,胃虚则具病”“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胃虚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等观点,这都表明“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损伤是疾病产生的源头。
汪机认为许多疾病都是由于脾胃受损所引起。《石山医案·病用参芪论》曰:“是以诸病亦多生于脾胃,此东垣所以拳拳于脾胃也。”又如“脾胃无伤,则水谷可入,而营卫有所资,元气有所助,病亦不生,邪亦可除矣”。只有当脾胃正常运行,人体营气、卫气和元气才能得到资助,邪气可除而病去。杨春荣等[7]阐述汪机在治疗内伤杂病时,常用“参芪”补充脾胃之气,化生气血,调和营卫,则诸病得愈。
徐春甫提出“百病皆因脾胃衰而生”“五脏之脾胃病”的观点。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内经》曰:“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脾胃是五脏六腑的重要组成部分,脾胃与其他各脏腑紧密相连,共同发挥作用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古今医统大全·脾胃门》治法中提到“肝之脾胃病、心之脾胃病、肺之脾胃病、肾之脾胃病”,这表明当脾胃不足时,不但本身发生病变,其他脏腑也受到牵连,因此可以通过调治脾胃,治疗肝、心、肺、肾之病。张宇佳等[8]对《古今医统大全·脾胃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认为脾胃不足会引起阴虚阳盛,“五脏之气不生”,进而引发一系列疾病。此外,徐春甫无论是在治疗用药还是养生等方面,都很重视脾胃。
三位医家都认为脾胃损伤能引起不同的疾病,李东垣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汪机提出脾胃不足,营卫失养,元气失滋,百病皆生;徐春甫提出“百病皆因脾胃衰而生”以及“五脏之脾胃病”之论。
2 三位医家脾胃思想的差异之处
2.1李东垣提倡升降浮沉理论和阴火论
《内经》有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脾胃论·脾胃盛衰论》云:“夫饮食入胃,阳气上行,津液与气入心,贯于肺,充实皮毛,散于百脉。脾禀气于胃,而浇灌四旁,荣养气血者也。”李东垣推崇升降浮沉理论,因脾胃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其化生的水谷精微通过脾升清胃降浊的方式遍布周身。李东垣还在《脾胃论》中列“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之图”描述对五脏应在特定的时辰季节遵循升降浮沉的原则进行补泻,“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和“阴阳升降论”论述天地阴阳气机变化时脾胃起到的显著作用,“调理脾胃治验治法用药若不明升降浮沉差互反损论”阐述治疗脾胃病时应遵循升降浮沉之理。宋文鑫等[9]认为李东垣对于脾升胃降理论,提出不仅“脾气升清”,而且“胃气喜升浮”的“胃主脾从”观点。
李东垣对阴火论的论述略少,《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曰:“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盛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阴火的产生由于脾胃虚弱,气血生化失常,肾阴失养,不能向上制约心火,使心火过于亢盛化为阴火;脾胃虚弱,气机升降失常,湿浊向下入肾,郁而化热,上乘脾胃,化为阴火。由于李东垣并未给予阴火明确的定义,因此诸多医家观点各异。白建英等[10]认为阴火实质是各种原因引起脾胃内伤,气血不足,元气失滋,脏腑失养而引起的火热邪气。李沅骋等[11]主张饮食、情志等在损伤脾胃的同时,也使命门气郁化火,引起阴火上冲。究其根源,阴火是相关脏腑在脾胃气虚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火邪。
2.2汪机提出“营卫论”
汪机私淑朱丹溪,又推崇李东垣,补前人之不足,结合所处时代背景,提出“营卫论”,为固本培元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汪机的“营卫论”主要是对营气的论述,认为丹溪的滋阴即是补营,又提出“营卫一气”论,将补营转化成补气,从而突出气补气思想。潘云等[12]认为营卫互为阴阳,营者又可再分阴阳,营又包含气血,无论是补阴还是补阳都是补营之阴阳,所以体虚之补即补营也。《营卫论》云:“故曰血之与气,异名而同类。补阳者,补营之阳;补阴者,补营之阴”“故古人于阴字下加一气字,可见阳固此气,阴亦此气也。故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同一气也。”综上所述,气、血、阴、阳、营、卫皆归为气,所以汪机的“营卫论”,实际是对补气思想的转化和包装,以应对当时提倡滋阴理论的时局。
2.3徐春甫主张“治病当察脾胃虚实”和脾阴论
徐春甫强调“治病当察脾胃虚实”。《翼医通考·医道》云:“甫观今世医者,多不工于脾胃,只用反治之法攻击疾病,以治其标,惟知以寒治热,以热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而已。”表明徐春甫指责当下医者,不明脾胃的重要性,只知治标,不知求本,即使伤及脾胃元气而不自知,导致疾病加重而不明其理,因此提出“调和脾胃,为医中之王道”“治病不察脾胃虚实,不足以为太医”等观点。又如《古今医统大全·脾胃门》曰:“百凡治病,胃气实者攻之则去,而疾恒易愈;胃气虚者攻之不去。盖为本虚,攻之而胃气益弱,反不能行其药力,而病所以自如也,非药不能去病也,主气不行药力故也。”治病先分脾胃虚实,实则攻之,虚则补之,胃气实加之药力则病愈,胃气虚加之药力反受其害,使胃气更虚,强调治病首先要辨脾胃虚实。赵军等[13]认为徐春甫此观点解释了医者在治疗相同疾病,运用不同的治法和用药却有相同疗效,是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调治脾胃的结果。徐春甫还提出了脾阴虚观点。明代以前的脾胃学说中主要是对脾气和脾阳的论述,但脾亦有阴阳之分。受到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观点的启发,徐春甫开始关注脾阴在疾病中的变化。《脾胃门·药方·枳术丸》中“能食者但食后饱闷难化,此胃火旺、脾阴虚也”,首次明确提出“脾阴虚”的概念[14]。《翼医通考·医道》中提到:“胃阳主气司受纳,阳常有余;脾阴主血司运化,阴常不足。胃乃六腑之本,脾乃五脏之源。胃气弱则百病生,脾阴足则万邪息”,表明脾阴在人体生命活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综上所述,汪机和徐春甫在推崇东垣内伤脾胃论的同时,又加以引申发挥,使三位医家的脾胃思想既紧密相连又各有所长。李东垣根据脾升胃降的生理特点提出升降浮沉理论,将脾胃虚弱引发机体产生的火邪称为阴火论;汪机融合丹溪滋阴和东垣补气思想创立“营卫论”;徐春甫治病注重察脾胃虚实,针对李东垣阴火论明确提出脾阴论。
3 三位医家脾胃思想形成背景的比较
3.1相同之处:三位医家打破其所处时代医者治病思想之固垒,提倡脾胃理论
李东垣所处的金元时期,战争频繁,疾病流行,患病者十之八九,众医者用原有方法治疗,收效甚微。《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有云:“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疫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二三月,胃气亏之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其死也无疑矣。非惟大梁为然,远在贞祐、兴定间,如东平,如太原,如凤翔,解围之后,病伤而死,无不然者。”李东垣突破当时中医固有思想,认为此疾非伤寒也,而是人们长时间劳累饮食不当,引起脾胃亏损,之后又饮食过饱,又经伤寒之法调治,病情加重而亡。所以其以内伤脾胃为依据治疗当时疾病,在大量临床积累下,编撰《内外伤辨惑论》,又恐世人不明内伤证重在内伤脾胃,于是晚年又编撰《脾胃论》《兰室秘藏》等著作。
汪机所处年代,正式丹溪学说盛行之时,当时众多医家皆遵循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过于滋阴,重用苦寒之品。如《营卫论》云:“何世人昧此,多以阴常不足之说横于胸中,凡百诸病,一切主于阴虚,而于甘温助阳之药一豪不敢轻用,岂理也哉?”汪机也深受丹溪学说影响,但他对丹溪学说理解更加透彻。如《营卫论》曰:“且治产后的属阴虚,丹溪则曰:‘右脉不足,补气药多于补血药;左脉不足,补血药多于补气药’,丹溪固不专主于血矣。”汪机明确指出丹溪并非所有疾病皆用滋阴之法,其滋阴降火主要针对当时滥用《局方》香燥的时弊所发,而当时许多医家不明其理而偏用重用滋阴之品,于是汪机提出“营卫论”。
徐春甫所处年代也是丹溪学说盛行之时,以王纶为代表的大量医家,用药过于苦寒,提倡滋阴降火,忌用人参、黄芪等温补之品,以致脾胃损伤,形成时弊。徐春甫在《脾胃门》中提到:“何今世之医不识元气之旨,惟见王纶《杂病》戒用人参之谬说,执泥不移,乐用苦寒攻泄病之标,以至误苍生死于非命,抑何限耶?”说明在当时众医者不懂元气的重要性,盲目遵循丹溪学说,不懂温补脾胃之重,失治误治使病情加重。徐春甫跟随汪机,重视元气,提出脾胃元气论。
综上所述,李东垣生于战乱年代,民众脾胃损伤,故其打破固有思想,创立内伤脾胃论。汪机和徐春甫由于丹溪学说盛行,大部分医家用药过于苦寒,损伤脾胃形成时弊,他们打破固有思想,分别创立了“营卫论”和脾胃元气论。
3.2不同之处:三位医家成长经历各异,以致形成的脾胃思想各异
李东垣饱受战争之苦,其素来脾胃虚弱,对脾胃方面的研究更加关注。连年战争,为李东垣提供了大量临床实践机会,这皆促使李东垣脾胃论的形成,并且其脾胃理论具有很强大的科学性和应用性。汪机推崇李东垣,重视脾胃,在其《营卫论》等主要著作中曾多次引用李东垣的观点,“营卫论”的生成深受其影响,“营卫论”实际上是丹溪学说和东垣脾胃论的融合。徐春甫自幼学习儒学,从小体弱多病,于是拜汪宦为师,专研《内经》。明代医者地位有所提高,很多人通过医术谋生,使得其医术在大量临床实践中迅速提高。徐春甫私淑李东垣,推崇其重视脾胃的观点,创立脾胃元气论。
4 三位医家用药特点的比较
4.1相同之出:三位医家用药偏于温补
李东垣首创甘温除热法治疗内伤发热,代表方补中益气汤,首列黄芪、人参、甘草三味药,他认为此三味药“皆甘温为主,凡脾胃虚,乃必用之药”。楚永庆等[15]指出李东垣主要用补虚药补脾胃元气,以甘温益气为主,如人参、黄芪、白术、炙甘草等,共使用113次,占所有补虚药的71.5%,占所有中药频数的21.2%。
汪机在提出“营卫论”的同时,一同产生的还有“参芪说”。他临床善用人参、黄芪,对参芪有独到的见解。其在《营卫论》中提到“是知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也,可见人身之虚皆阴虚也。经曰‘阴不足者,补之以味’,参芪味甘,甘能生血,非补阴而何?又曰‘阳不足者,温之以气’,参芪气温,又能补阳,故仲景曰气虚血弱,以人参补之,可见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所以汪机认为参芪气血阴阳皆可补之。孙超等[16]论述人参、白术、当归、甘草、黄芪在《石山医案》中出现频次最高,依次为53、42、39、37、36次,累计用药频次207次,占所有纳入药物用药总频次(467次)的44.32%,这些药多属于补气之品。这再次证明了汪机“营卫论”中以补气为根本。
徐春甫推崇健脾保元治法,自创许多顾护脾胃类方剂,例如大健脾养胃丸最具有代表性,“余固首集大建脾丸,为医家之主药,人生之根本,不可须臾离也。诸人服此丸,脾胃大壮,饮食多进,诸病不生,寿考长龄,此其基本”。强调脾胃对于人体作用显著,只有脾胃强健,人才有长寿的可能。他还认为,人的衰老与脾肾亏虚有关,强调滋肾扶脾,但“补肾不如补脾”,故在诊治疾病中用药多偏于温补[17]。
三位医家在临床用药上,都善用温补之品。李东垣主张甘温益气,常用补中益气汤;汪机创立“参芪说”,善于参芪温补营气;徐春甫自创自制大健脾养胃丸顾护脾胃。
4.2不同之处:三位医家用药风格各异
4.2.1 李东垣用甘温之药时根据不同症状配以它药 《脾胃论·脾胃盛衰论》有云:“今所立方中,有辛甘温药者,非独用也。复有甘苦大寒之剂,亦非独用也。”这表明东垣在甘温泻火的同时,也配以甘寒泻火之品,如黄芩、黄连、黄柏等,在其100多个处方中都有体现。《脾胃论·脾胃盛衰论》曰:“是以检讨《素问》《难经》《黄帝针经》中说脾胃不足之源,乃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当从六气不足、升降浮沉法,随证用药治之”“以火酒二制为之使,引苦甘寒药至顶,而复入于肾肝之下,此所谓升降浮沉之道,自偶而奇、奇而至偶者也。泻阴火,以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令阳气生,上出于阴分,末用辛甘温药接其升药,使火发散于阳分,而令走九窍也。”内伤脾胃,元气不足,脾不升清,引起体内气机升降失调,李东垣尤其重视升降浮沉之理,常以升麻、柴胡、茯苓、泽泻为升降之药。李东垣继承其师张元素“风生升”类药,后将其称之为“风药”,包括防风、升麻、柴胡、葛根、羌活、独活、细辛、白芷、藁本、川芎、蔓荆子、天麻、麻黄、荆芥、薄荷等味薄清轻升散之品,主要用于内伤脾胃后引起的不同症状,取其升阳泻阴火散湿之功[18]。李东垣处方用药味多且量少,但其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的配伍法度相当严谨,临床也有较好的疗效[19]。
4.2.2 汪机用参芪之时多配滋润之品 汪机善用药物配伍来制约参芪偏性,其在辨《明医杂著·忌用参芪论》中提到:“是知人参不惟补气,亦能补血。况药之为用又无定体,以补血佐之则补血,以补气佐之则补气。是以黄芪虽专补气,以当归引之,亦从而补血矣。”汪机虽然“营卫论”偏于补气,受东垣影响颇深,但他在临床用药时,参芪多配麦冬、白芍等清润之品,少配升麻、柴胡、羌活、防风等辛散之品,更偏与丹溪用药风格。
4.2.3 徐春甫提出用药贵精不贵多 徐春甫还提出与二十四节气相对应的“二十四方”,保元堂起家的“三十六方”,独具特色,将枳术丸传统剂型丸剂改为“汤滴小丸”,便于消化,治疗脾胃大虚有奇效。临床用药偏于温补,善用人参、黄芪、白术,并且重用白术。徐春甫认为用药贵在精不在多,推崇药味少而有奇效的小方,“上古用药最简,以其药治某病,单方一味,故其力专”,所用方剂大多8-15味药[20]。
综上所述,三位医家虽然用药偏于温补,但具体药物上各有偏好。李东垣在温补之时非独用甘温之品,并且偏爱升降浮沉之理,常用升阳药;汪机善用参芪,多配麦冬、芍药等清润之品;徐春甫注重方药配伍、剂型,也善用参芪,但喜重用白术。
5 讨论
现如今由于饮食不节、劳倦过度、情志不遂等引发的脾胃病,在临床上最为常见,对脾胃的治疗仍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李东垣的内伤脾胃论、汪机的“营卫论”“参芪说”和徐春甫的脾胃元气论,既紧密相连又各具特色,皆以脾胃为中心,对三者比较分析有研究价值。三位医家根据各自临床经验归纳出由脾胃不足引起的一系列疾病的理法方药,现对三位医家脾胃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突出强调了脾胃元气的重要性、脾胃不足是引起其他疾病的关键、脾胃用药应偏于温补等,对如今的脾胃思想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对现在脾胃病的治疗提供了方向,为脾胃学说进一步完善做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