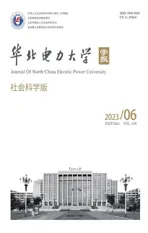唯美主义的中国叙事:论《水榭》对《合影楼》的跨文化改写
2023-03-16桑瑞
桑 瑞
(华北电力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2206)
改写(adaptation,该词也可译为“改编”)作为人类文学创作传统的一部分,历史悠久。于西方文学而言,改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神话叙事。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提出,改写是对源文本有意识而公开的创造性修正,在创作过程中展现了内在的多层叠刻性(palimpsestuousness),并在美学上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1]改写是后世文学与文学传统发生互文关系的常见技巧,为经典文本探索了新的讲述方式,使原作获得第二生命,同时凸显了起源文本的无穷魅力。
在全球化语境下,改写实践得到进一步拓展,成为世界性文化景观,跨文化改写(transcultural adaptation)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跨文化改写是在多元文化和多重传统的交织中进行的创造性写作实践,它将源文本的元素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使原作在全新文化氛围中得到艺术再生与价值重构。同时,作为一种“创造性叛逆”[2],跨文化改写能够反映出文本背后的历史社会背景、文化传统、诗学理念等多重层面的异质性,对文明互识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3)于1846年发表的短篇故事《水榭》(Le pavillon sur l’eau)是跨文化改写的优秀案例。《水榭》讲述了一则发生在中国的爱情故事,其改写的起源文本为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所著拟话本小说集《十二楼》的首篇《合影楼》。但戈蒂耶并未读过李渔的《合影楼》原文,他的改写行为是以《合影楼》的法译本为基础而发生的。本文立足个案研究,从跨文化改写视角出发,通过文献爬梳、文本细读及对照,结合作者的异域观和诗学理念,探析《水榭》的改写动因、策略和价值。
一、《合影楼》之演变:文本的流转与《水榭》的诞生
《合影楼》出自李渔所著拟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十二楼》包含十二个以不同楼阁名字命名的故事,结构纤巧,情节曲折。《合影楼》是《十二楼》的首篇,讲述了发生在元朝至正年间广东曲江县的才子佳人式故事:屠观察和管提举同为一家之赘婿,但性情各别,由此不睦。岳父母去世后,他们将共有的住宅分为两院,建以高墙相隔,就连水池之上都架起石板,筑起石墙,只留石墙下方的池水相通。不料,管家之女玉娟和屠家之子珍生却通过水中倒影相识、互生好感,两人通过流水荷叶传诗通笺、互诉衷肠。珍生向管家求婚,却因两家交恶而遭到拒绝。屠、管两家共同之友路公为化解难局,提出将养女锦云嫁给珍生,被珍生拒绝。锦云受挫生疾,玉娟和珍生也因求爱而不得而患病。路公又从中斡旋,最终通过计谋促成珍生并得双美,三方皆大欢喜,两家恩怨也一笔勾销。
李渔在西方世界一直广受好评。法国汉学家谭霞客(Jacques Dars,1937—2010)将李渔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受人喜爱的天才之一”和“最可爱的怪杰之一”[3],李渔研究专家彼埃·卡赛(Pierre Kaser)认为其写作风格媲美法国启蒙作家狄德罗[4]。《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更是将李渔奉为“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西方世界对李渔的肯定和重视归功于汉学家对其的译介和研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官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则是译介李渔第一人。
德庇时于1815年翻译了《十二楼》中的《三与楼》,并在次年推出单行本。随后,德庇时继续翻译了《合影楼》和《夺锦楼》,于1822年在伦敦出版《中国小说集》(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包含上述三篇译文。关于德庇时对《十二楼》的节译,学界已有较多研究。译者身份为东印度公司翻译官,其翻译动机在于“从本土作品中获取关于这个国家的知识”[5],从而帮助英国了解和拓宽中国市场。译者主体身份和翻译动机影响了翻译策略,单论其对《合影楼》的翻译,德庇时以《水中影》(The shadow in the water)作为译文标题,对原文叙事结构做了大幅改动,删去了篇首、入话、头回、篇尾等拟话本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题目外,仅保留正话部分,且正话的大部分韵文被直接移除,只留故事本身,即正话的散文部分。德庇时以归化作为主要翻译策略,顺应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将人物对话译为普通叙述,对一些专有名词和谚语采取意译的方式,删减部分晦涩难懂的文化信息。此外,德庇时将故事男女主人公珍生和玉娟的名字理解为“珍珠”(pearl)和“玉石”(gem),这一思路在后续的转译及改写作品中均得到继承。
德庇时的《十二楼》节译本在欧洲影响颇广,1827年被转译为德、法文,其中的法文转译由素有“西方专业汉学第一人”[6]之称的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完成。
雷慕沙对中国俗文学很感兴趣,他翻译的法文版四卷本《玉娇梨》于1826年在巴黎出版,此书在欧洲引起很大反响,歌德、黑格尔都借助这部小说完成对中华帝国的整体认知[7]。在该书序言部分,雷慕沙发表了他对中国小说的看法,他认为,尽管传教士群体对中国人的生活进行了大量观察和记录,但他们很难深入中国人的内心,而中国小说“仿佛是一种游记”,且它们“比旅行家的游记更加准确,更加有趣”[8]67。同年,雷慕沙的论文集《亚洲杂纂》(Mélanges asiatiques, ou choix de morceaux de critique et de mémoires)第二卷在巴黎出版,收录了诸多有关中国经典的研究与译文评述。其中,在《关于若干译自中文的短篇小说》(Sur quelques nouvelles traduites du chinois)一文中,雷慕沙介绍并评述了德庇时的英译版《合影楼》和《夺锦楼》。雷慕沙充分肯定了德庇时译文的价值,再次表示翻译此类中国小说有利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社会风俗和民众心理。与此同时,雷慕沙根据自己对中国小说的阅读和翻译经验,推测德庇时“必定删减过许多细节,特别是删除了原文中所有的对话”,因为“中国小说家习惯通过大量对话来刻画人物情感和性格”[9]338。当时的法国盛行“不忠实”翻译策略,翻译标准倾向于阅读的舒适性,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被称为“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èles)。与善用注释、主张忠实再现原文风格的弟子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相比,雷慕沙相对更倾向于“不忠实”翻译策略,但他的“不忠实”仅限于对具体词句的意译,而对于德庇时删掉原文对话的做法,他认为极为不妥,是“为取悦欧洲读者而作出的牺牲”,呼吁“让读者来评判作品”,因此“译文应该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形式,保留其长度以及各种缺陷”[9]338-339。
1827年,雷慕沙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故事》(Contes chinois)由巴黎蒙塔迪埃出版社出版。该书选取了十篇中国短篇小说,其中三篇来自《十二楼》,即前述德庇时所译《合影楼》《夺锦楼》和《三与楼》,七篇来自《今古奇观》,原始译者有英文印刷商和翻译家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1814—1851)、已故的法国传教士殷弘绪(François-Xavierd’Entrecolles, 1664—1741),以及一个中国天主教信徒Abel Yan。在该书序言中,雷慕沙将中国短篇小说称作西方人了解中国风俗的“样品”(échantillon),在他看来,相比那些鸿篇巨制,短篇小说和寓言故事更易被翻译,也更易被欧洲读者接受,虽没有宏大叙事和对人物的精雕细琢,却足以使读者“了解私人生活和社会底层的家庭习惯”[10]。该书对汤姆斯、殷弘绪、Abel Yan的译文进行了细致的修订,而对于德庇时的译文,由于缺少中文原文,因此未做内容上的修订,仅将其从英文转译为法文。法译版《合影楼》沿用了英译版标题《水中影》(L’Ombre dans l’eau),形式、内容、注释也完全一致。雷慕沙没有明确指出该文的转译者何人,他在序言中提到Abel Yan的译文的修订者是儒莲,而对于其他修订者和转译者,雷慕沙使用的人称代词均为“我们”(nous和泛指人称代词on)。因此,法文版《合影楼》的转译者或为雷慕沙本人,或是雷慕沙主导,由他和学生共同完成。
如此,李渔的《合影楼》走出国门,经由英国传至法国,进入了法国读者的视野。1846年6月,法国《百姓书屋》(Musée des familles)杂志刊登了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的短篇故事《水榭》,并配有三幅插图。《水榭》即《合影楼》的创造性改写作品。《水榭》在《百姓书屋》首次发表后,先后被1852年出版的《虎皮》(La Peau du tigre)、1863年《长篇小说与短篇故事》(Romans et contes)、1897年《泰奥菲尔·戈蒂耶作品集:长篇小说与短篇故事》(Œuvres de Théophile Gautier. Romans et contes)三部文集收录,并于1900年在巴黎A. Ferroud出版社出版了配备大量插图的单行本。上述再印版本均未提及《水榭》的参照文本,因此,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法国文坛都将《水榭》视为原创作品。直到1915年,芝加哥大学学者亨利·戴维(Henri David)在对相关文本进行考据和对比的基础上,首次指出《水榭》一文是对雷慕沙《中国故事》中《水中影》一文的改写,同时在《玉娇梨》等三部法译版中国小说中借用了许多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11]戴维并未进一步探究《水中影》的原文和作者,《合影楼》和《水榭》的相关性一度不为人所知。2010年法国比较文学教授岱旺(Yves Daniel)在其著作中介绍《水中影》原文时,仍错误地提到“元代作品,作者不详”[12]60。直到2012年,汉学家彼埃·卡赛才在其个人网页首次提出李渔《合影楼》是《水榭》的起源文本,但卡赛并未对此展开详述。
与《合影楼》相比,《水榭》中屠、管两家人由“同门赘婿”变成了“远房亲戚”,且作者对二位老爷的姓氏做了置换。除这些细节之外,戈蒂耶对原故事进行了多角度改写,其改写策略受到他个人志趣及诗学理念的影响,下文将对此详细论述。
二、异域笔触:中国元素的运用与“怀旧”意象的隐喻
戈蒂耶选择改写一则中国题材的故事,首先基于他对异域情调的迷恋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法国比较文学专家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将异域情调定义为关于异域的“文学、艺术表述”,是与“意识形态和想象物”相关的“书写方式的总和”[13]。戈蒂耶酷爱旅行,先后踏足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德国、俄国、土耳其、埃及和近东各国。他珍视旅行中体验到的“异地感”(dépaysement),曾表示:“当我出发去旅行时,我首先在巴黎留下我的批评之鞭和‘法国审美裁判’的面具。”“我旅行只是为了旅行,也就是说,为了看到和享受新的风景,为了移动,跳出自己和其他人的框架。”[14]戈蒂耶偏爱东方文化,他的很多作品充满着具有东方色彩的异域情调。他对东方世界的热情始于对雨果《东方诗集》(Les Orientales)和东方主义画家们画作的欣赏。
戈蒂耶不识中文,一生中也从未到过中国。尽管如此,受到18世纪风靡于欧洲的“中国热”影响,他始终对中国这一遥远的东方大国怀有憧憬与好奇。在《水榭》发表前,戈蒂耶就多次零星在其文学批评和小说中提及中国。1830年,德国浪漫主义作家E.T.A.霍夫曼的作品风靡法国,19岁的戈蒂耶被霍夫曼新奇怪诞的写作风格所吸引,撰文评论道:“这些奇异的故事与迄今为止出版的所有故事都不同,我们阅读它们时,会感觉如同被人用弹弓从巴黎射到了北京,看到那些琉璃瓦屋顶、瓷砖墙壁、红黄相间的窗棂,那些商铺招牌上奇怪的文字和怪异的动物,还有那些在我们的屏风上出现过的、在我们看来如此古怪的人们,他们手持遮阳伞,头戴嵌有小铃铛的尖顶帽子,身着点缀着大花和带翅膀的小蛇的长袍。”[15]1835年,戈蒂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莫班小姐》(Mademoiselle de Maupin)问世,在这部被视为唯美主义文学奠基之作的作品中,作者六次提及中国和中国风物,包括中国花瓶、中国式小桥、民居、中国画、女式遮阳伞和竹筏。1837年,戈蒂耶的小说《福尔图尼奥》(Fortunio)在费加罗报连载,于次年出版单行本,书中数次谈到一位“皮肤如玉,眼睛如柳叶”的中国公主Yeu-Tseu,还提及讲中文和满文的教授、孔夫子,甚至提到汉学家儒莲在1837年刚出版的《桑蚕辑要》(Traité de l’éducation des vers à soie)。在《水榭》诞生前,戈蒂耶还写过一首以中国为主题的短诗,收录在1838年出版的诗集《死亡的喜剧》(La Comédie de la mort)中,题为《中国风》(Chinoiserie)。戈蒂耶在该诗中宣称“我之所爱,今在中国”[16],诗中对中国女子的外貌进行了描述,突出了中国女子与自然元素的互动。总体来说,早期的戈蒂耶对中国的想象以视觉想象为主。
据亨利·戴维考述,戈蒂耶“撰写一则中国故事”的想法萌芽于1840年,他曾在那年年初致信他的朋友、《百姓书屋》的主编亨利·贝尔图(Henry Berthoud, 1804—1891),请求对方借给他“一百本关于中国的书”,来使他的作品“充满地方色彩”。[11]《水榭》最终发表于1846年,这则“中国故事”为何拖延六年不得而知,但在这期间,戈蒂耶阅读了大量汉学书籍,其中包括雷慕沙翻译的《玉娇梨》和主编的《中国故事》。在研读过程中,戈蒂耶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习得了大量中国专有名词的表达方式,这些知识作为“异域情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榭》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相较于《合影楼》这部土生土长的中国小说,《水榭》作为改写作品,为了凸显异域特色,刻意增添了许多原作中并未涉及的中国元素。《水榭》所增设中国元素主要呈现为物质和精神两大维度。物质元素既包括中国器物,如屠老爷宅中“经过精心布置的雕花壁板、洁净如镜的案几、明亮的窗子、金色的窗棂、竹制雅椅、瓷器花瓶、或红或黑的漆柜”,两栋楼台书房中的“牙签、扇子、乌木烟斗、砚台、毛笔以及写作所需的所有文具”[17]1122-1123,也包括典型的中式自然元素,如菊花、牡丹、兰花、垂柳、报春花、睡莲等。这些元素在形式上构成了异质文化符号,为作品注入了浓郁的异域情调。
精神层面的中国元素更加丰富,也是《水榭》与戈蒂耶早期提及中国的作品之间最显著的区别。精神元素首先表现为中国的诗歌和书法在作品中的反复言说。在《水榭》中,人人都爱吟诗作赋。屠、管两位老爷在年轻时就喜欢“在花笺的格子上挥毫”,“即席赋诗,吟咏菊花之绝美”。两人不睦之后,屠专心于“书写那高悬于亭柱之间的格言对联”,家中墙上也挂着“装裱好的古诗词”,而管则“心如少年般飞旋,待诗句需字之际,其笔如流星,毫不停滞”。[17]1122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更是嗜诗如命,且写得一手好字。玉娟能熟诵《诗经》,“通晓所有的诗歌形式”,并且“做了很多才情横溢的诗,去吟咏譬如归燕、春柳和秋菊这类触动少女心怀的主题”,她的字迹“豪放又清晰”,当她提起笔来,“飞龙的速度都难以匹敌她那使墨水如雨倾泻的笔尖”。[17]1125作诗和书法功底是她评判男子的重要标准,她会因“字迹沉闷,平淡无奇”和“不懂《诗经》,押错了韵”等原因谢绝求婚的人,也会因男主人公珍生的情诗“笔迹之优美,用词之考究,押韵之准确,意象之生动”[17]1130而为其所动。除《诗经》之外,戈蒂耶还在《水榭》中提及“杜拾遗”和“李太白”[17]1123。《诗经》自18世纪上半叶起就以节译的形式传入法国,且在1830年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1695—1767)的拉丁文全译本被正式出版。而李白和杜甫等诗人虽在18世纪的《中华帝国全志》中被提及,但唐诗真正被译介到法国已是19世纪60年代。尽管戈蒂耶在撰写《水榭》时并没有机会去真正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内涵,但他已然通过想象,勾勒出一个诗意中国。
精神元素还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隐性呈现。《合影楼》原作中道学先生的“古板执拗”与风流才子的“跌荡豪华”,在戈蒂耶的笔下得到了微妙的美化,两位老爷性格中消极的一面被抹去,他们的性情冲突化为“严肃沉稳”与“逍遥自在”的对比。而《水榭》后半部分,戈蒂耶完全改变了原作故事的走向,设计出两家夫人拜佛为各自儿女求姻缘,得到庙僧预言两家结亲之道,助力化解两家恩怨的情节。岱旺提出,戈蒂耶巧妙地通过两位老爷的性格特点,将“儒学卫士”和“道家诗人”的生活方式向读者展现出来,而两位夫人拜佛情节的增设,则是佛教文化的隐喻,由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以隐性方式在戈蒂耶笔下和谐共处。[12]63
除却中国元素的增设,《水榭》在故事中还暗含了作者对东方的“怀旧”(nostalgie)之情。正如《龚古尔日记》所指,戈蒂耶笔下的“异域”不仅是空间层面的异地,也是时间层面的疏离,展现了一种空间与时间上的双重距离感。[18]一方面,东方是西方人眼中的“他者”,是异质文化的集合地,用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话说,具有“多异”(divers)之美。另一方面,神秘、古老的东方文明又让戈蒂耶产生一种“怀旧”之情。歌德认为人类的“本原现象”(Urphanomen)可以在东方人身上看到。[19]160戈蒂耶视东方为故乡,曾在一封信中表示:“人并不总是属于自己出生的那个国家,因此,有的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真正的故乡;这样的人在自己的城市中感到被流放,在自己的家中感到陌生,被各种怀旧之情所困扰……我觉得我曾经在东方生活过。”[20]于戈蒂耶而言,东方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也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如钱林森所指,东方代表人类美好的过去,诗人们通过审美上的移情作用,可以把代表着青春、美和自然的历史唤回到他们的记忆中。[19]160
尽管戈蒂耶在开篇表示此故事无确切年代,但在文中近篇尾处,作者通过珍生之父管老爷之口,暗示故事发生的时代与此文撰写的时代是一致的。管老爷在珍生拒绝说媒之事后,威胁儿子若继续固执下去,就请求县官将他“关进那被欧洲蛮子占据的堡垒中”,那里能看到“那些恶魔发明的怪东西在黑水上驶过,机轮转动,喷吐出恶臭的烟雾”。[17]1129有学者认为此“堡垒”暗指鸦片战争爆发后被英国人占据的香港。[12]61戈蒂耶在此处转换视角,以中国人的口吻,将西方殖民者称为“欧洲蛮子”,将现代化工业产品称为“恶魔发明的怪东西”,暗示了他对传统东方文化遭到侵犯和破坏的忧虑,对一个乌托邦式东方世界被工业文明侵蚀的惋惜,隐喻了他对于异域、神秘、传统东方世界的“怀旧”之情。
三、“为艺术而艺术”:语言、情节与人物的唯美重塑
除了对异域情调及中国文化的偏爱,戈蒂耶自身的诗学理念和唯美倾向也影响了他的改写。戈蒂耶早年崇拜雨果,是浪漫主义的拥趸。1830年,在震动了欧洲的“欧那尼之战”中,年仅19岁的戈蒂耶身穿红马甲,为雨果欢呼呐喊。但戈蒂耶之所以名垂后世,是因为他后来的唯美主义转向。他是帕纳斯诗派的先驱,“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思潮的奠基人。“为艺术而艺术”是法国人对康德思想的通俗化和口号化[21],对于戈蒂耶而言,关于艺术的自主性和美的至上性的最早表述可追溯到他1832年出版的诗集《阿尔贝杜斯》(Albertus)的序言,而《莫班小姐》的长篇序言则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在这篇序言中,戈蒂耶强调了“审美无功利”的理念:“真正美的东西都是毫无用处的,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是丑陋的。”他以自己对中国的兴趣举例:“我不喜欢有某种用途的花瓶,却喜欢画有龙和中国人的中国花瓶,因为它对我毫无用处”。[22]戈蒂耶秉持艺术至上论,认为艺术不应具有任何说教的因素,而应追求单纯的美感,他注重文学作品的形式美,认为形式美是评价艺术的真正标准。《莫班小姐》的序言被学界看作唯美主义文学的宣言,他的诗集《珐琅和雕玉》(Émaux et Camées)被视为具有浓厚唯美主义色彩的作品。
作为《合影楼》的改写作品,《水榭》在语言风格、情节安排、人物形象等多层面的变异和重塑都受到了作者“为艺术而艺术”诗学理念的影响,是作者唯美主义文艺创作观在中国故事上的具体实践。
(一) 语言的唯美重塑
在语言风格上,《水榭》以精雕细琢的遣词造句,呈现了如油画般的视觉描绘。《合影楼》原文及英法译文的故事性极强,情节一波三折,少有对环境的描写。而在《水榭》中,感情色彩鲜明的人物对话几近全无,取而代之的是大篇幅细腻雅致的描写段落。例如,对于屠、管两家各自的水阁,《合影楼》原文仅简单介绍“后园之中有两座水阁,一座面西的,是屠观察所得,一座面东的,是管提举所得,中间隔着池水”,并未给予更多笔墨;而戈蒂耶则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其上铺设着圆润闪亮的瓦片,其鳞片状的排列宛如鲤鱼肚部密集的鳞屑。每条屋脊都精心雕刻着锯齿状的树叶与龙形花纹。红色的漆柱被一个如同象牙扇叶般镂空雕刻的中楣连接,共同支撑起这雅致的屋顶。柱子底部建立在一段矮墙之上,墙身精心贴上了对称排列的瓷砖,墙外环绕着一道独具特色的护栏,于是,在主建筑的前面形成了一个开放式走廊。”[17]1122-1123
从屋顶的瓦片开始,逐渐转向屋脊、柱子、矮墙,最后到开放式走廊,作者的描述顺序如同画家从画布上部开始作画,逐步填充至底部,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建筑结构和布局。
又比如,对于两家共有的后园,《合影楼》原文及译文均未提及园中景物,而戈蒂耶凭借自己的想象,用文字绘制出一幅美丽的中式园林风景图。他注重光与影、主体与背景的对比,阳光下金色的柳树与碧波荡漾的池水,明亮的翠颈鸭与暗淡的睡莲叶,这些对比令画面更加立体,更有质感,为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戈蒂耶的文字如同画家的笔触,细腻捕捉每一个细节,赋予每一个场景生动的色彩。
戈蒂耶擅长充满画面感的文字描述,这与他与生俱来对艺术,尤其是对绘画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从青少年时代起,戈蒂耶就表现出对绘画的兴趣,18岁跟随浪漫主义画家里乌尔(Louis-Édouard Rioult,1790—1855)学习绘画,一度决定以绘画为生。通过里乌尔的引荐,戈蒂耶结识了雨果,出于对雨果的崇拜和对文字的痴迷,他决定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尽管放弃了绘画,但他对绘画艺术的爱好并未消退,仍乐于以“诗人和画家”自居。对绘画的爱好培养了他对色彩的敏感,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龚古尔兄弟将戈蒂耶的写作风格定义为“艺术写作”(écriture artiste),并描述为“赋予细节非凡重要性的形式”。戈蒂耶力求其文字如艺术作品一般产生视觉和音乐感觉,他曾表示希望“所有艺术都将在同一作品中共振,每一件作品都将漂浮在光和香气的环境中”[23],他在《水榭》中的视觉描述正体现了“艺术写作”的风格。如果说德庇时的译文以实用为导向,丧失了原文的部分文学韵味,那么戈蒂耶的创造性改写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故事的文学价值。
(二) 情节的唯美重塑
《水榭》的情节与原文相比呈现了显著的差异性,作者的唯美倾向是情节变异的重要因素。首先,戈蒂耶将故事化繁为简,将男女主人公“对影生情”的情节作为新故事的核心,赋予其更多的文学重量。这一选择恰好与17世纪巴洛克文学青睐的“水中倒影”意象相呼应。在巴洛克文学中,“水中影”象征着“间接视觉”和“多层次的现实”[24],具有多维的文学解读空间。《合影楼》故事原型中,水边双影相会的场景可能是触发戈蒂耶改写念头的最初火花。戈蒂耶对这一意象的使用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审美偏好,而且强化了故事的唯美主义特质。
其次,故事的结局经过解构与重塑,原作中的重要角色路公和锦云被刻意地忽略,而男主人公“并得双美”的设定也被改写,改写后的故事以男女主人公终成眷属画上完美句号。《合影楼》的结局带有深刻的封建婚姻文化的烙印,若将审美对象还原至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从封建社会普通民众的视角出发,珍生能同时迎娶玉娟和锦云,化解各方矛盾,是既满足个人情欲,又合乎封建礼教的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对于生活在一夫一妻制婚姻文化传统的19世纪法国普通读者来说,这样的情节安排是难以接受和理解的。《百姓书屋》杂志自创刊之日,便以打造“平民的卢浮宫”为宗旨,面向文化程度较低的普通家庭以启迪民智。戈蒂耶身为期刊撰稿人,对结局的改写无疑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敏感性,但更重要的原因应归结于戈蒂耶本人对原作结局“破坏美感”的评判。
雷慕沙就曾两次对《合影楼》的结局表示不满。1826年他评述德庇时译文时,提到“这则故事的结局是较弱的部分,远未能与(故事的)整体构思相媲美”[9]341。在《中国故事》的序言中,他再次表达了对《合影楼》结局的遗憾:“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浮现在他脑海中的巧妙构思,以及随之展开的令人愉悦的情节,并不总能支撑他走到最后”[10]ix。事实上,作为专业汉学家,雷慕沙对古代中国的一夫多妻制早有了解。此前他翻译的《玉娇梨》亦讲述了两女心系一男、三人喜结连理的故事,他在该书译本序言中表达了他对书中这种特殊婚姻状态的看法。一方面,雷慕沙很清楚欧洲道德体系下的民众对一夫多妻制极为反感;另一方面,雷慕沙认为这是民族习惯和国家观念的不同,呼吁读者“用小说家的眼光而不是用道德家或哲学家的眼光来考察事物”,提议读者去观察作家如何从社会制度中汲取养料来完成自己的创作。[8]80可见雷慕沙对《合影楼》结局的批评并非基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分歧,而是出于对故事本身情节发展的不满。
戈蒂耶也了解过《玉娇梨》中的情感模式,他发表于1833年的一则短篇小说《选哪个》(Laquelle des deux)就以第一人称身份讲述了男主人公同时爱上一对孪生姐妹,不知该选哪个,最终两姐妹都离他而去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借男主人公之口提及《玉娇梨》,表示苏友白同时爱上白红玉和卢梦梨的情节让他对这本中国小说“有一种奇特的欣赏之情”,因而视其为“世界上最美的小说”。由此可见,无论是雷慕沙还是戈蒂耶,两人均未对《玉娇梨》情节表现出不适和反感,反而以一种“猎奇”的心态视之。然而与《玉娇梨》不同的是,《合影楼》中的锦云与男主人公并无感情基础,她是为解决男女主人公面临的棘手问题而出现的,缺乏主体性意识,该角色的设定破坏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纯粹的爱情。高唱唯美主义论调的戈蒂耶选择了摒弃这一角色,在他的改写版本里,男女主人公双方没有权力和地位的差异,也没有第三人的介入,从而实现了一种美学上的平衡与和谐。这样的处理增强了故事跨文化的审美吸引力。
(三) 人物的唯美重塑
相比《合影楼》原作,《水榭》中所有人物的形象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美化。尤其是女主人公玉娟,与原作的形象有很大区别。在《合影楼》原文及其翻译文本中,叙述视角和叙事焦点皆在男性,而玉娟虽是故事的主人公之一,但她的所言所行占据篇幅并不多,远少于男主人公珍生和周旋于两家之间的路公,关于玉娟的描写也多从珍生的视角展开。她虽通晓诗书,且有自由恋爱之意愿,但骨子里仍是一个胆小矜持、不敢违抗父命的封建女性,对男主人公娶二妻的安排也欣然接受。李渔笔下的女性呈失语状态,原作中罕有女性的心理描写,在封建父权文化语境中,女性自觉将男性观念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行为规范。而戈蒂耶的《水榭》则展示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完美玉娟:她拥有惊人的美貌,更拥有非凡的才华,绣花、书法、吟诗作赋,样样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她个性独立,对爱情持有坚定的主见,在遇到珍生之前,她“素来认为自己在世上是无双的”,谢绝了众多向她求婚的男子,宁愿承受“独自踏入桑榆”的孤独,也不愿为了婚姻而委屈自己。她受父母所宠,父母也完全尊重她的想法,面对她的固执,父母只是暗暗叫苦,却没有半点责备之意。这样的玉娟,已然脱离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女性形象。戈蒂耶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玉娟的才艺与性情,刻意塑造了一个在西方读者眼中完美的中国女性形象。在描述男女主人公首次在水边因影相遇的场景时,戈蒂耶摒弃原作的全知视角,而采用聚焦玉娟的内视角,放缓了叙事节奏,细致描写了从玉娟眼中看到的风景、对面的人影,以及她因对影生情而波涛翻涌的内心世界。
在这则中国故事中,玉娟就是美的化身,承载着戈蒂耶的美学理念。当写道玉娟因看到珍生的影子而心动时,作者一改波澜不惊的叙述风格,迫不及待地为玉娟辩护:“世人不必因此而轻易责怪玉娟轻浮。仅仅因为一个男子的影子便动情……这固然疯狂!但在没有通过长久来往而深入了解一个人之前,我们又能从他身上看到什么?无非是他外在的一面,与镜中之影没什么不同。少女的本性,不就是凭牙齿的洁白和指甲的修剪来揣测未来郎君的性情吗?”[17]1128明面上,作者在为玉娟辩护,而实际上,作者是借故事的旁白之口传达自己追求“形式美”的理念,是为自己“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辩护。
四、结语
《水榭》是戈蒂耶基于汉学家的译作,间接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的创造性改写,是中国的故事原型和作者的“异域”追求、唯美追求相交汇的果实。李渔笔下的中国爱情故事经过汉学家、域外作家的多层次传承,实现了跨文化突围。事实上,法国作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本进行创造性改写,在戈蒂耶之前已有先例。早在1747年,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Zadig ou la Destinée)的第二章就是对耶稣会士殷弘绪所译《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改写,而1755年,伏尔泰又将耶稣会士马若瑟所译《赵氏孤儿》改写为《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在巴黎公演后好评如潮。以汉学为媒介,中西文学会合、交融,原本的故事话语在不同文化的互动和碰撞中得以更新与再生。
作为“19世纪上半叶法国文学讲述中国文化的稀有之作”[25],《水榭》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正如岱旺所说,“在戈蒂耶的庇护下,中国文化和文学荣耀入场,登上了法国文学的舞台”[12]77。戈蒂耶打破了19世纪初期法国文坛对中国文化的淡漠,重燃了法国作家对中国题材的热情。另一方面,戈蒂耶以其在法国文坛的影响力,将李渔的作品由汉学圈引向文学圈,将雷慕沙“小众化”的汉学转译作品,变为经过精心润色的法国主流文学,由此跨越文化障碍和文学界限,进入世界文学空间。从《合影楼》到《水榭》的翻译和改写过程,生动地阐释了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充分展示了早期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