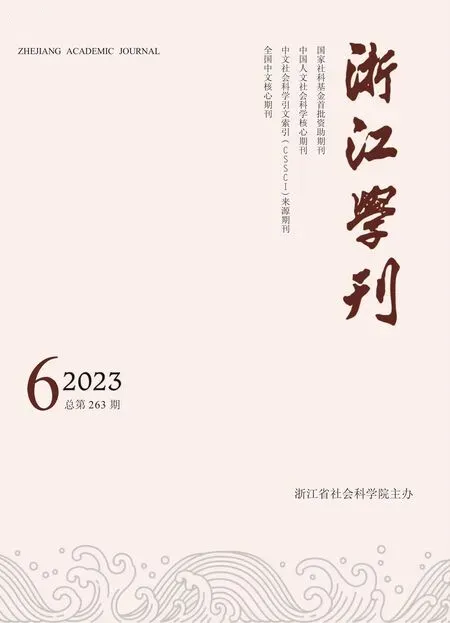阐释·诠释·解释·说明
2023-03-10李红岩
李红岩
提要:阐释学内部主要包括四个概念,即阐释、诠释、解释、说明。“阐释”在于表明一种不饱和的整体性非封闭展开状态,即 “思的开放”。“诠释”是在确定、收敛、统一中将“看”的行为实施出来,同时在“看”中确定“作什么”。“解释”是“再通过讲说加以昭显”,即将“共置”或“端呈”之物的内部结构展示出来。“说明”在于对经过确定、解构、分析、显明之后的对象的功能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予以言说与揭示。四个概念依次递进,即从抽象到具体。倒转过来,则意味着从具体到抽象,同时标识着阐释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关于阐释行为的内在结构或基本范畴,或曰阐释学(Hermeneutik)的内部概念层次结构,应是一个层级性的概念有机体。这个概念有机体,主要由四个概念组成,即阐释、诠释、解释、说明。四个概念的外延,依次收缩递进。在谈到现象学与阐释学的关系时,保罗·利科认为这些概念是现象学的阐释学前提。(1)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洪汉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85页。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谨从张江先生关于“阐”“诠”“解”辨析的论文(2)张江:《“阐”“诠”辨》,《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出发,对这四个概念略加检核。
一、关于“阐释”
“阐释”(Auslegung)在于标明、呈现某种整体态势。具体说,就是开放性、延展性、多样性的态势,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谓此在的“开觉”或“打开”状态,是一种Ganzseinkönnen状态,即不饱和的整体性非封闭展开状态。或者说,它更像是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哲学本质:“一种思的开放”(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形而上学导论》,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页。。
在德文中,与Auslegung这个名词相应的动词是auslegen,具有陈列、摆出、展示、铺设、布设、规划、布局、放出来等意思,显然与上述所言一致。
《春秋繁露·精华》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核心意思就是标明开放性。其中“达”包含“向”的意思,向一种可能性存在,“向能够存在的被展开的可能性投开”(4)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85页。。因此,“阐释”意味着在谈话开始或进行当中不首先制定与遵守一套约束性模式,意味着对基础认识论的反对。
上述意思,恰好浓缩在汉语的“阐”字当中。这是张江先生的一个发现。在汉字中,“阐”的本义是“开”;“开”的本义是“张”;“张”的意思是“施弓弦”。“施弓弦”的特点是已经察觉对象,但并未表明具体是哪一个对象。无论对象是一种行为,抑或是一个确定的物体,“阐”都意味着这个对象处在一种开放的可迎受他者的状态当中。因此,所谓“对象”只是对“可能性”的标明,而不仅是一个固定的靶子。在汉语世界,“阐”总是与“义”捆绑,连成词组,古籍如《春秋阐义》,即属此类。“义”的多义性与“阐”的多义性相对接,释放出开放性的意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总趋向,一言以蔽之,即“阐”。正如卡普托所说,这本书“唯一根本的东西”就是它“创造的开放性,而不是解决”(5)约翰·卡普托:《激进诠释学:重复、解构与诠释学筹划》,李建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页。。这正是罗蒂心目中阐释学的立场,亦即阐释学只表达一种希望,“由认识论撤除所留下的文化空间将不再被填充”(6)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35页。。“不再被填充”就是所谓“创造的开放性,而不是解决”。“解决”则意味着“达诂”“达占”“达辞”。当然,《存在与时间》所创造的开放性,并非没有具体所指。它所创造的开放性,实际上是生存论意义上此在的开放性,也就是人的开放性。
众所周知,早在三十几岁时,海德格尔就对Hermeneutik这个词作了词源学意义上的简单考察。他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施莱尔马赫直到狄尔泰涉及这个词的使用情况及涵义,统称为传统概念,而他的新阐释学理念,则旨在使此在“彻底觉醒”。为达到此目的,他指出阐释学绝不意味着“尽快结束”,“而是要尽可能长久地经受”。(7)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1、24、26页。在《存在与时间》导论的第七节C段,他又专门对这个词的基本意思作了说明。再后来,他甚至不再使用这个词,目的只是“为了让我的思想保持在无名之中”(8)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4—97、116页。。所谓“无名之中”,亦即敞开状态,不被名称所固化,向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开放,特别是回到《老子》所谓“无名,天地之始”的始源状态。
那么,“阐释”与“理解”是什么关系?从“理解”的视角是否可以显现“阐释”的上述基本特性?对此,海德格尔是有相关论述的。在他看来,正是通过阐释,理解才得以成型。也就是说,“理解”之所以能够被人理解,必然要由“阐释”来加以表明。他说:“开觉状态之形诸存在就构成了理解;而阐释是开觉状态之形诸存在的实现方式。”可见是“阐释”将“理解”实现出来。阐释虽然是所有认知的基本形态,但它“并未在原本的意义上有所开显(erschließt),因为理解或此在本身所经营的就是这种原本的开显。”换言之,“阐释”只是一种次生或附属行为,“理解”才是原生行为本身,阐释则将这种原生行为从“开显”带向“彰显”,而“彰显”反过来“就构成了理解的一种内在的可能性的成型过程。”因此,“阐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昭示”或“突显”。他说:“阐释的最为切近的日常样式具有昭示(Appräsentation)的作用形态,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关于意蕴的昭示,也就是对向来可通达的指引关联所作出的一种突显。”那么,这种“昭示”或“突显”的过程、方法与目的又是什么呢?他说:
阐释将照面中的世上物的有待被看“作什么”(als Was),即有待被理解“作什么”带向彰显。作为理解之成型,所有阐释的源本的形态就是以其“作什么”为据的关于某物的称述(Ansprechen)、把某物看作某物的称述,这就是说,将那在源本的和引导性的称述中得到昭示的东西再通过讲说加以昭显。……通过对某物的“何所为”(Wozu)和“为何之故”(Worumwillen)加以彰显,不可理解状态得到了去除,意蕴的意义仿佛成为清晰可见的,此意义形成了语词。(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06—407页。原译文将Auslegung译为解释。
这些话并不特别拗口。它表示,作为对开放性、延展性、多样性状态的呈现,阐释本身并未在原本的意义上有所开显,因为这种开显需要理解去经营,“阐释所操办的,从来都只是对被开显者的彰显”。所以,阐释意味着“昭示”“突显”“昭显”“称述”,意味着“指引关联”,意味着去除不可理解的状态,意味着将意蕴的意义引向仿佛清晰可见,意味着可以用一个语词去凝缩这些意思,等。“阐”字的形成,意味着它的语词意义与它所意谓的实事得到了区分,意味着这个词的意义结构很复杂而“就其不同的阐释可能性而言更为变化多端”。海德格尔的这些论述,可以说很好地诠释了汉语“阐”字的意蕴,使得其意义“仿佛成为清晰可见”的了。
这种诠释,从理论层次上讲,表明“阐释”处于最为居先的位置。海德格尔认为“阐释是所有认知的基本形态”,这就表明了这个词作为概念的一般性与统摄性。我们从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非常偏爱这个词。但是,“阐释”的居先位置,从本质上说,是由“阐释”的“先”结构所决定的。保罗·利科在介绍海格德尔的相关思想时,特别强调了阐释相对于阐释对象的居先性。他说:
解释(interpretation)对理解的依赖性说明了阐释(explication)为什么总是先行于反思并在最高主体构造任何客体之前就出现。这种先在性在阐释层次上是由“预期结构”来表现的,预期结构阻止阐释不依赖前提而对先给予的存在进行把握;阐释在先有(Vor-habe)、先见(Vor-sicht)、先把握(Vor-Griff)、先见解(Vor-Meinung)的模式中先行于它的对象。(10)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洪汉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2页。
这种理解与汉语“阐”字所蕴含的意思,完全相符。“阐者,开也”,显然还具有打开阐释的“先”结构的意思。
这里所谓“先……”,即《庄子·天下》引惠施所谓“今日适越而昔来”。钱基博解释说,“今日适越,昨日何由至哉?思适越时,心已先到;犹之是非先成乎心也”。“旅人之适越,在今日也;而云‘昔来’者,心先驰也。”(11)钱基博:《子部论稿》,傅宏星校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这可以说是对海德格尔所谓“先结构”的绝妙搭接。所谓“是非先成乎心”,所谓“心先驰”,正是所谓“前见”“先见”。当然,这并非唯一的解释。比如李约瑟说:“这个辩辞竟然像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教科书中的一段。确切地显示出承认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时间尺度’。”(12)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江晓原主持,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7页。这种相对性的解释,与所谓“心先驰”的“前结构”显然并不矛盾。当然,我们绝不可以说,惠施已经具有海德格尔那种意义上的“先”结构理论。
二、关于“诠释”
巧得很,“诠释”之“诠”,与德文的interpretation一词非常贴合。
如果说阐释将照面中的世上物的有待被看“作什么”(als Was),即有待被理解“作什么”带向彰显,那么,“诠释”就不再是“带向”,而是固化或固定。具体说,就是将“有待被看”的“有待”去掉,在确定、收敛、统一中将“看”的行为实施出来,同时在“看”中确定“作什么(als Was)”。
在汉语中,“诠”的本义是“具”;“具”的本义是“共置”,具有海德格尔所谓“给出”“端呈”的意思。(13)参看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4页。只有“给出”“端呈”“共置”,才能“看”,也才能看出对面是什么(als Was)。因此,如果说“阐”之德在于“圆而神”,那么,“诠”之德就在于“方以智”。在带向彰显的开放状态中进行确定,确定照面中的世上物“作什么”(als Was),就是“诠”。
海德格尔关于“置放”的讨论,有助于深化对“诠”这个概念的理解。在解读巴门尼德的过程中,海德格尔很详细地讨论了“置放”的意义。他以图书出版为例,指出“书出版了,意思就是,它现在呈放出来,它在此了,它作为在场者现在可以与我们有关了”。他接着说:“置放,即言说、置放,关涉到呈放的东西。置放就是让呈放。当我们关于某物说些什么时,我们让它作为这样那样的东西呈放出来,同时也即让它显现出来。使……达到先行显露和让……呈放,这就是希腊人所思的‘言说、置放’和‘逻各斯’的本质。”其结构是“需用:置放、让呈现”(14)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什么叫思想?》,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3—234页。。这些言词,让笔者感觉好像是在解释汉语的“诠”字。
“诠释”的西语词源,美国学者佩顿(William E.Paden)说,interpretation这个词来自拉丁语interpres,意为“介于双方之间的代理人,谈判者、掮客、解释者”。前缀inter-是“介于……之间”的意思,但pres的含义有点争议。有人把它与pretium相联系,即“价值、价格”;也有人把它与梵文的词根prath-相联系,意即“向海外传播”(15)W.E.佩顿:《阐释神圣:多视角的宗教研究》,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伽达默尔说,interpres“指的是居中说话者,首先指的就是口译者的原始功能,口译者处于操不同语言的讲话者之间,通过他的居中讲话把操不同语言的讲话人联系起来。正如在这种情况下是克服外语的障碍,当在操同一种语言时出现理解障碍也需要进行克服,在这种情况下是通过回溯,亦即把它作为潜在的文本而达到陈述的同一性”(16)伽达默尔:《文本和解释》,洪汉鼎主编:《伽达默尔著作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444—445页。。总之,它突显的是“居中”或“居间”串联说话的意思。由于这种属性,故interpretation应属于伽达默尔所谓再现性的阐释。
海德格尔也简单讨论过inter这个拉丁词的语义,以之说明“世界”与“物”贯通时的“中间”状况,指出只有在“中间”中,二者才成为一体,因此才构成亲密关系,但“亲密”并非“融合”,因为在亲密关系中“有分离起作用”,“在区-分中成其本质”(17)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第16页。。
作为一个动词,正如学者所说,interpretieren常见于音乐演奏,是指演奏者解读乐谱。马克思所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的“解释”,用的就是这个词。马克思之所以使用这个词而不使用更具哲学意味的verstehen,就因为这个词更容易理解。(19)彼得·奥斯本:《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导读》,王小娥、谢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5页。所谓“更容易理解”,即包含这个词的意义更加固化的意思。伽达默尔说,interpretation这个词既被用于科学的解释,同时也被应用于艺术的再现(Reproduktion),例如音乐或戏剧演出。(20)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15页。所谓“科学的解释”,显然就是不容易产生歧义的解释,也就是更具有固定意义的解释。将这样的词同时用于音乐或戏剧演出,也就是将相关的解释引向固化,而非引向开放。反过来说,一般被翻译为“阐释”的另一个德文词Auslegung,并不被用于艺术的再现领域,因为它的意思更开放。
interpretation在非语境的纯语义意义上,只能对应汉语的“诠释”。但在特定语境下,它可以指向“诠释”下面的一个类型,即“解释”。换言之,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哲学家们都是用“解释”的方式去“诠释”世界,就仿佛演奏家们诠释音乐的意义。上述讨论表明,“诠”对于意义的固化、固定或确定,是由于居中者的言语行为,使得围绕或面对共置物、端呈物的各方达成共识,比如依据价值而达成价格谈判上的一致,讲不同语言的人达成同一性的理解,在分别中达成亲密关系等。所以,固化、固定、确定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居间说话的协调活动来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维柯指出,“诠释”一词与“父亲”“工作”具有关联性。这实际上是把“诠释”行为所具有的神圣作用与一般意义揭示出来了。他说,“爸爸”这个词来自惊叹声,然后又派生出多种意思。他说:“patrara(父亲)一词的原义是‘制作’或‘工作’,这是天神的特权。patrara这个词的原义也用在《圣经》中,《创世纪》里说,‘到了第七天’神停止了‘他在做的工作’。从工作(opere)这个词一定派生出动词impetrare,仿佛就是代impatrare,占卜术是用interpatratio(解释),即解释占卜中天神的谕旨。”(21)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09页。维柯这段话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在西方,神就是父亲,父亲就是工作者,工作是指神的或为神的工作,而这种工作需要或带来诠释。希腊宗教中的宙斯,即有父亲之意。(22)约翰·博德曼等编:《牛津古希腊史》,郭小凌、李永斌、魏凤莲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年,第290页。在这里,汉语译者朱光潜先生将interpatratio标为解释,我们则无妨将其看作诠释。总之,从维柯的论述可知,诠释是一份非常神圣的工作。
与东方不同,父亲在这里并不单纯地表示血缘关系,更标识血缘与信仰的统一,即“神父”的意思。血缘与神性、神性与血缘相贯通,而血缘最终服从神性。而在中国,血缘则与宗法相贯通,神圣性最终来自宗法性,即所谓“祖宗”。“神父”与“祖宗”分别标明两种不同的神圣性,一将血缘归于神性,一将血缘归于宗法,由此而成为中西精神血脉、文化基因不同的一大关键。
关于中西文化基因在宗法性上的差异,黑格尔说:“希腊没有出现任何宗法的家族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建立在家族关系的基础上的”,“希腊人不是由若干个部落合并而成,而是由诸多部落和民族混合而成的”。而“中国的国家原则完全建立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之上。这种关系决定了一切”(23)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黑格尔全集》第二十七卷,第I分册,刘立群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22、285页。。大量史料表明,这种区别极大地造成了中西之间思维方式、阐释行为及阐释范式的不同。
三、关于“解释”
在“诠释”中,“作什么(als Was)”被整体性地“共置”“给出”“端呈”出来,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接下去,依照海德格尔的提示,还需要“再通过讲说加以昭显”,需要把“何所为”(Wozu)和“为何之故”(Worumwillen)彰显出来,从而达到“意蕴的意义仿佛成为清晰可见的”这一效果。如此一来,“解释”(Erklären,Erklärung)便登场了。
“解释”的作用,在于将“共置”或“端呈”之物的内部结构展示出来,“通过讲说加以昭显”。具体说,就是看看“端呈”之物的里面是什么样的,以达到“清晰可见”的效果。
德罗伊森说,有三种科学方法,一种是哲学、神学的玄思方法,即erkennen(认识);一种是历史方法,即verstehen(理解);另一种是物理的方法,即Erklären。(24)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请注意他对Erklären这个词的用法,完全偏重在词义的“物理”性(即自然科学属性)上。
在汉语中,“解”字的物理性同样非常鲜明。“解”的本义是“判”,也就是用刀去解剖、分解。因此,“解”首先意味着一个物理性对象的存在。由针对这个物理性对象的行为,引出“解”的结构特点,即对确定对象的分析,将整体要素化、对结构明晰化,对“诠”的“再讲说”。
由于将整体要素化,因此在“解”中分离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由于这个问题的出现,因而又辐射出胡塞尔关于具体部分和抽象部分、独立部分和从属部分的区隔辨析一类问题。对此,我们暂且打住。
显然,“解”最突出的行为特征是“分析”。解释就是通过分析方法去讲解。黑格尔说过,分析方法是经验主义最常使用的方法。这个方法的特征,黑格尔描述道:“分解过程的主旨,即在于分解并拆散那些集中在一起的规定,除了我们主观的分解活动外,不增加任何成分。但分析乃是从知觉的直接性进展到思想的过程,只要把这被分析的对象所包含的联合在一起的一些规定分辨明白了,这些规定便具有普遍性的形式了,但经验主义在分析对象时,便陷于错觉:它自以为它是让对象呈现其本来面目,不增减改变任何成分,但事实上,却将对象具体的内容转变成为抽象的了。”(25)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3页。这段话非常漂亮地揭示了汉字“解”的意蕴。所以,“解释”的功能是进一步地趋近于澄清,故可视为澄清性阐释。海德格尔说:“澄清解释即是对不领会的东西有所领会地加以揭示,故而一切澄清解释都植根在此在的原本的领会中。”(2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中文修订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58页。显然,“解释”同样具有先见结构,并不像经验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直接、简单,但是,它“有所领会地加以揭示”的基本意涵是清晰确定的。
从语言多义性角度看,“解释就在于辨别出说话者在普通词汇的多义性基础之上建构什么样的具有相对单一的信息。用多义性的语词产生出某种相对单义性的话语,并在接收信息时识别这种单义性的意向:这就是解释的首要而最基本的任务”(27)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洪汉鼎译,第5页。。从多义性走向单义性,就是走向确定性,也就是黑格尔所谓“把这被分析的对象所包含的联合在一起的一些规定分辨明白”,当然也就是“对不领会的东西有所领会地加以揭示”。
汉语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很形象地揭示了上述基本意涵。庖丁解牛之所以称之为“解牛”而非“诠牛”或“阐牛”,即在于突显其分析的本质。当单义性话语被建构出来时,“牛”所包含的联合在一起的规定被分辨明白,解牛过程完成。
因此,“解释”以“解构”为行为的起点与过程,“在于分解并拆散那些集中在一起的规定”,然后从中识别出单义性的意向。但是,它们并非一回事,而各是释义过程的相关项。“解释”是目的,“解构”则是手段与过程。“解构”意味着拆开(undoing)与拆除(ab-bauen),以达到“解释”必然需要的释放效果,达到以“解”为“释”的目的,但其本身并不含有释义功能,其释义功效是“解释”赋予的。“解释”与“解构”虽然都以“解”为前提,但前者落脚于“解”的目的或结果——释,后者落脚于“解”的对象、手段及过程。解构是拆解结构,解释是认识结构。解构提供构件,解释提供说明。处在“解构”与“解释”之间的,是“分析”。
就历史学而言,“解释”首先意味着对史料的分析,即展示史料如何“讲得通”。因此,它具有阐明或澄清的指向。其次,它意味着对历史现象组成要素及各种原因的揭示。在各种解释中,最好的解释就是将要素分解得最为充分、呈现得最为详备的解释。
四、关于“说明”
“说明”(Anleitung;Exposition)在于对经过确定、解构、分析、显明之后的对象的功能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予以言说与揭示。比如一架被拆解的飞机,拆解者一一指明其不同部件、组件或零件是做什么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康德在解释拉丁文exposition时,说他将其“理解为将一个概念里所属的东西作出清晰的(哪怕并不是详尽的)介绍”(28)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册,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因此,“说明”并不派生出或复合出与它对等的概念,而是在“介绍”的范围与规定下运作,所针对的是“概念里所属的东西”。就整体而言,“说明”没有增加任何东西,但就认识的深入性与上手性而言,它又是扩展的。很显然,相对于“阐释”与“诠释”“解释”,“说明”其实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解释”是进入“事物内部的理解和诠释”,“重点在阐明那个事物存在的理由,它的重点是在reason,就是理由”。“解释”“要先有一个消极性的‘瓦解’过程,再达到一个新的‘开显’的过程,并且落实下来,用另外新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那个牵涉一个积极性的‘建构’。”而说明(explanation)“重点是一个外在的、扩张性的因果说明”,“重点在causation”(原因)。总之,“说明”是比较外在性的,解释是比较内在性的。(29)林安梧:《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这个观点是可取的。它肯定了“解释”必然具有的“瓦解”即分解过程,这与笔者的分析一致。分解的目的和结果是“开显”,因而是积极的。这与笔者的分析也一致。同时,“解释”意味着进入“事物内部”,这又与笔者的分析一致。不同在于,笔者将“说明”指向“要素”的介绍,这里指向“原因”的揭示。但是,这种不同也不矛盾,因为对“要素”的“介绍”,也就是对“原因”的显明。原因在哪里?就在要素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当中。因为“说明”只是介绍整体内部组成要素的性状,所以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许多思想家认为,传统历史学实际只是在“说明”的层面上工作。“说明”就是对“为什么”的回答。
很明显,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主流历史学,都是说明性的。这种主流史学通过描述史实来追问本质,认为历史的本质是第一位的,描述与叙事都服从于历史的本质。但是,到21世纪90年代,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历史学绝不可停留在“说明”层面,而应向上提升。因此,以往那种以“说明”为属性的史学样式整体性式微。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流行,“描述”(description)与阐释的功能得到突显(当然“说明”的取向与主张并没有消失)。(30)阿兰·梅吉尔:《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黄红霞、赵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特别是在史学理论系统中,由于历史阐释学对于历史认识与历史知识理论的强调,使得整个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表现出鲜明的阐释性,从而使得史学理论的焦点与范围不再局限在方法论与文献技术的范围之内,而更趋近于阐释学。(31)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页。
换言之,就阐释学的概念而言,当下的历史学已经不再局限在“说明”的层面,而是向着解释、诠释、阐释的层面提升、扩展。这正是历史阐释学要表明的一个基本道理。
五、关于四者的关系
阐释、诠释、解释、说明是依次递进的关系,所以上层概念不一定运行至下层概念,而下层概念却必定蕴含上层概念。“阐释”可以不涉及诠释、解释、说明,但后三者却均以自己的方式和范围在“阐释”。吃水果并不一定意味着吃苹果,但吃苹果一定意味着吃水果。四者的逻辑与实际关系,正相仿佛。
哲学家解释世界,就是用解释的方法阐释世界。哲学家解释世界,都希望确证世界的确定性。因此,就目标而言,他们其实都是在“诠”,亦即建构一种完备、完足的确定性理论体系。
在西方传统中,只有体系,才是确定性的固化形态。所以,恩格斯说,“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3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海德格尔说:“唯当认知是绝对认知,才能够以合乎认知的方式来发现和塑造这样一种体系。在德意志观念论中‘体系’被明确把握为绝对认知的要求。体系本身就明确地成了绝对的要求,并由此不折不扣地成了哲学的主导词语。”(3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王丁、李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9—70页。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主流趋向,就是打掉这种以建构绝对认知为目标的哲学体系,而现象学与阐释学在其中发挥了众所周知的重要作用。
因此,马克思说哲学家们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可以理解为直到马克思的时代为止,哲学家们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建构体系,也就是以“诠”为目标。这是观念论的基本特点。
有德汉词典将“interpretieren”一词直接翻译为“诠”。可谓确当。进入具体语境,将其翻译为“解释”,也顺理成章。至于有学者将这个词翻译为阐释、说明,则是出于个人理解,当然也不能认定为错。对此,在义理思辨澄明之后,只须心知其意、得意忘言。
阐释、诠释、解释、说明四个概念的关系,可以通过庖丁解牛这一经典案例加以说明。从庖丁解牛的故事看,“阐释”在于遭遇一群动物——海德格尔所谓照面中的世上物,“诠释”在于从中确定一头牛,“解释”在于分解牛,“说明”在于对分解后的牛的心肝肺等要素一一予以介绍。
单就庖丁解牛的“解”而言,又可以细分为阐、诠、解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所见无非牛者”,是为族庖阶段,为“阐”;第二个环节“未尝见全牛”,是为良庖阶段,为“诠”;第三个环节“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是为道庖阶段,为“解”。这三个阶段,“正是一个完整的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34)参看庞朴:《解牛之解》,《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1995年,第192、216页。
上面所言种种,包含一个逻辑顺序,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亦即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所谓反身抽象,或如马克思所说“叙述的方法”。
从阐释、诠释到解释、说明,是概念不断下降、落地的过程,是概念的演进。如果我们将这个逻辑顺序倒转过来,单纯从阐释学实际发展的历史循序来考察,则会形成另一个先后顺序,即发生学意义上的秩序,或如马克思所说“研究的方法”。也就是说,从说明、解释到诠释、阐释,又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概念上升、扩展过程。
洪汉鼎先生对西文的“阐释”一词作了专门探究,提出“阐释”既不同于“说明”,又与一般“解释”相区别,Auslegung应该翻译为阐释而非其他。这一见解,显然是正确的。洪先生又依据杜登(Duden)大辞典提出,Interpretation是一个“种”的总体性概念,而Auslegung与Erklärung均是它的“下属”概念、下属类型。这种解释或许适合于科学主义统领一切的时代,但自新康德主义之后,情况则发生了翻转。
杜登辞典的义项解释,乃是Interpretation一词的单纯词义,而非阐释学的学科概念。单就词义而言,阐释、诠释、解释、说明之内部,均可细分为这四个部分。以“说明”为例,其运转过程,即可析出阐释、诠释、解释、说明四层结构。因此,认为“说明”统领着“阐释”,也未尝不可。但是,一旦从词义跳到学科系统上来,特别是从哲学阐释学运用上述四个概念的实际情况来看,就会发现真正的“种”概念,应该是“阐释”而非“诠释”。这一点,从洪先生的具体论述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
比如,洪先生提出,Interpretation的特征“只是把已经明确说出的东西加以说明”。这就表明这个概念是有前提的,也就是所谓“已经明确说出的东西”。而Auslegung的特征,洪先生说是“通过解释主体的努力和发掘,把解释对象未能明显表示出来的东西揭示出来”。换言之,这个概念的前提是“未能明显表示出来的东西”。“未能明显表示出来的东西”当然居于“已经明确说出的东西”的前面。因此,我们认为,Auslegung居于Interpretation的前面,其总体性特征较之Interpretation也更加突出。
在Auslegung一词的使用上,狄尔泰曾强调它在人文精神科学领域的常用性。在阐释学视域下,狄尔泰将“理解”设定为人文学科或精神学科的主要关切、关键概念,从而“用一系列特有术语对之加以阐释,尽管这些术语基于一种心理学化的生命哲学”(35)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杜玉生、卢华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9页。。
海德格尔也非常重视这个词,说它代表一种“更为深刻”的阐释活动,“强调揭示性的和阐发性的更深一层意思”,是一种深入的揭示活动,是一条“主导观念自身以其光芒四射的力量显露出来”的道路。所谓“更为深刻”或“更深一层”,显然不是指外延更为狭窄,而是指更为广泛,不然就谈不上比Interpretation意思彻底,更富于“揭示性和阐发性”,更谈不上“光芒四射”了。
从狄尔泰与海德格尔对这个词的定位而言,Auslegung显然较之于Interpretation更具有统领性或统摄性。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海德格尔关于阐释一词的用法。洪汉鼎先生曾引用王庆节先生的一段话:“在德文中,Interpretation与Auslegung是两个同义词,一般都理解为‘解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区别使用这两个概念,前者,或者是在一般宽泛解释的意义上,或者是在比较具体的说明解析的意义上讲,而后者则更多的是在海德格尔所讲的存在真理的去蔽、阐明、展开的意义上说。”王庆节表示,他在翻译中将前者译为“解释”,后者译为“阐释”,“但读者也应注意到,由于这对概念的区别在本书中并非紧要,所以海德格尔似乎也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两者”(36)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18页。。这个解释非常重要,笔者深表赞同。但是,这个解释显然并不支持洪先生的论点。
至于Erklärung(洪先生译为“说明”),洪先生说它的特征是常用于自然科学,因而“以描述性为特征”,注重“客观性和描写性”,“平实中庸”,“比较客观”,其取向显然更与专注于精神活动、发誓要驱离自然科学本体论的哲学阐释学的取向不同。(37)洪汉鼎:《论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对此,笔者以为研究者无妨依照自己的理解去抉择去取舍。
总之,一旦立足于阐释学的学术属性,就会发现最具有统摄性的概念,是阐释。由于Interpretation(洪先生译为“解释”)这个词更多地应用于音乐演奏、艺术再现,因此更难说比阐释一词的涵盖性广。
余 论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顺着阐释、诠释、解释、说明的顺序,显然是一个概念下降或展开的过程。在下降或展开过程中,“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思维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因此它“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而在概念上升或归纳的过程中,“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3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0、701页。
总之,“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思维“只能把这样一些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些意识的要素中或者在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3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 页。。
依照上述论述,人们可以顺着下降或展开的过程进行考察,也可以顺着上升或归纳的过程进行思考。下降与展开意味着“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上升与归纳意味着“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但是,每一个“要素”其实都蕴含着“统一体”。这与思维全息理论所揭示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此,从“阐释”到“说明”,是下降或展开;从“说明”到“阐释”,是上升或归纳。就下降或展开而言,“阐释”是一个统一体。就上升或归纳而言,后面三个概念原本就蕴含着这个统一体。搞清这个道理,才会厘清逻辑秩序。
保罗·利科曾说,诠释(interprétation)是解释(explication)的一个构成要素,诠释是解释的“主观”对应项。诠释的第一要务是澄清(clarification)。(40)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第463页。对这样的讲法,须联系具体语境,看其是在怎样的范围与规定内立论的。总而言之,每一个概念都有其结构和功能,阐释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也不例外。对此,应该加以辨析。
依照上升或归纳的过程,将其置于发生学的演进路径上,会发现:说明、解释、诠释、阐释,恰好标明了阐释学发生、发展、演进的四种形态。那就是:“说明”标识神话与巫师阐释学,意在说明创世学说与神的意旨;“解释”标识语文与文字阐释学,意在解释文字与文本的意义;“诠释”标识神学与法学阐释学,意在确证信仰的唯一性与法条的权威性;“阐释”标识一般与哲学阐释学,意在揭示阐释的通用规则与阐释的存在论意义。由此,“历史的”与“逻辑的”达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