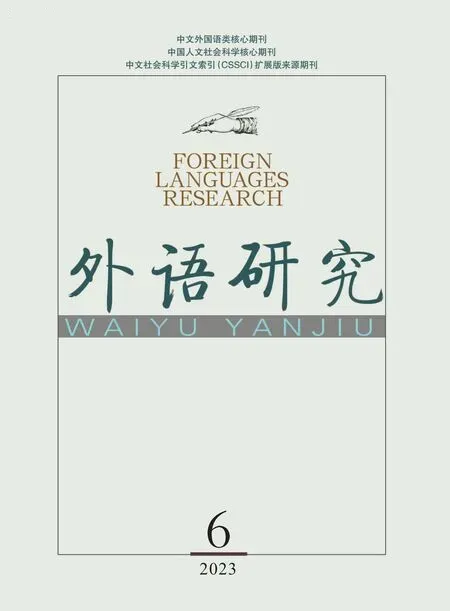德里罗《白噪音》中的环境非公正*
2023-03-08李怀波
李怀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200)
0. 引言
《白噪音》(White Noise, 1985)是“美国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Self 2022)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最受欢迎的小说”(Bloom 2003:1)。德里罗善于描写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与生态自然的对立,其中后工业时代频发的生态危机与生态灾难是其小说书写的重要题材之一。德里罗关注后现代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困境与危机,反思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对立,体现出鲜明的生态意识。对于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国内外从人与自然对立的生态批评视角已进行较多研究,主要分析了作品中因人为因素而导致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灾难及其后果与警示,但这种视角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小说中环境灾难事件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影响而导致的环境非公正现象(Environmental Injustice)。小说中毒雾事件确实占据较大篇幅,但是作者的重点并非毒雾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对毒雾事件的反应,是毒雾事件对社会各阶层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小说中,生活在贫民窟的居民与社会中上层人士所受影响差异巨大;同时,后工业社会以电视、手机与网络为代表的媒介对现实的拟像化表征严重扭曲了人们对现实与自我的理解,现实被放逐,而这些拟像化表征成为了现实本身;环境灾难好似仅在电视等媒体上出现,供特权阶层消遣娱乐,这进一步加剧了因种族、阶级及贫富差异而导致的环境非公正现象的产生。因此,本文将从生态批评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视角解读小说中“空中毒雾事件”的差异性影响导致的环境非公正现象,探讨后现代拟像文化对自我与现实的表征如何影响人们对环境灾难的反应,从而揭示隐含其中的作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1. 环境公正
“环境公正”这一术语广泛使用于20 世纪80年代美国南部黑人社区反对美国政府不公正地为环境有害设施选址而开展的大规模抗议运动(Coolsaet 2021:6;Atapattu et al. 2021:9)。其中1982年北卡罗莱纳州沃伦县非裔美国人抗议政府在其居住区选建有毒物质垃圾填埋场事件成为环境公正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发展至今,尤其是21 世纪初以来,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毒性增加、资源枯竭、物种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可耕地迅速消失”(Ammons & Roy 2015:2)的现实问题,环境公正运动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受瞩目的学术和环保运动之一。作为环保运动与社会正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环境公正运动认为,种族和阶级的社会不平等往往会导致环境不平等,环境风险“不成比例地”影响贫困社区、有色人种社区、移民、原住民和全球其他边缘化社区(Bullard 2000:6-7;Pain & Cahill 2022:361)。“无论在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都是穷人和弱势群体为国家和全球精英的生活方式付出代价”(Atapattu et al. 2021:2)。边缘化群体暴露在更高水平的污染、有毒物质、自然/人为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同时亦被排斥在能够影响环境结果的决策和政府机构之外(Harrison 2019:3)。环境公正主张环境负担和利益应该由所有人平等分享,因为“在对生命至关重要的资源有限的同一个地球上,所有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Wienhues 2017:367)。而“目前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发达国家和世界各地的精英们过度消费资源所造成的环境危害和危险,不成比例地落在世界的穷人身上,其中绝大多数是有色人种,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而环境利益却由占世界人口一小部分的特权阶层所享受”(Ammons & Roy 2015:1)。从经济活动中获益的人与承担其不利环境影响的人之间的不平衡是环境非公正的标志之一。环境问题,从水、土壤、大气污染到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全球变暖等,影响我们所有人。然而,世界各地的环境危机一再清晰地表明,环境问题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平等地影响我们所有人。“这种不平等和有区别的定位,通常将最沉重的环境负担置于边缘化、弱势人群身上,构成了环境非公正问题的核心前提”(Holifield et al. 2018:1)。种族、阶级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与环境风险暴露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和有色人种组成的社区始终暴露于较高程度的环境风险中,如危险废物处理场、空气和水污染、噪音等。“从1945年到现在,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危险废物从500 万吨增加到4 亿吨。这些废物大部分是在富裕国家产生的,并被出口到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处理”(Atapattu et al. 2021:1-2)。因此,环境公正主张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过程中给予所有人公平待遇。环境公正倡导“所有的人和社区都有权得到环境和公共卫生法律和法规的平等保护”(Brulle & Pellow 2006:104)。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改造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开放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世界,其中最弱势群体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转引自Atapattu et al. 2021:5)。环境公正与可持续性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环境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也就无从谈起(ibid.:9)。
2.《白噪音》中的环境非公正现象
在争取环境公正的斗争中,人们认识到环境破坏程度及其危险后果非常重要,但仅仅向人们提供这类信息数据还远远不够。文学在这方面至关重要,且能发挥其独特作用。“以环境非公正现象为题材的虚构故事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是统计数据和风险评估报告所无法比拟的”(Athanassakis 2017:13)。“关于环境破坏的艺术想象力叙事可以帮助人类应对表面上看似无法控制的地球剧变”(ibid.:ii)。正如有论者所言:
对环境公正的呼吁必须深入人们的内心、情感、良知、精神和思想。文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文字具有改变人类灵魂的力量,它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转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提醒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我们真正信仰、熟知并珍惜的东西到底是什么。(Ammons & Roy 2015:2)
令人庆幸的是,古今中外,大量有识之士为此“鼓”与“呼”,留下了很多呼吁环境公正的诗歌、小说、散文、演讲、歌曲、理论作品、调查报告等,成为推动环境公正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对环境非公正现象的关注是《白噪音》的一个重要主题。1985年《白噪音》出版几周之前,印度博帕尔(Bhopal)毒气泄露。由于书籍出版的周期性,实际上《白噪音》在博帕尔毒气泄露之前就已经完成书写了,因此很多评论者认为《白噪音》中描写的“空中毒雾事件”预言了发生在印度博帕尔的化学品泄漏事件。这也让很多读者认为《白噪音》是一部环境灾难小说。对此,勒克莱尔(Tom Leclair)认为,因为对化学有毒气体泄露的描写,《白噪音》确实是一部灾难小说,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灾难小说。德里罗“颠覆了灾难小说的惯例”(2003:7),与流行的灾难小说不同,《白噪音》没有描写伤亡。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灾难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描写对灾难的反应的小说。正是通过小说中各色人等对“空中毒雾事件”迥然不同的反应,尤其是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Jack Gladney)教授对待毒雾事件的态度,德里罗向读者展示了美国后工业社会中人类因自身因素造成的环境灾难,揭示了在面临环境灾难时自以为是的“有身份”阶层的傲慢与环境非公正思想,以及在灾难发生后建构在后现代主义“拟像身份”保护下的虚假幻象砰然崩塌时“自我身份”的否定与重构。
《白噪音》男主人公格拉迪尼是“山上学院”(Collegeon-the-Hill)希特勒研究系主任,该系由格拉迪尼创建,创始人身份赋予了他一定的权威。为适应这一角色,他刻意增加了体重,戴上了厚重的黑框眼镜,修改了自己的姓名(J.A.K. Gladney)。新名字“意味着尊严、意义和声望”,他就像“穿着一件借来的外套一样戴着这个新的姓名标签”(德里罗2002:17;以下此书引文只标注页码)。对于格拉迪尼而言,希特勒已经变成了后工业化社会中被他首先发现的“商业机会”,成为“格拉迪尼的希特勒”,而他自己则变成了“姓名背后的虚构人物”(同上)。甚至就连山上学院院长也因为格拉迪尼“立竿见影的、令人振奋的创新之举”而飞黄腾达,连任“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的顾问”,直至“在上山的滑雪缆车中”去世(4)。德里罗极具讽刺性地指出,后工业化社会中资本主义商品物化已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学术圈。有论者对此评论道,“希特勒象征着所有破坏现代生活稳定的非理性和危险的力量,但对格拉德尼来说,希特勒却是他成功事业的坚实基础”(Cantor 2003:56)。这种建构在后现代主义模拟幻象基础上的身份,是虚幻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在一次因为化工废料泄露而引发的“空中毒雾事件”中,小镇居民仓皇撤离,而格拉迪尼则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有身份的教授,不可能在毫无政府预警的情况下就受到环境灾难的影响。
穷人居住的暴露地区才会发生这些事情,社会以特殊的方式构成,其结果是穷人和未受教育的人成为自然和人为灾难的主要受害者,低洼地区的住户遭受水灾,棚户区居民遭受飓风和龙卷风之害。我是一个大学教授,你在电视上的水灾镜头中,见到过一个大学教授在他所住的街上划着一条小船吗?这些事在铁匠镇这样的地方不会发生。(127)
格拉迪尼认为,社会的构成方式让特权阶层免受毒雾影响。因此,特权阶层漠视发生在弱势人群身上的环境灾难,这会降低特权阶层对于环境保护的“参与积极性”(Murphy 2004:267)。对此,环保主义者尼克松(Rob Nixon)创造性地提出了环境公正运动中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术语“缓慢暴力”(slow violence)。根据尼克松的说法,缓慢暴力是“一种逐渐发生的、看不见的暴力,一种分散在时间和空间的延迟破坏的暴力,一种通常根本不被视为暴力的消耗性暴力”(Nixon 2011:2)。有毒污染、气候变化、森林砍伐、土地退化和环境种族主义都会导致“缓慢暴力”的产生。这些不同形式的暴力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但往往被主流媒体和政治体系所忽视。尼克松认为,“缓慢暴力”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不够壮观”,而电视等媒体只愿意报道“壮观”“引人注目”的事情。“我们的媒体对壮观的暴力的偏爱加剧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同时也使弱势人群变得更加脆弱”(ibid.:4)。
特权阶层在休闲的周末全家人围坐在电视前观看水灾、地震、泥石流、火山喷发,并被这些灾难所吸引,为之着迷。“我们寂静无声地看着房屋被大水冲进海洋,一座座村庄在大团流动的火山熔岩中整个儿倒塌、起火。每一场灾难都让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灾难”(71)。格拉迪尼一家人如此陶醉于电视灾难镜头中,希望看到“更大、更宏伟、影响更广泛的”灾难,以至于当教授妻子想调换电视频道时,遭到全家其他人的“激烈抗议”,“对于暴力视而不见,那样才会洋溢一种天真无邪和快乐的精神”(237-238)。格拉迪尼对于弱势人群所遭受的环境危害视而不见显然并非因为灾难“不够壮观”,而是因为主人公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因为这些穷人是“可抛弃的人”,所以这些“引人注目的故事”在格拉迪尼一家看来并不重要。帕里什将此称之为一种后现代文化的逻辑,“它被戏剧性的暴力、死亡和自然灾难的景象所迷惑,同时又因为它们作为图像的可重复性而对其麻木不仁”(Parrish 2013:294)。戴维斯认为,“对边缘化群体的痛苦漠不关心的政治有助于维持环境非公正,使当地受害人对有毒物质伤害的呼声被压制”(Davies 2022:421)。至于泄露化学品,无论收音机里怎么称呼它,“羽状烟雾”“一团滚动的黑色烟雾”“空中毒雾事件”,无论它对人类有什么影响,引起“皮肤瘙痒和掌心出汗”“恶心、呕吐和气喘”“心悸和幻觉”,无论家人们因为传言而感到如何恐慌,格拉迪尼都无动于衷。“这些事情并不重要,至关紧要的是位置。它在那儿,我们在这儿”(130)。“我不仅仅是一位大学教授,我还是系主任。我不能在一场空中毒雾事件中逃跑。那是住在穷乡僻壤的养鱼场附近活动房里的人干的事儿”(ibid.)。面对环境灾害,格拉迪尼的“白种人特权”意识让他“察觉不到”自己易受毒雾的伤害(Murphy 2004:266)。
德里罗在小说中描写了步行的人们逃离时所遭遇的环境非公正现象,情景令人动容。
我们缓慢地驶向一座立交桥,看见上面步行的人们。他们扲着盒子和箱子、床单包裹的物品,一长串人跌跌撞撞进入纷飞的大雪之中。人们怀抱宠物和幼小的孩子,一个老人在睡衣外面裹着毯子,两个女人肩扛一条卷起的地毯。有人骑着自行车,孩子们坐在被拉着的雪橇和手推车中。有人推着超市的购物车,身穿各种各样肥大厚实外套的人们从深深的帽兜里往外张望。有一家人用一张巨大的透明聚乙烯薄膜将他们自己全部罩了起来。他们步伐一致地在他们的罩子下前进,夫妻俩前后各一人,中间是三个孩子,他们都裹在闪闪发亮的雨衣里,作为第二保护层。(134)
在毒雾飘荡的户外,车内的人和车外的人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车内的人可以躲在车内尽可能快地逃离毒雾,而车外的人却携带一切可能携带的物品,用衣物塑料薄膜等“保护”自己,步履蹒跚地、悲壮地、“史诗”般地苦难跋涉。这些“低机动性人口”——老人、体弱者和没有汽车或其他手段逃离城市的穷人——很少受到政府和灾害撤离规划者的关注(Sze 2020:87-88)。
3.《白噪音》中的拟像现实与环境非公正
德里罗描写的是美国后现代社会中的消费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现实被媒体和技术无休止地表征和模拟。“各种媒介吸引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日常注意力,以至于这些媒介不再仅仅表征现实,而是作为现实本身被体验”(Duvall 2008:4)。这与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所描绘的信息世界十分相似。“一个以真实的崩溃和信息社会中符号的流动为特征的世界,一个在模拟的黑洞和符号的游戏与交换中‘真实被放逐’的世界,图像、符号和代码吞噬了客观现实,变得比现实更真实”(Wilcox 2003:98)。现实被脱离其原有意义的图像、符号和象征所取代。这些图像、符号和象征随后被媒体复制、操纵和传播,形成了一个指涉意义递减的“表征迷宫”,掩盖了任何现实或真实性的概念。
通过在小说中描绘电视上的拟像现实取代现实中的灾难这一怪诞而荒谬的现象,以引起读者的关注,这正是德里罗创作《白噪音》的原因之一。1982年德里罗在国外生活了三年回到美国时,开始注意到电视上每天有关于毒物质泄漏等新闻。“灾难只是电视上的灾难,在现实中无人提及,似乎只有灾区人们受到影响,现实中甚至没有人谈论这些灾难。这就是我写《白噪音》的动力之一”(DePietro 2005:23-24)。
小说中,拟像现实取代现实所形成的“表征迷宫”在格拉迪尼参观“美国被拍照最多的谷仓”这一情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到这儿不是来捕捉一种形象,我们之所以在此是来保持这种形象。每一个照相的人都强化了这儿的光环……来到此地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投降。我们所见的仅仅是旁人之所见。过去来此的成千上万的人,将来要到此一游的人。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一种集体感觉的组成部分……这座谷仓没有被人拍照之前是个什么样子?它以前看起来像什么?它与别的谷仓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读过标示牌上写的东西,看见过人们咔嚓咔嚓地照相。我们不能跳出这个光环,我们是它的一个部分。(13)
人们无法看到谷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看到被无数照片、广告和旅游指南所表征的形象。真正的谷仓“没有人看到”了,因为他们受到了符号和照片的影响,这些符号和照片告诉人们应该看到什么。谷仓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和意义,变成了一个拟像,一个没有最初或现实所指的复制品或多层表征之后的产物。
德里罗在小说中讽刺性地指出这种拟像现实如何影响小说中人物的身份、认知和行为,以及电视等媒介“如何潜在地塑造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行为和反应”(Engles 2008:68)。在格拉迪尼看来,社会是为保护特权阶层而构成的,环境灾难只会发生在穷人身上,不会发生在像他一样有身份有地位的特权阶层身上。实际上,格拉迪尼这种“白种人特权”思维也是一种如小说标题一样的“白噪音”,一种能够“淹没”人物身边其他声音的“白种人噪音”。“白种人特权”意识“淹没”了格拉迪尼的感知能力,使其对电视上的毒雾危害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杜瓦尔(John N.Duvall)对此评论道,“生活在模拟文化中的杰克·格拉德尼是一位只对纳粹美学感兴趣的希特勒研究教授,他对纳粹的恐怖历史视而不见。这使他对媒体驱动的、审美化的现在的恐怖同样视而不见”(Duvall 2008:2-3)。灾难失去了最初的含义,仅仅变成在电视上存在的表征符号。“只有灾难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想得到它们,需要它们,依赖它们——只要它们在别处发生”(72-73)。小说中格拉迪尼一家周末非常“有仪式感地”围坐在电视前,“幸灾乐祸地”欣赏各种灾难景象,甚至“觉得非常好玩”(ibid.)。恩格尔斯(Tim Engles)认为“媒体所呈现的暴力的仪式化模式既使我们对暴力的反应变得迟钝,又增加了我们对暴力的欲望”(Engles 2008:71)。
小说中最具讽刺性的拟像现实取代真正现实的情景是灾难撤离过程中的实景模拟演习:
“但是,现在的疏散行动并非模拟,它可是真的。”
“我们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想用它做一个模式。”
“一种实习形式?你是说你们抓到了一个机会,利用真正的事故来进行这场模拟演习?”
“我们的行动实打实地在街头进行。”
“进行情况怎样?”我说。
“嵌入曲线不如我们希望的平稳。可能性超标。此外,假如这是一场实际的模拟,那么应该说伤亡人员并未安置到我们要求的位置。”(153)
这是格拉迪尼与进行模拟疏散(simulated evacuation)的SIMUVAC 组织的一名员工之间的对话。“环境破坏问题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生意’,而不是一个改善美国社会的机会”(Giaimo 2011:87)。奈特(Peter Knight)对此评论道,“在因果关系的逆转中,模拟成为原始事件,而现实仅仅是其模仿的对象”(Knight 2008:30)。真正的灾难被利用成为消费主义的对象,而演习则取代灾难本身成为一种新的现实,比现实中的灾难更现实、比真实的灾难更真实。而真正的灾难及受灾难影响的人们反而没有人关注,“电视网络上空无一物……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张画……没有一篇现场报道”(176)。小说中,在隔离场所手提微型电视机并不时向人们展示空白电视屏幕进行演讲的人愤慨地说道,“难道这类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到没有人再在乎了吗?……怎么竟然没有一个人对于这样的事进行实实在在的报道呢?……难道必须先死上二百个人,够得上称为罕见的灾难场面才行吗?”(176-177)。
鲍德里亚用“超现实”(hyperreality)指称这种生活在一个由拟像和仿真主宰世界中的状态,没有真实与人工、真实与虚假、原创与复制的区别(Baudrillard 1994:120)。在这种“超现实”世界中,拟像现实进一步加剧了弱势群体所遭受的环境非公正。但是德里罗在小说中警示人们:当世界末日一般的空中毒雾真正来临时,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幸免于难。最终,当格拉迪尼一家和镇上其他人一样因毒雾污染开始逃难时,即是主人公“白种人特权”身份开始幻灭之时。这是格拉迪尼思想认知上的一个转折点,只有在这时他才最终无奈接受了这一事实:他和镇上的其他人并无两样。“开始下雪时,我们终于来到了公路上。我们相互间几乎无话可说,我们的头脑尚未调整过来以适应现实的世态,荒唐的撤离事实”(133)。这时候,格拉迪尼再也不把自己看作是高人一等的特权阶层,相反,他认为自己其实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人们在撤离时最容易出现的恐惧,就是权势人物早已逃之夭夭,让我们自行对付一团混乱”(ibid.)。在经过一家家具商场时,他看到里面的男男女女站在硕大的橱窗边好奇地看着外面逃难的人们,觉得自己“好像傻瓜”(ibid.)。里面的人们悠哉悠哉地逛商场,而自己却“在暴风雨中惊慌失措地耽搁在乌龟爬行似的汽车中”(ibid.),他觉得里面的人们可能了解某些外面的人们不知道的内幕消息。在这种恐惧与担忧中,格拉迪尼不断地揿着汽车上的收音机按钮,希望能听到某些“内幕消息”(ibid.)。这时,格拉迪尼已经被迫认识到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与先前他瞧不上眼的贫民窟里的人们别无二致(Olster 2008:79)。“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小说中的重头戏,德里罗对这一事件、疏散和随后的乱哄哄的场面的描述既充满了讽刺,又令人不寒而栗,因为没有一个读者能逃脱‘它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感觉”(Weinstein 2003:133-134)。环境灾难不会只是发生在别处,成为供“有身份的人士”一家围坐在自家客厅欣赏的模拟事件,它会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正如奥斯特所言,《白噪音》“空中的毒雾事件暴露了在后现代的世界中(国家、种族、性别、贫富等)所有的边界是多么的松散”(Olster 2008:82)。
不管是1984年印度博帕尔化工厂发生爆炸,还是两年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亦或是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难等,都被认为是“可怕但单一的灾难”,“事实上,这些和其他类似的环境灾难都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孤立的。相反,它们显然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对弱势群体产生了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Ammons&Roy 2015:1)。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在《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1872)中写道:“如果我们对所有普通人的生活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感知,那就像听到小草的生长和松鼠的心跳一样。那么,寂静对岸的咆哮,会振聋发聩,置我们于死地”(Eliot 2003:194)。“寂静对岸的咆哮”如今已变成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等攸关全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弱势群体不成比例地受害问题。人类的感知受时空局限,但如果我们继续对这些问题充耳不闻、漠不关心,终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将变成《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里所描绘的没有鸟儿歌唱的世界。
4. 结语
环境灾难不成比例地影响弱势群体,上层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拟像现实对真正现实的模拟,放逐并取代了现实本身,这进一步固化了环境非公正偏见,加剧了环境非公正现象。2022年,好莱坞著名导演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对《白噪音》进行了有趣而又非常时尚的电影改编,于威尼斯电影节上映。这再一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部出版于1985年的小说本身。对于这部改编电影,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并被评论界认为可与德里罗相媲美的美国当代女作家达娜·斯皮奥塔(Dana Spiotta, 1966-)在《纽约时报》撰文评论道,这部伟大的经典作品不仅准确地反映了其所处时代,也讲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精准地对当下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诊断,当下20年代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能在这部小说中找到其缩影。其中某些趋势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加剧”(Spiotta 2022)。文化焦虑、科学技术的滥用、人为环境灾害频繁发生、存在主义焦虑、末世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小说中不断呈现。小说中的电视如今已经被互联网和手机所取代,但是这些媒介所具有的“诱惑力和感染并吞噬大脑的令人恐惧的力量”(DeLillo 1985:16)并没有如小说中作者希望的那样逐渐减弱,反而变得尤为令人担忧。小说中描写的环境非公正在当今世界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反而随着环境灾难的增多而日益严重,正如朱莉·施(Julie Sze)在其论著中所言,“环境公正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Sze 2020:2)。恰恰在这一危险的时刻,理解环境公正及其运动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德里罗在其访谈中就创作《白噪音》的动力所言,媒介化、系统化的影响让人们对于某些结构性社会不公正习以为常,冷漠旁观。重读这部“预言式小说”,不仅能让人们对其所处时代的环境非公正及其背后的社会非公正有深入理解,同时也促生了当下进一步推进社会公正与环境公正的紧迫感与使命感。当然,对德里罗在《白噪音》中所描绘的媒介表征的拟像现实与环境非公正之间的关系应辩证分析,不能一味地批判媒介的负面影响而抹杀媒介及时报道关注环境灾难、推动救灾纾困等环境公正方面所起到的正面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