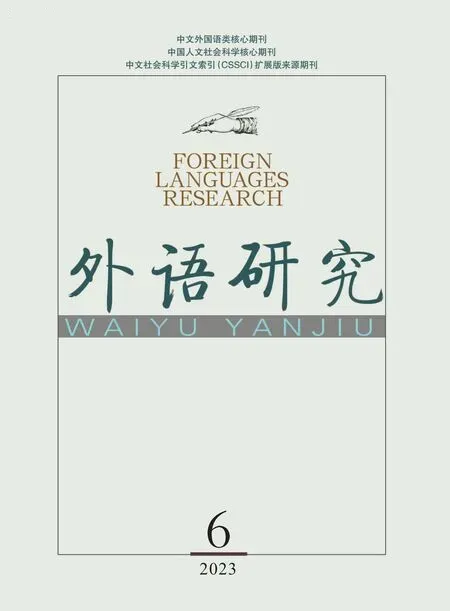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兼容互补性刍议
2023-03-08辛斌
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0. 引言
一直以来,人们试图从社会和认知两个角度解释语言及其使用,“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和“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CL)堪称这两方面努力的典型代表,它们先后对“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来源。从批评话语分析在21 世纪的发展来看,SFL 和CL在CDA 中一方面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互补作用,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在不断地相互影响和融合。
1. 作为CDA 理论基础的SFL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它视话语为说话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空间,在其中同时出现对世界的认知和表述与社会交往互动两种基本的社会过程,因此对语篇的分析离不开对话语实践过程本身及其发生的社会语境的分析。CDA 的这种关于语言及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点要求把语言看作一个多功能的系统,SFL 自然就成为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源。SFL 是一种基于目的和选择上的语言理论,主张语言的本质和功能与其使用者对它的需要紧密相关,关注说话者在具体场合通过语言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SFL 认为自然语言在词汇语法和意义层面上分布着三种不同意义模式:“概念意义”(ideational meaning)、“人际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和“语篇意义”(textual meaning);与其对应的就是语言的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关注经验的识解,将语言视为一种现实的理论和反映世界的资源;人际功能关注如何通过语言经营人际关系、扮演和分配话语角色、协商态度等,是话语实践中主体间互动的一种资源;语篇功能关注如何将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组织成具体语境下的话语。
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看作人类识解经验的三个“基块”(base)。“概念基块”(ideation base)控制语法中概念系统的那部分意义,包括小句中的“及物性”(transitivity)和小句复合体中的“投射”(projection)与“扩展”(expansion)。语言的概念意义资源帮助人们识解世界经验,将自己所经历的现象识解为不同等级的意义单位,组织成各种意义网络。意义单位在这个等级体系的不同层次上执行各种功能或角色,形成各种“构型”(configuration);例如“图形”(figure)是由过程、参与者和情景成分构成的结构,分为数量有限的几大类,包括行为、发生、感知、言说、存在、拥有等图形。概念基块由分别支撑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互动基块”(interaction base)和“语篇基块”(text base)所丰富和补充,前者为交流双方提供经营主体间关系的资源,后者为说话者提供在具体语境中生产话语和引导听者理解话语的资源。
Wodak(2001:8)指出,“要想真正理解CDA 必须首先了解Halliday 语法的基本主张和其对语言理解的看法”。Young & Harrison(2004:1)则认为SFL 和CDA 之间存在诸多共同之处,包括:(1)SFL 和CDA均将语言视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资源;(2)它们都认为语言在所有层面上不仅其表达的内容有意义,其表达形式也有意义;(3)它们皆主张语言和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语言选择取决于交际情景,另一方面这些选择又规定交际事件的性质,包括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4)SFL 和CDA 都主要从语用目的角度考察语言,认为语言系统是为满足其使用者的交际需要而“设计”的,所谓“功能”既指语言演化而来的各种用途,也指说话者在具体话语中的各种用法,它们参与构建社会及其文化:“语言使用总是同时建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知识信仰体系”(Fairclough 1995:134)。
SFL 至少在以下方面有助于CDA 达成其目标。首先,SFL 采取建构主义的语言观,认为人们正是通过语言来识解经验和建构客观世界。这意味着语言并非任意的,它一方面是人类进化的一部分,是人类物质、生物、社会和生存方式的符号反映,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功能以不同而又互补的方式与现实相联系。意义并非先在于实现它们的词语,它们形成于人们的意识和环境之间的互动(Brandt 2020:231-235)。经验范畴和关系并非赋予人们来被动表达经验,而是由语言建构的,词汇语法是这种建构的驱动力。CDA 从一开始就认同建构主义的语言观,认为不同的语言形式或用法因为被使用的语境和交际目的不同而包含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语言并不像传统语言学家声称的那样是人们借以交流思想的透明媒介,它也不仅仅是某种稳定社会结构的反映;语言传播各种世界观,是社会过程的一种不间断的干预力量。话语“既塑造社会,也被社会所塑造”(Fairclough 1992:8)。
其次,SFL 具有社会符号学的性质。Halliday(1973,1978)将语言定义为一种意义潜势,并从语义、语法和语用三个层面对语言进行动态的功能解释,认为语言的形式结构会受到意义潜势的制约。语言使用者做出的意义选择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们具有语言学意义,因为从语言系统中所做的选择可以被解释为意义选择的一种现实化;另一方面,它们具有社会学意义,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人们洞察既是社会结构的表达形式又为社会结构所决定的那些行为模式。因此,Fairclough(1989)在其提出的CDA 三维分析框架中强调对语篇生成、传播和接受的生活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对任何具体语篇的批评性分析都应该包括三个步骤:(1)描写(describe)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2)解读(interpret)语篇与生成、传播和接受它的交际过程的关系;(3)解释(explain)交际过程与其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
最后,SFL 以意义为基础而不是句法,即它从意义出发考察语篇中各种语言成分的表意功能。Halliday(1973)把言语行为分为行为、意义和语法三个层次,每一层次都由一组选择构成。行为层包括人类的各种行为,言语行为构成其中的一类;意义层包括人类能够表达的所有意思;语法层包括一种语言用于表达意思的各种手段。人们说话就是从行为层到意义层再到语法层的一次次选择。Halliday 的这种语言观符合CDA 关于意义服务于权力和语言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思想。
2. SFL 和CL:识解经验的不同视角
SFL 从一开始就“总体上是反对理性主义的”(朱永生,严世清2011:74),不太重视对语言和语用的认知心理机制方面的研究。这在CDA 中很早就引起了注意。例如van Dijk(2008:30)认为,SFL 和其许多观念都来自Firth 的语言学和Malinowski 的人类学传统,其“社会认知理论的缺失很难为语用和话语提供有解释力的功能理论”。在他对SFL 的语境理论提出的六点批评意见中,最后一点是SFL“没有认识到语境作为心理表征的识解和解释特征以及知识和其他相关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和社会特征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没有解释语境如何能够影响话语的生成和理解,也没有解释话语如何反作用于语境。特别是,由于忽略了语言使用者通过对交际事件和情景的动态理解和表征/再表征建构语境的心理因素,因而无法解释语境的动态性”(ibid.:54)。van Dijk 的这一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三个语境变量所包含的具体要素来看,SFL 将语境主要视为客观外在的,忽视了其作为心理表征的一面,因而也就未能考虑到语言使用者对认知语境的动态建构作用。也就是说,按SFL 的理论,语境与语言的功能和结构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语境直接决定语篇,忽视了认知心理的中介作用,因而其语境概念是静态的,无法解释语境的动态性。
不过,SFL 也并非完全忽视认知心理因素对语言及其使用的重要性。早在1967年Halliday 就谈到及物性和认知的关系,认为前者是有关认知内容选择的集合,是对语言外经验的语言表达。Halliday &Matthiessen(1999)系统地探讨了人类如何借助词汇语法来识解各种经验现象,从该著作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其对认知的关注。与CL 从认知的角度考察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能力在语言中的反映不同,该书从语言的角度观察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关注的是人类如何识解作为资源的经验。在认知科学中,经验通常被视为以概念分类、图式、脚本等形式组织储存于大脑中的知识,但Halliday & Matthiessen(ibid.:2)提出了一种互补的看法,将经验看作意义而不是知识:“我们将‘信息’看作意义而不是知识,将语言视为符号系统,更具体说是社会符号系统,而不是人类大脑的一个系统。这一视角令我们并不会像认知方法那样强调个体;与传统上理解的思考(thinking)和知道(knowing)不同,意义表达是一种社会性的主体间过程。如果将经验理解为意义,其识解就变成了一种合作行为,时而会有冲突,但总体是一种协商行为”。可见,SFL 强调语言在交际场景中的使用过程,尤其是意义在被建构或表达中的动态调整。
在认知科学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大脑中的信息,这种信息以某种方式组成概念系统,构建起人的心智(mind)。Langacker(1987,2008)把意义视为理想化的个体所经历的认知过程,认为意义处于个人的大脑中,是一种心智现象,最终必须参照认知加工做出描述,而语法结构的本质就是认知加工处理的模式。他因此提出采取一种“概念”(conceptual)或者“观念”(notional)的意义观:“至少在理论上以一种原则性的、连贯和明晰的方式来把这种现象的内在结构描述为思想、概念、感知、意象和一般意义上的心智经验是可能的。……意义结构这样就被定义为概念结构,其在语言表达中扮演着意义的角色”(Langacker 1987:97)。Kenttä(2003)对这种意义观提出质疑,认为它忽视了语言现象的社会层面,更突出个体认知对意义的构建。Brandt(2020)批评认知语言学中的“心理空间理论”(mental space theory)延续分析哲学的传统,未从表征的视角看待意义,而是将其视为基于真值条件组合原则上的真实世界的事情。由于这种基于斯宾诺莎(Spinoza)经验主义和逻辑主义的哲学背景,“心理空间分析未能抓住意义生成以及匹配和整合产生的语义和含义的动态图式特征,未能表明意义是如何在实际中具有合理性的”(Brandt 2005:1579)。Spinoza 认为“意义就是‘现实’,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Fauconnier及其心理空间理论的观点……心理空间理论无法顾及认知中发生的在线现象……未能分析在话语、语篇和对话等中实际发生的意义”(Brandt 2020:68)。Nuyts(2011)质疑认知语言学及其构式观将语法和意义简单化和静态化,认为认知语言学需要解释如何在言语交际中运用概念表征,形成具体的语义解读过程,解决语言使用中意义的动态调整问题。
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认为概念意义观具有片面性,它从心智过程开始,却忽视了言说过程,因而也就忽视了其人际功能。在SFL 的概念基块中,意识与经验的其他部分是分离的,正是感知者作为感知过程的媒介在进行思考和感知。SFL 的这一观点与皮尔斯(Peirce)的符号学思想如出一辙;皮尔斯主张在“符号”(sign)和“对象”(object)之间存在一个“解释项”(interpretant),而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正是解释项居间识解的结果,也正是该解释项将语言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在认知科学中,这个“解释项”或者感知者被抹去了,整个感知过程被物化为参与者,变成了研究对象。既然感知者消失了,那也就没有了人际互动,人际成分也丧失了。然而事实上像感觉、情感、恐惧和激情这样的情感因素都是帮助人们了解世界的认知形式。Halliday & Matthiessen(ibid.:603)认为经验被识解为意义而不是知识:“经验是通过语法被识解的,‘知道’(knowing)某事就是将某部分经验转化为意义。”这种意义内在于语言,是在语言中创造的,而非人类经验的某个独立领域。
SFL 认为“知识”和“意义”是关于同一现象的不同隐喻,表示不同的指向和假设。CL 将语言视为一种编码,认为任何语法形式都有意义,不同的形式意味着不同的意义;语言或多或少歪曲性地表达独立存在的概念结构。Halliday&Matthiessen(ibid.:465)则指出,符号系统不是一种能揭示或者掩盖事物的外衣,而是把经验转换成意义的手段或者资源:“如果认为语言歪曲事物或思维,最后将以歪曲语言告终。”SFL将语言视为人类经验的基础,把意义看作人类意识的基本模式,提出了“意义基块”(meaning base)的概念。意义基块和“知识基块”(knowledge base)的不同之处在于识解的方向,SFL 是从语法开始自下而上建构意义模型,而不是自上而下先假定一些由概念表达的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经验。Halliday 和Matthiessen认为,将知识理解为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东西是虚幻不实的,知识由符号系统构成,而语言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所有的知识表征首先都是由语言建构的:“我们尝试将语言表征为一种资源,人类和每位成员借此建构其现象世界的功能性心智图谱:发生于外部世界和自己意识领域的过程经验”(ibid.:29)。经验没有自己的秩序,而是语言赋予它秩序,我们事实上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定义经验:经验就是我们通过语言识解的现实。因此,语言就是人类构建现象世界心智图谱的一种资源,心智图谱其实是一种符号图谱,将知识建模为意义就是将其视为语言建构,而非独立于语言存在的概念系统。
Tenbrink(2020:32)认为CL 和SFL 代表了如何看待语言表征思想的两种方式;前者静态地看待语言和心智的关系,认为语言结构表征认知结构,语言系统的各个方面与思想表达之间具有对应关系;后者关注的是语言系统如何被说话者用于思想表达以及在此过程中其大脑中都发生了什么。Halliday &Matthiessen(1999:30)指出,SFL“强调语言做什么,而不是它是什么”试图通过语言过程来解释认知,而不是用认知来解释语言;在他们看来,理解某事物就是将其转换为意义,所谓“知道”就是完成了那种转换。将经验识解为意义的观点摆脱了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和真值条件语义学的束缚,充分考虑到了认知者的感知系统在符号表达式和其外延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而这正构成CDA 语言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3. SFL 和CL 在CDA 中的相似性和互补性
作为与形式语言学分庭抗礼的两股主要力量,CL 和SFL 经常被放在一起加以讨论(Nuyts 2007;Langacker 2012;van Valin 2017),国内也曾有学者探讨两者的差异和互补的可能性(张玮2004;周频2009)。如果说语言相对论关注的是语言如何限制人的认知和思想,那么CL 则是将语言作为心灵的窗口,主要关注“语言如何表征思想”(Tenbrink 2020:11),而SFL 则注重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待语言,更加关心语言使用如何塑造语言系统并决定使用者在其语言资源中的选择。
Halliday&Matthiessen(1999)认为,西方在看待意义上主要有两种传统:“逻辑哲学”(logical-philosophical)和“修辞人种学”(rhetorical-ethnographic)传统;前者从逻辑和哲学的视角将语言看作规则系统,后者则从修辞和人种学的角度将语言视为资源。CL 主要属于逻辑哲学传统,而SFL 则主要属于修辞人种学传统,但也兼顾逻辑哲学传统。这两种传统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逻辑哲学视角将意义看作外在于语言而独立存在,修辞人种学视角则认为意义内在于语言,构成语言的一部分;(2)逻辑哲学视角认为意义的基本单位是命题,修辞哲学视角则认为其基本单位是语篇;(3)逻辑哲学视角的意义指的主要是概念意义,而修辞人种学视角则认为意义与修辞密切相关,其范围不限于概念意义,也包括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4)逻辑哲学视角主要关注横组合关系,即意义结构;修辞人种学视角虽然也关注结构,但更重视聚合关系,即意义系统和潜势。
虽然分属修辞人种学和逻辑哲学两种传统的SFL 和CL 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但它们在语言观和方法论上的相似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SFL 和CL 都反对客观主义的语义观,认为语言不仅可用于表达有关世界的知识,还可以告诉我们其使用者是如何识解这个世界的。SFL 和CL 均从社会“沉积”(sedimentation)和个体“自发”(spontaneity)两方面看待语用问题,重视相对稳定的常规结构和更具动态变化的临场使用之间的辩证关系(Zlatev 2018),例如CL 中的“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趋近化”(proximization)、“力量态势”(force dynamics)等理论以及Langacker(1987,2012b,2016,2017)提出的纵向/横向范畴化关系和其“基线/详述”(baseline/elaboration)概念识解加工模式等,无不反映了其静动结合的研究关切和对语言在意义建构中动态调整的重视。Langacker(2008,2009)甚至认为动态性是认知语法的本质特征,强调意义不仅包括概念化的认知内容,也包括认知主体对于认知内容的主观识解。就是说,SFL 并非像van Dijk 批评的那样在语境因素和语言功能上完全抱持决定论的思想,CL 也并非像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所说的那样将概念系统视为完全静态的孤立于语言之外的存在,两者其实都兼顾了沉积性的结构和自发性的实例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前者产生于后者并对后者具有规范限制作用,而后者的累积作用又会影响前者的稳定性并促其发生变化。只不过,虽然CL 也将意义视为规约化的社会共享知识,但它又往往将其与一般的认知能力或大脑的神经活动联系在一起,令人感觉其所关注的意义问题不是社会性或主体间性的,而是属于个体认知的。
在看待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上CL 和SFL 的观点颇为相似,都具有建构主义的倾向,承认语言在认识和塑造社会现实中的重要作用。SFL 强调社会现实并非天定的,必须对其进行解读,而解读是一种符号过程,不仅涉及自然界,也涉及符号建构的社会文化领域。Halliday & Matthiessen(ibid.)认为人类大脑是在建构现实中进化的,从进化视角看待人类对经验的识解就可以从其与其他物种的共同之处着眼,而非总是突出人类的独特性;另外这样一种视角也可以使“经验”这个概念具有群体意义,即经验是物种成员共享的东西,是被识解为“集体意识”的东西。集体意识具有语言的性质,如果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系统,那么集体意识也具有社会符号的性质。这意味着,虽然人类具有相同的大脑并以同样的方式来识解经验,但人们生活的局部环境各不相同,因而不同群体识解经验的方式也不同。
在认知语言学里,Jackendoff(1983:29)认为心理学理论必须在环境输入来源和经验世界之间做出区分,前者为真实世界,后者为“投射世界”(projected world):“现在应该清楚了我们为何要质疑那种语言传达真实世界信息的天真观点。我们有意识接触到的只是那个被投射的世界,那个无意中被大脑组织的世界……因此,语言表达的必定是关于那个被投射世界的信息。”Lakoff(1987,1988)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复杂范畴是由经验建构的,而经验具有文化特征。意义只存在于符号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中,投射世界是创造性感知行为的结果,是被建构的一种感官输入模型,带有感知系统自身的信息。Ungerer &Schmid(2001:50)指出“认知模型当然不具普遍性,而是依赖一个人成长和生活的文化;文化为我们形成认知模型所必须经历的所有情景提供背景”。Paolucci(2021:6)指出,认知并非只是表征现实,它也通过意义建构现实;意义不是关于世界的表征,而是习惯和意义构建活动的结果。CL 的这种建构观与SFL 殊途同归,后者强调语言本身而非“认知”在这种表征或者建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经验的范畴和关系不是自然‘赐予’我们的,不是被动反映在我们的语言中,而是以词汇语法为动力,由语言主动构建的。语言作为一种分层的符号系统,具有独特的属性,能够将经验转化为意义”(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31)。可以看出,CL 和SFL 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坚持语言是认知的反映,而后者则强调认知由语言所塑造。
CDA 一直将SFL 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来源,可以说正是SFL 为早期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和CDA“提供了解构社会建构的(因此也是语言建构的)权力机制的工具包”(Chilton 2005:21)。但进入新千年之后,“CDA 中出现了一种认知转向,其动力主要来自CL 及其所催生的新的分析框架”(Hart 2014:14)。一些CDA 学者在应用这些新的CL 分析框架的同时,尝试将CL 的理论方法与SFL 相融合。Hart(2010)将CL 和SFL 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兼容并蓄在一个他称之为“策略性交流的部分草案”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中;Hart(2014)展示了CDA 中基于SFL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视觉语法”(visuogrammar)和“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等语法方法如何可以和CL 一起为CDA 做出互补的贡献。
Hart(2010,2014)认为,SFL 适合CDA 描写阶段对语篇的表征和评价特征的分析,对解读阶段的分析却没有多少解释力,原因在于这后一阶段更多涉及受话人如何建构话语的意义,以及带有特定视角和意识形态意义的话语对受话人有关现实的心理表征和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对于这种心智现象各种认知语法和心理语言学的加工方法更具解释力。CDA中目前的认知方法主要关注语篇中语言结构和参与者大脑中概念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前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和唤起后者。这个问题对CDA 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话语首先建构人脑中的知识,它才能够建构人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话语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由互动成员的意识形态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中介的”(Hart 2014:108)。CDA 中迄今最为人们所熟知和应用的认知理论和方法包括van Dijk(1997,1999,2008,2009,2010)的“社会认知方法”(socio-cognitive approach)、Chilton(2004,2014)的“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Fauconnier(1997)的“心理空间理论”(mental space theory)、Cap(2006,2008)的“趋近化模型”(proximization model)等。SFL 和CL在CDA 中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范式,叫作“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其与CL 的主要区别是,它像SFL 和CDA 一样,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在描写方式上都强调意义的社会性和主体间性(张辉2023;张辉,杨艳琴2019)。
CDA 中其他的认知研究大多集中在隐喻和力量态势方面。CDA 致力于分析话语结构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SFL 的语法隐喻和CL 的概念隐喻正是这样一种结构。隐喻基于我们对经验进行比较的能力,它系统地组织我们所有的经验(Lakoff & Johnson 1989,1999),通过唤起某种意象图式给情景强加特定的图式结构,以促成特定的世界观。SFL 认为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都是我们通过扩展意义来识解经验的策略,两者都涉及将某一个经验域重构为另一个,都是对经验的不同识解,因而是重构经验的资源。Hodge & Kress(1979:15)认为意识形态涉及“对现实的系统性组织的表征”,而由于隐喻“所界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认为的那个现实”,因此它具有意识形态性质。Fairclough(1989:119)指出,“经验的任何方面都可以通过隐喻来表征,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不同隐喻之间的可替代性,不同隐喻会带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含义”。Reisigl & Wodak(2001:58)探讨了隐喻“在指称和表述中建构自己人集团和外人集团上的重要性”。Charteris-Black(2004)提出“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探索具体隐喻在实现指称策略和表述策略中所能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对事物间力量态势的理解是人们识解现实世界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所谓“力量态势”是指不同实体之间的力量互动,这方面的分析旨在从压力和运动的角度解释因果关系。Talmy(2000)把处于力量互动关系中的实体分为“主动者”(Agonist)和“对抗者”(Antagonist)。力量态势分析模式令人注意到主动者和对抗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性质,在语篇生成者通过语言表征给双方分配的角色中往往存在着意识形态倾向,“选择不同的动词、语态形式或者论元关系表明对事件力量态势结构的不同认识”(Croft&Cruse 2004:66)。力量态势分析与SFL 的及物性分析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最近几年出现的“认知话语分析”(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CODA)主张通过对语言使用者在线加工过程的研究来揭示心智表征和复杂认知过程,其主要理论方法不仅来自CL,也来自SFL。Tenbrink(2020:83-84)认为SFL 可以在理论和具体方法上为认知话语分析提供很多真知灼见:“做认知话语分析意味着考察语言选择:从说话者许多可能的以言行事中识别其最终用语言做了什么。理解说话者选择做什么的意义因此与理解他们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密切相关。……由于有了‘选择’这样一个核心概念,系统功能语法就为解读具体出现的每一例话语提供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工具箱。”
4. 结语
认知符号学认为感知涉及感知者和被感知者的相互参与(Abram 1996:59),意义具有制定性、参与性、互动性和象征性(Zlatev 2018:14)。任何符号都并非以客观中立的方式表征现实,而是要基于表义者按常规惯例和具体语境要求所进行的识解(Möttonen 2016)。语言编码识解,同一事物、事件或者情景可以不同的方式被概念化,描述客观现实时使用的不同语言形式或结构会导致对其不同的识解。话语策略通过语言手段来实现,而语言手段只有通过概念化才能产生言后效果。本文的讨论表明,CL 可以作为CDA 的重要理论和方法来源,因为它在坚持研究语言的交际功能的同时十分重视探究语法背后的心智过程。SFL 和CL 因此可以相互参照,分别从社会和认知两个视角为CDA 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CL 有助于解释大脑中的概念体系如何帮助或者限制语言使用者认识和表征现实,但这些概念体系是什么和从何而来则需要从社会认知和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在人们的社会互动及其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去加以理解和解释,而这正是SFL 所重点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