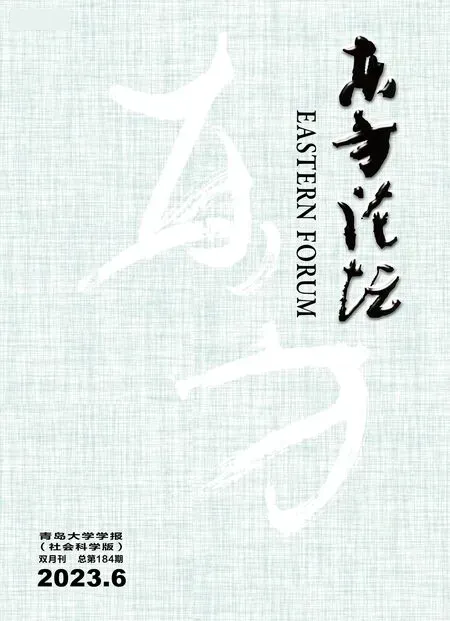周作人译《戚施》与《塞外》的底本考证
2023-03-07张宇飞
张 宇 飞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一、《域外小说集》底本研究综述
1909 年,在日本留学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1、2 册分别于当年3 月和7月出版。根据周氏兄弟的计划,这两册翻译集只是向中国介绍外国新文学的开始,但因前两册翻译集销路不佳,第三册只好中止。鲁迅曾言,自己早期并不想创作,而是注重介绍、翻译外国文学,尤其是短篇,并称自己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创作仰仗的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①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525—526 页。《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正与鲁迅的回忆一致,《域外小说集》中收录的小说不仅可以反映出周氏兄弟在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中精心挑选的良苦用心,也可以呈现出周氏兄弟当时搜集外国文学的历史原貌。周作人曾对他们当时的搜集情况进行了回忆:
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一篇关于俄国文学的绍介或翻译,一定要去买来,把这篇拆出保存,至于波兰自然更好,不过除了《你往何处去》,《火与剑》之外,不会有人讲到的,所以没有什么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书目,设法购求古怪国度的作品,大抵以俄国,波兰,捷克,塞尔维亚(今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新希腊为主,其次是丹麦瑙威瑞典荷兰等,西班牙义大利便不大注意了。②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 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450 页。
据周作人的回忆可知,他们在搜集外国文学作品时,不仅关注日本的文艺杂志,还查阅了大量英文、德文书目。众所周知,周树人离开仙台后,就进入东京独逸语专修学校学习德文①[日]北岡正子:「独逸語専修学校に学んだ魯迅」,『魯迅研究の現在』,東京:汲古書院,1992 年,第5—43 页。;而周作人在赴日以前就已经学习过英文②宋声泉:《江南水师学堂与“原周作人”的肇基——以四本字典的考订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19 年第9 期。,因此可以判断周树人主要是通过德文、周作人主要是通过英文翻译《域外小说集》中的外国小说。关于《域外小说集》底本的来源,周作人也在《东京的书店》一文中有过回忆:
一九〇九年所刊的《域外小说集》二卷中译载的作品以波兰俄国波思尼亚芬兰为主,法国有一篇摩波商(即莫泊三),英美也各有一篇,但这如不是犯法的淮尔特(即王尔德)也总是酒狂的亚伦坡。俄国不算弱小,其时正是专制与革命对抗的时候,中国人自然就引为同病的朋友,弱小民族盖是后起的名称,实在我们所喜欢的乃是被压迫的民族之文学耳。这些材料便是都从丸善去得来的。日本文坛上那时有马场孤蝶等人在谈大陆文学,可是英译本在书店里还很缺少,搜求极是不易,除俄法的小说尚有几种可得外,东欧北欧的难得一见,英译本原来就很寥寥。③周作人:《东京的书店》,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 卷,第343 页。
由此可知,翻译《域外小说集》所使用的材料“都从丸善去得来的”。此外,周作人还提到了当时向日本介绍“大陆文学”的学者马场孤蝶。可见周氏兄弟从丸善书店购买的英、德译本书目是翻译《域外小说集》时所参考的重要资料。
关于《域外小说集》参考底本的研究,虽然是学者们历来都非常重视的课题,但由于受到外语与一手资料等因素的限制,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日本学者谷行博在《周作人译爱伦·坡〈默〉》一文中,引用了收录爱伦·坡作品原文的The Tales of Edgar Poe一书,但并未确认该书就是周作人翻译《默》所借助的底本④[日]谷行博:「周作人訳E.A.ポオ「黙」」,『大阪経大論集』第152 号,1983 年。。张丽华确认了王尔德《安乐王子》、显克微支《乐人扬珂》、穆拉淑微支《不辰》和《摩诃末翁》、安特莱夫《谩》和《默》所借助的底本⑤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结构为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25 页。。崔文东不仅详细考察了“雷克拉姆万有书库”等德语世界文学丛书对鲁迅阅读外国文学的影响,还考证了《域外小说集》收录的大部分作品所依据的德文底本,填补了《域外小说集》底本考证的空白⑥崔文东:《青年鲁迅与德语“世界文学”——〈域外小说集〉材源考》,《文学评论》2020 年第6 期。。近来,笔者在整理日本明治时期契诃夫作品的译介状况时,发现了《域外小说集》中周作人翻译契诃夫《戚施》和《塞外》所依据的英文底本。因此,拟在崔文东德语底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周氏兄弟与契诃夫小说英译本的关联,同时探讨留日时期的周氏兄弟是如何接触到俄国作家契诃夫及其选译《戚施》《塞外》的原因。
二、留日时期周氏兄弟周边的契诃夫
契诃夫是周氏兄弟非常关注的俄国作家。除《域外小说集》中收录的两篇作品外,鲁迅于1934至1935 年间翻译了契诃夫的8 篇短篇小说,集为《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周作人于1919 年翻译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爱的人》。毋庸置疑,周氏兄弟关注契诃夫最早的时间应该是在其日本留学时期。这反映在《域外小说集》对契诃夫的介绍文字中:
契诃夫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著戏剧数种,及短篇小说百余篇,写当时反动时代人心颓丧之状。艺术精美,论者比之摩波商。唯契诃夫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怀希望,非如自然派之人生观,以决定论为本也。《戚施》本名《庄中》,写一兀傲自熹、饶舌之老人,晚年失意之态,亦可见俄国旧人笃守门第之状为何如。《塞外》者,假绥蒙之言,写不幸者由绝望而转为坚苦卓绝,盖亦俄民之特性,已与其后戈理奇(Maksim Gorjki)小说中人物相近矣。①周作人:《〈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 卷,第153 页。
此外,周作人回忆称,契诃夫的《决斗》也在周氏兄弟翻译计划之内②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 卷,第451 页。。周氏兄弟在东京从事文艺运动时,契诃夫的文学作品一定是陪伴在其周边的。与周氏兄弟同时代的郭沫若就曾断言:“毫无疑问,鲁迅在早年一定是深切地受了契珂夫的影响的。”③郭沫若:《契珂夫在东方》,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1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469 页。研究者们曾推测契诃夫《黑修士》《第六病室》的日译本都可能影响过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作④李家宝、黄忠顺:《“医学作品”特质的“神怪小说”——论契诃夫汉化历程的起点》,《外国文学研究》2016 年第12 期。李冬木:《“狂人”的越境之旅——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20 年第5 期。,周作人翻译的《戚施》对鲁迅的《肥皂》产生过影响⑤[日]谷行博著:《〈肥皂〉是怎样作成的?》,靳丛林译,《鲁迅研究月刊》1997 年第2 期。。笔者本人则曾探讨过契诃夫《变故》的日译本与鲁迅《兔和猫》的关系⑥张宇飞:《契诃夫的〈变故〉与鲁迅的〈兔和猫〉之比较》,《中国俄语教学》2023 年第1 期。。以上推测都具有合理性,但如果能够明确周作人所翻译的两篇契诃夫小说的底本,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周氏兄弟与契诃夫关系的研究。崔文东则主要考察了留日时期鲁迅德文藏书的情况,发现鲁迅在留学期间收集了5 种德译本契诃夫小说,其中万有文库版《女人的王国、在流放地、蚱蜢》中包含《塞外》的德译本,但并未发现《戚施》的德译本⑦崔文东:《青年鲁迅与德语“世界文学”——〈域外小说集〉材源考》,《文学评论》2020 年第6 期。。
为确认周作人译两篇契诃夫小说的底本,笔者对《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前契诃夫作品的日译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截止到1909 年3 月,共有50 篇契诃夫小说被翻译到日本⑧[日]川戸道昭等:「明治翻訳文学年表 チェーホフ編」,『明治翻訳文学全集43·チェーホフ集Ⅱ』,東京:大空社,2000 年。。其中,桐生悠悠译《配所之月》(「配所の月」)和角田浩浩歌客译《流人》(「流人」)的内容都与周作人翻译的《塞外》⑨现译《在流放中》,本文所引用的契诃夫作品中译名均参考汝龙译《契诃夫小说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年版)。又,《戚施》,现译作“《在庄园里》”。一致,但并未发现《戚施》的日译本。这个调查结果至少可以说明《戚施》并非根据日译本翻译的。另外,通过对这50 篇日译契诃夫作品的调查,还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一阶段日译者大都是精通英语的学者。其中19 篇(包括1 部专著)出自翻译契诃夫作品的第一人、女翻译家濑沼夏叶之手,升曙梦、嵯峨之屋御室等精通俄文的译者也翻译了多部作品,剩下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角田浩浩歌客、正宗白鸟、薄田斩云、小山内薰、马场孤蝶等精通英文的译者翻译的。这是否意味着英文译者都通过同一部契诃夫英译作品集向日本翻译契诃夫作品的、周作人是否也目睹过这部作品呢?这可以从周氏兄弟都很关注的马场孤蝶的评论文章中得到答案。
马场孤蝶的《契诃夫短篇集〈接吻〉》 《新译〈契诃夫短篇集〉》①[日]馬場孤蝶:「新訳『チェ—ホッフ短篇集』」,『早稲田文学』第40 号,1909 年3 月。都提到一部英译契诃夫小说集——丸善书店近期购买的最新英译本契诃夫《接吻》(The Kiss and Other Stories)。马场孤蝶还对同一译者翻译的较早的另一部译本进行了介绍:
关于契诃夫短篇英译作品,之前有罗伯特·朗翻译的《黑衣僧》一书,即The black monk-Anton Tchekhoff-London;Duckworth &Co,1 03-¥3.00。其中收录的《黑修士》《在路上》《问题》《在家里》《在流放中》《洛希尔的提琴》《父亲》《仇敌》《困》《在庄园里》《变故》《第六病室》等作品,均是契诃夫的代表作。②[日]馬場孤蝶:「チェーホッフ短篇集『接吻』」,『慶應義塾学報』第139 号,1909 年2 月。又,此引文为笔者翻译,以下引文如不做特殊说明,均为笔者翻译,不再出注。
根据马场孤蝶介绍的目录,可以确定该书为英国译者罗伯特·朗(Robert Edward Crozier Long)翻译的《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 (The black monk and other stories),该书共收录有12 篇小说,分别是《黑修士》《在路上》《问题》《在家里》《在流放中》《洛希尔的提琴》《父亲》《仇敌》《困》《在庄园里》《变故》《第六病室》。由目录可知,《域外小说集》中收录的《戚施》《塞外》均可找到英文版,被研究者们指出的可能影响鲁迅《狂人日记》的《黑修士》《第六病室》也在其中。周作人极有可能是通过这部英译契诃夫小说集翻译了《戚施》和《塞外》这两篇小说,而这部英译契诃夫小说集也是周氏兄弟在留学时期共同阅读契诃夫的一部重要作品。
此外,角田浩浩歌客、正宗白鸟、薄田斩云、小山内薰、马场孤蝶等人翻译过的契诃夫作品,都有与这部英译契诃夫小说集一致的篇目,这些译者极有可能也是以这部小说集收录的作品为底本进行翻译的。蓜岛亘在《俄罗斯文学翻译者列传》中指出,马场孤蝶发表在《芸苑》杂志上的《六号室》所参照的底本,正是罗伯特·朗翻译的《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一书,正宗白鸟、角田浩浩歌客等人翻译的契诃夫作品也是根据该书③[日]蓜島亘:『ロシア文学翻訳者列伝』,東京:東洋書店,2012 年,第155 頁。。樽本照雄的《吴梼的汉译契诃夫》确认了薄田斩云在《太阳》杂志上发表的译作《黑衣僧》的底本也是这部英译小说集中的The Black Monk,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第一位翻译契诃夫小说的译者吴梼正是根据薄田斩云的《黑衣僧》而翻译的第一篇汉译契诃夫小说《黑衣教士》④[日]樽本照雄:「呉檮の漢訳チェーホフ」,『清末小説』第33 号,2010 年。。这足以证明这部英译小说集也间接影响了契诃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据马场孤蝶的介绍文章可知,罗伯特·朗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集都是通过丸善书店而进入日本的。正宗白鸟曾作为亲身经历者、回忆了当年英译契诃夫翻译集进入丸善书店时引起的轰动:
由于题为《黑衣僧》的英译短篇集抵达丸善,契诃夫的大名便在青年文学者间广泛传播。
之后传入的英译契诃夫短篇集是以《吻》为题的红色封面的书籍,我是通过小山内薰的介绍而得知的。……小山内氏对我巧妙地讲述了《牡蛎》的概要。孩子连壳将牡蛎吃下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由于《樱桃园》的故事也是从小山内氏那里听到,通过庭园的樱花落地的声音也能引起我对这部崭新的戏剧产生兴趣。①[日]正宗白鳥:「故人の追億」,『文芸』1935 年10 月,转引自蓜島亘:『ロシア文学翻訳者列伝』,東京:東洋書店,2012 年,第177 頁。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是丸善书店的常客,周作人在《东京的书店》和《关于鲁迅之二》两篇文章中都回忆到了他们在丸善书店找书、购书的细节。李冬木也曾指出,周氏兄弟通过阅读丸善书店的书籍与“丸善所构成的新知和时代思潮”发生关联②李冬木:《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东岳论丛》2014 年第3 期。。可见周氏兄弟在丸善书店中阅读到的不仅仅有尼采、左拉、托尔斯泰、易卜生、勃兰兑斯等人的作品,还有在当时名震明治青年文学者们的契诃夫小说。
三、《塞外》和《戚施》的底本考证
从史实的角度年,周氏兄弟极有可能通过丸善书店购买并阅读到《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这个契诃夫小说的英文翻译集。就文本对比的角度而言,周作人译《塞外》《戚施》两篇契诃夫小说的底本也极可能来自该翻译集。
(一)《塞外》的底本
《域外小说集》正式出版前的契诃夫小说,除英译本外,还有1904 年5 月桐生悠悠翻译的《配所之月》和同年6 月角田浩浩歌客翻译的《流人》这两个日译本。据上文提到的蓜岛亘的研究可知,角田浩浩歌客译《流人》参考的底本是罗伯特·朗的英译本,桐生悠悠译《配所之月》的参考底本尚不清楚。那么周作人的译作究竟是参考罗伯特·朗的英译本还是其他两部日译本呢?笔者通过文本对比,发现周作人是根据英译本进行翻译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是周作人翻译的这段文本:
老人笑曰,“汝会当安之耳!今汝幼且昏,口上乳汗未干也。以幼昏故,遂以为世人困苦,无过汝矣。第他日时至,汝当曰,神造人生,都如是耳。曷且视我!比复七日川水下,仅容小舟,汝可往鲜卑行乐,独吾留此,往复操舟。吾守渡于此,二十年矣,鱼鳖居水下,而吾息其上。然神可谢也!吾无所需。神造人生,都如是耳。”③[俄]契诃夫:《塞外》,周作人译,伍国庆编:《域外小说集》,长沙:岳麓书社,1986 年,第179—180 页。
对比可知,在一些关键词句的翻译上,周作人并未参照两部日译本。例如,英译本中出现了两次“God grant everyone such a life”(译文:神赐予每个人这样的人生),周作人两次都将其翻译为“神造人生,都如是耳”,而两个日译本的翻译分别为“神様tt如何tí者にも斯tí生活をfhせられtfのfk”(译文:无论何人上帝都给予他们这样的生活吧)和“神fhま、どうfk此様tí生涯を誰にも彼にも授けtfやうにして下fhい”(译文:神、请务必把这样的人生授予所有的人吧)。再比如,英译本中出现了“you'll be off to Siberia to amuse your selves”(译文:你们将要到西伯利亚游玩娱乐),而两个日译本都未翻译出Siberia 一词,只有周作人的译文将Siberia 译为“鲜卑”,这也足以说明周作人是参考英译本进行翻译的。
此外,关于《塞外》主人公“绥蒙”外号的翻译也值得注意。小说开篇第一句就介绍了“绥蒙”的外号:“Oid Semion,nicknamed Wiseacre,and a young Tartar,whom nobody knew by name,sat by the bonfire at the side of the river.”①Anton Chekhov, "In Exile", The Black Monk and Other Stories, translated by Long R. E. C., London: Duckworth &CO., 1903:109.其中,wiseacre一词的意思为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桐生悠悠将其译为“气焰家”,角田浩浩歌客将其译为“天狗”②日语中“天狗”有自以为是、自傲的人的意思。,周作人的翻译则是“诨名多尔珂微(此言智士)者”。汝龙译《契诃夫小说全集》中,将《在流放中》主人公的外号译为“聪明人”③[俄]契诃夫:《在流放中》,汝龙译,《契诃夫小说全集》第8 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年,第263 页。。通过对如何理解并翻译“绥蒙”这一外号的对比也可以判断,周作人显然是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小说《塞外》。
(二)《戚施》的底本
周作人曾以“独应”为笔名在《河南》杂志第8 期发表了短篇译作《庄中》和《寂寞》,《庄中》后来易名为《戚施》收录在《域外小说集》中。郜元宝通过对北京鲁迅博物馆藏的周氏兄弟中文剪报中收录的周作人翻译的爱伦·坡的《寂寞》和契诃夫的《庄中》的校改情况推测这两篇小说虽为周作人所译、但校改很可能出于鲁迅之手,是周氏兄弟合作翻译外国小说的又一物证④郜元宝:《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周氏兄弟”中文剪报校改考释》,《鲁迅研究月刊》2018 年第11 期。。在《河南》杂志第8期出版以前,并未发现《庄中》的相关日译本,因此周作人所使用的底本只有可能来自英译本。据题目可以判断,“庄中”正是At the Manor 的直译。现试举周作人翻译的一例文本予以说明:
罗舍微支先曰,“吾于此事,万不更有所哄。若就群聚而言,谓人悉平等,则自属无间物我。彼牧猪奴密伽,亦是善人,何不逮瞿提(德国诗人)或伏力德烈大帝者。然试就学理观之,勿徇勿缩,君自当知所云皙骨(按贵胄之别名)一节,正非偏说,非愚妇人见地也。吾友,缘彼皙骨,在自然史上,确有信征,如欲力斥此说,吾意犹云鹿之无角,宁非巨谬。今可据实为言,君治法学,言事悉本人情,此外不复更究,故中于平等群治诸说,自长妄见。第以吾言,吾则固执不化之进化论家也。凡种类贵族名门诸语,于吾意皆不为虚响。”⑤[俄]契诃夫:《戚施》,周作人译,伍国庆编:《域外小说集》,第160—161 页。
由以上文本可以看出,周作人的译文完全遵循了英译本的原文。例如,周作人将该篇小说的关键词“the white bone”译为“皙骨”,并根据英译本文中的注释“Blue blood”在“皙骨”一语之后补充“贵胄之别名”予以说明。另外,周作人还将“fraternity”译为“群聚”,将“swineherd”译为“牧猪奴”,将“Darwinian”译为“进化论家”,将“a silly woman's invention”译为“愚妇人见地”。从这些词汇的翻译可以看出,周作人既遵循了英译者的原意,又尽可能的将译文“汉语化”,以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小说后来的题目“戚施”,是从罗舍微支两个女儿口中说出的对自己父亲表示厌恶的外号。谷行博查证1986 年出版的英译契诃夫作品,认为该词的词源有可能是“old toad”一词①[日]谷行博著:《〈肥皂〉是怎样作成的?》,靳丛林译,《鲁迅研究月刊》1997 年第2 期。。通过考察周作人所采用的底本,可以确认“戚施”是从“the toad”一词译出,即“蟾蜍”的别称。因而可以推测,周氏兄弟极有可能认为,将“戚施”作为作品的题目更能凸显出这一“兀傲自熹、饶舌之老人”是如何固守俄国门第之状的,也使小说题目更具有趣味性。
除上述对周作人译两篇小说与罗伯特·朗英译本的文本对比,笔者还发现了可以证明周作人参考英译本的另一个证据。在周作人以“独应”为笔名、刊发于1908 年12 月5 日《河南》杂志第8 期的短篇小说《庄中》译文末尾,附有简要的作者介绍:
契诃夫(A.P.chekhov)以千八百六十年生俄之南方,长学为医,后以文章名世,著有传奇数种及小说百余篇。凡所为文,趣旨与西欧迥别。俄人斯忒兰涅克(I.strannik)论之曰,近世俄国施政至厉,灵志之士不适于生,而庸众反多得志。著者亦尝云,贤人困顿,盖其定名尔。惟世究尟贤哲,故所图写,以猥琐者为多,而于书中之人,则不寄之同情,特有讽刺而已。如此篇者,即其一也。
在这段介绍中,周作人提到了斯忒兰涅克(I. Strannik)的论述。而在罗伯特·朗英译本序言中,也有对Ivan Strannik 即斯忒兰涅克及其作品的介绍:
一位法国评论家(伊凡·斯特拉尼克,Ivan Strannik,1903 年,巴黎,阿曼德科林图书馆)最近在名为L'impuissance de vivre 的一章中评论了他(按:契诃夫)的故事,这段评论很好地概括了契诃夫要讲的话。现代俄国的政治内容充满了对智力和积极性的压制,或者说,至多也只是将人们的智力转移到毫无创造力的官方渠道;因此,在《第六病室》中展现出来的对生活的厌恶和智力的停滞,贯穿了契诃夫所有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他的戏剧,其中大多数作品以理想幻灭或自杀而告终。在契诃夫看来,俄国的生活就是极少部分清醒的人同大多数平庸的人进行的毫无意义的斗争,他的书页上满是精神病患者、天才和美德的堕落者,他们无力地反抗生活的卑鄙和平庸,并且没有能力同身边强健、野蛮但愚蠢的力量作斗争。②Long R. E. C., "PREFACE", Anton Chekhov, The Black Monk and Other Stories, translated by Long R. E. C.,PREFACE:Ⅶ-Ⅷ.
对比可知,周作人极有可能在阅读完英译本序言后,概括出了《庄中》文末关于契诃夫的简介,但误将法国评论家“斯特拉尼克”记为“俄人”。
四、周氏兄弟选译《塞外》和《戚施》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认,《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收录的《在流放中》(In Exile)和《在庄园里》(At the Manor),分别是《域外小说集》第一册收录的《塞外》《戚施》的底本。该翻译集共收录有12 篇契诃夫的小说,周氏兄弟为何只选择《塞外》《戚施》两篇进行翻译呢?
在这12 篇小说中,最耀眼的当属第一篇《黑修士》(The Black Monk),因为该翻译集就是以《黑修士及其他的故事》为题的。当该翻译集传到日本后,这篇作品很快就被薄田斩云翻译为《黑衣僧》。另一篇引人关注的是该翻译集的最后一篇《第六病室》,它被视为契诃夫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马场孤蝶于1906 年将其译为日文。如前所述,这两篇小说都被研究者认为是可能影响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外国小说。目前虽尚不能确定鲁迅可能通过哪个版本读到这两篇小说的,但《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的发现,至少可以证明这两篇小说的英译本就在周氏兄弟身边。周氏兄弟为何没有选译今天看来影响力相对较大的《黑修士》和《第六病室》,而是选译了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塞外》和《戚施》呢?
关于《戚施》,前引周作人文称:“《戚施》本名《庄中》,写一兀傲自熹、饶舌之老人,晚年失意之态,亦可见俄国旧人竺守门第之状为何如。”张丽华认为这理解并不准确,在《戚施》中,契诃夫使用了似贬实扬的反语技巧,通过对一位没落贵族奇怪而惹人厌的言谈举止的描摹,寄寓了对这一阶层无可挽回的命运及其面对时代的无力感的深切同情①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结构为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39—140 页。。周作人曾指出,《域外小说集》选译的作品更趋向于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②周作人:《弱小民族文学》,《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399 页。。但《戚施》似乎与弱小民族并无直接关系。笔者以为,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撰写的广告词,更能反映出周氏兄弟选译这篇作品的原因。鲁迅指出,《域外小说集》的作品都是“近世名家短篇”,且“结构缜密,情思幽眇”“斐然为文学之新宗”③鲁迅:《〈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初刊于上海《时报》,1909 年4 月17 日,第1 版;后收入《鲁迅全集》第8 卷。。而短篇小说《戚施》通过描写一饶舌老人对贵族血统的吹捧和对平民血统的鄙视,反映出俄国社会阶层、门第森严的状况;该老人的言行不仅得罪了自己中意做女婿的平民出身的“迈依尔”,也让自己遭到女儿们的厌恶。可见,周氏兄弟所看重的,不仅是这篇作品新颖的讽刺手法,更是其所反映的俄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状况。
关于《塞外》,周氏兄弟称其“假绥蒙之言,写不幸者由绝望而转为坚苦卓绝,盖亦俄民之特性,已与其后戈理奇(Maksim Gorjki)小说中人物相近矣”④周作人:《〈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周作人散文全集1》,第153 页。。笔者认为,周氏兄弟选译这篇小说的最大理由也是看重其题材。《塞外》主要描述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鞳鞑人与渡船船夫“绥蒙”的对话,通过“绥蒙”的讲述揭示了西伯利亚流放生活的艰辛,这种艰辛的生活把本是教堂持事儿子出身的“绥蒙”消磨为毫无感情的石头人。这篇小说通过描写“不幸者由绝望而转为坚苦卓绝”,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一种韧性。而俄国文学中有关流放西伯利亚题材的作品,正是留日时期的周氏兄弟关注的重点内容。鲁迅《摩罗诗力说》结尾处就提及柯罗连科描写西伯利亚流放题材的《末光》,周作人也曾在《民报》第24 号发表过译作《西伯利亚纪行》。可以说,《塞外》是周氏兄弟关注的又一篇以西伯利亚流放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域外小说集》选译《塞外》和《戚施》这两篇契诃夫小说的做法,也符合鲁迅所讲的“各国竟先选译”。藤井省三提出,鲁迅对安特莱夫的翻译与日本的文学者处于同一时期,甚至可以说鲁迅与日本的文学者争相翻译安特莱夫的作品①[日]藤井省三:『ロシアの影 夏目漱石と魯迅』,東京:平凡社,1985 年,第144 页。。而周氏兄弟对契诃夫作品的翻译也符合这一现象。
上述研究表明,周氏兄弟与日本明治时期多位英文学者共同选取罗伯特·朗《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翻译集中的短篇小说翻译并介绍到本国。可以说,在对契诃夫文学的接受过程中,周氏兄弟与角田浩浩歌客、正宗白鸟、薄田斩云、小山内薰、马场孤蝶等日本学者处于同一知识平台。这再次体现了周氏兄弟留日期间的工作与明治三十年代的文学界具有“同时代性”②[日]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8—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