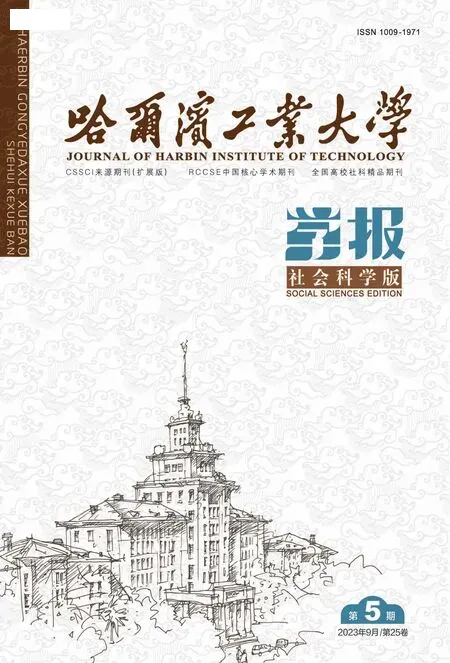自然及其 “神性” :论雷平阳的生态诗学
2023-03-07李秋瞳
李秋瞳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 150500)
引 言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面对人类现代文明的扩张,曾指出,现代文明是 “一个四处扩伸、兴奋过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沉默击破,再也无法还原了。热带的香料,人类的原始鲜活性,都已被意义可疑的一片忙乱所破坏变质。 一片忙乱迫使我们压抑我们的欲望,使我们注定只能取得一些受过污染的回忆”[1]30。 此种 “现代性的隐忧” 同样可以指涉我国云南少数民族聚焦地社会转型时的尴尬遭际:当自然资源被无休止地开发、消耗和掠夺,环境污染成为社会的毒瘤,珍稀动植物濒临灭绝,这也恰恰从反面折射出了人类精神的空洞和无知,自然的蜕变是人类生态意识、神性意识退化的直接反映。
雷平阳的诗歌以描写云南生态为主,为家乡云南 “立传” ,正是希冀让诗性文字记录下云南的大江大川、雪山雨林和一花一世界的美景,从中开掘出抚平内心、抵御现代化和消费社会的神性力量。 “云南南方山水里所发生的旧传说和新故事,它们一旦来到我的记忆中,来到我铺开的稿子上,就会成为我饥饿的灵魂无限迷恋的食物。 我相信山上和水中的神灵,也敬重道法自然的山规,在图穷匕见的工商文明时代,这差不多是我得以偷生人世的一个秘密。 因为相信,我有了属于自己的荒烟蔓草的生活,自己可以鲜为人知地生活在旷野上、神话中和过去的时间里。”[2]雷平阳诗意的书写正是将人与自然修葺为生命共同体,从中聆听自然的 “神谕” ,他诗作中的云南的山水风物,常常是一些具有 “神性” 的意象与境界。 他的写作,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自然观和生态伦理观。
一、自然的 “复魅” 与 “神性” 的想象
文化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英国理论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73)曾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类似的环境恶化的危机感。 每一个时代都怀着一颗怀旧的心在回望历史,比如20 世纪怀念19 世纪英国的 “有机社会” ,19 世纪悲悼18 世纪 “幸福的伊甸园般的时代” 的终结[3]。 这种 “怀旧” ,是对当今的抗议和消解。 对 “神性” 山水的向往也成为云南烟瘴里的另一种 “追忆逝水年华” , 然而,雷平阳追忆的不是古老的时间和空间,不是退守旧的原始的云南和它庄严的历史,而是对云南文化记忆的寄诉:那相对封闭的族群、世代流传的图腾、先人头人的足迹和那巍峨雪山、蜿蜒大河、低徊峡谷、红土高原……它们共同建构了雷平阳诗歌的主题风格和典型意象,诗中流淌着先祖跋涉的生命印记、自然现实的粗粝、历史沧桑的变迁,这些云南边地的低语、粗犷或咆哮都转化为诗人庄严、神圣的诗之音蕴,彰显出了雷平阳诗文的质感、启谕出了他独特的 “文化地理学” 的审美感知和生态自然意识。
同样是 “追忆” ,现代文明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却与从前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浪漫的怀旧情绪的结果,而是真切体现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生态灾难。 在物质上,现代文明日益侵蚀着云南神性的田园,遮蔽了曾经的自由山水;在精神上,现代人的生活也正面临着 “现代危机” 的分割与拆离。雷平阳对神性山水的追忆,正是 “祛魅” 时代下的 “复魅” 诗篇。 当今社会所有自然和人文景观都处于可以通过科学原理来衡量与诠释的状态,自然更多作为资源被开发和利用。 机械性、物质性的现代世界取代了传统的神性自然山水,人类面临的是自然的灵魂被现代文明挤压和放逐的现实。 现代性,就是持续的 “世界的祛魅的过程”[4]。 现实世界中背负着大量 “现代文明” 的云南,在雷平阳的诗中,则被打开了通往庙宇和心灵的阶梯,这也就是探寻我们之外 “另一种文明的开始” (列维-斯特劳斯语)。 这条少有人问津的小路,却充满了不一样的风景和未知的神秘:雷平阳尊重云南地方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必然与其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密切相关,就像雷平阳自己在《亲人》中所述: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5]48雷平阳对云南、对家乡情感就像 “针尖上的蜂蜜” ,暗示出了诗人对红色大地、亲人、个体记忆、历史经验和民族心理的眷恋,对这里充满执着、偏执的爱,这些正是诗人感悟出的云南灵魂所在——那里的山川满是神灵,让其心生敬畏,因此,雷平阳诗歌的底色中始终弥漫着一派 “神灵之气” ,构筑起了一座 “精神乌托邦” 。
《春风咒》中,自然中一切景物都幻化为族人血液中的基因、向往和希望,都被 “天梯” 的美梦和神祇赋予灵性之光[5]49。 质感粗糙、坚硬的自然意象(坚硬的岩石、溪水、野花、树木),充满了诡秘、旷达、原始、朴质的情感寄托,开启了雅鲁藏布江谷地的部族歌音,这种自然通灵的诗写方式更大程度上弥补了现代人精神的缺憾,拓宽了汉语诗歌的文化脉络、语词表达和技艺,激活了杂糅于地方文化里的根性记忆,也陌生化地呈现出了一片神性莫测、浪漫纯真的 “高原” 。
雷平阳叙述出一个古老的神性自然,使外在自然与当代人的情感世界发生深切的关联。 中国古代,人可以被自然干预而产生 “物感” ,人心灵对自然反映而产生 “心动” ;在西方,自然也经历了从浪漫化想象到生态危机的现代凝视。 雷平阳通过 “自然的复魅” ,对云南的 “自然” 作想象性的 “还原” ,外在的自然世界被呼唤为一种有生灵依附的情感现实,人能与自然进行沟通。 雷平阳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有一本诗集,叫《云南记》。 评论家谢有顺就说,起个名字叫 “云南记” 挺有意思……如果是谢有顺这样一个福建人写一本书叫 “福建记” 这个名字就怪怪的。 一本书起名叫《云南记》是充满想象的,因为 “云南” 两个字一旦出现,中国人仿佛觉得就是远方,就是想象,白云、寺庙、青山绿水。 其实我们生活在里面,生活在人们说的远方,我们看见了整个群山被毁坏,那些青山破碎了,那些江河被一次一次地被拦腰斩断,一座又一座的寺庙被连根拔起。 正如谢有顺所说,雷平阳将自己的写作成为 “送葬” ,为了渐行渐远的村庄和消逝的亡魂[6]。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家布依尔(Lawrence Buell)曾从四个方面界定了 “生态文学” 的概念:一是文本中的环境有更大的范畴,场景以外还包含客观的自然存在。 二是指出人类的利益在文本中不是唯一合法利益;三是从伦理角度指出人类对自然的责任;四是文本的环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既定事实,或者恒定存在[7]。 这四条定义很符合雷平阳在复兴云南山水神性光辉的路径上所作出的文学想象。 原始时代,云南少数民族的初民在仰望高山和探测江河的生命体验中,窥探隐藏期间的山神、水神,有的部落将其诗化为自己部落的图腾和神祇,加之山水自然同样哺育了一代代的族人,更是对自然心存感激和敬畏,慢慢这种生存体验和精神感受升华为对自然的宗教情怀和朴质的图腾崇拜。 这些图腾和神祇象征了云南自然风物作为存在符号的历史变迁,而不是恒定不变的历史部落图景。 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景,都是云南图腾文化的部分。 此时,人们所能做的,不是 “旁观” ,而是可以和自然发生互动的 “瞭望” 。 孔明山和基诺山隔江对峙,孔明山是当地人死后灵魂的栖息之所,基诺山自古是基诺人繁衍生息的地方,而这种神性山水,在雷平阳诗歌中的另一种出场方式,是伴随着的山水之痛——工业文明、商业文化侵蚀下云南日益消散的田园生活。 如今,追寻这种 “神” 之属地,只能向更远的深山探查,向更远的部落寻找,这也正是诗人不断在中心和边缘游走的症候,是一种历史与现实、原生与现代、浪漫与生存的对抗,是那山那水无法追忆的失落与留恋。可以说,一座座山中盘踞的灵魂被现代社会彻底消解了神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无法引起人们的怜悯和共情,但是自然山水的实质不会改变,变化的只是人类对 “神” 的拒绝和远离。 “只有贩毒的人是快的/在这儿,其他都很慢/最慢的是怒江/只有吸毒的人是快的/在这儿,其他都很慢/最慢的是苍山” (《快和慢》)[5]71。 这种 “快和慢” 泾渭分明的对比,恰恰诠释了诗人对 “旧山水” 的执念,也隐喻了社会生活中现代人精神的贫瘠与堕落。
在对自然神性的 “复魅” 的进行中,雷平阳的努力包括对云南文化记忆作为 “存在” 的 “瞭望” ;有感于 “田园之失” ,为延续 “偏执的爱” 而努力向自然更深远的地方挖掘,甚至一度抵达最深远的死亡。 “他们相信一种神奇的动物,被他们所受的强烈痛苦和他们的祈祷词所感动,不得不在他们眼前出现;会看到意象显示使他们明白,他们日后的保护神是谁,他们可以依照该保护神的名字取名,因此得到特殊的能力(权力),并因此而决定他们能享受的权力,决定他们在自己社群中的地位。”[1]35《昆明,西山道上》[8]39作品中,原始部落或传统社会当中人类拥有的权力乃是大自然赋予的,所以神圣自然才是人类的归宿之地。
雷平阳的诗歌在描述云南原初之地时,经常将生态自然放置在 “生” 与 “死” 的循环中来看待 “瞬间” 与 “漫长” 的关系,诗人在人有限的一生中打通万重山、千里海,延长生命的极限,扩容诗歌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通过云南边地特有的宗教器物、景物等具有一定神圣意味的物象、意象,给予自然之 “神” 无处不在的神秘感,流露出对自然之 “神” 的敬畏之心。 这种叩问生死的自然书写,俨然已经成为雷平阳诗集《云南记》和《出云南记》的一部分,这本身就具有一份神圣的意味。 雷平阳的 “云南记忆” 作为诗歌地标镶嵌在诗歌当中,也演化为了云南地方、东方经验乃至人类生命体验的多重探查和传递,这是集地方、传统、文化、经验、生活、自然、心灵、神域为一体的诗歌写作向度, “物我合一” 早就凝缩为诗歌肌理和写作习惯,渗入雷平阳的身体和血液里,所以,魂魄、尘念、轮回、华亭寺、天国、咒念、超度、坟冢才能和小雨、薄雾、松木、风、林间、阳光、月色、牛犊、山河相勾连,进入自然而然、通达澄明的写作境界。
二、面向 “自然” 的 “神性” 寻求
云南的乡间百姓普遍信仰佛教,甚至是每个村寨都会有一座寺庙的点缀。 雷平阳曾在采访中提到,云南的佛教文化塑造了其特有的写作观,慈悲、道德之根、文化底线和天地之正气是其作品的底色,文化中蕴含的现实为诗歌的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这种佛教的渊源与原生自然宗教的淘洗,成为大部分云南人精神的天然皈依之所,这也让雷平阳的诗歌始终偏爱自然的神性和佛教的意旨,并确立了自己 “在寺庙旁写作” 的诗学理念和自然伦理观念,即佛性的慈悲之心、无欲之空、静悟之感,它与自然天地之正气、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相结合,产生了雷平阳经久不衰的创作灵感、诗意想象和自然审美情趣。
向 “自然” 的寻求,向人类初始之地的回溯,这源于人类在原始蒙昧年代当中对自然力的敬畏和神往,所以通向自然天地的大门最终总是向神性敞开,总是寄寓着宗教的想象与情怀。 “梭罗的榆树还见证了社区的历史。 《古兰经》的那段节选最为突出树木的生态意义,但其描绘性却是最弱的。 如果在忠实这方面来认识,一个极简的、表意符号的‘格式塔’已经足够。 那棵树,那匹拉车的阉马,那位郁郁寡欢、流离失所的原住民言说者——无处置身、走投无路的受害者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苦涩的三元组合。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梭罗借用历史典故,不惜笔墨地渲染了他那棵树的神圣品德。”[7]61同样是从 “自然” 到 “神” 的书写路径,雷平阳的生态诗歌,则构建了一条独特的从故乡到诗歌的隐秘栈道:内心的诗性情怀、云南故土、亲人、风土人情交融互渗,别具一番哀愁与凄婉;这份情绪倒映在充满粗粝气质的怒江、湄公河、高原、古寨、寺庙、哀牢山中,又融汇为一种雷平阳特有的博大与气魄,细细品味,似乎是一盏氤氲、绵柔、悠长的云南普洱茶,浸润诗人的孤独、感伤和苍茫。 作品《春风咒》中,作者寄情于 “牢山的荒草” “梨花坞的桃花” “旧城的衰败” ,哀愁与凄婉之情在 “寺庙超度的钟声” 和 “无人哀悼的白骨” 下被骤然放大。
雷平阳的写作是 “送葬” , “送葬” 的目的是 “复活” 。 雷平阳在诗歌中复活了云南的寺庙、牌坊和祖屋,复活了祖先的白骨和灵魂,复活那被历史烟云遮盖、被现代文化浸染的失落文明,记录下它日益沉重、衰败、老去的生命状态,承担了历史追忆者、修复者、重建者的重任,作为诗人的责任和救赎,他用笔像巫师般神秘、诡谲、魔幻地记载了云南的过往,自然生态物像被雷平阳点石化金,赋予了生命灵魂,这些生态诗歌中佛意,苍茫而悲壮。 如《春风咒》中,诗人一方面将佛之情感寄托于山川河流、历史古迹、传说故事、故乡田园,借景抒情;诗人另一方面,通过寻找哀牢山深处、金沙江之畔被现代文明毁于一旦的那座佛教古城,将自己与云南自然生态、历史现实、佛教悲悯有机联结,充满一种旷达、睿智、冷静和忧郁,变奏出了云南古道上一曲苍凉、神奇的自然牧歌。
由于云南地方长期宗教文化的浸润,雷平阳早已形成了维系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思想共同体,宗教信仰便是人们彼此相通的纽带,当然,也是人与自然沟通的一座神性桥梁,蕴藏着传统生态伦理的情怀和极具民族象征性、寓言性的事物。 由于云南自然地理环境和地方文化的影响,使佛性因子在雷平阳的内心落地生根,进而,佛教文化传递出的自然精神和自然感悟,也频频化身于诗作中,使诗歌在强大的宗教文化熏染下,形成了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取向,弥漫着对大自然的歌颂、神往和想象。 “在曼糯山中/ 一块巨石顶上有个小坑/ 布朗人说/ ——它是佛陀留下的脚印/ 我去朝圣。 建在小坑上的金色佛塔/ 在透过密林的阳光里宛如巨石内/ 藏着的圣殿/ 露出了神圣的尖顶……那儿射下来的/ 一束橙光,正好把他照亮/ 真的就像是佛陀/ 那一天正从他头顶路过。” (《照亮》)[9]佛陀的启蒙之光 “照亮” 一片光洁的土地,这是朝圣的人们日夜寻找的灵魂居所,是雷平阳诗中祈求精神家园的永恒呼唤,每一个自然景物的书写和布置,彰显了诗人的虔敬之心和对佛陀的朝拜之感,使生活的褶皱在佛的光照下闪现出了佛性和法度。
“在寺庙旁写作” 的雷平阳不止于 “自然” 与 “佛性” 的表面书写,更有对现实生活中剥离神性光环的 “人” 的挖掘。 现代社会, “人” 是纯粹动物性的营养生命和外在政治生命的结合, “人” 是不得已被驯化成 “人” 的。 按照阿甘本的说法,现代社会就是随时可能被 “赤裸生命化” 的过程,人们需要不断适应 “政治生命” ,否则就面临着 “营养生命” 被剥夺的风险。 现代人的活动,就是犹太人被监禁在集中营中的一种翻版[10]。 人作为主体的存在被放置于社会的例外状态之下,被化约成为生物层面上的存在形式。 因此,为了追求人作为主体性的幸福, “超验” 成为了雷平阳的书写选择。 “裸命” 时代的人都是生活在此时此地,所谓 “超验” 就是跳脱具有表面经验的 “此时此地” ,而是在另一个超越表面经验的领域见证着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 在佛教看来,囿于当下的无超越性是极其痛苦的, “超验” 不仅是追溯主体性的方法论,也是幸福的渊薮,而对 “超验” 的抵达则始于我们探求生命究竟的愿望。
“裸命” 的人类了解生命究竟的渴望总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超验” 恰恰就是对探寻之渴望的解放。 正如雷平阳的佛教观在人类早期对未知世界的探寻上的体现,许多自然图腾巫术、自然力的原始崇拜、神灵永生的祷告、祭祀自然的神秘等因素,形成了诗中人物、族群的集体无意识,这种生态伦理的自然思维方式构成了诗作的 “原始思维” 模式。 因此,雷平阳的长诗也许不会直接出现佛教、寺庙、经幡、香火等意象,但却是以一种更为宽广、深厚的诗史结构,展露出了苍劲、古朴、苦难、追寻、神圣之美——像近期雷平阳长诗的代表作《鲜花寺》,诗中夹杂了原生宗教文化里衍生出的价值理念,天国、鬼国和人间构成了一个交汇场,云集了从不同国度里赶来寻找希望的人、鬼和神,这里人与鬼、生与死、灵魂与超度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阿嫫杳孛现身次日夜,鲜花寺的高僧法莲/在空深阁书写了十个字:‘人老笔椽下,云生砚瓦边’暗中嘱咐弟子:‘从此寺门不开放/我要另创一种时间、钟表和计算单位’/他圆寂的托词解救了众僧,寺门之内/另创之物直奔永恒:诵经法万籁俱寂。”[11]雷平阳的《鲜花寺》将佛与云南大江大河、动物植物、地方文化、民族历史、传奇故事、原始宗教、现代宗教、社会现实等因素相融合,史诗般的叙事中展现了佛、鬼、人、自然的多重叙事空间,将诗歌的诗写表现、意象运用、结构铺展等手法淋淋尽致地展现出来,充满了古朴原始、奇谲诡异的氤氲之气。
三、 “神性” 自然与人性的复归
互联网、科技智能、现代工业日新月益的飞速发展,仿佛让人类进入了更加轻松、快捷、优雅的生活环境之中,但是这种幻象掩盖了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像艾恺对于现代性定义的阐释: “我的定义建立在两个关键性的概念上:‘擅理智’和‘役自然’(即对环境的控制)”[12]现代人确实利用科技进步的设备保护自然、美化自然、欣赏自然,与早期工业时代相比,如今现代智能科技引发的生态问题可能更为隐秘,但人类却无法摆脱发于本能的对自然的控制或占有,科技理性的高度化、智能化甚至有时不自觉地成为我们役使自然的 “帮凶” ,这也最终导致更加广泛的生态危机或生态灾难。 这些现代性陌生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对于科技理性中更为深层内质的发掘,进而从社会文化、思想意识、民族心理等层面,深入思索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
雷平阳生态诗歌的创作不是对自然景致进行单纯白描,也不是片面地批判生态环境破坏后的价值沦丧,而是深入生态危机的深层肌理,深挖其背后隐藏的根性危机和人性因素,其生态诗歌创作的每一步都是直抵读者内心,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中探讨人性的缺憾。 确实,现实文明、科技理性的四处蔓延,使得社会伦理价值和宗教神性的情怀越来越稀薄,取而代之的是感官享受、拜金主义和欲望泛滥,人类不知不觉地沦为毫无精神依靠的 “孤独的人群” ,雷平阳将诗写延伸至离神最新的高地,以神性精神、神性自然治愈现代人久已麻木的内心和痼疾,平复焦躁、不安的心理,从自然天地间找寻一种本然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价值,以及天然且纯净的生态理想。 “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13]“他在山中建了一座小庙/光头,袈裟,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守着/功德箱很大,很沉,晚上/他不用它抵住庙门/酒多的时候,门外松涛虎狼奔突/他就搂着一尊泥菩萨/天人合一,睡得如痴如醉/没有晨钟幕鼓,也无早课和静修” (《建庙记》)[5]76本诗叙事中颇有汪曾祺《受戒》的神韵,一幅饥来便食、困来便眠的天人合一的画面,远离尘世的山中,独自一人的隐居生活正是将生活本身以慢节奏的心态活下来,告别了假意的伪装,卸掉面具,露出了人的真性情,以童真童心去观赏自然、享受自然。
通过反思现代性的危机,雷平阳的诗歌自觉回归到了人生的原初之地,以生态自然的伦理观重新审视我们久已习惯的现代文明和科技文化,可以说,无论是互联网时代中消失的自然神性,还是人类为了一己的物欲涸泽而渔地开发、利用自然,都将为撇开自然关怀而快速发展经济付出的代价。今天,生态文明业已成为显学和国家发展战略,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观成为主流,这也正是诗歌回归自然、重拾自然的契机和责任。 海德格尔曾认为人与自然应当是一种 “诗意栖居” 的朴素关系,但是,随着今天物质欲望的泛滥,人又何曾栖居于自然大地之上。 雷平阳以云南生态诗歌的创作,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答案,即透视复杂的现实,以诗意视角关注自然的写作,通过生态诗歌的创作唤醒人们对于自然的眷恋,让自然生态的灵性之光、神性之思重新点燃麻木的人群。 诗集《云南记》中就对江河单独辟出一卷——《流淌》: “悬崖卷起波浪/天空发出声响/帝王的人马,浮雕于河床上/子嗣绵长啊,自由而哀伤/ /天空露出红色/一种从其底部,逐渐向下/咄咄逼人的红。 白云,薄如蝉翼/覆盖,基于象征,不有盖住/太阳很快出来,天空之王/目空一切,带着热血上路,群山跪伏/江河环绕寺庙,绛黄色的水/是一支和尚的队伍。 天威之下/神性,最先从碧洛雪山/缓缓地袒露,人性则升起于大峡谷/——久违了,多年来,我又一次/看见了太阳出行的仪典,短短五分钟” (《怒江,怒江集》)[8]87。诗人通过地理环境的主观再造过程,将地理景观升华为精神世界的怒江,以诗性的想象和联想,丰富了诗意的多维性和艺术性。 这首组诗中的怒江本身就代表着云南地区沧桑、古朴、苍凉、雄壮的地域文化的写照,蓬勃欲出的红日,薄如蝉翼的白云,巍峨耸立的群山,神性遥远的雪山,这些独特的地理环境已然上升为云南的精神地标。
“近几年,我常常寄身于滇南山中,生活里也发生了一些大事,比如父亲西游。 这就使得我在此期间写下的诗作,总是绕不开山水、密林、寺庙、虫鸣、父亲、墓地、疼痛和敬畏等等一些‘关键词’。 它们像笔尖上活着的灵魂,自然而然,就来到了纸上,温暖或者冰冷。 它们是多了,还是少了? 我没有进行测度,也没用刻意地进行文本意义上的增删,就算是一种常态和生态吧,像安顿自己的亲朋,我淡定而又真诚地,为它们准备了一个个方格子,让其住下来。 虽说一切都在纸上,却也希望纸上有片旷野。”[8]112对于这位滇南山中的古朴诗人,云南的山水、森林、庙宇、墓地都是他笔下的灵魂,生活其中是一种常态和生态,自然天成、自成一体。 可以说,雷平阳是云南文学地图的构建者和想象者,他借助云南的地理风貌,将人的精神情感投射到生态自然的阔达之地,再现了自然的狂野和粗犷,呈现出了自然神性的力量美学。
结 语
自然神性的魅力是自然之力和自然之美结合的产物,人类只有仰望自然,才能顿悟其中孕育的曼妙、宏伟、壮阔和美好,才能弥合人性的裂隙。 雷平阳在《白袍后面的袈裟》一诗中寓言般地刻画了一群庸人,他们毫无信仰可言,迷信自己穿上白袍就能融入自然,被万物接纳,不曾想遭受到的却是暴雪、寒冷、荒野的报复,而只有纯粹自然的真人、至人才能抵达真正的 “自然庙堂” 。 综上所述,自然之道、佛性禅悟和人性之光才是雷平阳冥想、参透出的生态诗学,也是现代人涤净内心、重返大自然的正途:诗人以诗意语言、智性写作构筑了自然的庙堂,走上一条少人问津的小路,这是一段追寻生态自然、生态诗学的朝圣之旅,赋予诗作宗教般的神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