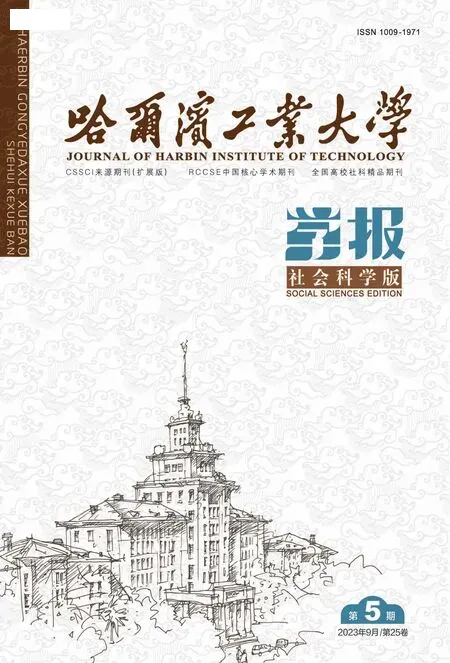论张九龄的文化史意义
2023-03-07马莉娜
杭 勇, 马莉娜
(1.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西安 710100;2.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19)
张九龄是盛唐著名的贤相,开元二十二年兼知集贤院院事,成为继张说之后的政坛兼文坛领袖,为盛唐政治和盛唐诗风的形成,以及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做出极大的贡献,对中国古代文官制的形成、唐诗的演进,特别是岭南地区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深层次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史、唐诗史、岭南地域文化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张九龄的政治史意义:文官政治形成之标志
曹魏推行 “九品中正制” 选官用人,朝政尽被上层贵族把持,政坛形成了 “上品无寒士,下品无世族” 格局。 这种格局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直到唐代全面推行科举制度,科举出身的文官才逐步取代了贵族成为政坛的主导力量,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官政治。 张九龄出身庶族,凭科举官至宰相兼知集贤院院事,成为政坛文士集团的领军人物,打破了李唐王朝建立以来宰相非勋即旧的惯例和魏晋以来贵族政治的传统,标志着中国封建文官政治的初步形成。 同时,他以儒雅刚正的 “九龄风度” 称为后世文官的典范[1]84,他的用人观念也对文官政治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代,在唐代得到全面推广,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建立之初,皇族为了笼络豪强势力,曾短期实行过九品中正制。 不久又废止了九品中正制,改用科举制选官。 但在初唐,科举还不是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每年以科举进入官员队伍的人员大约只有一千多人,且绝大部分担任流外的杂色官吏,没有进入政治核心。 武则天执政后,为排挤李唐王室及其背后 “关陇贵族” 的政治势力,鼎力推行科举选拔新人,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科举出身的文人逐步成为政坛一支重要力量。 这支队伍在中宗、睿宗朝进一步壮大,到玄宗时成为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和贵族出身官员相抗衡的政治力量。
梳理唐代玄宗之前的宰相队伍,可以准确看出朝廷高层官员结构的上述变化过程。 唐高祖朝16 位宰相和唐太宗朝29 位宰相,全出身 “关陇贵族” ,无一人出身科举。 高宗朝47 位宰相,扬武和李敬宗2 人无准确的出身记录,其余45 人均为贵族,绝大多数也是唐朝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功臣;8 人出身科举者亦均为关陇贵族或旧臣。 武则天朝78 名宰相,5 人无准确出身记录,其余67人出身关陇贵族或皇族恩旧;20 名出身科举者仅4 人非贵族。 中宗朝宰相38 人,2 人无详细的出身记录,其余36 人为出身关陇贵族或皇帝的恩旧,15 名科举入仕者均为贵族。 睿宗朝宰相25人,虽有17 人出身科举,但25 人全部为关陇贵族,多人是平定外部叛乱叛或辅助皇帝争夺大位的功臣。 玄宗朝宰相共34 人,截至张九龄担任宰相时共27 人,科举入仕的16 人中除了萧至忠和张九龄出身江南外,其余皆为关陇贵族和王室恩旧,只有张九龄出身庶族①以上数据和材料,根据五代刘昫《旧唐书》的唐高祖、太宗、高宗、则天皇后、中宗、睿宗、玄宗本纪,以及以上七位帝王在位时的历任宰相列传材料统计。。 总体上看,唐朝建立以来以宰相为代表的高层官员一直以 “关陇贵族” 为主,没改变隋朝的 “关中本位” 政策,但科举出身的人数有大幅增加,从睿宗开始,科举出身的宰相已经占到了大多数,代表了这一时期唐朝高层官员出身的基本状况。
唐代选人观念和官员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武则天虽重视科举,但朝廷还没形成重文的用人观念。 狄仁杰是武则时出身科举的名相,他向朝廷推荐张柬之时就说: “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娇、 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 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 “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2]2895表现出轻视文士而重视吏才的用人观。姚崇受狄仁杰提拔,成为武则天的名相,他向武则天推荐的桓彦范、敬晖、张柬之、崔玄暐、袁恕己五人,后成为拥护中宗复辟的五王党并相继担任宰相,也均以吏才见长[3]199。 李峤、苏味道虽以文才获武则天赏识而位居宰相,但武则天只是让两人 “草诏应制,兼修国史,很少让他们直接知政事,荐士用人之权更少沽边”[4]。 基于这种用人观念,武则天时朝廷虽大力推行科举选拔文士,但高层官员队伍的构成并无明显变化。
唐代上层用人观念明显变化始于中宗和睿宗朝,代表人物为上官婉儿和张说。 中宗时, “婉儿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 , “又通于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2]2175张说在《唐故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也说: “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 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5]这时朝廷部分重臣有了重文士的用人观念。 官员选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中宗时科举出身的李峤执掌吏部, “奏置员外官员数千人”[2]2995。 这些官员大多出身科举,虽然他们多为中下层清流,并无实权,但培养了一批后备官员。
玄宗开元年间,科举出身的文官队伍才真正壮大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与贵族出身官员队伍相抗衡的实力。 开元中期,以张说、刘幽求、张九龄为首的文士派和以姚崇、宋璟、李林甫为首的吏治派之间,在官员选拔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科举出身的文士派虽在张说和张九龄为相期间在朝廷的实力有很大的发展,但二人罢相后,以贵族门荫出身和以功勋见用的吏治派又占据了上风。 对此汪篯曾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一文进行过充分论述[3]196-208。 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玚就说: “诸色出身比明经进士多过十倍,胥吏入流数目超过学子甚巨,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不应独独压抑明经进士。”[6]此时宇文融和裴光庭等吏治派执掌相权,科举出身文士官员受到排挤,贵族出身官员又占了绝对的优势。
张九龄是这场争斗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他和张说、刘幽求同属科举出身的文士派,但是身世与二人有很大差异。 张说出身范阳贵族,睿宗朝在处理谯王李重福谋反和评定突厥叛乱及拥立唐玄宗都有一定功劳;刘幽求出身冀州贵族,在诛杀韦皇后、拥立睿宗、诛杀太平公主拥立玄宗的过程中均有不小贡献。 两人出身科举,也是贵族和皇帝的恩旧。 张九龄出身庶族,凭科举入仕,并官至宰相兼知集贤院院事,成为张说之后的政坛兼文坛领袖,是唐建国以来没有门第凭科举官至宰相的第一人,成为开元吏治与文士派争夺中文士派主要代表人物。 张九龄与唐玄宗、李林甫关于朝廷用人的争论充分体现他的用人观念。 《新唐书》载: “李林甫无学术,见九龄文雅,为帝知,内忌之。 会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斩可突干功,帝欲以为侍中。 九龄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玄宗)又将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九龄执曰:‘不可。 尚书,古纳言,唐家多用旧相,不然,历内外贵任,妙有德望者为之。 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谓何?’……帝怒曰:‘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 卿固素有门阅哉?’九龄顿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 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 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 翌日,林甫进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书邪? 九龄文吏,拘古义, 失大体。’ 帝由是决用仙客不疑。”[7]4426这些争论反映出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玄宗和李林甫与张九龄选官用人的观念的差异。 玄宗用人重视门阀和功勋,是李唐王室一贯的非勋即旧的观念。 李林甫用人强调吏才,颇嫉妒张九龄出身文吏的学术才华。 张九龄则用人不看重门阀,重视德望和文才,强调 “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先德望,后劳旧”[7]4427。 这种差别也体现了科举出身的文士与吏才派的差别。 二是这些事件中张九龄表现出的为政风格。 他坚持道义,不畏权贵,明知道忤逆玄宗和得罪权贵李林甫的后果,但为了国家社稷不畏与玄宗和李林甫争执,拒不让步。 这种守道直行、外儒雅内刚强的为政风范,是张九龄学养、人格、器识的外现,也是被历代称道的 “九龄风度” ,成为后世文官的典范。
以上事实昭示了武则天朝以后唐朝在用人观念和官员队伍的变化。 可以说张九龄登上相位,标志着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政治的初步形成,从此文官政治逐步深入人心,文官政治逐步取代了贵族政治,打破了曹魏以来以门第为基础的贵族政治格局,同时他重视文士的用人观念也对文官制度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张九龄出身庶族经由科举登上相位的重要政治文化史意义。 陈寅恪就说: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 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统治之关中本位政策。” “迄之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 “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8]准确指出了唐代实行科举制以来,官员队伍的深刻变化。 宋代全面推行文官政治,外儒内刚的九龄风度亦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有学者就说: “随着门阀贵族的消灭和科举制度的日益成熟,自宋以后,以寒士庶族为主体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九龄风度’获得了宋人特别的关注。” “更重要的是,其出身寒微、科举入仕以及‘九龄风度’,使他颇具象征性地成为此后文人士大夫的典范。”[1]88正体现了张九龄及其风度在文官政治史上的标志和典范意义。
二、张九龄的诗史意义:盛唐气象形成之标志
张九龄对唐诗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开启了盛唐山水诗的创作先河,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唐诗的精神面貌。 他的诗充满对大唐盛世的赞美与自信,以昂扬朗健的情感基调改变了初唐寒士诗歌苍凉悲壮的格调,具有了盛唐诗乐观昂扬的时代精神,是诗史上倍受称道的 “盛唐气象” 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 在张九龄的笔下,唐诗完成了由初唐到盛唐内在精神气质的转变,标志着盛唐诗风的到来。
初唐诗坛台阁诗风盛行,内容空虚。 “四杰” 使唐诗由宫廷走向市井与关山大漠[9],抒发积极的个人理想与功业追求,充实了唐诗的内容。 陈子昂追求恢复诗歌风雅兴寄的传统,追踪慷慨悲壮的汉魏风骨,与片面追求词藻的六朝诗风划清了界限,对唐诗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林庚先生就说: “陈子昂作为盛唐诗坛的先驱,也是盛唐气象和建安风骨之间的桥梁。” “揭开的正是盛唐的序幕。”[10]30但四杰和陈子昂一生身处卑位,经历坎坷,急切的功业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们的诗充满了与建安诗歌相类的悲凉之气,还没有盛唐诗的那种昂扬的情感基调。 盛唐诗从感情的浓烈、壮大这一点,他们与建安是相同的。 但是建安风骨是在感情的壮大和浓烈之中,带有悲凉或悲壮的情调, 而盛唐除个别诗人略带一点悲壮外,却只有壮大明朗,而没有悲凉, “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宏伟气魄和雄厚力” 。[11]陈子昂的诗歌恢复唐诗风骨的功劳确实值得赞誉,但还不具备盛唐诗歌的特点。
张九龄的诗表现了对圣明时代的赞颂和个人前途的自信,这是诗人盛世情怀的自然流露,具有一种自信、明朗、昂扬的格调。 “盛明今在运,吾道竟何陈?” (《商洛山行怀古》)表达了诗人欲在盛明时代、乘运而起有所作为的愿望。 “一木逢厦构,纤尘愿山益” 的强烈功业心,正是源于他对时代和朝廷的信任。 “展力渐浅效,衔恩感深慈。且欲汤火蹈,况无鬼神欺。” (《赠沣阳韦明府》) “感恩身既许,激节胆犹尝。” (《巡按漓水南行》)这种感恩许身、赴汤蹈火的精神,正是开元盛世所激发而产生的积极向上的心态,是诗人对盛世的讴歌,使他的诗有了高昂的基调。 张九龄诗中表现出来的功业追求,与初唐诗人有很大的不同。 初唐诗人多注重个人的富贵显达,他们的诗在表达功业追求时多用富贵、功名等字眼。 而张九龄的诗却表现出强烈的济世济民的道义,超越了单纯的个人功利。 “致君尧舜,不惟比于管乐”[12]644便是这种人生追求的写照。 从军边塞被初唐诗人普遍看作建立个人功业的最佳途径,但在张九龄的诗中却这样写道: “义无中国费,情必远人安。 他日文兼武,而今栗且宽。 自然来月窟,何用刺楼兰。” (《送赵都护赴安西》)这种用道义安定边疆、使国家省去征战耗费的思想,表现出了一种安邦定国的大气。正是这种超越单纯个人功利的高洁人生追求,使张九龄的诗比初唐诗多了一种清高、脱俗、自信的气质。
张九龄诗歌高昂的格调最突出地表现在那些抒写逆境中旷达心态的诗作中,与初唐同类诗形成鲜明的对比,更能反映诗人的主体精神。 张九龄仕途困顿的时候,处境与初唐的四杰、陈子昂等人相似,但诗歌的情感基调却和他们有很大的差别。 四杰的诗大多反映自己怀才不遇、飘零不偶、有时无命的悲叹以及对人生仕途的绝望。 悲、伤、痛、苦、忧、叹、患、惘、惆等字词在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读后往往有一种悲怆的感觉。 张九龄诗中写到的贬谪生活往往为另一种景象。 面对失意,他常常表现出一种 “悠悠天地间,委顺无不乐” (《杂诗五首》)的旷达。 即使身处逆境,张九龄对人生和仕途仍怀有希望,他在贬谪荆州后的诗中写道: “凤凰一朝来,竹花斯可食。” 陈子昂在失意时的诗中却说: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感遇诗》)两首诗都反映了诗人失意时的心态,张九龄诗表达出只要有机会、就可东山再起的自信,而陈子昂诗却流露出无比绝望的心态。 作为盛世宰相的诗人,张九龄诗中表现出的豁达、大度是初唐诗人无法相比的,使唐诗有了一种高昂朗健的格调、乐观向上的气息,表现出盛唐文人才有的情怀。
林庚先生认为, “盛唐气象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性格的艺术形象。” “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是盛唐气象和盛唐之音的本质”[10]34。 它主要来源于在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条件下形成的情绪昂扬、抱负宏大、胸襟开阔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即 “盛唐时代所孕育的人们特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13]。 张九龄诗中表现出来的情怀和格调正是时代精神的诗化,也是张九龄作为盛世宰辅的人格风度在诗中的再现,他的诗基本上具备了盛唐诗的审美特点。 盛唐著名诗论家皎然在《读张曲江诗》中说: “立程正颓靡,绎思何纵横。” “飘然飞动姿,邈矣高简情。” “始欣耳目远,更使机虑清。 体正力已全,理精识何妙。”[14]称赞张九龄在改变初唐诗格调低靡过程中的里程碑意义。 宋代严羽从诗史的角度提出 “张曲江体”[15]的说法,认为张九龄的诗自成一家,代表了唐诗史乃至整个诗史一个重要的阶段。 明代徐献忠也说张九龄的诗 “通于远调,上追汉魏而下开盛唐…… 自余诸子持志高雅,则峭径挺出;游泳时波,则蘼芜莫剪,安能少望其风度哉! 近体诸作,绮密闲淡,复持格力,可谓备其众美。 虽与初唐作者并肩而出,更后诸名家,亦兼丈人行也。”[16]肯定了张九龄诗歌的风骨格力以及其在诗史上的转型意义,并进一步点出了心态的变化和其诗风变化的关系,以及他开启盛唐诗风的贡献,对张九龄在诗史上的作用做了更加明确的阐释。 高步赢先生也说: “唐初犹沿陈隋余习,未能自振。 陈伯玉起而矫之,感遇之作,复见建安、正始之风。 张子寿继之,途轨益辟。”[17]明确地说陈子昂的诗风与建安、正始相似,评张九龄诗 “途轨益辟” ,称赞其有高出陈诗之处。 可见,张九龄使唐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具有划时代的诗学意义。 张九龄是初盛唐之际的诗坛领袖,开元十四年前后他的诗歌创作进入高峰期和成熟期,这正是殷蟠所说的 “颇通远调” 和 “风骨声律始备”[18]的时期,即唐诗由初到盛转型的重要时期。 作为政坛和文坛领袖,唐诗发展转型期的一个关键人物,其诗风的变化就不只是个人风格的问题,对盛唐诗坛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他对唐诗发展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无疑具有巨大诗史意义。 张九龄的诗歌具有了鲜明的盛唐时代精神,反映了盛唐时代气象,是盛唐诗风形成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三、张九龄的岭南地域文化史意义:岭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标杆
张九龄不仅在唐代政治与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他对岭南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岭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唐代之前,受交通的影响,岭南东部的发展明显落后于西部。 秦时灵渠开辟了内地通往岭南的第一条大通道,从洞庭湖溯湘江而上经灵渠连接珠江的西部的支流漓江,极大促进了西江流域的发展。 到了汉代,西江流域成为了岭南人口密集、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19]。 “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和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20]35。 汉代又开辟了第二条内地通往岭南的大通道,这条路溯湘江而上,经湘江支流耒水接珠江的北江西部支流到达珠江的北江流域,促进了北江流域的发展,三国时期, “广州便取代交趾和苍梧成为岭南中心”[20]35。 但是北江以东的岭南地区还比较落后,大部分地方在唐代还是瘴疠弥漫的蛮荒之地。
岭南的全面发展是在张九龄开辟大庾岭道之后,这是张九龄对岭南发展所做出的最突出贡献。大庾岭路开通后,成为了唐以后中国古代内地通往岭南持续发挥作用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陆上交通通道,对北方文化传入岭南、推动岭南地区特别是岭南东部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开凿大庾岭路的目的,张九龄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说得非常明确:一是朝廷的长远目的,加强对偏远岭南地区的统治,即文中所说的 “理内及外,穷幽极远” 。 二是现实目标,改变北方与岭南交通不便,即克服 “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12]608的状况,促进南北的商品交流与经济贸易。 大庾领路由鄱阳湖溯赣水到江西的大余,穿越梅岭到达粤北南雄,沟通了珠江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水系。此后,岭东旧路由 “载则曾不容轨” 变为 “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12]608。 向北连接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东南联通了新兴的经济文化重地江淮地区,被称为古代的京广线,有极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价值, “开创了岭南交通史上的新纪元”[20]37。 大庾岭路开通后,沿途商贸一片繁华: “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责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宋与夫越裳白雉之时,尉佗翠鸟之献,语重九译,数上千双,若斯而已哉!”[12]608唐宋时广州被称为 “金山珠海,天子南库”[21]。 明清时代,梅岭道上仍然一片繁忙, “庚岭,两广往来襟喉,诸夷朝贡,亦于焉取道。 商贾如云,货物如雨[22]。
大庾岭路不仅促进了岭南经济的繁荣,更加强了朝廷对岭南的管理和岭南的全面发展。 唐咸通三年(862 年)交趾兵乱时,朝廷就发兵从大庾岭路前往平叛[23]。 唐末北方战乱、北宋末年金兵入侵中原的时候,大庾岭更是中原人南迁的重要通道。 北方人口的南迁,把内地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文化带到了岭南,到了宋代岭南的发展逐步赶上全国发展水平。 北宋时广东的居民户数是唐代的2.8 倍,粤北的人口密度已非常接近全国的平均人口密度。 随着岭南的发展,唐宋在岭南东部特别是粤北地区密集设立州县地方机构。 唐武德年年间,岭南道东部只有韶、广、循、潮等,而同期岭南道西部有50 多个州[24]60-70。 北宋在岭南东部单独设广南东路,将唐代的四个州重新划分为连、 英、 韶、 南雄、 广、 惠、 循、 梅、 潮等九个州[24]34-35,充分反映了宋朝岭南东部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
张九龄在岭南文化史上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为岭南文学发展确立了榜样,对地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人整理岭南诗文总集,大多以张九龄为始祖。 如清代的《广东文献》《粤东诗海》《岭南风雅》《岭南诗存》等均自张九龄起。 清代黄子高在《粤诗兔逸序》中说: “专于诗者,《岭南五朝诗选》《广东诗粹》《广东诗海》,大抵以广收并蓄,表扬前哲为主。 顾每观各选,俱首曲江,一似曲江以前无诗者。”[25]这样做的目的正如温汝能在《粤东诗海》例言中所言: “所以志景仰之深也。”[26]16这足以说明,岭南地区对张九龄文学贡献的重视与推崇。 明清时,岭南掀起了张九龄诗文集刊印和学习热潮,在岭南流传的张九龄集的版本有明成化九年苏韡韶州刻本、雍正十二年(1734)广东布政使武遂等据张氏裔孙振文所提供的 “家藏善本” 重刻本、乾隆五十七年(1792)温汝适校本等近20 种,这些刻本基本都是岭南文人和地方官员所为,张九龄集在岭南影响到了 “藏家著录,书肆贩鬻,无不有之” 的地步[27]。 清代韶州相江书院教职梁炯编选张九龄诗集单行本使书院诸生 “得以人挟一册听夕讽咏。”[28]岭南诗论家普遍把张九龄推到了岭南诗宗地位,是公认的陶冶一方风气的文学先辈。 徐信符在《温氏校本〈张曲江集〉序》中说 “岭南文家,以张曲江为最古”[29]。 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把张九龄尊为广东诗人鼻祖: “吾粤诗始曲江……千余年以来……作者彬彬,皆谨守曲江规矩。”[30]温汝能《粤东诗海》例言则云: “吾粤如白沙、海目、湛若、一灵、煌傣诸公,皆其(曲江)嫡派。”[26]16罗学鹏也说: “曲江五言古体……如以粤论,则曲江后推白沙,继白沙惟有海目。”[31]岭南诗论家梳理出唐代至清初粤诗大致源流,唐代张九龄开先,明代陈献章、邝露、区大相继之加以发展,清代屈大均、程可则进一步发扬光大,后代诗人均是张九龄的嫡派,可见张九龄在岭南诗史上至高的地位。
基于张九龄对岭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岭南从唐代开始修建庙祠纪念这位伟大的乡贤前哲。 中唐时岭南便有文献公祠庙,据白居易的张仲方《墓志铭》记载: “(仲方)尝撰先行射府君神道碑及垂相文献始兴公庙碑。”[32]宋代以后,岭南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张文献公祠。 据史料记载,张文献公祠韶关有1 处、大庾岭上梅关1处、南雄3 处、乐昌1 处、始兴3 处。 在韶关、南雄、始兴、仁化、梅州、广州、惠州等地还建有张九龄的合祠至少有8 处,大部分建在地方学校和书院之中,作为文庙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宋天禧郡守许申又在曲江县建立风度楼,官府还将风度楼所在街称为风度街[33]。 从宋到清代时各地对上述建筑有过30 多次的大规模的修缮与重建。 宋代开始,韶关张九龄的祠有专人看管,并在每年春秋进行定期的祭祀,对岭南地区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岭南刊印张九龄诗文集、修建张文献公祠堂等活动,普遍有当地官员和民众的广泛参与,体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张九龄的普遍认同,这在岭南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充分体现了张九龄在岭南,特别是广东文化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当时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 韶关张献公祠的门联道出了张九龄在岭南人心目中的历史地位。 明代礼部书丘浚说: “岭海千年第一人,一时功业迥无论。” (《寄题张相祠》)明广东籍邱濬也说: “开元、天宝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显者……由是以观,公非但出岭南,盖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34]177清代诗人杭世骏有诗句 “荒祠一拜张丞相,疏凿真能迈禹功” (《梅岭》),把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与大禹治水的功勋相提并论。 清代霍尚守更说: “四方之学者往来于兹,谒公祠,瞻遗像,志摛藻者仰其文章,事功烈者慕其相业,尚操节者思其风度,安社稷者鉴其先识,以直道见斥者慰其安义,以奸邪被逐者惧其灵耿,仁者淑其利泽,贪夫娩其秽迹。 是祠之建,实所以昭报劝而广风教也。”[34]178通过对乡贤前哲的遵从体认,教化后人,凝聚人心,推动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地域文化建设与成长的一大特点。 梁启超就曾说: “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 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人格及学艺,其鼓舞濬发,往往视逖者更为有力。”[35]岭南民众推重张九龄的心理动因亦当如是。 他们为张九龄 “绘像立祠” 的目的,就是以先贤大德为榜样激励后人,以达到 “扶持正论,兴起人心” 的社会效益[36],把岭南发展的功劳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乡贤张九龄,屈大均引邱濬话说: “自公生后, 五岭以南, 山川烨烨有光气,信哉!”[37]
张九龄开辟大庾岭路,极大地方便了岭南与中原及江淮地区的交通往来,推动了岭南、特别是岭南东部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 同时,以其个人才学、德望、器识以及守道不回的名相风范与气度(九龄风度),为岭南社会树立了崇高而无以伦比的乡贤典范,作为巨大的精神动力驱动着岭南社会文化的发展,深层次促进了岭南地区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步伐,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综合张九龄在古代政治史、唐诗史以及岭南文化史上的意义,他不仅是岭南文化史上的标杆人物,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