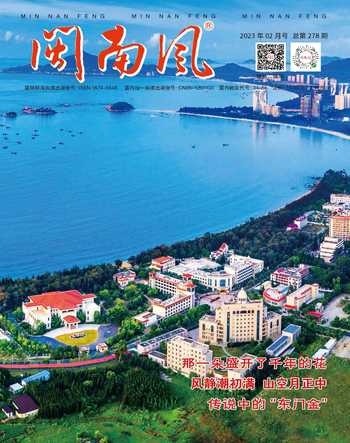寻找平衡
2023-03-03于燕青
于燕青
老舍在小说《离婚》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销,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麻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相片,只许成功,不准失败。”看了忍俊不止,按现今的话说,这位张大哥很现实,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很佩服老舍的神来之笔。现实中,看到有妙龄靓女嫁老翁的,在婚姻的天平上,青春美貌所对峙的另一边要么是金钱,要么是名利地位,筹码相当,达成平衡,仿佛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它物体,而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饮食男女的婚姻就是一种平衡。谁看到博士自愿嫁娶文盲?特定历史环境另当别论。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在学堂上被要求画圣母时却无厘头地画了一架天平,也许在他眼里圣母就是公平公义的化身?我不得而知。平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平、公正、不偷斤减两、不倾斜。反正我就是一个在生命中不断寻找平衡的人。
我跌倒多次。那一年的夏日,我再次跌倒了。我被抬上120救护车的那一刻,肉体难耐的疼痛以及心底的恐慌比车笛更凄厉。我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遭遇不幸,病了几个人或死了几个人,地球照样转,太阳照样升起。那一夜,繁华的街市照样车水马龙,灯照样红酒照样绿,就好像没有灾难发生过。可我的世界已然不同了,我的世界倾斜了。我一再地被問,你怎么又跌倒了?我无以回答,我若有答案我愿意像祥林嫂那样一遍遍地回答他们,可我没有答案。我只能一遍遍地咀嚼这句话。这句话将我引向两个歧途,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是命运的。多数朋友认为我的身体出了毛病,而命运的那条路似乎有更强大的引力,让我想到一些玄奥的,超出以往认知经验的东西。我有限的思维都朝着这个方向倾下去、倾下去,我找不到平衡,我在人生的平衡木上举步维艰。那时我开始脱发,一枕一地的落发纷纷叹息着,叹息我人生的坎坷,不平衡。
那个夏日我在医院的骨科病房住了一段时间,我饱含汁液地绽放成一朵夏日灾花。我从不知道我可以这般肥沃,疼痛在我的身体欢乐筑巢。我也因此结识了很多病友,残弱病痛让我们惺惺相惜,这是怎样的缘分?一对夫妇下坡时摩托车车轮飞了,两人摔成熊猫脸,男的表情凄惨,女的还能笑,虽有些勉强,她叹了一口气,说她去年同样也作了骨科手术。我知道了,她笑是因为她在寻找平衡。另一女子,手指被机器轧断,也是一副坦然的样子,正当钦佩油然升起,并羞愧于自己的脆弱时,那女子忽然一个低头便抽泣起来,我的心也疼了起来,我把面巾纸悄悄塞给她,她惊愕地抬头说了很大声的“谢谢!”吓了我一跳。这是个知道感恩的人。隔壁病房有个要开脑的病人,据说他茫然的眼睛总是看向窗外,大家担忧他的精神要出问题。从病房看出去,窗外,是同一个天空,天空下却是不同的人。每个不幸的人都有各自的不幸,都要经历一段痛苦的心路才能寻找到一种平衡,才能接受现状,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平衡。这里的痛苦刺着我的眼球,这里听不到为赋新诗强说愁。
到了夜晚,月亮似乎总是低悬的、幽暗的、诡异的,不再是“一钩新月天如水”,月亮成了病人苍白枯槁的映照。我特别想回到跌倒之前的日子,可惜生活没有还原键。病房里的电视是打破夜空、打破孤寂的利器,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本市第N届饮食文化节开幕,打广告的人白天已经窜进病房送来街头小报,里面还有医药广告,也有某影星的绯闻等等,某些健康到无聊的人正在弄出极大的动静,这使我们的内心更加不堪。我躺在病床上翻开苏珊·桑塔格的《床上的爱丽斯》,第一幕:暗场。(爱丽斯的卧室)护士的声音:你当然起得来。爱丽斯的声音:我起不来。护士:是不想起。爱丽斯:是起不来。护士:不想起。爱丽斯:起不来。哦。好吧。护士:想起。你想起。爱丽斯:先把灯掌上。
我那时也需要一盏灯,一盏能引领我走人生平衡木的灯,我是个平衡能力很差的人。文森特·梵高也是一个不会走平衡木的人。他渴望找到一家咖啡馆展出他自己的作品,他起初信心满满,可是,在生活的磨难中他也没能把持住,他没有经济来源,他的画得不到世人的认可,感情屡屡受挫,经济又拮据,成为弟弟的负担,他一直在挣扎,他的天平一再失衡,以至于他没能看见整个世界都成了他的咖啡馆。就连我们这个小城也有一处以他命名的地方“梵高小镇”。他的画像和他的《星夜》印在墙上很大幅,他的画有种摄人心魄的美,色彩凌厉的艳,他真的很会配色,他就是一个天才,只是天平失衡了。乔·麦克唐纳说:“伟大往往是各种对立品质自然平衡。” 从梵高的自画像看,虽然他眼神坚定,但整个面部表情依然落魄、狂躁、愤怒、忧郁。才气、自信与颓废、绝望在天平上较量着,天平在双方的筹码中摇摆不定,此起彼伏。他不知道,一旦天才成了天平的一端,另一端可能就是各种苦难,或是无边暗黑的寂寞。天才,稍有不慎就能把人碾得粉身碎骨。他并不具备抵御这一切的能量。尤其高更的离去,仿佛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梵高画了《高更的椅子》,那把有着红漆的老式座椅成了他刺眼的寂寞。那《星夜》整个天空暗黑幽蓝,那些充斥在星月之间的旋涡很暴力,他是在画中释放自己,终于,他没能扛得住,他向着忧郁、愤怒的方向一路狂奔,天平彻底倾斜了。他最后的画《麦田昏鸦》,整个画面线条粗硬,那些黑黢黢的乌鸦仿佛是死亡的预告,梵高最终精神崩溃,自杀身亡。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的苦难也太普通了,甚至,普通得不足挂齿。可是,什么样的苦难,都不能被虚抛、被荒废,苦难应该开出花来,这也是一种平衡。可是我的苦难像干瘪的种子,不能生根发芽开花,我配不上我的苦难。我没有与苦难抗衡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没有任何筹码可以平衡苦难这个大筹码。我是多么的不甘,但我也曾经找到过平衡。那是我被雨后路面上的乳胶漆滑倒之后的事。我躺卧家中。高高翘起的腿,像一杆失去平衡的称。那条腿肿得有两条腿粗,青紫色发亮的皮肤像要涨破,大拇指甲脱落,血迹斑斑。恰逢钟点工来做卫生,她见到我这个样子立马闭上眼不忍目睹,嘴里不住地感叹:“水人没水命!水人没水命!”闽南语“水”就是漂亮的意思。她的话和她为我发出命运不公的叹息,安慰了我,温暖了我,几乎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就像一杆破败的称终于找到了平衡点,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并非我真的自以为“水”,我知道那只是她对我的偏爱。我只是从“水”得到了启示,看到那盘命运的葡萄,不全是青葡萄,也有紫葡萄。我开始数算我生命里的恩典,一个两个三个……我数算不完,我空手来到这个人间,我已经得到很多。况且,苦难也给了我益处。这就是我寻找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