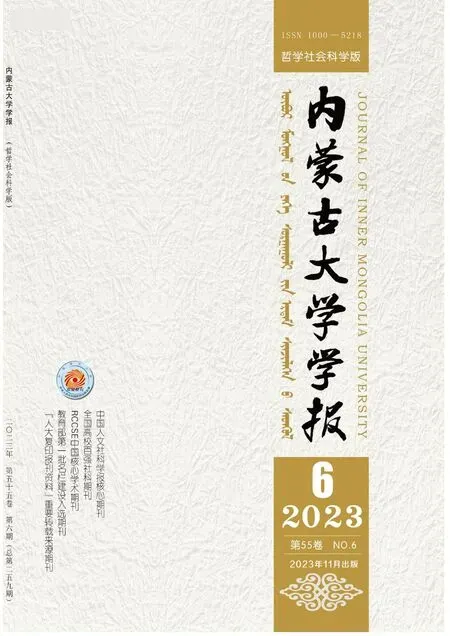作为后形而上学“爱智”追求的前提批判
——以《哲学通论》为中心
2023-03-02盛进洪
盛进洪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从词源学上来看,“哲学”一词在古希腊语文中是由动词philos(爱)和名词sophia(智慧)结合而成的,因此,哲学(philosophia)就是对“智慧”发生爱慕之情并追求不已的“爱智”。①在此之上,张岱年先生又提出,“哲学之进步,系于哲学家爱智之程度。 哲学家们能纯乎爱智,则哲学进;哲学家们不能纯乎爱智,则所言常只是戏论”[1](103-104)。的确,对于任何真正的“进步”哲学来说,它必定是基于实践的、以爱智为心者的“纯乎爱智”的结晶。 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的《哲学通论》(除引用外,以下简称《通论》),就是这样一部纯乎爱智的进步哲学。 从1998 年第一版出版至今,《通论》已历经25 年学术历程和十余个版本更新,在当代中国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影响之所以巨大,原因就在于,它不仅对以往“教科书哲学”所造成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更在哲学“终结”之后创造性地坚守了一种作为后形而上学“爱智”追求的前提批判哲学。
一、摒弃占有智幻想:《通论》的“爱智”前提
从哲学史上看,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在探讨宇宙本原的过程中就已初步形成了“形而上学”思想,如赫拉克利特的“道”、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等。 而求知是人的本性,随着认识的进步,形而上学在希腊鼎盛时期便得到深入发展,如柏拉图以“理念”解释事物的原因,认为事物存在的原因在于分有了“那个实体”。 尤为明显的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更是直接提出了形而上学(即第一哲学),并强调说,它所要考察的是“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和作为实是所应有的诸质性”[2](69),它所要寻求的是事物所依据的“基本”和本体的原理与原因等。 而这些关于事物背后的统一性根据或基本,是哲学家还未认识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问题之前直接断言、“思考这个世界”的结果。 由此,世界被这些原理分裂为“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而中世纪它又被分割为“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
由于上述困境,近代哲学承担起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使命。 无论是经验世界、尘世之城,还是超验世界、上帝之城,在认识这个本体“世界”之前,必须首先“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因为,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是无效的。 而当反思这种认识方式之时,就出现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由此,近代之前的二元矛盾被转化为近代哲学关于“主观世界”(思维)与“客观世界”(存在)的矛盾关系问题。 具体来看,对于唯理论来说,它以“理性”作为认识起点来克服上述问题,如笛卡尔提出从“我思”这个逻辑前提出发,去解释存在、上帝、万物等;而对于经验论来说,它则以“感性经验”作为认识基点来解决上述困境,如休谟从知觉、经验、习惯出发,以怀疑论的精神依次否定了物质实体、心灵实体和上帝的可知性。 根据以上经验论和唯理论,我们可得知,虽然近代哲学明显是在讨论认识论问题,但事实上,它还是在围绕近代以前的,尤其是古代哲学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展开和论证,其实质仍是一种追求统一性原理的形而上学。
而哲学家莫尔顿·怀特等人却提出,黑格尔哲学即为传统形而上学,因为,它把对这种统一性原理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3](7)在“认识论转向”的基础上,黑格尔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并试图凭借思维去克服这种对立。 对此,他把先前对思维把握和解释存在的“全体自由性”追求升华为以概念发展体系来实现作为思存统一的“绝对理念”的自我认识。 对于这种绝对理念,他辩护说,“要这样来理解那个理念,使得多种多样的现实,能被引导到这个作为共相的理念上面,并且通过它而被规定,在这个统一性里面被认识”[4](405)。 由此,孙正聿提出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哲学家主要是以个人头脑中的思辨活动去追求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5](373)。 但“全体自由性”的追求却内含一个矛盾,它与各环节的必然性只有在对各个环节予以区别和规定之后才能成为可能,而黑格尔把它消解在了他批判的纯粹思辨这种“抽象的方式”之中。
同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可直接视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由于对思存关系的解决方式,黑格尔哲学遭到了来自现代哲学的多方攻击和批判,最终被认为传统“哲学已经或应该终结”[6](4)。 对于黑格尔以“绝对理念”的自身运动来论述思存所服从的同一规律这个问题,以赖欣巴哈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对普遍性作超科学认识的“狂妄的理性”,因而这种纯思辨的“假解释”应该被予以“改造”和“治疗”;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也作了类似批判,认为黑格尔的这种“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是无“人”逻辑的“冷酷的理性”,因而它从“人的丰富性”出发,把对黑格尔的批判诉诸对人、人性的哲学反思。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实践的角度也对此作了批判性考察,并提出应“扬弃哲学”②,那种由一个人代替全人类才能完成的哲学应被终结。 黑格尔追求的“全体的自由性”在实践中只能是相对的绝对真理,而把哲学所认识的相对性成果看作对绝对真理的占有的这种幻想、信仰应被摒弃。
然而,有论者认为,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意味着“爱智范式”哲学的终结,由此使哲学开始走出爱智范式而转向现实生活,最终使“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成为辉煌的史诗”[7]。 也有论者提出,马克思的存在论哲学革命,它不仅超越了黑格尔哲学,而且还颠覆、终结了近代的整个柏拉图主义和全部形而上学。[8]对此,我们不禁要问:黑格尔哲学的“终结”,是终结了“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的占有智幻想,还是终结了“以往的全部哲学”所进行着的“爱智”追求? 以往那种占有智有何缺陷? 我们如何看待传统形而上学占有智幻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实践所坚守的作为后形而上学“爱智”追求的前提批判哲学的区别和联系?这些都成为后形而上学之“爱智”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 而基于这种逻辑,就“应运而生”了孙正聿的《通论》。
要说明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实质是否定人的认识的过程性、否定性,如恩格斯对其所批判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观点。 而以这种思维方式看待理论的前提批判和“统一性原理”,必使之变成非批判信仰和终极性真理。 与之相反,马克思则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及以之为基础的认识活动是发展的过程,即,人的认识包括以往的“统一性原理”具有相对性质;而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并向“全体的自由性”前进。[5](230-231)并且,人的认识总是由相对性过渡到绝对性。 这就是后形而上学“爱智”的实质。
本质上讲,黑格尔哲学是以逻辑概念来规定现实世界,因而它是一种迷恋最高主宰和终极真理的思维方式。 而作为逻辑概念世界的统一性原理有如下特点:一是绝对性,二是终极性,三是非历史性。 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思维及特点,孙正聿概括说,“传统哲学的根本特征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寻求‘绝对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把哲学所追求和承诺的‘本体’视为永恒的终极真理”[9](27)。 这种“终极真理”,即为以往那种占有智所追寻和承诺的作为终极确定性的、不可变易的绝对真理或幻想信仰。 具体来说,孙正聿把传统形而上学那种占有智中的“智慧”归结为“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而这些终极真理是没有内在否定性的幻想,它们被占有并用来说明现实世界。 虽然它们也是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根据,但却被绝对化、信仰化了。 因此,随着黑格尔哲学的终结,这种幻想信仰也就此被抛弃。
摒弃传统形而上学占有绝对真理的幻想,是要抛弃把对“全体自由性”追求的相对性成果视为终极真理的信仰。 但后形而上学“爱智”在撇开单个人以“体系的迷宫”获取绝对真理而沿着“实证科学”和“辩证思维”相统一的路径去寻求“相对真理”的同时,仍要追求“全体自由性”这个相对性的绝对目标。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传统本体论占有绝对真理的幻想,但并不拒绝基于人类实践本性和人类思维本性的本体论追求”[5](231)。 人的实践是思维的本质的基础,基于实践之上的人的思维和认识能力,在“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上来说,它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而在“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 上来说,它则是“至上的” 和“无限的”[10](92)。 而要实现人类思维和认识从不至上到至上、从有限到无限这种逻辑层次的跃迁,就必须在实践基础之上对思想再思想、对认识再认识。这种再思想、再认识,是对思想和认识的内在前提进行反思,即“思想的前提批判”。 在此前提批判中,人类追求的“全体自由性”目标,表现为“时代之绝对”和“历史之相对”的辩证智慧。 因此,思想的前提批判,既是摒弃传统形而上学占有智幻想的关键,又是《通论》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往后形而上学“爱智”追求的创新理解。
二、思想的前提批判:《通论》的“爱智”原则
“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个主题,一直是近代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以来所要解决的终极性问题。 康德在其知识论形而上学中认为,在探寻“本体”之前,先要考察人的认知能力,即,先学会了游泳,后才能下水。 对这种“认识论”的考察,开始了形而上学的“前提批判”。 当然,这种批判还只是形而上学的准备性工作。 在康德的基础上,黑格尔以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逻辑学建立起了形而上学体系,这就是直接下水学游泳,从而使“前提批判”回到了形而上学本身。 因而在他的逻辑学形而上学中,相比于认识论,前提批判更具有本体论意义,前提批判即为形而上学。 但是,以他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还存在诸多问题。而正是在反思他的基础上,《通论》创造性地坚守了一种作为后形而上学“爱智”追求的思想的前提批判。
为了探讨前提批判这个原则,孙正聿首先重点阐述了常识、科学、哲学这三种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在他看来,这三种方式是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它们提供了性质不同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因而构成了“客观知识论结构”。 但是,在前提批判之中,这种“结构”包含并超越康德的以主观的直观形式所只能认识事物“现象”(非不可知的“物自体”)的“主观知识论结构”。 在对常识、科学等“经验”的反思中,孙正聿提出,科学和哲学是对常识的超越而非对它的延伸和变形,由此,应当“用哲学去‘化’常识”,并对过去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区分、剥离科学和哲学的对象、职能这种“哲学的知识论立场”[5](89)予以批判。 而在“客观知识论结构”的基础之上,孙正聿还对包括常识和科学的经验作了深入反思,并在反思中确立了思维和存在的思辨统一关系,即,思维与思维所把握到的经验(常识和科学)是统一的。[11]
孙正聿认为,在反思的知识论结构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前提批判的基础和对象。 从这个作为基础和对象的思存“关系”到“反思”再到“前提批判”这三者关联来看,思维对存在的反思,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对象)来思考,而思想的前提批判是超越一般意义的反思思想内容的“哲学反思”。[5](175)把存在作为问题或对象来思考,“关系”才能成为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 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关系”却是一种直接的“统一”。 具体来说,与“一般的思想”相区别,黑格尔主张直接下水游泳,把哲学上的“反思”归结为“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12](39),因此,他在反思之中直接构造了“关系的同一”。 而事实上,在这个反思的规定中,黑格尔只说明了“思想”这个总体对象,并没有解释它的具体对象(即到底是“思想内容”,还是“思想前提”即“关系”)。 对此,孙正聿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把思想这个反思对象规定有“内容”和“前提”两个层次,对思想前提即“关系”的批判才是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因此,应把“关系”纳入前提批判反思。 除了上述反思的知识论结构外,孙正聿还对辩证法理论作了类似的新阐释。 我们知道,辩证法的批判性本质本是黑格尔最具价值的东西,但他却迷恋于对本体的最终追求,因此,批判性被他建构的绝对真理体系所窒息。 对此,孙正聿结合马克思的观点,从实践出发,提出辩证法是对“关系”问题的批判性反思,它是“自否定性的反思方法”,其重要启示就在于,它能对任何的思想前提进行彻底批判,并由此而展现出哲学自身的魅力和力量。[13]
对于“关系”这种思想前提,它其实是思想构成其自己的根据、原则和逻辑支点。 因此,哲学的“爱智”,即为对思想前提的反思。 而作为“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前提,它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等特征,因而对其反思极其艰难、富有挑战。但是,为了思维跃迁和思想解放,揭示其中隐匿着的前提,并解除其原有的逻辑强制,已成为哲学反思之必要。 由于思想前提在思想形成之中所出现的“二重性”(即在思想的特定过程或结论中具有确定性、不可变易性,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和变易性)问题,从而使得思想前提具备“可选择性”。 又因为,思想过程或结果中所隐匿着任何前提都具有“可批判性”,所以,这二者使得哲学反思得以可能。 而恩格斯对思想的前提作了这样的阐述,“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 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0](538)。由此可知,思想的前提既是“幕后的操纵者”,又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 这就出现了“二律背反”的知性认识。 对此,思想的前提批判对二者作了思辨联结,即,作为“本体”的思想前提必然扬弃为认识论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
对思想前提的批判,能使思想的逻辑层次得以跃迁。 在《通论》中,孙正聿对这个原则的阐述,不仅参考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前提批判理论,而且还借鉴了古希腊时期的“爱智”哲学。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以“苏格拉底方法”[4](55)展开了对人们据以形成其伦理概念或一般结论的前提和根据中的“矛盾”的批判,从而揭示出“有知”中的“无知”,并从无知中求索“真知”。 在探讨“美德”“正义”“友谊”“虔敬”“勇敢”等伦理定义时,以“对话”形式从对方所承认的前提出发,引出前提中的矛盾,剥离出普遍原则,最后归纳出一般定义。 由此,孙正聿批判性地认为,“爱智”哲学“内涵着以否定性的思维去反思各种知识和理论的前提,揭示知识和理论的前提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前提”[5](10)。 而在这里,揭示前提中更深层次前提的前提批判,是相对于知性思维而言的。 以知性予以前提批判,必然得出“哲学以自己所承诺的‘统一性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以自己作为‘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哲学解释循环”[5](186)。 对此,孙正聿在《通论》中强调,与这种知性的前提批判循环不同,哲学的前提批判超越了这种“哲学解释循环”,并提出“前提”是自己所确立的“内在前提”,所以,前提批判便是“前提的自我批判”。
更为重要的是,在孙正聿看来,前提的自我批判深深植根于人类生活的历史发展。 也正是这种实践根基,使得作为后形而上学“爱智”追求的前提自我批判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占有智幻想,并展开了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和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精华”。 因此,前提的自我批判首先表现为在实践基础之上对“时代精华”予以自我批判。 而对时代精华的自我批判,是相对于知性思维对其解读所造成的矛盾而言的。 如果以一种知性思维来看,这种时代精华却有着这样的内在矛盾,“从历史的进步性看,每个时代的哲学理念,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类所达到的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最高理解,即该时代人类思想的最高支撑点,因此它具有绝对性;从历史的局限性看,每个时代的哲学理念,又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作为人类思想的最高支撑点,正是表现了人类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所无法挣脱的片面性,因此它具有相对性”[5](186-187)。 由此可知,前提的自我批判对这种知性思维予以批判性反思,并把时代精华的“绝对性”与“相对性”辩证联结了起来,所以,时代精华乃是一种历史之绝对、时代之相对,绝对与相对互为对方环节的批判性哲学理念。
三、哲学修养与创造:《通论》的“爱智”指向
由上可知,《通论》在摒弃传统形而上学占有绝对真理的幻想的同时,又在实践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坚守了一种作为后形而上学“爱智”追求的前提批判哲学。 思想的前提批判,不仅仅是为了对思存关系这个前提予以批判性反思,更是为了把前提批判这种外在的纯粹“学术”阐发转变为内在的人民“学养”和“现代教养”。 这如论者说,“作为‘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的《哲学通论》,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和学理阐发,更是一种哲学学养。 ……哲学在根本上就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哲学的深度就是人修养的厚度,哲学的品格就是人自身的品格。 ……作为《哲学通论》的哲学解释原则的‘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必然要从外在的学术研究和学理阐发转变为内在的学养和品格养成”[14]。 因此,在论证前提批判的学术阐发之外,《通论》还重点阐述了它作为“学养”和“现代教养”这个“爱智”的归宿或指向。
从“学术”到“学养”的转变,是以学术培养人的品格、以真理指导人的行为的过程。 然而,这种转变的前提是,前提批判哲学自身拥有着重要品格。 具体来说:其一,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在批判地考察以往的全部哲学,都在揭露并修正以往哲学所存在的诸种问题或矛盾,从而使前提批判具有一种“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向上的兼容性”。 其二,这种处于各个时代中的前提批判哲学,并不是非现实的玄思和遐想,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思想中的时代”。 因此,它具有与现实密切关联的“时代的容涵性”。 其三,上述前提批判哲学所呈现出的,不管是它的深刻的历史性,还是它的鲜明的现实性,它们都是以逻辑化的概念形式进行更迭、展开的,因此,前提批判哲学又具有一种“理论的系统性”。 其四,哲学理论自身具有反思性、理想性和功能性,因此,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时代之中的哲学还具有一种“思想的开放性”。 总之,由于前提批判哲学自身所具有的上述重要品格,才能够决定着、培养着人的品格、本性和修养。 对此,如同孙正聿所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具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巨大的逻辑感”和“博大的境界感”,通过学习它,能使人增强理论思维能力和提高整体教养水平。[5](430)
思想的前提批判,重在对思想进行怀疑、辩难、训练、研究、探求的过程。 这个过程,能使人真正地形成如同孙正聿所说的“求真态度”“反思取向”“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分析方式”“辩证智慧”等。[15](444)对此,在恩格斯看来,对理论思维这种“与生俱来”的才能或素质的“发展和培养”,必须“学习以往的哲学”或“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也就是说,只有对哲学史有了深入学习和通晓,才能对经典“文本”予以真实的研究和真切的思考,最终形成个人的求真态度;才能对众多“熟知”或“有知”的名词、思想、条文、结论等予以前提批判,揭示这些“无知”中所蕴含的“真知”或“真理”,从而形成个人的反思取向、批判精神、分析思维等。 在前提批判中,应当适时解除旧前提中的逻辑强制,而以新前提作为思想构成其自身的逻辑支点、标准和原则,这才能使思想得以解放、开阔和创新,使“培养创造性的头脑”[5](序)得以可能。 另外,如上述所说,人们以往常以知性思维去看待哲学的前提批判,由此导致他们孤立地看待事物的规定性而形成一种“怀疑主义”。 对此,前提批判哲学超越了知性思维所导致的二律背反困境而达到了对它们的辩证联结,从而使人们形成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智慧。
前提批判哲学不仅是理论反思本身,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对思想进行前提批判,其最终目的就在于培养一种哲学的生活态度,即,“高远的气度、高明的识度和高雅的风度,对宇宙之谜、历史之谜和人生之谜进行永无止境的求索”[5](461)。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它们都在讨论,前提批判这种“爱智”追求可以使人树立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如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哲学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是人“求理想的生活”,使人从“自然境界”提升到“天地境界”等;[15](16)如黑格尔所提出的,“有勇气去追求真理”和“相信精神的力量”等是哲学研究“不可低估和小视的”,“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12](36)等。 而在马克思这里,体现最明显的是,他与恩格斯毕生都致力于“为全人类而工作”这个关于人类解放和自由的“始终如一”的伟大事业和目标,并在“自由人联合体”之中论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相互关系。 当然,这样一些“高远的气度”更呈现为“高明的识度”。 在孙正聿看来,这种识度不仅要具有哲学史背景,还要具有激活知识的能力,以便驰骋自己的想象并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问题。 此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要进行永无止境的“爱智”求索,只有“不畏劳苦的人”才能攀登科学之道和揭示世界的奥秘之所在。 而《通论》中所说的“哲学的修养与创造”,是在求索、攀登“崇高”“理想”的过程中被确立起来的。因此,为学、为人的过程,其道是一致的。
此外,由于20 世纪80 年代前“教科书哲学”的长期通行,使得哲学成为被到处套用的“刻板公式”和“词汇语录”,而其中作为纯粹“学术”,尤其人民“学养”的前提批判更是被否定或被忽略。其原因在于,“教科书哲学”无“人”(或“我”),这是它的“最大的弊端和悲哀”。 对此,孙正聿首先提出要丢弃这种无“我”哲学而恢复创建有“我”的哲学。 哲学有“我”,才会激励人心和征服人心,进而才能恢复哲学的“爱智”精神,并使前提批判从“学术”转向“学养”。 所以,在《通论》出版之前,孙正聿就明确提出,开设这门课程的最大期待就是,要通过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其理论视野、撞击其理论思维和提升其理论境界等重要途径,使之成为高等院校各个专业的“人文教养”课。 因为,现代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不仅要培养掌握各种具体技能的“专才”,而且还要培养更为重要的具有“学养”和“现代教养”的“现代人”。[5](475)“学养”和“现代教养”作为前提批判的社会功能,是由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和境界决定的。 因为,它汇集了人民的最美好的精髓,由此才成为时代精华和“文化的活的灵魂”。
作为“学术”和“学养”这二者相统一的前提批判哲学,有着自己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和重大的哲学史使命。 对于其社会文化意义而言,《通论》恰好满足了大众对“精英文化”的“爱智”诉求,“它既坚持了哲学的尊严,坚持了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崇高典范地位,坚持了哲学对大众常识乃至科学进行反思性前提批判的权利和能力;同时又依据哲学作为‘人民学养’这样一种全新的哲学观理解,以‘学养’和‘现代教养’的方式,把大众文化时代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话语带入哲学反思的层面和境界,实现大众文化与哲学学术的和解”[16]。 而且,这二者的统一更深度摒弃了传统形而上学占有智的幻想,使哲学恢复了其本有的、作为前提批判的“爱智”本性。 比如,在“导言”至尾声中,《通论》一直贯穿着作为“爱智”追求的前提批判这个原则,并在尾声中以“哲学的修养与创造”凝练和升华了前提批判的“爱智”本性。 为此,孙正聿说,跨入新世纪的哲学已经出现了很大改变,尤其认识到了要以“思想”为对象、以“批判”为使命、以“爱智”为本性的哲学定位。[17]在此基础之上,孙正聿还明确地强调:“作为‘学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哲学理念实现为每个人的自觉追求。 这样的哲学‘学养’与当代中国人是最为亲切的,因而也是在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时需要深长思之的。”[18]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前提批判哲学承担着一个意义重大的哲学史使命。
注释:
①根据苗力田先生所制定的“希腊字母与汉语拼音对照表”,“哲学”的希腊语φιλοσοφ α 可被改为philosophia 这个词。 参见苗力田的《亚里士多德论幸福》,载于《哲学译丛》1999 年第2 期,第80 页。
②笔者赞同邓晓芒教授把“消灭哲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之中的“消灭”更译为“扬弃”,从而使扬弃一词照应并意味着“使哲学成为现实”。 它并“不是指从此以后就没有哲学了,而是指哲学意识到了自身固有的实践性,不再是那种与现实生活对立的‘纯粹哲学’(形而上学)了”(邓晓芒《论马克思对哲学的扬弃》,《学术月刊》2003 年第3 期,第27-28 页)。